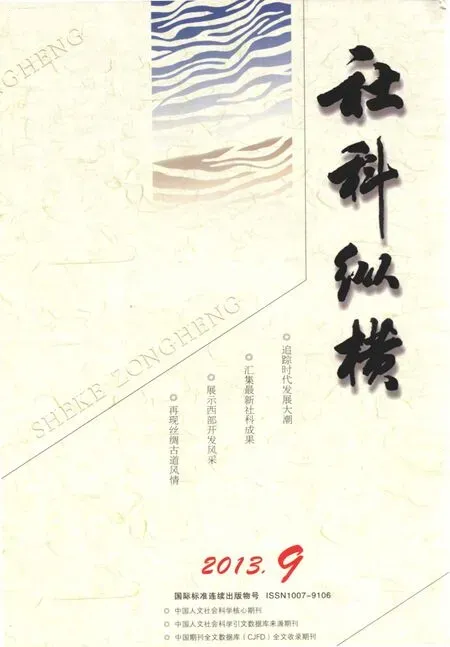进化史观与晚清历史小说
2013-04-11权绘锦
权绘锦
(兰州大学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历史观是不同时代人们关于历史与人的关系、历史的存在形态及发展规律所形成的观念。在历史小说创作中,正是历史观制约着作家对历史的理性认识、情感态度、价值评判和审美表现。历史小说是晚清文学之重镇。对这一时期历史小说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是进化史观。晚清时期的进化史观有其特定语境和特殊内涵,它是在晚清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和变法自强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形成的,其内核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公例”及由此而来的关于历史的一些基本理念。在这一历史观念的指导下,晚清时期出现了三类主旨迥异于传统历史演义的历史小说:其一,部分作家在鲜明的“世界意识”和生存竞争观念指导下,创作了一批取材于外国历史的小说;其二,在现实危机和救亡图存时代风潮的冲击下,《洪秀全演义》等历史小说在宣扬民族革命主张的同时,表现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勾画出了作家心目中理想的现代民族国家蓝图;其三,《孽海花》等作品表现出浓厚的文化归罪意识,对传统文化及其弊病进行了批判和揭露。这些历史小说尽管并不完全成熟,体现着鲜明的过渡性特征,但无疑都是晚清时代特定文化思潮的反映,并成为“五四”文学之先导。
一、晚清外国历史题材小说的兴起
近代以前,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是包含着严明的等级秩序观念的“内夏外夷”的思想模式。中国是自然而然的中心,其他民族统统被称为“四夷”;中华文化理所当然处于优势,扮演着传播文明的恩主的角色,其他文明处于劣势,只能无条件地臣属和学习。这种秩序井然、等级森严的文明观念不仅造成了国人的愚昧无知和盲目自大,也由此使中国在与西方的实力交锋中屡屡败北,形成人类历史和世界范围内古怪离奇的民族悲剧和文化悲剧。
这种民族悲剧和文化悲剧使中国民族的精神心理遭受了巨大创伤,却也使中国人真正开始“睁眼看世界”,逐渐改变“内夏外夷”的思想模式,一种新的“世界意识”开始形成。列文森说:“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1]这一过程虽在明代已开始,但直到晚清才真正显示出其深刻性[2](P447)。在洋枪大炮的轰鸣和割地赔款的屈辱中,中国人才清醒意识到,中国并非世界中心,其他民族国家也并非蛮夷不化的“蕞尔小邦”,其文明成果甚至远超自己。于是,在深入心脾的忧郁愤激、屈辱无奈、紧张焦虑和忧患悲凉中,对本民族文明的自信心和优越感彻底崩溃,革除积弊、变法自强的呼声成为时代最强音。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1896年,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严复的翻译是一种特定时代需要下的有意“误读”。史华兹说:“《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为严复介绍他所理解的斯宾塞的进化哲学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在《天演论》中,他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它所包含的伦理的深深信仰。他清醒地知道这一伦理暗示了在中国将有一场观念的革命,现在他的注意力之所向正是这场革命。而对于严复的许多年轻读者来说,构成《天演论》中心思想的,则显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口号。”[3]严复翻译并有意“误读”《天演论》的目的是为了表达他强烈的“警世”愿望,是为了“使读焉者怵焉知变”[4],是为了于“自强保种之事”[5]有所助益,即为政治和文化变革寻找思想资源和支持。
在这一意义域上接受进化论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取得优胜的民族,必定是在毅力、体力、智慧上更强,更能适应环境的人。梁启超说:“世界以竞争而进化。竞争之极,优者必胜,劣者必败。久而久之,其所谓优者,遂尽占世界之利权;其所谓劣者,遂不能自存于天壤,此天演之公例也。”[6]这不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之间在权利上存在等级分化,还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化图式的基本坐标是“富强”。在这一进化观念构筑的历史图景中,西方恃强凌弱的“强权”与生存发展的“权利”相重叠。“富强”就等于“优胜”,就等于生存和发展;反之,就只配被淘汰。因此,知识分子的任务就不仅是探求列强之所以强盛的原因,还要通过揭示那些与中国有着同样被殖民命运的民族国家历史,向国人提出警示。这样,就出现了两类以外国历史为题材的历史小说著译:一类着意表现列强变法革命、“奋匹夫,建大业,以兵得天下”[7],图自强、求发达、争霸权的历史;另一类主要表现各殖民地国家的历史,作为前车之鉴,以激励爱国热情,强国御侮。
前一类作品包括《罗马史演义》、《十九世纪演义》、《自由钟》、《洪水祸》、《东欧女豪杰》、《亚历山大外传》、《华盛顿外传》、《拿破仑外传》、《俾斯麦外传》、《西乡隆盛外传》等。比如,《自由钟》“即美国独立史演义也。因美人初起义时,于费特费府建一独立阁,上悬大钟,有大事则撞之,以召集国民佥议焉,故取以为名。首叙英人虐政,次叙八年血战,末叙联邦立宪。读之使人爱国自立之念油然而生。”而《洪水祸》“即法国大革命演义也”,“初叙革命前太平歌舞、骄奢满盈之象,及当时官吏贵族之横暴,民间风俗之腐败;次叙革命时代空前绝后之惨剧,使人股栗;而以拿破仑撼天动地之霸业终焉。”[8]
后一类作品以被殖民的印度、缅甸、朝鲜、波兰、越南等国家的历史及其社会各阶层的反应为题材,或赞颂殖民地人民坚苦奋战的斗争精神,或叙述殖民地人民的悲惨生活,或揭露其统治集团的窳败等。这些都有助于国人了解中国当时在世界格局中的弱势地位,激起大众的爱国心和斗志。如许指严的《波臣腥闻》、天谬生的《孤臣碧血记》、“亡国遗民之一”的《多少头颅》等,以别国历史为鉴,抒写亡国奴的悲惨,鞭挞卖国贼的腐败,警示国人自立自强,勿蹈覆辙。《多少头颅》写波兰之亡,以激发国人。正如“作者之友”在序中所说:“作者以小说之笔,写亡国之史,忧愤歌哭,则慷慨无前,嬉笑怒骂,则淋漓尽致。”“设起波兰亡国民于九原之下读之,一睹当时躬受之祸,历历如在目前,当不知若何抚膺痛哭而怨艾不置也。虽然,作者之意岂为已死之波兰作记者,亦深惧夫今日未死之波兰,将转瞬而为昔日已死之波兰也。”“吾四万万同胞国民读是书,而能奋袂以举乎?庶不负天之相我国民,作者之思我国民,已死之波兰福我国民哉。”[9](P389)警世题旨极为明显。
毋庸讳言,这些取材于外国历史的小说译著整体上水平不高,既不能跟传统历史演义相提并论,也没有为现代历史小说提供多少益助,“甚至未纳入‘新小说’的运行轨道。”[9](P395)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在民族危机促发和进化史观的推动下,对外国历史的介绍既扩展了历史小说的表现领域,又在中西对比的语境中为历史小说贯注了浓郁的现实忧患意识;既承担了宣传当时最为先进的思想和知识的职能,又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经世致用精神。这是自迁、固以降的传统历史及演义作品不可能具备的[10]。
二、《洪秀全演义》与进化论的历史图式
进化史观不仅促生了晚清知识分子的“世界意识”,使他们从传统的“天下世界观”转向现代“国家世界观”,并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历史图景和“弱肉强食”的现实危机中体验到对民族命运的深重忧患和强烈悲慨,还使他们获得了一种发展的历史观,把人类历史看做有其自身逻辑的连续整体。人类社会在不断进化、进步和发展,因而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各个民族国家通过自身努力,克服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必将创造未来,并最终置身于独立繁荣的光明领地。这种将人类历史理解为不断上升和发展的有机序列的理念,使历史小说创作发生了根本改观,催生了如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等在思想主旨上完全不同于传统历史演义的新型历史小说。
首先,《洪秀全演义》是一部着意为天平天国翻案的作品。在强调“正僭”之辨的传统观念中,那些崛起底层、揭竿而起的造反者,除少数夺得政权获得“正统”名分外,统统被视为“盗贼”。因此,在《洪秀全演义》出现前后,有一批出自正统文人之手的取材太平天国的作品,如《扫荡粤逆演义》、《曾公平逆记》、《国朝中兴记》、《中兴平捻记》等,从正统观念出发,对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痛加诋毁。黄世仲则按照一个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志士的政治理想,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原型加以改造的基础上,将太平天国起义描绘成了一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将钱江、洪秀全、冯云山、李秀成等塑造成了具有民族民主革命理想的英雄人物。这些起义领袖不仅仅是为了改朝换代,重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专制王朝,也不仅仅是为了“民族大义”而“为种族争”,更是为了“民权公理”而“为国民死”[11](P363),鲜明地揭示出这场起义既具有民族革命又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作品先写道光帝昏庸无道、朝政日非、听信谗言、民不聊生,次写太平天国革命的酝酿,引出洪秀全、钱江、冯云山等领袖人物,以及他们如何分析形势、确定目标、创建组织、发动起义,表明此乃是清政府腐朽统治导致的正义行动。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发布檄文,明确指出,由于“朝上奸臣,甚于盗贼;衙门酷吏,无异豺狼”,以致“上下交征,生民涂炭;富贵者稔恶不究,贫穷者含冤莫伸”,“朝廷恒舞酣歌,粉乱世而作太平之宴;官吏残良害善,讳涂炭而陈人寿之书。萑苻布满江湖,荆棘遍于行路。火热水深,而捐抽不息;天呼地吁,而充耳不闻”,因而才有起而革命之举。由此,堂堂正正道出了起义的革命性质。因为此举代表着人民的意愿,也就受到人民的拥护,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加上钱江、冯云山等的观变沉机,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萧朝贵等的智勇坚毅,以及洪秀全的领袖气质和下层骨干的同心协力,革命烈火迅速燃烧,数年即夺得半壁江山。作家对太平天国及其英雄人物的崇敬不言而喻:他们都是对未来充满热情和向往,满怀希望和幻想的人;是顺应历史潮流而出现,从而创造了历史的人;是致力于为民众建设属于未来理想的“地上天国”的英雄;他们所致力的也并非王朝政权的兴衰更替,而是救民水火、争取民权公理的新型理想社会。这就使小说一方面否定了“治乱分合”循环不已的历史观,将社会历史看成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将历史人物从命定论或因果报应的历史认知与评价系统中解脱出来,承认人才是历史的中心。这相对于传统历史演义对历史人物及其作用的简单化理解,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其次,作者有意把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建设类比于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权,显现其优越和进步于满清政权的种种所在,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勾画了一幅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蓝图:“君臣以兄弟相称,则举国皆同胞,而上下皆平等也;奉教传道,有崇拜宗教之感情;开录女科,有男女平等之体段;遣使通商,有中外交通之思想;行政必行会议,有立宪议院之体裁。此等眼光,固非清国诸臣所及,亦不在欧美诸政治家及外交家之下。”[12]这一现代民族国家理想无疑是从康梁等维新改良派到孙中山等民主革命派共同追求的目标。李泽厚说:“虚君共和也好,民主立宪也好,民主共和也好,这都是外在形式,实质基本一致,都是要求从君主专制和封建官僚统治体系走向适应现代经济基础的民主分权制。因此,也可以说改良派(康、梁、严)与革命派的手段虽有不同,在目标上倒是近似的。”[13]小说中这一题旨的出现无疑体现了进化史观的影响。因为不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权都是他们心目中最理想的社会形态。在康有为的“三世说”中,居于人类社会进化高级阶段的“太平世”,就是现代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14];而孙中山的“民权时代”,也以欧美社会政治形式为重要参照[15]。
为了贯彻这一主旨,作者通过虚构钱江这一诸葛亮式的人物,协同洪秀全制定战略决策和制度建设,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按照钱江设计,建都南京后,“时外人有旅居上海者,见洪秀全政治井井有条,甚为叹服。有美国人到南京谒见秀全,亦见其政治与西国暗合,乃叹道:‘此自有中国以来第一人也’。”洪秀全还派洪仁玕出使美国,向美国总统递交国书。美国也遣使来华,两国共通和好。显然,钱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主张及其实施情况,实际上是作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投射,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现代民族国家景况。他在《自序》中说:“当其定鼎金陵,宣布新国,雅得文明风气之先。君臣则以兄弟平等,男女则以官位平权,凡举国政戎机,去专制独权,必集君臣会议。复除锢闭陋习,首与欧美大国遣使通商,文明灿物,规模大备。视泰西文明政体,又宁多让乎!”[11](P364)
因此,尽管《洪秀全演义》在体式上仍采用历史演义体,在人物塑造和叙事、描写、语言等方面皆未能摆脱传统束缚,但由于进化史观的影响,其在思想主旨上对传统历史观念的背离与突破却不容忽视;当然,由于作家过于借重历史人物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使小说带有理念化色彩。而作家按照自己的意图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所作的大幅度改造,则损害了历史小说应有的艺术魅力,体现出晚清文学特有的过渡性特征。
三、《孽海花》与民族文化归罪意识
晚清知识分子是在天崩地裂、危机四伏中接受进化论的。这一特殊背景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在中西对比中探索摆脱危机出路的自觉。在严复看来,要认识中国文化之不足,仅从其自身出发,无法做到。必须寻找高于自己的文化形态作为参照,才能认识到其缺陷和改造方向。而符合这一条件的就是西方近现代文化[16]。因此,列强既是导致中国危机四伏的海盗,也是引领中国进步的导师。西方文明能够使中国“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17]这样,严复就把进化的普遍必然与中国时势相结合,找准了问题症结和出路,在当时的知识界振聋发聩。
这种中西对比的运思方式使一部分知识分子敏锐地发现,传统的文化模式不再适配,古老的法则不再适用,旧的标准不再适宜。由此,他们开始反思传统,引发强烈的文化归罪意识,将传统文化视为阻碍民族进步和自强保种的消极因素;但相伴而生的文化认同危机却也成为他们无法摆脱的梦魇,因而尴尬地游移于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2](P690)。这种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混杂,使晚清知识分子时时处在理智与感情的矛盾冲突之中:一方面,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近现代文明的优越和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弊病,因而在理智上赞同世界主义,向往和追求西方近现代文明,难以压抑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憎恶与批判;但另一方面,在感情上,又无法彻底斩断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联系,在民族主义驱动下,试图书写中国文化的新形象。《孽海花》正是这样一个生动表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奇特心态的文本。
金松岑的初衷是要写一部揭露帝俄侵略野心的政治小说[18],仅作六回便付与曾朴续作。《孽海花》正式出版时改称“历史小说”。对其写作宗旨,曾朴说:“这书的主干意义,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全景一般。”[19]从而“展示出近代中国方生未死之间的全部历史内容”[20]。
从叙写“政治的变动”看,《孽海花》将中法战争、中俄边界之争、中日甲午战争、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帝后宫廷斗争、强学会建立、兴中会成立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纳入视野。但这些历史事件只是背景,曾朴的主导思想是,想要以金雯青和傅彩云的经历为线索,“避去正面,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21]由此,叙写出“文化的推移”。这也正是其价值所在。
在《孽海花》中,曾朴首先,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科举制度及国民“科名崇拜”的病态心理,嘲讽了一批科举制度塑造的所谓社会精英。通过这些人物,曾朴揭示了在传统文化面临挑战的“五洲万国交通时代”,这些固守在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根本无法支撑大厦将倾的危局,他们的失败表征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没落的遭遇。曾朴对士大夫文人或轻浮狂躁徒做大言,或顽固保守昏聩无能,或怯于公仇勇于私愤,或毫无操持、不学无术、浪得虚名的弊病看得相当清楚,清醒地认识到,正是由于朝政把持在这些科举制度造就的怪胎废物手中,才使得民族积重难返、病入膏肓,因而揭示了晚清危机的总根源。
其次,曾朴也试图以平等开放的眼光大胆描摹和想象西方,以达到沟通中西、掌控历史变迁大动脉的目的。鲁迅曾说:“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来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和我们一样的。”[22]鸦片战争以来,国人总是在“精神文明第一”的虚幻想象中获得心理满足,同时将西方妖魔化了。这种病态心理及历史认知和道德评价上的偏颇是曾朴纠正的对象,他通过讲述夏雅丽等洋人的经历和命运,表明西方也有成熟合理的伦理道德,也有为了民族国家不惜牺牲性命的英雄,也有亲情、爱情、友情等,体现了他在进化论影响下的世界主义眼光以及为本民族文化改造寻找的理想参照。
最后,曾朴也试图通过虚设的西方人眼光,重塑中国形象。既然传统文化在其批判性审视中一无是处,既然以金雯青为代表的士大夫官僚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只能成为受害者,那么,中国自身的形象应当怎样?国人应如何与西方交往?曾朴通过傅彩云这一形象试图作出回答。
在“五洲万国交通时代”,通晓外语以“周知四国、通达时务”是精英分子的标志。但这在雯青眼中只与“洋戏法”等值。于是,彩云这个风月场上的“花魁”凭借机缘努力,获取了通行证,成为唯一能被西方接纳的中国人。“蕊宫榜首”代替了“金殿大魁”,妓女颠覆了士大夫的价值系统。这不仅再次表现了作者对科举制度和传统文化的讽刺与批判,也在将雯青之流置于被遮蔽境况的同时,使彩云的形象得以凸现。当雯青整日闭门谢客,考证《元史》时,彩云却大放异彩。在他们出使德国等待晋见的一个多月里,“偌大一个柏林城,几乎没个不知道傅彩云是中国第一个美人,都要见识见识,连铁血宰相的郁亨夫人,也来往过好几次”。郁亨夫人又介绍她认识了一位自称维亚太太的贵妇,两人一见,非常投契。而维亚太太就是德国皇后,她们的亲密交谊传为佳话。
雯青作为帝国使臣,理应是国体民风之代言。但这个向西方展示中国形象的机遇却被一个放诞冶艳的青楼女子代替,并被作为中国形象而在西方人眼里永远定格。德国皇后与彩云在皇宫会面时说的话,典型代表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维亚太太笑道:‘不瞒密细斯说,我平生有个癖见,以为天地间最可宝贵的是两种人物,都是有龙跳虎踞的精神、颠倒乾坤的手段,你道是什么呢?就是权诈的英雄和放诞的美人,……如今密西斯又美丽,又风流,真当得起‘放诞美人’四字。”“美人”与“英雄”都可“颠倒乾坤”,这是德国皇后赐予彩云的最高赞誉,也使她成为西方人眼中中国的象征。显然,在这个强势的德国皇后眼中,强盛的德国是充满阳刚之气的男性英雄,中国只能沦为女性的放诞美人。彩云在西方世界如花绽放,未必真因为她的魅力,而是因为她是西方人眼中可感的东方奇观,是这个古老而又神秘的文明的象征符号,她的魅力更多来自不明真相的西方人对东方的主观想象。而彩云与雯青的角色互换又进一步强化了其牢固性。
将中国乃至东方文明想象为放诞美人,主动呈现在以男性英雄自居的西方面前,若站在西方立场看,合乎殖民主义逻辑。萨义德揭示了东西方关系中被忽略的性别指向:欧洲19世纪文学对整个东方的想象是冶艳、瑰丽、充满性的诱惑的。东方国家被无一例外地与性期许、感官刺激与无止境的欲望相联系,“‘东方的性’像大众文化中的商品一样被标准化了”[23]。周蕾也分析了中国在西方话语中的性别位置:“中国虽然‘从根本上’是不同的,却只可以算是一个‘女性’,这个女性的物质性/肉体成为受压抑的标志”[24]。这就是说,在殖民主义话语中,作为被殖民对象的中国被女体化,体现了殖民者的强横霸道、猎奇心理和民族歧视及其历史必然。但问题是,曾朴如此书写的文化心理和动机是什么?曾朴有爱国热情,不乏对西方的了解,也感同身受过民族苦难和现实危机,他为什么要将这个放诞美人傅彩云书写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揣测曾朴如此书写中国形象是有意迎合殖民者的猎奇心理,显然是诬枉;认为曾朴因遵循史实而如此书写,也不符合实际[25]。那么,可能的解释还要归结到进化论上来。在曾朴看来,中国曾引以为傲的道德伦理恰恰是民族生命力衰退的根源。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现实中,只有鸢飞鱼跃的亢奋激情、永不餍足的欲望追逐和不择手段的狡诈机智才能生机蓬勃。彩云的美貌慧黠、善于逢迎、精力无穷、恣肆浪荡、伶牙俐齿正是她获取生存、快乐和独立的唯一资本,也正是作者所认定的进化论精神的绝妙体现,更是国人应该师法的对象。就在彩云之外,曾朴还讲述了夏雅丽和日本女间谍花子的故事。前者以身事仇,完成了组织任务;后者借美色诱惑,在甲午海战前获得绝密情报,保证了日本大获全胜。于是,女性个人因突破了道德桎梏,既成就了个人事业,也保证了国家强盛。夏雅丽是彩云的导师,花子是她的补充。曾朴正是以她们为参照,塑造了彩云,并将其所蕴含的精神特质看作他想象中的未来中国人必备的素质。也许曾朴试图传达这样一种奇特讯息:在天崩地解的时代动荡和文化裂变中,在列强环视、危机四伏的现实环境里,现代民族及其国民,只有打破传统道德束缚,以恶抗恶,才能实现与西方的对等交流,进而加入强者行列。这也恰好印证了黑格尔著名的历史论断:“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26]
[1]列文森,郑大华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87.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3]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叶凤美译.严复与西方[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101.
[4]天演论.吴汝纶序[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2.
[5]严复.〈天演论〉自序[M].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1321.
[6]梁启超.论商业会议所之益[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二册)中华书局,1941:10.
[7]几道,别士,陈平原,夏晓虹编.本馆附印说部缘起[A].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1.
[8]陈平原,夏晓虹编.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A].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60.
[9]欧阳健.历史小说史[M].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
[10]沈惟贤,陈平原,夏晓虹编.〈万国演义〉序[A].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05.
[11]黄小配,陈平原,夏晓虹编.〈洪秀全演义〉自序[A].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2]黄小配,陈平原,夏晓虹编.〈洪秀全演义〉例言[M].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66.
[13]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M].(中)第655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14]王杰秀.康有为进化论思想的两重性[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2).
[15]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1讲[M].孙中山文粹(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810.
[16]严复.泰晤士·万国通史序[M].严复集(第二册)[C].中华书局,1986:270.
[17]严复.国闻报·缘起[A].严复集(第二册)[C].中华书局1986:455.
[18]参见1904年.爱白由者撰译书广告[M].孽海花资料,魏绍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34.
[19]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M].孽海花资料,魏绍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29.
[20]时萌.曾朴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30.
[21]曾朴,魏绍昌编.曾朴谈《孽海花》[A].孽海花资料[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28—129.
[22]鲁迅.随感录·四十八[A].鲁迅全集(第一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36.
[23]爱德华·W·萨义德,王宇根译.东方学[M].三联书店,1999:246.
[24]周蕾,张京媛主编.看现代中国[M].如何建立一个种族观众的理论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24—325.
[25]参见陈子平.《孽海花》:在历史与小说之间[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
[26]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C].人民出版社,1972: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