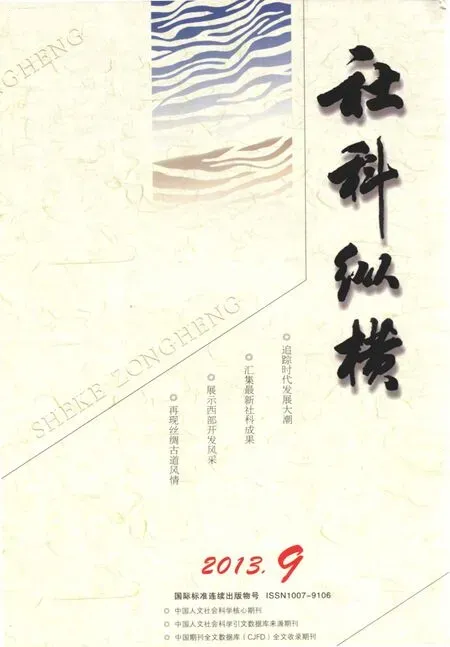反思性判断力视域中的实践智慧
2013-04-11李永刚
李永刚
(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荆州 434023)
“实践智慧”(phronesis)①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当代实践哲学的复兴浪潮中,伽达默尔更是将其作为整个哲学解释学体系的核心,甚至说:“我的全部哲学就是实践智慧”[1](P54)。与亚里士多德仅仅将“实践智慧”限于实践生活领域,而在实践生活之上还有理论生活、沉思的生活相比,伽达默尔无疑大大提升了“实践智慧”的重要性,使其在所有关于人的学问,即精神科学中居于核心地位。伽达默尔为什么能够实现这一转变?其原因就在于他将康德的反思性判断力引入实践智慧之中,在一般与个别、普遍原则与特殊处境之间关系的理解上拓展了实践智慧的内涵。
一、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
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善的理念的空疏性的基础上,以“属人的善”取代了“善的理念”。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善不是先天的,不是由“回忆”而获得的,是通过习惯和教导而发生的,是通过对其运用而获得的。这里的“习惯”和“教导”对应着人的两种不同德性,即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这是亚里士多德以灵魂与德性的对应关系为根据做出的划分。他把灵魂区分为无逻各斯的部分和有逻各斯的部分,有逻各斯的部分,即理智部分,是灵魂进行思考的部分;无逻各斯的部分又被区分为植物性的部分和欲望的部分,前者,如造成营养和生长的部分,是动植物都普遍具有的,与逻各斯毫无关系,而后者则是受逻各斯影响的,“在像听从父亲那样听从逻各斯的意义上分有逻各斯”[2](P1103a3-4)。如此,灵魂在严格意义上具有逻各斯的部分所对应的德性就是理智德性,它主要是通过教导而形成的;在分有意义上具有逻各斯的灵魂部分所对应的德性是道德德性,它由习惯养成。
人的善或德性是通过对德性的运用,是通过人的受逻各斯指导的实践活动而实现的。德性作为一种好的品质以相对于我们自身的“适度”为准则,这里的“适度”并不是数学意义上的“中间”,比如,对于一个人而言,10磅的食物太多,2磅的食物又太少,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中间”的6磅食物就是对他而言的“适度”,因为这要取决于此人自身的饭量。这就是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奉行的“适度”原则是相对的、可变的、不精确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我们的确应该谴责偏离“适度”的人,但“至于一个人偏离得多远、多严重就应当受到谴责,这很难依照逻各斯来确定。这正如对于感觉的题材很难确定一样。这些事情取决于具体情状,而我们对它们的判断取决于对它们的感觉。”[2](P1109b20-24)但这并不是说,“适度”原则就如同每个人的感觉那样千差万别,这是所说的“感觉”乃是一种共同体所普遍奉行的“意见”,一种对生活的善的考虑的可错的意见。
人的行为的“适度”是由实践的逻各斯规定的,而具有实践逻各斯的人也就是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因为“正确的逻各斯也就是按照实践智慧而说出来的逻各斯。……德性不仅仅是合乎正确的逻各斯的,而且是与后者一起发挥作用的品质。在这些事务上,实践智慧就是正确的逻各斯。”[2](P1144b24-29)因此,道德德性与实践智慧紧密相联:一方面,道德德性的获得必须以实践智慧,即实践的逻各斯为指导,离开实践智慧就不可能有道德德性;另一方面,实践智慧也必须体现在各种道德德性之中,如勇敢、节制、友爱等。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离开了实践智慧就没有严格意义的善,离开了道德德性也不可能有实践智慧。”[2](P1144b31-32)
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肯定和否定真的方式有五种,即技艺、科学、实践智慧、智慧和努斯。其中,科学与智慧是“知识”部分的理智,它们思考的是始因不变的事物,技艺和实践智慧是推理(考虑)部分的理智,它们思考的是可变事物,而努斯作为一种“理智直觉”仅关注于对“始点”的思考。从这种区分可以看出,与其说实践智慧更靠近于科学,不如说它更类似于技艺,但它与技艺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一,实践活动与制作活动的始因,即目的不同,制作活动本身并不是目的,仅只是实现某一外在目的的手段,但实践智慧本身既是手段又是目的,而且实践智慧作为“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2](P1140b6-7),更为根本地就是目的;第二,技艺虽然需要经验的积累,但作为一种知识,是可以学习,也可以遗忘的,而实践智慧与此不同,它通过教导而发生,通过把道德原则运用于具体处境而真正成为有道德的,因此,“具有理解(亚里士多德把“理解”看作是实践智慧的三种基本因素之一,但有时也把理解与实践智慧并列为理智德性——引者注)的人并不是无动于衷地站在对面去认识和判断,而是从一种特殊的使他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隶属关系去一起思考,好像他与那人休戚相关。”[3](P458)第三,技艺和实践智慧都涉及到把普遍原则应用于具体处境的问题,但技艺的应用是制作者把技艺应用于被制作者,而实践智慧的“应用”本质上是把道德知识应用于自身,它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知识。综上,我们可以总结说:“实践智慧,其中包含有伦理知识,既不是那种本身即是目的的纯粹的、理论的知识,又不是那种把其自身作为手段而以应用自身于其他事物为目的的技术知识。相反,它是应用于自身的知识,自我知识。因此,手段与目的是合一的。”[4](P189)
亚里士多德虽然强调了实践智慧的价值,但从其整个哲学体系来看,实践智慧只同人类事务相关,即只是实践活动的德性,但还存在着远比人优越事物,如宇宙天体。“智慧”,作为科学和努斯的结合,它一方面“沉思”永恒不变的事物,另一方面又探究它们的始点,因而智慧以这些最高等的事物作为沉思的对象。我们说像泰勒斯这样的人有智慧,而不说他们有实践智慧,是因为“这样的人对他们自己的利益全不知晓,而他们知晓的都是一些罕见的、重大的、困难的、超乎常人想象而又没有实际用处的事情,因为他们并不追求对人有益的事务。”[2](P1141b5-9)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智慧是最高的理智德性。
二、实践智慧与反思性判断力
伽达默尔重新恢复了解释学的“应用”维度,使哲学解释学成为了理解、解释与应用的三位一体。所谓“解释学的应用”就是在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把某种普遍的东西,即具有自身同一性的历史流传物和文本,应用于理解者自身具体的历史处境之中,或者说,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理解历史流传物和文本。因此,“应用”就涉及到了一般与特殊、普遍原则与具体处境的关系。如何理解二者的关系,或者说,如何实现应用,这既是实践智慧的问题,又是一个关于判断力的问题。
判断力与实践智慧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点:第一,二者都是无法通过学习而获得的,因为同实践智慧一样,并没有指导如何做出正确判断的规则,“所以判断力一般来说是不能学到的,它只能从具体事情上去训练,而且在这一点上,它更是一种类似感觉的能力。”[3](P50)第二,判断力同样与“善”相关,“谁具有一个健全的判断,他就不能以普遍的观点去评判特殊事物,而是知道真正关键的东西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以正确的、合理的、健全的观点去观看事物。”[3](P52)如果不与善相关,有些人就可能利用这种算计能力去做坏事,如骗子虽然具有超强的“计算”能力,并经常为了行骗而做“正确的”事,但他不具有健全的、即善良的判断力,这就如同“聪明”如果不与善相关就可能成为“狡猾”一样。
康德把判断力看作是一种联接想象力与知性的能力,其有两种形式:“一般判断力是把特殊思考为包含在普遍之下的能力。如果普遍的东西(规则、原则、规律)被给予了,那么把特殊归摄于它们之下的那个判断力(即使它作为先验的判断力先天地指定了惟有依此才能归摄到那个普遍之下的那些条件)就是规定性的。但如果只有特殊被给予了,判断力必须为此去寻求普遍,那么这种判断力就只是反思性的。”[5](P13—14)判断力涉及到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规定性判断力是在普遍、一般被给予的条件下,把特殊、个别归摄于其下的能力,而反思性判断力是特殊、个别被给予的条件下,为其寻求普遍、一般的能力。实践智慧、解释学的应用与这两种判断力都相关,但从根本上说,反思性判断力更能体现实践智慧、解释学应用的“创造性”。
就传统理解而言,判断力就是规定性意义上的判断力,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也多半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的,因为实践智慧涉及到人在具体处境中如何选择善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把共同体所奉行的道德原则贯彻于个人的实际生活之中的问题。同时,解释学的应用也更多地意指把普遍的原则应用于具体处境之中,“理解乃是把某种普遍东西应用于某个个别具体情况的特殊事例。”[3](P441)这样的理解并没有错,但它容易导致把“应用”看作是在理解、解释之后的一个附属的、可有可无的成分这种观点,就像古典解释学所理解的那样,这就没有真正在实践智慧、解释学应用的基础上理解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在反思性判断力的意义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即“个别”不再被动地接受“一般”,而是主动地寻求符合自身的“一般”,而且扩充着“一般”:“正如实践智慧的分析所显示的,一般不能事先被理解,对个别的应用也不是随后的,因为不但个别隶属于一般,而且一般也隶属于个别。因此,一般不是可以在先认识、在先给予的共相,因为它是被个别持续地规定的,即使它也规定个别。应用不是多余的,而是创造,特别是它并不是单方面的。”[4]](P192)这种反思性判断力意义上的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表明,实践智慧与解释学应用并不是仅仅把“一般”应用于“个别”,而且“个别”也扩充着“一般”。亚里士多德在分析了“公正”这种德性之后,又提出了作为对法律公正的一种纠正的“公道”的德性,因为制定的法律作为一般规则相对于具体的案情来说,总是不完善的,总是需要补充和修正的,因此,法官在“应用”法律进行审判的时候总是需要具有实践智慧,他在一些情况下松懈法律的严厉性,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加强法律的严厉性,这是根据具体案情的需要而做出的改变,但这并没有超出法律允许的界限,“并没有降低法律的声誉,而是相反地发现了更好的法律”。[3](P450)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公道本身就是一种公正,而且是为了更加公正。
同样,解释学的应用并不是附属于理解和解释之后的一个偶然成分,即把理解和解释所获得的普遍东西简单地应用于具体处境之中,因为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应用,或者说,应用“从一开始就整个地规定了理解活动”。[3](P459)但与自然科学意义上规则的应用不同,这种应用并不是客观的、与应用者无涉的,相反,“研讨某个传承物的解释者就是试图把这种传承物应用于自身。”[3](P459)因为传承物并不是立于我们对面的客观的事物,等待着我们去理解,而是它本身就构成了我们理解得以可能的传统、“前见”,正是在对传承物的理解中,我们获得了关于我们自身的知识,即“自我知识”。这种意义上的应用不仅扩充了普遍的对象,即文本的意义,而且扩展了对我们自身的理解,这就是精神科学理解,或者说解释学应用的独特之处。
反思性判断力为我们理解实践智慧和解释学应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反思性判断力的意义上,我们更为正确地理解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并将其与人类自身整体的善相关联,从而把握了整个哲学解释学,或者说整个精神科学的特质。因而,反思性判断力视域中的实践智慧成为了整个精神科学的核心。
三、实践智慧与人文主义主导概念
精神科学的探究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性的探究,它无法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因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本身是抽象的和本质上非历史的,因此,“为了比现代科学的认识概念更好地对理解宇宙加以理解,它必须对它所使用的概念找寻一种新的关系。这种思考必将意识到,它自身的理解和解释绝不是一种依据于原则而来的构想,而是远久流传下来的事件的继续塑造。因此这种思考不会全盘照收其所使用的概念,而是收取从其概念的原始意义内涵中所传承给它的东西。”[3](P7)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对于人文主义传统来说,伽达默尔提出了四个主导概念,或者说,精神科学的四个基本要素,即教化、共同感、判断力和趣味。我们可以根据上面已经分析过的反思性判断力意义上的实践智慧对它们加以理解,从而表明实践智慧在整个精神科学中的核心地位。
“教化”被认为是18世纪最伟大的概念,并表现了19世纪精神科学赖以存在的要素。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教化的具体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但教化作为一个真正历史性的概念体现了精神的一种历史性运动,即异化与复归的循环运动,“在异己的东西里认识自身、在异己的东西里感到是在自己的家,这就是精神的基本运动,这种精神的存在只是从他物出发向自己本身的返回。”[3](P26)这种循环运动就是精神向普遍性提升的过程,而且是无止境的,“精神总是永远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它作为一种不断地向更完全地是其所是的运动而存在。”[4](P71)这种“永远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的精神运动本质地体现了反思性判断力意义上的实践智慧所理解的一般与个别的辩证运动,因为个别或具体处境并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一般或普遍原则的指导,而且通过这种“应用”扩展和完善了对一般或普遍原则的理解,使其更成其为一般。而且,这种“一般”并不是与我们的存在无涉的客观的一般原则,而是从共同体所处的具体处境中提升起来的“一般”,也就是共同体成员所生存于其中历史传统,它一方面指导着共同体成员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又在这种指导中不断地在新的历史处境中被改变、被重新理解,这并不是历史传统的消除过程,而是其不断完善的历史进程。无论是教化,还是实践智慧或解释学的应用,都是人类精神本身的一种向着自身不断完善化的历史运动,如此,精神科学的理解就是一种历史性的理解。
“共通感”,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共同的感觉,但它与我们的嗅觉、味觉等通常意义上的感觉完全不同,因为它并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在人的具体实践活动中造就的,它对于人类生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它对于整个精神科学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精神科学的对象、人的道德的和历史的存在,正如它们在人的行为和活动中所表现的,本身就是被共通感所根本规定的。”[3](P38)共通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它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它是具体的,因为它是在共同体的具体处境和历史传统之中被造就的;其次,它又具有普遍性,因为它能够指导个体在具体的处境中做出恰当的决定,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具有实践智慧的人,“经验使他们生出了慧眼,使他们能看得正确。”[2](P1143b14-15)最后,它具有强烈的道德—政治色彩,它既是对人与人交往中好的品质的感觉,又是对共同体而言共同的善的感觉,这种“感觉”未必是完全正确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意见”一样,但却是人类行为的普遍原则。这种意义上的共通感就如同实践智慧一样,不仅调解着人与人、人与共同体的关系,而且是人追求“真”的方式之一,这种“真”虽然这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真理,但却是对于人的历史处境而言的正确意义上的“真理”,也就是精神科学所追求的真理。
“趣味”(Geschmack,亦译作“鉴赏”)是人的一种认知方式和辨别能力,它虽具有巨大的个体差异性,但同样具有普遍性,而且是一种理想的普遍性,“人的趣味并不认为每一个人会或将会赞成他的判断,相反,它认为理想的共同体会赞成他的判断。”[4](P77)也就是说,这种普遍性是一种“应当”,即具有好的趣味的人都应做出这样的判断。但好的趣味仅是一个形式标准,因为并没有判断什么样的趣味就是好的趣味的普遍标准,且趣味本身更多地关涉于个体,或者说,好的趣味的形成在于为具体处境寻求理想的普遍性,因此,“趣味应归入这样一种认识领域,在这领域内是以反思判断力的方式从个体去把握该个体可以归于其下的一般性。”[3](P60)正是趣味的这种反思性判断力的特性使其具有了高度的创造性,因为不管是法律还是道德的普遍原则都是通过其具体化,通过其实践性的应用而得到补充和完善的,这也正是反思性判断力意义上的实践智慧或解释学应用的特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教化、共通感和趣味不仅是我们的认识方式,而且是我们自身的存在方式,并且正是在与反思性判断力意义上的实践智慧的关联中彰显出它们作为我们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的意义。因而,我们可以反思性判断力意义上的实践智慧来统领这些人文主义的主导概念,使其在实践智慧的基础上突破康德美学所给予的狭隘化,展现其原始的丰富意蕴。
四、作为实践智慧特例的“艺术真理”
“真理”是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一书的主导性概念。哲学解释学的主旨就是要探究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由于“理解”与“真理”的密切关联,此问题本质上就是奠基于存在论基础上的“真理”何以可能的问题。解释学的真理,或精神科学的真理并不是由自然科学的“方法”保证的,“不是方法的掌握,而是解释学的想象力才是富于创造性的精神科学家的标志!”[6](P10)而这种“解释学的想象力”就是对于问题的“敏感”,它并不取决于方法,而是取决于伽达默尔所说的“实践智慧”。
伽达默尔对解释学真理的探究是从艺术经验开始的,这是一条“捷径”,因为艺术经验如此明显地超出“艺术科学”的控制范围,通过艺术作品所经验到的真理是用任何科学方法所无法获得的。那么,如何本真地把握艺术经验,如何赢获艺术真理呢?伽达默尔通过对审美意识的批判而开始了这一探究。
在伽达默尔看来,“审美意识”是一个近代概念,是笛卡尔把所有的知识都奠基于主体的自我确定性之上的结果。在审美意识主观化的过程中,康德的审美判断力批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认为“美”并不是客观的认识对象或某种属性,而只是对事物表象的一种主观评价,是对事物的一种情感和态度。由此,康德确立了审美意识的自主性,强调了美学的主体化倾向。这样,作为美的表象的艺术是与现实相对立的,而审美意识的教化就是要放弃审美个别性而上升到普遍性。审美意识的普遍性就在于撇开艺术作品的非审美性要素,如目的、作用、内容意义等,而专注于使艺术作品真正成为艺术作品的东西,也就是艺术作品的“形式”或质的规定性。因而,审美意识活动乃是一种抽象的区分:一方面,艺术作品与其原本所属的世界,即其原始的生命关系相区分;另一方面,艺术作品与艺术家的精神和生命相区分,艺术作品并非仅仅是艺术家的精神客观化物,更重要的在于其脱离艺术家的精神和生命而独立存在。正是通过这一双重区分,艺术作品抛弃了其自身的历史性和处境性,获得了一种形式的普遍性,从而成为了“纯粹的”艺术作品,但这也就抽象掉了我们用于理解一部作品的所有条件,失去了其自身的真理性。
为了理解一部作品,就必须反对任何审美区分,而承认“审美无区分”,也就是承认教化、共同感、判断力和趣味这些为康德美学所极大地狭隘化了人文主义主导概念的丰富意蕴,从而克服康德美学所导致的主观化倾向,超越“审美意识”。但这一对审美意识的批判和超越并不意味着拒绝康德美学,因为康德美学在阻碍我们承认艺术真理的同时也开启了通往艺术真理之源泉的通道,因此,伽达默尔不是拒绝,而是要倾听比康德所说的更多的东西,“这种在美学中所能找到的‘更多的东西’是一种知识样式和真理源泉,它们使精神科学成为科学。”[4](P79)这种在艺术中的“更多的东西”就是我们超出审美区分所能经验到的东西,即与艺术作品的遭遇、照面,而艺术作品本身也并不是完成了的、封闭的,而是未完成的,即需要理解者的理解与解释,并且这一理解与解释本身就构成着艺术作品,因而,艺术作品并不是立于主体对面,供主体审美和认知的对象,对艺术作品的经验也并不为主体所拥有,或可用科学方法论加以控制,相反,艺术经验,即艺术真理“不是隶属于主体的对象,而是主体所隶属的某物,主体不能控制的某物。这个某物是事件,真理事件,我们赢获它是因为我们属于它。”[4](P100)
这种关于艺术作品的“真理事件”体现在艺术游戏之中。在近代美学,特别是在主体化的审美理论中,“游戏”被看作是主体的一种享受性的态度和行为,被看作是主体性的自由活动,但伽达默尔将其从与审美理论的关联中解放了出来,将其与人的存在相关联。这种奠基于人类生存,而非人类的审美体验的“游戏”就是人类经验艺术作品的方式,也就是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因为我们对艺术作品的经验就是与艺术作品的遭遇、照面,而这种方式就是一种游戏,反过来,艺术作品本身也就是在这种遭遇、照面,即“游戏”中存在着。
作为艺术作品存在方式的游戏,其主体并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游戏并不附属于游戏者,而是有其自身的存在,有其自身的“精神”,这种精神并不是由游戏者所赋予的,而是由构成游戏本质的“规则和秩序”所决定的,而游戏的实现和进行就是这种“规则和秩序”的展开,因而,游戏的存在方式就是其“规则和秩序”的展开,反过来,游戏的“规则和秩序”的展开就是游戏的进行,所以说,游戏的存在方式就是游戏本身的自我表现。这里涉及到游戏本身与游戏的自我表现的辩证关系:游戏的规则和秩序具有权威性和规范性,因为它们规定了游戏的每一次自我表现;同时,游戏的自我表现在实现游戏本身意义的同时,也扩展了游戏的意义,实现了游戏的“在的扩充”。以观赏游戏,如戏剧为例,参与者根据原型,即剧本而展开每一次的演出,但每一次的演出由于其处境的差异,在实现剧本原型的同时又加入了一些处境性的因素,这些处境性因素并不是审美体验中需要被排除的偶然因素,它们也参与着戏剧游戏的实现,而且是同一戏剧游戏的实现。因此,“一部艺术作品是如此紧密地与它所关联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以致这部艺术作品如同通过一个新的存在事件而丰富了其所关联的东西的存在。”[3](P215)这就是说,游戏或艺术作品的自我表现、再现并不是柏拉图所说的“摹本的摹本”,游戏与艺术作品本身就体现在这种再现之中。
作为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的“游戏”彻底超越了主客二分的审美意识,理解到了艺术经验中的“更多的东西”并不是需要排除的历史性、处境性的东西,相反,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艺术作品的每一次“自我表现”,实现了艺术作品的“在的扩充”,而这就是超出科学方法论控制的对真理的经验,因此,超越审美意识的艺术经验就是艺术的真理。这种艺术真理鲜明地体现了反思性判断力意义上实践智慧关于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艺术作品作为一种具有自身意义的统一体,并不是审美区分意义上的“纯粹艺术”,它必然要在历史性、处境性的理解与解释中获得其存在;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历史性、处境性的理解与解释丰富了艺术作品本身的意蕴,使其真正成为历史性的艺术作品。在解释学中,艺术作品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种文本,如此,艺术作品的理解乃是文本理解的典范,艺术真理也就成为了精神科学真理的典范,所以,整个精神科学的真理也就体现在这种反思性判断力意义上的实践智慧之中。
五、结语
亚里士多德以“实践智慧”为实践的逻各斯,用来指导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但它并不是最高的德性,因为实践生活是服从于理论生活或沉思生活的。伽达默尔在当代实践哲学的复兴浪潮中,把实践智慧与康德所说的判断力相联系,在肯定对实践智慧的规定性判断力意义上的传统理解的基础上,强调了在反思性判断力基础上对实践智慧的理解,也就是强调了历史性、处境性的个别对一般原则的补充和丰富。这种补充和丰富正是哲学解释学所说的在文本的理解与解释中所获得的“更多的东西”,也就是精神科学意义上的“真理”。反思性判断力意义上的实践智慧统领了传统人文主义的主导概念,并成为了精神科学真理的源泉和典范,因此,我们可以说,反思性判断力意义上的实践智慧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最核心的概念,甚至可以说,伽达默尔的整个哲学解释学就可以归结为反思性判断力意义上的实践智慧。
注释:
①“phronesis”也译作“明智”,廖申白所译的《尼各马可伦理学》、苗力田等所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皆译作“明智”,为了突出与“智慧”的对照,并便于与伽达默尔的论述相衔接,本文采用了“实践智慧”这一译名。为了行文的方便,笔者对中译文凡译作“明智”的一律改译为“实践智慧”。
[1]A Century of Philosophy:Hans-Georg Gadamer in Conversation with Riccardo Dottori,translated by Rod Coltman with Sigrid Koepke,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roup Inc,2006.
[2]亚里士多德.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伽达默尔.洪汉鼎译.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Joel C.Weinsheimer,Gadamer’s Hermeneutics:A Reading of Truth and Method,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5]康德,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判断力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伽达默尔,杜特.金惠敏译.解释学 美学 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