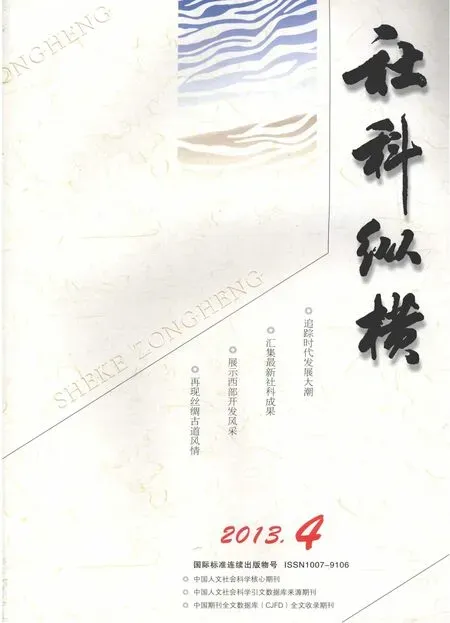以理服人辨析
2013-04-10马丽
马 丽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广东 珠海 519085)
我国不同国民教育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学校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基本方式。它们的教学效果直接关系着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学生中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教育是一种以理服人的价值教育,背离了这个基本的教育理念,就容易成为没有根本和缺乏内容的形式说教,无法抵及受教育者的心灵世界。但是,以理服人的真正内涵是什么,需要深入厘清。
一、以理服人的教育隐忧
笔者在给大学一年级新生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休息间隙与同学交流时,不少新生讲述了他们在中学上思想政治课的一些情况。尽管笔者曾经历过与他们类似的教育历程,深知升学率对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挤压,但是,他们与笔者聊天时所表现的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情绪和态度,促使笔者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与107位新生,从2011年9月20日到12月26日,展开了深入交流。这些同学高中时代选读的是文科或者高考时选考的是政治科目。
在105位(98.13%)学生眼中,思想政治教育只是宣传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工具。“中学所受思想政治教育,无非是爱党爱祖国。‘政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统治阶级为进行阶级统治所使用的种种手段。‘思想政治’便可以说是,或者基本上是,对学生进行‘教化’的工具。总的来说,中小学所受思想政治教育无论出发点是什么,采取的手段是死板甚至可以说是引人反感的。”(HJ)有7位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和发展人的功能并没有体现出来。“至于思想道德的学习,关于做人的学问,我在课堂上没有取得太大的进步。我们只是重复地记忆,真正去做的人很少。所以,这就还真只是一门‘课’。”(WJW)
103位(96.26%)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没有好感。这包括对教育者教学能力的评价不高,“上课老师很少能讲出课本知识的真正内涵、更高层次的内涵。”(CLY)除此以外,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课被学生想象为教化官方意识形态的课程,而教师就成为党宣传意识形态的工具,因此,这种角色想象也成为学生降低对教师评价的重要原因。“上这些课的老师大部分可以被称为老古董。要不拿着无聊得课本照本宣科,要不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粉丝,把一大堆马哲理论和党史搬出来对我们进行洗脑。”(CZH)“在我经历的政治课中,政治老师方佛都是一些特正经的人物,会一直按书中所说的宣扬共产党的好,仿佛就是党派来的代言人。所以一直不怎么喜欢学校的政治课。”(KSQ)
104位(97.20%)同学认为,他们现在并不认同中学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所传导的内容。“当时总是习惯把老师的话奉为圭臬,总是很虔诚地很‘革命’地去奉行各种条条框框,真的是以‘马列主义毛邓思想共产党理论’为荣。而现在看来,当时思想教育的内容未免太理想太革命,与当下的现状相比不由得觉得可笑。”(CXY)甚至有学生极端地自我价值否定。“小的时候上思想教育课,看到赖宁救火、雷锋奉献,心里心潮澎湃,常感动得热泪盈眶。但现在有种被骗的感觉。”(QSY)
101位(94.39%)学生认为,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应试,课堂教学的内容主要是应考知识灌输和应试技巧讲解,使得思想政治课成为枯燥乏味的理论课程。“对于大学之前的政治课的感受,一是枯燥,二是官方。老师们更着重的是解题技巧与如何得分。”(KSQ)应考知识由考试大纲规定,应试技巧也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路径遵循。因此,学生回答思想政治问题的程序基本类似流水线上生产工人的体力活。他们只需要根据不同的题目内容和类型,以相关的知识点熟练地填充到对应的答题摸板中。它无形当中压抑了学生的想象力。“大题的答案都是有组织的。每个人对同一问题都是同一看法,不能有别的想法。”(HPY)“政治课上老师多按教学方案授课。总是一个大课题,底下分列许多小标题,从某一概念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讲起,课堂上外拓是有,但比较少,几乎全是贴着课本讲,并且要我们背许多的内容。作业的题型灵活而相对单一,回答、分析每一种现象都大部分搬课本原理,‘活学活用’。”(CLY)
107位(100%)学生反映,中学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标准,主要是要求学生考试中能够以储存的知识有效地回答试题,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对这些知识的阐发和运用不被看重。“中学时代的政治课,大多是照本宣科,老师把课本的内容念一遍,做些讲解,画出考试的重点,再让我们背得滚瓜烂熟,足以应付答卷即可。”(XJY)“高中的政治课就是讲四本书,很无趣。我觉得我们学到的更多是如何利用这些理论在考试中获得最高的分数。我们都只是很枯燥地背考点、背理论,没有把这些知识结合到我们的生活中去。”(CYQ)这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脱节,学生也不会产生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改造主客观生活世界的观念,而是将之仅仅视为一门跨入更高一级教育阶段的必考科目。考试结束后,这些知识也基本被遗忘了。
即便是理论知识的灌输,也可以有多种形式。在98位(91.59%)学生看来,中学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方式比较单一,基本上是教育者围绕考试要求的“填鸭”式教学和学生死记硬背的合体。“老师从上课说到下课,黑板上写得满满的(全是抄课本上的要点),是老师的独台戏。下面的同学也不用回答问题,气氛特闷。许多同学甚至不听,写别科的作业。到后来有时老师就不讲了,直接告诉我们哪里要背,之后就不停地背。中学的政治课给我最大的印象是不停地背,无法摆脱无法背完的试卷、课本。”(ZYQ)“说真的,高中的政治变成了薄薄的四本书,世界仿佛向我们关了门,我们只能看书中的风景。国内外发生的大事被老师一笔带过。”(KSQ)学生要通过强行背诵理论知识的“死去”过程,以换取考试回答题目时得心应手的“活来”结果。
可见,这种尴尬的教育困境之所以出现,除了社会因素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学时代的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因为教育使其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引导生命成长的价值性,仅仅因为它是考试和升学的工具。这种思维方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说理的教育,而是无理的应试教育;不是关怀人和贴近人的教育,而是远离人和抛弃人的教育。既然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价值性没有被透彻地阐释出来,学生只是似懂非懂地记忆应考知识,那么,只要他们顺利进入高等院校而摆脱考试的压力,就会抛弃此前的思想政治教育而去选择自认为是真理的其它思想流派。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必须重新深入开掘以理服人在马克思主义教育中的当代价值。
二、以理服人的语义分析
在汉语中,语词的理解是非常复杂而有趣的语言学现象。一词多义或者多词一义无论是对域外人还是域内人,都时常构成文本解释的障碍。马克思主义教育中的“以理服人”是比较典型的例证。一般意义上,“以理服人”的经典注解,是马克思的论断:“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根据马克思的这段论述,理论只要具有真理性,就可以为群众所接受和悦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对“以理服人”最直接的表达。但是,这种表述不仅没有充分开掘马克思的本意,而且歪曲了“以理服人”的本质内涵。若要完整而准确地再现“以理服人”的真谛,就必须通过语词分析的分式,在明晰每个字所隐含的教育理念的基础上,整体性阐发其孕育的教育精神。
“以”之“因”与“用”。汉语中的“以”因为语境的差异,或是连词,或是助词,或是介词,具有不同的含义。“以学校为荣”中的“以”指代的是“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中的“以”等同于“用”。在“以理服人”中,“以”同时兼具“因”和“用”的含义。它既是“因理服人”,又是“用理服人”。但是,相同的“人”在前后表述中指称的是不同的客体或者对象或者宾语。受教育者为教育者所传播的“理”说服,这是“因理服人”。“人”是指教育者。但是,受教育者“服”教育者的唯一而内在原因,不是师道尊严的习俗或者其它功利性考量,而是“理”。教育者的身份或者地位,无论帝王抑或平民,在产生说服受教育者的教育效果中,没有参考意义。“用理服人”是从教育者的角度立论,指教育者用“理”说服了受教育者,既不是以力服人,又不是以德服人。因而,此处的“人”指受教育者。尽管从所产生的“服人”效果来看,“因理服人”和“用理服人”具有同一性,但是,它们分别有着重要的教育价值分歧。在“因理服人”中,“理”具有至上性、神圣性和崇高性,是教育者真正“服”的对象,它自身就具有目的性;但在“用理服人”中,教育者仍处于中心或者支配地位,“理”成为他“服人”的便捷手段。“理”的手段性角色暗示着,它可以因教育情势的变迁而被废弃或者被置换,由“用力服人”或者“用权威服人”取而代之。
“人”之“需要”与“意志”。人兼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论点。人的自然属性使其与其它生物保持着紧密而内在的勾连,例如必须首先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和生理需要,换言之,必须满足生存需要。但是,人与其它生物的根本区别在于,生存需要既是其它生物的底线,又是其目标,同时成为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因此,对于其它生物而言,它们是存在于世或生存于世。但是,人不仅要努力图谋生存,更要反思生存得更好的方式。他追求的是一种美好生活。这种反思性使得人渴望精神需要的满足,从而在本质上区别于其它生物,呈现出人丰富的社会属性。回应人的精神需求成为一切教育共同的追求。其它生物服从生命本能的内在冲动以实现生存需要的满足,人却有着更深刻的自由意志。它不仅规范和指引着人的生存需要和精神需要,平衡着彼此间的冲突与协调,而且会因生存需要或精神需要的变化而改变。自由意志使人对其“所为”、“所是”或“所去”保持着深切的自我反思,对其“所当为”、“所应是”或“所当去”有着理性的自我觉醒,由此成为外在的价值或者观念进入主体自我的“过滤器”。无论是自我反思或者自我觉醒,其终极的有效标准在于主体需要的实现。因此,通过教育的途径,直接改变主体的自由意志尤为艰难;而使教育经由关注或者满足人的需要的方式,间接引导主体的自由意志更加现实。
“理”之“真理”与“说理”。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愿望和要求。它必须由年长一代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地把人们积累的有关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的经验、知识和技能,系统地有步骤地传授给年轻一代。”[2]因此,只有教育内容具有真理上的价值,才具有传授的意义。这也是“以理服人”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理”缺乏真理的普遍性和有效性,那么教育者即使全身心投入,也难以产生长久而持续“服人”的教育效果。教育就成为名副其实的“说教”。“说教”有两层含义:对于教育者而言,只是说一说而已,从不指望受教育者践行;对于受教育者而言,只是听一听罢了,从未想过以之指导社会实践。但是,如果教育者缺乏“说理”的技巧,未能充分阐述教育内容的真理性价值,那么,它也难以获得受教育者的认同或者悦纳,不能产生“服人”的教育效果。“说理”不是“强词夺理”。“强词夺理”的本质仍是不讲理,要么所依据之“理”不是真理,要么“强夺”方式本身失“理”。“说理”要求言说者不仅要清晰地阐发理论内在而严谨的逻辑体系,体现理论的自洽性;尤其要结合听说者的需要,揭示其有效性。因此,为了“服人”,教育内容不能毫不讲理,教育者也不能有理说不请。
“服”之“说服”与“服务”。教育有效性的直接目的是受教育者接受了教育内容。因此,“以理服人”的基本含义是受教育者认同了作为教育内容的“理”。“服”首要而基本的内涵是“说服”。它区别于“制服”或“压服”。“说服”的教育场景想象是,教育者以讲理的方式呈现教育内容的真理性,而受教育者是否接受教育内容,选择权在受教育者。而“制服”或者“压服”尽管为了取得“服”的效果,有时也重视讲理和真理,但是,如果受教育者仍不认同,那么,就采取压制的手段,使教育者被迫表面上认同。“以力服人”或者“以权服人”实现的是“制服”或“压服”。“说服”也不同于“恩服”。“恩服”的动机是对方的恩情或者德行,它是依据感情行事。因此,感恩或者慕德有时会毫不讲理。“以德服人”是典型的表现形式。“服”除了“说服”外,还有“服务”的意思。因此,“以理服人”不仅是以“理”“说服”人,而且这“理”必须“服务”人的需要。“理”的“服务”内涵不能仅仅从工具论角度去理解,而是必须同时将之视为“理”的本性、特质或者目的性追求。重视“理”的“服务”本色使得“以理服人”类似于“以利服人”。但是,“理”真实合法普遍有效,而“利”可以虚构、伪造或欺骗。因此,“以理服人”要统摄“理”对人的“说服”和“服务”。
“以理服人”经过逐字的语言学分析后,就可以提炼出一种整体性的概括。在教育中,真理通过说理的方式,发挥服务人的需要的功能,引导人的自由意志,产生说服人的教育效果。这就是“以理服人”的本质定义。它不仅强调内容的真理性和传授方式的说理式,更关注理论及其呈现方式对人的需要的满足,从而使教育的真理性表达和价值性追求统一。它的主语是“真理”,从而不仅淡化了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主导性和支配性,而且凸显了真理的至上性,不仅传达了教育主客体之间平等的德性价值,而且彰显了真理在教育事业中的神圣性和崇高性。“说理的方式”和“引导人的自由意志”内在地屏弃了说教、压服、恩服等方式,突出了教育主客体之间自由而民主的德性前提。真理服务人的前提是了解人和发现人,因此,“发挥服务人的需要的功能”隐含了教育对人的理解的德性立场。在满足这些德性要求后,“以理服人”就能产生“说服人的教育效果”。“以理服人”不仅是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更是德性精神和德性追求。
社会价值形态的多样化发展凸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艰难,也彰显了以理服人教育理念的当代意义。官方虽然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尊崇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并在各级学校课程设置中表明其重要地位,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经由教育的途径,通过以理服人,取得更大的理论优势,那么,教育主客体仅仅是出于功利的算计而被迫接受马克思主义知识,无法从内心深处体察马克思主义崇高的真理性和厚重的价值性。因此,当马克思主义经由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证实为真理后,教育者要通过说理的方式,结合受教育者的需求,呈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实现以理“说服人”的教育效果和以理“服务人”的教育理想。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2]王天一等编著.外国教育史.修订本(上册)[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