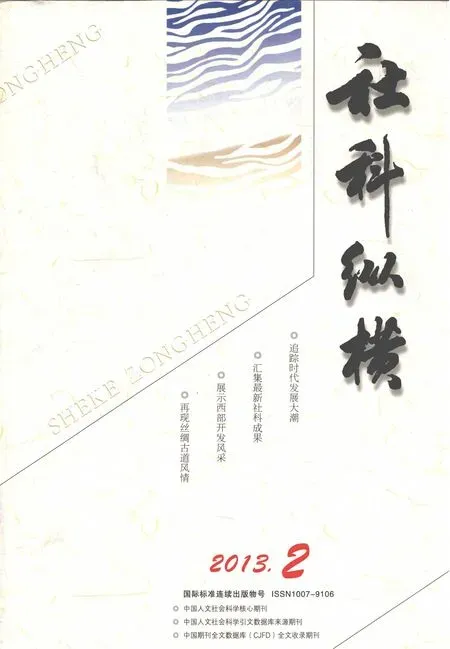草原承包制度的困境及改革路径
2013-04-10代琴
代 琴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100088)
引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度,广大农民获得利益。与此同时,我国北方草原牧区也开始进行牲畜承包,集体所有的牲畜分配到牧户,实行“草场公有、户有户养”制度,极大的刺激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因为草场是公有的,牧民无限制地利用公有草场,导致草原压力增加,草原严重退化。当时,普遍认为草场退化是因为草原产权不明晰,牲畜吃“大锅饭”,牧民掠夺性地利用草原导致的,因而发生了“公地悲剧”。上世纪80年代末,草原牧区开始实行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将草场分配到牧户。但是情况并没有好转,本世纪初草原环境进一步恶化,严重程度引起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关注。此后,草原的问题开始进入国家的视野,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治理退化草原,进一步推进草原承包制度,采取禁牧、休牧,草畜平衡,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列措施。但是,草原退化的现象并没有得到遏制,反而使牧民的负担增加、返贫程度加大。目前主流观点仍认为牧民超载过牧是导致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但是,当我们换个角度思考问题时发现,我国草原承包制度是简单地引进农业生产经营观念和模式,忽略草原原有的自然特征及人文文化,改变千百年来草原生产生活中自发形成的草原利用方式造成草原的退化。
一、内蒙古地区土地制度的变迁与草原利用方式的改变
内蒙古地区的土地产权制度的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古代蒙古时期,清朝民国时期,人民公社化时期和草原承包时期。在这四个阶段,草原的使用范围依次减少,古代蒙古时期游牧单位是“爱马克”(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清朝统治时期,游牧单位以旗(县)为界限[1]。解放后,我国牧区经过社会主义初级合作社及人民公社化时期,游牧的单位变为大队,改革开放后,草原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将草场分配到户,牧民开始定居,在承包的草原上进行“定牧”生产。草原承包到户后,草原的生产单位“原子化”,牧户在承包经营草场上进行小范围的放牧,放牧的方式也从游牧到“定牧”,再到半舍饲、舍饲。
(一)牧主土地占有权与草原游牧利用方式
古代蒙古时期,在帝国内,土地都是大汗的,大汗将土地以“忽必”①的形式分给其功臣和孩子们。功臣和孩子们将大汗分封的土地分给下属的各部落。各部落的领主将分封的土地再分给下属的牧主。在牧主的领地内有些牧奴,他们在牧主分封的土地上放牧主的牲畜,获得一定的报酬。皇帝(可汗)对土地具有分封和收回的绝对权力。大臣和孩子们受封后,也就获得了对草牧场的长期占有权和经营权。清朝时期,全部草牧场的额毡(主人),由蒙古皇帝转化为清朝皇帝;清朝皇帝给扎萨克那颜(王爷)以旗(“和舜”又写“和锡衮”、“和锡温”)土地的世袭占有权[2]。这时期,旗内的苏木(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只管理其辖区内的人口,没有固定的地域,旗内的草场由旗内的牧民共同使用。除汉人开垦的土地和官地等部分土地外,草牧场是旗共有地。“土地是公有,任旗所编使用,即使是王公,上层喇嘛以至呼图克图格根也没有专用的特别土地,任何人均享有平等权利,放牧自己的牲畜。……所有蒙古人,自王公以至奴才,只能在本旗领地内放牧,至于越旗放牧则须经该旗允许[3]。旗扎萨克和蒙古王公既有对旗地的实际占有和分配权,又须按爵位等级占有牧地而不得超越所分地界肆行游牧占有旗地,更要按规定垦放旗地牧场,必须得到清廷同意,否则将受到处罚[4]。清末至解放前,经营管理牲畜采用“苏鲁克”②制度;民国时期,所有制形态为封建牧主所有制,草场公有,牲畜私有。
草原的所有权属于大汗或皇帝,但从草原利用权利而言,大汗和皇帝的所有权是虚空的。草原的控制权主要掌握在封建领主或王公手里。蒙旗共有的公地,由于牧民本身就隶属封建贵族,公地实际为主人侵占。[5]贵族具有土地占有使用权,贵族的属民们在贵族的土地上放牧“苏鲁克”。在游牧的条件下,草原无法分块占为己有。但是,游牧的范围也不是无界限的,贵族的牲畜和属民的牲畜只能在贵族占有使用的土地内移动,尽管遇到灾害时可以占用其他贵族的土地,但是受到他们民间规约的约束,一般在贵族之间协商同意才可以相互进入他人的领地。
(二)集体经济的土地使用权与草原游牧利用方式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初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根据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的复杂性,借鉴我国农区土地改革的成果,在中央政府的批准下实行“三不两利”③政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在制订“三不两利”政策同时,又相应地制订了“牧场公有,放牧自由”的政策,宣布内蒙古的草牧场为公有,牧民在各行政区划内都有放牧的自由,这就结束了牧区的草场和自然资源长期为极少数王公贵族、上层喇嘛召庙及大牧主所占有而广大牧民不能自由放牧和使用的历史[6]。人民公社化时期,全民所有制取代了民族公有制,草原成为全民所有的财产,生产大队对全民所有制草原有永久的占有使用权。《内蒙古自治区牧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草牧场为全民所有,固定给生产大队使用,生产大队有永久使用权和经营保护权。”1963年1月14日,中央批转的《关于少数民族牧业区工作和牧业区人民公社若干政策的规定》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草原,依据各牧业区的不同情况和历史习惯,划归生产队固定使用”、“草原长期固定给人民公社、合作社、国营牧场和公私合营牧场使用。”人民公社化时期,集体经济组织的草场边界已经清晰,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单位使用的草原产权制度已经形成。集体的牲畜在自己的草场上游牧,只有遇到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才可以进入其他集体组织的草场。这一时期草地的公有产权制度及相应的畜牧业政策并没有对草地生态环境造成太大的影响,反过来这时候畜牧业效率也是最高的[7]。
(三)牧民草场承包权和草原利用方式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内蒙古自治区效仿农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畜草双承包责任制度。人民公社解体以后,草场“两权分离”,草场所有权由人民公社所有变为集体所有,牧民享有草场的使用权。1983年底,内蒙古自治区提出牲畜“作价归户”的问题,之后“牲畜作价归户,私有私养”的做法在牧区普遍推广开来。即把集体的牲畜作价出售给牧户,牧民自主经营。[8]在畜草双承包制度实行前期,集体牲畜分配到户,但牧民的草原使用权界限不清楚,实际上出现了牲畜私有,草场公有的草原利用状况。牧民对草原的使用是无偿的,而草原上放的牲畜是个人的。在利益的驱动下,牧民尽可能增加牲畜的数量,过牧问题日益加剧,导致草原严重退化。80年代末,本着“大稳定,小调整”的政策指导下,内蒙古自治区进一步落实草原承包权,界定草场边界,核发草原承包合同,明确草原承包权责。到2000年草场承包经营权的落实工作才基本结束。随着畜草双承包制度的进一步推进,草原的利用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牲畜的私有化和草场的承包经营,改变了传统游牧经济的运行模式,确立了草原的小规模、分散式的经营模式。这种分散式的经营模式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刺激了牧民的致富积极性,草原的生产功能被大大强化。草原承包制度只强调草原的经济职能,认为草原仅仅是提供饲草料的基地,忽略了草原的性质特征,开垦、滥牧、滥采等现象普遍出现。从上世纪末起,草原上出现了沙尘暴天气,引起人们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关注。与此同时,连续发生的干旱、水土流失、“白灾”、“黑灾”等灾害的原因,昔日的丰美草原现在已经变成“天苍苍、野茫茫、老鼠跑过见脊梁”的草原。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同时草原生产能力普遍下降。
二、草原承包制度的社会环境及困境
清代末期放肯蒙地以来,草原的人口和草原的利用方式发生变化。随着开垦草原面积的增加,放牧草原的面积急剧减少,游牧的半径也日益缩小。人口的增长增加了草原资源的压力。解决草原放牧空间和草原的人口之间的矛盾,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改善草原的利用方式,强化草原的生产功能。在此情况下,产权的明晰化被提到日程。通过固定草场的界限、延长草原承包期,改变牧民只利用草原不建设草原的格局,激发牧民对草原的建设保护和利用的积极性。但是在北方草原生态特点和承包经营制度之间出现的矛盾,未能达到草原产权明晰化利用草原的预期目的。草原自然的运作规律被打破。草原承包制度在这片草原上遇到诸方面的困境。
(一)实行草原产权明晰化的社会环境
草原面积的压缩。草原的大面积开垦大大的压缩了放牧草场的面积,牧民不得不在更小的范围内放牧。从清朝末期开始,开垦草原的势头一个比一个高。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王朝废止了过去的“边禁”政策,正式开放蒙荒,内蒙古地区共放垦土地3207万亩[9]。民国时期,内蒙古草原的开垦面积超过3259万亩。建国后在“以粮为纲”、“牧民不吃亏心粮”的政策思想的引导下草原的开垦进一步加大,开垦面积超过3100万亩。改革开放后,草场和耕地的概念不清晰,草场的保护力度不够,导致了又一次大面积草原开垦,上世纪最后十年间内蒙古地区开垦面达1450万亩。[2]如此上百年开垦草原的结果是草原放牧面积大量减少,开垦草原上的牧民被迫前往生态环境低劣的不适宜开垦的草原上,增加了移入地区草原的人口数量。人口的增加导致草原利用空间的相应减少,增加草原的压力。
人口的增加。人是世界的主人,人的能动性能够改变世界,创造历史。但物极必反,人口无限制的增加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内蒙古地区人口的过剩导致草原资源的极度紧张,开垦、过牧、滥采促成了草原严重恶化。据史料测算,直到1570—1582年(明朝隆庆万历年间)居住在内蒙古的总人口不过180万左右。到19世纪初,内蒙古地区的总人口达215万以上[10]。从19世纪初至1949年,内蒙古总人口持续上升,从215万人增加到608.1万人。[11]建国以后,内蒙古自治区人口依然高速增长。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从建国初期的608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2384万人,几乎增加了3倍,而同期全国总人口才增长了一倍[12]。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2010年11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人口24706321人[13]。内蒙古自治区的牧区人口的增长也很快,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刚成立时,牧区人口为22.8万,2000年增长至192.92万。[11]因为,在各时代内蒙古地区的版图不断发生变化,以上数字不能准确说明内蒙古自治区范围人口的增长数字。但能够体现内蒙古地区人口在各时代的增长速度和趋势。草原牧区的范围不断减少,草原牧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对草原的利用效率不断加强,放牧空间不停地被压缩,牲畜不能大范围流动,牧民放弃游牧生活,被迫定居下来。
防御草原灾害。内蒙古草原的海拔较高,纬度高,外表平坦,降雨量少,植物品种单一,因此在草原上旱灾、雪灾、风灾、鼠灾、虫灾等灾害很多。游牧生产方式没有固定的定居点,不能建设长期性的防灾设施,防灾能力较弱。据统计,1952年至1978年,内蒙古地区平均每年因灾害死亡牲畜250万头(只),年均死亡率达7%以上。1977年锡林郭勒盟遭受特大风雪灾,全盟700万头(只)牲畜死了300万头(只)。[14]在此情况下,游牧被认为落后的生产方式,国家大力开展牧民定居工作,建设牧民居住房屋、饲草种地,牲畜棚圈等防御自然灾害。定居后草原的利用范围渐渐固定下来,牧民一般在定居点附近放牧,尽管牧民之间的草场界限尚未确定,但是在牧民之间逐渐形成草场利用的民间规则。
国家政策环境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农区大范围的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制已经被证明为能够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当时,家庭承包责任制成为改革农村经济的法宝。牧区是我国农村的组成部分,家庭承包责任制同样被认为给牧区带来巨大效益,通过承包牲畜和草场,明确牧民的责、权、利,牧民享有畜牧业经营的剩余索取权。这样就可以激励牧民的生产积极性。1983年通过的《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试行)规定,拥有草原所有权的单位可将草原的使用权承包给所属的基层生产单位或个人长期使用,落实草原管理、保护、利用、建设的责任制,使其同牲畜的承包责任制统一起来。时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周惠同志在1984年第10期《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指出:“联系畜牧业生产责任制和个体经营户而建立起来的草原管理责任制,实际上就是一种既包括牲畜又包括草原的‘双承包制’,‘牲畜和草原双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家庭经营的积极性结合起来,使小规模分户经营与专业化、社会化生产有机地结合起来”[15]。在国家的农村改革大环境下,我国北方草原也响应国家的政策,开始实行草原承包制度。
由于放牧草原面积的大量减少,牧区人口的高速增长,长期以来认为游牧生产方式落后的思想观念,我国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全国范围的推广等诸多原因,草原的承包成为必然。在游牧空间缩小,牧区人口大量增长的情况下,大范围的游牧成为不可能。游牧生产方式的抗灾能力的薄弱性也促成牧民定居,建设长期性的防灾设施。由此,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北方草原普遍实行草原承包责任制度,明确草原的权、责、利,草场分配到户,牧民经营小规模牲畜。
(二)草原承包制度的影响
1.草原的承包制度打破了“人民公社”时期的“草原无主、放牧无界、牧民无权、侵占无妨、建设无责、破坏无罪”的无序状态,激发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了牧民收入。承包责任制首次分开权、责、利,牧民取得了草场的使用权、收益权、在承包草场上自主经营畜牧业,收益归牧民。这不仅使牧民对草原的使用有了法律依据,也使牧民对承包草原的投资建设有了稳定的法律环境。牧民对承包草原的投入由集体经济时期的纯劳动力的投入向多项投入,如固定资产投入,畜牧改良投入等,多数牧民在承包草原上建设房屋、饲草地、棚圈,改善畜牧业的生产环境。同时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畜产品价格逐步生长,牧民的总体收入稳定提高。
2.公平、正义是法律永恒追求的价值。法其实来自于正义:实际上,就像杰尔苏非常优雅地定义的那样,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16]。在集体经济时期,牲畜和草场均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因此,在草原的利用方面,集体经济组织内无从谈起公平不公平。“牲畜作价,户有户养”的政策实施后,集体经济组织的牲畜归牧民所有,但草场由经济组织内的成员共同使用。牲畜承包到户后不久,牧民之间出现贫富差距,有些牧户的牲畜数量增加,有些牧民的牲畜减少,甚至出现无畜户。草原的共同使用一方面导致集体成员对草原的过度利用,另一方面也造成大户吃小户草场,有畜户吃无畜户草场的不公平现象。上世纪末期,通过草原的几轮承包,草原承包工程基本完成。在法律层面来说草原的承包,能够划清承包户的草场界限,牧民在承包草原上有了自主经营的权利,集体的成员之间公平使用集体所有的草原。
3.牲畜是牧民谋生的财产,草场是牧民的主要活动场所。人—畜—草的线性关系当中,草是最基本的,是牧民生存的基础保障。草原承包到户后,牧民可以在承包草原上放养牲畜保证生计。贫困牧民即使没有牲畜,也可以将草场出租给其他有畜的牧户或承包他人的牲畜在自己的草场的放牧收取费用。在牧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承包草原对牧民生存起到保障性作用。
4.草原的承包改变了牧民的传统生产方式。草原的承包给牧民的草场划清界限,明确草原产权。牧民对承包草原具有排他性的使用权,可以限制其他人对其草场的进入。草原被分割后,牲畜的移动受到限制,游牧已经不可能了。产权的明确界定促使牧民定居,牧民在自己承包的草原上建立住房、棚圈,建设草饲料地。草场的分块利用打破了传统游牧生产方式,牧民开始过“定牧”生活。
(三)草原承包制度的困境——草原的退化及治理退化制度的失败
草原具有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生态环境和特殊的使用方式。因此,草原上实施的法律制度必须符合草原的特点、草原自身运行的规律才能取得良好效应。土地承包制度是我国农业社会内部产生的土地利用制度,在农业社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草原承包制度实行二十年后,在制度的实施和效应方面均遇到了困难。当前我国制度选择与制定的主体当然是农耕文化指导下的多数人,他们会不自觉地把农耕地区的制度移植到草原上,全盘照搬了农耕区的系列制度,草原牧区也实行了类似农区的“草场公有,承包经营”的责任制[17]。但是,事实表明,被普遍认为实施承包制度取得草原长足“发展”的近20年,恰好是草原退化和荒漠化空前加剧的时期[7]。
1.草原承包权法律性质的限制。《物权法》通过后,草原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以基本法的形式被确定下来。而草原承包经营权物权性质的保护遭到极大的挑战。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不能违反法律的明文规定。物权法定原则是现代物权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是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均须由法律加以明确的规定,不允许当事人任意创设与法律规定不同的物权或者合意改变物权的内容。[18]草原承包经营权的设立以《物权法》的规定为标准,发承包方及国家机关等第三人不能改变承包经营权的法定内容。《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草原法》对草原承包经营权内容的规定模糊不清。行政机关及发包方对承包方的草原的使用权进行大量的限制,极大地削弱了物权法定性质。《草原法》规定,草原承包经营者应当合理利用草原,不得超过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载畜量;草原承包经营者应当采取种植和储备饲草饲料、增加饲草饲料供应量、调剂处理牲畜、优化畜群结构、提高出栏率等措施,保持草畜平衡。国家对草原实行以草定畜、草畜平衡制度。国家提倡在农区、半农半牧区和有条件的牧区实行牲畜圈养。草原承包经营者应当按照饲养牲畜的种类和数量,调剂、储备饲草饲料,采用青贮和饲草饲料加工等新技术,逐步改变依赖天然草地放牧的生产方式。对严重退化、沙化、盐碱化、石漠化的草原和生态脆弱区的草原,实行禁牧、休牧制度。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草原法》的规定势在必行。甚至有些研究人员提出“草原承包经营权生态化”[19]、草原承包经营权和草原环境权协调保护、“社会性的所有权”、“环境物权”的概念。[20]但是,从物权法的角度看,草原承包权的诸多限制,剥夺了牧民自主经营畜牧业的权利,草原承包经营权失去了其用益物权的本质含义。牧民对发包方和国家在草原承包权采取什么样的限制完全没有预期性。
2.草原承包制度在适应草原生产方式的困境。我国农区耕地承包制度和北方草原承包制度的本质属性相同。但是这两种承包制度实施的社会、自然环境截然不同。我国农区耕地水分充裕,土地肥沃,产量稳定。农耕地区有条件开展水利建设,抗灾能力强。农耕地区的土地和人的关系相对简单,农民在耕地上耕种一份收获一份,精耕细作能够适量提高土地的产出,土地上的种植物不可能“超载过种”的问题。这种情况下,耕地的分散式的分块经营不影响耕地生态环境。我国草原的降雨量少、植物产量低,迫使牧人采取轻度、轮牧的方式控制放牧强度和远距离游牧,以使牧草获得休养生息的时空条件[21]。草原畜牧业是人—畜—草之间的生产关系。牧民的财富以牲畜的数量来衡量的,牲畜数量的多少也是由草场的面积和质量决定的。牲畜是移动的,牲畜的适当移动能保证草的生长和恢复。草场的分散式的小范围的利用引起牲畜对草原的重复踩踏和过度啃食,对草原的生长和恢复不利。草场承包到户的制度,牲畜被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无法进行移动,导致对草场的强度利用,加剧了一些地区草场退化、沙化的速度[22]。由于农耕经济和畜牧经济的生产基础、生产方式不同,在农耕经济适合的耕地承包制度不一定完全适合草原经济。
3.草原承包制度为基础实施的草原治理政策的失败。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国家认为草原的共同使用导致草原环境的退化,试图推动草原承包责任制度,阻止草原恶化现象。经过几轮的草场承包后,牧区的草场承包工作基本结束。但是草原的承包仍然没能遏制草原上的“超载过牧”、草原的进一步退化。为此,国务院《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2]19号文件)》中提出保护草原的三大措施(基本草地保护制度;草畜平衡制度;划区轮牧、休牧、禁牧制度)之一。实际上,从草场承包给个人开始,我国牧区就始终没有放弃对载畜量的控制。就以内蒙古为例,早在1980年4月《全区草原工作会议纪要》就提出草原合理利用的关键是合理的载畜量,要逐步实行以草定畜,实现“两个平衡”。1981年4月,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内蒙古自治区畜牧厅的报告,再次强调要实行以草定畜。1983年7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试行)》和1984年7月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都规定,草原使用单位要定期对草场进行查场测草,根据实际产草量,确定每年牲畜饲养量和年末存栏量,实行以草定畜,做到草畜平衡。从此,以草定畜、草畜平衡的原则作为地方立法确定下来 (内蒙古自治区畜牧志编委会,2001)。在分块承包经营的情况下,草原是各个牧户拥有的,草原不能整体规划,整体利用。我国草原生态系统具有异质性,草原的承载率不是固定的,决定草原承载率的主要因素是降水。我国北方草原的降水无规律,具有非平衡性。降水量多时,牲畜数量较多也不会出现“超载过牧”现象,而当极端干旱连续发生时,较少数的牲畜也出现“超载过牧”,造成草原的退化。因此,现行的草原治理措施都围绕着“减畜”展开,而无视具体的时空尺度,尤其是忽视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气候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目前“草畜平衡”制度中出现的众多问题,其根源或许不是承载力确定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该方法是否符合目标生态系统特点的问题[23]。
在牧区实施休牧、禁牧意味着牧民饲养牲畜的成本大大增加。在市场环境优越,供应渠道畅通的地区进行高投入高产出的畜牧业可以缩短生产周期,取得较高的利润。但不生产饲草料,只依靠天然草场的牧区休牧、禁牧、舍饲、半舍饲提高饲养牲畜的成本,导致牧民收入不足以支出。为了降低舍饲的成本牧民通过普遍的偷放来逃避政策。监管部门加大力度执法,牧民以各种方式逃避执法,例如“夜放”、“节假日放”、“周期性放”等,监管部门和牧民之间形成“猫鼠游戏”。而且休牧禁牧主要是草不生长的冬季和春季进行,对草原的保护作用极其有限。因此,休牧禁牧结果加大了牧民的生产成本,却未能达到保护草原的预期目的。在我国北方草原上草畜平衡、禁牧休牧制度已经实行十多年,但草原的生态环境没有好转而日益恶化。这就说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实施的草原治理退化制度皆告失败。
在集体经济时期,草原退化主要是因为政策的错误导致的④。改革开放后,草原实行畜草双承包制度,但草原退化、牧民返贫更加严重。当政者和学者们普遍认为草原的退化是因为产权制度不明确造成的,草场的共同使用造成“牲畜吃大锅饭”,导致“公地悲剧”。通过赋予牧民一块草场的长期使用权促使牧民合理利用草场是很多研究者和政府推行的消除过牧、保护草场的制度解决办法[24]。在以国家的角度考虑,环境治理政策的实行必须以草原承包制度的全面落实为前提条件。只有在承包以后才能计算每个牧民家庭的牲畜载畜量,才能计算休牧禁牧补贴,退牧、还草项目也是建立在草场承包基础上的[25]。因此,草原承包制度及草畜平衡、休牧禁牧轮牧政策是一个制度群体。在我国北方草原的性质特征决定,草原承包经营权的实施必然导致草畜平衡、休牧禁牧轮牧制度的实施。国家管理政策和牧民利益之间的博弈中,相互未能找到一个平衡点,最后牧民未能取得利益,自然环境继续恶化。
三、草原承包制度的改革路径
研究草原的问题不能离开人—畜—草三者之间的关系。因为草原上的人口大大增加,草原的使用空间越来越小,草原的使用功能已达到极限。仅仅考虑人—草的直线关系不能解决草原的根本问题。草原的承包是以草原上居住的人为基础,将草原分配给牧民,以人数决定草原的使用方式。草原有其固有的运行规律,而不以其上的人数所决定的。解决草原的问题,必须充分掌握草原的运转规律,设计出符合草原运转规律的利用制度。当今,草原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即牧民利益和草原生态。草原承包制度在产权保护、社会保障等问题上起到一定作用,但忽略了草原生态环境利益。而草原环境利益的损害最终会对牧民利益带来了不可弥补的后果。根据草原目前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牧民利益及环境利益、结合草原自然规律,对草原承包制度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一)草原承包制度的改革必须转变观念,以草原作为制度的中心
我国北方草原土壤贫瘠、生态脆弱、降水变率大,土地只能生长草本类植物,不宜农耕,只适宜轻牧、轮牧。草原承包制度是以草原上的人数为基础,将草原分配给牧民,以牧民数量的多少来决定单位草原利用面积的大小。以人数分配草原的方式不符合草原的规模化移动式利用的特征,增加草原的压力,导致草原的退化。与农区土地利用方式不同,草原的利用是通过草原上的牲畜来实现的。牲畜是移动的,如果牲畜的移动空间过小会导致牲畜对草原的过度啃食和来回踩踏,草原难以得到恢复。在合理空间的草原上移动式放牧合理数量的牲畜,能够减少单位草原的过度放牧,延长草原的恢复时间。根据草原的位置、草的长势、水源等特征,结合牧区传统经验和现代科技,合理划分单位草原的面积,计算出草原承载的牲畜数量才能够发挥草原的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因此,转变草原利用观念,由人数决定单位草原的面积转变为草原的自然规律决定单位草原的利用面积。在此基础上,重新组合单位草原利用主体制度,保证主体之间的利益,实现主体的公平。
(二)草原利用方式改革的路径
草原的利用方式的改革应从两方面入手,第一是草原面积的重新划分。第二是草原上的牧民的重新组合。草原利用主体的重新建构应以草原的重新划分为基础,对草原承包经营权主体的改组来实现。为了克服承包草原分散式的利用方式对草原生态和牧民权益带来的缺失,应以家庭承包的草原重新整合为合理面积的单位草原,精确计量草原的承载力,根据草原的实际情况划分放牧区、打草场,依照草原的运转规律,进行移动式放牧,为草原自我恢复提供机会。划分草原的方式应因不同性质的草原而不同。例如,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位于温带湿润地区水热条件较好,植被覆盖度较高,恢复能力强,划分的面积可以相对小点。而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部地区草原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草原的降雨量少、植被覆盖率低、恢复能力低,其划分的面积应该较大,充分考虑水源问题,对人畜的饮水提供便利条件。牧民的改组以重新划分的单位草原为基础,单位草原上的牧民以草场入股及牲畜入股的方式完成。在草原承包经营权落实的基础上,以承包草原入股是草原利用主体重新组合的重要形式。牲畜是牧民的重要财产,也是草原利用主体的经济来源。以牲畜入股也是改组草原利用主体的重要方式。
(三)改革的预期经济社会效应
草原承包以后,牧区的互助合作关系断裂,集体经济组织的公共管理职能被弱化,牧民在草原生态保护和市场竞争面前束手无策。草场的分散型分配明确了牧户之间的草原边界,牧民之间整合草场移动式放牧成为不可能。国家推出的舍饲圈养和休牧禁牧的环境政策及草场围封等费用增加了牧民的生产成本。在水资源缺少的牧区,牧民的承包草场上没水井,从他人的水井上拉水的费用非常昂贵。很多牧民因为不能承受这些放牧的费用已经放弃放牧。牧民购买饲草料,出卖牲畜市场活动中不能形成规模,供应渠道不畅通,在市场体系中位于弱势地位。对保护草原生态环境,防御自然灾害,共同应对畜产品市场,草原文化的保护等方面,改组后的经济主体的作用单个牧户无法替代。草原利用方式和利用主体的改革并非是单一的经济模式的转变,而是将社会、文化、教育等功能集于一身的社会经济主体的改变。
注释:
①“忽必”在蒙语里是封赐的意思。每逢祭拜山神水神或庆祝战功时蒙古大汗将金银、酒肉等物品赐给其功和孩子们,做为大汗对他们战功的奖赏。
②“苏鲁克”,蒙语的意思是畜群。解放前,内蒙古牧民代养牧主的牲畜叫“养苏鲁克”。蒙古王公贵族、上层喇嘛、旗府、庙仓以劳役形式将畜群交给属民放牧,称为“放苏鲁克”,牧主和商人将畜群租与牧工放牧,也叫“放苏鲁克”。
③“三不两利”是指“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初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根据《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要求开展民主改革运动,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斗争牧主、评分牧畜,但是因为牲畜是可以流动的,其评分耕地不同,很多拥有大量牲畜的牧主们逃离或屠杀牲畜,给牧区造成巨大的恐慌。当时,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力劝中央政府在民族地区实行符合当地的民主改革措施。在中央政府的批准下,1948年内蒙古自治区实行“三不两利”、“牧场公有、放牧自由”的政策。1953年政务院批转民委《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地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将“三不两利”、“牧场公有、放牧自由”的政策推广全国。
④这里指的政策错误是指“以粮为纲”、“牧民自给粮食”的口号下,全盘否定畜牧业,大面积的开荒导致草原的退化。
[1]王建革.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42~43.
[2]包玉山.内蒙古草原畜牧业历史与未来[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73~85.
[3][日]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82.
[4]张植华.近代内蒙古牧区生产关系及其对生产力的束缚[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65~72.
[5]邢亦尘.清代蒙古游牧经济浅议[A].中国蒙古史学会编.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336~339.
[6]阳吉玛.略议制订“三不两利”政策的客观依据[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1):86~88.
[7]达林太,娜仁高娃,阿拉腾巴格那.制度与政策的历史演变对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J].科技创新导报,2008(1):114~120.
[8]荀丽丽.失序的自然—一个草原设区的生态、权利与道德[D].2009.
[9]恩和.草原荒漠化的历史反思:发展的文化维度[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3-9.
[10]布仁.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人口的历史与现状简述[J].内蒙古统计.2003(1):36-37.
[11]包红霞,恩和.内蒙古牧区人口变动研究[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9-15.
[12]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EB].见htt p://www.hlglpop.gov.cn/_d270815289.htm/,2012-08-24.
[13]内蒙古自治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EB].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2011-5-9.
[14]李文军,张倩.解读草原困境—对于干旱半干旱草原利用和管理若干问题的认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68.
[15]盖志毅,李媛媛,史俊宏.改革开放30年内蒙古牧区政策变迁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28-31.
[16]罗智敏.法学汇纂[M].(第1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17]马桂英.内蒙古草原生态恶化的制度因素与制度创新[J].兰州学刊,2006(9):182-184.
[18]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著.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48.
[19]王俊霞.草原承包经营权生态化研究[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31(3):39-42.
[20]特日格勒.草原承包经营权和草原环境权的法律协调保护[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7):85-89.
[21]敖仁其.草原放牧制度的传承与创新[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3(3):36-40.
[22]徐斌.‘三牧问题’的出路:私人承包与规模经营[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53-58.
[23]李艳波,李文军.草畜平衡制度为何难以实现”草畜平衡[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24-131.
[24]刘艳,齐升,方天堃.明细草原产权关系,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J].农业经济,2005(9):30-31.
[25]王晓毅.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内蒙古六个嘎查村的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