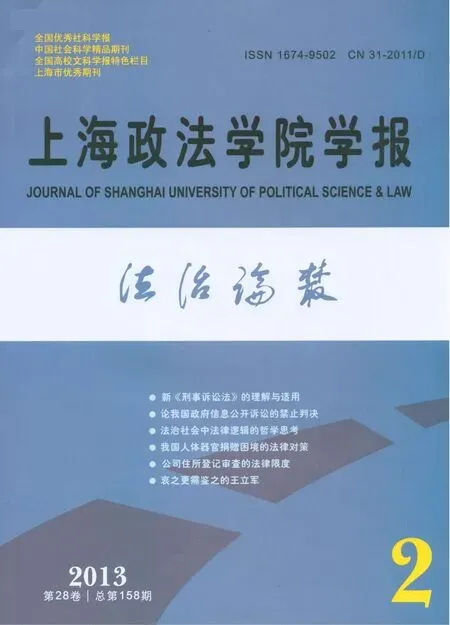我国人体器官捐赠困境的法律对策
2013-04-10胡田野
胡田野
(国家法官学院,北京 101100)
●法学论坛
我国人体器官捐赠困境的法律对策
胡田野
(国家法官学院,北京 101100)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面临器官供应短缺的困境,以至于出现了器官买卖黑市,甚至强迫器官买卖等犯罪行为。世界各国在器官捐献的同意制度上,有推定同意与明示同意之分,推定同意包括“纯粹的推定”,“可推翻的推定”及“部分推定”等不同类型。我国立法应吸纳推定同意制度中的一些做法。人体器官的买卖应被禁止,但是对器官捐献者进行补助和激励,却是立法上应当鼓励的。关于死亡标准问题,我国立法既要考虑社会的接受程度,又要考虑是否有利于器官移植。为了使我国走出器官短缺的困境,我国应建立器官协调员制度,明确捐献意愿的载体,加强器官捐献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
人体器官;器官捐献;器官移植法律对策
我国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人体器官移植面临着器官供应短缺的困境。①据报道,中国每年有15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但是成功移植者不足1万人,器官来源短缺严重。《中国器官移植来源短缺,官方致力构建捐献体系》,http://www.chinanews.com/jk/2012/03-23/3767938.shtml,中国新闻网,2012年11月14日访问。器官严重短缺,不仅仅导致很多病人在等待中死亡,而且导致人体器官交易黑市的出现,甚至强迫器官买卖等犯罪行为。器官短缺与社会文化有关,但是与法律的不完善也有关系,例如缺乏对捐献者一定的补助。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器官捐献是无偿行为,捐赠者不能从捐赠行为中得到经济上的弥补。立法者唯恐将对器官捐赠经济补偿等同于器官买卖。但是这样一来,却严重影响了捐赠者的积极性。②《贫困男子患直肠癌无钱治病,曾义捐已故女儿器官》,http://news.sina.com.cn/s/sd/2012-04-09/ 104524241578.shtml,新浪网,2012年11月15日访问。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也存在一些立法技术的缺陷,如死亡标准不确定等,不利于人体器官的捐赠与移植。③《丈夫车祸院方称已脑死亡,妻子欲捐器官惹争议》,http://news.ccvic.com/shehuixw/shehuiwx/2012/ 0415/188207_2.shtml,华媒网,2012年11月15日访问。
器官移植有3种类型,即活体器官移植,异种器官移植(xenotransplantation)和尸体器官移植。活体器官移植主要发生在近亲属之间。④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0条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活体器官移植对于解决器官移植的短缺并不具有太大的作用。异种器官移植是将动物器官移植到人体之内。但由于科技尚未足够发达,以至于应用有限。尸体器官移植(Cadaver Donors)最为常见且由于供体最多,在解决器官移植短缺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最大。本文以尸体器官移植为研究重点,探寻解决器官短缺这一困境的立法对策。
一、器官捐赠的推定同意与明示同意制度
摘除尸体器官用于移植,是否需要死者生前同意或者死后由其家属同意,相关国家的规定并不相同。第一种模式是推定同意模式,即如果生前没有相反的意思表示,法律推定公民死后自愿捐献其器官。西班牙、比利时和挪威通过了推定同意器官捐献的法律。推定同意制度可以大大缓解器官短缺的现象,例如西班牙就是器官不短缺的国家之一。但是,推定同意制度也带来法律上的难题,即该制度涉嫌侵害死者近亲属对遗体的支配权。
因此,推定同意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各国依据各自的社会背景和立法理念,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纯粹的推定”,“可推翻的推定”及“部分推定”等。奥地利属于“纯粹的推定”的国家。奥地利法律规定,只要死者没有反对摘除其器官,死者的器官就可以被摘除,而不需要死者近亲属的同意,此即为“纯粹的推定同意制度”。
“可推翻的推定”是指如果死者生前未作意思表示,法律推定公民死后自愿捐献其器官,但是其近亲属可以推翻该推定。这种更加宽松的推定同意制度在芬兰、希腊、意大利、挪威、比利时、瑞典、西班牙等国实施。这种制度中,家属可以推翻死者生前决定捐献其器官的意愿。法国的推定制度要宽松一些。事实上,如果没有家属的同意,法国医生是不会摘除死者的器官的。
还有一种制度是“部分推定”。“部分推定”是指,法律仅仅对特定人群就特定器官捐献作出同意的推定。例如新加坡仅仅对特定人群捐献特定器官予以推定。新加坡起初采用的是器官移植的自愿的制度。1987年新加坡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法》(The Human Organ Transplant Act)。该法律推定一些人群死后同意捐献其器官,但是另一些人群不同意捐献其器官。新加坡的人体器官移植法规定:“所有智力正常的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年龄在21-60之间,如在意外事故中死亡,推定同意捐献其肾脏,且其近亲属并不需要同意的表示。”①Sean R. Fitzgibbons,Cadaveric Organ Donation and Consen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Singapore, and China, 6 Ilsa J Int'l & Comp L 73(1999).可见,新加坡的推定制度中,存在三个条件:只对肾脏捐献进行推定;只对意外事故中的死者推定其同意的意愿;只对智力正常的青壮年进行推定。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推定,都存在一些基本性的问题:第一,推定同意中存在一个基本法律问题,即推定同意是否侵害了死者及其家属的权利?第二,死者近亲属对死者遗体是否有民事权利?该权利的性质是什么?国外很多法院承认死者近亲属对死者遗体享有以安葬为目的的准财产权。因此,对推定同意的制度的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第一,推定同意制度不能保护捐献者的意思自由,反而可能侵害其权益;第二,推定同意制度不能保护那些未作意思表示,但是不愿意捐赠器官的人的愿望。②Lisa M. Derco,America's Organ Donation Crisis: How Current Legislation must be Shaped by Successes Abroad,27 J. Contemp. Health L. & Pol'y 154(2010).
因此一些国家并不采取推定同意制度,例如美国和中国。尽管美国器官移植的数量缺口很大,但并没有采取推定同意的法律制度。截止到2011年4月13日,美国有110758个人在等待器官移植的名单上。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可供给的器官数量。并且,每年这个差额都在扩大。但是,美国的《统一尸体器官捐赠法》(The Uniform Anatomical Gift Act ,UAGA)在1968年被所有的州采纳之后,2006年该法被修订,其目的却是提高器官捐献中的意思自治。2006年共45个州采纳了该法,2011年又有三个州采纳了该法律。美国采用的是“选入”的方法,即个人必须在死亡之前明确表示愿意捐献其器官,或者其家属明确同意捐献死亡亲人的器官。UAGA法规定,任何人不能改变死者决定捐献器官的决定。但是,器官移植机构继续想办法取得家属的同意,如果家属反对器官捐献的决定,尽管这违背了UAGA的表述,但是器官移植机构还是会尊重家属的意见。①Hayley Cotter, Increasing Consent for Organ Donation: Mandated Choice, Individual Autonomy, and Informed Consent, 21 Health Matrix 599(2011).
我国法律并没有采取推定同意制度。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8条第2款规定: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捐献、摘取该公民的人体器官;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的意愿。因此,我国法律规定,器官的摘取须基于明示的意思表示。
我国采取这种方法有其现实的社会文化基础。我国民众自古以来认为,死后要保持全尸,尸体破损会影响家族运气等。我国目前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8条第2款规定属于权宜之计,如果采取新加坡的立法模式,既照顾到社会文化基础,又解决人体器官移植最需的、移植技术最成熟的器官需求,倒是一种相对较好的立法举措。即使是我国当下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规定,也存在一些尚需明确的问题:第一,如果死者生前同意的,近亲属能否推翻该同意?第二,如果死者生前不同意的,近亲属能否推翻?第三,如果死者生前未表示的,近亲属决定捐赠器官的顺序是共同决定,则增加了器官捐献的难度。这些问题不清,致使法律适用上的困难。笔者认为,死者生前同意的,近亲属应不能推翻该同意的意思表示。原因在于,死者的遗愿应得到最大的尊重,死者家属也应如此。如果死者生前不同意捐献其器官的,近亲属应允许推翻其遗愿,因为器官捐献有益于社会;如果死者生前未表示的,有权决定的近亲属应当有先后顺序。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器官捐献须取得近亲属的一致同意,实际上增加了器官捐献的难度。
对于我国是否在立法上实施推定同意制度,笔者有3个建议:第一,一种可取的办法是强制性选择。即要求成年人在死亡之前须对是否捐献器官作出选择。强制性选择可以提高个人的意思自治,确保个人能够对自己的遗体如何处理作出决定。立法应规定,个人的意思表示优先于家属的意见。例如在申请驾驶证或者更新驾驶证的时候,或者填写税单的时候,须明确表示是否同意捐赠器官用于移植,如不选择则不能申请或者更新驾驶证。第二,是加强公共教育,为将来推行器官捐赠的推定同意制度打下基础。器官捐献的公共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我国民众的传统思想,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实际要求。第三,在将来推行“可推翻的推定”制度或者“部分推定同意”制度。“可推翻的推定”是指如果死者生前未作意思表示,法律推定公民死后自愿捐献其器官,但是其近亲属可以推翻该推定。该制度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得以实施。该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于,在社会利益和近亲属的利益之间达成较好的平衡。或者采取新加坡的“部分推定同意”的模式,也有助于解决目前的器官短缺的困境。
二、器官捐献的无偿原则与激励机制
人体器官买卖不应被允许。不过,世界上也存在允许器官买卖的国家,例如伊朗。自从1996年开始,伊朗建立国家管制的模式,允许器官买卖。伊朗的制度有两个特点:第一,通过国家统一管理器官买卖的模式,打击私底下的器官买卖;第二,对于需器官移植的穷人,由国家及慈善机构予以补助来购买器官。
我国的一些研究者也支持人体器官买卖,“人体器官商业化则是将人体器官买卖等器官交易行为纳入国家法律规范和政府管制之下,以建立透明有序、诚信合法的人体器官市场。因而,人体器官商业化与为获取器官而进行的器官犯罪行为两者存在本质的区别。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供体器官短缺并且不允许人体器官商业化恰恰是造成器官黑市交易、器官走私、移植旅游等器官犯罪行为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①王荣平、付媛:《人体器官商业化之合法性探讨》,《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但是笔者认为,器官买卖制度过于激进。尽管伊朗的器官买卖是由国家控制,统一管理,但是该制度会存在一些危害:第一,器官买卖有损人的尊严。尽管物权法上可以将脱离人体的器官视为物,等同于脱离人体的血液、皮肤等,但是人体器官终究与人格有紧密的关联;第二,即使器官由国家统一买卖,但是该买卖制度如果存在漏洞,实施器官买卖的国家将成为其他国家购买器官的“原产地”;第三,器官买卖将会使贫富不均以血淋淋的方式呈现。
笔者反对器官买卖,但是支持对器官捐献者或者其近亲属进行合理的补偿,构建器官捐献的社会激励机制。第一,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器官不应被买卖,但是器官捐献制度不应当排除对捐献者的合理补偿,包括确实的开支,例如收入的损失,身体恢复的成本等等。第二,对器官捐献者或者其近亲属进行合理的补偿,有助于激励社会公众产生器官捐献的意愿;第三,对器官捐献者或者其近亲属进行合理的补偿,也符合公平原则。尽管医院声称只收取器官移植的医疗费,并不收取器官本身的费用,但是如果没有器官,就谈不上收取器官移植的医疗费,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方面是医院收取巨额医疗费用,一方面器官捐献者没有任何补偿,这是不公平的;第四,器官捐献有助于社会以及国家医疗水平的提高。因此,国家也有道义对器官捐献者进行合理的补偿。
笔者认为,构建我国的器官捐赠的激励机制,大致可以包括如下的几个方面:第一,对捐赠者或其家属进行合理的经济补偿。一些国家诸如法国、加拿大和英国,均允许对器官捐献者进行补偿。法国要求补偿捐献者的交通及住宿费用;加拿大有联邦的激励机制,例如失业保险、医疗费的税收减免等。第二,建立器官捐赠者及其近亲属的受赠器官的优先权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愿意在死亡之后捐献器官的人,如果自己或其近亲属需要器官移植的时候,具有优先权利。第三,医疗费用的减免制度。凡是愿意捐赠器官者,其医疗费用或其近亲属的医疗费用,可以得到减免。例如美国威斯康辛州于2004年颁布法律,对器官捐赠者进行所得税的税收减免。第四,对器官捐赠者死亡后的丧葬费支出进行合理的资助。
器官捐献的激励机制不同于器官买卖。器官买卖是直接的货币交换,但是激励机制主要是对费用支出的补偿等。对器官捐献进行经济奖励,是否会迫使穷人为了获取激励而捐献其器官?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穷人可以自己做出理性选择;只要充分告知其风险,并由其自愿做出决定,应该是可以的;否则会出现器官交易的地下市场;甚至是强迫他人捐献器官的现象。”②Sara Krieger Kahan, Incentivizing Organ Donation: A Proposal to End the Organ Shortage, 73 U. Cin. L. Rev. 1101(2005).笔者认为,器官买卖与器官捐赠的激励机制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为了解决我国器官短缺的现状,《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应当做适当的修改,确立器官捐赠的激励机制。
三、器官捐献中的死亡标准
死亡标准与器官移植有着重要的关联。以心跳、呼吸停止为标准还是以脑死亡为标准,一直存在争议。医学界强调以脑死亡作为器官捐献中的死亡标准,首先是技术上的原因。捐赠的器官须是活体,换言之,如果以呼吸停止为死亡标准,则呼吸停止后15分钟内要取出器官,否则器官就不能使用,③王文科:《施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器官移植供需困境的影响》,《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但是如果采取脑死亡标准,则器官移植就容易得多;其次,死亡标准也是界定医生的法律责任的重要前提条件。如果法律未认定捐献者已经死亡,医生就摘取其器官,医生很可能要承担谋杀的法律责任。
1980年美国《统一死亡判断法》(The Uniform Determination of Death Act)规定了医生合法宣告尸体器官摘除的开始。该法规定了心肺系统的完全终止为标准,以及完全的脑死亡标准。①Sean R. Fitzgibbons,Cadaveric Organ Donation and Consen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Singapore, and China, 6 Ilsa J Int'l & Comp L 73(1999).该法同时规定,脑死亡不包括大脑新皮质死亡(neocortical death)及永久性植物人。因此,美国《统一死亡判断法》采取的并立的死亡标准,即脑死亡和心肺系统终止作为死亡的两个标准。一些学者研究认为,“韩国器官移植法并没有正式采纳脑死亡,但是为了使摘取脑死者器官的行为适法化,该法吸收了脑死说的合理内核,在脑死状态下,通过立法的方式有条件地允许摘取脑死者的器官。也就是说,该法颁布之后,摘取脑死者器官的行为就属于依法令的行为,对此已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因此没有必要明示性地采纳脑死亡。”②莫洪宪、李颖峰:《韩国器官移植法对我国的启示》《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如果采取美国《统一死亡判断法》中的判断标准,明确确立脑死亡标准,也未尝不可。但是,死亡标准的确立,不仅仅需得到医学界和法学界的认可,更主要的是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接受。因此,目前我国直接规定脑死亡标准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事实上,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就回避了这个问题。如果采用韩国的立法模式,即立法上不规定脑死亡是否为死亡标准,而是将脑死亡作为医生摘除器官的合法条件之一,可能使我国社会各界更加容易接受。
四、我国人体器官捐赠与移植法律制度的完善
除了前述的一些法律制度需要完善,以应对我国器官捐赠的困境之外,笔者认为如下的制度也应在立法上有所反映。
(一)建立人体器官移植协调员制度
西班牙建立起完备的器官移植协调员制度。西班牙168个医院中均有器官移植协调员,这些协调员的作用是对失去亲人的家属,劝慰并讨论捐献器官的可能性及对他人的益处。这种方法似乎很有用处。据统计,“起初拒绝捐献器官的家庭,在器官移植协调员与之讨论之后,78%的家庭改变了主意,表示愿意捐献器官。实施了协调员制度之后,西班牙的器官捐献率大大提高,从1989年的每1.4‰提到到2008年的每3.4‰,具有世界上最高的捐献率。”③Lisa M. Derco,America's Organ Donation Crisis: How Current Legislation must be Shaped by Successes Abroad,27 J. Contemp. Health L. & Pol'y 154(2010).美国1987年的法律要求医院指定人员去询问病人是否有捐献器官的愿望,并寻求病人近亲属对捐献器官的同意。协调员的作用是很大的,可以劝说病人或其亲属同意捐赠器官。我国尚没有国家层面的器官移植协调员制度。但是可喜的是,一些地方目前进行了探索,建立了人体器官移植协调员制度。④《河南有了器官移植捐献协调员,首批110人开始培训》,http://www.cnr.cn/hnfw/yyws/yaowen/201111/ t20111111_508762354.shtml,中国广播网,2012年11月17日访问。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捐献问题
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器官捐献决策又如何进行呢?例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父母决定将智力不正常的孩子的器官移植给另一个正常的孩子是否可行?美国通常采取两种办法:第一种是替代决策标准(substituted judgment standard),即假设捐献者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形下,也很可能作出捐献的决定,则可以决定他的捐献,该决定当然由其监护人或者法院作出。如无民事行为能力在未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前,曾经有过器官捐献的表述,则该表述应当是值得认定的。替代决策标准试图解决这个两难境地——一边要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自由意志,一边要甄别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真实的想法。第二种方法是最佳利益标准。法院采用该标准决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器官捐献决定。谁可以做出捐赠的决定?美国1968年的统一器官捐献法规定:任何年满18岁且心智正常的人,可以做出捐赠的决定;如果没有死者自己的决定,则死者的近亲属(next-of-kin)可以代为做出决定。
(三)明确捐献的意思表示的方式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8条第1款规定:捐献人体器官的公民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公民捐献其人体器官应当有书面形式的捐献意愿,对已经表示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意愿,有权予以撤销。但是,有“书面形式”是指的什么?该行政法规语焉不详。
1968年的美国《统一尸体器官捐赠法》(UAGA)的法律规定:器官捐赠通过执行遗嘱或者遗嘱外的文件的方式进行;如果是遗嘱外的文件,则捐献者本人和见证人都需要签字;如果是近亲属做出决定,则需以电报或者记录的信息表示。1987年该法做了修改,主要规定:捐献方式的简化,遗嘱外的文件不需要见证人;同时,允许各州规定在颁发驾驶证以及身份证时候填写的资料,作为捐献器官的有效文件。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应明确捐赠意思表示的载体,而不能简单规定为“书面形式”。单独的捐赠器官的声明、遗嘱、申领驾驶证等证件时的表格等均可以作为器官捐赠意思表示的书面载体。
(四)完善器官捐献的专门机构管理制度
就我国目前人体器官移植的实践看,人体器官的供需很不平衡,有限的器官资源并没有完全用于那些最需要接受移植的人,器官供需信息也没有实现共享,这是产生各种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有人提出,应当建立统一的登记协调机构,对人体器官移植实行统一的登记协调管理。也有人提出,目前不适宜建立统一的登记协调机构,可以由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通过信息共享的方式自行协调即可,还有人提出,鉴于我国骨髓捐献登记协调工作体系已初具规模,可以将人体器官移植登记协调工作纳入这一体系中。①张海燕:《人体器官移植立法问题研究》,《东岳论丛》2008年第6期。
美国1998年的《转诊与请求规则》(Referral and Request Regulation)规定:医院将逝去的病人以及即将死亡的病人,转移给当地器官移植机构(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OPO),该类机构有经过培训的经验丰富的人员,知道如何取得近亲属捐献其亲人器官的同意的意见。
美国的器官移植组织机构是器官共享联合网络(The 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UNOS)。该机构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慈善机构,管理美国以移植为目的的器官收取和分配。该机构的宗旨是,通过教育、技术和政策的发展,为了病人的利益,提高人体器官的供给量。该机构有全美等待器官移植的人员名单。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该机构全天候地将所捐献的器官与受赠者之间进行匹配。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应规定器官移植的管理机构,建立全国性的信息共享网络,进行器官信息供需之间的快速的匹配。
(五)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提高器官捐赠意识
我国器官移植的困境还在于传统文化的约束。我国传统社会观念,排斥人体器官的捐献,于是,一边是焦急等待器官的病人,一边是有用的器官被化为灰烬。因此,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改变传统观念是解决人体器官捐赠困境的最根本的方法。
(责任编辑:王建民)
DF01
A
1674-9502(2013)02-101-06
国家法官学院
2013-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