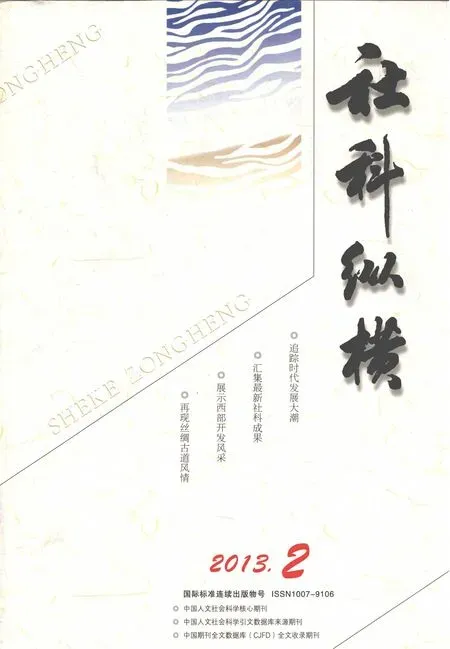回眸河西走廊60年新诗创作
2013-04-10保继霭
保继霭
(张掖中学 甘肃 张掖 734000)
当下,诗歌界都能感到甘肃的诗歌创作很活跃,无论说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都非常看好;无论是诗人还是诗评者,都显得强势而活跃,就像一座厚积薄发的高地正在崛起,合力塑造“诗歌大省”的形象,这其中就有河西诗人的积极努力。河西,是个狭长的走廊,也是块宽广的诗田。
河西的新诗创作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新时代的热情中,歌英雄、颂领袖、唱时代是当时的主旋律,文人的诗笔被人民的兴奋点感染着,歌颂劳动人民的齐心协力与冲天干劲,以及团结一致追赶经济建设的豪情,是那个年代诗歌的“大事”。李季和闻捷分别于1952年和1958年走进了河西走廊,他们站在河西走廊的一端,感悟于河西的山川风物与当时“跨越式前进”的豪情,写下了《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礼》《玉门诗抄》《玉门诗抄二集》《河西走廊行》等诗集。此外,他们将河西儿女的求索精神融进了《生活之歌》《复仇的火焰》《扬高传》等长诗中,还把河西生活的体验带进了《戈壁旅伴》《西苑草》等作品。李季和闻捷以河西生活为题材的诗歌,是河西新诗的预演,拉开了河西新诗创作的序幕。
在上世纪70年代,河西大地上才真正成长起来自己的诗人。是林染最早举起大纛的。林染来自河南,一到河西就扎下了生命的根,他很快就把灼热的情思谱写成诗篇,在国内广为传播,有的诗作还登载到了香港、台湾、美国、日本、新加坡的报刊上。林染的诗题材丰富,色彩繁复,意象瑰丽,浸染着西部本土色彩,从诗歌意象到诗中的精神以及人生体验,有一种矗立于旷野临风而立的浩气,也有清新细腻、冷静柔美的一面,在深邃浑阔的意境中徜徉着淡淡的忧伤。林染的诗不仅让读者领略了西部的大漠、戈壁、雪山、绿洲,凸显了河西人民的顽强、坚韧、婉丽、多情,还让读者认识了西北人的宗教情怀和敦煌情结,是河西诗歌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说林染了不起,不是因为林染以河西题材出版了《敦煌的月光》(1985)、《林染抒情诗选》(1988)、《相思路》(1988)等诗集,也不是因为林染不拘诗情、童心未泯,出版了儿童诗集《漂流瓶》(1993)、《秋天的朗诵》(2000)、《冬天的朗诵》(2000)、《国花国书歌谣》(2000),主要因为林染不仅用诗歌把河西带到了全国,带到了国外,还在于林染凭着在河西大地上的韧性和对“诗意地栖居”的执着,以河西大地上的“恋乡”情结和突围困境的忧思为“燃料”,把河西人表达新时代、新生活带来的新烦恼、新困惑的情感触点给点亮了,促动了一大批新人开始突破“走廊”拘囿而吟咏赋诗,河西大地上出现了青年人谱写新诗的热潮。也可以说是林染把河西的诗谱给褥热了,提升了河西人借助诗歌描摹生活的自信。
从80年代初期开始,河西大地成长起来了一批热爱文学的青年,如江长胜、唐光玉、于进、张子选、古马、刘惠生、贺中、赵兴高、徐学等,他们相继出版了个人诗集,以勤奋与执着为河西新诗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期,河西的文学创作氛围愈演愈浓,武威、张掖、酒泉三地市及其所辖的部分县政府也陆续设立起了文联、作协,还办起了文学刊物,集结了一颗颗不甘寂寞的跳跃的心灵,播撒着一个个富有超越精神的梦想。这些音符相互感染着,弹拨着这片土地上栖居的意蕴,逐渐汇聚于挖掘美、关注价值的哲性高度。
进入90年代,河西的诗歌创作出现了“遍地开花”、“处处繁盛”的景象:像林染这样的“老诗人”笔力更健,硕果累累;像古马、梁积林、胡杨、孙江、倪长录等历练成熟的年轻诗人更是风头正健。新凸现出来的年轻诗人也势如春笋逢雨,活力无限。如张掖有王登学、苏黎、王振武、贺继新、杜曼、肖成年等;酒泉、玉门、敦煌一带有于刚、马兆玉、杨献平、万小雪、王新军、陈思侠、马旭租、旎姗、李茂锦、方健荣等;武威有谢荣胜、刘新吾、仁谦才华、齐鸿天、徐兆宝等;金昌有张精锐、阳山等。他们以文联、作协和地方刊物为依托,积极向省级、国家级刊物投稿,团结了数支诗风清新、风格各异的创作队伍,出版的诗集接二连三,积极为河西的文学锦上添花。新老诗人在反思生活和表达怀想上互相响应着,经常交流、勉励,激励着自己,也鼓励着身边的河西人。迄今为止,已有6人走进了《诗刊》社组织的“青春诗会”,50多人早已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诗歌,近30人出版了个人诗集。
还没出诗集(或正准备出版)的也诗心不眠,笔耕不辍,如妥清德、马克、李天银、王生福、雪山魂、俞中斌等,还有很多写诗的人,在此就不一一点将签到了。他们中每每有诗作被《诗选刊》《文化博览》等转载,入选《中国诗选》《中国诗歌选》《**年度最佳诗歌》《<星星>**年诗选》《<诗刊>**周年诗选》《**经典诗歌》《中国诗歌档案》《中国先锋诗人作品选》等,每每有人捧来省级、国家级的奖项时,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庞大的激情涌动的群体,他们热爱生命、缜密思考、乐观展望、积极抗争的诗歌尽显了河西人民朴实、真挚的情怀,充盈了河西文学的芬芳与力量。
在当今的河西,诗歌不仅是一道人文风景线,还是一种生命抗争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凸显着河西人民的理性诉求。河西人能把诗歌当成一种精神品质来追求,这当然不仅仅是李季、闻捷、林染这样的诗人起了带动作用,还有如下几方面的因素给了助力,当然也是河西诗人走向成熟的动力:
一是地域文化。河西走廊地域独特,文化驳杂。除了绵绵高山、巍巍雪峰、烈烈大漠、油油草原、脉脉河川,还有碧瓦蓝天、戈壁沙滩、雅丹地质、湿地公园、瑰丽胡杨。在这个走廊,曾有商队会馆、驼铃舟船,也有过发展经济、开发西北的“会战”,旧有丝绸之路的驿站,新有欧亚大陆桥的辙行;远有霍去病、汗血马的麾影,近有红西路军的功章;古有秦时明月汉时关的余光和“边塞诗人”的诗篇墨香,今有进军现代工业文明的钢城、镍都、卫星发射中心,以及塑造“铁人”精神的油田。在这里,有“坐佛”、“卧佛”的香烟,各宗教的寺庙佛龛,有敦煌、天梯山、榆林的洞藏,还有民间信仰的祠堂、广场;有牧民的歌舞和哨鞭,也有流传至今的戏曲小调、民歌民谣、“贤孝”“宝卷”……可谓是钟楼鼓楼坐中央,古城长城缀成片;城乡融合多民族,农工商牧齐灿然。河西走廊有深层积淀的儒道传统,有多民族融合的共荣历史,是一块名副其实的文化富矿。大自然和历史共同赋予了河西丰富的蕴藏,备足了河西人燃烧诗情的资源,寄予了感慨抒怀的契机,也敦促了河西人抒情写意的习惯。
二是差距感。河西走廊一方面墨守着大自然给予的特殊位置和状貌,包括物产、气候等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在新时期以来全国经济建设带来的快速变化中“甘”当了“后方”,在经济实力上、发展机遇上它忍受了与中东部发达地区的鸿沟。它贫瘠得那么坦然,孤独得那么真实,矜持地维系着与发达地区、发达城市的距离。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的时代,河西人能清楚地感受到:那个鸿沟随时随刻都在刺激着河西人的差距感,那种“不平衡感”随时随刻都在提醒着河西人“不平则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面对妖冶的世界,面对各种诱惑对河西人原本平静的心灵的冲击,河西人所面对的挑战和承受的压力,就变成了酝酿诗歌的一股动力。在这个空旷的河西走廊,人会变得渺小,如隔山赏景、临渊观物,而这份渺小感没把人压缩成猥琐的自卑者,反而放大了人的想象和梦想,他们已习惯了面对渺茫的怀想和忍受寂寞的遐思。可以说,有差别就会有动力,不作诗就无以表达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真实感受。距离感日积月累汇聚成笔端悬垂的墨露,催其写下在这片土地上的爱和忧思,助其淘洗生命的诗意。
三是自由意识。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在河西演绎了“美是自由的象征”之理念,追求自由成了河西人重要的精神导向。另外,甘肃诗人还较早地直接参与了朦胧诗的上演,朦胧诗的登场正是中国新诗乃至中国文学冲破禁锢的表现。1980年在兰州成立了当时全国第一个青年诗歌学术组织——“甘肃青年诗歌学会”,会员遍及全省各地,很快发展到4000余人,声势浩大,影响全国。这个学会带动了甘肃各地的诗歌创作。1981年秋天兰州的唐祈曾邀请了朦胧诗的“五虎上将”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来兰州参加诗会,顾城、舒婷虽没能来成,但是蔡其矫来了,他们沿着刘家峡、酒泉、玉门到达敦煌,在河西走廊把“诗会”变成了“诗游”,其行其景在河西刻下了追求自由、追求文学理想的深刻印象。另外,《飞天》《当代文艺思潮》和后来的《敦煌诗刊》的积极创办,以《飞天》“大学生诗苑”为核心的“大学生诗歌运动”,把林染、唐光玉、胡杨、漆进茂等河西的诗歌创作者,引到了李云鹏、何来、吴辰旭、李老乡、高戈、嘉昌、唐祈、孙克恒、谢昌余、高平、彭金山、张明廉、常文昌、叶知秋、管卫中、王若冰、马步升、邵宁宁等本省的诗人和评论家面前,甚至带到了叶延滨、王家新、于坚、西川、徐敬亚、欧阳江河等外省诗人的面前。河西诗歌创作被盛情带动着,紧紧跟随着文学自由、人性自由的步子,这是今天河西诗歌创作有“再生力”的重要因素。
四是平台支撑。河西在1978年就有了地方文学刊物《红柳》,由原武威地区(今武威市)文联主办,1980年公开发行(1996年停刊),1989年前最大发行量达5万余份。1979年《阳关》创刊,由原酒泉地区文联主办,1981年起面向全国公开发行,一直以“西部文学的园地,西部文化的窗口”为宗旨,刊发中国“欧亚大陆桥”沿线作者的作品,也积极刊发其他省作者的作品。接着河西各地县文联也有了自己的内部文学刊物,其中有:1982年原张掖地区文联的《甘泉》、1989年金昌市文联的《西风》、1989年民勤县文联的《柳笛》。90年代新办的有:1990年玉门市文联的《走廊》、1992年山丹县文联的《焉支山》、1999年原武威地区作协的《西凉文学》、1999年古浪县文化体育局主办的《古浪文苑》、1999年民乐县文联的《祁连风》。进入新世纪以来,还有2002年临泽县文联的《枣林》,2002年肃南县文联的《牧笛》,2003年张掖甘州区文联的《黑河水》,2003年酒泉市青少年文学社主办的《祁连山文学报》,2007年武威市凉州区文联的《凉州文艺》,2008年玉门市文联的《玉门文苑》,2009年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党河源》,2009年武威市诗词楹联学会的《天马诗刊》,2010年酒泉市文学创作编著协会的《新边塞》等。这些刊物都设置了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栏目;虽然大多为内部刊物,但它们栏目自由、广纳佳作、按期出刊、定期传阅,成为扶持和鼓励河西文学交流的重要平台,河西的许多作者,如荆歌、车前子、阎强国、雪漠、王新军等,都适时地找到了磨练的机会,在这些刊物上练硬了笔力、练足了信心,一步步成长为成熟作家。这些刊物为培养河西诗人、作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不能忽略河西的这些地方刊物为河西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个亲切、严肃、便捷的交流园地,为河西诗歌的走向成熟提供了锤炼的场所、提升的平台。
可以说,自建国以来,河西人逐渐增强了“诗”的意识,从刚开始个别人尝试新诗,到后来不仅写诗的人多了,而且读诗论诗、采风交流、出版诗集、聚会、办刊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诗”成了河西人现实生活中一种“形而上”的追求,说明河西人民不仅在发展着物质层面的生活高标,还在同步地提升自己的心志追求,在不断地丰富和建构着自己的精神世界。也即随着时代的前进,河西人民不但提高着物质生活,还改变着精神文化,不断地储备着精神力量。近60年来,河西人民生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丰裕度上,还体现在精神与心灵的饱满度上。因此说,河西人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作品,真实地记录了河西人民精神文化的嬗变,那些发自内心深处的歌吟不仅是时代变化的表征,更是精神诉求的印记,诸多精彩诗篇还投射了困于地域之限的河西人的心灵预期。所以,我们在高度肯定和评价河西诗歌的积极向上的同时,还应反思其亟待完善的成长空间,其中有三点需要明说:
其一,上文提到的这些诗人随着工作环境、时代感悟等的变化,有的抽身去别的工作了,有的坚守诗歌,专擅诗歌,还有的一边笃守着诗歌,一边“兼擅”着其他体裁。总体看来,诗歌的气脉不仅没有因为诗人地位、身份和生活境遇的变化以及市场经济中的物质媚惑和金钱崇拜而中断,反而扩容了多种形式,趋于“多元化”。但是,“多元”之中又有着视域窄、境界小、多重复的缺憾。河西诗歌的主题拓展不是太深,时有琐碎、零乱之感,对文化底蕴和时代特性挖掘也不够深刻,有打“擦边球”之嫌,多半诗歌缺乏一种雄浑、博大、厚重、深邃、贯通的大气。诗人中,感时伤物者多、孤寂慨叹者多、苍凉忧虑者多、沉重自赏者多、婉约阴柔者多。除个别诗人风格稳定,绝大多数诗人行进在不断探索的路上,给人的感觉是:还没把一类诗歌写成熟,就匆忙换成另一种风格的尝试了,从风格上没能体现出地域诗人的优势,似乎“没有特色”就是河西诗歌的“特色”,因此也就没能形成一种由“片”成“面”的“气候”。
其二,河西的少数民族作家也是一支“骁勇”的“生力军”。他们都是抒写本民族灵魂的佼佼者,均擅于汉语创作,大都钟情于诗歌的高贵。他们的文学作品反馈了在时代递进过程中的忧虑与阵痛,诗歌既是他们的血脉记录,也是表现他们怅惘和向往的最佳载体,在抒写民族文化传统、镌刻历史痕迹方面保留了浓缩的记忆和诗性向往的空间。他们的创作不仅给河西的诗歌创作注入了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民俗原浆,还从题材上、诗歌观念上丰富了河西诗歌的含量,反映了“众小民族”与“被包含”民族如何在有限的区域内承传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如何选择性地保存本民族文化记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推演民族文化精髓。但也应看到,多年来河西地区稳定地生活着蒙古族、回族、藏族、裕固族、哈萨克族、土族、满族、维吾尔族等近30个少数民族。按理说,民族越复杂,文化也越复杂;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和经济生产的竞争,民族间演绎“接触—冲突—融合”的故事也就多,因此作家作品也就多。然而目前河西走廊凸显出来的少数民族诗人、作家主要为裕固族和藏族,如裕固族的贺中、贺继新、妥清德、杜曼·叶尔江、玛尔简、达隆东智、苏柯静想等,藏族的仁谦才华、才旺瑙乳、旺秀才丹、刘树丙、王生福、雪山魂等。民族多而民族作家少,从文化繁荣、文学繁盛的角度来说,亦为憾事,这只能证明:在河西走廊民族“融合”得极为顺畅、少数民族“汉化”得极为深刻,河西各民族找到了共存共赢的合力。但是,少数民族作家有些嫌少,创作也欠活跃,所彰显出来的民族风情和民族文化特性也就很有限。各少数民族作家展露独特的风采,这应是我们从多民族文化共荣的角度对河西诗歌的一点期望。
其三,河西地区的女性作者也是不可忽略的,但力量需要扶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元素在河西走廊埋藏得深、流失得慢,“儒释道”、“官政商”与“迷信”观念糅合下的种种习俗成了河西人生存的法则和人际交往的模式,是维系稳定、谋求和谐的惯常“规矩”。譬如说河西地区“大男子主义”思想就比较明显。在“大男子主义”的影子下,女性创作就可能天然地受到压抑,就可能存在人性之释的偏颇,缺少“巾帼”“挥毫”的爽朗与豪气。她们的书写背景是乡村生活,沿着承袭已久的文化习俗,抒放着她们对新时代的理解,迎合着现代“女性主义”思想对她们的召唤,在嘈杂与喧闹中分辨着“半边天”的“园地”。河西的女作者只有言说的“细语”,没有响亮的“声音”,似乎对“话语权”极不自信,大都尚未成长为与世界“对话”的“女性作家”。虽有赵淑敏、万小雪、苏黎、刘梅花、旎珊、胡美英、邢剑丽、宋云等的积极努力,河西各县市文联、作协也都能列出一个女作者的清单,但是她们尚未在文坛上凸显出来,暂处于默默笔耕、悄悄地“跟随”状态。其实,倘若她们能抒写,也就能突破,突破旧习、突破男权、突破自我将是必由之路。女性创作是河西诗歌别样的审美维度,从她们身上也某种程度地显示了河西历史文化的变迁,反映了河西走廊的现代化程度。因此,我们应该鼓励她们更为活跃、更为自由、更为个性地表达。
生活安逸,对“命运”脱敏的人是很难写出大悲怆、大悲悯的诗歌的。河西人能在朴素中秀出庄重,写出渗透了大悲、大爱、大忧的作品,这不是偶然,这是历史、时代、地域现状共同促成的机缘,是这份机缘赋予了河西人正视生命、正视现实、正视自我的惯性和意识。这种“正视”的延续,也正是河西人在当今社会里抚慰理想、积极抗争的精神支撑。河西的诗人虽没有抱团形成一个宗旨明确、理念统一的流派,也没有死拽“边塞诗派”的尾巴苦吟边缘意识,他们坦然地站在河西大地上,站在青藏高原的山坡上,站在生命的中间,秉持柔中带刚的个性,裹挟着地域文化和时代的召唤,以真情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积极理念畅想着崭新的明天,正在把河西的诗歌创作捧向一个新的高峰。他们挥洒着与天水诗歌、陇东诗歌、陇南诗歌、甘南诗歌、兰州诗歌别样的诗笔,各展技艺,绘织着河西走廊上新的诗歌风景线。他们的创作为表现河西的民风民俗和“走廊文化”付出了努力,为挖掘河西大地上的精神资源做出了贡献,他们的诗歌是甘肃诗歌乃至中国当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容忽略的一笔精神财富。河西诗歌正在走向成熟,河西诗人必将成为当代中国诗坛的一支“劲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