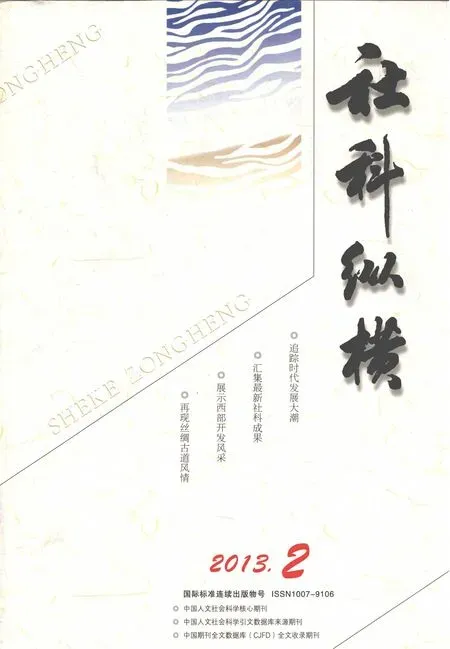略论发遣刑与清代的边疆开发
2013-04-10刘炳涛
刘炳涛
(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我国古代的刑罚中,有一类刑罚是把犯人发往边疆地区服刑。这类刑罚在历朝历代名称不一,有迁、徙、徙边、流放、长流、充军、发配、发边外为民等说法,但从刑罚种类上来区分,都可以归入流刑。这些被流放到边疆的犯人是很多的,他们虽为罪犯,但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到了清代,除原有的流刑、充军外,又出现了发遣刑,明确规定把犯人发往北部边疆,使清代留驻边疆的犯人大增,为我国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便着力阐述发遣刑对清代边疆开发的意义,使那些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的遣犯们能够不被人们所遗忘。
一、发遣刑的含义与特征
在清代,发遣一词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发配,作动词用,指把军犯和流犯发到指定地点服役。《大清律例·名例·犯罪免发遣》条规定:“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军流徒免发遣,分别枷号。”这里发遣就是指发配。在清代的条例中“照例发遣”之类的用语较多,即是把罪犯照条例前面所定的刑罚发配。其二,即是指一种特殊的刑罚,指把罪犯发往东北地区或新疆分别当差、为奴,被发遣的罪犯则称为遣犯。按照《清会典》的解释,发遣刑是“发往黑龙江、吉林、伊犁、迪化等处,酌量地方大小,均匀安插,分别当差、为奴。” 由此可见,发遣有着特定的含义和特点,与充军和流刑有着一定的区别。
第一,发遣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在五刑之中,流刑本来是仅次于死刑的刑罚,明清充军比流刑为重,而发遣比充军更重,原因在于发往边疆与当差、为奴相结合所产生的惩罚功能更强。发遣为奴人犯在到配后一般被分给当地驻防兵丁或少数民族群众为奴,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生活待遇,均极为低下。为奴实际上是清代入关前的奴仆制度的延续,在入关之后,又结合前代的统治手段,将其正式法律化,制度化。
第二,发遣地点固定为东北地区和新疆两大地区。从清初到乾隆中期,遣犯主要发往东北地区,并且逐渐由南向北转移。清初,遣犯大多发往尚阳堡、盛京、辽阳、铁岭,以后渐次向吉林、黑龙江方向扩展。乾隆中期,新疆纳入清朝版图,清廷开始把遣犯大规模地发往该地。新疆的主要发遣地是伊犁和乌鲁木齐两处,此外还有巴里坤、哈密、南疆各回城等地方。遣犯发往东北与新疆是发遣与充军的重要区别。“军罪虽发极边烟瘴,仍在内地,遣罪则发于边外极苦之地,所谓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者,此军与遣之分别也。”[1](P9955)从乾隆朝开始,发遣新疆、发遣黑龙江与充军极边烟瘴相互调整,共同组成了清代的边疆流放体系。
第三,遣犯服刑的主要方式是当差和为奴,在新疆还有种地一项。这是与军流罪的又一重要区别。流犯到配后官府对其稍加约束,听其自谋生计,没有实际的刑罚约束内容。军犯的情况与此没有实质差别。明朝实行的是卫所制和军伍世袭制,军犯要入军籍为兵,而清朝实行八旗和绿营兵制,废除了卫所制,士兵的来源固定,罪犯被充军后不可能再入伍当兵,只能由配所州县进行管束。与军流犯相比,遣犯到配后当差,给士兵为奴役使,实际是服劳役,有具体的刑罚执行内容。在清廷看来,这样能有效地惩治罪犯,所以发遣受到统治者的青睐,成为常用刑,适用范围渐广。
第四,发遣刑不仅仅是一种刑罚,还具有移民法的性质。发遣刑出现于顺治朝后期,在立法上正式确立是在康熙十九年颁行的《刑部现行则例》。此后到乾隆朝,不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发遣刑的规定与使用逐渐完善。乾隆中期,新疆纳入版图,朝廷制定条例开始规定向新疆发遣人犯,以补充当地的劳动力。为增加人口和防止遣犯脱逃,还规定家属同遣之制。光绪年间,为补充因新疆战乱而丧失的劳动力,修改遣犯安置办法,新疆遣犯照民屯章程办理。由此,发遣刑的刑罚惩罚功能减弱,而移民实边发展当地经济的功能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发遣刑的执行过程中,并没有规定遣犯统一的服刑期限,而是根据对遣犯的役使形式和发遣地的不同,规定了不同发遣年限及遣犯的不同出路。其中,一小部分遣犯永远为奴,另有一部分遣犯因立功和服役十年以上回原籍为民,大部分遣犯则是在服役三年、五年、十年后在当地为民,不准回原籍。乾隆三十一年,规定乌鲁木齐遣犯“有家属者,查系原犯死罪减等发遣者,定限五年,原犯军流改发,及种地当差者,定限三年,如果并无过犯,编入民册。”[2](卷744)乾隆五十三年,清廷又延长了为民期限。“发往伊犁、乌鲁木齐为奴遣犯在配安分已逾十年,令其永远种地,不得为民。若发往当差遣犯果能悔过悛改,定限五年,编入该处民户册内,给与地亩,令其耕种纳粮,俱不准回籍。其有捐资入铅铁等厂效力者……如系为奴人犯,入厂五年期满,只准为民,改入该处民户册内,不准回籍。”[2](卷742)准入民籍意味着在边地落户为民,不能再回到原籍。为充实新疆人口,对于为民遣犯清廷给予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比如把遣犯眷属官费资送到遣犯所在地,贷拨给遣犯生产生活资料使其能够生活下去。以上措施施行后,不断有遣犯附籍为民。据记载,乾隆四十三年乌鲁木齐一地就有为民遣犯一千二百四十二户[3](P59)。遣犯为民后,多从事农业生产,逐渐成为新疆土著居民。
总之,从历史上看,清代的移民规模是非常大的,这其中既有内地之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有内地向边疆的人口迁移。在后一种移民中,既有自愿的,也有被迫的,而发遣就是被动的一种移民方式。因发遣而移民的流向主要是两大发遣地东北和新疆。东北地区由于是满族的发源地,清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禁止内地民众向东北迁徙,对东北实施封禁政策。从清初就开始的发遣把大量不愿迁移的罪犯发往东北,这些罪犯大部分不再回内地,而是成为当地居民,间接促进了东北地区人口的缓慢增长。与东北相反,清廷对向西北的移民却大加鼓励,从罪犯发遣新疆开始,就带有增加新疆人口的目的。经过不断发遣,遣犯及其家属在新疆人数之多,实为历史上所罕见。纪昀在遣戍乌鲁木齐期间所写的《乌鲁木齐杂诗》之一“鳞鳞小屋似蜂衙,都是新屯遣户家。斜照衍山门早掩,晚风时袅一枚花”的景象,就是遣犯移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清朝利用发遣刑来促进边疆的发展,取得了成功。
二、发遣刑对清代边疆开发的意义
对于遣犯个人及其家属来说,发遣是降死一等的重刑,意味着受苦受难,但是如果把发遣刑放到边疆开发的大环境下,它对我国东北和西北边疆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第一,增加了边疆地区的人口,为边疆开发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东北地区经过明末长期的战乱和满洲人的大量入关,人口稀少,而清廷采取的封禁政策又限制了内地人口向东北迁徙,使东北人口不能大量增加。新疆经过清廷与准噶尔部的长期战争,也是人口凋零,一片荒凉景象。把遣犯发往边疆地区,正好弥补了当地人口一定程度的不足。在发遣的高峰期,遣犯本人加上家属,一次发遣人数常至数百人以上。乾隆中期,今齐齐哈尔一地就有遣犯三千多名。光绪九年,黑龙江将军咨呈军机处称该省历年接收遣犯二万六千多名[4](P1122),新疆的遣犯数目当不必此少。据估计,清代发往新疆的遣犯及其家属的总人数约在十万至十六万之间[5](P142)。如果东北和新疆两地遣犯加在一起,当有数十万人。考虑到当时整个边疆地区地广人稀的状况,这个数量应当说是很大的。这么多的人口改变了边疆劳动力不足的状况,为边疆发展提供了比较充足的人力资源。
第二,为抵抗侵略、巩固边疆地区的国防作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年间,沙俄侵略东北地区,当时有大批遣犯被编入水师营、火器营中充当水手和匠役,他们为抗俄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乾隆十年,黑龙江将军疏称:“本处水师营内发遣当差人犯,俱系顺治、康熙年间,发宁古塔等处安插之人。后征俄罗斯,作为鸟枪、水师二项兵出征,凯旋后编为六个佐领,令入旗披甲,录用官员。”[6](卷243)道光二十七年,南疆和卓后裔叛乱,有遣犯数千人随清军作战,为平叛作出了贡献。清廷“以随征回匪有力,释回遣犯一千一百七十四名”[7](卷449)。道光二十八年,“以派赴巴尔楚克防堵出力,释回遣犯五百名”[7](卷445)以上史实说明,遣犯为保卫祖国的北部、西部边疆,反击外国侵略、巩固祖国的国防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三,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北部边疆经济上较内地落后很多,遣犯通过艰辛的劳动,为改变边疆的落后面貌,促进边疆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首先是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发往东三省和新疆的遣犯,无论为奴、当差,大部分从事的仍是农业生产。在新疆,种地遣犯被组织在一起,专门进行屯田,形成了“犯屯”这一新的屯田形式。通过遣犯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共同努力,边疆的土地被大量开垦,粮食产量和品种显著增加,农业生产技术与工具得到了改进。有学者经过调查,指出乾隆四十二年时,新疆“南北两路兵、犯垦地共二十八万二千六百余亩”[8](P278)。粮食产量的增加,使“天下粮价之贱,无逾乌鲁木齐者”[3](P172),这其中自然有遣犯的一份功劳。其次,促进了手工业和矿冶业的发展。发往边疆的遣犯,有很多具有手工业技术,在服役的过程中,他们把这些技术传承给当地,改变了边地技术落后的状况。发往新疆充当苦差的遣犯,从事挖矿、冶炼铜铁等最为艰苦的劳动,为新疆矿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四,促进了边疆地区文化的发展。边疆地区不仅经济落后,文化也很落后。遣犯中有不少文人,即举贡生监。职官或举贡生监,都是清代社会中有身份的人,他们一般并不发遣为奴,而是当差,从而有较多的时间传播文化知识,为改变边疆地区文化落后面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这些人士中,最著名者当属康熙时著名学者陈梦雷。康熙二十一年,陈梦雷因三藩之乱的牵连被从重发往盛京给新满洲披甲为奴。他到配后,“诸公卿子弟执经问字者踵接”[4](P972),促进了盛京地区文风的转变,从而改变了该地文化荒芜的面貌。此外,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文人,在发遣地传经授徒,也对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发遣刑是清代独具特色的刑罚,它既有刑罚的功能,也有移民的作用。对个人来说,它刑罚残酷,对国家来说,它功劳甚大。我们在评价它的时候,既要看到它落后的一面,更要看到它移民实边,促进边疆地区发展的一面。
[1]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2]昆冈.清会典事例[M].北京:中华书局,1991.
[3]王希隆.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4]李兴盛.中国流人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
[5]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
[6]董诰.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花沙纳.清宣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