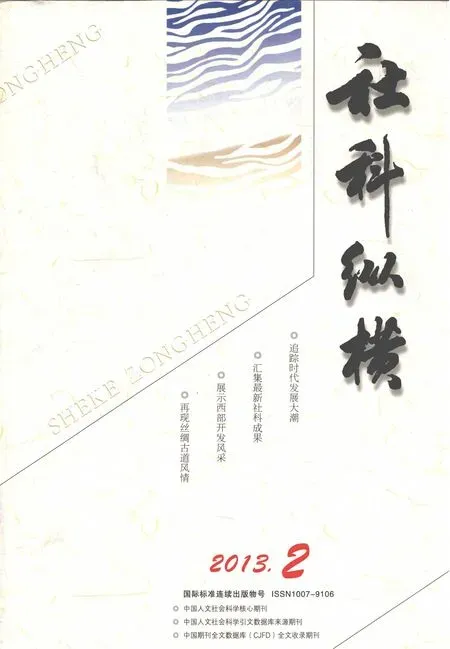祭拜、认同与大、小传统互构①——以关中Y村为例
2013-04-10董敬畏
董敬畏
(浙江行政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一、问题缘起
信仰与仪式问题作为社会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的核心话题之一历来受到关注,学者们试图借此视角检视人类社会,分析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社会学研究制度性宗教,而人类学则以民间信仰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尤其是当面对中国这个复杂文明缺乏西方的制度性宗教时,国内外学者就把民间信仰当成与西方制度性宗教相似的社会制度来进行研究,杨庆堃称之为“分散型宗教”[1]。学者们借中国民间信仰研究,既检视西方的宗教研究,同时也希冀理解中国社会及其文明。
然而检视已有研究之后我们发现,有关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依然还未脱离涂尔干宗教与社会研究的传统(涂尔干,1999)。学者们大都从制度性宗教的思路出发,重点研究民间信仰的功能、组织架构、仪式过程等(韦伯,2003;弗里德曼,1974;武雅士,1974;韩森,1999;杨庆堃,2007;杜赞奇,1994);也有一些学者关注民间信仰与中华帝国政权之间的关系(华生,2006;科大卫,2007;王斯福,2008);还有一些学者关注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的关系(陈春声,2003;郑振满,2009)。这些已有研究都力图在中国文化的本土逻辑中,阐释民间信仰,理解中国社会性质,然而却并不尽如人意。比如对于民间信仰与中华帝国政权之间关系的研究,依然延续制度性宗教研究的逻辑,从文化认同及社会统合角度考察民间信仰的研究如凤毛麟角。加之中国地域广阔,各区域之间的文化习俗和民间信仰又不尽相同,因此即使对文化认同及社会统合有过论述,深度也欠缺。
笔者试图通过关中社会Y村民间祭拜中展演出来的大、小文化传统的关系,讨论中国社会中的文化认同及社会统合问题。通过Y村祭拜的考察,笔者认为民间信仰与仪式不仅是一种文化一统的建构过程,更是大、小文化传统相互形构的过程。经由这种互构,不仅大传统代表的国家意识形态在村落赢得民众认同,国家整体层面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层面维系了统一,而且小传统也获得了自身再生产的动力。
二、Y村地景
Y村位于关中平原的东部,由村子再向东可达渭南,向西可达泾阳,向南可达蓝田和长安,向北可达富平。村子座落于东经109`5`49~109`27`50之间,年平均气温约13.5摄氏度,年降水量约604毫米,年日照时数为约2000小时,年无霜期约219天。
Y自然村隶属于XK街道办S村村民委员会,包括四个村民小组,314户居民,1256人,1444亩耕地。因为土壤肥沃,村落的人们都以农耕为主,精细农业技术较发达。Y村土地包括水田和旱田。水田在村落的下方位置,旱田在村落的上方位置,村落位于水田和旱田中间位置。旱田除了种植一些耐旱作物之外,基本摞荒。Y村水田以前靠引附近的河水进行灌溉,后来人们普遍使用机井进行灌溉,水田的作物成为人们生计的主要来源。
Y村人们也发展畜牧业作为副业,主要是养牛和羊。牛奶和羊奶卖给乳品厂,间或可以卖牛肉和羊肉。水田中的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旱田作物以棉花、油菜、芝麻为主。Y村一年有冬小麦和秋玉米两季收获。收获和播种庄稼时,区内的家户习惯三五户组成合作单位,共同应对农忙时劳力不足的问题。
Y村是一个移民形成的村落社会。通过县志记载我们发现:Y村形成于明后期,祖先因为被皇帝罢官、流放,到Y村这个地方,觉得环境不错,就住了下来。
Y姓祖先买下村子的地,祖先有四个儿子,成家立业之后每人分得一块,四个儿子根据哥东弟西,哥南弟北的居处原则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小世系群。Y村仍然同祭一个祖先,共用一个公共墓地,全村人也共同排辈论号。通过祭祀,Y村形成一个共同体的生存样态。
今天的Y村被两条国道夹在中间,东面是西临线,西面是西韩线,塬上5里陇海线由村旁经过。Y村离西韩线只有10分钟左右路程,由西韩线坐车可以四通八达。尽管Y村离西临线较远,然而因为行政上属于XK管辖,所以人们也和它有紧密的关联。村子的公共事务、民众的户籍事务等都要到XK镇去办,因此XK镇也是人们经常去的集镇之一。
由此,Y村周围有三个集镇圈,BQ区的BQ镇、GL县的GZ、LT区XK镇。三个集墟日期各不相同,BQ镇每周日一次,GZ每逢公历 1、4、7一次,XK镇每逢公历3、6、9一次。三个集市中,GZ离Y村最远,大约有15里。XK镇次之,10里。BQ最近4里地。
三、Y村的祭拜传统
Y村历史上民众的祭拜对象包括祖先、村落神灵等,民众首先祭拜的是祖先。作为单系继嗣群,Y村民众认为逝世的祖先依然是他们的亲人,与他们离得很近,也时刻关注他们的生活。因此逢年过节,活人做什么,祖先也要做什么。只有有了祖先的护佑,后代子孙才能兴旺发达。
祖先也是由活着的人经过死亡变成的。因此Y村民众对于祖先的祭拜,首先从丧葬开始。在Y村,传统的丧葬分三个阶段,分别是报丧与入殓、搭灵堂与迎魂、奠酒与披红②。在这三个阶段,民众当着村落其他人的面,多次表达自己对于父母及祖先的敬意。逢年过节时,祖先都会被请回家来和家人团聚。每年清明和农历十月一,民众都要给祖先烧纸,因为天气变了,祖先需要钱财买衣服穿。
村落民众祭拜的神灵是“大婆”。大婆庙位于Y村黄土台塬最高处,里面供奉着以孝出名,被村人敬奉的外来媳妇。村人告诉我,“大婆”是附近村落嫁到Y村的媳妇。她孝敬公公婆婆,是村里有名的孝媳。村人说就因为孝,她家庭和睦,子孙满堂。后来她七十岁时某天,儿子和一名村人陪同去庙里拜佛,回家之后当天晚上,村人就看到她家有祥光笼罩,儿子晚上向母亲请安时,发现母亲即大婆已经坐在床上“坐活了”(羽化)。死后她还在村落中屡屡显灵,帮助那些有孝行的村人。也不知从何时起,村人修庙纪念她。因为她屡屡显灵,声名卓著,十里八乡的民众都到这里来祭拜她。传统时期也有官员参与祭拜,现在则以乡镇及村委会名义举办庙会进行纪念。
另外,村落中还有一些其它的民间信仰和祭拜的存在。比如对于药王孙思邈的祭拜。孙思邈是唐代的著名医生,同时也是道士,出生于陕西耀县,后来陕西多处可见对他的祭拜。村人对于他的祭拜,多于孩子出天花时,家中有人生病时。
村落所有民间信仰和祭拜在解放后都戛然而止了。根据国家的宣传,这些都是民间迷信,是统治阶级用来压迫民众的工具。祖先祭拜不再被允许,大婆庙及其它的庙观全部被拆掉。而且国家通过各种政治运动,既宣传又给民众以精神和生活双重压力。这种情况下,村落中的祭拜从此逐渐消失。国家官员的委任一直深入到村里,深入到民众的家庭中,试图通过此种方式完成近代以来一直在进行的国家重建(state building)。国家以行政权力统合所有资源的方式,把自己塑造为神,认为自己可以解决民众日常生活中所有的问题,从而打破了传统帝国对于基层社会的统合方式:即从文化层面进行统合而非直接从政治层面进行统合。
村落祭拜在改革开放及分田到户以后又重新开始出现。随着国家改革的逐步推进,以前深入到村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国家权力开始逐步退出,国家对于民众来说,再也不是神,它也没有能力主管民众的一切。由此村落的祭拜传统重新又开始逐渐恢复。首先是村落中一些个体,重新开始大操大办丧葬。慢慢地,普通民众也敢在节日里公开给祖先烧纸了,再过后不久,村里的庙会以搞活经济的名义恢复了。1990年代初期恢复的庙会依然称为“大婆庙会”,时间定为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五,由村委会出面主办,乡镇协办,经费来自于村民和企业捐助。Y村目前的祭拜大致就两这种。
四、Y村当前的祭拜
Y村当前的祭拜,除了个体祖先祭拜之外,就是村落集体对大婆的祭拜了。下面笔者先描述一下当前村落的祭拜及其变化,然后对此加以分析。
首先,在祖先祭拜的过程中,国家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在国家放松对于民间的控制之后,国家权力通过自己前一阶段的控制,已经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打下意识形态很深的烙印。这体现在恢复的祭拜仪式当中。
首先,报丧与入殓阶段,一般民众不再像从前一样,请秦腔戏班和唢呐吹手。在陕西关中地区的丧葬过程中,以前在报丧与入殓阶段秦腔戏班和唢呐吹手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使用高音喇叭播放国家规定的哀乐。另外,报丧的人现在会追赶时髦,说给自己亲人开追悼会。其次,在搭灵堂与迎魂阶段,现在增加了一个由村人或者其他地位比较高的人致悼词阶段,悼词的内容一般是有关死者如何为村里做贡献,如何在村里与人为善,如何教育孩子使得孩子成为栋梁之材等等。在迎魂的过程中,唢呐被洋鼓洋号取尔代之。这些乐队吹奏的不再是传统的丧曲,而是一些象征国家的曲目。比如血染的风采、春天的故事、长城长等。问他们为什么不吹一些传统的曲目,他们说那些曲目不上档次。在奠酒与披红阶段,本意是要表彰子孙对于老人的孝敬,现在则增加了子孙如何成材、为国效力的内容。
其次是七星庙会对大婆的祭拜。重建后的七星庙内部格局如下:最当中,坐着以孝敬闻名的神,她的左右手各是一个不知名的神,村人说那是土地神和财神,这三个神统一坐北朝南。神像的最上面挂一横幅“有求必应”,两边对联左边是“仁孝节义,人人得而敬之”,右手边是“忠诚爱国,人人得而礼之”。神的面前,有一个大的香炉,供民众烧香。香炉旁边是民众摆放祭品的地方。
在三个神的左右手两边,又各是四个童子模样的人,左手边一男一女,面向西方站立。右手边一男一女,面向东方站立。左手边男的手持“孝”的木板,女的拿“忠”的木板;右手边男的拿“勇”的木板,女的拿“仁”的木板。
大婆庙会复办的第一年,向每户村民征收10元钱的会费,不设上限。会费表示你对神尽义务,神对你有责任,这10元钱在本质上是一种区别村落社群内外边界的手段和方式。除了向每位村民征收之外,在每年过庙会的时候,村里所有的村办企业都需要自发向庙会组委会捐助。这种捐助村里会仔细地把捐助数额用本子记下来,庙会每年的账目都会公布出来,让民众心中有杆称。笔者接触的民众都说给神的钱不敢贪,那是功德。
大婆庙的祭拜开始时都是村里的老人,村里的年青人最初因为受到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一直认为那是封建迷信。然而最近两年有所变化,青年人也慢慢多了起来,原因在于庙会宣传的一些东西与正统意识形态宣传的多有重合。大婆庙神的祭拜,也是模仿电视上的形式,首先是村里的领导单独上香,然后是村民集体上香。村民集体上香时,站上四五排,每排七八个人,然后在神像前手拿点燃的香火三鞠躬,然后把香火插在香炉当中即可。如果有人有特殊的需要,可以在集体祭拜完成之后,再单独买香,单独祭拜。村民集体上香祭拜时,旁边有专门司仪,指导民众的祭拜,这个司仪是几十年前Y村被批斗致死的村中老司仪的儿子,村民称他为“贺礼生”。
正如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描述的那样:“一方面,个体从社会那里获得了其本身的精华,这给了他与众不同的特性和相对于其他存在的特殊地位,给了他知识文化和道德文化,…另一方面,社会也只有在个体之中并通过个体才能存在和生存”,“只有通过共同行动,社会才能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赢得自身的地位……”[2](P455,552)Y村民众通过祭拜的方式,获得了村落的集体人格,从而也彰显了个体的存在。
然而,从上述角度分析并不是我们的重点。恢复之后的村落祭拜,在笔者看来,依然延续了大、小传统互构的形态,这种形态在祭拜过程中有明显的表现,下面我们对此进行分析。
五、大传统VS小传统
雷德菲尔德在《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农民社会与文化)中认为研究复杂社会的学者们要注意乡民与士绅、农村与城市、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在他看来,小传统是乡民社会中一般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大传统则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以绅士和官员及政府为支撑的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两种传统依靠不同的方式流存,大传统的成长与发展主要依靠文字、教育;而小传统基本上是通过口传的生活实践在乡村中传播(Redfield 1969)。
在中国基层乡村中,大、小传统的关系是笔者试图想在本文中讨论的话题。Y村的祭拜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因素:一是“祖先”和“神”在民众观念和事实中的存在。二是国家权力若隐若现地存在于类似祭拜活动中,并企图使祭拜带上自己的印记,符合自己的意图。三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干预后,国家重新认识到民间小传统的功能,重新开始在尊重民间小传统的前提下,利用各种手段引导民众接受大传统的理念,从而在事实上维护大传统。这种情况下,小传统在大传统的影响下也开始发生变迁,最终导致大、小传统的互构。
丧葬仪式三个阶段中,每个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大传统的影子。比如丧葬第一阶段,人们逐渐以追悼会取代原来的报丧。丧葬第二阶段,开始有了致悼词的做法。第三阶段,在表彰儿女孝的过程中,增加了孩子为国效力的内容。这些都体现了国家提倡的移风易俗的效果。
七星庙的祭拜中,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出大传统的影响。无论是从庙中神的位序还是民众对于神的祭拜方式还是庙中文字,都能明显地看出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庙会的主办方及领导先拜的形式,无不给村落民众以国家在场的感觉。
而村落的小传统也依然故我。尽管国家提倡移风易俗多年,然而一旦高压的行政力量稍有松懈,民间传统就开始重新出现。尽管这种重新出现是“旧瓶装新酒”,然而只要旧瓶仍在,新酒也一定只是一种变迁之后的混合物。这一点我们从Y村的祭拜中也可解读出来。比如,在对祖先的祭拜中,原有的三个阶段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其中的某些细节内容。在七星庙会的祭拜中,人们依然存有“孝、忠、勇、义”的观念,依然对“有求必应”感兴趣。依然有香火的观念。
Y村大、小传统的互构,既是国家力量与民间社会相互博弈的写照,同时也是大、小传统互构、影响的深描。在博弈和互构的过程中,二者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种局面是以国家承认小传统的合法性,并且尊重和引导小传统为前提的。同时,小传统对于国家权力的在场,也采取承认的态度,从而使得二者共同在Y村祭拜的场域中和平共处。
六、讨论
对于Y村民众来说,“祖先”和“神”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处于重要地位。神和祖先无时无刻不在监督着他们的生活,对于Y村村民来说,他们需要公开祭拜神和祖先,才能取得生活中的平安,获取他们的保佑。一方面,这是民众通过祭拜企图获取的超自然力的保护。而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村落集体的行动,他们达成了一种村落公共性文化:即像涂尔干分析的,村落的社会性存在。村落的这种社会性存在,对于个体来说,就是一种公共性。“不管宗教仪典的重要性是多么小,它能使群体诉诸行动,能使群体集合起来,举行仪式。所以说,宗教仪典的首要作用就是使个体聚焦起来,加深个体之间的关系,使彼此更加亲密。”[2](P456)
正是因为Y村有了这种祭拜,村落的个体才在祭拜中明显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Y村集体的祭拜仪式重新塑造了村落的个体和群体,使得个体在面对外界的不确定时更加有信心,也使得村落更加团结,从而也创造了Y村的社会秩序。通过仪式和祭拜,Y村的个体重新获得了生活的意义。因为与神秘的力量(神力)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不仅个体得到了支持,而且个体与个体之间也树立了牢固的内群观念。通过祭拜,个体与村落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并且获得了自身的地位,由此产生了个体之间及个体与村落之间的合作。Y村的祭拜不仅巩固了村庄的团结和秩序,而且在精神层面再生产了村庄,再生产了村庄的公共性。
其次是国家的在场。现代国家不仅垄断着暴力工具,而且拥有不同程度的文化霸权。它不仅是政治共同体,也是意识共同体,是知识、规范的生产者和维护者,又是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源。它需要在意识形态层面塑造自己的合法性,因此国家需要把村民对于村落的忠诚转化为对于自己的忠诚。国家的转化逻辑与村落的转化逻辑相似。国家是由千万个村落组成,村落对于国家的认同就像Y村中个体对于村落的认同一样。只有把村落的内部认同转化为村落对于国家的认同,国家的合法性才可能成立。因此国家需要把各地的祭拜标准化和统一化,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间。
华生(James.Waston)曾经讨论过中国华南沿海地区的妈祖的祭拜。在他看来,国家通过把地方神转变为国家鼓励对于“允准”神灵的信仰,进而以巧妙的方式把某种统一强加于地方社会。“中国政府对文化整合的聪明之处在于:国家强加的是一个结构而不是内容。……很灵活,足以让社会等级各层次上的人都可以建构他们自己对国家允准神灵的看法。换一种说法,国家鼓励的是象征而不是信仰。”[3]
在Y村,国家通过文化层面大、小传统互构的方式,把民众的祭拜纳入到国家意识形态之中,从而确立国家在文化层面对村落的统合及村落对于国家的忠诚。与此同时,祭拜所产生的村落内部的秩序也得到国家的承认。而这种双重承认,则是建立在村落祭拜基础之上的。国家统合地方祭拜仪式,把自身的意识形态输入到小传统之中,再通过祭拜的转喻,把输入小传统的意识形态转化为自身合法性存在。通过祭拜场域的转化,不仅村落的秩序和团结得到维护,村落公共性得以确立,国家合法性及民众对于国家的忠诚也得以确认。
作为Y村普通的民众,他们生活在具体的村落,既是村落共同体的成员,需要对村落共同体保持认同和忠诚。但同时他们又是更大的大传统与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他们承载着地方的小传统,如何使地方小传统的成员及村落保持对更大的大传统与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呢?大传统在此采纳了与村落的小传统互构的方式推行这一认同与忠诚。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这种互构,是大传统对小传统的内容有选择的承认,并把它纳入到大传统的范畴中间,从而村落小传统不仅获得合法性,大传统也获得了村落的忠诚及自身的合法性。
在此,我们既可以说是大传统以退为进,尽管形式上大传统放松了对基层社会小传统的管制,然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大传统却重新获得了自己在乡村小传统中的存在。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基层民间小传统以一种配合大传统的方式延续了自身。正是这种大、小传统的互构,才使乡村的小传统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并且表现出村落特有的公共性。
注释:
①祭拜概念出自牛津大学科大卫教授(David Faure),笔者在此借用这一概念考察民间信仰中的祭祀,谨此向科大卫教授致谢.David·Faure.2007.Emperor and Ancestor: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②有关陕西丧葬仪式三个阶段的详细描述,可参见董敬畏.关中地区丧葬中互惠共同体[J].青海民族研究,2008(4).
[1]杨庆堃.范丽珠等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爱米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詹姆斯·沃森.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祭拜天后的鼓励[M].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8-83.
[4]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民间何在,谁在信仰[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高丙中.一座博物馆——庙宇建筑的民族志[J].社会学研究,2006(1).
[6]韩森.包伟民译.变迁之神[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7]马克斯·韦伯.王容芬译.儒教与道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王斯福.赵旭东译.帝国的隐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9]韦思谛.陈仲丹译.中国大众宗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0]科大卫(David Faure).Emperor and Ancestor: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J].中山大学学报,1995(5).
[11]Arthur P.Wolf.Belief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12]Donal·S·Sutton.Ritual,Cultural Standardization,and Orthopraxy in China:Reconsidering James L.Watson's Ideas。.Modern China(33),2007
[13]Robert Redfield.The little Community and Peasant and Cul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