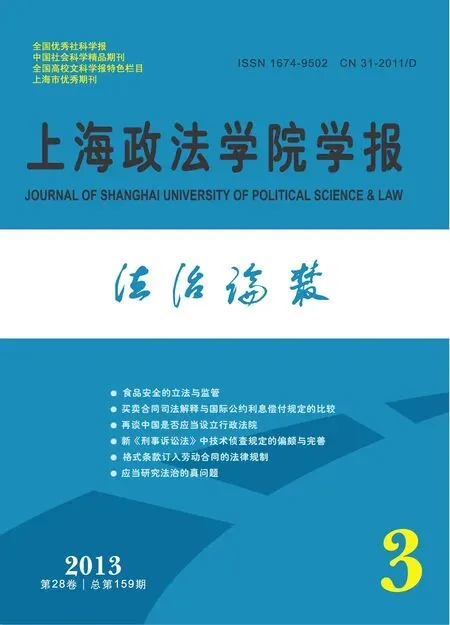论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共生效应
2013-04-10巩寒冰
巩寒冰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法学论坛
论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共生效应
巩寒冰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被告人供述证据因其直接证据的属性以及丰富的证据线索而为案件侦破提供了有力支持。在现行的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下,被告人供述证据的非法获得与使用滋生了严重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新《刑事诉讼法》仍旧立足原有司法体制土壤的孤立技术革新难以形成制度群的互补共生效应,制度的有效实施,不但需要本身逻辑的严谨,技术的精巧,更需要与之配套的外部环境,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运行必然依赖一系列与之配套的规则体系,讯问制度的规范化、透明化建构,辩护律师在场制度,法庭质证规则的直接言词表现,侦查人员出庭制度等,使之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形成一种共生效应,以此推动相关规则的落实运行。
被告人供述;刑讯逼供;案卷笔录;举证责任倒置;共生效应
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法律条文中确立已久,①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已明确了非法供述证据的排除规则。而从司法实践的反馈来看,这一规则仍未摆脱停留纸上的命运,②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77页下。法院系统就非法供述证据的排除也鲜见报端。③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2012年版,第72页。有学者认为两部具有司法解释效力的法律文件的颁行(即“两个规定”),“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框架结构已经初步形成”。④陈瑞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中国模式》,《中国法学》2010年第6期。时至今日,“两个规定”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际运行状况不容乐观,⑤杨学成:《“两个证据规定”执行中的问题与改进建议》,《人民法院报》2011年11月9日第6版。那么以此为基础建构起来的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及其相关条款在2013年之后将会呈现怎样的情况,非法供述证据在司法实践中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排除?对“刑讯逼供”的遏制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以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为框架的非法供述证据排除体系,能否通过对相关规则自身的逻辑严谨性和概念完善度的提升,而促进这一规则的实践运行状况呢?可以说一项制度的有效实施,不但需要其本身的逻辑严谨、设计合理,更需要有着与之相配套的外部环境,只有当相关制度形成了一种互补、互助的共生效应,⑥在自然界中,当一株植物单独生长时,显得矮小、单调,而与众多同类植物一起生长时,则根深叶茂,生机盎然;同样在人类群体中,英国卡迪文实验室从1901年至1982年先后出现了25位诺贝尔获奖者,便是“共生效应”一个杰出的典型。才能从根本上赋予制度体系以生命力,使其能够走上良性循环的演化道路。本文以共生效应原理探讨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自身及其外部环境的运行机制,分析以上问题。
一、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存在现状
(一)被告人供述证据获取过程的内部冲突
被告人供述通常包含丰富的案件信息,一方面被告人是犯罪事实的亲历者,由其提供的关于犯罪事实的陈述,常常包含所有犯罪事实的构成要件,成为控诉方指控犯罪的直接证据;另一方面被告人供述包含作案过程的部分甚至所有的细节信息,以犯罪过程的事实推进为主线“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在同周围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证据源。如在一起故意杀人案中,嫌疑人关于犯罪事实的过程陈述本身即构成了指控犯罪的直接证据,而同时其必然涉及犯罪使用工具的物证信息,往来犯罪现场路径上的足迹痕迹,犯罪预备阶段所遗留现场的唾液、烟头等证据信息,原始犯罪现场的指纹、血迹、毛发等证据信息等大量的间接证据。被告人供述证据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被告人供述证据的重要性也加剧了其获取主体间冲突的尖锐程度:获取被告人供述的直接、唯一途径,即是犯罪嫌疑人开口之述,因此在侦查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开口了”被认为是相关案件侦查的标志性事件。尤其是在公安机关案件侦破的行政压力下,尽快的、全面的获取嫌疑人供述成为侦查阶段的重要指标;而人类本能的趋利避害决定了陷入刑事追诉程序的被告人不可能总是自动、诚实的供述相关犯罪事实,逃避责任、虚构事实往往是一种常规现象。被告人供述证据的相关主体间的矛盾冲突也导致了刑讯逼供现象的屡禁不止。
(二)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重灾区
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现实层面的关注始于赵作海、佘祥林、杜培武等一系列冤案错案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实行10年之后的井喷式爆发,我国现行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受到了司法实践的严峻拷问,尤其是刑讯逼供问题,更是引发了来自社会舆论与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与忧虑,①赵作海、佘祥林、杜培武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产生,并由此引发的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实际上正式作为对相关事件的积极回应才催生了六部委《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被告人供述证据的违法性获取成为1996《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冤假错案的集中爆发点。在侦查实践中,突击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成为提供侦查线索、获取间接证据、实现案件侦破的核心环节,这一案件侦办思路在佘祥林杀妻案②http://baike.baidu.com/view/163011.htm,百度百科。中得到充分体现,在将重大嫌疑锁定佘后,侦查人员即通过刑讯逼供获取佘的有罪供述,而后依据其“犯罪过程”的具体描述,明确了“杀人工具”、“抛尸地点”,形成了“现场勘查笔录”、“被告人作案行走路线图”。以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为剧本,编排了佘祥林杀人过程的完整证据链条,此时冤案错案的发生已经并非基于合理的人为过失,而是肇始于政府的不法行为(检察机关或警察的不法行为)。③[美]吉姆·佩特罗、南希·佩特罗《冤案何以发生——导致冤假错案的八大司法迷信》,苑宁宁、陈效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页。正是以上“亡者归来”式的惨剧,引起了一切良知的不安和催发了改革的导火索,加之随着人权保障理念的深入确立、社会舆论监督制约力度的不断强化、法治国家的初步建立,刑讯逼供的严重违法性及在案件侦破过程中作用的局限性开始逐渐暴露,该系列冤假错案的集中爆发正是这一现状的体现,突破了社会容忍限度,使得非法供述证据排除问题成为1996《刑事诉讼法》实行过程中的重灾区。
(三)非法供述证据的存在现状的外部矛盾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生存现状的决定因素在于法庭质证环节的相关表现。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法庭裁判模式,使得被告人供述的质证过程表现为相关笔录的出示与宣读。法庭审判中对于供述证据的间接、书面审理方式,给侦查阶段的非法取证行为提供了滋生土壤,反过来刑讯逼供行为给本就缺乏稳定性的言词证据,造成了随意性的更多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公开、透明的庭审阶段成为辩护方重点发力的最后阶段,实践中“以刑讯为由的翻供策略”几乎成为一种常态,却无实际意义。司法解释确立了被告人庭前供述一致,而当庭推翻供述的情况下,优先采信庭前供述的规则,①参见《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尽管有学者分析“在公开法庭上……被告人更容易反悔当初的有罪供述,利用最后机会为自己做出辩解”,②陈瑞华:《论被告人口供规则》,《法学杂志》2012年第6期。但显而易见的是庭前供述的取得环境毕竟处于控诉方的有效控制下。刑讯逼供现象的普遍存在标志着非法供述证据的大规模使用,而如佘祥林、杜培武类被揭露出的冤案,毕竟仍属少数,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中,通过犯罪嫌疑人客体化,从直接突破口供入手获取证据是最为简单、便捷的,刑讯行为两千多年时间里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其可以保障一定程度上的实质真实,传统的控制犯罪职能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追诉了应当被追诉的人,而并不关注以何种方式追诉”,在该意义上讲,刑讯逼供所获得的非法供述证据甚至有益于快速、准确的侦破案件,因此控制犯罪的相对准确性掩盖了人权保障功能的丧失,在佘祥林杀妻案中,如非体制内来自政法委的行政干涉,仅刑讯逼供行为本身,并不足以导致冤案的产生,因此可以说佘祥林案暴露出的仅是非法供述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冰山一角,“尊重与保障人权”功能的实现仍然有赖于制度化的更加科学、合理的非法供述证据筛选模式。
二、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存在问题的反思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4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就“被告人供述证据”的非法获取规定了“刚性的程序违反惩罚机制”,通过遏制刑讯逼供、制约侦查权力,体现了吓阻警察违法的原理论;第56条第1、2款分别明确了“非法供述的法庭特别调查程序”以及“特别调查程序的启动标准问题”;第57条确立了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以及“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的规定;第58条再次重申了对于非法取得的被告供述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并规定了有利于辩护方的证明标准。以上规定构成了新《刑事诉讼法》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框架体系。其基本延续了2010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条文表述,但相较于德国《刑事诉讼法》、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在可操作性以及实际效果上,其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一)立法明确非法供述证据获取方法是否必要?
通说认为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规定存在以下问题。“刑讯逼供”概念本身不具有明确性。这一概念并不具有明确固定的指称内容,其同正常的审讯行为之间如何辨别,对“刑讯逼供”概念内涵、外延的明确性研究成为学界的关注焦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刑讯逼供等行为的指称范围;③第65条第2款“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以逼取供述的行为。”第3款“其他非法方法是指违法程度和对犯罪嫌疑人的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而迫使其违背意愿供述的方法。”在学界,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确立获取被告人供述的禁止手段应当立法包括,“酷刑,法律禁止的威胁、引诱、欺骗,测谎仪测试、麻醉分析、心理测试等有损记忆力、理解力的措施,违法羁押,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方法。”④兰跃军:《论言词证据之禁止——以<德国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分析》,《现代法学》2009年第1期。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司法解释至少应当明确包括,“使人身体产生较剧烈特通的肉刑,使人疲劳、饥渴的变相肉刑,使人意志力和判断力丧失的服用药物和催眠术,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方法。”①观点参见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2012年第1版,第69页。也有学者提出了一种过于中庸的看法“过于限缩的解释将放任司法实践中的‘隐形’刑讯逼供行为,而过于扩大的解释则会严重影响侦查机关的正常审讯工作”。②万毅:《论“刑讯逼供”的解释与认定——以两个证据规定的适用为中心》,《现代法学》2011年第3期。以上研究出于学术严谨及规范的考虑十分必要,但就非法供述证据的排除而言实无裨益,也反映了刑讯逼供现象的理论研究视角同司法实践的认定模式间存在偏差,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说明相关问题:
2012年4月开始审理的谢亚龙受贿案为非法供述证据排除的分析提供了实证思路,③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20428/034811948511.shtml,新浪网,2012年4月28日访问。也得以窥视“两个证据规定”时代,何以非供述证据在实践中遭遇难以排除的困境。在一审庭审时谢以遭受刑讯逼供不得不编造犯罪事实为由,推翻了大部分指控。谢称:“2010年9月4日,我是戴着头套、反戴着手铐被带上火车的。坐火车的时候,办案人员就不停地打我。在之后几天的审讯中,我被办案警察灌凉水、打耳光,他们还电击我的心脏……”当法庭要求谢进一步提供刑讯逼供相关证据时,谢又称:“接受审讯时就他一个人,并不能提供相关证据”。对此公诉方提供了一份谢收押辽宁省看守所时的体检报告。报告上“检查情况及结论”一栏注有谢体检时的体温、血压、脉搏等数据,并写着“神志清,查体合作,心肺正常。腹平坦,无压痛。全身无感染及外伤,四肢自如,神经系统正常。同意收押”等字样,并有谢亚龙本人签名。据此法庭认为,有办案人员和相关人员提供的多项证据、有体检报告等多项证据证实,谢前诉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
依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的规定,谢已经完成了有关人员、地点等线索材料的提供义务,但法庭依然依据在没有提供“讯问全程录音录像”、没有相关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甚至无法保证口供是否真正取得于“正式讯问程序中”(如,是否因押解途中的暴力、虐待导致了犯罪嫌疑人的恐惧心理而使其在收押看守所后的“正式讯问”中“自愿供述”),仅凭隶属于侦查机关的看守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就认为不存在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④“法庭依据侦查机关起草的‘情况说明’,法庭凭此驳回辩护方的非法证据排除动议,认定不存在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问题”这一情况是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38页。于此可以看出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在“两个证据规定”时代的呈现形式,相较于立法条文的规定以及理论的关注焦点,实践运行完全呈现另一种状态,一种完全脱离理论的实践运行,在当时情形下的理论研究根本无助于相关实践问题的解决。
毋庸置疑,即使刑事诉讼法建立了“刑讯逼供”概念的明确标准,进一步假设谢所遭受的正是典型的刑讯逼供行为,但从该案的法庭审理来看,仍然于事无补,法庭关注的焦点显然不是刑讯行为的定性问题。即使我国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确立了详细的、严格的供述证据的非法获取方式,清晰界定了刑讯逼供概念的外延与内涵,但如何证明仍是难以把控的,如谢案中的“情况说明”是否足以达到反驳“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非法取证行为”的内心确信,法庭开庭审判之前,犯罪嫌疑人处于漫长的未决羁押状态,在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同外界相隔绝,信息闭塞,即使遭受了酷刑、折磨等非人道方法的审讯行为,其固定、保留证据以在庭审时成功排除非法供述证据将是十分困难的;且如上文所说辩护律师翻供策略的常态化,一方面包含当事人的合理诉求,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用证据证实,将会给法官造成翻供是“辩护律师的拙劣技巧”的心理暗示,加之刑讯逼供含义模糊,造成了实践中辩护方“非法供述证据排除动议”难以获得法庭认可。
依据上述案例,来自侦控方的“情况说明”将说明重点置于明显的体表损伤检查,且不论大多数的刑讯行为不会造成明显的外表损伤,如有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人体极限范围内的不让休息,即使刑讯行为造成了肢体损伤或神经系统损伤,在漫长的审前羁押中,人体自身修复机能也会使相关证据“灭失”,在看守所仍隶属侦查机关的 “侦羁体制”下,相关“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客观性也值得怀疑。
(二)证明责任倒置的实际效果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将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证明责任倒置给控诉方,在被告人履行了“相关线索或者材料”提供义务后,由控诉方承担不存在非法获取被告人供述的证明,即证伪刑讯逼供行为。
1.证明责任的“实际承担者”常常是被告人。实践中,自“两个规定”颁布以来,法院认定供诉方提交的被告人供述笔录“无法排除刑讯逼供可能性”而裁定排除的,多基于嫌疑人明显的身体外伤。从该角度而言,非法供述证据的排除不是因为控诉方承担的证明责任未达到相关标准,而是嫌疑人自身的“伤痕”证据证明力太过强大,以至于法官、检察官、侦查人员均不能做出“合理解释”。
法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的倒置规定,在现实中演绎得颇有讽刺意味,实际上,嫌疑人以自身的“伤痕证据”承担着证明非法取证行为存在的证明责任。
2.举证责任倒置的形式性。在现行诉讼体制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新《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的条文表述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的相关规定,赋予控诉方的举证手段和证明要求都过于笼统,相关做法如侦查人员出庭、全程录音录像等并不具有成熟、健全的运行环境,其本身在司法实践中仍处于实验阶段,很难寄希望通过这些手段保障控诉方证明责任的实质意义。
3.“线索或材料”标准难以把握。新《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线索或者材料”标准因取消了“非法取证人员、时间”等的列举式规定而显得更加原则化、宽泛化。①新《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规定:“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②《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就“线索标准”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列举式规定。在此基础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8条的规定将相关标准予以细化,明确了检察院的受理程序,这一规定在操作性和人权保障方面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和内容等材料或者线索的”的提供仅仅作为一种启动标准,对于是否进行实质性审查,则语焉不详;同时,新《刑事诉讼法》中法庭的“合法性疑问”审查被取消,③《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经审查,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的规定,实质上将非法证据排除启动权交给了法庭。即非法证据排除动议一旦成立将直接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进而控诉方完全承担相关证明责任。这一规定无疑是悬在控方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其无法证明所提供证据的合法性,严重时将丧失成功指控的机会。在我国现有公检法三机关的独特架构体制下,公、检机关必然寻求方法抵制这一连锁反应的发生,法庭将受到来自公、检机关的强大压力而在一定程度上屈从于案件侦破目的,立法规定的随意性恰好给予了这一压力得以影响诉讼的条件,使得举证责任难以真正由控诉方承担。“合法性调查程序”的举证责任倒置对于发现刑讯逼供行为、排除非法供述证据所具有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立法仅表达了对于非法供述证据的排除态度。以上对于现阶段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中存在问题的分析,仍然暴露了确立该制度对于遏制刑讯逼供、贯彻正当程序理念的乏力表现,更深层次的是反映了当前理论研究以及问题的解决思路,同社会以及制度实践发生了偏离。
三、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共生效用
共生效用是自然界以及人类群体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现象。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刑事诉讼法》是由证据制度、辩护制度等一系列基本制度构成的,每个基本制度又包含了若干具体的规则,不同的具体规则之间即构成了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共生关系,一项规则的缺失常常引发一种连锁反应,甚至造成整个体系的崩溃,而一种规则的单独建立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一种现状,这也是上文谈及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进行了长达10余年的制度构建,却始终原地徘徊,无法切实发挥排除相关证据、遏制刑讯逼供、净化司法环境的作用。如,证人出庭制度的有效实行需要也依赖当庭质证制度的实施,而当庭质证制度则是同有效的辩护制度想关联的。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效用发挥,同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若是忽略了共生效应的作用机制,那么无论非法供述证据规则具有如何完善的逻辑结构以及精确的概念表述,其最后都难逃停留纸上的命运。我们因循共生效用的作用机理,研究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和使用环境,以此分析探讨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何以呈现以上现状。
(一)被告人供述证据的产生环境
被告人供述证据产生于侦查阶段的讯问过程中,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讯问等强制性措施的使用,由侦查机关自行批准和决定,缺乏事前的司法审查机制,对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非法言词证据在审查起诉阶段、法庭审判阶段缺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救济,由此通过讯问过程的刑讯逼供或变相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得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畅通无阻,于是“口供”的价值和证据地位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加强;加之“口供”获取的便捷性,一同滋生了刑讯逼供现象的内在动力,而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在侦查阶段又转化为各种形式的侦查线索,办案机关依据该线索完成了证据的采集和固定,形成了指控犯罪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链条,同时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未实质确立的现状,带来了侦查权任意形塑供述证据的可能,如“侦查阶段对前后取得的内容相互矛盾的被告人供述笔录只移送有利于支持犯罪指控的一份作为证据,不同证人作出的指向不一致的证人证言被侦查机关有选择的采纳而后移送”,①陈瑞华:《案卷移送制度的演变与反思》,《政法论坛》2012年第5期。由此也可理解非法供述证据为何排而不除、禁而不止。而在新《刑事诉讼法》中针对讯问环境的相关制度规定,并未得到实质纠正,如沉默权制度、辩护律师在场制度等仍未确立,单单依靠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身的逻辑搭建很难真正实现非法供述证据的有效排除。
(二)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庭运行环境
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作用阶段存在于法庭审判过程中,得益于这一阶段的公开透明以及当事人的有效参与,使得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共生效应问题在这一阶段得到了集中、全面的体现,本文选取以下几个角度对此展开分析,论述共生效应对于非法供述证据有效排除的实际意义。
1.供述证据合法性调查的证明标准问题
2012《刑事诉讼法》第57条立法将“供述合法性调查”的证明责任置于控诉方,但随之相伴的证明标准问题,法律规定模糊,上述案例反应的司法实践也证明了,独特的司法体制造成法庭倾向于相信采纳来自公安、检察机关的证明文件,造成了实践中,相关证明标准虚置,因此研究的重点应是如何明确一个相对规范、严格的控诉方证明标准,利于法官形成合理的内心确信,如英国法院在就非法供述证据排除判例中所反映出来的英国法官关于控诉方证明标准的一个相对具体的审查角度,包括“审查有无暴力或者暴力威胁,讯问延续时间长度,两次讯问之间间隔的时间,被告人是否得到足够休息,是否保证了嫌疑人与辩护律师接触的权利,是否存在非法羁押等”。①陈瑞华:《比较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以下。由此对刑讯逼供行为本身的审查判定只是排除非法供述证据审查的一个部分,更多的标准是依赖剥夺嫌疑人程序权利的推断,即只要侦查机关违反了关于嫌疑人程序权利的保障规定,如存在超期羁押问题、违反讯问时间规定、剥夺辩护律师会见权等即推定为非法供述证据而予以排除。
同时,新《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院就被告人供述证据的排除的证明标准问题存在着自由裁量权难以监控、无法得到有效救济的问题,在我国因法官个人并不具有独立的审判地位,合议庭、审委会、法院系统、司法行政机关使审判法官处于一种类似行政级别的架构之中,加之常常受到社会关系网的干扰,更造成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形同虚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两个规定”颁布以来,非法证据个案排除凤毛麟角,对此急需相关司法解释予以规制、细化,并做好自由裁量权的法律规制与监督。②江必新:《论司法自由裁量权》,《法律适用》2006年第11期。可以说,正是“合法性调查”程序所建立的证明标准存在的诸多问题,造成了即使有着清晰明确的非法供述证据的认定,实践中也难以予以切实排除。
2.被告人供述证据的质证环境。被告人供述证据最终将呈现于公开的法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这一环节是对非法供述证据的“最终审判”,也是被告人维护自身权益的关键阶段。然而法庭审理中言词证据笔录的出示与宣读的书面质证模式,使得被告人供述证据除却了言词证据的本性,成为了类似物证的“哑巴证据”。法官通过审阅、研读被告人供述与同案其他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判定是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这一法庭裁断的逻辑进路,同前述侦查人员以犯罪嫌疑人口供为突破口,并以之为线索采集固定其他证据,生成形式合理的证据链条用以指控的侦查思路相一致,因此除非侦查人员过分疏忽在证据链条的构建中出现矛盾,否则庭审对于言词证据的质证无非是案件侦破过程的重新推演。非法供述证据因此获得了在质证中生存下去的可能,反过来质证环节的无效又助推了刑讯逼供现象的滋生。
2010年《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4条“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互相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有罪。”依照较权威的观点,该规定标志着“口供补强规则在中国刑事证据法中的正式确立”。③张军:《刑事证据规则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56页。明确了在排除串供、逼供、诱供可能性的基础上,完成被告人供述与源自该供述的其他证据间的印证关系。这一规定忽略了被告人供述证据与衍生自该证据源的其他证据间的天然联系,在我国现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法庭审理模式下,被告人供述的证据源性质或将造成“印证规则”为刑讯逼供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
(三)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其他共生规则
1.警察出庭难以保障。④陈卫东、柴煜峰:《刑事证据制度修改的亮点与难点》,《证据科学》2012年第2期。新《刑事诉讼法》第57条,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逻辑延伸,警察出庭作证被立法确认,然而立法在此处的规定缺乏具体实施程序规则和刚性的程序违法惩罚机制,如果侦查人员拒绝出庭不配合法庭调查,立法并未规定惩戒处理方法,侦查人员必然可出庭可不出庭,造成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面临“停留纸上”的命运。即使侦查人员出庭,法条虽规定了“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但并未规定是怎样一种说明程序,是否接受控辩双方询问?且侦查人员应以怎样的身份出庭说明情况,是作为控方证人,还是独立诉讼参与人或是“刑讯逼供”调查案的当事人?法条均未予以说明,是否仍会延续侦查机关出具“情况说明”的做法仍不到而知。对此我们认为“侦查人员及相关人员”的出庭问题,可以借鉴新《刑事诉讼法》第59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的规定,将此时的侦查人员赋予证人的身份,真正落实“非法证据”的质证问题。
2.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实践变异。在体制结构保持稳定的基础上,仅仅通过技术革新很难摒弃根植于制度层面的陈规陋习,为遏制刑讯逼供现象而引入的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即是如此,由其所带来的改变必然只是表面的,难以触及问题根本,导致这一制度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变异。全程录音录像的采集者和保管者的中立性问题是决定这一制度设计发挥作用的最关键环节,而这一问题的实质仍是侦查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在现阶段,录音录像过程形成于看守所讯问期间,由侦查机关委托专人进行,难以保证中立性,不但可能出现有选择的截段录取,甚至可能出现任意的剪接和变造,因此单纯的引入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并不能保证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甚至“对真正的刑讯逼供具有一定的掩饰作用”,①陈瑞华:《论被告人口供规则》,《法学杂志》2012年第6期。架构有效的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必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明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制约本质,由中立的第三方机构负责录音录像的采集和保管,以此才能保证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真正可以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有利于非法供述证据的确认和排除。
3.完善辩护律师在场制度。在现行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中,看守所划归第三方中立机构、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证、司法审查机制、侦查公开、沉默权制度等均不具有明确的现实价值,而依据新《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37条的规定,如若能够保障侦查阶段,尤其是讯问过程中的辩护律师在场,那么相信对于保护嫌疑人免遭刑讯逼供,以及在遭受刑讯逼供后可以及时采集、固定相关证据均是很有意义的。
以上规则,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间构成了共生效用的作用关系,对被告人供述证据获取方式的证明有赖上述规则的运行成果,而上述规则的合理运行又防止了非法供述证据的获取,即使存在着非法供述也会在共生制度的作用机制下被程序剔除,由此又警示了后续的刑讯逼供行为,可以看到,相关规则所构建起来的共生体便会在一种既定的良性循环中自行演进。
四、结 语
通过分析探讨:刑讯逼供现象理论研究的视角同法庭认定刑讯逼供行为的视角间的偏差,以及立法赋予检察机关举证责任的实际效果,明确非法供述证据在新刑诉时代仍将存在的排除障碍,这一障碍背后反映了非法供述证据的普遍存在是根植于现行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的,可以说体制基础即决定了其必然产生也决定了其难以有效排除,仅仅通过孤立技术创新很难触及根本,但是为解决非法供述证据的排除问题、贯彻保障人权的程序理念,坚持通过技术革新影响并推动体制改革在当前也是不无益处的,应当在此基础上注意共生效应在刑事诉讼制度中的作用机制,注重制度群的整体搭建,以优化配合发挥相关规则的实践效果。
(责任编辑:丁亚秋)
DF713
A
1674-9502(2013)03-095-08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2013-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