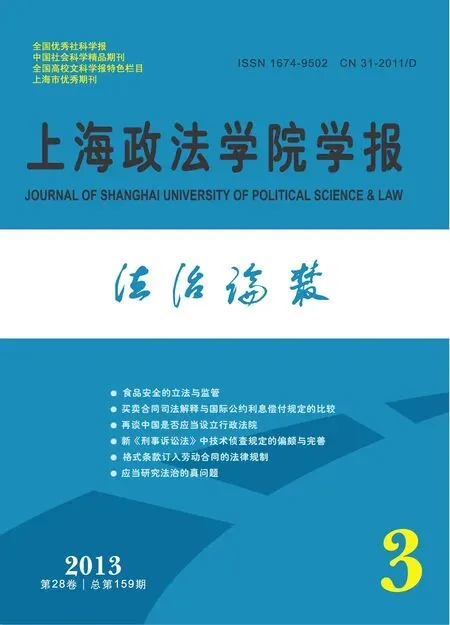食品安全相关罪名认定问题研究
2013-04-10曹俊金崔
曹俊金崔 磊
食品安全相关罪名认定问题研究
曹俊金1崔 磊2
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持续关注,而重大食品事件导致的食品安全犯罪问题也引起了很大重视。《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犯罪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刑法修正案(八)》也对食品安全犯罪问题予以修订,但实践中对于如何正确区分食品安全相关犯罪、如何正确定罪仍有不少困惑。本文以近年来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判例为视角,结合学术界对于食品安全犯罪问题的探讨,拟为司法实践提供一定参考。
一、食品安全犯罪相关罪名简析
我国《食品安全法》及《刑法》对于食品安全相关犯罪都作了规定,其中《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较为笼统,即: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修改前的《刑法》有两个条文对食品犯罪作出了专门规定,即第143条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第144条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原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将其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已于2011年4月2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0次会议、2011年4月13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60次会议通过,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相应地将罪状的表述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行为”,并修改了法定刑。针对第144条,《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法定刑。此外,《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食品监管渎职罪,对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并最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作了特别规定。②由于食品监管渎职罪是渎职罪的一种,其犯罪主体为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与生产、经营者的食品安全犯罪相比存在较大区别,在定罪中不容易混淆,因此下文对食品监管渎职罪不进行探讨。
除了上述三个专门规制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之外,在现行的司法实践中,其他可适用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还有:非法经营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比如,在最近的几个案件中,“刘襄等制造、销售瘦肉精案”和“张玉军三鹿奶粉案”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作出裁判的;在上海染色馒头事件中,对当事人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对杨松等将死因不明且未经检疫的动物尸体加工并销售的行为认定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现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将宋德兵在制作辣椒面的过程中添加苏丹红并销售含有苏丹红的辣椒面的行为认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此外,从理论上而言,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还可能会构成其他犯罪,如虚假广告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相关贪污受贿渎职类犯罪、妨害公务罪以及假冒注册商标罪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①梅传强、杜伟:《论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现状与立法再完善》,《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舒洪水:《关于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思考》,《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为便于区分,本文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称为“食品安全犯罪”,将这两种罪名以外的食品安全犯罪称为“其他食品安全犯罪”,食品安全犯罪与其他食品安全犯罪统称为“食品安全相关犯罪”。
问题是行为人实施的均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为何会触犯如此众多不同的罪名?这一方面源于每一个案件具体情况不同,另一方面是由于规定各个罪名的法条之间存在竞合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这些罪名进行区分并合理处理竞合法条间的关系,正确定罪量刑,不仅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同时也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否则将增加定罪处刑的不确定性,不利于追究食品安全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也不利于对食品安全犯罪进行监管。
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认定
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前,《刑法》中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法修正案(八)》将前罪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从理论上而言,这两个罪名的界限较为明显,主要存在如下区别:
第一,犯罪对象不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犯罪对象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这里的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食品不安全;其二是造成这类食品不安全、不合格的原因是在于食品本身,并非由于食品中掺入了其他非食品原料。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对象是有毒、有害的食品,这里的有毒、有害系来源于非食品原料,而非来源于食品本身,并且是由行为人以积极的作为掺入的。第二,客观方面表现不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生产者、销售者在生产、销售中由于行为人操作不规范、不按食品安全标准执行或不作为等原因,使食品受到污染、变质等导致食品不合格,甚至出现一定的“毒害”作用,可以认为是一种不作为犯;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客观方面系行为人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故意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要求其以积极的作为来实施的一种犯罪行为。第三,犯罪形态不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是危险犯,行为人除了实施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外,还要求该行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即构成犯罪。因此,从理论上而言,两种犯罪的界限是相对清晰的。
但根据近年来的司法判决,可以发现实践中在区分这两个罪名的时候,仍存在疑问。比如,从主观方面而言,两罪均是直接故意犯罪,但是故意的内容并不同,主要体现在明知的内容不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中行为人明知所生产的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行为人明知在生产的食品中掺入的是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但实践中,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或属于何种“明知”则并不容易,如在“崔小连、马太祥、王世安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案”中,正是由于三被告人均否认“明知”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在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向奶粉中故意掺入了三聚氰胺,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知道该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的情况下,只能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①参见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2011)沁刑初字第33号判决书。但实际上,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及当时的背景,三被告人知道涉案奶粉中三聚氰胺超标的可能性应当是非常大的。这说明虽然在理论上区分两个罪名的主观方面较为容易,但实践中由于主观方面的内在性和易变性的特征以及证据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导致在罪名认定上会存在困惑。
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综合行为人的年龄、社会阅历以及案件的具体情节来推定行为人的明知内容。此时侦查过程中的证据采集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一方面要通过搜集证人证言以强化犯罪嫌疑人的主观证据,以防止其无理辩解或翻供;另一方面通过固定相关书证、物证,包括其进货账本、销售记录、食品包装等客观证据,以推定其主观故意。因为主观方面是无形的,因此如果没有通盘的考虑是难以正确认定主观明知的,在罪名类似的场合尤其如此。但是,如果能够综合考虑食品的来源渠道、交易价格以及被告人的自身情况,那么对于行为人是否明知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销售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情况作出合理推定,则应当是较接近于行为人犯罪时的主观心态的,也更利于正确定罪量刑。
另外,从犯罪对象上而言,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罪要求行为人掺入的是非食品原料,或者明知其销售的食品中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如果行为人掺入的是食品原料,即使是有毒有害的,也不能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罪,依据法律就只能认定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其他食品安全犯罪。但对于什么是“非食品原料”,目前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判断标准,理论上争议也很大。因此,笔者认为,不应将那些无法判断是否属于非食品原料或者尚未列入检测范围的物质引起的食品安全事件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但实践中,由于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导致不得不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来追究其刑事责任,所以理论界近来主张应用“非食用物质”一词来指代“非食用原料”这一称谓,以此来提高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罪的效用,对两个食品安全犯罪的定罪作出有效区分,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困惑。遗憾的是,《刑法修正案(八)》并没有采纳学界的呼声,仍然保留了“非食品原料”一词。笔者认为,应当尽快明确“非食品原料”一词的法律定义,或者通过立法解释廓清“非食品原料”与“非食用物质”之间的关系,以此结合卫生部分批发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目前共发布六批)来正确认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罪,否则只能认定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其他食品安全犯罪,以免在司法实践中随意出罪与入罪。
三、食品安全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认定
如上所述,规定食品安全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法条存在包容关系,无论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还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均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表现形式。但在实践中,究竟是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还是以食品安全犯罪来认定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却也不无争议。如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11年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件》中,孙学丰、代文明销售超过保质期且三聚氰胺含量严重超标的奶粉案和叶维禄等生产、销售添加“柠檬黄”的玉米面馒头案,都没有定为食品安全犯罪,而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来定罪。另外,在崔小连等销售含有三聚氰胺奶粉案的定性问题上,究竟应判处食品安全犯罪还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也曾有过争议。在此情况下,对于食品安全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区分标准予以探讨,也就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犯罪构成上而言,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犯罪对象方面,前者的犯罪对象是伪劣产品,并非某一类特别产品;后者的犯罪对象是刑法规定的特定的伪劣产品。第二,在具体构成要件上,前者以“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为构成犯罪的最低要求,后者并没有犯罪数额上的要求,其中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以“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为构成犯罪的要件,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则仅要求行为人实施相应的犯罪行为即可成立犯罪。虽然存在如上区别,但从理论上而言触犯食品安全犯罪,当然也触犯《刑法》第140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这类普通法与特别法的法规竞合,通常应依特别法即食品安全犯罪的法条予以处理。但《刑法典》第149条第2款规定:“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即依照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处理这类问题,这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的例外。
在销售金额未达到5万元而构成食品安全犯罪时,应当以食品安全犯罪定罪处罚。如在“沈文柏、张花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中,由于被告人沈文柏和张花出售自制的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猪蹄膀”销售额为人民币27000余元,尚不满5万元,因此仅能按照“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定罪。①参见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法院(2011)云法刑初字第231号刑事判决书。
在生产、销售金额达到5万元时,即既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又构成食品安全犯罪的情况下,由于食品安全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均有不同的量刑档次,且量刑档次也不完全吻合,需在上述两个原则的指导下,应当按照实际情况予以具体分析,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档次,在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情况下,应当以食品安全犯罪定罪处罚,这一方面是由于相对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而言,食品安全犯罪的法条是140条的特别法;另一方面,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量刑档次为2年以下,而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量刑档次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量刑档次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此根据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也应当定为食品安全犯罪。第二档次,在销售金额为2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情况下,如果尚未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尚未发生其他严重情节,则尚不属于实害犯,在此情况下,如果按照食品安全犯罪来定罪处罚,则最高刑分别为3年和5年,而依照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定罪处罚,其最高刑为7年,因此,尽管食品安全犯罪是特殊类别的犯罪,但由于《刑法》第149条规定构成特殊罪名的犯罪,同时又构成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按照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定罪处刑,如在“石家庄裕康乳业有限公司销售伪劣产品案”中,被告单位明知其销售的奶粉已经过期并可能含有危害人身安全的有毒添加剂三聚氰胺,仍然销售给其他食品企业,销售金额达20余万元,同时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即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②河北省赵县人民法院(2011)赵刑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书。如果生产、销售的食品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则在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的食品罪的场合,应当按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因为在该量刑幅度,两个罪名的最高刑相同,但最低刑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起点高。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场合,应当按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无论是从特定罪名还是从处罚轻重的角度而言,都是如此。第三档次,在销售金额为5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的情况下,如果尚未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尚未发生其他严重情节,当然是依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即使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发生其他严重情节,由于其销售金额巨大,因此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所受到的刑罚更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仍应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只有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且后果特别严重(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罪)的情况下,③有些案件中定为公共安全罪,具体见第4部分。才能依据食品安全犯罪定罪处罚,不能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第四档次,在销售金额200万元以上的情况,按照前述定罪原则,一律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四、食品安全犯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认定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使用与放火、决水、爆炸等行为危险性相当的其他方法并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刑法》规定该罪名是由于实践中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形式、手段很多,刑法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所有的犯罪形式、手段都列举出来,因而以“其他危险方法”作概括性的规定。①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3-344页。由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也就是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而食品安全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食品卫生的管理制度和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值得注意的是,在食品安全犯罪中,行为人所生产、销售的不符合安全标准或有毒、有害的食品所流向的人群也是不特定的。这在理论上而言即是对公共安全这一客体的侵犯,因此在构成食品安全犯罪的同时,也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者属于想象竞合犯。刑法对于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是从一重处罚,在两种犯罪的比较中,仍应按不同的量刑幅度予以比较,具体不再详述。
问题在于,目前司法实践对于严重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比如在“瘦肉精”案中,被告人刘襄、奚中杰、肖兵、陈玉伟、刘鸿林明知使用盐酸克仑特罗饲养生猪对人体有危害,被国家明令禁止,仍然使用盐酸克仑特罗饲养生猪并致使生猪大量流入市场,严重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致使公私财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社会危害极大,影响极其恶劣,5名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11年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件》。再如“三鹿奶粉”案中,也最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定罪。③参见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8)石刑初字第353号刑事判决书;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9)冀刑一终字第57号刑事裁定书。这两个案件均是震惊全国、影响巨大的食品安全案件。
尽管上述两个案件是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定罪,但其他类似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却并未用该罪名来处断。如“宋德兵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④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07)江刑初字第310号刑事判决书。“王岳超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等均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来定罪。⑤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0)奉刑初字第195号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一中刑终字第332号刑事判决书。但不可否认,这些行为也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为什么前述两个案件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判处,而后面列举的罪名则以特定的食品安全犯罪来判处呢?即使抛开不同区域间法律适用倾向的差异和案件承办人的主观认知差异,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仍然值得探讨。从食品犯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定刑而言,即使尚未造成危害结果,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比食品安全犯罪重,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理应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但是在这两个案件中却都以食品安全犯罪来定罪处罚,这无法从想象竞合犯的原理进行解答,只能考虑规定这些罪名的法条是否存在竞合。从刑法典的结构来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定于第二章,食品安全犯罪规定于第三章,且依前述分析得知,两类犯罪的犯罪客体并不相同,因此法条上不可能是完全包容关系,而是一种交叉包容关系。
实际上,司法实践对于该罪名并非完全按照想象竞合犯从一重予以适用,也未统一以“特殊法优于一般法”予以适用,而按情节不同定以不同的罪名。并且,除了食品安全犯罪以外,对于其他犯罪如危险驾驶案件、偷窨井盖等案件中也曾适用过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使得该罪名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口袋罪”。如此定罪的法理依据何在?究竟如何在实践中正确适用这两类犯罪呢?笔者认为,该罪名之所以能够被上述案件所广泛适用并沦为“口袋罪”,其原因是《刑法》对于该罪名的概括性,概括性必然导致刑法在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而模糊性则最终导致该罪名在适用上的“口袋化”。当然,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政策导向、司法独立性问题以及刑法的解释问题也均是造成该罪名“口袋化”的共同原因。但无论如何,在罪刑法定观念深入人心之后, 一个罪名被指斥为口袋罪,即意味着其与罪刑法定原则、尊重保障人权的冲突。①孙万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何以成为口袋罪》,《现代法学》2010年第5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频繁地适用于食品安全犯罪之中,势必会导致食品安全犯罪判决的不确定性,也必将影响刑法的实施效果,及对刑法理论和实践产生不必要的负面效果。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应当严格控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食品安全犯罪中的适用,除非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巨大,都不得加以适用。应当适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情况下不得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只有在极少数危害结果极其严重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情况下才能考虑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必须适用的场合,仍然需要同时考虑并满足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主观方面,如果行为人以危害公共安全为目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那么应当适用该罪名。但若行为人主观目的是通过违反国家对食品卫生的管理制度而获取非法利益,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即其直接目的并非是危害公共安全,那么行为人主观上至多是间接故意。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考虑行为人明知生产、销售的有毒、有害的食品是否会危害公共安全而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更要考虑其是否在知晓以实际发生的危害结果的情况下,仍然继续生产、销售并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只有如此,作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方面予以认定较为合适。
第二,客观上必须有危害结果发生,而且危害结果必须是明显表现出来的,确实已经导致不特定人的人体健康受到显性的伤害,危害极其巨大,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对公私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第三,在销售金额方面,如果销售金额过低,则没有必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定罪处罚,笔者认为以200万作为考虑该罪的起点是必要的,因为200万以下完全可以通过适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或者食品安全犯罪来定罪处刑。但是如果销售金额超过200万,按照前述讨论,只能按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来处罚,如果造成巨大的危害后果,并且满足主观要件,那么不仅可以按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来定罪处罚,在这个时候还可以考虑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五、结 语
由于食品安全相关犯罪之间存在相似、包容或者法条上存在竞合关系,导致食品安全犯罪罪名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困难。本文主要结合近年来关于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司法实践,就其中几个犯罪之间如何正确认定进行探讨,提出了若干建议,并期望司法机关能在处理食品安全相关罪名时予以关注,以能正确地对食品安全犯罪进行定性,切实在遵循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挥刑法对于我国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的重要规制作用。
1.上海杉达学院;2.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