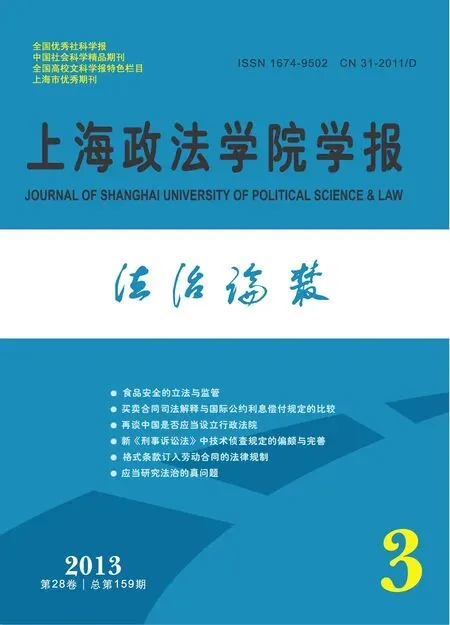食品安全地方立法研究
——以宁夏、上海和浙江三地立法为分析样本
2013-04-10丁冬陈冲
丁 冬 陈 冲
食品安全地方立法研究
——以宁夏、上海和浙江三地立法为分析样本
丁 冬 陈 冲
一部生命力持久的法律要在现实针对性与法律稳定性之间取得一种适度的平衡。这也就决定了法律条文的设置必须在具有可操作性与保持相当的原则性之间寻找平衡点。在我国长久以来奉行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原则指导下,《食品安全法》的法条设置就体现了立法者在追求法的现实针对性与稳定性之间的适度平衡过程中诸多思量。基于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属性以及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不平衡等基本国情的考量,①谢天放:《我国地方立法的流变与展望——以上海市地方性法规的分析为例》,《政府法制研究》2005年第4期。以及对我国食品行业复杂业态的认知,②不同于药品行业的高准入资格,我国食品行业的业态呈现出 “准入门槛低”,“行业主体多”(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零售企业、餐饮企业、小作坊和流动摊贩),“从业人员多且素质参差不齐”的特点。据统计,全国13亿多人口每天消耗200万吨粮食、蔬菜、肉类等食品,共有食品生产企业40多万家、食品经营主体323万家、餐饮单位210万家、农牧渔民2亿多户,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更是数量巨大。《食品安全法》在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纳入规制范围的同时,赋予各地省级人大常委会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监督管理的立法权。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以及食品行业的复杂业态,地方立法之于《食品安全法》实施的“拾遗补缺”和“配套衔接”功能不可忽视。通过食品安全地方立法,对国家相关制度进行补充和细化,是确保《食品安全法》顺利贯彻实施的重要举措。
一、食品安全地方立法的定位与意义
(一)定位
根据地方立法的内容和性质,在学理上可以将地方立法区分为执行性立法、补充性立法、自主性立法、先行立法、实验立法等。③崔卓兰:《地方立法实证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第8-13页。但在实践中一般很难绝对地将一部地方立法归类为执行性立法或补充性立法。相反,基于《立法法》的要求以及地方立法具有的从属性和地方性,许多地方立法具有混合型的立法特征。其中可能既存在为执行上位法的规定而进行的细化规定或者针对本地情况进行具体规定的内容,也存在上位法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对某些问题进行详细规定而进行补充性规定的内容。
食品安全地方立法也同样具有类似的特征,纵观目前宁夏、上海、浙江的立法,其中既有为执行上位法规定而进行的具体规定,也有根据地方实际与监管实践而对上位法进行的补充规定。
(二)意义
当下食品安全保障具有全国性和地域性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基于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以及物流网络的网格化,食品的流通性基本上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因此,一旦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或事件,其影响往往呈现出波及范围大、受累人群多等特点。三聚氰胺事件的爆发就生动地说明了食品安全保障具有的全国性特征。另一方面,基于各地饮食文化的不同,各地食品通常带有很强的地域特征的,面对着不同于其他地方的食品业态,食品安全保障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地域性的特征。比如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中,上海与云南相比,在面临的餐饮服务业态上就存在着餐饮服务单位的数量、类型、从业人员等方面的较大差异。①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研究中心课题组:《云南省食品安全“十二五”规划编制研究报告》;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年报(2011年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立法就承载了细化落实国家立法与针对地方特点拾遗补阙的双重功能,一方面针对具有共性的食品安全问题执行国家立法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可以针对具有地方性、地域性的食品安全问题在不违反上位法的情况下进行补充立法。
二、食品安全地方立法的共性分析与创新点
《食品安全法》的顺利实施,需要一系列配套性法规的支撑。《<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从国家层面对该法进行了细化。自2010年开始,宁夏回族自治区、上海市、浙江省三地人大常委会率先开展了食品安全领域的地方性立法实践。2010年1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办法》颁布、2011年7月,《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办法》及《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办法》颁布。这三部地方性法规,结合地方监管实践,对食品安全保障工作进行规制。三地食品安全地方立法实践的展开,是食品安全法制保障工作的有益探索。
(一)三地立法的共性分析
三地立法坚持贯彻《食品安全法》与针对本地实际增强法条可操作性的原则,主要着力点包括:通过调整监管职责、明确交叉地带监管归属,进一步理顺和完善监管体制,弥合监管罅隙,添补监管空白;明确、细化对食品小作坊和摊贩的相关管理规定,坚持采用疏堵结合的方式治理食品小作坊和摊贩问题;在注重与上位法衔接的同时,针对监管中存在的新问题,努力填补上位法的规制空白;构建和完善奖励举报制度,明确投诉举报的内部移转制度,办理时限等具体规定;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在强化监管举措的同时,将食品安全作为社会管理过程的重要命题贯穿于立法之中,凸显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监管理念,鼓励媒体、行业协会、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的保障工作。三地立法的以上特征,实际上体现了食品安全地方立法执行性与补充性的双重特征。
(二)三地立法的创新之处
1.宁夏回族自治区立法
《宁夏回族自治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办法》细化了《食品安全法》第52条的相关规定,《办法》第18条从细化责任、明确主体的角度,对商场、超市、集贸市场、集中经营区的开办者及食品柜台的出租者在食品安全保障方面的责任进行了明确界定,明确以上主体应从查验证照、检查生产环境与条件、指导并督促生产记录等相关制度完善、督促下架销毁不合格产品等方面协助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工作,并应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对未履行规定义务,导致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2.教学手段单一刻板,不灵活。遥感课程通常使用多媒体教学,这比较符合测绘信息类课程的实际需求,其特点是直观性强,能够帮助学生理解、记忆和分析等,但同时也在无形中加快了教学进度,一点鼠标,一个内容就过去了,并且下一个内容是提前预设好的,不会因为学生掌握程度的好坏而临时更改,这种模式导致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不透彻。
2.上海市立法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办法》主要着力点有三:一是通过制度安排,努力实现监管体制的无缝衔接;二是强化和凸显企业的食品安全保障责任;三是坚持疏堵结合和属地管辖的原则,治理食品小作坊和摊贩。具体包括:
第一,明确监管职责,理顺监管体制。上海市立法一方面结合本地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历史沿革和实践情况,将卫生部门食品安全监管的相关职责剥离出来,赋予食药监部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定、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①上海食品安全监管的一个实际情况是,上海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因此上海食品安全地方立法将食品安全监管的综合协调、重大事故查处、食品安全信息发布等职能赋予食药监部门,其中也考量到了食安委办公室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考虑到食品安全分段监管的复杂情况,又赋予市政府确定各部门食品安全监管具体职责的权力。同时,将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纳入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相关工作中来,充分发挥基层力量对食品安全监管的促进作用。
第二,以疏堵结合的方式,治理食品小作坊和摊贩问题。食品小作坊和摊贩一方面承担了增加就业机会、满足部分消费者日常饮食需求等功能,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卫生条件差、食品安全标准不达标、从业人员素质低等问题。如何在食品小作坊和摊贩的监管与发展之间取得适度的利益平衡,是监管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难题。上海市立法以疏堵结合的方式从加强监管和合理帮扶两个层面入手,来提升小作坊和摊贩的食品安全水平。其中,第26条、33条规定,政府部门应当建立相对固定、集中的生产经营场所,以方便群众、合理布局的原则进行小作坊和摊贩治理。明确摊贩的属地管理原则,第38条第3款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协调辖区内相关部门,对辖区内的食品摊贩进行监督管理,发现食品摊贩存在违法行为的,告知相关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第三,规范食品委托加工行为。食品企业、集团的扩张式发展导致其生产经营需借助其他企业来加以完成。诸如蒙牛、伊利、双汇等食品集团企业就拥有为数众多的代加工厂家。食品生产经营者委托生产食品的情况,在实践中较为常见,但《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对此未作规定。对此,上海市立法规定对委托加工食品的行为,受委托企业应取得食品生产许可并具有相应的生产条件和能力;且必须在获得生产许可的产品品种范围内接受委托生产食品,并向所在地的区、县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报告。此外,为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及时溯源的需要,受委托企业还应当对自己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和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信息,在受委托生产的食品标签中明示。
第四,强化举报奖励制度的作用,设立统一的食品安全投诉举报电话。为发挥社会监督保障食品安全的作用,弥补监管资源的不足,方便广大市民开展食品安全投诉举报,上海市立法第46条规定:“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应当设立统一举报电话,并向社会公布。”上海市食品安全投诉举报热线的受理范围包括了食品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的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并确立了案件的内部移转制度。为及时处置投诉举报问题,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提供了平台。
第五,引入保险机制,构建食品安全事件的损失分担与权利救济制度。食品安全事件为代表的大规模侵权事件的多发,给受害人的权利救济与损失分担带来了严峻挑战。涉事企业在事件发生后,面临着来自受害者、职工、税务、享有抵押权质押权的债权人以及其他普通债权人的权利追索,其本身的财力往往难以支撑。发展产品责任、环境污染责任等保险业务,利用保险事前防范与事后补偿相统一的机制,充分发挥保险费率杠杆的激励约束作用,将保险纳入灾害事故防范救助体系,成为国家层面的共识。①参见《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23号)第5条的相关表述。上海市立法第25条规定:“鼓励婴幼儿食品、生食水产品等食品的生产经营者,大型餐饮、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以及承担重大公共活动食品供应的单位,投保食品质量安全责任险”,率先引入保险机制,发挥保险业务在高风险食品行业领域的积极作用。
3.浙江省立法
第一,规范网络交易平台服务者相关行为。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以淘宝、一号店、当当、卓越等为代表的网购平台迅速成长,团购这种新兴购物方式也火爆一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有效保障网购食品的安全、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得以维护、遭受损害可获赔偿,就是一个重要问题。浙江省立法第22条规定了网络交易平台服务提供者的食品安全保障责任,明确其应当对通过网络交易平台经营食品的经营者加强管理,课以其对违法行为的报告义务、暂定网络交易服务义务以及对消费者投诉举报的协助调查义务。
第二,对小作坊生产加工的食品实行目录管理。浙江省立法第31条明确禁止将“高风险食品”、“专供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列入小作坊生产加工的食品目录,严格控制小作坊可生产加工的食品种类和范围。
第三,明确餐饮具集中消毒行为规范。餐饮具集中消毒存在的行业乱象频频遭到媒体曝光,准入门槛低、多头监管、卫生条件差等问题多发。②《餐饮具消毒业恶性竞争 欠款压价乱象丛生》,http://finance.qq.com/a/20120710/003626.htm,腾讯网,2012年6月30日访问。《武汉消毒餐具行业监管存空白 17年企业亏本经营》,http://news.cjn.cn/sywh/201207/ t1966919.htm,长江网,2012年7月20日访问。《办法》专设第5节(第40条至第44条),从餐饮具集中消毒的生产经营条件、规范和监管方面填补规制空白。
第四,明确食品监管交叉地带责任归属。《办法》第46条第2款规定:“面包糕饼、卤味烤禽等现场制售形式的食品经营活动,以及在歌舞厅、网吧等休闲娱乐场所内提供餐饮服务及现场制售活动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商场、超市的现场制售活动以及食品交易市场中的现场制售活动,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第五,明确投诉举报首问负责制。《办法》第52条第3款规定:“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接到投诉、举报,应当实行首问负责制,不得推诿、拒绝;对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受理并及时进行核实、处理;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书面移交有权处理的部门处理并告知投诉人、举报人。有关部门对接到的投诉、举报和核实、处理的情况应当予以记录、保存。”
宁夏、上海、浙江三地率先开展的食品安全地方立法,在贯彻执行《食品安全法》的同时,对监管实践中亟需立法加以规制和指导的问题,通过地方立法形式进行了尝试性的规范。餐饮具集中消毒、网络交易平台服务者、委托加工等方面的立法规制,对食品安全监管提供了执法依据。
三、食品安全地方立法的实践与挑战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食品安全地方立法呈现出两种形式,一种是针对食品摊贩和加工小作坊的监管问题进行专门立法,比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立法;另一种则是综合性立法,将本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问题统合到立法当中,同时对食品摊贩和加工小作坊的监管问题做出规定。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结合地方监管实践对上位法的延伸和细化。一部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其表达与实践的统一。地方食品安全立法能否发挥其“拾遗补缺”和“配套衔接”的双重作用,在保障地方食品安全方面得以切实的实践,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分段监管的弊端无法通过地方立法得以化解
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其特征可以概括为“有协调的分段监管体制”。在分段监管体制下,其首要特征在于:各个监管部门的监管重心在环节而不在食品。各个部门只对属于自己监管范围的环节进行监控,而不对食品质量进行严格的把控。换言之,以三聚氰胺事件为例,在以环节为中心的监管模式下,质监部门可以以问题出在种植养殖环节而非生产加工为借口进行责任推脱。而一种有效的监管则应该建立在以食品为中心的监管模式之上,即只要问题发生在监管的某个环节,就应该由哪个部门来负责。这样,各个监管部门之间形成了一种竞争性的关系,建立了一种以食品质量安全为导向的监管理念和责任落实。
其次,在现有体制下,食品安全信息 “部门化”、“垄断化”和“封闭化”的特征十分明显,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缺乏有效性。而对各监管部门监管行为进行的综合协调涉及多部门的共同协作问题,行为产出结果是一个多部门共同产出的结果,部门间协调行为存在着难以清晰衡量和评价的特点。①詹承豫:《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博弈与协调》,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因此,存在着因协调行为而产生的成本大大高于具体执法成本的问题。以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为例,就存在着承担综合协调职责的人员数远大于执法专项人员数的情形。
面对分段监管体制的弊端,受制于《食品安全法》和《立法法》等上位法的限制,地方立法无法建立如前所述的一种以食品质量安全为导向的竞争性监管模式,而只能采取对各监管部门的职责分工进行再细化的方式来应对分段监管弊端的对策。比如,浙江省立法就通过细化规定来进一步确定面包糕饼、卤味烤禽等现场制售,歌舞厅、网吧等休闲娱乐场所内的餐饮服务及现场制售活动,以及商场、超市现场制售活动的监管分工。但是,这样的做法只能是对当下暴露出的监管分工不清晰的部分问题进行权宜性解决,却无法穷尽这样的监管难题。比如,在针对前段时间暴露出来的豆芽菜监管职责不清问题上,某地政府发文规定,由农业部门负责对农户生产豆芽的行为进行监管,质监部门负责对工业化生产豆芽的行为进行监管;工商部门负责对商场超市等销售企业、批发市场、商品交易市场销售豆芽的行为进行监管。即使这种区分,在一线监管部门还存在如何区分工业化生产和散户生产的疑问和争论。可见,以这种清单的方式来明晰监管部门职责,会陷入“无法穷尽”的监管困局之中。
(二)复杂的食品业态对食品安全地方立法的实践造成了极大挑战
不同于药品行业的高准入门槛,我国食品行业的业态呈现出准入门槛低、行业主体多、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且流动性极大等特点。据粗略统计,我国目前有中国13亿多人口每天消耗200万吨粮食、蔬菜、肉类等食品,全国共有食品生产企业40多万家、食品经营主体323万家、餐饮单位210万家、农牧渔民2亿多户,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数量更为庞大。现行《食品安全法》第29条第1款规定:“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实际上,相关的立法背景资料显示,食品安全法草案在该条后面还有一句“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规定。考虑到这一规定的实际可操作性,在立法审议过程中删除了这一规定。②《食品安全法(草案)》,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4/20/content_8021987_4.htm,新华网,2012年7月16日访问。这种立法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认识到我国食品行业复杂业态下做出的不得已选择。
反观地方立法,同样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相较而言,食品小作坊一般都具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其监管难度相对较低。而食品摊贩由于数量较多且具有极大的流动性等特征,是地方立法的规制难题。虽然食品安全地方立法对食品摊贩的生产经营条件、要求、范围以及索证索票制度等进行了明确规定,但基本上缺乏现实可操作性。上海市食药监管部门组织人员对4个区11个街道650个摊贩样本的调查数据显示,食品摊贩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从业主体多样化,来沪务工人员所占比重较大,且以个体户为主;二是摊主健康卫生状况较差,未取得健康证明的比例达83.7%,而取得健康证明又同时持有卫生许可、营业执照的仅占2.3%;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不规范情况严重,被调查摊贩中有86.3%的人不戴工作帽、69.9%的人不穿工作服、74%的人裸手接触货币;食品生产加工设施卫生状况差,加工操作又交叉污染的占37.5%、用具不清洗不消毒的占16.5%、提供直接入口的食品未配备防虫防蝇设施的占63.7%;食品原料来源可识别或可追溯难度大;食品包装材料和餐饮具卫生状况堪忧。①谢敏强:《上海市食品摊贩抽样调查结果及监管对策研究》,载唐民皓主编:《食品药品安全形势与监管政策研究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8-84页。与此同时,该调查还发现食品摊贩在市民早餐环节扮演着重要角色,供应时段在早点时段的占56.5%;摊主的经济状况还存在着普遍较贫困的状况。②同注①。
面对食品摊贩的监管问题,实际上存在着安全与发展、安全与民生的双重挑战。一方面,食品摊贩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亟需治理,而另一方面其又在促进外来务工人员就业、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基本生存权利、便利民众就餐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面对这样的监管难题,监管三地立法都普遍宣称以疏堵结合的方式治理食品摊贩问题,但实际上反观地方立法条文可见,对待食品摊贩问题地方立法的态度仍过于模糊,在到底是以堵为主还是以疏为主方面踯躇不前。③余志强:《食品安全地方立法:能否满足公众高期待》,《上海人大月刊》2011年第2期。而提出的经营范围、条件、索证索票等规范化要求在监管力量不到位的情况下,又处于监管不能的境地。
由此导致食品安全地方立法诸多条文都处于表达与实践的背离之中,法律表达的悬置化亦使得《食品安全法》试图将小作坊和摊贩的监管职责课于地方的立法选择大打折扣。
四、结 语
宁夏、上海、浙江三地的食品安全地方立法,是《食品安全法》颁布以来各地率先开展的地方立法项目,在发挥其“拾遗补缺”和“配套衔接”双重作用的同时,也为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制保障提供了积极的参考借鉴作用。其在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局和挑战不仅是我国《食品安全法》实践困局的缩影,也是其他地方立法所不得不面临的挑战。
在我国《食品安全法》所确立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未发生变动的情况下,食品安全地方立法的配套衔接功能,只能发挥有限度的作用,而无法超越上位法的要求。因此,对各部门监管职责所进行的清单式的细分和再确定,也只能是权宜之下的无奈之举。对于《食品安全法》第29条赋予的小作坊和摊贩的立法管理权限的落实,在复杂的食品业态挑战和既定的监管资源下,既无形成统合的监管思路,也无法提出真正切实有效的监管对策。反倒是,地方立法在面对监管实践中的新问题、难题所及时作出的积极回应,成为食品安全地方立法的亮点和特色。委托加工、餐饮具消毒、网售食品等问题的规制,无一不反映出食品安全地方立法的积极导引作用。因此,今后的食品安全地方立法如何更加突出地发挥拾遗补阙作用,对本地区食品安全监管实践中的问题进行系统地规制,使得食品安全地方得以提供“在地化”获得更强的实践性和生命力,成为食品安全地方立法充分发挥其效用的可能途径。
总之,食品安全地方立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面临的各种困局,再一次印证了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的论断。作为社会管理过程的食品安全保障命题值得深入地发掘和思索。
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