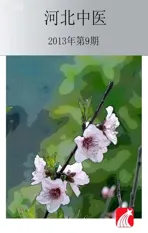《伤寒论》中脾胃病证治思想研究
2013-04-09陈桦逸
陈桦逸
(上海中医药大学伤寒教研室,上海 200032)
《伤寒论》是中医学经典著作,为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俱全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经典专著,该书十分重视脾胃在人体发病和辨证论治中的作用。书中如阳明病篇、太阴病篇所包含的脾胃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伤寒论》重现脾胃的观点,对外感病的辨治有指导意义。鉴此,探讨《伤寒论》的脾胃观,尤有必要。国内许多学者做了许多有益的研究,现综述如下。
1 《伤寒论》中对脾胃病证治探讨
脾胃学说是中医学的一大瑰宝,历史上重视脾胃的名医如李东垣、叶天士等为世人所皆知,但若追溯其源,仍当首推张仲景。《伤寒论》一书古今往来研究者颇多,其在治疗中重视顾护脾胃的思想也为越来越多的现代医家所重视和研究。
俞群力[1]对《伤寒论》的脾胃思想进行研究指出,首先,重视脾胃,要强调病机。《伤寒论》作为张仲景代表作,更可反映出其重视脾胃的学术思想。如《伤寒论》所载的各种诊法,十分重视胃气,在太阳、阳明、少阳等各篇中均有治疗脾胃之详列。正如《古今医统》所说:“汉张仲景著《伤寒论》,专以外伤为法,其中顾盼脾胃元气之秘,世医鲜有知之者。” 并认为张仲景调治脾胃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治脾胃当辨虚实。②理脾胃尚须兼顾它脏。③顺承胃气,脏病宜通。④辛开苦降,以复升降。⑤脾恶湿,健脾当祛湿。⑥木克土,扶土应抑木。⑦调补脾胃必用甘味。⑧调护脾胃助用食疗。其次,反对克伐,主张护元。由于胃气与正气息息相关,故正确地施治,有利于正气和胃气的恢复,反之则病邪不祛徒伤其正,临床中导致脾胃及正气受损之原因甚多,其中误治和妄施克伐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故历代医家均将“保胃气”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疗原则。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主张,根据不同体质,分而治之,反对一味克伐损伤胃气的做法。蒋小敏[2]的研究提出,首先,要重视脾胃与外感发病的关系:①脾胃不足是导致外感病的基本原因。外感疾病的发生,感受外邪固然是引起疾病的根本原因。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②重视脾胃气机升降运化。《伤寒论》虽没有明言脾升胃降之说,但将脾胃之升降理论运用于临床,并创制了一系列调理脾胃气机升降的治法和方剂。其次,脾胃虚实不同,影响外感病的辨证、传变和治疗。在《伤寒论》中,张仲景介绍了单纯的外感病的辨证论治,如太阳中风表虚证、伤寒表实证及其兼证,表郁轻证,又借助兼证、合病、并病的途径,介绍了伤寒外感病不仅表现为太阳病的证候,而且与原有的内伤脾胃病证有密切关系。故学习《伤寒论》,正确认识外感与原有脾胃病的关系,对治疗外感病有重要的意义,对脾胃病证的辨治也有重要意义。邱明义[3]研究指出《伤寒论》脾胃病的病因:①外感六淫是《伤寒论》脾胃病的主要病因。②误治损伤脾胃导致脾胃病甚多。③饮食劳倦是导致重要因素。④体质因素在脾胃病发病中亦是重要因素。⑤情志因素也会间接影响脾胃病。《伤寒论》脾胃病的病机如下:阳经病实,阴经病虚;脾胃升降失职;肝胆疏泄失常。《伤寒论》脾胃病辨证:辨阴阳;辨虚实;辨寒热;辨气血。《伤寒论》脾胃病的治疗原则:注重泻实补虚;注重调理脾胃的升降;注重疏泄肝胆。李合国[4]研究认为,《伤寒论》以脾胃为本的学术思想渊源于《内经》。从六经病的理、法、方、药等方面探讨张仲景脾胃学说的内涵,认为六经病证的发生发展多取决于脾胃的盛衰。①六经发病,重在脾胃。伤寒的发病过程,是邪正相争的反映。病在三阳,则邪正俱盛,相互搏争;若正气不足,则易邪陷三阴。而正气以后天脾胃为化源,赖水谷精气以充养,脾气的盛衰决定伤寒病证的发生、发展,故张仲景在《素问·刺法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基础上提出“四季脾旺不受邪”的发病观点,太阳发病—营卫不和;阳明发病—胃燥津伤;少阳发病—血弱气尽;三阴发病—脾胃虚弱;伤寒兼夹—痰饮水食。②六经传变,脾胃为枢。六经传变虽与病邪轻重、正气强弱以及治疗、调护是否得当等因素有关,但总以脾胃盛衰为前提。③立法处方,注重脾胃。在六经的辨证论治中,张仲景从理、法、方、药,处处以脾胃为本,其养胃扶正以祛邪及祛邪而不伤脾胃的思想贯穿其中,诸般治法均强调勿损脾胃。④预后吉凶,胃气为本。脾胃之气的盛衰存亡,可影响伤寒病的预后。⑤调养护理,培护后天。张仲景在药后护理和病后调养中也十分注重顾护脾胃,目的是充分发挥药效和促进胃气的恢复。
2 历代医家对《伤寒论》脾胃病内容的相关研究
《伤寒论》重视脾胃的观点,不仅对外感病的辨治,而且对临床各科疾病的辨治均有指导意义,对后世医家如吴鞠通、李东垣、叶天士、薛生白等脾胃学说,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并为脾胃学说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果志霞等[5]论叶天士在中医脾胃学方面的贡献。叶天士汲取东垣学说并结合自己临床实践,认为脾与胃虽同属中土,但其功能有别,喜恶不同,故提出了“胃喜润恶燥”的观点,强调治胃不可采用温燥治脾之法。在全面继承和发扬李东垣补脾升阳之说的基础上,叶天士创立胃阴学说,反对概用升补脾阳之法,倡导保护胃阴,运用甘平或甘凉濡润之品以濡养胃阴。《临证指南医案·脾胃》曰:“所谓胃宜降则和者,非用辛开苦降,亦非苦寒下夺以损胃气,不过甘平或甘凉濡润,以养胃阴,则津液来复,使之通降而已矣。”叶天士所创胃阴虚的理论和治法,弥补了李东垣脾胃理论之不足。同时,其在创立甘凉濡润胃阴大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胃以喜润为补”的观点。叶天士辨治脾胃之法,至今仍有重要学术价值,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赵长衍等[6]论叶天士学说指出,清代温病学家叶天士创立的胃阴学说,推动了脾胃学说的发展,丰富了温病及其他杂病治疗的理论和方法。①叶天士分论脾胃,为胃阴学说奠定理论基础。在脾胃病辨治方面,叶天士认为脾胃虽然互为表里,共同完成水谷的消化、传输,但是他们各有其特点,当分而治之。正如叶天士所曰:“胃为阳明之土,非阴柔不肯协和”,“脾喜刚燥,胃喜柔润”,是对脾胃生理病理的高度概括,明确了脾胃分治原则,为胃阴学说奠定了基础。②胃阴虚证的病因病机。纵观叶天士医案,形成胃阴虚的因素,大概有以下几种:a.情志所伤。秉素木火偏盛。烦劳郁怒,五志过极,阳升火炽,燔灼胃阴。b.外感温热燥邪。温热燥邪均为阳邪,最易耗伤人体阴液。正如叶天士所说“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肾液”,在温病的发展过程中,多见胃阴虚证。c.饮食不当。五味偏盛,或过食辛辣温燥之品。d.误治。如辛散劫阴,燥热助火等。③治疗以甘平或甘凉濡润为原则。叶天士是温病学派的巨擘,又是杂病治疗颇具独创精神的大家,其胃阴学说是对脾胃学说的补充和发展,也成为了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谷培恒[7]论叶天士治脾胃病四法指出,后人对于脾胃病之论治,往往笼统而治。惟叶天士发前人之未述,创养胃阴、温胃阳之法,以升降为契机,燮理阴阳,变通治疗脾胃病,不愧临床大家,令人回味。①温通胃阳法。胃为阳明阳土,多气多血之腑,以纳谷消化为职,一旦饮食所伤,每致伤及胃阳,水湿内停,胃阳不振。叶天士用药,本《内经》之旨“六腑以通为补”,采用温通为用,复其阳,振其衰。故叶天士主张“胃虚益气而用人参,非半夏之辛,茯苓之淡,则非通剂矣”。②清养胃阴法。叶天士云“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盖太阴之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若脾阳不亏,胃有燥火,则当遵叶氏养胃阴之法……”概而言之,凡胃阴不足者,皆可用此法。③温运脾阳法。脾阳伤,不能温运,阴寒内生,阻遏气机,阳失旋运。叶天士治之,重在动静相配。④濡润脾阴法。总之,脾胃之病,虚实寒热,宜燥宜润,固当详辨。胃为阳土,宜降宜润;脾属阴土,宜温宜运。同时,临证并有胃阳不足,脾阴津亏之证,故立养胃阳、救脾阴之法。知四法,则治脾胃病之法皆然矣。张晗睿等[8]论吴鞠通《温病条辨》是对《伤寒论》承气汤应用的继承。《伤寒论》中承气汤共有四方,即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和桃核承气汤。其中,大承气汤、小承气汤和调胃承气汤均见于阳明病篇,用于阳明腑实证。大承气汤用于燥热内盛、腑实壅滞,泻热通便两者并重;小承气汤以通便为主。治疗以腹部实证表现为主而热不盛的情况;调胃承气汤用于燥热内盛、腑实初成,以泻下燥热、调畅胃气为主;在《温病条辨》中,吴鞠通对《伤寒论》承气四方均有化裁应用。在阳明用下三法的论述中,吴鞠通明确指出热结液干之大实证用大承气汤,偏于热结而见旁流用调胃承气汤,偏于液干而热结明显的用增液承气汤,与《伤寒论》对三承气汤的论述基本一致。而温热病用调胃承气加减较多,而用大、小承气汤化裁较少的特点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温病下法对顾护津液的重视。因此,《温病条辨》很好的继承了《伤寒论》承气下法的内容。《温病条辨》对《伤寒论》承气下法的发展体现了对理论的深入阐述和方药的化裁应用上,其对“下后立法”的论述也颇具特色。徐景藩[9]论吴鞠通重视胃阴的学术思想时指出,脾胃为后天之本,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历来医家论脾胃之阴者颇多,尤以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为著,人皆知之。然而,吴鞠通在实践的基础上,步叶天士之后,对脾胃学说又有所阐发,有些论说甚为精辟。其中:①胃之特性“体阳用阴”。胃“体阳”,是指胃的组织结构和生理功能具有温热、运动的特性,胃“用阴”,是指胃需腐熟水谷所赖的主要物质,具有液状而濡润的特性,“体阳”和“体阴”共同完成胃特有的功能,并藉以维持人体各脏腑间的动态平衡。②甘凉养阴,酸甘化阴。甘能入脾、胃经,凉能制其郁热,甘凉相合能清养脾胃。不仅如此,甘凉亦能作用于肺,养肺清金。盖脾胃为后天之本,精微气血上奉于肺,故吴鞠通曰:“胃土为肺金之母也。”“凉”次于“寒”,凡内伤杂病的郁热证候,凉法的适用较为广泛、安全。吴鞠通在甘凉药物中参用酸味药物称甘酸法,并据酸甘药物的功用,具有化生阴液的效应而称为“酸甘化阴法”。戴桂满[10]研究薛生白认为,“气化湿亦化”是薛生白《湿热病篇》论治湿温的主导思想,湿温病多因内有脾湿,外感长夏湿热之邪而发生。湿为阴邪,其性黏腻。故湿温为病,多表现为阻滞气机,郁闷清阳,病变中心多在中焦脾胃,邪气留恋气分,缠绵难愈。针对以上特点,薛生白论治湿温,不外清热祛湿,宣气通阳,病之前期阶段多表现湿重于热,治疗以化湿为主,使湿祛则热孤。祛湿法的运用,根据湿阻的部位,证情之偏颇,分别有开上、运中、渗下之法,三法当中,均体现出“气化湿亦化”之理。湿温病以中焦脾胃为病变中心,湿邪侵入中焦蕴蒸不化,则致热处湿中,湿蕴热内,胶结难解,形成湿热之邪久留气分的局面。此时过用温燥则伤阳,过用苦寒则遏邪。故一般采用辛开宣化法,拨开湿邪达热于外。马明越[11]论王孟英学术思想认为,其活用张仲景方药,治疗后世杂病。纵观《王孟英医案》一书,王孟英运用的成方绝大多数为张仲景之《伤寒论》方,而且运用娴熟自如,圆机活法,多用加减,师古而不泥古。如阳明实热用白虎汤。阳明气分热证,宜服白虎汤,此为人所共知,然杂病之中亦可应用。此正是王孟英之慧眼独具矣。
3 小 结
《伤寒论》中顾护脾胃以及“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全文中多处涉及。其中六经辨证的方法对后世温病学家卫气营血辨证、三焦分证及三焦辨证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脾胃病的病因中,认为误治、外邪是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病机多以虚证、寒证为主,实证和热证所占的论述虽然不少,但热证多因伤寒转化而来,而且寒证和热证中又多兼有虚证,同时脾病多以寒湿为邪,胃病多以燥热为邪。这正符合了《伤寒论》中以狭义伤寒为主的伤寒治法。在治疗上多以温热性的药物对症治疗,对于脾胃疾病,多以白术、茯苓等健脾利湿,对于脾胃及其他脏器病症,多以炙甘草、人参、大枣、粳米等和胃益气补中。可见,脾胃在人体的疾病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脾胃能受纳腐熟、升清降浊,脾胃之气的虚衰以及寒热虚实的变化则影响其功能的发挥,直接或间接对整个人体的病理生理过程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温病大家均以《黄帝内经》、《伤寒论》为基础,结合前人的经验,以及自己的临床实践,形成具有自己独特辨证治疗体系和专著。他们对《伤寒论》中有关脾胃病证治的经典方剂进行继承发挥,用于温病的治疗,对顾护脾胃的思想贯穿于治疗的始终。
《伤寒论》将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在脾胃学说的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脾胃学说是中医理论之瑰宝,值得大家继续深入研究和实践。
[1] 俞群力.《伤寒论》的脾胃观[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5,(1):9-11.
[2] 蒋小敏.《伤寒论》脾胃病辨证探析[J].江西中医药,2011,42(12):7-12.
[3] 邱明义.《伤寒论》脾胃病证治规律探讨[J].湖北中医学院学报,2003,5(4):28-30.
[4] 李合国.《伤寒论》脾胃学说钩沉[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20(1):16-17.
[5] 果志霞,曹力明.叶天士学术思想概说[J].河南中医,2011,31(10):1106-1108.
[6] 赵长衍,席军生,王勇.论叶天士胃阴学说[J].河南中医,2003,23(3):6-7.
[7] 谷培恒.论叶天士治脾胃病四法[J].新疆中医药,1997,15(2):4-6.
[8] 张晗睿,谢婷,崔健,等.《温病条辨》对《伤寒论》承气汤的继承和发展[J].中医药学报,2007,35(6):3-5.
[9] 徐景藩.论吴鞠通重视胃阴的学术思想[J].江苏中医药,1988,(7):26-28.
[10] 戴桂满.从薛生白《湿热病篇》谈气化湿亦化[J].黑龙江中医药,1986,(5):7-8.
[11] 马明越.王孟英诊治杂病经验研究[D].石家庄:河北医科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