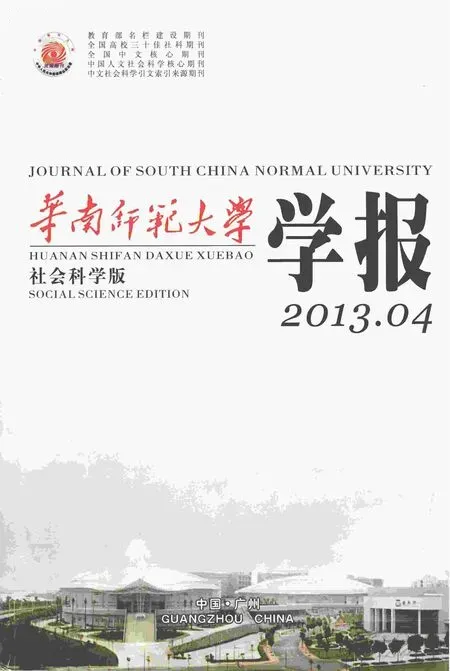依附与背离:宋若昭诗文探幽
2013-04-08郭海文
郭海文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710062)
宋若昭是大历时期一名非常有特点的女诗人。“在唐史领域,因其无关大局,向少人涉及;从女性史角度看,则其人、其作颇值得注意。”[1]127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她和她的姐妹编纂的《女论语》上,比如高世瑜的《宋氏姐妹与〈女论语〉论析——兼及古代女教的贫民化趋势》、山崎纯一的《关于唐代两部女训书〈女论语〉、〈女孝敬〉的基础研究》、黄嫣梨的《〈女孝敬〉与〈女论语〉》,这些论文都被收在邓小南主编的《唐宋女性与社会》中。对其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几篇硕博论文,比如西南大学宫月2010年的硕士论文《唐五代宫廷女性文学研究》、浙江大学余世芬2005年的博士论文《唐代女性诗歌研究》。目前,还未见对其散文进行研究的论文及论著。拙文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从性别研究的视角对宋若昭的论著、诗歌、散文进行详细梳理,以期厘清这些文学作品的意义及价值。因为“引入性别视角对唐代文学进行重新考量,其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女诗人及其作品的全面发掘,通过对男女两性的性别互动及其对士风、文风和作品特征的深入探析,重新评价和确定女性书写在唐代文学中的地位,关注唐代文学的性别因素及多样化表现,并为从全新的性别关系视角重新阐释唐代文学的生成、发展和演进提供一种思路”[2]。
有学者认为,相当多的资料表明,唐代妇女的生活实况与儒家伦理教条存在颇多不合拍之处,她们以对幸福生活和独立人格的执着追求,以冲破家庭狭小天地的积极态度,以柔韧坚定、大胆泼辣的鲜明个性,傲然冷对“主内”、“狭隘”、“依赖”等一贯加诸妇女身上的枷锁。那可谓空前绝后、个性张扬的唐代妇女形象,是当时社会环境、时代风气与其自身价值取向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中国传统文化为女性设计的角色定位有着很大差距。因此,在碰撞与冲突中的徘徊、挣扎乃至最终的超越或沉沦,也是唐代妇女群难以回避的话题。如此一来,唐代女性在开放、宽松的社会氛围中,试图冲破礼教的约束,追求爱情的权利,但又在宗法礼俗的濡染和潜在婚姻规则的制约下,最终依附于男子。她们的诗歌创作,则相应表现了这种期望与现实相背离而产生的矛盾和困惑。[3]这在宋若昭身上也有明显表现,她的《女论语》、《牛应贞传》和《奉和御制麟德殿宴百官》,都体现了这种依附与背离。
宋若昭,“贝州清阳人,世以儒闻。父廷芬,能辞章,生五女,皆警慧,善属文。昭文尤高”[4]3508。若昭生活的故乡贝州,“秦汉以降,政理混同,人情厚朴,素有儒学。自宇内平一,又如近古之风焉。”[5]4768与宋氏姐妹出生前后的大历年间(766-779)出现的“大历十才子”中有四人是河北人士,可见此地属于衣冠礼乐之地。若昭出身于儒士之家,受其父亲影响较深。
若昭生活的中唐时期正是朝廷恢复儒学的时期。唐王朝经过八年的艰苦挣扎,终于在广德元年(763)平息了“安史之乱”,勉强保住社稷。然而,表面上的光复并不能掩盖内在的隐患,重新建立稳固的社会秩序、恢复并强化原有的家庭伦理纲常成为全社会重要而紧迫的需求。这个总体需求体现在女训上,就是重视树立贞节观念,加强礼法教育,皇室、庶民均须守礼遵法。唐德宗曾下令:“旧例,皇姬下嫁,舅姑反拜而妇不答,至是乃刊去慝礼,率由典训。”唐宣宗在其女儿万寿公主出嫁的时候,特意下诏:“女人之德,雅合慎修,严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妇之节也。先王制礼,贵贱同遵,既以下嫁臣僚,仪则须依古典。”[6]840
若昭在当时,极有个性,极富才华。她既是德宗的尚宫,但“尝白父母,誓不从人,愿以艺学扬名显亲”。德宗也“嘉其节概不群,不以宫妾遇之,呼为学士先生”[7]。有学者经过考证认为:“宋氏写《女论语》,对古籍之使用虽较之《女孝经》稍逊,而出入经史,亦非一般人可比也。其用书,如《周礼》、《孝经》、《世说新语》、《礼记》、《仪礼》、《荀子》、《女诫》、《齐民要术》、《诗经》、《颜氏家训》、《千字文》、《列女传》、《周易》、《论语》、《晋书》、《左传》、《后汉书》、《尚书》、《苏武诗》皆顺手拈用,而《礼记》、《女诫》、《列女传》更屡用不缺,则宋氏亦难得之古代妇女学者矣。”[8]所以,“德宗召入禁中,试文章,并问经史大谊,帝咨美,悉留宫中”[4]3508。“由于跻身上流社会,耳濡目染了男性文化的判断标准和价值形态,加之渴求得到传统文化的认可,她们(宫廷女诗人)大多自觉地以男性的思想感情、审美旨趣和观念意识来写作,将符合正统的男性诗人的作品作为范本,刻意制造出一个类似于男人的世界。”[9]在这种背景下,她的作品应运而生。
一、教化与叛逆的《女论语》
《新唐书》记:“若莘诲诸妹如严师,著《女论语》十篇,大抵准《论语》,以韦宣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为颜、冉,推明妇道所宜。若昭又为传申释之。”[4]3508冠名《女论语》,表明了其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尊崇与传承。
《女论语》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教化;第二,叛逆。
(一)教化
《女论语》全书共十二章,分为: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和柔、守节。“其特点即在以浅俚之言把班昭《女诫》的精神化为训诲女子‘举止悉合于当然之则’的条规,且较《内则》更为切进易晓。”[10]287冠名《女论语》,表明了其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尊崇与传承。有学者认为:“在儒家‘齐治论’的系列中,对女性的要求的价值标准依次是重女孝(孝敬父母)、重妇德(贞专柔顺,三从四德)、重母教(教育子女)。”[11]39纵观《女论语》,其实也是围绕着这三部分来写的,是女孩子一生教育的教科书,即如何为人女、人妻、人媳和人母。从中可看出,《女论语》是对儒家文化的依附。
为人女:敬重爹娘。《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记载:“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唐代以孝治国,记述孔子与其弟子曾参关于“孝悌”的对话而得名的石台孝经至今还矗立在西安碑林博物馆。《诗经·小雅·蓼莪》也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女论语》则对上述经典做了详细说明:“女子在堂,敬重爹娘。每朝早起,先问安康。寒则烘火,热则扇凉。饥则进食,渴则进汤。父母检责,不得慌忙。近前听取,早夜思量。父母有疾,身莫离床。衣不解带,汤药亲尝。祷告神祗,保佑安康,设有不幸,大数身亡,痛入骨髓,哭断肝肠,劬劳罔极,恩德难忘。衣裳装殓,持服居丧。安理设祭,礼拜家堂。逢周遇忌,血泪汪汪。”[12]88
为人媳:供承看养,如同父母。《礼记》记为人媳者礼仪:“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衣绅。以适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问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父母舅姑必尝之而后退。”[13]234《女论语》的解说更容易被人理解。为人媳“阿翁阿姑,夫家之主。既入他门,合称新妇。供承看养,如同父母。敬事阿翁,形容不睹。不敢随行,不敢对语。如有使令,听其嘱咐。自古老人,齿牙疏蛀。茶水羹汤,莫教虚度。夜晚更深,将归睡处。安置相辞,方回房户。日日一般,朝朝相似。传教庭帏,人称贤妇”[12]90-91。
为人妻:夫妇有义。杜芳琴认为,夫妇有义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夫妇有敬,即夫妻相互尊重、恭敬;二是夫妇各行其宜,即双方各尽义务、各守职分的意思,义务和职分做到恰当适度,符合中庸之道。[11]56《周易》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14]366《女学》妇德第二章讲的就是事夫之德:“妇以夫为天,所仰望而终身者。好合则如鼓瑟琴、庭闱和乐,家道昌焉。夫妇反目,人伦之变,衽席化为戈矛,祸患无所底止。故事夫不可不学也。然则如之何而可?曰:敬顺无违,以尽妇道,甘苦同之,死生以之。”[15]7-8《女论语》继承了儒家这一观点,认为:“夫有言语,侧耳详听。夫有恶事,劝谏谆谆。夫若外出,须记途程。黄昏未返,瞻望相寻。停灯温饭,等候敲门。夫如有病,终日劳心。多方问药,遍处求神。百般治疗,愿得长生。夫若发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让,忍气低声。莫学泼妇,斗闹频频。粗线细葛,熨贴缝纫。莫教寒冷,冻损夫身。家常茶饭,供待殷勤。莫教饥渴,瘦瘠苦辛。同甘同苦,同富同贫。死同葬穴,生共衣衾。能依此语,和乐琴瑟。如此之女,贤德声闻。”[12]93
为人母:训诲之权,亦在于母。曹大为认为:“宗法血缘带强固的古代中国,惟接续宗祀至高无上。其含义不单在血脉连绵不绝,还包括保守家业、扬名显亲、光前耀后,这一切全靠在子孙身上。子孙贤,则家道昌盛;子孙不贤,则家道消败。而子孙好与不好,只在个教与不教上起根。在教育子女方面,母亲的言教、身教又起到特殊重要的作用。”[10]124所以,儒学家们特别重视母教。因为“人子少时,与母最亲。举动善恶,父或不能知,母则无不知,故母教尤切。不可专事慈爱,酿成桀骜,以几于败也”[15]151。所以,宋若昭训诫母亲的箴言是“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已长成,教之有序。训诲之权,亦在于母。”对男孩和女孩的教养不同,“男入书堂,请延师傅。女处闺门,少令出户。朝暮训诲,各勤事务。”如果男不知书、女不知礼,将会“辱及尊亲,有玷父母。”“如此之人,养猪养鼠。”[12]95与《礼记·内则》所说一致。“(对儿子)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13]250
关于这一点,李浩在专著中也提及:“检读唐代史传、笔记及碑志,发现有一个突出现象,这便是家庭教育中重视母仪母教。”[16]266“女性从事教育,尤其是母亲执教,虽然也能系统讲授知识,但更重要的还是情感教育贯穿于教育过程中,将爱渗透到教学内容和教育目标中。”[16]274
儒学的提倡,使女性向传统角色的复归成为一种社会趋势。
(二)叛逆
《女论语》教化的痕迹非常明显。宋若昭生于大唐,受过武则天、上官婉儿的影响,“有可能产生超越平常女性角色,成就男子功业之心”[1]154。一部教导女人如何立身处世的《女论语》,却是由拒绝婚姻、厌倦为家庭所束缚的女子所写。历史在这里错乱了性别。从中可以看到作者性别意识的不经意的流露,是那个时代性别意识觉醒的女性的代言。
1.作者自身形象定位
《旧唐书》中记载:“若昭文尤淡丽,性复贞素闲雅,不尚纷华之饰。尝白父母,誓不从人,愿以艺学扬名显亲……德宗嘉其节概不群,不以宫妾遇之,呼为学士先生。”[7]2198这种“拟男”心理和行为,“反映了她们不愿认同女性角色,一贯以男子自居的心理”[1]155,也印证了“以妇人身,行丈夫事”[17]533的可能性。据《唐六典》,尚宫是宫廷女官名。尚宫二人,正五品,掌导引中宫,总司记、司言、司簿、司闱四司之官署。凡六尚事务出纳、文籍皆印署之。司记掌印,司言掌宣传启奏之事,司簿掌宫人名簿、廪赐之事,司闱掌宫闱管钥之事。[18]349“姊妹中,若昭尤通晓人事,自宪、穆、敬三帝,皆呼为先生,六宫嫔媛、诸王、公主、驸马皆师之,为之致敬。进封梁国夫人。”[7]2199有评论认为:“宋尚宫之《女论语》虽才识不免迂腐,而趋向尚近雅正,艺林称述,恕其志足嘉尔。”[17]534“国夫人为外命妇最高封号。玄宗杨贵妃的三姐妹荣宠一时,不过封国夫人而已。依此,若昭不仅登上宫廷女官最高职位,而且得到外命妇最高荣衔。”[1]135宝历初,若昭卒,将葬,“诏所司供卤簿”[7]2199。可以说,“赐若昭鼓吹不仅是特殊的待遇,而且蕴含不以寻常妇女看待之意”[1]139。正如王建所称赞:“五女誓终养,贞孝内自持。兔丝自萦纡,不上青松枝。晨昏在亲傍,闲则读书诗。自得圣人心,不因儒者知。少年绝音华,贵绝父母词。素钗垂两髦,短窄古时衣。行成闻四方,征诏环珮随。同时入皇宫,联影步玉墀。乡中尚其风,重为修茅茨。圣朝有良史,将此为女师。”[19]176
2.不同社会角色的定位
正因为若昭生活在唐代,以女子之身而有男子之志、行男子之事,使得她不管是对父母、对公婆还是对丈夫,都不强调无原则的“卑弱“,而是针对不同的社会关系,提出不同的要求:对父母要“孝”,但孝不是一味的接受,而是有自己的话语权,“若有不谙,细问无妨”[12]88;对公婆要“敬”而“远”之,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是一味的奉献,“敬事阿翁,形容不睹,不敢随行,不敢对语。”“万福一声,即时退步”[12]91;对丈夫要“义”,不是一味的顺从:“同甘同苦,同富同贫。死同葬穴,生共衣衾。能依此语,和乐琴瑟。如此之女,贤德声闻。”[12]93最关键的是整篇并未提及唐代律法“七出”。关于七出规定,唐户婚律有“妻无七出而出之”一条。本条疏议曰:“七出者,依令: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20]297对其中最被人关注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以及妻妾相处“不妒”之美德,只字不提。《女论语》的内容“不重女教义理阐述,只讲述女性日常生活、言行的具体礼仪规则,即不重为什么,只重怎么做”[1]145。
3.在考证方面
有学者认为后两章——和柔章、守节章与前十章设题不类,此二章应非原著,而是后人增补。所增和柔、守节两章,正与礼教强化的趋势一致,反映了对女性柔弱与贞节的特别重视与倡导。[1]148从而也可以作为反证,宋若昭对此并不看重。
总之,宋若昭既是“著名的女教传教士,却又是事实上的女教叛逆者”[1]155。《女论语》有教化的功能,也是对女教的反叛。
二、追随与立异的《牛应贞传》
郭预衡先生在《中国散文史》中说:“隋唐五代是文章变化的又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21]364《四库全书总目·毘陵集》说:“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宝,诗格大变,而文格犹袭旧规。元结与及始奋起湔除,萧颖士、李华左右之。其后韩、柳继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极盛。”[22]775梁肃在《补阙李君前集序》曰:“唐有天下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以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6]5261“古文运动从酝酿到成熟,风云际会,与事者的文学追求其实颇有差异;但在对抗六朝之文道分离以及摒斥骈文之浮华靡丽这一点上,各家取得了共识。”[23]188宋若昭的《牛应贞传》也是一次追随主流文化、将文章从“骈俪变为散体”有益的尝试。全文文风质朴,少华丽辞藻。然而,作者在追随的同时,也在文中显示出与主流文化不尽相同的地方来。
在二十四史中,掌握话语权的无一例外全是男性作家。在男性作家树碑立传的人群中,女性的形象只出现在《后妃传》、《公主传》、《列女传》里,而且是群体的形象,没有单独立传,篇幅也完全不能和男性相比。在国家正史的写作人群中,女性作家的身影极为罕见。胡明先生认为:“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独偏于韵文尤其是诗词和弹词,这实际上也就决定了她们在整体战略上畏惧并放弃了古文。一部古文史除了徐淑两札书信,李清照一篇《〈金石录〉后序》外,几乎就没有什么作者。女子绝少做古文,她们在哲学、经学、历史、政治等领域便无法有像样的成绩,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女性的古文家、女性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中国妇女学术史上,除了班昭几乎没有出现过哲学家、经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这不仅决定了妇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微弱地位,无疑还严重地影响了她们文学作品中的人文思想基调。”[24]
宋若昭的《牛应贞传》可以说是个特例。从内容上讲,此篇为女子单独立传。作者及所撰写的人物,全是女性,可以说是一篇才女间惺惺相惜的文章。这一点也跟传统《后妃传》、《公主传》、《列女传》写法不同。这也许就是宋若昭标新立异之处。
全文写“四异”,突出人物才情,对主流文化最为看中的“品德”只字不提。
一异,读书异。当女孩子被教导着“朝暮训诲,各勤事务。扫地烧香,纫麻缉苎”[12]93时,牛应贞却“少而聪颖,经耳必诵。年十三,凡诵佛经二百馀卷,儒书子史又数百馀卷”。“初,应贞未读《左传》,方拟授之,而夜初眠中忽诵《春秋》,凡三十卷,一字无遗,天晓而毕。后遂学穷三教,博涉多能。”[6]1012寥寥数语,一个酷爱读书的奇女子形象跃然纸上。可惜“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25]11,与其说宋若昭在是给牛应贞立传,还不如说她是在给自己画像。
二异,交往人物异。女孩子被教导“女处闺门,少令出户”[12]93,其生活或交往的空间异常狭窄。在这种情况下,多才的牛应贞只能“每夜中眠熟,与文人谈论。文人皆古之知名者,往来答难。或称王弼、郑元、王衍、陆机,辩论锋起,或论文章,谈名理,往往数夜不已”[6]1013。其实,梦境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弗洛伊德说:“梦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荒谬的、也不是一部分意识昏睡,而只有少部分乍睡少醒的产物。它完全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达成。它可以算作是一种清醒状态的精神活动的延续。它是由高度错综复杂的智慧活动所产生的。”[26]36从中可看出,牛应贞在现实生活中属于曲高和寡的人物。
三异,著书立说异。胡适先生在《三百年中的女作家——〈清闺秀艺文略〉序》中认为:“这三百年中女作家的人数虽多,但她们的成绩都实在可怜的很。她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毫无价值的……这近三千种女子作品之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是诗词,是‘绣余’‘爨余’‘纺余’‘黹余’的诗词。这两千多女子所以还能做几句诗,填几首词者,只因为这个畸形社会向来把女子当成玩物,玩物而能作诗填词,岂不更可夸炫于人?岂不更加玩物主人的光宠?所以一般稍通文墨的丈夫都希望有才女做他们的玩物,替他们的老婆刻集子送人,要人知道他们的艳福。好在他们的老婆决不敢说实话,写真实的感情,诉真实的苦痛,大多只是连篇累幅的不痛不痒的诗词而已。即可夸耀于人,又没有出乖露丑的危险,我想一部分闺秀诗词的刻本都是这样来的罢?其次便是因为在一个不肯教育女子的国家里,居然有女子会作诗填词,自然令人惊奇,所谓‘闺阁而工吟咏,事之韵者也’。(叶观国题《长离阁集》)物稀为贵,故读者对于女子的作品也往往不作严格的批评。……在诗文选本里,闺秀和和尚道士,同列在卷末,聊备一格而已。因此,女子的作品,正因为是女子的作品,传刻保存的机会也就不少了。再其次,才是真正有文学价值的诗词,如纪映淮、王采薇之流,在这三千种书目里,只占得绝少数而已。”[27]586牛应贞的作品,并不是毫无价值之作,而是经过自己思考、有思想的产物。宋若昭为之作传,真是一篇才女间惺惺相惜的文章。
四异,插叙异。《后妃传》、《公主传》、《列女传》很少见到在传记中大段插入传主作品的例子。在《牛应贞传》中,却用了大量篇幅完整插入了牛应贞的遗作《魍魉问影赋》,这也是很奇异的一点。有人说:“传中略于事迹,而存其一赋,深得史法也。”[28]25而且牛应贞的《魍魉问影赋》自有其特殊的价值。
隋唐五代确是文体更为完备的时代,其中有些文体,诸如制诰、谏疏、序记以及赋体之文,都有新的特征。[21]365“唐人以文为赋,赋体之文有新的发展。在唐人的赋体之文中还有一种骚体,也是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21]374-375牛应贞的《魍魉问影赋》就是一篇以骚体为文的作品。作者“感《庄子》有魍魉责影之义,故假之为赋,庶解疾焉。”全篇感情丰沛、一气呵成,和《牛应贞传》融为一体。
总之,宋若昭的《牛应贞传》既是作者追随时代脚步的产物,也是作者性别意识流露、为女性立言的作品。
三、合唱与独吟的《奉和御制麟德殿宴百官》
胡明先生认为,大抵而言,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分两条大线索:一条是以《诗经·国风》为源头,经汉乐府、古诗直接晋以后吴声西曲为代表的民间歌曲,另一条妇女文学的大线索则是正统诗文辞赋的模拟创作。这条大线索的精神实质也正是一种“学”——妇女学男人。这个“妇女”,大体上包括了宫廷内后妃宫人、贵族、官僚高知的眷属、闺阁淑媛、风流才子们的声乐情人等。她们学习的对象是正统文辞赋领域的男人作品范本,不仅学内容结构词气体式、铺写技术,而且还学思想感情、审美旨趣、观念意识。浸染久之,自觉或不自觉间便沉醉于男性文化的判断标准与价值形态之中。[24]宋若昭的诗歌就是这种模仿的代表。
大历初至贞元中这二十几年,文学创作中失去了盛唐那种昂扬的精神风貌和风骨,转入对于宁静、闲适、冷落与寂寞的生活情趣和清丽、纤弱的美的追求,在诗歌创作理论上也相应地主张高情、丽辞、远韵,着眼于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的理论探讨。[29]122作为宫廷女性诗人代表人物的宋若昭,当然也加入到了时代的大合唱中。她的诗歌目前仅存一首,即《奉和御制麟德殿宴百官》:
垂衣临八极,肃穆四门通。自是无为化,非关辅弼功。修文招隐伏,尚武殄妖凶。德炳韶光炽,恩沾雨露浓。衣冠陪御宴,礼乐盛朝宗。万寿称觞举,千年信一同。[30]68
麟德殿在长安大明宫,是唐代帝王招待外宾和群臣的地方。这首诗是五言排律,作法要求比五律更严,除首联、尾联外,中间四联要全部对仗,且需工稳、贴切。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宋若昭的敏捷之才来。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箚记》中列有“唐德宗好为诗”条,曰:“唐诸帝能诗者甚多,如太宗、玄宗、文宗、宣宗,皆有御制流传于后,而尤以德宗为最。”[31]400唐德宗是一个以文武全才自命的皇帝。自贞元四年(788)至贞元十八年(802)这一时期,在诗酒宴会中唐德宗频繁出场,诗作亦不断,而贯彻其中的是有意识创造的承平理念。韦应物、戴叔伦、权德舆、崔元翰、卢纶、刘太真、武元衡等当时比较重要的文人也都得到了参与的机会。[32]贞元四年(788)三月,德宗宴群臣于麟德殿,赋诗,群臣属和;宋若昭、宋若宪、鲍君徽均有和作。[33]439
有学者认为:“入唐以来集中体现于宫廷诗中心时代与都城诗中心时代的应酬性诗歌创作,明显承携着以华美词藻外形、淫靡生活内容为标志的南朝宫廷文学传统。大历诗人在大乱初定的时代条件与乱极思治的心理状态的作用下形成的具有回味往昔升平气象的深层意绪的应酬诗创作潮流,也就在相当程度上造成唐初乃至齐梁文风在大历诗坛复兴、流行的特殊现象。”[34]110“这就使得整个贞元诗坛酬赠交往之作大大增加,在觥筹交错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也不会形成大格局。大多数诗作用语铺排而重在展现承平气象也是极自然的事情。”[32]作为大历时期宫廷女学士的宋若昭所创作的宫廷诗,与大历时期这种应酬应和声诗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大历宫廷女诗人,与大历时期诗人的诗风所受到的大环境影响基本上是相同的。他们的笔下,看不到“安史之乱”带给人民的灾难与痛苦,也看不到大历时期表面的平静下隐藏的危机。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贞元之时,朝廷政治方面,则以藩镇暂能维持均势,德宗方以文治粉饰其苟安之局。民间社会方面,则久经乱离,略得一喘息之会,故亦趋于嬉娱游乐。因此,上下相应,成为一种崇尚文词、矜诩风流之风气。”[35]87
对于宋若昭之应制奉和,诗句虽工而内容乏味,内容限于歌颂文治武功、祝福祝寿,有人评为:“(这些诗)全用御用文人的职业语言,说些歌功颂德的话,千篇一律,读来生厌。”[36]98但也有人从另外角度赞颂:“凝深静穆,有大臣端立之象,使人诵之,亦如对苍松古柏,钦其古肃之气,不复以烦艳经心也。”[37]集部339册“从其诗看,确如所言,诗风肃穆大气,有朝廷男性大臣之风,全无女子伤春悲秋、怜月惜花类纤弱与香艳气。与前朝宫廷才女上官昭容的带有女性特点的应制诗迥然不同。这正与宋氏姐妹为人的一贯风格相符。”[1]153“观此诗,即知宋若昭之胸襟与才情,品味高逸,固非一般泛泛之应制诗人所可比拟。”[38]105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九《谈丛》五又称:“女子能诗者有矣,惟宋尚宫姊妹五人为异。”胡震亨说的“异”,当指宋若昭的诗没有太多的脂粉味。
这首诗是当时大合唱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它放进那个时代宫廷男诗人的作品中应该也不分伯仲。但是,如果仔细阅读,还是能捕捉到宋若昭诗不同于大合唱的声部来。笔者曾经通过研读明人施端教的《唐诗韵汇》,发现支、真、微、东是唐代女诗人最喜欢用的上平韵,是那种不多么明快、喜乐的诗风。[39]宋若昭这首诗就是五排上平东韵,仍然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她的性别特征。阅读唐代女性诗歌,常常被其间或隐或显、或浓或淡的悲感意蕴所震撼。悲感成为唐代女性诗歌的另一主旋律,这是历史赋予一代诗人的情感色彩。唐朝前期在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综合作用下,妇女地位处于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在经历了“安史之乱”的空前浩劫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衰退,国家基本上处于“内忧外患”的处境下,于是朝廷大倡儒学,企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以维护尊卑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唐代女性的地位开始由前期的上升状态呈现出下降趋势。现实的失望使诗人们在悲伤与寂寞中咀嚼个人感情的悲欢,苦闷、迷惘、仿徨成为普遍传递的心音。[9]
总之,宋若昭是大历时期非常有才华的宫廷女诗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评汇》四称:“宫媛前有上官昭容,后有宋若华姐妹五人。昭容,仪之孙。若华,之问裔孙。诗固有种耶?”大体说来,“女性作品对于男性权力文化的依附与背离构成了唐代女性诗作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风貌”[9]。而宋若昭的诗文则是将依附与背离相结合的一种体验。她既是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才女,也受佛教影响,讲求“同甘同苦,同富同贫。死同棺椁,生同衣衾。能依此语,和乐琴瑟”[12]93。她既在韩愈和柳宗元提倡古文之前、与同时期的文人为文章由骈而散做了有益的尝试,又另辟蹊径为另一位英年早逝的才女树碑立传。她既是与德宗唱和相属时写应制诗的御用文人,其诗“凝深静穆,有大臣端立之象,使人诵之,亦如对苍松古柏,钦其古肃之气,不复以烦艳经心也”[37]集部339册。但是,诗中也在不经意间流露女性的特点。她的作品,既是对男权社会主流文学的模仿,但同时也是性别意识觉醒的自然流露;既是“安史之乱”后朝廷恢复儒教的表现,又可视为初盛唐时期女权张扬的余绪。
[1]高世瑜.宋氏姐妹与《女论语》论析——兼及古代女教的平民化趋势∥邓小南.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2]赵小华.性别:唐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3]韦依娜.唐代妇女创作群体及创作情况分析.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7).
[4](宋)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5](唐)杜佑.通典.王文锦,注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6](清)董诰.全唐文: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
[7](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8]黄嫣梨.《女孝经》与《女论语》∥邓小南.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9]余世芬.唐代女性诗歌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
[10]曹大为.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1]杜芳琴.女性观念的衍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12]李振林,马凯,主编.女论语∥中国古代女子全书 女儿规.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
[13](元)陈澔.礼记集说.北京:中国书店,1994.
[14]张吉良.《周易》通读.济南:齐鲁书社,1993.
[15]蓝鼎元.女学·妇德.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
[16]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0.
[17](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唐)李林甫.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
[19](唐)王建.王建诗集校注.王宗堂,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20](唐)长孙无忌.唐律疏义.刘俊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21]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2](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23]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4]胡明.关于中国古代妇女文学.文学评论,1995(3).
[25](唐)鱼玄机.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唐女诗人集三种.陈文华,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6][奥]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丹宁,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
[27]欧阳哲生.胡适文集4∥胡适文存三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8]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29]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03.
[30]全唐诗: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
[31](清)赵翼.廿二史箚记校正,王树民,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99.
[32]田恩铭.唐德宗与贞元诗风.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33]傅璇琮,陶敏,李一飞.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
[34]许总.唐诗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35]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6]苏者聪.闺帏的探视——唐代女诗人.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37](明)钟惺.名媛诗归.四库全书本.
[38]张修蓉.汉唐贵族与才女诗歌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
[39]郭海文.唐五代女性诗歌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