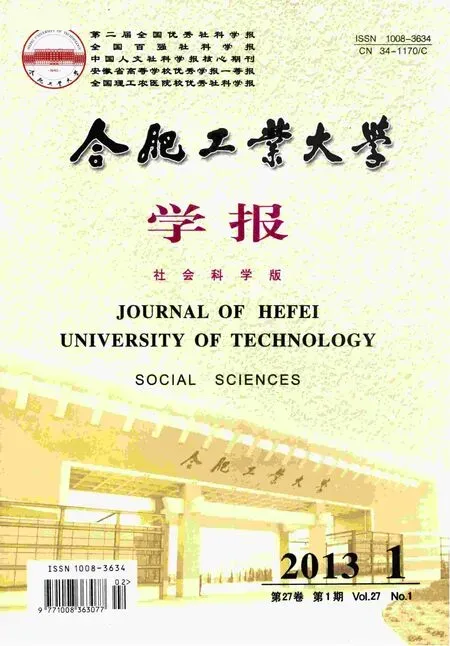异曲同工之妙的中西悼亡诗——比较《江城子》和《安娜贝尔·丽》
2013-04-07洪娇娇林玉鹏
洪娇娇, 林玉鹏
(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009)
冰心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亲情是一种深度,友情是一种广度,爱情是一种纯度。”人生在世,亲情、友情、爱情三者缺一不可。三者缺一,已为遗憾;缺二,实为可怜;三者皆缺,活而实亡。《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和《安娜贝尔·丽》,这两首悼亡诗的作者苏轼与爱伦·坡,出生于不同地点、时代以及文化背景,因为相似的坎坷生活经历,写出了同样流传于世的名篇佳作。
一、作品写作背景
本文将要比较的《江城子》和《安娜贝尔·丽》有着同样的主题,即表达对逝去妻子的思念,均为诗人悼念亡妻的作品,堪称两国文学史上悼亡诗中的经典。悼亡诗从文体分类来看,归于诗词,多为诗人即兴抒情之作,结合了爱情和死亡这两个文学创作中的两大永恒主题[1]。《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写于苏轼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时期,时年诗人四十岁。题目中的“记梦”,指的是记梦中之事,即梦亡妻之事[2]。此时,苏轼的结发妻子王弗逝世已然十年。她知书达理,生前与苏轼感情甚笃,堪称苏轼的贤内助,不仅对其的文学造诣,甚至于苏轼坎坷的从政生涯,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两人恩爱生活只过了十一年,王弗便病逝了,苏轼的痛苦可想而知。虽说这首词题为记梦,可是真正描写梦境的句子只有五句,其他皆是从现实角度出发,表达自己对亡妻刻骨铭心的思念。
《安娜贝尔·丽》是爱伦·坡除了《乌鸦》以外的又一名作。诗中描写的女主人公,通常被认为是坡逝世的妻子弗吉尼亚。1835年,坡与比他小三岁的堂妹弗吉尼亚秘密结婚,婚后生活拮据但是夫妻和睦。婚后第七年,弗吉尼亚就因为血管破裂,差点丧生,这之后一直也未能完全恢复健康。爱伦·坡曾写信给爱妻道:“你现在是我与令人讨厌、令人憎恶、令人失望的生活抗争之最大而唯一的动力。”[3]1847年,年仅23岁的弗吉尼亚去世。坡悲痛万分,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于两年后离开了人世。《安娜贝尔·丽》在他死后的年底问世[4]。
二、《江城子》与《安娜贝尔·丽》不同的表现手法
细品《江城子》全词,我们会发现词上片叙事,下片记梦言情,直语真情,沉痛感人。这与坡通篇以过去式的描写手法表达悲痛有所不同。坡很擅长营造阴郁、悲伤的情境,《安娜贝尔·丽》首句即为“It was many and many a year ago”,这一句就点出时间的久远,勾起读者无尽的遐思,也更能体现出作者的绵长爱意,历久而弥新。后文对一段哀怨爱情的描写,使读者仿佛置身于凄美梦幻的世界中,让人感受到一种虚幻朦胧之美。这也是坡的特别之处,他主张诗歌要脱离现实,在作者营造出的怪诞梦幻中品味到幽伤。然而,苏轼是在词的下片中直接描写梦境,使之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将其心中悲怆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直指人心。此外,梦境是超越时间与空间、虚无缥缈的,选取妻子对镜梳妆的生活细节,这样的场景对于苏轼来说必然是难以忘怀的,却也更加反衬出生离死别的悲伤。对于阔别多年的妻子,虽然还是平常的举动,如今只有在梦境中出现,在现实与梦境的交织中,谈不上丝毫久别重逢的喜悦,只有满腹辛酸,读来自然更加催人泪下。
其次,中国诗词讲究借景抒情,词中“孤坟”、“明月夜”、“短松冈”等意象无不表达出苏轼对亡妻深切的悼念之情。纵然是如此深刻的感情,还是跨不过生死界线,“无处话凄凉”。如果有幸还能重逢,妻子也认不出自己,可见生者在世间的辛酸。最后在梦境相逢,妻子仍与旧时一样,坐在窗前对镜梳妆,这更反衬出上片中“无处话凄凉”的悲惨。比较起来,爱伦·坡的诗歌创作更加讲求音韵美,基本上没有借景抒情,景物多起衬托作用。比如诗中“seraphs”,“soul”,“sepulcher”,“sounding”等词的运用,听起来就有如海潮涨起和海风吹过的声音,让人仿佛与诗人一齐置身梦境之中。“happy”,“heaven”和“demon”,“down”的连用也把作者对掠夺者的憎恶之情表现得酣畅淋漓。此外,坡用一个读来十分优美的名字代表自己的亡妻,Annabel Lee。它共出现七次,与“sea”,“me”,“we”等词押尾韵,贯穿全诗,不仅在音韵上非常优美,同时也象征着诗人自始至终从未改变的感情。虽然主题是爱情,但在诗歌这样悲凉的氛围里,没有一丝过往的欢乐,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只有凄凉月色和海边孤坟,令人为之动容。
再者,苏轼的这首悼亡词,与中国古代其他悼亡诗相似,多为歌颂妻子之“德”。譬如与自己相敬如宾、善良、勤劳等古代社会公认的、女子应有的品德,以及描写有关亡者生前日常生活平淡无奇的种种细节,展现出浓厚的人伦意蕴。而在《安娜贝尔·丽》一诗中,坡悼念亡妻,更加侧重体现妻子的貌“美”,诗中频繁出现“beautiful Annabel Lee”等直接描述妻子美貌的词语。这是因为在那时候的西方社会,相比起中国,女子的地位要高很多。西方社会追求男女平等,崇尚女子貌美,而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女子要遵守三从四德,只需做好贤惠妻子本分。
三、《江城子》与《安娜贝尔·丽》不同的诗学理论
不仅是苏轼的诗词,中国自古以来诗歌就推崇功用理论。虽说诗歌与政治无直接关系,但统治者将其用作束缚国人思想的工具。为了方便统治阶层的权力需求,诗歌也愈发侧重于其功用性。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认为诗歌应该做到含蓄美,“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5]。比起作者直抒胸臆,让读者在欣赏诗歌的过程中,体味作者的不尽之意,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表现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悼亡诗也就发展成为回忆过去、较少出现直接表达作者感情的诗作。以悼亡为写作主题,这本身在我国词的发展史上就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苏轼是豪放派代表性诗人,写诗从不在乎理论条框的约束,他诗词的风格总是随着情感基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苏轼刻意追求的写作风格,通常是将其慷慨激昂的感情和悲凉的情绪糅合到一起,表现在词作中。而在他人生经历的两次重大挫折之后,豪放中犹有一丝哀婉,凝聚着苏轼郁郁不得志的叹息。在《江城子》中,苏轼是将虚幻的梦境与现实结合在一起,当然,即便是梦境也是对作者生活状态的某种体现,因而没有脱离现实。紧紧围绕着“思量”和“难忘”四字,这与坡创造的意境完全不同。
在西方,诗歌更多的是推行表现主义。表现主义大量通过作者的主观幻觉、错觉,以及相对扭曲的手法表现主题,营造出压抑和恐慌气氛。它还提倡主观感觉和内心真实,这与真实影像互相交错,给人一种梦境般的不真实感。爱伦·坡就在《创作哲学》中写道:“诗歌是最崇高的文学表现形式。诗的主要目的是表现美,激发读者美的感受。美可以使灵魂激动而变得高尚,最高形式的美必然使敏感的心灵悲泣。因此,诗歌的基调就是忧郁。”[6]在《诗的原理》中,他则指出:“为了保持最深刻、最强烈的刺激的效果,一首诗应以半小时能读完最佳,过长或者过短的诗,如史诗或教训诗都是不可取的。”[7]除了对诗歌的基调、长短作出的具体要求,他还认为:“诗歌中应该使音乐通过它的格律、节奏和韵律等各种形式,成为诗中重大的契机,让感情得以激动,从而使灵魂的斗争最最逼近那个巨大的目标——神圣的美的创造。”[7]这首《安娜贝尔·丽》,就是他的诗学理论的最好支撑。它有着浓厚的哥特式氛围,营造出凄美的意境,自然地烘托出了诗人悲伤的情绪。
四、《江城子》与《安娜贝尔·丽》不同的文化背景
总结以上两点不同之处,是因为作者各自的创作理念不同而造成的差异,但除了个人因素,两人生活的文化背景不同,也使得这两首悼亡诗词各具特色。
(1)中西死亡观的不同 这也是两首诗作最大的区别所在,中西方人都对生死问题非常注重,而孔子的思想为中国文化中的死亡观奠定了基本框架。孔子曾曰“未知生,焉知死”,这正是儒家思想在面对死亡问题采取的基本态度:一种道义至上、相信命运的超然态度。同时这也是我国传统死亡观的基本观念,人们认为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点,面对死亡似乎终究摆脱不了“宿命论”的阴影。并不是说国人比起西方人有多么愚昧无知,这与一个人的知识水平没有必然联系,只是中国这种“信命”的理念本质稍显感性。认为天命不可违抗,更多的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精神慰藉,能够缓解在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下的压抑生活,甚至达到平衡心理的功效[8]。有诗词写道“人死犹如灯灭”,人死就意味着一切的消失,不可复归,面对死亡人们通常采取的态度都是忌讳、回避,因此对于爱妻死亡,苏轼是非常悲痛的,遥想爱妻长眠于地下的折磨万分难熬。并且,在中国古代社会坚信有神灵的人不在少数,回忆逝者生前的生活,怀念自己与其度过的快乐时光,也反映出诗人内心底对死亡的敬畏之意,因为它与生俱来、不可逆转,是始终笼罩在生命之上的巨大阴影。
西方人信奉基督教,宗教信仰使他们相信,死并不是万事的终结,死后去往乐土天堂也是一个人必然的归宿。而且比起一个人自然寿命的长短,真正有意义的应当是其生存价值,这就让西方人面对死亡,心态更为坦然。《圣经》中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死亡是注定的,唯有死亡,才能解脱原罪,最终到达天堂。丁宁生的著名诗作《过沙洲》,诗人就把面对死亡的来临,描写成在暮色苍茫时分扬帆过沙洲,泰然地期盼着与领航人(上帝)的见面。死亡是个体生命的终结,仍将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因而,西方人更能够直面死亡,保持一种恬静的心境。因为他们深刻相信,死亡是对“受难”人类的拯救,以到达永恒的天堂。比起如何避免死亡,他们企图达到灵魂不朽的境地,把绝望化为希望,死亡成为永恒的生命。《安娜贝尔·丽》也不例外,一句“天上的天使也不能将我们俩的灵魂分离”是坡坚信着,即使妻子已经逝去,灵魂仍在一起,表现出了一种超脱的乐观精神。
(2)爱情观不尽相同 苏轼通过提及妻子的日常生活琐事表达悲痛的感情,不仅因为古时诗坛推崇诗歌要含蓄美,更多的是因为社会因素。中国这样一个自古就很保守的国家,甚至未婚嫁青年男女也不能自由选择恋爱对象,这也决定了诗人不会大胆、直率地表达心中所想。而且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不仅要“门当户对”,还要建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基础上,可见保守、苛刻及专制的程度之深。中国古代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思想影响甚深,虽然婚姻多半并非双方满意,但中国人重家庭、重伦理的保守风俗也影响着我国古代诗人们。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苏轼对自己亡妻的这份深情相当难得。
正相反,开放的西方社会,产生了以“个人为本位”的爱情婚姻观,一切都以追求个体幸福为最终人生目标。人们自由选择婚姻恋爱对象,自我意识较我国古代社会人们要强许多。能够影响西方人择偶的社会因素很少,择偶不论年龄大小、相貌如何,甚至是否结过婚,追求的是所谓的“浪漫的爱”。与我国反差最大的就是女性的地位:西方社会女性与男性地位较为平等,日常生活中需要互相尊重对方,不像中国古代女性地位低下。因此在这样一个奉行个人主义的社会,天赋人权的思想自然成为了思维常态。有了这些社会形态作为基础,西方社会夫妻大多平等自由,讲求浪漫。在《安娜贝尔·丽》中,诗人也多直接描写夫妻间的恩爱感情。对于自己年轻妻子的早逝,坡把自己的悲痛之情渲染到了极致,即使面对着来自外界的各种压力,作者表现出了对命运的反抗,绝不妥协,就是死亡也不能分开他与爱人。
(3)宗教的影响不同 《安娜贝尔·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宗教给爱情带来的悲剧,是一种比死亡还要强大的力量。虽然社会风气开明、男女地位平等,但是基督教的教义中,一度传播甚广的禁欲主义还是给西方社会人们以重创。当“天赋人权”与“禁欲”的神性碰撞,势必会带来沉重后果。在本诗中,体现宗教性质的词汇有很多,如“the winged seraphs of Heaven”,“angels”,“demons”等。“Angels”象征着自然的力量。还有“her highborn kinsmen(她出身高贵的家人们)”,“家人们”的出现,想要把女主人公的遗体带走并埋葬起来,这象征着人世的巨大压力,即世俗的偏见,这样一种残酷的压迫力量,让人心生畏惧[9]。最后“tomb”一词,实际是暗指相爱的两人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在经过与压迫势力的斗争后,作者表现出的无所顾忌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追求,无疑可以感觉到“人”这一形象的高尚和伟大,从而赋予这段爱情悲剧美的内涵。诗作中这些明显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描写,完全符合坡的诗歌理论,即“把滑稽提高到怪诞,把害怕发展到恐惧,把机智夸大成嘲弄,把奇特变为怪异和神秘”[10]。
五、结束语
爱情和死亡,这两个文学作品恒久不变的主题,尽管都是悼亡诗,苏轼和爱伦·坡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各自信奉的诗学理论等原因,创作出了既相似又有很大不同的作品。通过对中西方这两首具有代表性的悼亡诗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但追溯根源,都是为了表达对亡妻深切的怀念。深切的动人爱情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矢志不渝的忠贞信仰打动了每一位读者的心。因此,无论主客观因素如何,人类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都是一样的,这样深刻的感情是没有国界、没有地域,也没有时空之分的。
[1]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4.
[2] 周汝昌.唐宋词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693.
[3] 巫阿苗,杨 斌.诗歌《乌鸦》艺术魅力分析[J].文学教育,2010,(11):90-92.
[4] 常耀信.美国文学简史(修订本)[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104-115.
[5] 刘象愚.文学批评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4-51.
[6] 曹明伦.创作哲学[J].中外诗歌研究,1998,(4):56-62.
[7] 曹明伦.爱伦·坡精品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675-708.
[8] 谭瑾瑜.论埃德加·爱伦·坡与海子诗歌里的死亡哲学[J].长沙大学学报,2008,(3):106-107.
[9] Walker I M.Edgar Allan Poe:the Critical Heritage[M].New York:Routledge &K.Paul,1986:27.
[10] 孙法理.爱伦·坡短篇小说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