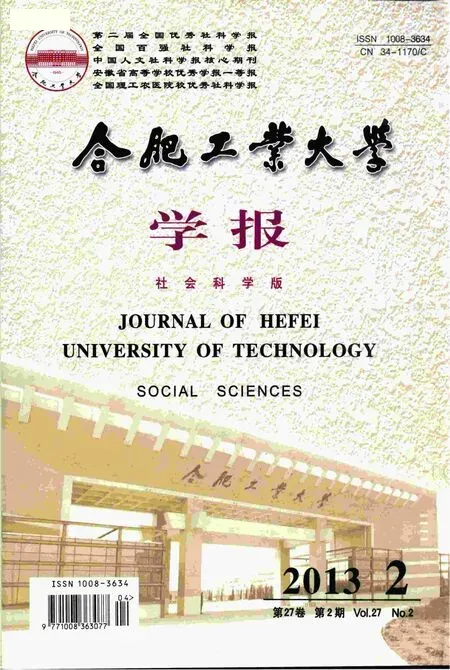翻译目的论视阈下的文学翻译批评——以《格列佛游记》为例
2013-04-07胡作友李而闻
胡作友, 李而闻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009)
一、引 言
对于功能主义目的论是否适合于指导文学翻译的问题,国内外翻译界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目的论只对非文学文本有效,文学文本要么没有具体目的,要么风格太复杂。但是有些学者则认为该派理论对于文学翻译具有一定的影响以及指导作用[1]253。作为以目的法则为主导的翻译标准多元化的理论体系,功能翻译理论强调译本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本预期功能为目的,根据各语境因素,选择最佳的处理方法。对文学翻译而言,语言功能、文本类型、翻译目的或翻译发起人以及文学和文化语境等因素都对翻译起着制约作用[1]254。本文从此论点出发,以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的两个文学译本为例,尝试分析翻译目的论对文学翻译批评的指导作用,并最终证明翻译目的论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批评。
《格列佛游记》是乔纳森·斯威夫特创作的一部杰出的游记体讽刺小说。作者通过幻想旅行的方式来影射现实,反映出当时英国社会的现实,深刻揭露了统治集团的腐败和罪恶,并有力抨击了侵略战争和殖民主义的危害。国内不乏对于《格列佛游记》的研究,但是多停留在文学层面,针对其译本的研究为数不多,尤其从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出发来研究其译本的论文则是少之又少。这也是本文为何以《格列佛游记》为例来尝试将翻译目的论用于文学翻译的原因。
二、翻译目的论概述
翻译目的论作为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中的核心理论,由汉斯·威密尔(Hans Vermeer)提出。威密尔突破了其老师凯瑟琳娜·雷斯(Katharina Reiss)所提出的原文与译文的对等功能的限制,将翻译研究从原文中心论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诠释翻译活动,从而发展了功能派的主要理论——目的论(skopos theory)。skopos是希腊词,意思是“目的”。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这个目的有三种解释:“译者的目的;译文的交际目的;使用某种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2]本文所强调的目的是其中的交际目的。
翻译是一种基于源语文本的转换行为,而任何翻译行为都有一定的目的,产生一种结果、一种新的语境或事件。决定翻译目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受众。这些受众有他们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的受众,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生产的语篇”[3]12。威密尔认为原文只是为目的受众提供部分或全部信息的源泉。因此,“翻译中的忠实不是对形式或内容而言,而是对文本功能而言。这就破除了语言学字词句观的局限,突破了传统直译意译的二元对立模式。这在理论上解决了直译意译的争端,在实践上有利于译者摆脱以文本为中心的等值论的束缚,有利于译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1]254。
三、《格列佛游记》两个译本语境条件、参与者和译本充分性的比较分析
笔者曾将威密尔的翻译目的论主要论点归纳如下:(1)翻译是一种基于源语文本的有意图的、人际的、以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互动行为。翻译行为的语境条件与历史和文化相关,语境中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决定行为人的语言或非语言行为,也决定其知识结构及其对世界的看法。(2)在翻译行为实施过程中,不同的参与人起着不同的作用。(3)目的语文本的充分性比等值更重要[1]252。
本文将在上述这三个论点的基础上,分别从语境条件、参与人和译本充分性这三个方面来比较《格列佛游记》的两个译本——张健译本和王维东译本。两名译者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差异而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产生出不同的译本,从中可以发现翻译目的论在翻译行为中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
1.语境条件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互动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交际行为。“每个行为都是特定文化情境中的行为,翻译也不例外”[3]34。也就是说,要把翻译看作具体的文化语境中的行为,“翻译中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在具体的语境中做出的”[4]13。语境(context)在交际学范畴中指的是影响语言交际者交际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而翻译行为中所指的语境条件则是译者在从事翻译工作时,目的语所在地的历史背景、文化以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等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决定行为人的语言或非语言行为,也决定其知识结构及其对世界的看法”[1]252。
根据在CALIS联合目录的查询,《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译介多达102种版本[5]51,其中张健先生译本算是其中比较成功的一个版本。张健先生翻译《格列佛游记》的时间是1944年冬至1946年夏,正值抗战胜利前夕至国共内战爆发初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局极不稳定,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惶惶。日本对于中国残暴的殖民侵略,使中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抗战最终取得胜利。但是,中国人民尚未从抗日战争中恢复过来,“国民党反动派就在美国的支持和策动下,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并于6月26日以公然大局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开始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内战”[6]。再加之此前国民党对于日本侵华采取的不抵抗政策以及后来在皖南事变中倒行逆施的做法早就令全国各地的进步人士对其深恶痛绝并口诛笔伐,因此使得中国人民对于国民党统治阶级的不满日益剧增。
与之相反的是,译者王维东先生翻译《格列佛游记》的时候,中国早已不再是当时惨受压迫、政局动荡不安、人民因饱受战争之苦而民不聊生的中国。21世纪的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后,无论是在经济文化还是科学技术上,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中国已然在国际社会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民来说,殖民主义侵略早已成为尘埃。
张健与王维东的译本,从语境条件方面来看,是截然相反的。这也就决定了两者在翻译《格列佛游记》时,定然会根据各自的目的语语境条件,来选择适合其目的语文化现状的翻译策略。
2.参与人
“一般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涉及三方面的参与者:原文作者、译者、译文接收者(读者或听众)。功能派还加入了翻译过程的发起者、译文使用者和收受者等其他参与方”[7]48。考虑到一个参与者可以同时扮演好几种角色,因此本文选取了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三个参与人进行对比分析,即:发起者、译者和译本受众。
(1)发起者 翻译过程中的发起者可能是个人、群体或机构,这个角色所承担的任务就是发起翻译活动。同时也是发起者给出翻译要求(translation brief),其中“包括需要译文的目的、原文、译文、收受者、使用译文的时间、地点、情形、交际媒介以及译文应有的功能”[7]48。译者在从事翻译时,必须遵循发起者给予其的一系列翻译要求来完成他的译本。因此,发起者这一角色在翻译行为中是十分重要的。本文所要探讨的发起者主要还是指出版这两个译本的机构——正风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张健先生的译本最早是由正风出版社于1948年出版。正风出版社是由当时爱国进步画家徐悲鸿在沙坪坝出资筹建的,出版了很多享誉文坛的世界名著译本和国内进步书籍,《格列佛游记》便是其中之一。作为一部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通过具体的情节,鲜明深刻地揭露社会的丑恶现象和矛盾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的某些本质。正如张健在1962年出版的译本序中所说:“《格列佛游记》是一部爱憎分明的杰出讽刺文学作品,它不但帮助我们认识18世纪初英国统治阶级的残酷和无耻,而且帮助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方面,从而使我们更加憎恶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8]14
因此,张健先生译本的出版实际上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其功能及目的就是为了启蒙和激励当时的中国人民,使其认清殖民侵略的丑陋目的以及资本主义的某些本质。这些都是由正风出版社爱国进步的性质决定的。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6月1日,是共青团中央领导的中国唯一的国家级专业少年儿童读物出版社,所以其读者对象针对的是0-18岁的少年儿童。成立至今,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所刊行的图书,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和促进未成年人在思想、文化、道德等方面建设,为了中华民族21世纪的伟大复兴,为了国家和社会的科学发展和和谐发展。因此,王维东先生是将《格列佛游记》作为儿童文学来翻译的。
相对于正风出版社来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针对的读者是21世纪的中国儿童,而非建国前,因饱受战争及动乱之苦而奋起反抗的中国人民,因此这两个出版社在本质上就存在着极大的区别。因为发起人在翻译行为中充当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所以其译本之间也会存在巨大的差别。
(2)译本受众 在翻译目的论中,受众是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其实这一点也同样包括在发起者所提供的翻译要求之中。根据上述对于发起人——即出版社的分析,两个译本各自的受众已经显而易见了:张健先生的译本针对的受众是刚经历了日本侵略战争,又因国民党对于权力的贪婪而再一次陷入内战的中国人民;王维东先生的译本针对的受众则是在21世纪和平年代中茁壮成长的少年儿童。这两类受众有他们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从而也就决定了译本在被创作时必须要考虑这些受众的接受程度,满足他们对于译文的期待。
张健先生译本受众决定了译本被创作的交际目的就是为了唤醒中国人民对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深刻认识,激发他们对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统治者的仇恨和愤怒,从意识方面入手,间接推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进程,争取早日得胜,中国农奴翻身做主人。而王维东先生的译本的受众决定了王维东先生在进行翻译工作时必须考虑如何使得译本能更加容易被中国的少年儿童们接受和理解,从而达到对于未成年人的启蒙和教育作用。正如王维东先生在译本的序中所提:“原作字艰词涩,行文技巧极其复杂,为了方便读者,译文采取了讲故事的手法,以求通俗易懂,自然流畅,让读者体悟到阅读是一件愉快惬意的事情。”[9]3
(3)译者 译者是翻译链上最重要的一环,这点毋庸置疑。译者根据发起者的翻译要求为指导,从特殊的翻译任务中总结出译文的交际目的(此目的也可以是发起者直接给出),交际目的则使译者决定如何完成翻译任务。译者是翻译过程中起积极作用的专家,完全掌握使用何种翻译手段,如何完成翻译工作[7]48。
由此可见,最终究竟会呈现出怎样的译本关键在于译者。张健先生是一名著名的翻译家,对于翻译策略以及技巧的运用游刃有余。再加之他亲身经历了战争与动乱,深刻体会了战争的残酷,因此对于译本交际目的的领悟极其透彻。王维东先生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副教授,迄今为止发表了不少关于翻译的论文、译文,也出版了不少译著,拥有极其丰富的翻译经验。因而正确把握译本的交际目的,针对中国21世纪的未成年儿童将《格列佛游记》作为儿童文学翻译出来,对于王维东先生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来,语境条件以及参与人中的发起者和受众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译本的交际目的,而译者则会根据交际目的,同时综合考虑以上这三个因素,通过其专业的判断,决定采取何种翻译方法和策略,最终呈现具有不同功能及交际目的的译文。
3.译本充分性
这里所说的充分性与等值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动态的、共识论的,表现为对翻译要求的实现效果,即译文功能是否有效实现;而后者是静态的、符合论的,即以与原文相对照的结果为判断的标准”[4]14。译本的“充分性指目的语文本应该‘充分满足’翻译的各种要求。翻译的目的决定充分翻译所需要的对等形式”[1]252。目的论认为“文本是一个提供信息的信息源,读者从中选择感兴趣的或重要的信息”[3]25,因而“原文不再是译者翻译首先或是首要考虑的标准,它只是译者选取信息时诸多因素中的一个”[3]31。由此可见“译文自身的功能性要比它对原文的忠实性更为重要”[4]14。毕竟,译文可能与原文的功能不同,所以译者应该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而不是对等原则。因此评判一个译本充分与否关键在于看这个译本是否满足翻译要求,是否达到译本的交际目的。
就充分性而言,两个译本都完成得很好。但是张健的译本可能更忠实于原文,对于原文信息的保留更多一些,所以就等值性而言,张健的译本要胜于王维东的译本。这主要还是因为张健的译文无论是历史背景、政治情况,以及功能都与原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因此,张健在从事翻译过程中为了完整地再现原文的功能,在考虑文化差异的情况下最大程度的保留原文的信息。相反的,王维东的译本功能与原文功能并不相同,所以翻译时仅仅保留有用的信息即可。同时考虑到未成年人对于信息的接受能力,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还需对原信息进行处理,使其通俗易懂,这样一来必然会再舍去一部分信息。
但是,在对信息根据翻译目的进行取舍的同时,还要考虑到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intratextual coherence)和语际连贯(intertextual coherence)的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呈现出一个好的译本。
四、《格列佛游记》两个译本翻译方法的对比分析
德国功能目的论的代表人物诺德(Nord)根据译文不同的功能将翻译方法划分为纪实翻译和工具翻译两种方法。“纪实翻译是对作者和源语文本的读者间的交际‘进行记录’,翻译时无须根据目的语语境作出调整。”“工具翻译的目的是在译语文化中实现新的交际功能。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交际功能,而不仅仅是对源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际行为所做的文献记录。”[10]89-91也就是说,纪实翻译注重的是源语文化,而工具翻译注重的是目的语文化。
由于张健先生和王维东先生的译本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实现的功能不同,所以两者采取的翻译方法也就不同。张健为了再现原文的功能,注重的是源语文化,所以采取的是纪实翻译的方法。而王维东为了使译本更易于被中国的青少年儿童所理解,注重的是目的语文化,所以采取的是工具翻译的方法。接下来,通过对于几个具体实例的对比分析,来更好地理解张健和王维东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不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
例1:原文:But the charge of maintaining me,although I had a very scanty allowance,being too great for a narrow fortune,I was bound apprentice to Mr.James Bates,an eminent surgeon in London,with whom I continued four years.[11]15
张译:虽然家里只给我很少的学费,但是这对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还是太重了。于是我就到伦敦城著名的外科医生詹姆斯·贝茨先生那儿去当学徒;我跟他学了四年[8]1。
王译:家里倒也给些生活费,但因入不敷出,我就拜伦敦一位很有名望的外科医生詹姆士·贝慈先生为师,跟他学了四年[9]1。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相较于张健的译文,王维东的译文更偏向于中国话语的陈述方式。王译中,仅“入不敷出”四个字便涵盖了“being too great for a narrow fortune”所要表达的含义。王维东采取的是意译的方式,而张健的译文则采取直译的方式,译成了“这对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还是太重了”。随后的“去……当学徒”以及“拜……为师”这样的翻译方式以及对于标点符号的处理方式也同样表现出张健的译本更等值于原文,而王维东的译本中的用语则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
例2:原文:On the 5th of November,which was the beginning of summer in those parts,the weather being very hazy,the seamen spied a rock within half a cable's length of the ship.[11]16-17
张译:十一月五日,那一带正是初夏时节,天气沉霾多雾,水手们在离船不到五十寻(三百英尺)的地方发现了礁石[8]25。
王译:到了十一月五日,在当地正是初夏季节,海面上雾气沉沉,水手们发现前方三百英尺远有一块巨大礁石[9]3。
两者对于原文中“half a cable's length”处理方式也截然不同。在张健的译文中,直接将其译成“五十寻”,然后紧接着直接用括号加注表明其具体的距离为“三百英尺”;但是在王维东的译文中,他直接将其译成了“三百英尺”,省略了“五十寻”的含义,并随后对其加注进行解释:“英尺:英制长度单位。一英尺约等于0.3米,300英尺约等于91米。一英尺合12英寸”。之所以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别就在于王维东的译本所针对的受众是中国的青少年儿童,对他们来说,“英尺”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计量单位。更别说“五十寻”了。因此,为了帮助他们理解,王维东省略“五十寻”的含义不译,直接将其译成“三百英尺”并对其进行详细的解释。由于张健的译本针对的是中国有知识、有思想、有学习能力的成年人,所以并不需要像王维东那样详细进行解释,而只是给出“五十寻”的概念并简单地解释为“三百英尺”,这对于成年人来说就已经十分好理解了。
例3:原文:For,if the town intended to be destroyed should have in it any tall rocks,as it gener-ally falls out in the larger cities,a situation probably chosen at first with a view to prevent such a catastrophe;or if it abound in high spires,or pillars of stone,a sudden fall might endanger the bottom or under surface of the island.[11]45
张译:因为他想毁掉的城市万一有一座耸立的岩石,这是比较大的城市常常有的情况,也许当时就是为了防备这类灾祸才选的这些地点;再者,如果一座城市到处都是高大的尖塔,和石柱,那么飞岛突然下降也许会危及岛底或下表面[8]151-152。
王译:如果想要毁掉的城市像通常一样矗立高高的岩石(当初选择城址时,人们也许已经考虑到对这类重大灾难的预防),或者如果该城市到处都是尖塔或石柱,那么突然落下去就会危及飞岛底部[9]152。
原文作者在写这一句的时候,含沙射影地影射了当时英国社会中的一些势力和现象,并非仅仅如表面意思那样简单。但是在这两个译本中,只有张健的译本给了注释:“岩石”是“影射有权势的贵族”、“尖塔”指代“著名英国国教教士”、“石柱”是指“有影响的‘白手起家’人士”,从而清楚明白地展现了原文的深层含义。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异,是因为王维东的译本的目的并不像张健的译本那样要激发起中国人民对于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厌恶之情,所以对于当时英国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文化背景的解释并没有必要。毕竟其译本所针对的受众是21世纪的中国儿童,而非20世纪前期受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压迫的中国人民。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译者只有根据发起人给予他的翻译要求为指导,综合考虑目的语所处的语境条件以及译本所要达到的交际目的和功能,在保证译本充分性的前提下,依据专业知识对信息的取舍做出判断,从而采取适当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才能创作出符合受众期待的好译本。本文打破认为翻译目的论不适用于文学翻译批评的论点,以《格列佛游记》的两个译本为例,在翻译目的论的指导下,从语境条件、参与人和译本充分性三个方面分别对张健和王维东的译本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比较两个译本各自采用的翻译方法和策略,结果印证了翻译目的论对于文学翻译实践的解释力。翻译目的论与文学翻译实践及其原理存在着合乎逻辑的不谋而合之处,说明翻译目的论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批评。
[1]胡作友.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述评[J].学术界,2008,(6):253-254.
[2]Mona Baker.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4:29-33.
[3]Christiane Nord.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12,34.
[4]潘平亮.翻译目的论及其文本意识的弱化倾向[J].中国翻译,2006,(1):14-15.
[5]滕 梅,颛 宇.意识形态作用下译作的变形——《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译介[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1,(5):50-53.
[6]王宗荣.全国解放战争史专题[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53-54.
[7]仲伟合,钟 钰.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1999,(3):47-49.
[8](英)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M].张 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9](英)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M].王维东,译.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
[10]方梦之.译学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89-91.
[11]Jonathan Swift.Gulliver's Travel[M].New York:W.W.Norton &Company,Inc,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