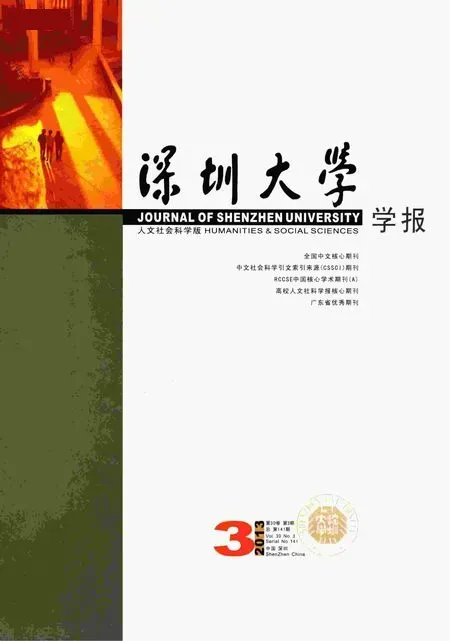满族汉化:对新清史族群视角的质疑
2013-04-07章健
章 健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满族汉化:对新清史族群视角的质疑
章 健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清史学界传统的“汉化”说近年来由于美国新清史学派的挑战,在西方主流学界已濒于式微。然而,这一学术进展却源自新清史对“汉化”极度狭隘的界定。新清史强调的满族族群认同的始终存在以及清末的反满浪潮,很大程度上均可以普世的、单一民族统治下都普遍存在的“反政府”、官民两大群体在社会功能性上的区别和对抗来解释,无须以“民族冲突”、“族群”视角理解之;此两种现象与满族汉化毫不矛盾;清代的民族压迫、社会地位以民族属性划分的传统史观,忽略了统治阶级、既得利益集团的优势积累效应,应该得到修正。
满族汉化;新清史;八旗;族群视角;社会分层
长期以来,学界解读清代政治成就时采纳的是“汉化说”,即清朝统治的核心特点在于统治者采取“汉化”政策和满族统治集团在方方面面的日渐汉化。近20余年,此观点受到美国新清史学派的强大挑战。盖博坚(R.Kent Guy)在2002年称汉化说“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可说已经死亡”[1](P163)。罗威廉(William Rowe)也在其新著《大清》中称新清史成功颠覆汉化说[2](P6)。尽管定宜庄在2008年严厉批评大陆史学界对美国新清史的忽视[3],它在中国其实不乏不同程度的同情者。郭成康早在2000年就在其《也谈满族汉化》一文中对传统的“汉化”观做出修正,口径与新清史颇为接近[4]。近年大陆出版的清史论著中,“汉化”二字明显叫得不像以前那么响亮。可以预想,挟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霸主之势,该派观点将进一步冲击我国史学界。
汉化论是否真的如新清史批评的那样在学理上站不住脚?本文通过对新清史的几位领军人物观点的直接分析,重新确立汉化观的合理性并质疑新清史强调的“族群”视角。
尽管涉及学者的人数众多,甚至未必所有学者都愿意被纳入该学派,但与前辈比较,新清史更强烈地呈现如下特征:(1)强调清朝是少数民族民族建立的“非汉”征服王朝,倾向于划清与中国历史上汉族王朝的界限;(2)强调清代满族(或者“八旗”)的族群认同和对满族特色的研究,反对满族被“汉化”的说法和“汉族中心论(Sinocentrism)”;(3)提倡以族群、边疆等视角和新的理论框架(如殖民主义)来审视清代,强调民族认同中的主观元素;(4)提倡采用汉语以外的满语、蒙古语、维吾尔语等少数族群的语言和文献进行清史研究。虽然清史名家柯娇燕(Pamela Crossley)自诩不属于新清史(她狭窄地将之界定为欧立德领衔的“阿尔泰学派”),但是她的学术立场总体上符合上述几项特征,因此本文依然视她为新清史的领军人物[9]。可以看出,该学派的学术立场、思路和方法相辅相成、融为一体。
一、中美对汉化的定义之争
何谓“汉化”?在包括笔者在内的多数中国学者看来,“汉化”是一个表述国家间、民族间文化交流中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靠拢、单边倾斜的缩略语。它跟世界古代史中出现过的 “埃及化”、“希腊化”、“罗马化”、“阿拉伯化”,以及最近两百年的全球“西化”乃至“美国化”等等政治文化现象没有本质区别。满族在关内的经历,就是这一定义的典范。虽然清帝强调满人“不能忘本”,冀望重振“满洲之道”,但是满语、后金旧的决策模式、收继婚、殉葬、骑射能力、萨满等满族的标志性旧俗,均在汉族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影响力渐渐趋弱。满族在长期与“汉人”交往的过程中,的确是“渐就中国之制”,在语言、审美情趣、价值观、生活习俗上日渐向汉人单边趋同。入关后的满人与努尔哈赤时代的女真人可谓大相径庭。反观清代的汉人,除了薙发留辫以示归顺新政权之外,与明代汉人总体上未见巨大改观。同样是少数人统治,满族入关与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经历迥异,不但丝毫没有影响汉族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以及汉民族的文化自信心,也并未撼动汉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主流地位。李鸿章著名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惊呼,完全针对磅礴汹涌的西方影响而发。所以,以我国学界对“汉化”的传统认识来看,满族汉化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新清史坚持用acculturation(“社会适应”、“文化趋同”、或者“涵化”),反对用 assim ilation(即“吸纳”,“汉化”的一个较中性的表述)或者sinicization(“汉化”),来表述满族的文化变迁。在他们看来,满族“汉化”与其在清代始终拥有的独立认同矛盾,也与清末汉人的“反满”浪潮矛盾。似乎,只有满族的族群认同消失,而且未发生排满,“汉化”才成立。柯娇燕的表述就很有代表性。她称:“有限的汉化根本称不上是汉化,最终毫无意义[6](P3)”。 如此,中美学界在汉化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变成了一个定义之争。应该指出,美国新清史的立场太过狭隘苛刻,近乎荒唐。因为如果没有发生政权更替,帝制和集权统治时代的执政集团怎么可能丧失其特殊的群体认同呢?即便是单一(同)民族统治下,这都不可能发生。作为清代的统治阶级,满族的政治地位被制度化,已经充分保障了其群体认同的延续。即便是汉族统治下的明朝,还是以后的统治者都有各自强大的群体认同,其认同也都有制度保障,发生政权更替时双方都会爆发激烈的流血冲突。所以,满族的群体认同的存续,与满族汉化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不可也不该混淆对待。
再者,“涵化”、“趋同”作为描述语,更为含混,貌似超越某种“中心主义”,却完全掩盖了民族文化融合中的巨大不均衡性和满汉文化交融中汉文化的主流性。如果我们将新清史的逻辑执行到底,我们不但不可以提满族汉化,历史上所有伴随帝国武力和文化征服而出现的文化融合,如“希腊化”、“拉丁化”、“埃及化”、“阿拉伯化”、“俄罗斯化”,乃至当今的“西化”、“美国化”等等描述性缩略语,都必须全盘抛弃。这显然是反历史的,也有失公允,毫无必要。在以下几个章节,笔者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二、晚清“反满”和“满洲之道”
新清史对纵贯清代、特别是晚清时涌现出来的“反满”思潮特别重视,强调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中对满人的仇视和屠杀,以此力证“汉化”说的虚妄。但是,“反满”思想极大程度上可以用人类历史中普遍存在的“反政府”现象解释,无须从“民族性”或者“民族压迫”视角考量,更无须跟“汉化”问题挂钩。我们知道,人类社会中“官”与“民”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张力。对政府不满意,持强烈批评、怀疑态度,甚至妖魔化政府,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官民矛盾激化时,常常你死我活,即便双方属于同一民族。农民军对朱姓藩王和明军将官从不手软,法国大革命中巴黎的断头台上鲜血淋漓,俄国革命中沙皇和贵族们遭大量屠杀和流放。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清朝中晚期,西风渐炙,政府丧权辱国,内外交困,变革迟缓,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国家每况愈下,致使民众对政府强烈失望和不满。在这个大背景下,清代即便是汉族政权当政,面对的社会矛盾一样尖锐,类似明朝末年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民间暴动发生的可能性很大。事实上,明王朝的灭亡很大程度上是同民族的流民大起义的结果。而且,以明朝皇权高度膨胀,藩王和王庄遍布全国,充当皇权爪牙的宦官势力空前庞大,明太祖清洗异姓功臣等情况来看,他们对异姓权臣(曾国藩、袁世凯)的出现,警惕心未必就会小于满族统治者;面对立宪呼声,明廷搞出一个“皇族内阁”、最终导致流血政变和革命的可能性并不小。
在野的太平天国和同盟会,敌视甚至想推翻当时政权,当然会发动一切舆论造势,妖魔化清政府。满族异族入侵的老账会被自然想起,而其“汉化”以及八旗组织贫困化的情况会被全盘忽略。辛亥革命成功,共和制度建立,被忽略的事实会被意识到,而“驱逐鞑虏”也会很快让位于“五族共和”和国族(“中华民族”)建构。 濮德培(Peter Perdue)曾讽刺说,中国(汉)民族主义者们“将满人斥为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却把自己建立的国家的疆域视为与大清帝国18世纪扩张最远时等同。如其他的民族主义者们一样,中国人建基在他们排斥的过去之上”[7](P4)。在笔者看来,民族主义,是为了方便“反政府”而扯起的大旗,跟清代平民起义时扯起“反清复明”的旗子是一样的。革命党人立场上的前后不一,是政治斗争的本质使然。革命党人毕竟不像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体制内的汉族官员那样,对清政府有切身经历,所以他们一时之言论和观点自然偏激、片面。笔者认为,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在民族问题上立场的前后不一致,以及汉人袁世凯称帝失败,恰恰证明了辛亥革命的深层次属性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一个西化色彩极重的政权更替。清末的反满,主要源于西方先进的共和思想对中国帝制社会的冲击和普遍意义上的“官民”张力。其实,北京“不分满汉,但问旗民”的老话,早就一语道破了问题的阶级、社会功能性的本质,所以“反满”表面上是反抗民族压迫,实质上是反政府、反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阶级斗争。
新清史乐道清帝们对金世宗的推崇,对“汉化”或者“汉习”的警惕、抗拒。但是,且不说清廷保持满洲纯洁性的努力均告失败,清帝们所理解的“汉习”实际上就是“民习”的代名词,甚至是“民习”中的糟粕。清帝们不可能不知道,耽于风花雪夜、宴乐享受是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个人都可能陷入的习气;绝大多数执政集团(不论民族、国家)都会警惕防范,因为它腐蚀官员队伍、败坏国家形象、沉沦世风、祸国殃民。我们只需要想一想历代汉族执政者反腐倡廉、保持官员队伍纯洁性的努力便可一目了然。乾隆提倡的“满洲之道”完全可以从这个方面去理解。面对长治久安下八旗集团的精神、作风、战力上的松懈,为了坐稳江山、保持执政集团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清廷提倡“国语骑射”、“满洲之道”。这是清廷保持执政集团的纯洁性和优良传统的努力。不加甄别地追随皇太极、康熙、乾隆诸帝在特定场合发表的一些关于汉文化的以偏概全的言论,会让我们得出康熙的被废太子胤礽的“汉化”程度高于其父,因为胤礽生活地足够堕落、道德足够败坏。但这一望便知是荒唐结论。我们在认识满族汉化问题上,不应该像新清史那样,被清帝或是一些带有反政府立场的汉族知识分子(王夫之、吕留良、章炳麟、邹容等)一时一地的片面认识牵着鼻子走。所以,“族群”视角将反满、清帝提倡 “满洲之道”等现象与汉化问题牵扯到一起考量,有对历史解读流于浅表之嫌。
三、语言与国家认同
新清史名家罗友枝(Evelyn Rawski)在她的《最后的帝王》中称,儒家礼仪从未在一个征服王朝(如大清)对国家礼仪占据垄断地位,仿佛承认清代政治统治呈现一定程度的多元性就足够推翻“汉化说”[8](P198)。然而,“汉化”的成立并不要求异质文化的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体现汉文化特征,或者被同化到完全看不到原貌。就礼仪而言,只需儒家礼仪在清廷执行的宫廷和国家仪式中处于主导地位就可以了,无须萨满或者藏传佛教元素消失得无影无踪。“化”,顾名思义,有其过程性、时间性,也有深度和广度之分。
新清史常讥笑持“汉化说”的学者动辄拿清代满族丧失满语能力说事。柯娇燕称:“汉化”有时仅靠采纳汉语一个事实就被激发[9](P14)。罗友枝也指出,满人的自我认同没有因为满语能力丧失而瓦解,且美国人和印度人也讲英语,却没有使他们将自己认同为英国人而不寻求独立[8](P5)。濮德培(Peter Perdue)更是在给笔者的电邮中,理直气壮地称“加拿大人说英文并不意味着加拿大必须在法律、政治上成为美国的一部分”。首先,应该指出两者之间的可比性很可疑。美、印两大殖民地与宗主国英国相距万里之遥,而且从文化上讲,英殖民者是以教化落后的原住民姿态在海外拓殖的,与满族政权对待汉文化的态度大相径庭。再者,如果英国就在美洲大陆上,美国会否寻求独立很成问题;至于加拿大,如果没有英国在1812年战争中撑腰,更是差一点就被独立不久的美国武力吞并。
其实,新清史将美、英、印、加等英语国家的人民各有自己的国家认同与满族的汉化类比,是将民族文化融合跟政权(国家)认同两个不同的范畴混为一谈。事实上,被公认文化、血缘、信仰、生活地域上近似或者同一的族群,可以因为各种历史环境和偶然因素,建立两个乃至多个政权或者国家。比如,中国史上历经400年汉朝统一管理后分裂的魏、蜀、吴三国,1949-1990年间的东德与西德,二战后的朝鲜与韩国,中国大陆与台湾等,被普遍视为同一民族建立的不同政权或国家。西亚、北非的20多个阿拉伯国家个个拥有独立主权,但是并不妨碍这两亿多人民普遍被视为阿拉伯人,同属一个大民族。难道可以因为阿拉伯世界里有如此众多的政权存在,便否认肇端于公元七八世纪西亚、北非的“阿拉伯化”(“伊斯兰化”)吗?显然,不同的政权或国家认同,并不排斥民族融合。
笔者赞同新清史不夸大语言重要性的主张,但是语言的归一是认定民族融合的前提条件和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在我国,满族、蒙古族、壮族等少数民族的“汉化”程度一般被视为高于维族和藏族,重要标志就是汉语的熟练程度。满族的汉化当然远远不仅仅体现在语言一项上。但是,总体而言,语言消长是体现文化变迁、民族融合的不撒谎的风向标。
四、军事征服、话语权、“诚心”——对柯娇燕的回应
作为新清史中反对汉化说的急先锋,柯娇燕的论述最有代表性。早在1990年,柯在其《对现代中国早期的族群的思考》的论文中称:
NSA建立的地名数据库中包括了9 000多个已核准的地名,收录了与地名相关的信息,如地名、地物类型、地理坐标与所属行政区划,以及为实现地名转化而需要借助标准阿拉伯名称翻译系统进行的音译和所涉及的地名审定机构的参考资料及其所有相关文献资料。地名数据库中较重要的信息源有地名字典、地图、官方统计报告、政府指令、决议和官方文件。
“汉化说”的最直接的暗指就是,汉文化是故在、僵硬、和排他的,接触着已经或者正在被消灭的其他世界。第二,它暗指仅仅凭借汉文化的内在魅力,各方的人们被吸引来到中国,然后没有大障碍挡路就融化在汉化的烈火中了。…… 从而“半汉化”和“部分汉化”之类说法应运而生,尽管有限的汉化根本称不上是汉化,最终毫无意义……[6](P3)
诚然,作为缩略语,“汉化”与“半汉化”,如“西化”与“部分西化”一样,内涵含混。但是明代的女真族,19世纪以前的朝鲜半岛,以及日本诸岛在语言、建筑、宗教、法律、政治、服饰、生活习惯的方方面面,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说他们在那段时间里经历“汉化”,虽然含混,毕竟凝练地概括了特定时空下文化变迁的方向和事实,以及满族和日韩文化长期以来的重大基本特征,怎可谓“毫无意义”?日本是否被“美利坚化(Americanization)”,并不以日本申请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为条件。判断美利坚化成立与否,我们也无需考虑美国文化是否确有“内在魅力”。我们只需看美国是否吸引了大量的商人、游客、移民和留学生的到来,并且大规模地影响了异邦人士原属地的价值观、政治理念、文化实践、生活风俗习惯即可。
在1998年发生的何炳棣、罗友枝的论战中,柯娇燕坚定地站在罗有枝一边。在1999年的《半透明的镜子》和2006年的《帝国在边缘》中,她对汉化论口诛笔伐:
汉学家们不是不可以使用accu lturation(趋同)或者assim ilation(吸纳)这样的字眼。既然如此,‘汉化’一词不过成为一系列表述与中国有着特殊关系的描述同化和融合的意识形态上的强加的工具。作为汉学学术史上的一个观念,‘汉化’说依然有趣且重要;作为当代话语体系的一个公式,它只代表一团无法证明和对发生于东亚的文化变迁的感情用事的解释[9](P13)。
“汉化”只有一个来自帝国中心的单一的文明化势力、射向不同的边缘族群……它倾向于将地方社会和本地族群从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剥离开来,使得帝国的军事征服史被忽略……汉化说对一个人(部分地和为情势所迫地)采纳文化标记与对一个想象出来的中国政治共同体的主观认同不加区分[10](P6)
笔者向柯教授指出,“汉化”一词,强调的就是满族文化向汉族文化的单向倾斜。没有单向倾斜何来“XX 化”? “文化趋同”(acculturation),仿佛在暗示文化交流的平等性。但是,中华王朝对日本、朝鲜的影响在近代以前远远大于日韩对大陆的反影响;清代(甚至清建国前)汉族文化传统对女真、满族传统的影响远远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反影响。目前在与他国的互动中,美国在所有领域都占据着明显上风,所谓的全球化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制度和价值观同化世界的过程。对这些过去和正在发生的不平等交流视若无睹,反而更像是“无法证明的”和“感情用事的”选择,相当极端且反历史。
此外,军事征服本身就是实现“XX化”的重要手段,与关注地方社会和原住族群对国家建构的影响并不矛盾。无可否认,“汉化”在帝国中心的话语体系里必然被表述为中心对周边所谓 “落后”、“未开化”或者“半开化”地区的“教化”,注重天命、文明、道德和价值观的说服,不强调蛮力征服的事实。武力支持下的美帝国(Pax Americana)的西进和扩张就被表述为“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100 多年来的中国西化,固然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有关,但是若将国人仰慕并学习西方的人文价值观、典章科技、语言文化视为纯粹武力征服的结果,必然偏激。毕竟,西人没有胁迫中国人去西方留学,也没有逼迫我们去推翻帝制、实现民主共和。所以,如果西方国家主导的话语体系将自己的文化扩张表述为“教化”之功,低调处理“武力”因素,可以理解且并非没有道理。同样,倘若明清朝廷主导的话语体系将西南边疆的汉化(如“改土归流”)表述为教化之功,同样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柯氏为代表的新清史认为满族统治者使用汉语,采纳儒家思想和典章制度,是迫于统治需要而对汉族妥协和演戏。这就牵涉到了 “诚心”(authenticity或者sincerity)的问题。尽管笔者相信,当年的满族统治者接受汉族价值观,就如当年日本人仰慕唐朝文化,如今的第三世界国家仰慕欧美文化一样,是真诚的,但是“诚心”似乎与“汉化”的成立无关。被迫接受的“化”,一样是“化”。而且,同样是少数人统治,为什么我们就没看到在印度的英国殖民者大规模学习印度文化,对原住民文化做出类似程度的妥协、逐渐丧失其自身的母文化标志呢?再者,倘若清帝接受儒家意识形态是在演戏,那么汉族统治者赵匡胤、朱元璋何尝没有统治需要,何尝不可故作姿态地推崇儒家价值观?满族皇帝宣扬“满洲之道”何尝不可是在演戏?岂非汉族皇帝假“汉”、满族皇帝假“满”?这样一来,新清史标榜的明朝为汉政权、清朝为非汉政权的分类对待,自身就失去了意义。
五、满文朱批、满汉畛域——对欧立德的质疑
新清史往往把“汉化”作简单化理解,以大量篇幅强调满汉间法律、经济、政治、待遇等方面的巨大鸿沟和贯穿清代的满人的族群认同,仿佛这便足以证明满族未被“汉化”。他们忘记了统治集团和被统治者之间有巨大鸿沟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即便是同民族统治亦然。欧立德(Mark Elliott)所津津乐道的清代笔记《啸亭杂录》中关于阿里玛的故事就是典型例子。满洲大力士阿里玛因多项罪名被判死刑,在离开北京内城的赴刑途中,突然脚蹬城墙,迫停囚车,高喊:“死则死耳,余满洲人,终不使汉儿见之,诛于门内可也”,而“行刑者从其语”[11](P86)、[12](P234-5)。虽然一望便知是笔记文学中的虚构,故事点明的满汉分殊现象对分析“汉化”启发意义重大。在欧立德眼里,故事只有一种解释:文中的“汉儿”=汉人,简单明了,满汉之间泾渭分明,且满人重视自己的身份认同。既然如此,满族“汉化”何从谈起?该思路顺理成章,貌似无懈可击,然而这恰恰是新清史最具误导性的地方。我们不能忘记,由于满洲人(或八旗)在清代等同于吃官俸的统治集团的代名词,“汉儿”一词已经成为“老百姓”、“民”的同义词。而死刑在我国又有公开和不公开执行的传统。公开行刑从示羞辱和以儆效尤,不公开,表示体恤和尊敬。且不公开行刑的主要有三类人犯:妇女、皇族、官僚贵族[13](P534-7)。比如,唐朝就规定,“七品以上及皇族若妇人,犯非斩者,皆绞于隐处”;五品以上“听其自尽于家”①。鉴于上述的理由,以阶级而非民族意义来理解文中“满洲人”和“汉儿“,更为妥帖。故事中的阿里玛是在强调自己的政治身份,而非自己的民族属性,诛于内城门内,是他祈望获得的最近似于家中自尽的待遇。一个获罪的汉族官员,亦都可能有类似阿里玛的诉求。
与上类似,欧立德在《满洲之道》中列举了从满文档案中苦心收集来的两三条清帝鄙夷 “汉人”的朱批,均可从阶级视角来解释。例如,雍正曾训斥满官们,“不可视米价上扬为灾难临头;否则便如无头无用的汉人一般,担忧的尽为小事”[14](P169)。康熙帝给皇子允禵的批折中写道:“然则尚有汉人狡猾善骗之本质;满嘴仁义忠孝,一旦有利可图,终不认父母”[14](P169)。但是,此类的鄙夷完全可以以满汉之间的“官民关系”来阐释。清代的普罗大众以汉人为主体。皇帝和官员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当然会鄙视民众的自私和愚昧。而且,古今中外的执政者一般都不敢公开表达对大众的鄙视,所以清帝使用满文时措辞较为开放,是合乎情理的。而群众抢购商品等各种一惊一乍的行为,即便当代都时有发生。至于康熙的朱批,欧立德没有提供语境,但是鉴于“汉人”在清代是“老百姓”的代名词,这些话完全可以理解为他对小民中没有公德、行事虚伪者的厌恶。康熙亲历过诸如孔有德、范承谟、马雄镇等对清廷忠心耿耿、不惜生命的汉族官员,也惩治过多个不法的满洲官员②。他当然知道,口是心非、为了个人利益而六亲不认等恶质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不可能为汉人特有。他自己在初废太子胤礽时就斥其 “恣行乖戾,无所不至,令朕赧于启齿”(《东华录·康熙八十二年》)。执政者和群众之间的社会功能性矛盾,即便是汉族统治时代亦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路康乐(Edward Rhoads)的名著《1861-1928 年间的满与汉》在欧立德眼里,揭示了清末新政时满人利益与汉人利益仅仅部分重叠、“满洲的利益仍然是满洲政治人物重要的考虑”的事实[15]。但是“满洲本位”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古今中外的执政集团都不可能忽略其视为国本的执政基础。清代的“首崇满洲”与明代的“首崇皇族”并无实质区别。米华健(James Millward)称,据欧立德计算,清代的八旗集团占据全国人口不到2%,却耗去全国25%的财政预算[16](P472)。可是比较汉族统治的明代,这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据张德信的计算,明宗室的俸禄仅嘉靖三十二年(1553)就已经占据国家财政的37.33%;如果按照明律足额发放俸禄,那么在1614年明政府即便倾全国之力都无法负担人口增至16万多人的明宗室,因为其总额已经超过全国田赋收入的总额[17]。同样,明代宗藩也因为人口增加出现贫困化现象,发生过宗室包围官府和暴力索禄事件,让我们想起发生在清代八旗身上的类似情况[18](P64-66)。柯娇燕在其名著《孤军》的末尾称明清两朝大相径庭,清朝满族与汉族被“围墙”、“法律”、“社会紧张”和“自我认同”隔开[19](P223)。可是,明朝的统治集团一样被围墙与民众隔开,法律上拥有高度特权和限制,和民众(李自成、张献忠)有着殊死的紧张关系,同样拥有强烈的自我认同③,与清朝没有分别。
六、清代社会政治地位是否由民族属性决定
毫无疑问,清代的统治集团序列中八旗满洲地位最崇,蒙古次之,汉军又次之,接下来是北方汉官,南方汉官垫底。这已是清史学界的共识和常识。联想到雍正朝清查八旗子弟的继嗣和血统纯正性,乾隆朝中后期汉军被迫大规模“出旗”的现象,即便中国学者(遑论新清史)都会认为,清廷倡导的“满汉一家”仅仅是虚假宣传。在表面上,统治集团内部的地位分配的确以族群属性划分。然而,依笔者之见,我们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清高宗实录》第一百八十四卷 (乾隆八年二月)的一则记载就很值得我们推敲:面对江浙籍的官员许久得不到升迁,汉官杭世骏上书敦请朝廷在用人上要消除满汉差别,而一向宣扬“满汉一家”的乾隆竟然勃然大怒,将杭削职,并振振有词地反驳道:“满汉远迩,皆朕臣工,朕从无歧视……国家教养百年,满洲人才辈出,何事不及汉人?”倘若乾隆没有在撒谎,难道是汉官们产生了错觉?
也许我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前述各集团地位的排序与各自投靠爱新觉罗氏的核心集团,参与大清建国和统一大业的时间先后顺序完全吻合。同为汉人,投靠早的辽左旧人、北人、南人差距明显,排序是按照投靠新政权的时间先后。同样是汉军出旗,投靠时间不同,命运也不同。据刘小萌言,入关前就投靠清廷的“陈汉军”,就不在出旗之列;被强制出旗的,是入关后才投靠的“新汉军”[20](P59)。这就意味着,民族属性也许仅仅是表象,问题的本质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资历的高下。
换言之,社会学上具普遍意义的论资排辈、优势积累、“强者恒强,弱者相对恒弱”的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理论,已经可以解释清代社会地位的划分。在清代,八旗满洲投靠爱新觉罗氏最早,接触和受恩养时间最久,军功也最高,资历最深。这一优势在入关后被迅速巩固,满洲子弟的汉语和执政能力迅速提升,集团资源被迅速整合。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把持机会资源,也掌握优质教育资源,从而使其子弟得到极好的教育和历练,在能力上并不逊于汉人,心理上也更为自信。这就好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发展先机的清华、北大、以及常春藤名校在各自国家高教界取得的崇高地位非常稳固,难以被后来者赶上。论资排辈,不一视同仁,优待、重用有背景者,乃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由此导致一步早、步步早,一步晚、步步晚的低社会流动,凸显出身、门第的重要。而门第社会,非清代、也非中国特有。两汉直至隋唐,“门阀士族”对官职的垄断、以及其与“寒门”的对立,就是中国史上的一个早期例子。
所以,虽然杭世骏所代表的南方汉官觉得受歧视并非错觉,而乾隆帝的“满汉一家”、满人“何事不及汉人”亦非妄语,毕竟八旗集团中充斥着汉人。而汉军“出旗”最早,并非因为其汉人血统,而是因为比起满洲、蒙古,汉军投靠和服务清廷的资历最浅。因为历史原因,在清代政治资历正好与族群属性高度吻合,很容易给人以民族属别决定政治地位的错觉。然而这在理解上很可能是为表面所迷惑的本末倒置。定宜庄就曾提及,很早投靠努尔哈赤的汉人,被分入八旗满洲且其后也未被析出[21](P23)。笔者怀疑,此中揭示的乃是满族早期构成的一个原则,即:政治资历决定民族属性,而非血统、语言、习俗等民族属性决定资历。突破对清代政治认识上的民族性藩篱,不但影响我们对清代的认识,而且会修正我们对蒙元王朝的理解。比如,将人民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4个等级,一直被当做是元朝实施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明证,甚至把汉族分列为两个不同等级视为蒙古统治者对汉人进行民族分化。然而这一理解,忽略了这4个等级完全是按照投靠孛儿只斤氏为首的蒙古统治集团的时间先后和政治资历高下划分的重大事实。虽然这并不排斥因为政治资历和民族属性的高度重合而被人们渐渐混为一谈,但是至少我们会意识到对所谓的征服王朝不应该简单地以民族性视角对待之。
虽然美国学者在深化我们对“汉化”的理解上功不可没,但是满族人民在与汉族人民长期的交融过程中,无可辩驳地渐渐丧失了各项客观存在的民族性标记。如果这还算不上“汉化”,还要被说成是“融而未合”,那么笔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算得上“融而合”。也许新清史会提“民族自觉”。这里又要引出新清史的一个重大矛盾之处。首先,新清史强调满洲的“非汉”性。这种说法本身就暗示有一个客观且不变的“汉族性(Chineseness)”标准,否则,“非汉“一词何从考量?其次,新清史质疑“民族认同”的血缘、语言、地域等“事实”基础,却在实践上将“主观意识”提到至高的地位。且不说没有“事实”作为基础的单纯的“主观意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会随着时间流逝、生存环境变化、私利的考量而变化,新清史的做法不啻将人的“主观意识”本质化、中心化和“事实”化了,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与他们经常自我标榜的 “去中心化”(de-center)和“去本质化”(de-essentialize)背道而驰。
余论
基于社会政治阶级性(或者社会功能)区别的“官民”分殊,已经可以阐释为什么满族在汉化的同时,其族群认同贯穿整个清代;官民矛盾也足以解释清代后期“反满”思潮的膨胀以及曾国藩为首的汉官集团坚定地帮助清廷打击太平天国势力。新清史对“汉化”的过度狭隘的界定,是其颠覆“汉化说”的主要手段。然而,满族的汉化与其族群认同的维系,并不矛盾。如果本族的底层人民都可以与本族政权对抗,为什么不能与高度汉化、且由超越民族的、多民族构成的八旗政权对抗呢?所以,“汉化说”绝不是新清史所理解的是汉族学者和前辈西方学者(如费正清和芮玛丽)对中国史的带有“汉族本位”的民族主义立场的解读。它有着深刻的历史现实来支撑。民族的融合和崛起必然导致一些民族的被吸纳和消亡(否则现在应该依然有匈奴人和契丹人,也应该有诺曼人),古今中外没有哪个民族对此有绝对的免疫力。
全面把握满族汉化,认识“族群”(ethnicity)视角的局限性,重视既得利益集团的优势积累导致的社会分层以及官民之间的社会功能性的差别,不但会影响我们对新清史的各项主张的评估,而且对理解辽、金、元、清等所谓“征服王朝”时代的民族构成和民族压迫等传统观念有修正、深化的作用。比如,前辈学者王钟翰和他的弟子们倾向于将满洲连同八旗都视为民族意义上的“满族”,而笔者则倾向于将八旗的旗籍视为超越民族、超越文化与血统、具有特定政权和政治诉求的多族群执政共同体的政治资格,类似现代的集权政党。这样的理解,似乎可以解决曹雪芹、端方、佟国纲到底是汉人还是满人的争论(笔者认为他们是满籍汉人)。笔者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对学界厘清这些重大问题有所帮助。
注:
① 井田仁升:《唐令拾遗》[M],粟劲等编译,长春出版社,1989,页696。转引自胡兴东(书目24)第534-6页。
② 见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16、384-390页。其中,马雄镇和马与进孙祖二人的女眷所体现出来的忠贞尤为令人惊叹。虽为一家人,但祖孙分别各自忠于明清。
③避难台湾的明宗室宁靖王朱术桂,在南明政权已经败亡20年,郑克塽决定率领台湾归顺大清的1683年,以66岁高龄举家自杀。这与绝大多数旧明民众和官员早早就归顺新政权的做法有天壤之别,即为著名一例。
[1]R.Kent Guy.Who Were the Manchus?A Review Essay[J].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61,No.1,Feb.,2002.
[2]William T.Rowe.China’s Last Empire:the Great Qing[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3]定宜庄.由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J].清华大学学报,2008,(1).
[4]郭成康.也谈满族汉化[J].清史研究,2000,(2).
[5]汪立珍.美国著名满学家、清史专家柯娇燕教授谈满学与清史[J].满族研究,2010,(3).
[6]Pamela Ky le Crossley.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J].Late Imperial China,Vol.11,No.1,June 1990.
[7]Peter Perdue(濮德培).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M].Boston:Harvard UP,2005.
[8]Evelyn Rawski(罗有枝).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the Qing Imperial History[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9]Pamela Kyle Crossley (柯娇燕).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10]Pamela Kyle Crossley.Ed.with Helen Siu&Donald Sutton.Empire at the Margins:Culture,Ethnicity,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
[11]欧立德.清代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和满洲人的中国统治[J].清史研究,2002,(4).
[12](清)昭梿.啸庭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3]胡兴东:中国古代死刑制度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14]Mark C.Elliott(欧立德).The Manchu Way: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M].Berkeley:California UP,2001.
[15]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J].故宫学术季刊,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06,24(2).
[16]James Millward.Book Review[J].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62(2).
[17]张德信.明代宗室人口俸禄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J].东岳论丛,1988,(1):77-82.
[18]杜婉言,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九卷·明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9]Pamela Kyle Crossley(柯娇燕).Orphan Warriors: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s of the Qing[M].Princeton,NJ:Princeton UP,1990.
[20]刘小萌:八旗子弟[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21]定宜庄.满汉文化交流史话[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23.
Rethinking Manchu Sinicization:a Critique of New Qing History’s Emphasis on Ethnicity
ZHANG Jian
(Shenzhen University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Shenzhen,Guangdong 518060)
Repeated challengesmounted by the US-based New Qing History these 25 years have largely discredited the old sinicization theory as an explanative paradigm describing the relative Manchu success in governing Qing China.This achievement is theoretically dubious because sinicization was in effect given an unfair narrow definition by linking it to the twin issues of the continuation of a Manchu identity and the anti-Manchu movement throughout Qing.However these two issue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Manchu ruling status and the ensuing class conflict,societal features that are not uncommon in Ming or even in othermono-ethnic ormajorityrule societies outside of China.Thus,a distinct and robust Manchu identity is hardly incommensurate with Manchu sinicization.New Qing History vastly exaggerated the importance and usefulness of ethnicity in approaching Qing politics because it fails to filter out the effects of vested interests and their cumulative advantage in engendering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Qing,elements that were (are)pervasive even in purported mono-ethnic ormajority-rule societies.A simple “ethnic” approach to the so-called Conquest Dynasties requires revision because itmighthave erroneously taken the surface for the depth.
sinicization; New Qing History; Manchu; Eight Banners; ethnic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K 092
A
1000-260X(2013)03-0153-08
2012-03-07
章健(1971—),男,江苏苏州人,英语文学和比较史硕士,深圳大学讲师,从事文化史研究。
【责任编辑: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