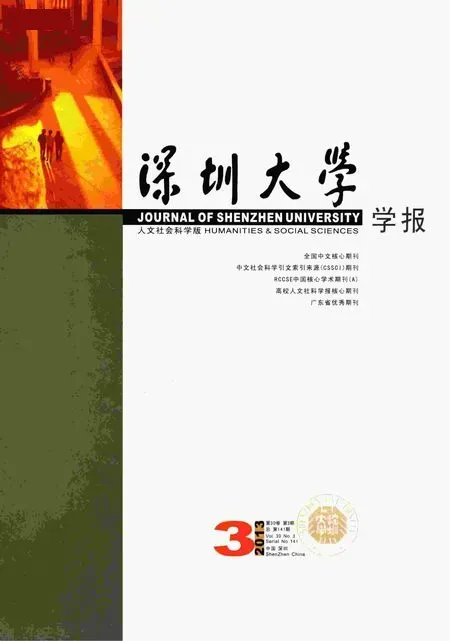明清珠三角“广州-澳门-佛山”城市集群的形成
2013-04-07黄滨
黄 滨
(广州大学政治与公民教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在明清以前千百年岁月, 中国处于典型的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 珠江三角洲地区很多地方在北宋前还是未被开发的水乡泽国,史载“南方烟瘴,地广人稀,田多山少”[1]。 农村耕作也“往往卤莽,一犁之后,无复用力”[2](P7)。 广州虽然从秦汉时代开始形成,并且很早就成为官府外贸中心城市,城市发展有着1500 多年的历史,但是,环广州区域农村地带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群民性商品大宗出产并不多,尚未近距离形成对广州强烈的市场性支撑。 广州以满足官需权贵有限需要为主的奢侈品外贸, 也不能对附近农村产生强劲市场拉力。 广州虽然是全国外贸中心城市, 但仍然不过是汇集全国进出口贸易而形成的单一的长距离远程官府外贸中心, 是一个典型的官贸通道型城市, 而非真正的全国市场中心城市。从商人构成来看,珠江三角洲远程贸易商人集团主力——广州商帮也尚未形成, 海外远程贸易虽然较早出现若干远程贸易商人,但仍稀少,远不如闽商驰名。相应的,从广州市的市场聚落的存在地理空间的形态来看,我们可以注意到,从秦汉时代到明代以前的约1500 多年漫长岁月中,广州一直是一个单体性的城市, 在附近的江河交汇处和出海口地带尚未形成自身的外港城市和内港城市, 尚未组成制成多体性的城市组团配伍,所发挥组织经济功能的空间,仅仅局限在非常有限的本城城郭附近区域范围。 明代以前, 珠江三角洲的空间分布, 只有广州一城独大,此外无任何稍大的城市与之组团。这与明代以后情形相比较,的确是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
而到明清, 中国进入以资本主义萌芽为标志的封建小商品经济普遍较快发展阶段。 由于地理上最靠近我国传统的主要海上贸易对象国, 同时也由于王朝政府的倾斜政策,水系发达、雨热充足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迅速后来居上, 成长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市场化、贸易民营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 以此为基础,广州作为全国最大的外贸中心城市,真正成为了当时全国第一位的市场中心城市, 国内外市场强劲叠加,市场经济辐射能力空前增强。表现在地理空间结构上,一个重大变局应运而生:广州突破千百年来单体发展格局,开始产生了内港、外港以及各种类型的卫星城市并与之复合配伍, 派生城市多体的强烈需求。 从区域市场发育角度看,明代崛起、清代高度繁荣的澳门、佛山,就是在这一时期广州辐射带动下分别作为广州的外港、内港城市体而形成发展的产物。 诚如中山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司徒尚纪先生所指出的:澳门、佛山都是广州的外港[3](P168-179)。 从此,广州迈入“一市多体”的多核式中心城市的时代,以自身为轴心,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城市集群——“广州-佛山-澳门”城市集群。 这一集群互为倚角,贯通内外,一体作功,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大广州”,不仅成为珠三角、广东全省经济中心城市,而且真正构成当时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 本文拟从明清广州市场辐射与外港澳门、 内港佛山的形成发展的关系角度,进行若干证探。
一、明清时期广州行业高度发达及外拓辐射强态形成
明清时期,我国商品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在这一进程当中,地处中国最大的、分布和联通着最多贸易对象国的海域——南海的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发展商品经济的天然优势条件,如雨热足、物种多、濒临沿海、境内交通水网丰富、广州长时间拥有独口通商外贸巨埠地位等, 从明代开始逐渐充分发挥出来。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商品性农业、农村手工业和圩市经济蓬勃崛起, 广州真正对珠江三角洲乃至整个广东发挥“百货之肆,五都之市”的枢纽作用, 城市经济行业获前所未有发展。 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广州已经是“天下商贾聚焉,”其经济行业的发展在全国显然处于最高水平, 时人曾经不禁将广州与当时的国都、 地处发达的江南地区的南京城相比较,“此濠畔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岛如海,番夷辐輳,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4](卷十七·宫语),这可以理解为,广州城市的经济行业经济总量是具有国都地位南京的数倍之巨。
首先,是广州进出口行业空前发展,无可比拟。进出口行业即牙行,专事为外商服务、承销外国商船进出口商品的商务。 该行业以往由于官衙市舶司垄断,发展弱小,常处于非法状态。永乐年间,在商品经济高涨大势下,官府终于允许“官设牙行”[5](卷三一),广州牙行取得合法地位, 并逐渐成为封建王朝指定包揽和管理外贸的“钦定商人”。据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在明代,实力最雄厚的是“十三家商号”。他们大举与各国商人贸易同时, 并取代官衙市舶司之类统办机构, 获得相当的政府外贸管理职能的代理权而迅速膨胀势力,取得了对外贸易垄断商的地位,通称“十三行”[6](P55)。清代,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发展成为广州公行制度。 明清进出口行商无疑发展成为广州最大的商业巨擘。每个时期通常只有十几、二十家行口充任行商,但关键是,他们作为龙头商家,以政府授权为杠杆,将广州几乎所有的、数千上万的涉猎进出口的大小“散商“、”铺户”、“行栈”,以及广州所有的收购行店、批发销售行店都链接起来,整合为一个特大的进出口行业系统——“散商”“铺户”、“行栈”为行商组织和提供出口的货源;行商则为“散商”、“铺户”、“行栈”组织和提供进口的货源。形成一个具有“贾客干家万家室”[7]的巨大行业系统。 广州怡和洋行洋商伍家高达2100 万银元资产,乾隆年间“藉外来洋船以资生计者约数十万人”[8](P139),可分别旁证广州进出口行业的顶层实力和全行业从业人员规模,在全国无任何一座城市可以比拟。广州进出口行业的贸易规模之巨大, 更能从梁嘉彬调查的洋商贸易出入货簿记录见其一斑: 经过广州粤海关的货值, 以白银计, 嘉庆十七年进口出口货价合计2780 万两。 而当时清政府主要赋税田赋常年收入也不过5400 万两白银[9](P4)。 这个数字反映了当时广州一座城市的进出口行业贸易额, 竟相当于整个中国主要赋税来源——全部田赋的51.5%, 而当时的中国可是世界上版图最大、人口最多、以农业为主的国家。 可见广州进出口行业,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行业形式发展水平、行业系统的完善和成熟,无疑雄冠全国。
由于进出口行业的超级发展,在它的带动之下,广州其他经济行业也大获发展, 发展水平同样远在全国各个城市之上。嘉庆时,广州“其行店为当商、放账铺、换银铺、洋货铺、珠宝铺、参茸行、布行、生铁行、铁器行、绸缎棉布行、青麻行、铜行、锡行、西货行、海味行、京果行、油行、豆行、谷埠、米行、槟榔行、烟叶行、金丝行、磁器行、干果行、药材行、柴行、炭行、糖行。”[10](卷二)此外记载,清初广州有七十二行,如土丝行、颜料行、米埠行、磁器行、牛皮行、金行等[11](卷一二)。 笔者见及有记载的还有海商行、票号、银号、百货行、茶行、牙雕行、盐业行、客船运行、茶楼业、娱乐行、戏班演艺、武馆业、郎中行、船运及修理业木匠行、饮食店、珍腊味店、民信局、邮递、赌博嫖娼行等。 上列行业,分工精细,门类繁多,相互交叉,体系完整,高度集聚,辐射功能强大;行业发育得这种完备程度,在当时全国是罕见的。由于环绕着全国最发达的进出口行业的发展而成长, 广州各类行业在全国当时也大多达到最高或领先的水平和规模。如明代,如前所举的广州百货业、餐饮业、娱乐业、珠宝业、象牙业等,已经“过于秦淮数倍”。 又如清代广州盐行,清代粤盐行销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云南、贵州7 省,纳饷近70 万两[12],仅次于淮盐,业务规模在全国高居第二位;广州邮递批信业,到了光绪三十年,仍然居全国第一位,高于当时已经发展为全国新的最大经济中心城市的上海。
伴随着城市经济行业的高度发达, 明清时期广州的市场辐射力也强势形成, 并在全国城市中遥遥领先。 宋代,广州的商人虽然也已经开始活跃,但是在全国仍然表现平平, 标志城市经济辐射能力强大的远程贸易商人集团仍然没有形成,因此在史料中,我们很少看到广州商人在国内外的远程贸易踪迹,倒是福建商人的名气远远大于广州商人, 在宋代的典籍中常见身影。但到明清情况发生根本变化,广州商人已经成为全国乃至海外远程贸易商人集团中最强势的一支,足迹布满全国和海外。 对海外,前往南洋经商的人数和势力远远反超福建人,成为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商业的重要力量[13](P270-276)。对国内,更是无所不往。 明末清初《广东新语》记载:“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利,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4](卷十四.食语)。1798 年,来华长期留居的瑞典人龙思泰,在《早期澳门史》[14](P301-322)一书记载:广州不仅是广东货流中心,而且是全中国货流中心,福建、浙江、江南、山东、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江西等“每年都有大量的产品运到这里,换取西方世界的物产和制品”;同时,“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为中心。 ”[14](P301-322)
值得我们从经济地理视角关注的是, 明清时期广州城市经济行业的发达和辐射强态呈现的过程,同时又是广州城市空间分布持续不断的外张运动过程,具体表现为以广州本城为轴心,在尽可能近的距离和尽可能佳的位置,按广州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催生出广州的临海外港和内河上游内港, 以改变自身千百年来贸易军政活动集中一处拥挤不堪, 在珠江三角最重要的珠江出海口地带和西江与北江汇流处均无规模足够的贸易港口接应的状态。澳门与佛山,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应运而生的。
二、广州经济辐射与作为广州外港城市形成的澳门
广州市场辐射首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位处珠江出海口的澳门成为广州的外港城市, 或者说是临海港市。
澳门, 原为广东省香山县濠镜澳一个渔业性的临海半岛,位于中国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南端,珠江口的西侧,珠江与西江的出海口附近,距广州仅105公里。其总面积仅为23.50 平方公里。在古代可谓具备着天然良港的条件,所谓“澳者,舶口也”[15](P23)。因此, 明代以前这里也会成为渔业生产和外贸时常临时停泊船只的地方,但是,远没有形成有一定规模和设施的专业性贸易港市, 本地居民基本上以渔业为生。明代以后,广州作为全国独口通商口岸呈现出超常规的繁荣, 自然陆续将各自的重要的经济能量注入这个距离广州不远、 位置前突、 三面临海的半岛。 入明以后,广府地区许多人涌往澳门营生,明王朝政府也逐渐明确把澳门建成为与广州距离最近,能够延伸广州的经贸功能和军政控制功能, 允许外国人比较自由居住和贸易的“番坊”特区。同时,刚刚完成地理大发现,在1498 年打通欧洲通往印度航线的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也受广州强烈吸引。其中万里迢迢前来广州与中国贸易的葡萄牙,一马当先。为了囤积货物、避风歇息、停泊船只以及自由买卖,葡萄牙渴望在广州出海口地带, 建立一个能够有自己独立的治理体系、自主自治的城市;以便能就近与广州贸易,并通过广州与整个中国的贸易。澳门以其位置之优越自然成为了葡萄牙最佳的选择目标。 正德十二年(1517 年)葡萄牙人驾大舶叩关广州。 在请求朝贡通商遭明王朝拒绝后,遂在香山县濠镜澳(即澳门)安营扎寨,建立贸易据点,从事民间贸易。嘉靖十四年(1535 年),广东官府移市舶司至澳门,承认了这一现实,允许外国商船入泊濠镜澳,允许在澳门进行中国与外国的贸易互市, 这应该视为澳门口岸诞生并且形成广州外港的标志性事件。后来,又在中国管辖主权不变、保持军政机构管理的前提下,陆续允许葡萄牙居澳自治权。1557 年,“广东官员在当地商人的要求下,将澳门港划给我们(当时经历此事的葡萄牙人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的叙述——笔者注)做生意。 ”[16](P698)1573 年中国政府与葡萄牙政府就澳门正式形成租赁关系, 广东当局规定每年对居住澳门的葡萄牙人征收500 两地租。1583 年允许成立议事会作为自治的最高权力机构, 管理葡萄牙人内部的治安、贸易规范、征收商业税、安排自治机构的财政支出等。 从此澳门成为外国人暂时居留中国的合法特区。 这里特别指出,澳门之所以最终成为口岸,广州因素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考量项, 而且广东官府始终保持着主动决策的主导姿态。在此以前,广东官府曾经在香山的浪白澳设官与外国商船抽分“常贡”,这里一度成为贸易中心,但经过观察比较终于意识到“对中外商人来说,浪白澳距广州太远,而且交通不便”[17](P8-9),于是,才将移市舶司至澳门。对于掌控东西方航线和贸易的葡萄牙人而言, 广州等始终是他们期望中的与中国贸易的主要目标城市,所以选择澳门作为登陆的桥头堡,也正是因为澳门与广州近距离水陆相通。 经明清两代约300 多年发展, 澳门已经发展成为广州贸易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成为中西贸易最重要的桥头堡和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的外贸自由港市。 如16 世纪70 年代至17 世纪40 年代, 以在澳葡人为主建立起的三大贸易航线:澳门—果阿—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墨西哥,伸展到欧洲、亚洲、美洲,编织成以澳门为中转枢纽港、 以里斯本为财富归宿地的国际大三角贸易网络[18]。然而,澳门这一伸展到全球各地的巨大商业网络所依托的城市基本支点, 始终主要是广州。
历史资料表明,广州、佛山所汇集的巨大的商品货物,大部分都是经过澳门出口。 史称,澳门地方货物“均由省镇、佛山各处市镇转运到澳售卖”[19](卷二十九)而运销海外。 而大量从海外换回的白银(有一说占当时全世界白银的2/3)[20], 也大多是从澳门吸入、再经广州的输往中国各地[21](P51-52)。 虽然,澳门作为一个重要城市, 它的确是经过葡萄牙人根据西方与中国以及远东贸易需要所营建, 但澳门更始终是环绕广州城市外拓发展、海外贸易需求而形成的。务实的广东官府对葡萄牙人在澳门的留居与自治状态的默认,实际上也有着借助于澳门港口城市,延伸和扩大广州城市功能,扩展外贸以资国用、以济民生的考量。 万历四十三年(1614 年),以霍与瑕、张鸣冈等开明官僚提出了准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贸易的方针; 俞大猷也放弃了自己最初提出的驱逐葡萄牙人方针,其理由就是开放广州为中心市舶贸易。他指出的理由是:“市舶之开,惟可行开广东,盖广东去西南之安南、占城、暹逻、佛朗机诸番不远。诸番载来乃胡椒、象牙、苏木,香料等货。船至报水,计货抽分,故市舶之利甚广。 ”[22](卷七)
关于明清时期澳门作为广州外港的性质, 屈大均居留澳门时有深切的感受。他根据亲见亲闻,引民谚云:“广州诸舶口,最是澳门雄”。 另外,1836 年,长期生活在澳门的瑞典人龙思泰撰写 《早期澳门史》,竟用全书1/3 的篇幅撰写了《广州城概述》[14]。 由此也可见,时人言澳门必言广州,言广州必言澳门。
澳门的广州外港的性质还明显地体现在, 澳门的基本居民多为广州府人。如1830 年,时人统计,葡萄牙人及土生土长葡萄牙人仅为4628 人[14](P37),虽然他们掌握着澳门治理权, 但人口在澳门人口的比重中仍只占很少比例。在明万历年间,澳门人口就已有10 万之众[23](卷三),到清代前期,更不止此数。 依此计算, 主要由中国人构成的澳门基本人口当是葡人十数倍。而据材料表明,澳门的中国人口中又大多是闽广两省人,特别是广东人,其主力又是“广州望县”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食语》专门记载“南走澳门” 的广州人的情形:“广州望县, 人多务贾与时逐利,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其黠者南走澳门”。 按照历史资料叙述的语气和所透露的信息可推知,中国人中闽人虽然众多,能量也不小,但是闽人毕竟从家乡迁来距离较远,澳门十数万众的基本居民当多为广州府人, 其中相当部分是今广州区域的来民; 这种现象其实是广州经济辐射推动着澳门口岸形成的人文体现。
从经济运行来看,澳门行业运转也都以广州为轴心。 据司徒尚纪先生研究,广州船几乎都经澳门再放洋,“闽由海澄(漳州)开洋,广(广州)由香山澳”[24],广州则是澳门的番货销售和批发市场,每年春夏间番舶抵港时,不少“客纲”、“客纪”,“群自广州赴澳门承买番货,获利甚丰”[8](P14)。 明后期每年冬夏还在广州举行定期市, 每次开市数星期或长至数月,主要买卖澳门番货。广州濠畔街、高第街、卖麻街就是经营番货的著名街市[3](P180)。 据李龙潜《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 第210 页所列葡船自澳门运往果亚、长崎贩货利润表(约1600 年):白丝运往果亚l 000 担,运往长崎500-600 担,在广州买价每担50两、澳门每担80 两,在日本买价,每担140-150 两,在果亚每担200 两;绸缎、麝香、水银、茯苓、黄铜手镯、白糖、黑糖、各种陶瓷器,都从广州进货,买往日本、 果亚, 到日本的利润率分别为111-127%[25](P210-211)。
明清时期, 澳门是广州的市场近距离辐射与以葡萄牙为先峰的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工商业远程辐射相交汇所形成的城市结节点, 也是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工商业因素被广州市场强烈吸纳的结果。 澳门港市的形成, 使广州终于在自身出海口处拥有了自己的外港。 有外港与无外港,对于广州乃至广东,甚至全国,经济发展局面就大不一样。 有了自身的外港,广州在100 多公里的距离之间就进一步形成了框架更大经济政治分工体系; 广州许多重要的外贸业务活动就大量分流延伸到澳门进行; 外贸专业分工水平从而就获得进一步的提高。 澳门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实际上也构成了广州外贸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是广州外贸经营业务链条向出海口口岸地带的直接前移;同时,澳门港市的形成,大大增强了广州城市的国际开放度, 大大扩张了广州城市的经济辐射功能。澳门作为广州外港,吸引了规模空前的外商外资前来投入,从房地产到各项工商业,以及口岸城市的建设。 这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确保主权前提下真正租赁土地、 吸引外资的经济开发“特区”。 更重要的是,在明清时期的五百年间,在全中国总体上还处在闭关自守状态的当时, 由于澳门引入了完全不同于中国国内封建体制的全新的经济体系甚至文明体系——资本主义体系, 从而为广州市发展注入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动力, 广州最早也最大量的接纳了西方资本主义商人以及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公司经济活动; 最早也最充分地吸纳了近代西方工商业文明元素、思想观念,使广州最早也最深厚地形成了包容开放的城市传统。
于是, 广州与澳门首先结成了珠江三角多核中心城市组团中的首要连环——“广州—澳门” 连环,这是以广州为轴心, 伸展向海外巨大国际市场方向的关键性的城市链条。
三、广州经济辐射与作为广州内河港市崛起的佛山
广州市场辐射很大程度上还促成了地处西、北两江至广州的主要航道的佛山成为广州的内河港口联轴城市。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司徒尚纪先生曾提出,其实,澳门、佛山都是广州的外港。笔者在深受他将澳门和佛山都视为广州外拓发展形成的港口城市观点启发的同时, 却更倾向将佛山和澳门作进一步的区别, 把佛山看成广州外拓发展形成的内港,或者内河港市。
佛山,明清时期属广州府南海县地,地处西、北两江至广州的主要航道佛山涌的交通要冲。 距离广州仅40 里地,“佛镇距省四十里”[26](卷十四,梁绍献列传),与广州有西江航道一水相通达,一天之内一日往返可以数次。 一般来说,内地出口的商品来货,先抵达佛山,再抵达或者中途经过广州。
但是,一直到明代以前,佛山基本上一直都只是一个人口密度稍大的农业性的村落。唐宋时期,佛山开始形成了若干渔村墟市, 逐渐聚集了一些原始零星的工商业;北宋称为佛山堡,明初佛山堡的八图居民仍然多以农耕为业,不过只有3000 多户以农业为主的人家。 虽然在明清时期“佛镇距省四十里,客人买卖来往日凡数回”[26](卷十四)的经济城市发展的优势凸显,但是在此以前,这样的优势尚未有机缘真正焕发出来。
到了明清时期, 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的高涨发展,近在咫尺的广州城市空前繁荣,使佛山获得了从农村转变为经济巨市的历史机缘。
首先, 商品经济高涨发展条件下广州官府公务需求, 直接刺激了甚至催生了佛山赖以立市的基本行业——冶铁业的产生与起步。
广州原也有满足城市需用的打铁业, 但已经无法满足城市发展对铁产品迅速增加的需求。 广州需要最靠近自身的、 同时也最具备制造能力的城市形成规模足够、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冶铁手工业,以支撑一个巨大城市的运转。佛山原先并不以冶铁出名,但在广州市场需求的刺激下,一些村民为了增收益“孤村铸炼”,而后渐成规模,形成声名。由于冶铁密切关联国用民生,“上资军仗,下备农器”[27],佛山“铸炼”自然引起政府重视。于是,广东官府大力将佛山扶植为省会广州的政府机构需求提供专门的冶炼服务的专门场所。明朝政府规定,广东所有的生产铁矿的地方一律不在各处冶铁, 而全部将铁矿石运到到佛山统一冶炼。 官府就规定:广州、南雄、韶州、惠州、罗定、连州、怀集等地的生铁必须输往佛山[28]。 对佛山冶铁,“官准专利”[29]。 地方政府陆续将佛山的农户转变为打铁的铺户,统一管理和派役[30],规定铺户可以生产冶铁商品自由上市,牟利营生,但是前提是必须完成政府的派役任务。在相当程度上,铺户完成任务得到的回报部分也是数量可观的现金回报。 以中国之国情, 商品经济高涨发展条件下官府公务需求是首先发生膨胀的,其数量非常巨大,而且非常稳定,首先促使了兼业冶铁的佛山堡居民“农转非”,完全转化为专业的冶铁手工业者或者业主。 据佛山碑刻史料记载:明代“本堡食力贫民”已经“皆业炉冶”,“分别班行,遵应公务。但铸锅炉户答应铁锅,铸造铁灶答应铁灶,炒炼熟铁炉户答应打造军器熟铁,打拔铁线之家答应铁线、御用扭丝灶链,打造铁锁胚炉答应御用灶链、担头圈、钩罐身,打造笼较农具杂器之炉答应御用煎盆镬、抽水罐,小口口,卖铁钉答应铁钉。 自古亘规,各依货卖答应,毫无紊乱。 ”[31](P13)值得注意的是,铺户、炉户完成政府订购任务,并不是无报偿的奉献,而是“各依货卖答应“的买卖关系。最大公务需求当为广东省城广州,如崇祯年间,广东官府修造战船,需要取办大量铁钉,先向佛山铁钉铺户取办,不足,又向佛山炉户取办。 “省下公务取铁钉,答应自十斤以上至数百斤。铺行不堪赔累,议炉户帮贴。 ”[32]
第二, 广州高度发达的进出口贸易和国内外贸易对城市建设和人口聚集的巨大需求, 同样也直接刺激了甚至催生了佛山赖以立市的基本行业——冶铁业产生与起步的蓬勃发展。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广州人口已达到30多万,道光二十年(1840 年)左右增至100 万人;巨大用铁需求使广州成为佛山冶铁业第一大消费市场。 广州“生铁行、铁器行”,主要的职能就是销售佛山的冶铁手工业产品。人们的用铁需求林林总总,每家每户生活需要的锅瓢盆等, 海外贸易大船的制作和维修需要的巨量铁钉、铁锚等,人们的宗教和朴巫活动所需要的香炉、器物,人们日常劳作需要的铁制工具等等,都需要佛山冶铁业供应。正是在广州的市场需求这种刺激之下, 佛山的冶铁手工业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 明初,“南海为广州首邑。 所治乡落,佛山、九江并称繁盛,所以治之则异。佛山地接省会,向来二三巨族为愚民率,其货利惟铸铁而已。”[33](卷八)到成化、弘治年间发生了明显变化。 当时丘浚的《东溪记》记载:“南海之佛山,去城七十里,其居民大率以铁冶为业。 ”冶铁业十分兴盛,形成栅下、祖庙、汾水三个具有商业中心功能的核心地点。 它们是佛山城市最初的胚体。同时还形成了居民住宅区。到景泰年间,佛山“民庐栉比,屋瓦鳞次,几万余家。 ”[34]至明中叶竟已发展成为“两广铁货所都,七省需焉”的手工业巨市[35](卷三六八)。
第三, 广州市的高度发达的进出口贸易和国内外贸易对城市建设和凝聚人口的巨大需求, 直接刺激了甚至催生了佛山其他手工业支柱行业——例如陶瓷、纺织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据19 世纪30 年代游历广州的外国人记述:“许多需要供应广州各商号的制造业, 都在广州城西数里外名叫佛山的一个大镇进行。 ”[31](第一册,P304)这说明广州市消费者需求对佛山发展的刺激和带动不限于冶铁手工业, 而且包括其他主要手工业。 如驰名海内外的佛山制陶手工行业,应首先是在广州市场需求拉动下发展起来的。《粤中见闻》卷一七记载:“南海之石湾善陶,由来已久,供给通省瓦器之用”[36](P124)。明末清初的屈大均记载石湾陶器称:“凡广州陶器皆出石湾。”[4](卷十六·器语) 正由于广州需求庞大, 佛山石湾陶业迅速成长,明天启年间发展到八大行业,后来又发展到二十余行[37]。
不仅如此, 广州商贸海运需求也是佛山市各种手工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动力, 佛山有许多手工业产品就是直接供应广州用以出口的; 雍正十年(1732年),广东巡抚杨永斌给雍正皇帝奏疏言:“广东省城洋商贾舶云集, 而一应货物俱在南海县属之佛山镇贸易。 该镇绵延数十里,烟户十余万。 ”[38](P13-14)广州洋商许多货物也在佛山置办。
第四, 广州市的高度发达的进出口贸易和国内外贸易对城市建设和凝聚人口的巨大需求, 还直接刺激了甚至催生了佛山经贸行业的蓬勃发展。
广州外贸职能也刺激了佛山成为全国外贸商品货物在广州附近的大规模的储存地、囤货地、等待地和交易地。道光年间,“西北各江货物聚于佛山者多,有贩回省卖与洋者”[39](卷十一·艺文下·佛山赋)。 广、佛两地铅户和运铅水客也“在佛山地方合设铅务公所,省中设立公栈”。 一切贸易事宜由佛山公所负责。 洋船到粤,由佛山公所司事、水客会同通事与夷商议价买定。 由保商代运赴省报验, 然后将铅起回公所[40](卷三·户·铜铅)。云南土铅到粤,全部起贮佛山公所,“凭洋商收买,陆续运省报验,然后卖与夷人”[41]。 这种储存、囤货、等待的货量是巨大的。嘉庆年间,洋商在佛山转运白铅出口曾年达三百三十余万斤。 嘉庆二年(1807 年)粤海关监督常显奏言:“十年以内出洋细数内,至少年份七十余万斤,至多年份三百三十余万斤, 其余年份一二百万斤不等……查白铅向于佛山镇地方凭洋商收买,陆续运省报验,然后卖与夷人出洋”[41](卷十七·禁令一),以后,广东官府始议定以最少年份为度,“每年额定七十万斤, 于佛山镇凭洋商收买,运省报验转买”[42](卷一八·经政略23·市舶)。另一方面, 广州进口的洋货也需佛山推销到省内外各地。乾隆年间,佛山已是“商车洋客,百货交驰”。市面上的珍奇洋货充斥,有“玛瑙、玻璃、珊瑚、翡翠、火齐、木难、方诸、阳燧、鹤顶、龟筒、犀角、象鼻”等等。由于紧贴广州这一独口通商的巨大的外贸中心作功,佛山还直接承接了广州大量的内贸业务功能。以至于佛山在明清时期商业贸易也高度繁盛,甚至“商贾丛集,阑阅殷厚。 冲天招牌,较京师尤大,万家灯火,百货充盈,省垣不及也”[43](17 册,农商类)。 在全国有“天下巨镇”之誉。 并且,以广州为轴心,在商业上形成了同城运转的“大广州”分工体系:广州十三行聚集的是“外洋百货”,负责集散外国商品和出口的土特产品;而佛山镇聚集的是“内地百货”,负责集散“广货 (广东产品)” 和 “北货 (全国内地产品)”[44](P243)。 实质上,两相衔接,分工整合,良性循环,总体以广州的贸易发展和枢纽组织需求为主导。 佛山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广州城市经济延长发展的结果,因此,在当时人们的话语中,也往往言佛山必言广州,言广州必言佛山,如乾隆十五年(1750 年)时任和平县知县的胡天文说:“查粤省之十三行、佛山镇、外洋、内地百货聚集。”[45]很自然就将“省佛”并称。
这样,继“广州-澳门”连环之后,广州与佛山又结成了珠江三角多核中心城市集群中的第二连环——“广州—佛山”连环。这个链环,同样以广州为轴心, 是伸展向国内巨大内地市场方向的关键性的城市链条。
余 论
广州、澳门、佛山三相整合,就构成了珠三角经济、广东经济历史上第一个复合型城市中心集群。这一集群,以广州为轴心,贯通内外,一体运转,不仅成为珠三角和广东全省经济中心, 而且构成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而且为后来发挥同类作用的近现代“香港-广州-佛山”新三核城市集群、当代“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 新的六核式城市集群格局形成、发展、演化,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这一重要的城市经济发育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重要轨迹,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珠江三角城市集群发育的若干特点, 科学地认识和把握当下珠三角地区新型城市化和城镇化建设规律将有所裨益。
[1] 黄慈辑.珠玑巷民族南迁记[M].广州: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57 年刻印本.
[2] (宋)方大琮撰.铁庵方公文集:卷33[A]. 广州乙巳劝农文.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89 集部[G].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3] 司徒尚纪.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
[4] (清)屈大均. 广东新语[M].扬州:广陵书社,2003.
[5] (乾隆)张廷玉等奉敕撰..续文献通考[M].纪昀等校订.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万有文库(图片版),1929 年至1937年.
[6] (法)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M].萧濬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7] (民国)孙典籍.广州歌[A].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G].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8] (民国)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9] 徐凤晨,赵矢元主编.中国近代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
[10] (清)龙廷槐.敬学轩文集[M].影印本.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
[11] (宣统)梁鼎芬修,丁仁长等撰.番禺县续志:卷一二[A].实业志:旧志[O].宣统三年刻本.
[12] (清)赵尔巽、柯劭忞等.清史稿:卷一二三.志.九十八[Z].北京:中华书局,1977.
[13] 黄滨.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
[14] (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10.
[15] 查灿长.转型、变项与传播:澳门早期现代化研究(鸦片战争至1945 年)[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
[16] (葡萄牙)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远游记:下册[M].金国平译注.澳门基金会等,1999.
[17] 邓开颂等.粤港澳近代关系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3.
[18] 莫世祥. 近代澳门贸易地位的变迁——拱北海关报告展示的历史轨迹[J].中国社会科学,1999,(6).
[19] (清)梁廷枬.粤海关志[M].上海:文海出版社,1986.
[20] 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白银的输入[A].梁方仲文集[G].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21] 费成康.澳门四百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2] (明)俞大猷.正气堂集[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23] (明)王临亨.粤剑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4] (明)宋应星.舟车[A].天工开物:卷中[O]. 扬州:广陵书社,2008.
[25] 李龙潜.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6] (清)潘尚楫等修,邓士宪等纂.南海县志[Z].同治8 年(1868)刻本.
[27] 罗一星.明清时期佛山冶铁业研究[A].朱培建主编.佛山明清冶铸[G].广州:广州出版社,2009.
[28] (清)伍长华辑.两广盐法志[Z].铁志. 清道光16 年(1836)刻本.
[29] (民国)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Z]. 佛山刻本,1926.
[30] 唐文基.明代的铺户及其买办制度[J].历史研究,1983,(5).
[31] (崇祯八年)广州府南海县饬禁横敛以便公务事碑:佛山碑刻[A].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G].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32] (明)颜俊彦.盟水斋存牍[Z].二刻,卷一.诬指接济刘韬等二杖四徒[O].卷二.息讼霍见东等杖[O].《盟水斋存牍》二刻“详袁崇焕家产并流徙地方”.崇祯五年序刊本.
[33] (清)潘尚楫等修.邓士宪等纂.(道光)南海县志[Z].卷八.舆地略[O].(四).风俗. 清同治8 年(1869)刻本.
[34]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Z]. 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
[35] 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Z].北京:中华书局,1962.
[36] 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藩宪严禁挖沙印砖碑示:佛山碑刻[Z].明清佛山经济碑刻文献资料[G].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37] 广东文物展览会编.李景康.石湾陶业考[A]. 广东文物:卷十[G]. 中国文化协进会刊行,1941.
[38] (清)朱批谕旨:第52 册[A]. 四库全书423[G].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9] (清)吴荣光纂修.佛山忠义乡志[Z]. 清道光11 年(1831).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40] (清)黄恩彤.粤东省例新纂[Z].清道光26 年(1846),广东藩署刻印本.
[41] (清)梁廷枬.粤海关志[Z].上海:文海出版社,1986.
[42] (道光)广东通志[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3] (清)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4] 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M].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12.
[45] (清)曹鹏翊等修.朱超玫等纂.和平县志:卷一.舆地.险要[A].附录胡公讳天文详文[O]. 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