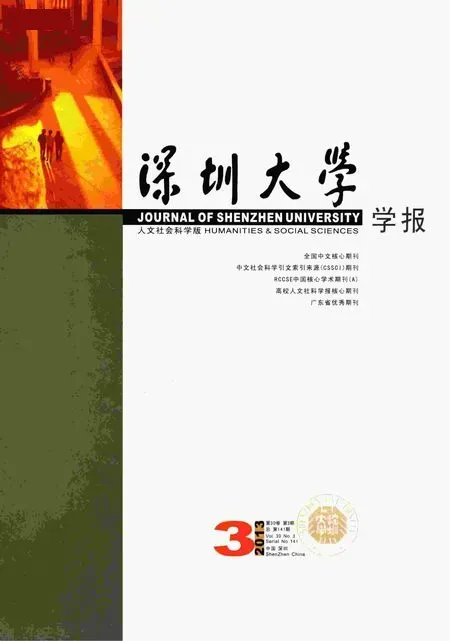从确认到竞争:人大代表选举的现存问题与改革向度
2013-04-07胡胜全
陈 文,胡胜全
(1.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广东 深圳 518060; 2.中共中央编译局, 北京 100032)
选举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涵, 选举制度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 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八大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历经五次修正①,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在实践中日渐完善,但客观地看, 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在运行中仍存在一些现实问题, 亟待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实现政治秩序稳定的双向维度予以制度调适, 逐步实现从“组织确认”到“有序竞争”的转变。
一、组织确认:人大代表选举现存问题的内在逻辑
人大代表选举的现实问题主要表现在选举程序、选举方式、选举理念、选区划分、候选人产生机制和人大代表履职等方面。
(一)“确认型选举”的程序设计
选举作为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实践形式, 不可不存在竞争。 “民主需要竞争,没有竞争的民主是没有活力的,甚至是形式上的民主。 民主不仅需要竞争,而且民主内涵着竞争。 ”[1]“没有进行竞争性选举,选举就可能变成推举”[2]。 作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法理上和文本层面内蕴着充分的民主制度优越性, 但其在实践中诸多民主因子并没有得以激活和有效落实, 高投票率往往需要行政动员才能实现。 我国人大代表选举长期以来实际上是一种“确认性选举”[3]的模式,即由组织推荐候选人,然后通过行政力量动员选民参加,最后经由选民投票确认产生代表。因此,选举制度事实上被简化为对组织安排的候选人予以确认的 “投票制度”,投票环节实际上变成了对必须当选代表的候选人的确认程序,正式候选人往往由组织认定,候选人之间缺乏竞争,不能通过公开的座谈、演说等方式与选民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及时了解选民的实际需求,争取选民的支持;而选民在实际的选举过程中, 也无法真正地了解候选人的政治态度、主张、履职能力等。 此种“组织确认”的选举模式,导致选举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竞争机制, 选民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受到一定制约, 人大代表的素质和履职能力也较难保证,往往不能真正代表选民的利益,协商酝酿程序不透明、间接选举中多重代理、高投票率假象、选民厌选情绪较高等问题就在所难免。
(二)单位选区划分法易导致人为操纵选举
选区是选举活动开展的基本场所, 而选区的划分直接影响着选举的公平公正。 《选举法》第二十四条规定“选区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也可以按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 ”但在我国选举实践中,首先,选区划分主要采取的是单位选区划分的做法,这种划分法存在诸多弊端,随意性很大,易导致人为操纵选举。单位选区充斥着各种复杂的因素,比如上下级关系、人际关系等,受单位因素影响,选民通常难以真实表达自己的选举意愿,而且这种单位选区选举出来的代表也很难真正代表选区选民的利益,而通常与单位利益绑定在一起,无法切实为选民利益履职。 “按工作单位划分选区使得人大代表选举成了不同单位之间的相互协商,选民难以当选代表,采取单位划分选区的选举实际上是不平等的选举;并且单位选举使选举行政化,不利于民主的发扬。 ”[4](P8-17)其次,选区划分的随意性较大,法治化程度偏低, 选举组织者往往利用选区划分确保其中意的候选人在选区内获得优势地位, 造成候选人之间的不对等关系。 同时选区划分的不稳定性不利于选民了解候选人, 容易造成选民厌选和盲选。“选民登记和选区的划分缺乏统一的法律准则,也为选举管理部门拥有了广阔的选举操纵空间。 ”[5]再次, 在实践中选区内的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存在较大差距,这与《选举法》第二十五条“本行政区域内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之规定明显矛盾。
(三)选民登记与投票计票环节存在缺陷
选民登记环节是对公民政治权利予以确认的重要步骤,直接影响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有序、规范和合法的选民登记能有效保障选民的政治权利。 选民登记是公民实现自我政治权利的自觉自愿的行为,但在我国选举实践中采取的则是被动登记方法,“选民登记”实际上演变为“登记选民”。 并且由于选民登记过程的透明度不高,往往出现漏登选民、人为选择性登记选民的现象, 容易引起选举争议甚至诉讼, 而且被动登记选民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也不利于培养选民的公民意识。
在选民投票环节上,《选举法》明确规定“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 选举时应当设有秘密写票处”, 但是秘密投票原则在现实中没能落到实处,比如许多选区并没有设立秘密写票处, 选民的投票行为直接暴露在公众之下; 流动票箱与委托投票又不规范,往往被滥用,选民难以真实表达选举意愿。 而在计票环节上则缺乏公开性、透明度,整个计票环节的监督不够,选民往往只知道选举结果,而不知计票过程是否透明和公开,选举的公正性受到质疑。列宁曾经说过:“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 ”[6]
(四)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产生机制不完善
根据《选举法》第二十九条关于“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的规定可以看出,在法理上,这两种方式推荐的候选人应当具有平等的权利地位。但是在实际的选举中,党团组织提名的候选人通常具有组织优势, 利用组织资源扩大影响力参与选举, 与选民联合推荐的候选人或者以“另选他人”的方式参与竞选的候选人之间存在不对等关系。
在正式候选人的确认上,“将初步候选人筛选为正式候选人的过程, 是由一个没有客观标准且不透明的协商环节来界定的。 ”[7]讨论、协商、酝酿方式不够详细具体和公开透明,酝酿过程也无明确的标准,而且欠缺对协商、酝酿不成的救济制度,而预选程序作为协商、酝酿方式的备选,又因人为地有意无意回避而导致难以启动, 这使得正式候选人的遴选具有较大的主观性, 特别是许多依法产生的非组织候选人在这一环节被协商下去,造成不少选举争议。在正式候选人的介绍上, 选举机构对正式候选人的介绍机械简单, 同时又缺乏必要的候选人与选民的会面沟通机制, 无法真正使选民全面了解正式候选人的政治态度、代表意愿、当选承诺及履职能力等。
(五)选举的组织制度和诉讼救济制度不健全
选举机构是组织选举和维持选举秩序的重要保障,为保证选举按既定的规则和程序进行,通常需要设有中立的、制度化的选举组织。选举管理组织大致可包含选举主持机构与选举争议处理机构, 为保证选举的公正性,选举的主持机构必须相对中立,而选举争议的处理机构则又必须相对独立。 然而在我国选举实践中, 选举组织往往由各级人大及党政负责人在选举年临时组成,这既难保持中立,又非常设机构,因此制度化程度低、稳定性差、专业化程度低。
同时, 由于我国目前没有设立专司选举监督职能的机构,选举组织者本身还是选举的监督者,这实际造成监督的虚化。除此之外,选举实践过程中也缺乏选举的诉讼救济制度, 对选举中出现的诉讼争议没有专门司法机构受理裁决, 人民法院对于此类案件往往采取不予立案的处置方式, 这使得选举本身的公正性遭到质疑。
(六)片面强调人大代表的结构而忽略参政能力
我国人大代表选举为了实现代表形式上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往往人为地硬性规定代表的构成比例,“重结构,轻能力”[8]的现象比较普遍。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安排型选举的出现, 也造成以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为标准来确认人大代表候选人的问题, 在人大代表的构成中党政官员的比例过大, 人大代表名人化倾向明显,比如一些欠缺参政能力的体育名人、企业家、社会名流等成为人大代表,这不仅剥夺了选民的选择权,而且为了保证组织认定的候选人当选,往往造成候选人之间的不平等参选, 也使得具有强烈自主参选意愿的选民被拒之门外。
(七)人大代表兼职化影响其专业化履职
由于兼职化和监督缺乏, 人大代表实际上荣誉性较强、 责任性不足, 人大代表的履职状况不甚理想。多数人大代表平时担任着繁重的本职工作,仅仅视代表为“第二职业”,无力顾暇联系选民和反映民意的政治性工作。 人大代表兼职化直接导致人大代表履职责任性不强,积极性不高,人大代表与选民或所在选区联系不紧密, 难以切实反映选区选民的利益诉求;加之人大代表素质参差不齐、代表活动经费保障困难以及缺乏相应的培训机制等原因, 致使人大代表提案率低、质量不高,代表价值难以体现。 人大会议上,有的代表是“哑巴”代表(不发言),有的是“个人”代表(凭个人的认识水平,发表一通个人见解);有的是“观风”代表(看别人怎么发言,怎么投票划圈),这都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民,不需要对谁负责,代表与选民脱节造成的[4](P8-17)。
(八)间接选举过程中存在多层代理问题
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分为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两种方式。《选举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因此在制度运行过程中, 人大代表选举中不可避免存在多层间接选举与民意的多重代理问题。 这使得基层民意难以通过制度化渠道,如实有效地上升为国家的政治意志。在选举实践中, 多层间接选举不仅造成选民和代表之间沟通不畅,利益联系变得愈发淡薄,选民厌选情绪日益浓厚, 同时也使得选民监督代表变得困难重重,极大地影响了代表的履职水平。 “现实中的多层间接选举模糊了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之间的委托责任关系。 ”[9]有的甚至认为,“人大代表所在人大的行政层级越高,其民主性越差”[10]。
(九)人大代表的罢免程序难以启动
人大代表的罢免制度是保障选民拥有完整的政治权利的重要制度设计。我国《选举法》中明确规定,人民不仅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同时也具有罢免人大代表的权利,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受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的监督。选民或者选举单位都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但是《选举法》在实现选民罢免权的制度设计上并不完善, 在法理上,选举权与罢免权同属宪法性权利,选举是对代表的授权行为,罢免则是收回授权的行为,选举与罢免都是选民当家作主的体现,都体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应当具备同等的法律地位[11]。 但是实践中并不如此, 如选民十人即可联名推荐候选人, 而罢免案的提出却须至少30 名代表联名提出,且必须得到全体选民半数以上同意才能形成最终的罢免。《选举法》对选民行使罢免权规定比较粗糙,对罢免理由的规定并不详细, 对罢免理由的审查形式也无具体规定,罢免争议的解决机制不健全,最终导致罢免流于形式。
二、有序竞争: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改革向度
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板块,其发展好坏直接关乎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能否实现, 涉及到党和政府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能否科学制定和实施。 因此改革与完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势在必行, 以提高我们党对现代民主选举的驾驭能力。 鉴于现阶段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暴露出来的以上诸多问题, 改革与完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应该遵循从“组织确认”到“有序竞争”的改革路径,实现其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运行。
(一)增强正式候选人遴选程序的公开性透明度
协商酝酿方式是我国选举过程中确认正式候选人的主要做法, 但该方式操作时欠缺公开性与透明度。 第一,应该明确酝酿协商方式的操作细节,就如何酝酿协商做具体规定和标准设计, 如协商酝酿前公布候选人信息、协商酝酿时增加候选人参选演讲、选派选民代表参与协商讨论等。第二,应当充分保证候选人的知情权, 对获得或未获得正式候选人资格应当给予正当理由。 第三,为增强公开性与透明度,可考虑在协商酝酿时进行全程监督、电视转播等。第四,必要时可考虑放弃协商酝酿方式,改而主要采用预选方式产生正式候选人。
(二)建立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制度和竞选机制
为确保大多数选民知晓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建立选民与候选人的利益关联, 除必要的候选人情况介绍外,应建立候选人与选民的见面机制,如通过座谈会、走访选民等方式,让选民真正了解候选人的参选意愿、政治态度、履职能力等。在选举过程中,可适当引进竞选机制,增加有关竞选的具体内容,对竞选方式、竞选程序、竞选行为、竞选时间、竞选地点、竞选管理、竞选资金等做出明确规定,在选举投票前允许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进行选举宣传等,确立和强化选举的差额选举、秘密投票和选举回避原则。改变实践中“确认型选举”或“安排型选举”的现状,真正尊重和实现选民的主动选择权。
(三)设置中立的选举管理和监督机构
设立中立、常设的选举管理组织,有助于提升选举管理组织的公信力, 增强选举的合法性认同。选举管理组织的职能可包含负责人大代表的选举、选举争议的处理、人大代表的培训管理、民主政治的宣传教育等,其整个运行过程应当向全社会公开,其成员不应当与候选人混同,否则应予退出。为保证选举的公正公平,应当健全选举的监督保障机制。可引入第三方机构在选举时全程参与选举观察与监督,如社会团体、新闻机构、研究机构等[12],并对选举的公正性做出评价,确保整个选举的公开性、公平性与透明度;除此,还应当设立专门的司法机构,对选举中出现的选举诉讼予以受理, 对选举效力与选举过程中的违法操作予以公正裁决。
(四)依据选民的利益同构度来划分选区
应依据选民的利益同构度, 主要按地域和居住状况来科学划分选区,使选区划分制度化、法治化、稳定化, 解决单位划分选区造成的选区内人口数和选民数相矛盾的现象, 避免单位因素阻碍选民真实意志的表达;并且选区的划分应当相对稳定,使得选民能够真正了解选区的状况, 熟悉选区内的优秀人物和民意代表, 避免人为操纵选区划分控制选举结果的现象。
除此之外,为增强人大代表的履职责任,密切选民与人大代表的利益关联,提升选民的选举热情,强化选民监督与罢免权的动力机制, 使人大代表切实为选民服务,应当建立人大代表与选民的联系制度,可考虑制定人大代表定期会见或走访选民制度,包括走访或会面前的通告、走访或会面后的汇报及选民事务的处理等, 也可考虑在选区内设立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等,完善人大代表联系选区(社区)制度。
(五)规范选民登记和投票计票环节
应当按属地原则和自愿原则改革选民登记办法,改变选民被动登记的局面,让选民主动登记,不可简单倚重行政动员式的“高投票率”。 在依据利益同构原则划分选区的基础上, 考虑在选区内设立选民登记站,在登记日期内可通过报纸、电视、海报等进行选民登记的宣传, 同时还可派登记员上门散发传单和通知等,以此告知选民登记事宜,强化选民登记意识。
在选民投票过程中,应当规范投票过程,特别应当设立秘密划票间,让选民按自我意愿写票和投票,同时应规范委托投票程序和流动票箱的设置标准。为增强计票环节的透明度,在计票环节上,应当保证计票的公开公正,做到即时计票、即时公布选票和宣布选举结果, 可考虑采取电视直播的方式让整个计票环节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六)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
应当建立法治化、制度化的人大代表工作制度,逐步推进人大表专职化。 一是完善人大代表述职制度。 明确向谁(选民或者人大会议)述职、如何(述职报告或者选民质询)述职、述职内容(提案数量、工作情况等)、何时述职及述职时间间隔等。 二是完善人大代表的辞职制度,破除人大代表届内“终身制”。明确辞职类别、辞职程序等,对不能履职、不愿履职、不尽心履职的代表可主动辞职或劝其辞职。 三是完善人大代表罢免制度。明确罢免标准,科学设立罢免程序(如提出程序、受理程序、听证程序、申辩程序等),尊重选民罢免权和人大代表的申诉权。 四是完善人大代表培训制度。明确人大代表的培训周期,采用多样化的培训方式 (定期学习、 举办讲座、 专题讨论等),培训经费应当专款专用,培训内容应当涉及党和国家重大政策法律及代表参政议政能力等, 同时可加强培训交流和人大代表之间的联系等。 五是逐步推进人大代表专职化,建立相应的职业保障制度,比如行业规范、离退休制度、工资制度、履职制度、奖惩约束制度等。 逐步限制各级人大代表中党政官员的名额,提高弱势阶层的代表名额,同时明确人大代表的责任, 不以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等作为标准提名人大代表候选人, 逐步扭转人大代表的名誉化倾向。
(七)扩大直接选举范围
根据《选举法》规定,我国直接选举的范围仅限于“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 在公民政治参与扩大化情况下,我国现有的直接选举的范围明显过窄。经过改革开放30 多年的发展, 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进步, 人们的利益意识、权利意识、参政意识不断提升,人文素质与政治知识也有较大提高,无论是在技术手段上,还是在人们的政治素质上, 均为我国实行民主选举创造了条件。 因此,应该适当扩大直接选举范围,适度平衡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 可尝试在全国和省级人大代表中设置一定的直选代表比例, 在人口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进行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试点。
注: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分别在1982、1986、1995、2004 年以及2010年进行过修正,本文所引用的条款内容均来自第五次修改后的选举法。
[1] 谢庆奎.民主需要竞争[A].载唐娟,邹树彬主编.2003 年深圳竞选实录[C].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299.
[2] 钱昊平.俞可平看政府创新:“不进行竞争性选举,选举可能变成推举”[N].南方周末,2012-01-16.
[3] 黄卫平,唐娟,邹树彬.2003 深圳市区级人大代表竞选现象的政治解读[A].载唐娟,邹树彬主编.2003 年深圳竞选实录[C].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195.
[4] 蔡定剑.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4,(6):8-17.
[5] 邱家军.2011 年上海人大代表直接选举观察报告[A].黄卫平,汪永成主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第10 辑)[C].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51.
[6] 列宁选集:第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3.
[7] 何俊志.选票里的公平[J].阳光,2012,(9)(总第124 期).
[8] 唐娟,邹树彬.2003 年深圳竞选实录[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262.
[9] 邹平学.中国代表制度改革的实证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39.
[10] 秦前红.如何解读“申纪兰现象”[EB/OL].共识网,2013-03-16.
[11] 王全法.完善基层人大代表罢免制度的若干思考[J].人大研究,2012,(1):35-39.
[12] 蔡定剑.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