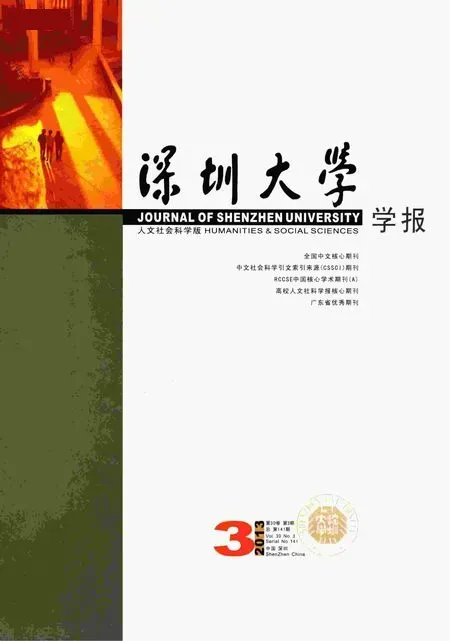消释死亡恐惧:马克思“关系”死亡论对传统死亡论的超越
2013-04-07尤吾兵
尤吾兵
(安徽中医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8)
死亡是极难描述和定义的, 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对死亡经验做出感受上的说明, 所以有人把死亡形容为一个无法认知的文化“黑洞”。 “恐惧死亡”成为民众心理的常态。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展,在以崇尚经济理性为内涵的思想文化形态作用下, 影响着人们对现代死亡的认识呈现出“物质化、个己化、单面化”等趋向,而这些对死亡表象的认识却常被误当作死亡的本质属性, 其直接后果是加重了现代民众对死亡的恐惧。 超越死亡恐惧需要回归对死亡本质的正确认识, 这可以通过从哲学角度揭示死亡的价值来实现。 哲学视域中对死亡本质的认识产生有“灵魂论死亡观、道德论死亡观、存在论死亡观”等传统观点,但这些思考往往陷于个体死亡维度的认识,没能从群体角度辩证地认识死亡, 对死亡本质的揭示缺乏普遍适用性。 而马克思“关系”死亡论立足于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规定, 深刻揭示了死亡的社会关系实质,消解了死亡恐惧意识,是应着力深入研究的理论形态。
一、市场境遇下死亡意识的异化
市场经济的推展带给社会经济的巨大腾飞,相应也影响着民众对死亡本质的看法。 市场经济具有“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张扬个人主义、崇尚急功近利” 的人文特征, 这就影响着现代死亡意识产生异化,呈现出“物质化、个己化、单面化”等表征,而这带来的结果是更加重了民众恐惧死亡的心理, 造成民众的“生死品质”越来越低下。
(一)死亡物质化
所谓死亡物质化, 是指现代死亡不纯粹是一种自然现象,更多地表现为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人们希望用现实中更多的物质东西来粉饰死亡, 试图把死亡装扮得不那么可怕,冲淡对死亡的恐惧,使死亡呈现为物质化趋向。这在现实社会中表现为:死者的陪葬品越来越昂贵,丧葬仪式越来越隆重,厚葬观念越来越强烈。比如在我国大部分农村,为死去的亲人选择墓地,总爱找所谓的风水先生来测寻;埋葬要选择高级的棺臼;下葬时习惯把用纸张做成的纸马、电视机、小汽车、甚至小洋房在坟前焚烧。 城市里对于死亡的处理更显物质化,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报道,高额殡葬费、 天价墓地不断出现等。 城市人总要托关系、走后门,花很大一笔钱买上一块好的墓地安放死去的亲人,以致城市人惊呼“死不起!”死亡物质化趋势的加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经济社会条件下让人们过分看重现实的物质利益, 物质成了现实中最真实的东西,其它的都被认为是虚无的,社会成了以索求经济利益为轴心的场所, 所以大多人喜欢追求现实物质与金钱的获取,以求取利益、求取享受为人生的目的。 而现实中这些东西在人死去时又无法带走,于是人们曲折地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在死亡陪葬品上、死亡仪式等方面拼命花费金钱,目的是让自己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延续着现实中的物质享受。深层分析死亡物质化趋势可以看到,人们这样做其实反映出的还是对生的过分依恋, 对死的极度害怕。但在死亡不可避免地降临时,本意想通过对死亡进行物质化地粉饰,减少死亡的恐惧,但死亡却被异化为高级棺臼、昂贵陪葬品、粉怖的送葬场面等,这样却更加重了现代人对死亡的恐惧。
(二)死亡个己化
所谓死亡个己化①,可以理解为现代死亡越来越成为是个己一人的事情, 把死亡看作由当事人个人来全部担负,与其他人无任何关联,其他人也无能为力的事情。 这样,现代个体的死亡就成为一无所依、孤单的事件,死亡恐惧由此更加强烈。这当然也与经济社会环境有关系。经济社会讲究竞争,讲究个性的张扬, 个体必须在激烈的竞争中把自己打造得无比坚强, 把自己的独特释放到极限,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人们练就了热衷追求自我生命最高点的完成,习惯自私地生存下去,常有人对生活这样诠释:“生活是自己的,要为自己活着,自己幸福就好”;“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等。学者康琼的解释更能说明这点:“(个我化) 认为生命是我的,生活是我的,人生亦是个我的,追求绝对个我的感觉和个我的价值。 ”[1]这样造成了人们的欲望越发膨胀起来,对生的依恋就越来越强,时刻担心死亡会降临,从而毁灭现实中的一切,相应对死亡就会越发恐惧:“这种个我化固然可以抓住现实的物质获取和生活上的享受, 但在死亡面前则必然会感到一无所依,人之死成为无可挽回的死。个体生命的丧失无法成为人类生命延续中的死, 最个我化的生活与最个我化的人生也导致最个我化的死亡, 而这引发的死亡恐惧必然是相当强烈的。 ”[2]
反观中国传统社会, 由于传统中国一直是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 人们对经济利益的冲动没有现代人强烈,死亡意识就不会出现“个己化”的状态。我们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当时人的生存理念,人们往往把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与家庭、国家联系起来。 自己的生存发展和价值实现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更是关涉家庭、整个家族的事情,放大点说,是与国家息息相关的。 这样,个人是家庭、集体和社会大家庭中的人,个人的自私观念就不强烈。在死亡问题上也是如此, 个体的死亡不会是孤单个己的事情,因为个体是与家庭密不可分的,死亡往往主要是家庭去对待的事件,家庭、家族都会对个己的死亡给予各种关注。在对死亡意义认识上,人们也不是把个己死亡看作是对个体的彻底毁灭, 因为他们认为个体虽然死亡了, 但与其相联系的家庭子孙的延续和家族的续存却是个己继存的体现形式,这样,传统社会里人们恐惧死亡的心理相对会弱些。
(三)死亡单面化
所谓死亡单面化, 是指现代人追求的只是良好现实生活和生存状况的实现,活在当下,享受现实,把死亡简单等同于对现实的彻底毁灭, 而不愿意去思考甚至放弃思考死亡具有价值和意义的另一面,即缺乏对死亡积极价值一面的理解和思考, 死亡意识呈现出单面化趋向。死亡问题需要人们以“安静的心境、舒展的态度、深入的冥想,才能对死亡看透、思透、解透、参透”[1],也就是对死亡的认识必需经过艰辛的思想的探索历程, 跳出现实中简单认识死亡的一面,进入意义世界以真正把握死亡的价值。只有这样面对死亡,才能超越死亡。 反之,死亡单面化意识只会加剧死亡恐惧的产生。很明显,死亡单面化也是经济社会现实影响下的结果, 经济社会中人们喜欢讲究效率,使生活节奏空前加速,朋友、亲人见面问候“近来生活还好么? ”回答的常用语就是“忙死了!累死了! ”这样,人们应付现实的心态多是急功近利型的,能够快速、便捷地提高效率或者获取经济利益最大化,被认为是发展的最佳途径,导致人们不愿拿出时间去思考经济利益之外的事情, 哪怕是安身立命的死亡问题。 “短、平、快”的心态导致人们缺乏对事物的深度解析。对死亡问题亦是如此,“单面化”而不是“多维化”来思考死亡,死亡恐惧的加剧是必然的结果。
二、哲学视域中“死亡本质”认识的三种传统理论
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同学科都曾试图对死亡本质进行“解密”,以此来中和死亡带给人们的恐惧。在众多学科中,生物学、医学等学科对“死亡”进行了表象上的定义,如:死亡是指机体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的终止, 死亡是心肺功能丧失或不可逆脑功能的丧失等。这些认识实质是把死亡等同于肉体的毁灭,没能认识到生命的精神属性一面, 死亡成为生物体 (人类)不可避免的宿命。这种认识很容易使人产生死亡恐惧。
哲学是对事物本质进行探求的学问, 对死亡研究来说,哲学与生物学、医学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不是简单地从死亡的现实表现来认识死亡, 而是通过透视死亡现象来揭示死亡的实质问题, 即对死亡的本质进行拷问。 这里我们可以凭对西方哲学的考察为例。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一直关注死亡的研究,哲学家们甚至把死亡研究规划为自己最终极的研究目标。从柏拉图喊出“哲学是死亡的训练”开始,不同的哲学家、哲学学派对死亡都给出见解,呈现出缤纷多彩的死亡观。西方哲学对死亡进行定义时,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始终围绕着“人是什么”这根红线来展开的。因为死亡是人的死亡,哲学在首先解决了“人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上升到对终极问题——死亡问题的思考。围绕“人是什么”的解释,哲学对死亡本质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传统观点:
(一)灵魂论死亡观
人是灵魂和肉体的集合, 这是西方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直到现在,灵魂是构成人的主体的观念仍占据着大多人的思想。因此在解释死亡时,把死亡定义和灵魂紧密联系起来是西方哲学研究的习惯做法。 第一个从哲学高度来认识灵魂的应是毕达哥拉斯,他对死亡的定义就是和灵魂联系起来,认为灵魂和肉体的结合构成了人,在这个合体里,由“数”构成的灵魂是伟大的,它不仅推动自身,也推动人的肉体,但一旦人去世,灵魂就会离开,身体便变成了尸体。毕达哥拉斯认为灵魂在肉体里如同在监狱里,会受到束缚,所以灵魂要获得新生,死亡是必要的过程,“因此, 在他看来, 人的死亡对灵魂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对肉体束缚的一种解脱。 ”[3]被冯友兰比喻为“希腊三子”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解释死亡时,也都与灵魂有关。从灵魂论上对死亡定义的著名人物是柏拉图。 柏拉图也认为灵魂是构成人的主要部分,并且灵魂也是不朽的。柏拉图认为这也是可以论证的。柏拉图继承毕达哥拉斯的观点,同样把灵魂看作是受肉体困顿的,所以对于死亡,他认为“死亡只不过是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很明显,柏拉图把死亡当成了是对灵魂的解放和拯救的方式。 传统灵魂论往往把灵魂看作是构成人的存在的实有,即相信灵魂可能是某一实在东西,但随着社会发展,灵魂被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所解蔽,灵魂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一种思想信仰。 但近现代西方哲学在解释死亡时,依然认定灵魂的存在,如理性主义代表人物笛卡尔。笛卡尔是身心“二元论”的建立者,他认为“灵魂”和“物质”均为地位相同的“实体”,但人是思维的存在,所以“灵魂”会比身体更恒久,也就是灵魂不朽,“人的精神或灵魂, 按其能够被自然哲学所认识的程度来说,是不死的。 ”[4](P155)但“人的灵魂虽与全身结合,可是它的主要位置仍在脑部;只有在脑部,它才不但进行理解、想象,而且还进行直觉活动。 ”[4](P49)可以看出,灵魂在理性主义者那里,已经丧失了以往神圣存在性, 而上升为一种精神信仰上的东西。 总之,西方文化中预设灵魂,把灵魂看作不朽的实有或信仰都是赋予灵魂具有形而上学意义。它的作用是使人获得内心信念的坚定性, 满足人的终极性向往。而从灵魂上来定义死亡,其目的就是看到了肉体具有毁灭性,而预设了灵魂存在,可以消释死亡毁灭肉体带给人们的恐惧性。 灵魂论死亡观移开了人们对死亡恐惧注视的视野。
(二)道德论死亡观
人不仅被看作使肉体的集合体, 更多的是精神的集合体,或者称为是道德价值的集合体,这是近现代西方文化对人的本质的认识。 西方许多思想家对人是道德体进行了讴歌, 莎士比亚就讴歌人是宇宙的精神,万物的灵长。西方谚语“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也说明人是具有道德性的一面。 对死亡的定义,从道德价值上看也是一种西方的死亡观。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应是康德。 康德的整个哲学可以说就是对“人”的反省,从“人能知道什么”到“人能做什么”,再到“人能信仰什么”的追问,即从“纯粹理性批判”到“实践理性批判”再到“道德形而上学”的追问,康德历经层层理性批判, 最后揭示出人之为人的特色,人就是具有“感性、知性、理性”能力的道德体。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说“定言命令只有一条,这就是: 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律的准则去做。 ”[5]在对死亡的认识上,康德首先认为从灵魂上界定死亡的传统死亡观存在着极大的问题,那就是传统思想定义死亡的前提是灵魂不朽且灵魂可以被证明。 康德认为既然灵魂不可以在经验中见及,我们不可见及也就无法去认知,那么我们对灵魂便不可避免地无知,所以关于灵魂不死的任何理性设定都是不允许的。“灵魂作为单纯的内感官对象的持存性仍然未获证明,甚至是不可证明的。 ”[6](P298)但这并不是说康德否定了传统灵魂不死的论证理路,就否定灵魂的存在。相反,康德坚信灵魂、上帝存在,但这种灵魂、 上帝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推导论证出来的精神实体, 而是具有更高层次的即道德上的意义,“这种确信不是逻辑上的确定性, 而是道德上的的确定性,而且由于它是基于主观根据,所以我甚至不能说:上帝存在等等,这是在道德上确定的;而只能说:我是在道德上确信的等等。 这就是说:对上帝和来世的信念和我的道德意向是如此交织在一起的。 ”[6](P627)既然灵魂只是具有道德上的确定意义, 而人的死亡又主要集中在灵魂不朽与否的讨论上,那么在人的死亡定义上,康德就把死亡和道德联系起来,即在康德看来,人们要达致意义的人生或者灵魂上不朽,必须树立高尚理想并全力以赴,注重自身道德价值的实现 (其实也就是灵魂获得了道德确定性), 人的生死才有意义。 “为了实现一个伟大抱负,去进行按部就班、勇往直前的工作,结果就充实了时间(因为工作延长生命),这是使自己快乐,且满足于生活的惟一可靠手段。‘想得越多,做的越多,你就活得越长久(哪怕是在你自己的想象中)。 ’”[7]意志主义哲学家尼采的死亡观也是这样认识的, 他认为人们只有通过不断创造来实现自我价值, 才能成就人生, 在死时才能显示出道德性,“在你们的死之中,你们的精神和德性当依然熠熠生辉,有如晚霞环绕大地:要不你们的死是不成功的。 ”[8]类比来看,道德论死亡观的意义和中国儒家文化里“朝闻道,夕死可矣”思想是相通的。
(三)存在论死亡观
存在主义可以说是影响20 世纪西方思想的最大的哲学流派, 它关注的不是传统哲学热论的诸如抽象意识、 道德概念等方面的问题, 而是以人为中心,注重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探求。它把人当作一种精神的存在,而且是唯一的真实的存在,并且把人的精神意识同社会存在以及个人的现实存在对立起来。其代表人物有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以及萨特等人。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是“存在”,这种“存在”不是用来泛指事物的存在, 而是更多地用它来解释人的生存意义, 把人解释为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的存在者。比如在海德格尔那里,当谈及人是有理性的生物体时,他就属于现象世界;而当把人指向可以“自由选择”的维度,他就是本体世界的“存在”。 海德格尔还用一个专门词语“此在”来表示人是这种特殊的存在者,这种“此在”其实就是作为存在着的人的先于一切本质的可能性,“此在不是一种附加有能够做这事那事的能力的现成的东西。此在原是可能之在。此在一向是它所能是者;此在如何是其可能性,它就如何存在。 ”[9](P167)因此,在存在主义哲学那里,“此在”就是存在着的人的本质。海德格尔更认为解释人的生存意义,必须把死亡和“此在”联系起来,“死亡所意指的结束意味着的不是此在的存在的到头,而是这一存在者地一种向终结存在。 死亡是一种此在刚一存在就承担起来的去存在的方式。 ‘刚一降生,人就立刻老得足以去死。’”[9](P282)死亡始终伴随着“此在”的过程,“死亡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 向这种可能性存在,就为此在开展出它的最本己的能在, 而在这种能在中, 一切都是为的是此在的存在。 ”[9](P302)这样就对于死亡做出了全新的认识,即把人解释为始终与死亡相伴随的存在者, 死亡是世界上最私有的东西, 每个人都具有但任何人又不能代替他人,是“最本己”的,而人存在的意义又必须在死亡中展现出来,只有死亡才可以“把此在之存在的所可能具有的本真性与整体性从生存论上带到明处”[9](P269),所以人是“向死而生”的存在。 这成为海德格尔其实也是存在主义死亡观的核心观点。 存在主义对死亡的认识可以说是把死亡限定为体现人存在意义的必然环节, 这样就把死亡意义上升到一个高度, 可以让人从对死亡恐惧的现实沉沦状态中超拔出来,实现存在的意义。
可以这样理解,灵魂论死亡观、道德论死亡观以及存在论死亡观超越了对死亡的现象学认识, 从哲学高度赋予了死亡在不同意向上的内涵, 对理解死亡本质、超越死亡恐惧具有一定的价值。但这些思考死亡本质的理论观点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 就是它们虽然承认死亡的必然性、客观性,但它们往往还是陷于现实世界以及个体死亡维度,片面认识死亡,没能真正从死亡的积极价值方向和群体角度辩证地理解死亡,对死亡本质的揭示缺少普适性。也正像学者周德新认为的:“它们不能科学地、 合理地把握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个体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没有正确回答死亡的本质问题。 ”[10]另外,最主要的是这些理论都把“人”排除在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环境之外来考虑, 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指导民众消释死亡恐惧的可能性大打了折扣。其实,能够消释民众死亡恐惧的理论,还须回到对马克思“关系”死亡论的探究上来。
三、马克思“关系”死亡理论形态的内蕴
马克思的死亡论可以说是一种科学的理论。 它用辩证的方法审视死亡,藉以对“人”本质做出科学论断。从“关系”维度揭示死亡的本质,马克思的这种死亡观可以称为“关系”死亡论。 它把个己的死亡上升为与社会群体相联系,死亡具有社会价值性。又由于马克思哲学自身固有“实践”特性品质,这决定了属于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关系”死亡论切实具有指导死亡实践的价值。
在对死亡的认识上, 马克思首先承认死亡是一种自然规律,具有必然性,人也是不能逃离的。“死似乎是类对特定个体的冷酷无情的胜利, 并且似乎是同它们的统一性相矛盾的; 但是特定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存在物, 而作为这样的存在物迟早要死的。 ”[11]马克思哲学从辩证法角度对这种必然性进行认识,提出“辩证法就是死亡”的著名论断,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死亡。 死亡不是一个外在于人的生命之外的事件, 死亡是与生命紧密相联系的。死与生是相对的,但又是辩证统一的。对于这种辩证关系,云格尔所说的话语是最好的注解:“死与我们相关。 因为,只要我们存在,死就存在;如果我们未曾或不再存在,死也就不存在了。 死依据生活着。 ”[12]同样,唯物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对待死亡的认识也是相同的,“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 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 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 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这样。 ”[13]
最应关注的是, 马克思对死亡本质的揭示是从“关系”维度来进行的,这需要联系马克思对“人”的诠释来看。 那么“人”是什么呢? 马克思对此的论断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4](P56)这个经典表述把“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殊规定性界定为“社会关系”,科学地阐明了“人”的本质。 其意义有三:一是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人”不仅是具有肉体的存在者,“人” 和动物区别开来的主要依据只能是“人”会进行社会生活,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14](P270)二是“人”是社会中的“人”,“人”的本质又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是社会关系的某一个方面。 在社会生产实践过程中, 人们不仅结成了生产关系, 而且形成了政治关系、思想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 所以,揭示“人”的本质,只有把“人”放到各种社会关系中综合考察,才能真正把握“人”的本质。三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规定,不仅表示“人”的本质具有客观性,而且也有变动性、历史性。 社会是具体的、历史的,因此必须对“人”的社会关系做具体的历史考察。总之,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能到现实生活之外去寻找,“人” 的本质就存在于现实的、可感知的、发展变化着的社会关系之中。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揭示告诉我们:对死亡进行哲学定义时应与 “社会关系” 密切联系。 既然“人”是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死亡又是对“人”的最大的毁坏,这种破坏的对象很明显是“社会关系”,所以可以理解成 “死亡是人的现实社会关系的终止”。 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在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中延续和表征着自我的存在, 显示出自己存在的个体性和独特性, 而死亡标志着作为存在着的“我”的一切社会关系从此不复存在,所以,死亡在哲学上就可以定义为:“人的现实社会关系的终结”。 这也就是马克思“关系”死亡论的内涵。 从马克思把死亡看作是“类对个体的残酷无情”,也可以清晰看出马克思的死亡观是“关系”论的主张。
另外,进一步思考,“关系”死亡论让我们认识到“人”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切社会关系包围下的存在,相应它就警示我们应注意,死亡本质不仅仅表现在个己躯体、 灵魂等方面的消失, 死亡是和各种“关系”联系起来的,死亡的社会属性被凸现出来,这种社会性即死亡已是超出个己范围的事情, 而是与社会群体发展相关系的, 死亡具有社会价值性。 所以,“关系”死亡论要求将个己的逝去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 尽力弥合死亡带给个体的各种“关系”的破坏。也就是说,不能把自己的死亡看作是单纯的个人事件, 个人死亡要体现出对他人和社会具有的意义。惟此,“关系”才不会因为个体的消亡而消亡,社会才能延续下去。其实也可以说,这种“关系” 死亡论内蕴着死亡是一种不断打破现存社会关系而又在不断重新组合社会关系的力量, 它重点不是强调一切“关系”终结,而是强调这种终结只是现实社会关系方面;死亡也不仅仅是个己的死亡,而是为他者、 为社会的死亡; 要体现出死亡的利他性价值,才能维护各种社会关系的延续。这是死亡表现出的应然伦理维度。
再有,马克思“关系”死亡论是具有实践意义的。因为马克思哲学始终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在 “实践”上,“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的鲜明品性,所以作为马克思哲学体系一部分的死亡哲学不是简单地陈述死亡的观点和看法, 而是教导人们在死亡实践中认识生命的真正意义,正确对待死亡,从畏惧死亡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所以,按照马克思“关系”死亡论来“实践”时,当我们把个己生命和他人、社会联系起来时,即使死亡来临,也是无所畏惧的。 在革命战争年代,那些革命先烈在刑场上、战场上能够从容面对死亡就是例证, 因此马克思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 为大家而死,高尚的人将为此洒下热泪。 ”[15](P7)
四、马克思“关系”死亡论对当下死亡恐惧意识的消释
马克思“关系”死亡论辩证地揭示了死亡本质,在最高层次上对死亡进行了定义, 这是灵魂论死亡观、道德论死亡观、存在论死亡观等不可比拟的。 在灵魂越来越受到怀疑、道德越来越高不可攀、存在与虚无之争越来越强烈等现实状况下,“关系” 死亡论可以帮助我们消释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无论怎样,我们都不会否认人们是处在现实关系之中,马克思“关系”死亡论具有的实践价值就在于此。
首先,“关系” 死亡论可以消释死亡物质化带来的死亡恐惧。 市场经济社会把生命意义追求一味引向经济的获取。面对一个人的死亡,对其“盖棺定论”的评价也习惯上看这个人财富获取多少, 评价人的死亡价值往往也是与金钱划等号。 因而逝去者的丧葬场面越隆重和越华丽越好,逝去者的坟墓越豪华、骨灰盒越贵、 陪葬品越多越好, 死亡呈现物质化趋势。 死亡物质化只会增长人的死亡恐惧心理, 而对“关系”死亡论的认识可以改变这种状况。
“关系”死亡论认为死亡是一切现实社会关系的终止。 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利益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等等,这在一定意义上告诉我们,“人”不是简单的经济利益关系的总和。 经济利益关系当然是一切关系的基础性关系, 但还有更多的其它关系需要人们去认识。 简单地把“人”等同与经济利益关系的总和的危害性是很大的。 把“人”的内涵简化为物质利益性,而物质利益是外在的、附加性的,这样就会使人丧失掉“人”的内在应该具有的精神性特征。 更主要的是,物质利益是外在的,它可以随时被毁灭,不能永久被拥有,一旦人面对死亡,物质利益的丧失会使人产生“万事空”的恐惧心理。 “关系”死亡论把“人”看作是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不但包括外在的经济利益关系, 还包括内在的精神、 思想方面的关系, 这样就还原出一个真实存在的现实中的 “人”。“关系”死亡论超出“物质现实”来看待死亡,物质利益虽然是人存在必须具有的基础, 但获取物质利益不是唯一选择,存在着的“人”还有很多关系需要去建构和处理,这才是社会中“人”的真实存在目的。跳出死亡物质化认识,认识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帮助人们减少对死亡的恐惧心理。
从“关系”角度来解释死亡,死亡可以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断裂和终止。 比如,人在死后,不可能再继续拥有财产、 利益等, 经济关系随着人的死亡而终结。政治关系也是一样。这样会不会导致人们面对死亡而感到恐惧呢?其实应该看到,在社会关系里有种重要“关系”在现实社会世界里断裂了,但在意义世界里是可以永远延续下去的, 它不会随着人的死亡而终止, 这就是伦理关系, 也就是位格序列的关系(祖辈、长幼等关系)。例如一个家庭里虽然父母离开了现实世界, 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的社会关系可能中断了,但他们和子孙的伦理关系(位格序列关系)是不会消失的。伦理关系具有不可终止性,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人是永远无法选择他出生的家庭,也无法脱离这种家庭伦理关系的。在现实社会中我们一直都在进行着祭祀活动, 祭拜先人就是这个意义。 “关系”死亡论可以使民众认识到虽然经济利益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随着死亡而消失,但有种更重要的关系——伦理关系还会继续存在, 这种关系不会因为自己的死亡而消失。 民众在现实中积极扮演好自己作为父母、 子孙的角色,“安伦守份”,是可以传承自己的精神的。 这样,面对死亡,民众可以坦然接受死亡,超越对死亡的恐惧。
其次,“关系” 死亡论可以消释死亡个己化带来的死亡恐惧。 死亡个己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下的结果,由于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求,现实社会人们生存在一个讲究个己独立的世界里,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情况下变成了纯粹的物质利益关系, 亲情友情越来越淡化,死亡变成了由个己一人承担,成为个体一无所依的事件,死亡恐惧由此更加强烈。
马克思“关系”死亡论对化解现实死亡个己化有着重要作用,“关系”死亡论恰巧强调“人”不是一个个别的存在,“人”是复杂社会关系包围下的人,个人和社会其他人都会发生联系, 人与人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独立与社会关系之外的“人”是不存在的。 作为一个现实人,他(她)可能是作为一个父亲、母亲存在,也可能是作为一个儿子、女儿存在,也可能是作为他人的一个朋友、一个学生、一个知己等等身份存在,这样每个人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对于一个人的死亡,“关系” 死亡论不是把死亡看作单个个体的死亡,他的死亡也是和其他人具有联系的,按照上面的分析,他(她)是作为一个家庭成员逝去,个体死亡就会是家庭、家族事件,他(她)最为一个朋友、知己逝去,其他人身边就会失去一个可以倾听的对象。这样当个体逝去时,“关系”死亡论认为个体的死亡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群体需要处理的事件。 其实在现实中也是这样, 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在现在的中国农村,当个体死亡时,往往还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重大甚至是头等需要处理的大事, 很多人都会围绕着即将逝去的人,照护着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只不过现代社会,人们意识由于受到市场经济冲击,把生死大事看的比以前有所淡化。 所以“关系”死亡论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自己是处在各种关系之中的,自己的死亡不是完全由个己来承担,家庭、家族、社会亲朋好友都会关心着他,为他分担自身生活、家庭经济以及面临死亡的各种痛苦等, 这样个己的死亡成为众多人关心的事件, 个己就会感到自己没有被抛弃,不会因为孤单无助而惧怕必将到来的死亡。
再者,“关系” 死亡论可以消释死亡单面化带来的死亡恐惧。 现代社会中的现代人忙于物质利益的获取,无暇也不愿意去深入思考现存世界的一切。对于死亡亦然,人们已经习惯于简简单单来认识死亡,认为死亡就是毁灭,因而死亡没有积极意义,对死亡的认识呈现出单面化特点。 单面化的认识造成对死亡不能深入理解,忽视了死亡的价值意义,往往会产生恐惧死亡的心理。
“关系”死亡论对消释死亡单面化带来的死亡恐惧可以起到作用。 马克思死亡论是辨证的、 实践的“关系”死亡论,在对死亡的认识上,它不是简单认为死亡只是具有消极意义, 死亡在毁灭现实尤其对个体,毁灭个体的肉体这点来说可能是消极的,但辨证来看, 死亡其实蕴含着丰富积极价值, 可以这样理解,从“关系”角度认识,死亡对于个体和社会来说都有着积极的价值。对于个体来说,完整生命包括生死两部分,死亡是整个生命的组成部分,甚至代表整个生命的意义,“死亡是不朽的本原”,“生就意味着死”。 虽然它是生命中瞬间发生的事情,但它是生命中最终极事件,它会影响着人的一生全过程。没有悬挂在每个人头顶上的死亡,没有死亡在追赶着我们,我们就不会去珍惜现在的生,不会去领悟生的真谛,所以死亡是促使人成长和生活好的推动力。 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如果没有死亡,人类的生存状况也是不可以想象的, 社会的平衡发展必须要有死亡才能维持下去, 死亡也是人类繁衍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和特殊推动器。
可见,马克思“关系”死亡论是从辨证角度出发揭示了死亡价值,它要求我们跨出现实世界,深入意义世界去思考死亡价值,参透生死的深刻内涵。 “关系”死亡论不是把死亡理解为虚无的灵魂的死亡,也不是把死亡理解为肉体的消亡, 而是在更高层面上将其理解为一种积极价值意义。 这是立足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哲学概括, 对死亡本质的认识最具有阐释力。 而在现实实践中,一旦人具有了这种认识观念,就会把个己死亡与他人、 社会联系起来, 把个己放大,改变死亡单面化认识。 面对死亡时,个己能够认识到死亡的这种积极价值,就不再会恐惧死亡。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就指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毛, 为人民利益而死, 就比泰山还重。”马克思也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 ”[15](P7)这些叙述揭示的都是:当个己认识到死亡是与他人、社会相联系而具有丰富的价值意义时,就不会惧怕个己的死亡。
注:
①郑晓江、康琼等学者把这种表征总结为“个我化”,本文参考之并认为“个己化”更为恰当。
[1] 康琼.人的生命价值与死亡的超越[J].江汉论坛,2009,(12):61.
[2] 陈蕃,李伟长.临终关怀与安乐死曙光[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189.
[3] 段德智.西方死亡哲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3.
[4] 笛卡尔.哲学原理[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5]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8-39.
[6]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 康德.实用人类学[M].邓晓芒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36-137.
[8]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孙周兴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92.
[9]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0] 周德新.论死亡本质及其社会性[J].社会科学辑刊,2010,(3):72.
[11]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80.
[12] 云格尔.死论[M].林克翻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14.
[1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71.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