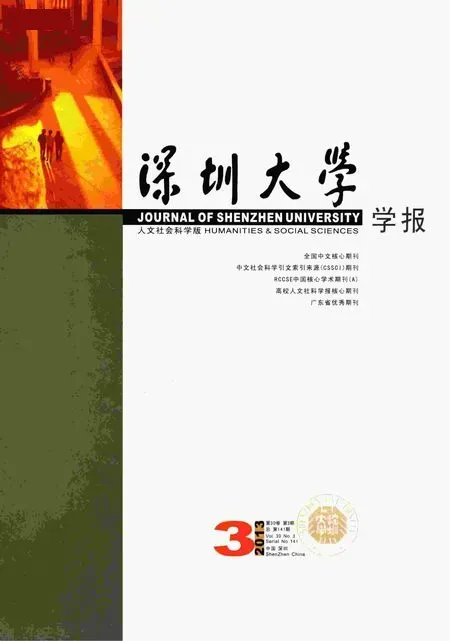关于“无”的真理:比较视域中的中西修辞美学观念论析
2013-04-07谭善明
谭善明
(聊城大学文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尼采、海德格尔、巴特等众多西方思想家对东方文化兴趣颇浓, 同时他们也无限向往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古希腊文明,那是一个修辞学兴盛的时代。我们不禁要问,20 世纪西方思想家、 东方文化和古希腊及其修辞学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深入分析20 世纪西方修辞美学观念,发现其对生命审美状态的颂扬和对虚假观念的批判, 激发了一种别样的对“无”的肯定和对“真”的追求,正是在这一点上中西文化产生了共鸣。
一、20 世纪西方修辞美学观念:在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中走向“无”
对西方20 世纪修辞观念的梳理,我们选择了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这条线索, 这一线索在尼采等人的思想中都比较清晰, 意识形态问题涉及到他们的哲学立场,即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而与审美问题相联系的则是对新的生存境域的开启。 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讲,是用“无”替代大写的“有”,从审美角度讲则是用“有”充实生命。 审美是人感性层面上的一种情感活动, 审美在修辞中主要表现为在话语中进行的形式创造, 审美冲动使得话语始终保持新鲜活力,并不断推陈出新,它保障了话语的生成。 关于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那是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 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各种虚假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不仅存在于政治话语中,更是广泛存在于经济、社会、文化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是广义上的,它不仅仅指那种和上层建筑相联系的社会意识,更关键的是强调某种固化的虚假观念, 意识形态既有欺骗他人的成分,也有自我欺骗的成分,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其虚假性就获得了合理化的面目,并且在话语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修辞,作为一种话语活动,处在审美过程和意识形态过程的变奏之中。在审美过程中修辞满怀信心地编织语言的花环, 为某种意见进行充满形象的、饱含激情的“强论证”,而当这一论证得以完成,意见也被人们广为认同之后,修辞就从审美滑向了意识形态。任何关于真理的话语、道德的话语、宗教的话语,无不是以审美的方式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但由于二者的矛盾关系,修辞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帮凶,也是意识形态的破坏者,从审美走向意识形态是修辞活动的一半, 从意识形态重返审美也是任何话语不可逃避的命运。最终结果是,修辞美学通向了“无”,这样一种观念从尼采伊始,经巴特、福柯、德里达、德曼等人的发扬,促成了20 世纪文论的现代性转型。
尼采早期便从古典修辞学中获取了有价值的思想,并尝试确立一种“修辞认识论”,这成为他后来重估一切价值的重要依据, 即坚持一切语言和思想观念的修辞特性,从而将人类创造的真理、宗教和道德视为生成游戏的一部分。他指出,真理的形成乃是审美化的过程,它是“一群活动的隐喻、转喻和拟人法,也就是一大堆已经被诗意地和修辞地强化、 转移和修饰的人类关系”固化的结果[1]。 在这一基础上,尼采强调生成的游戏是生命的真实境况, 无论是他早期对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描述, 还是后来从权力意志角度对人类生存的重新阐释, 都突出强调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追求抽象的概念和理性, 而就在当下人与世界的遭遇中,人通过“解释的游戏”为世界进行修辞赋形并确立自己的存在。 这就是人之于世界的“形式创新”,作为修辞学家的尼采在其中发现了人的有限性和真理的有限性, 即作为艺术家的人要直面被自己称为真理的谎言——“艺术比真理更宝贵”[2],这就意味着人只能在话语修辞中既不断地以审美的方式创生真理, 又要不断地以审美的方式毁灭它,这种永恒轮回使创新走向彻底的虚无。这就是尼采关于生成的修辞游戏。 它强调生命应以强者的姿态面对、经历这种虚无。
相对于尼采对世界“永恒轮回”的揭示,巴特更关注在此岸生活中如何超越意识形态的围困。 在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中, 巴特指出意识形态已经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名字叫“军团”,这里的意识形态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而是已经成为“语言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语言结构(la langue)。 ”[3]他在早期社会神话研究阶段, 就开始剖析作为修辞的社会神话是如何进入符号学系统, 并如何以审美的方式行使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的, 而后来则更是关注如何破解修辞之谜并揭露意识形态话语的虚构性, 这就是首先将一切视为修辞编织的符号或文本, 然后以一种审美冲动破坏意识形态之网,即采用漂移、偏离的途径拆解整体性, 于破碎、 断裂之处寻觅文之“醉”。 为了避免修辞的审美过程被意识形态过程所取代, 巴特认为最好的办法并不是用审美置换意识形态,而是要在文本和符号中保持两条边线:一条是意识形态状态, 另一条则是审美状态,“恰是它们两者间的缝隙,断层,裂处,方引起性欲。 ”[4]巴特清醒地看到,我们无法脱离意识形态而过活,但他尝试通过审美与意识形态的不断交替回到生成之源即事物本身,这就是从修辞走向空无。
福柯则是通过将历史、真理和主体转化为“无”而使个体重新找到生存的快乐。在他看来,历史和真理一样都是话语修辞的产物, 他的考古学就是将历史从理性轨迹上拯救下来并使之成为话语的碎片,这就是词与物的断裂、知识与实践的不相吻合,一切合理性因此化为虚无。然后他从话语、陈述和策略的角度来对历史重新进行测量, 从而揭示真理诞生的秘密, 他的谱系学就是考察话语如何以审美的方式获得一种稳定的秩序,进而以真理的面目展示出来。对此他指出,“在任何社会里,话语一旦产生,就立刻受到控制、筛选、组织和重新分配”[5],意识形态的每一次变动无非就是话语审美形式合理性的重新论证。福柯将这一过程看作是话语权力运作的过程。主体在话语中被赋予特定功能从而倒空了真正的主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功能主体或修辞建构的主体。如何回返人的真正存在? 福柯认为必须打破主体的修辞幻象,将自我从历史和道德的负担中拯救出来,以自身体验为中心, 唤醒作为身体感觉性的个体存在。如此,福柯在感性生存的层面上试图将人从意识形态的围困中拯救出来。 这也正是福柯本人所身体力行的:“享受自我,与自己享乐,在自己身上找到全部快乐。 ”[6]
解构思想与“无”也是直接相关的。 德里达用差异取代同一,用替补置换中心,从而认为本原即是空无。 他认为修辞性和诗性是任何话语包括形而上学话语的基本属性, 真理和本质只不过是一套修辞话语。这样修辞学便毁坏并重新规划了哲学。本原的缺失使哲学文本和文学文本同样是一种修辞, 理性的秩序无非就是非逻辑、 非科学的修辞性表述,“文学结果成了哲学以及它所向往的真理模式的主题”[7],而修辞性则是一切文本的真正“本质”。 德曼等人延续了尼采和德里达的修辞思想, 关注文本的内部研究,进而确立“原生性的修辞”。强调修辞的原生性意味着文本被看成是混杂而多元的, 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其中充满着重复和误读等差异性的运动,即自我解构的游戏。正是由于差异性运动,文本的生命力才得以生生不息,文本才获得其“存在之真”。原生性的修辞既是对审美也是对意识形态的超越, 使文本回返到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原初混沌状态。只有在这里,任何意识形态的风险才能被真正化解, 这也是解构思想的真正旨归。
这样一种思考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修辞观念在20 世纪思想中的价值。 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修辞使话语始终保持着一种审美冲动, 在解构与建构循环的游戏中,任何既“有”的观念被破除,在“无”的突然降临中,世界真正向我们敞开。 将20 世纪这种修辞美学观念与中国古代“无”的思想和柏拉图的真理观相联系,则更是提供了一条澄明之径。
二、中西文化传统:修辞之“变”和“无”与真理追求
在中西文化传统中有着同审美与意识形态变奏可比较的思想倾向,那就是强调语言和修辞之“变”以超越人的有限性,并朝向最原初的真理。
《周易·文言传》有言:“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修辞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活动,从不与某种指向性相分离。表面上看,这种指向性被描述为试图脱离时间之流的意识形态, 其实在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过程中,修辞指向性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在这段话中,“诚” 是强调言辞修饰活动要与某种心意状况相符,这也是话语生成的驱动力所在。正是由于这种驱动力,“过程”才具有了特定的审美意味,“辞”才会成为“美辞”。 但是,为了通达“诚”,“辞”必须是顺应情境而常“修”的,否则就会成为空洞之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有化为意识形态的风险。 所以这段文字的最后指出“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这里所说的忠、诚、信、几、义都是“因其时”而呈现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样才会“无咎”。 这启示我们:对修辞的阐发要居于“变”,而非“不变”。前者是强调动态的话语生成过程,后者则停留于静态的话语形象。我们同样可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庄子的“得意忘言”:“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为什么庄子将“言”看成是和荃、蹄一样的工具,而在目的达成之后工具也就在人的视野中消失了? 无论将之解释成对言的有意忽视还是说出于不信任, 都无法解除人们的疑惑,因为紧接着的一句话是“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这不是矛盾吗? 在理解这段话时我们有必要区分这两个“言”。 作为名词的“言”是指语言的常规意义,是常人用以交流的工具,其中沉淀的乃是各种“意见”,我们可以借“言”达“意”,但因言的局限性,无法通过它体“道”,所以庄子说:“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 ”(《庄子·则阳》)作为动词的“言”乃是“真言”,只有忘却了那种他者之言,才可以真正言说,才能通达意和物本身,言是真言,人也就成了真人。 不过,“忘言”并非易事,正是由于言容易固化,庄子是对其持批判态度的,“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至人,天而不人”(《庄子·列御寇》), 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必须得禁言?那么《庄子》洋洋之文岂非自相矛盾?所以庄子必然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即如何言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 ”(《庄子·寓言》)无论是自编故事,还是对他人之言的利用和改造,最根本之处在于使言“不囿”(亦即破除意识形态性),使言在人的生存境域中“物化”、“随成”,这就是“巵言”——无心而自然流露出来的言,也就是无“成见”之言,摆脱了“意识形态”风险之言。
当我们转向古希腊,似乎会发现另一种情况,这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柏拉图对修辞学的厌恶和批判。 他多次强调修辞学的价值在于其对真、善、美的追求,工具性、外在性、装饰性是修辞学鲜明的特征。在他看来, 一个演说家如果一味地以优美的言辞来迷惑观众,而不进行事实判断,不以真理为指引,“只在人们的意见上捕风捉影, 他所做出来的文章就显得可笑,而且不成艺术了。 ”[8](P141)相反,柏拉图规划了一种高尚的修辞学,它在真理的指引下,洞察灵魂的本性,用言辞增进美德。 柏拉图看到,在坏修辞学中话语与事实、真理之间是断裂的,正如前面所说的,修辞所使用的优美言辞中充满了固化的观念,后来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也指出“修辞式三段论的前提很少是有必然性的”[9],其中包含的不过是经过强论证的“意见”。 这表明修辞学的话语生成虽然立足于当下情境的判断, 但它仍是使用他者的话语来进行劝诱和说服,这样,事物便不再成其为本身,而是披上了一件华美的外衣, 本性被遮掩起来——这正是人们对修辞学所诟病之处。 柏拉图强调在高尚的修辞学中有着真理的追求, 就是要纠正修辞学的这种偏离。 他在《斐德罗篇》中引用的埃及传说也是要表明这一问题。在这个传说中,塞乌斯发明文字以改善人的记忆力, 而国王则认为文字在人的灵魂中播下遗忘,“他们就信任书文, 只凭外在的符号再认,并非凭内在的脑力回忆”[8](P159),文字提供的并不是真正的智慧,显示的只能是事物的影子。 所以,语言、文字作为工具都有一种坏的倾向,那就是以他者和外物的身份建构起人与世界的疏远关系。 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在庄子那里我们看到是要通过 “忘言”而体道、进入自由之境,而在柏拉图这里则是强调言对“真理”的追求而化解言意关系的危机。 但我们不能因为尼采的大肆批判而将这里的真理等同为前文所说的“意识形态”。在真理问题上,柏拉图是很清醒的,他在《理想国》用一个线的比喻将认识能力分为四个阶段:理性、理智、信念和想象[10],前两个把握可知世界,后两个涉及可见世界。柏拉图所说的真理(理式)只有理性能通达,而由于肉体的限制,人的灵魂是无法见到真理的, 他最多只在理智的层次上不断地向往真理, 就像人的眼睛无法直视太阳 (在《圣经》中人也无法见到上帝)。这就设定了人的有限性:只有向往真理才能拯救灵魂,但肉身性的人终究见不到真理。 人通过自己的智慧创造的世界就只能是对真理的偏离, 语言文字则使这一偏离以可见的形式固定下来, 人在任何时候宣称自己发现真理的时候都是陷入了疯狂, 他其实是高估了自己理解世界的能力,是对最高真理(理式)的背弃,从而在人的理智中只存在“意识形态”而没有真理。所以,人一方面要不断追求真理, 另一方面要时刻牢记自己的有限性,只有这样灵魂才能最终得以提升。这正是苏格拉底在德尔菲神谕中所领会到的:认识你自己。人要求知,首先就要确认自己的无知,真理引导着灵魂的不断提升——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相对性的 “知”,但真理最终又是人永远无法见到的——这注定人只能“无知”。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柏拉图对修辞学的态度了, 因为单纯通过语言文字所获得的只能是相对性的“知”,人如果以此种方式进入世界只能见到假象和幻影,况且他认为修辞学是有意制造偏离,而真理的追求则赋予人类知识的有限性, 促使人们不断求知,修辞学若成为有益的也必须以真理为导向,而不停留在对虚假观念的论证上。
如果我们将中西这两种关于语言的思想对读,可以发现求“变”是其中共同的倾向,只有“变”才可以使人朝向“真”(道或理式),而固化的语言作为“符号”遮蔽了通向真理的道路。 差别似乎在于,在庄子那里“忘言”是“言”的前提,而在柏拉图看来不断地求知是朝圣真理的前提,一个是“忘”,一个是“追”,这构成了中西文化的重大差异。 但如果我们在这一解读中将“忘”看成是消极避世的,而将“追”看成是积极进取的,那真是中了“意识形态”的诡计了。与此相应的另一误解是,一个强调“无”,一个是强调“有”(存在)。二者其实是一致的,因为只有在遗忘中才能摆脱自身有限性从而不断地追求真理, 只有不断地向新的境域敞开已然之物才能被抛弃。 只是从时间性的角度来看, 庄子强调对 “有” 的瞬间抹除而归“真”,柏拉图则是指出了通向“真”的辩证过程,即不断地使有限性的“有”成为无从而朝向无限的“有”(理式),庄子那里的“无”是和这无限的“有”根本一致的,它们都通向“真”。 在他们看来,语言既是一种工具,又是一种障碍,它一方面促成了哲学之思,同时又使人沉沦于庸常之见,如若不从“无”或“真”的高度对语言进行批判,恐怕人将永远沉沦下去。而修辞作为对语言有意识的组织和运用, 是在语言中已有成见的基础上再次堆叠“意见”,必须设定修辞的有限性以防止人与世界的疏远。 这正是《周易》中所指出的在“变”中“修辞立其诚”,也是柏拉图所强调的在不断求知(这也是不断抛弃成见即变的过程)中朝向真理。
三、修辞对生存境域的开启:关于无的真理
通常在论及20 世纪人类思想状况的时候,人们都会强调传统形而上学观念的终结, 真理不再成为人们的崇高追求,各种“后”学兴起,似乎人类已经抛弃了沉重的传统思想包袱, 兴致昂然地建构一个新世界,但同时又在各种危机面前茫然无措,慨叹人心不古。人类思想将何去何从,这是思想家们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 通过从审美和意识形态变奏的角度深入分析20 世纪的修辞观念并结合中西文化传统,我们发现情况没有想象的那样糟糕:第一,真理追求并未淡出理论视野;第二,一条澄明之径在向我们敞开。
先看第一个方面。我们有必要追问,尼采等人批判的真理是什么? 那是以审美的方式编织出来的意识形态话语, 是柏拉图指出的人类认识能力四阶段中的“信念”或“想象”。它最多只能是“理智”,而不是真正的真理。在真理问题上人们小看了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以为自己都是从洞里逃出来的人,在自由的世界中向往光明。 其实人类在历史中越来越自高自大,从而忘记了自己的有限性,为一点点的发明或发现得意忘形,并将众多自己建构的观念奉为真理。这表明,人类还是长久被锁链束缚着,更有甚者,人类是在不断地给自己制造锁链, 用各种偏见和谎言禁锢头脑和心灵。 尼采以来的思想家们批判的就是那些虚妄的、貌似真理的观念,但他们又注意到人类生存的巨大困境, 即人类总是以审美的方式破除意识形态的牢笼,然后又在意识形态中沉睡,人与世界的关系在修辞中一次次地重新确立。 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规划的追求真理之途依然有效,人们在无知中编织谎言,在对谎言的认定中打开那扇通向真理之门——无论是苏格拉底、 柏拉图还是尼采、巴特、福柯、德里达、德曼,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告知人们必须砸碎锁链获得自由: 或要承认自己的无知,或要人们正视世界的生成和流动,或要让艺术和生命本身取代意识形态。不同的是,前者更强调否定,20 世纪的思想家更重视肯定。 总之,他们都是要揭示并认同人的有限性, 为真理的绽放奠定同样的基础。但是,我们不要期望以此种方式人类最终就能把握真理。 真理追求无非是防止人类的堕落和沉沦,它本身并不具有拯救意义。 那么,生成的游戏又要将我们带向何处, 我们究竟该如何摆脱生存的困境?
当尼采说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的时候, 其实是展示了他自己的真理观, 那就是在权力意志的驱动下将谎言视为谎言, 认定人生的虚无并毫不畏惧地经历它, 并将过去的记忆和未来的期盼融入到当下生命的情境中。 尼采视艺术为最高的真理, 即是用“谎言的谎言”置换了柏拉图“高贵的谎言”,这是对世界和生命的清醒认识,也划定了知识的有限性。自康德以来,知识的有限性就被一再强调,如张世英所说,西方思想家认识到,“以为靠真理、靠科学知识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把握人生,可以穷究万物之本性,一句话,以为科学能指导人生,那是愚蠢。 ”[11](P318)这是人们对柏拉图有关真理的教导遗忘的结果, 而尼采等人通过对现象界真理的批判再次将无限和有限的问题显明:人的有限性生存必须面向无限性,否则就会陷入自设的圈套, 即用修辞话语织就的意识形态。 审美和意识形态的变奏正是通过不断打破人的有限性,而进入永恒轮回的游戏。 但问题仍然在于,如果就此将这一无限性等同于柏拉图的最高真理,还是无法摆脱生存的困境,所以尼采呼唤超人。那么常人呢?难道只能在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中堕入虚无?
正是这一关于“无”的真理给了我们启示。 20 世纪西方修辞审美理论对“无”的呼唤是耐人寻味的。我们可以将之视为现代性危机的产物, 但决不可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人类的绝望。 我们要看到“无”的深刻性:一方面,尼采在《权力意志》等文稿中倡导“彻底的虚无主义”以开展价值重估的工作,巴特在《符号帝国》、《文之悦》等著作中强调“空无”以对抗意识形态,德里达、德曼、米勒等人则以解构的方式开启了文本之“无”,这恰恰是为了通达事物本身;另一方面,无论是尼采的“上帝之死”,还是巴特的“作者之死”,抑或福柯的“人之死”,都是通过对大写的“有”之拷问,进而探寻生存的真相。 这种“无”不是空虚的,而是充盈的,因而也就是“无限”,这正是关于“无”的真理。同样是对无限性的强调,柏拉图是看到了“有”(理式),尼采等人却走向了“无”。当“真”被转换成“无”,生命的价值就得以重新衡量,由对身体的否定转向了对生命意志的肯定。自柏拉图以来,对无限真理的向往是在否定的辩证法中进行的, 其结果是一方面让生命在朝向真理的道路上得以绽放,另一方面这又容易导致对生命本身的忽视。 而当真变为无,彼岸世界就不再是令人向往的,此岸世界的意义才真正能得以显现。无的意义是非同一般的,正如海德格尔“向死而生”一语所昭示的,在死亡和虚无面前人重获新生,因为无使得一切“外物”失去价值,正是在对无的注视中, 包裹事物的所有意识形态话语瞬间瓦解,事物作为它自身而显现出来,生命也从精神性存在转化为肉身性存在, 从而使真理在其中自行绽放。所以我们在解读20 世纪修辞观念的过程中发现, 和审美与意识形态变奏同时发生的, 是将“真理”转换为“无”,再将宇宙论的“无”转换为存在论的生命之充盈;修辞以对“有”的解构揭示话语中心的“无”,再从中心的“无”回返到对当下偶然性的陶醉。“无”使生命摆脱外物的羁绊,无限肯定自己正在面对的“有”,并将这“有”视为“所有”。
这种对生命的理解我们会觉得似曾相识。 在中国思想史上,道家也是强调生命的自由状态,排斥对象化、固定化的观念。 庄子要消除一切有无是非的终极局面,如《齐物论》中所言:“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 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 ”只有“不由”才能依天乘时而“游”,才能使生命本身的境域敞开。 如前文所述,庄子强调那种“无心之言”,就是没有停滞于对象和主体的概念化、 固定化之言, 即化于语境之言、“巵言”,“庄子视那依语境本身而说话的语言活动为道言或大言, 与只知去判断是非的小言迥然不同”[12],“大言” 因此揭示了一个澄明的人生境域,这是对生存的当下性和非现成性的强调。 “游”的终极状态就是“道”与“我”的统一,而并不是要走向一个超越性的主宰。 这样,以“无”化解一切可依可凭的“有”,使生命得以释放,最终绽出的“有”就成了“所有”。 禅宗强调非语言、非逻辑、非概念的顿悟,也是对固化观念的阻断,并由此让生命在直觉中完全与世界融合为一体,这也是在“无”中点亮生命、走向真我。所以,在禅宗那里,无表面上看是否定性的,其实乃是“肯定性的”,“它不是空无,而是作为存在和非存在的根源的圆满……它表明决不可被对象化的真我、真正的主体性,就是您的存在、您的生活、您在社会和历史中活动的根本。 ”[13]无不是要消极地否定现实生活,否定人的生命本身,而是对人的无限肯定,是在搁置一切现成物后人生的圆满。 微尘中可见大千,刹那间便是终古,“无”的无限肯定造就了当下体验中个体生命之真与宇宙之真的交汇。于是,一便是一切,一切便是一。
在“无”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中西思想发生了碰撞。二者都有相同的趋向,通过“无”摒弃或化解包围着人与世界的既成之见(亦即修辞话语),使人走向自由境界,在生存的具体境域中体验到“有”和“真”。而且, 这是更多地具有审美意味的自由, 是超功利的、无外在目的的、以人和事物本身为观照对象的。但是,中西由“无”所引发的哲学思考还是有着重大差异的。西方思想是以主客二分为主导,中国则是天人合一。前者引领人们对世界进行不尽的探索,后者则强调人与世界不分你我的浑然一体; 一个是对象化,一个是非对象化。“无”便是对主客对立模式的消解,使人与世界的关系走入类似天人合一的境况。建立在主客二分和天人合一基础上的“无”各有利弊,如有学者指出,“自由如不超出必然性的认识, 则自由仍有限度,不是最高层次的自由;但自由如不经过必然性的认识,则自由的意义玄虚。”[11](P101)在中国思想史上我们的确能看到, 未经分化和批判的无的思想既产生了天人合一的生存方式, 也因过于空疏而对人的精神起着消极影响。
所以必须清醒地看到, 不加反思地认同中国哲学中的“无”是危险的。西方20 世纪思想中对无的理解包含而又超越了主客二分的模式, 是以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朝向无(酒神冲动、偏离、解构),也就是在审美和意识形态的变奏中不断进行修辞建构-解构的游戏,以宇宙论的“无”肯定生存论的“有”,从而召唤着高超的、自由的、诗意的人生。 当西方思想在20 世纪反思主客对立模式所带来的困境时,它走向了东方思想中的天人合一; 而身处21 世纪的中国,当我们思索自己文化的现状和未来时, 在自豪与失望之余,是否也要考虑借鉴西方思维模式。
基于这样一种思考,20 世纪西方修辞美学观念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是: 既不是以主客对立模式造成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 也不是在毫无批判和反思中走向天人合一, 而是要在具有酒神精神的审美冲动中不断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其要义在于,第一是解决天人是“怎么”合一的,第二是主客对立要走向何方。天人合一是一种高层次的追求,如果二者都不是“真”,那这种合就有随遇而安的味道,所以在合之前必须先去“伪”,就是要充分认识到人的有限性,把面前的一切认之为解释、符号、文本,即关于世界的话语修辞,既看到它们的合理性,也要意识到它们的虚构性和短暂性, 在经历了建构-解构的生成游戏之后, 再搁置话语修辞的牵绊而走向天人合一也就是去伪存真了。第二点,主客对立模式追求一种超越于人的客观真理。 这最终导致了西方思想的现代性危机。但它有益于破除人的主观固化观念,如果将它的“目的因”从客观真理转向存在论的主观真理,从彼岸转向此岸,那么这种对立也就具有内在价值了,认识活动也就通向审美活动了。 审美与意识形态变奏的修辞游戏, 是在破坏与重建中使世界保持生成和澄明状态。天人合一具体化于“过程”中,认定人生的修辞性和戏剧性,陶醉于其中,而又不被任何形式所局限。 所以这样说来,不是要“走向”天人合一,而是要不断“创造”和“经历”天人合一。
总之, 修辞中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是对无的开启,是对真的呼唤,是对生命本身的无限肯定,其中既有西方思想的精髓,也有东方文化的闪光之处。在全球化语境中思考这一命题是颇有价值的。
[1] [德]尼采.哲学与真理[M].田立年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06.
[2] [德]尼采.权力意志[M].张念东,凌素心译.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262.
[3] [法]巴尔特(巴特).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A].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C].北京:三联书店,1988.4.
[4] [法]巴特.文之悦[M].屠友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6.
[5]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216.
[6] [法]福柯.主体解释学[A].杨国政译.福柯集[C].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474.
[7] De Man. Allegories of Reading[M].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115.
[8]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编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9]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M].罗念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27.
[10]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71.
[11] 张世英.天人之际[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51.
[13] [日]阿部正雄.禅与西方思想[M].王雷泉,张汝伦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