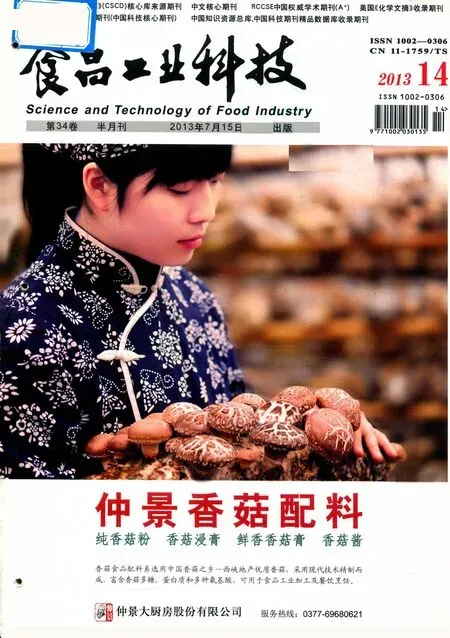食品安全治理的国外研究新进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2013-04-06陈煦江蒋夏霞
陈煦江,蒋夏霞,高 露
(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重庆400067)
食品安全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难题。其原因错综复杂,既有自然力因素,也有人为因素,前者囿于当今人类的科技力量,但后者可通过食品安全治理得以规避。因此,食品安全治理成为当今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农学、食品工程学等领域的学者研究的热点,目前国外学者对食品安全治理研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本文根据近年发表于SCI、SSCI、EI等来源期刊的主要文献,从有关食品安全治理的环境、模式、机制、工具四个维度进行概要综述,并为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提供几点建议。
1 食品安全治理的制度环境研究
大量食品具有经验品和信用品特征,导致食品市场信息严重不对称而产生食品安全问题。为解决食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不少学者开始关注食品安全的制度环境议题。Nesve等[1]运用比较法律框架理论分析了英美食品安全治理框架不同的原因,发现英国主要依靠议会立法治理食品安全,法院执法处于次要地位,这一议会主权制度环境决定了英国采用立法导向的食品安全治理框架;美国宪法遵循“人民主权”原则,其食品安全治理的重心在于切实保护消费者和企业的合法利益,这一宪法至上的制度环境决定美国采用了执法导向的食品安全治理框架。由此表明,处于不同制度环境的国家照搬他国的食品安全治理模式与机制将会导致低效甚至无效。Alin等[2]认为,食品安全是食品供应链中各成员协同努力的结果,是各成员就食品生产、加工、销售等形成的委托代理矛盾,虽然目前流行的运用代理理论研究食品安全的供应链治理十分重要,但由于食品供应链内嵌于广泛复杂的制度环境中,有效的食品安全治理模式与机制应当首先基于其所处的法律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制度环境进行现实性和系统化的构建。
2 食品安全治理模式研究
2.1 共同治理模式
Henson等[3]最早提出共同治理模式,认为通过公私部门协作能够提高食品安全治理的效率。该模式被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采用。Marian等[4]考虑到食品安全公共管理部门存在资源短缺和职能部门间竞争,认为只有实施公私部门紧密合作的共同治理模式,才能降低食品安全治理成本,提高治理绩效。他们比较英美两国实施的共同治理模式后发现两国的行政法规存在显著差异,影响着共同治理模式的不同实施路径,表明在跨国层面推行共同治理模式尚存巨大障碍。Elodie等[5]构建了一个食品安全共同治理概念框架,并以法国进口食品中农药残留量限制规定的执行效果为案例研究发现,在政府保障激励和信息畅通的前提下,共同治理模式逐步实现了从传统的惩罚导向现代的预防导向转变。
2.2 综合治理模式
综合治理模式最早由Kaplan等[6]提出,该模式强调食品安全治理是一项对个人和社区的文化、卫生、心理等进行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一些学者发展了综合治理模式,Loring等[7]强调应当根据地域性特征将公众健康、社会文化、生态环境、消费者心理特征及生物医学技术等结合起来解决食品安全治理问题。目前,美国的一些社区等基层食品治理单位开始采用综合治理模式。Loring等[7]对美国阿拉斯加州的调研发现,综合治理模式成功实施的关键是识别食品安全的综合影响因素和分地域性特征。Marion等[8]在总结12篇经典文献的基础上,认为欧洲应当实施一个广泛集成科学、预防和公众参与的食品安全综合治理模式。Mikael等[9]认为欧洲目前的食品安全治理模式缺乏充分的民主性和有效性,应当建立整合合法性、公共责任和信任的全过程民主综合治理模式,其中,公众以何种方式参与及参与的有效性是保障该模式实施的关键。
2.3 其他治理模式
Ladina等[10]分析了欧盟当今采用的“个人——公共部门——国家——超国家(欧盟)”这一多层级治理模式与欧盟统一市场相矛盾的缺陷,由此,他们提出一种集中化管制代理治理模式,即由欧盟而非成员国集中统一地直接治理欧盟的食品安全问题,并以HACCP的执行效果为案例研究发现该模式在降低欧盟食品产业的不确定性、促进食品安全治理的优化创新、改善消费者信任等方面优于多层级治理模式。Ansell等[11]则认为,欧盟实施的多层级与多主体治理模式是一种争议治理模式,表现在该模式未考虑欧盟成员国在文化参数、法制环境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以及成员国间互信的缺失和治理机构间的利益冲突等;因此,欧盟今后应当以影响消费者信任的文化和制度两大关键变量为核心,采用“文化——制度”治理模式,即以欧洲的不同饮食文化为基础构建食品安全治理制度及模式。Hoffmann等[12]认为,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建立一个全球化的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模式十分必要,但应在充分考虑各国主权和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实施,全球协同治理的关键不仅在于各国政府间的协同治理,更在于国际食品供应链的协同治理。
3 食品安全治理机制研究
为了控制食品安全风险、节省治理成本、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和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目前各国采用了多种手段治理食品安全,但由于国家间的法律制度和人文环境存在差异,使其治理手段各有侧重,形成了以主要手段为核心的多种治理机制。
3.1 消费者治理机制
Todt等[13]以转基因食品为议题,通过调研发现西班牙消费者普遍感知自身的消费权益过度受到食品产业的影响,消费者强烈诉求根据科技知识和自身偏好进行食品消费决策,并要求政府提供快畅的信息、企业贴示转基因标签等方式保障其知情权。然而,Dzifa等[14]基于英国食品生产企业的案例研究发现,大部分企业虽已实施食品安全管理系统以预防食品安全风险,但企业宣称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认证过分地偏向消费者,而未对食品供应链中全部利益相关者所受影响进行充分的评价,由此导致食品产业发生了本可避免的巨额成本。Michiel[15]以禽流感事件为议题对荷兰消费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和探测性研究,发现消费者的偏好存在诸多差异,对食品安全的认知具有实质区别,表明多重消费者理性客观存在,因此,政府实施差异化的食品安全治理机制将优于现行的通用型机制。Cope等[16]基于欧洲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引致消费者信心受挫的现实,提议食品风险治理机制应以透明和负责任的方式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食品安全风险沟通机制的成效受到消费者的风险认知和食品安全信息需求的影响,主要包括消费者的个体偏好、信息需求差异、所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以及信息的可鉴定性、预防性、一致性等因素。因此,今后采用国家或地区范围战略开展食品安全风险沟通比当前采用的泛欧洲战略更有效。Gonzalez[17]认为,在坚持科学性、意识形态差异性和道德伦理观三个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以保障消费者的基本人权、健康与营养安全权益为宗旨的全球化食品安全治理机制才有可能逐步实施。
3.2 媒体与网络治理机制
Dillaway等[18]采取实验方法研究了美国消费者对媒体报道鸡胸食品安全事件的反应,发现媒体报道正面或负面的食品安全信息均显著影响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其中,名牌食品受到的影响更大,消费者对负面事件的记忆具有快速性和长期性。Donal等[19]基于网络治理机制倍受欧盟推崇的情境,以2008年爱尔兰发生的二噁英污染猪肉事件为案例,研究发现当前欧盟的食品安全网络治理机制是失败的,原因在于它未能解决网络治理的灵活性与稳定性、广泛性与效率性、内部合法性与外部合法性三对主要矛盾。其中,前者表现为事发后对事件信息的动态更新不及时和报道口径不一致,中者表现为治理机构未能与广大消费者进行广泛深入的直白式沟通,后者表现为未能充分考虑到爱尔兰消费者和其他欧盟成员国消费者的法律认知、伦理意识、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因此,今后有效实施网络治理的关键是科学地平衡这三对矛盾,并增强信息的透明度。Corrado等[20]采用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的食品安全评价标准对EFSA建立的“公共咨询网”以期实现“直接民主式网络治理机制”的效果进行评价表明,网络治理机制确有一些优势,但因网民的食品安全科技知识不足,限制了网民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实际水平。
3.3 协同治理机制
Knudsen[21]认为,风险治理应当被整合到食品安全治理框架中去,重点是实现框架制定、风险预期、风险评价、风险管理、风险分析五个步骤的整合,并按照科学、透明、公开、参与式管理的原则由各利益相关方进行协同治理。Qin[22]基于中国的食品安全现状,采用博弈模型分析发现食品安全治理绩效的提高依赖于政府、市场与第三方的协同治理。Edward等[23]通过深度访谈发现,中国水产养殖业的食品安全标准存在双边机制:一边是生产符合进口国标准的水产品以占领国外市场;另一边是生产较低安全标准的水产品投向国内市场。他们认为其根本原因不是企业对国内消费者的歧视,而是中国实施的多部门监管模式导致监管部门间的协作机制弱化,所以中国需要创新实施以监管部门间协作为重点的协同治理机制。
3.4 跨国治理机制
Alexia等[24]认为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实施的食品安全跨国治理机制需要进行三方面的拓展和完善:一是CAC标准的制定应当考虑各国的政治体制对跨国合作监管的影响;二是完善国际诉讼制度,保障私人部门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合法权益;三是CAC应当保持自身的公正性与独立性。Vieira[25]对由巴西牛肉出口商和欧盟进口商组成的跨国供应链进行探测性案例研究发现,出口商参与跨国食品供应链治理产生了一种倒逼效应,促使供应链上游的生产商加强技术升级和技术交易,催生了全球食品供应链上不同主体间达成更高程度的互信。Chan等[26]针对香港地区设计了一个由预防、紧急处理、重构再造三阶段构成的食品安全危机预防机制,认为该机制有助于实现地区内外卫生部门与政府的跨界联络及经济与政治议题的平衡,并顾及公众文化、食品安全教育和道德伦理等因素对食品安全治理的影响,从而有利于保障消费者健康,恢复消费者信心。
4 食品安全治理工具研究
4.1 HACCP等食品安全治理工具实施的成本、绩效与限制因素
HACCP是国际上公认度最高的食品安全治理工具之一。Satish[27]对印度食品加工企业采取问卷调研和因子分析发现,食品的质量和销量是激励企业实施HACCP的首要因素,企业实施HACCP的生产准备成本和运行成本主要受所处食品子行业和企业规模的影响,因此,政府提供金融贷款或财政补贴、行业协会开展管理与技术培训、食品企业开展水平或垂直整合是推广HACCP的必要措施。Ksenija等[28]对克罗地亚150家食品企业进行田野调查和问卷调研发现,实施食品安全与质量管理规范(HACCP,ISO22000或ISO9001)后,其中60%的企业的收入并未增长,61%的企业的成本并未降低,统计检验显著地表明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规范的实施与企业的收入和成本无关。Demet等[29]对土耳其28家乳品企业进行实地访谈和问卷调研发现,企业实施HACCP和食品安全计划(FSPS)能够降低法律风险,增加客户信任,但企业管理层对HACCP和FSPS知识的缺乏、高昂的实施成本是障碍二者推广的主要因素。因此,政府应当提供培训、咨询和财税支持。Imca等[30]对日本东京地区13家乳品企业进行深度访谈后发现:实施HACCP的企业的安全食品产出量更大,风险更低;13家企业的食品安全技术行动(包括预防措施、干预过程等)得分均高,但质量监测、质量保证等管理行动得分均低;这种重预防轻监测的原因可能是在日本垂直立法背景下形成了“危害基础”和“立法基础”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有别于欧洲的预防与监测并重的“科学或风险基础”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4.2 企业实施的食品安全标准的影响
一些跨国食品公司采用了比国际标准或部分国家标准更严格的食品安全质量标准,其影响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Steve等[31]的研究表明,欧洲零售商领导肯尼亚生鲜农产品供应商采用更严格的企业标准,赢得了“高质量”的声誉,成为一种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市场竞争工具和回应利益相关者诉求的战略管理工具。然而,Sodano等[32]基于社会学的网络理论和信任理论研究发现,企业的食品安全标准存在诸多缺陷,主要是缺乏透明度与民主性、排斥小微型食品企业于全球供应链之外、认证机制缺乏可靠性和对欠发达国家不公正等问题,可能导致全球食品供应链由关系型向权力型转化,造成全球性的社会福利损失。
4.3 食品安全治理新工具的探索
Luning等[33]设计了一套诊断工具,用于评价食品企业实施食品安全管理系统(FSMS)的绩效,其中企业保障FSMS有效性的能力是诊断FSMS持续改进绩效的首要指标。Marion等[34]提出将社会责任影响评价(SIA)整合到食品安全治理中去,并建议欧盟基于成员国多元化的政治历史背景采取初步框架构建、关系评估、社会影响评价三个阶段逐步实施整合,其中保障公众参与和风险沟通是成功整合的关键。Zhang[35]根据三鹿奶粉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系统的忧虑,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平衡计分卡,根据完整性、可测量性、可行性原则构建了一套由系统成本指数(认证与检验费、监控支出、研发费等)、系统绩效指数(政府满意度、顾客满意度、合格率等)、系统管理内部运行指数(用料出错率、网站评价满意度、公告及时性等)和系统发展指数(培训有效性、管理者学位率、科技创新成果率等)构成的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系统的有效性评价指数体系。White[36]提议在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自2011年推行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的背景下,美国企业需要加强有关危害分析与风险基础预防控制工具的研发和责任保险工具的创新与推广。目前,国际政府组织(IGO)建议各国食品安全管理当局运用适当保护机制(ALOP)和食品安全目标(FSO)作为增强食品安全信息透明度和可量化性的两种治理工具。Gkogka等[37]根据荷兰熟食店生产的肉制品存在含有李斯特氏菌的风险案例,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检验发现ALOP与FSO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对二者在企业实践中的结合运用进行了探索。
5 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经验借鉴与改进建议
5.1 逐步向共同治理模式或综合治理模式转型
2009年实施的《食品安全法》明确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采用“多部门分段监管模式”,2010年我国设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务院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2013年新成立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原过于分散的监管主体进行了部分合并。可见,目前我国尚处于自上而下的以食品安全监管改革为核心的阶段,代表公众利益的消费者协会、食品行业协会、专家团体等非政府力量共同参与治理的作用还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可能会导致监管政策的民主性、科学性与可行性不足。前述文献表明,西方发达国家采用的共同治理模式或综合治理模式均重视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团体等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评价、标准制定、安全监管等各环节、全过程、全方位的参与,而非单一片面的政府监管。因此,建议基于我国的人文环境,借鉴同属大陆法系的欧洲经验,在法规政策的制定和机构设置中充分保障消费者协会、食品行业协会、龙头企业、专家团体、公众团体等非政府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引导他们与政府部门共同参与食品安全形势分析、研究部署和统筹指导食品安全工作、提出食品安全监管的政策措施,以及督促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等决策,促进我国目前以监管为重心的食品治理模式逐步向共同治理模式或综合治理模式转型。
5.2 开展对我国多重消费者理性的调研工作并制定实施配套政策
前述文献显示,国外学者发现由于消费者所处的经济与社会文化环境、个体偏好、信息需求等存在差异,因此对食品质量、食品安全、食品伦理等问题的理解存在诸多甚至重大差异,即消费者对食品具有多重理性。我国幅员辽阔、地域经济与文化差异大、多民族文化共存、饮食文化种类丰富,消费者多重理性客观存在。但是,目前对我国多重消费者理性的研究尚为空白,也无相应的政策措施。因此,建议政府组织力量根据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地区,以及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消费者进行大样本的实地调研工作,摸清我国多重消费者理性的基本大类、主要特征和演化规律等,为我国的食品安全法规与标准制定、风险监测与评估、食品检验等政策制定与完善提供科学可行的依据,以及为恢复当前我国低迷的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提供参考。
5.3 创新实施国家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建设
《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十二五”规划》提出国家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建设框架由一个主系统(国家、省、市、县四级平台)和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相关子系统通过建立横向联系网络构成,主要发布监测检验、监管执法、法规标准、风险预警等方面的信息,发布方式为信息统一公布制度。根据前述文献分析可见,欧美国家运用食品安全网络治理和媒体治理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消费者,目前其网络治理低效的原因是对消费者的信息需求、信息解读能力、信息获取渠道等认知不清。然而,从我国食品安全信息平台的框架、信息内容和发布渠道来看,目前服务的主要目的是国家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并且信息的专业性强且相对零散,公布渠道的便利性与有效性不足。因此,建议在国家食品安全信息平台中整合由食品企业提供的食品安全信息、可追溯信息、诚信信息和消费者及其他组织的反馈信息等相对系统的信息;既要披露原生的专业术语信息,也要提供广大非专业人员能够解读的解释性信息;既要保持现行的“黑名单”制度,还需实施“红榜单”制度,让消费者采用“用脚投票”、“弃暗投明”、“惩黑奖红”等方式对食品安全进行实效性治理;在保障信息的一致性和权威性的前提下,采用政府官网、企业网站、主流网络媒体、食品类主流大众报刊等进行多渠道传播信息。
[1]Nesve A,Turan Brewster,Peter D Goldsmith.Legal systems,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nd food safety[J].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7(36):23-28.
[2]Ng Esmond Alin,Victoria.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the Examination of Food Safety[J].International Food and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Review,2012,15(2):21-45.
[3]Henson S,Hooker N H.Private sector management of food safety:public regulation and the role of private controls[J].International Food and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Review,2001,4(1),7-17.
[4]Garcia Martinez Marian,Fearne Andrew,Caswell Julie A,et al.Co-regulation as a Possible Model for Food Safety Governance:Opportunities for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J].Food Policy,2007,32(3):299-314.
[5]Rouviere Elodie,Caswell Julie A.From Punishment to prevention:a French case stud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coregulation in enforcing food safety[J].Food Policy,2012,37(3):246-254.
[6]Kaplan G A,Everson S A,Lynch J W.The contribution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tribution of disease:a multilevel approach[M].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00:25-30.
[7]Philip A Loring,S C Gerlach.Food,culture,and human health in Alaska:An integrative health approach to food security[J].Environmental Science&Policy,2009(12):466-478.
[8]Dreyer Marion,Renn Ortwin,et al.Food safety governance:integrating science,precaution and public involvement[J].Risk,Governance and Society Series,2009(15):25-37.
[9]Klintman Mikael,Kronsell,Annica.Challenges to legitimacy in food safety governance?the case of the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EFSA)[J].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2010,32(3):309-327.
[10]Caduff Ladina,Bernauer Thomas.Managing risk and regulation in european food safety governance[J].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2006,23(1):153-168.
[11]Christopher Ansell,David Vogel.What’s the beef?the contested governance of european food safety[M].Cambridge,MA:MIT Press,2006:400.
[12]Sandra Hoffmann,William Harde.Food safety and risk governance in globalized markets[J].Health Matrix,2010,20(5):5-54.
[13]Oliver Todt.Consumer attitudes and the governance of food safety[J].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009,18(1):103-114.
[14]Mensah Lena Dzifa,Julien Denyse.Implementation of foo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 in the UK[J].Food Control,2011,22(8):1216-1225.
[15]Michiel P M,M de Krom.Understanding consumer rationalities:consumerinvolvementin european food safety governance of avian influenza[J].Sociologia Ruralis,2009,49(1):1-19.
[16]Cope S,L J Frewer,J Houthton,et al.Consumer perceptions of best practice in food risk communication and management:implications for risk analysis policy[J].Food Policy,2010,35(4):349-357.
[17]Humberto Gonzalez.Debates on food security and agrofood world governanc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0(45):1345-1352.
[18]Robin Dillaway,Kent D Messer,John C Bernard,et al.Do consumer responses to media food safety information last?[J].Applied Economic Perspectives and Policy,2011,33(3):363-383.
[19]Casey Donal K,Lawless James S.The parable of the poisoned pork:network governanceand the2008 irish pork dioxin contamination[J].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September,2011,5(3):333-349.
[20]Finardi Corrado,Pellegrini Giuseppe,Rowe Gene.Food safety issues:from enlightened elitism towards deliberative democracy?an overview of EFSA’s‘public consultation’instrument[J].Food Policy,2012,37(4):427-438.
[21]Knudsen Ib.The Safe Foods framework for integrated risk analysis of food:An approach designed for science-based,transparent,open and participatory management of food safety[J].Food Control,2010,21(12):1653-1661.
[22]Li Qin.A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food safety governance based on cooperative game[J].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Science Procedia,2010(1):423-428.
[23]Broughton Edward I,Walker Damian G.Policies and practices for aquaculture food safety in China[J].Food Policy,2010,35(5):471-478.
[24]Herwig Alexia,Maier Leo.Beyond legalisation:developments in transnational food-safety governance[J].Law&Society,2007(1):5-8.
[25]Luciana Marques Vieira W,Bruce Traill.Emerald Article:Trust and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The case of a Brazilian beef processor[J].British Food Journal,2008,110(4):460-473.
[26]Chan S F,Chan Zenobia C Y.Food safety crisis management plan in hong kong[J].Journal of Food Safety,2009,29(3):394-413.
[27]Deodhar Satish Y.Motivation for and cost of HACCP in indian food processing industry[J].In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2003,2(2):193-208.
[28]Dumicic Ksenija,Gajdic Dusanka.Research of influence of food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pplication on business results in croatian food businesses.with english summary[J].Poslovna Izvrsnost/Business Excellence,2011,5(1):9-32.
[29]Karaman Ayse Demet,Cobanoglu Ferit,Tunalioglu Renan,et al.Barriers and benefi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foo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 among the Turkish dairy industry:A case study[J].Food Control,2012,25(2):9-32.
[30]Sampers Imca,Toyofuku Hajime,Luning Pieternel A,et al.Semi-quantitative study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a HACCP-based foo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in Japanese milk processing plants[J].Food Control,2012,23(1):9-32.
[31]Jaffee Steve,Masakure Oliver.Strategic use of private standards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vegetable exports from kenya and elsewhere[J].Food Policy,2005,30(3):316-333.
[32]Valeria Sodano,Martin Hingley,Adam Lindgreen.The usefulness of social capital in assessing the welfare effects of private and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food safety policy standards:Trust and networks[J].British Food Journal,2008,110(4):493-513.
[33]Luning P A,Marcelis W J,Rovira J,et al.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core assurance activities in a company specific foo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J].Trends in Food Science&Technology,2009,20(6):300-312.
[34]Dreyer Marion,Renn Ortwin,Cope Shannon,et al.Including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in food safety governance[J].Food Control,2010,21(12):1620-1628.
[35]Xiangrong Zhang.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food quality safety market admittance system[J].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2011,3(3):240-245.
[36]Gelse Roseanne White.Risk management key to food safety[J].Business Insurance,2012,46(25):12-13.
[37]Gkogka E,Reij M W,Gorris L G M,et al.The application of the Appropriate Level of Protection(ALOP) and Food Safety Objective(FSO) concepts in food safety management,using Listeria monocytogenes in deli meats as a case study[J].Food Control,2013,29(2):382-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