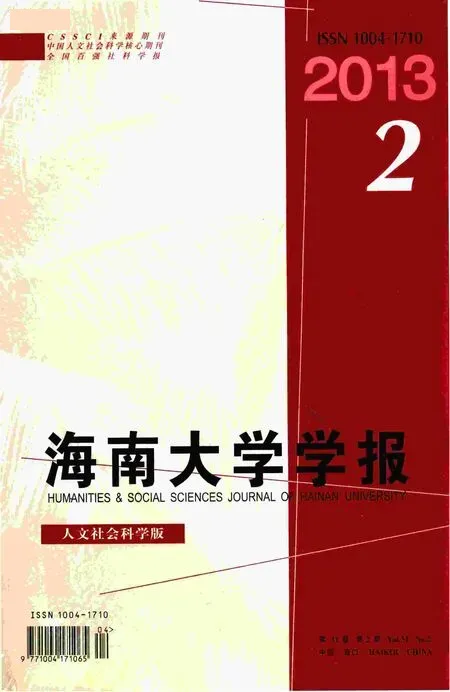在法律与行动之间:基层行政执法的自由裁量权及其治理
2013-04-06许雄
许 雄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海南 海口570204)
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法的核心与精髓,指的是“法律规范仅对行为目的、行为范围等作一原则性规定,而将行为的具体条件、标准、幅度、方式等留给行政机关自行选择、决定的行政行为”[1]82。作为一种行政过程中自由选择的权利,自由裁量权在我国法律尤其是行政法领域的研究中曾有过大量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不过,法学界对于自由裁量权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行政机关在行政决策中的自由选择权,而对于具体执行法律或法规的基层行政执法者的裁量权的探讨,则相对有限得多。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人们往往认为基层行政执法者将会自觉按照法律、法规和上级的命令来实施其执法行为。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基层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将采取合作模式的假设基础之上,然而事实上,在法律与行动之间,往往存在着大量的自由裁量空间。基层行政执法者正是借助于这一裁量空间,在行动中改变甚至重构法律或法规。为此,本文将从基层行政执法的这一裁量空间出发,探讨如何理解并有效治理基层行政执法裁量权,以实现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实质正义。
一、基层行政执法的自由裁量空间:街头官僚理论的视角
基层行政执法的自由裁量权是横亘于行政法学和公共行政学的交叉课题[2]。虽然在行政法领域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但在公共行政学领域则对这一课题有着极为深入的研究。利普斯基(Lipsky)于1977年所开创性提出的街头官僚理论(Street-level Bureaucracy Theory)便是其中最为经典的理论。按照利普斯基的界定,街头官僚所指的是“在工作过程中与公民直接联系,且在执行工作时拥有大量裁量权的那些公共服务工作者”[3]3。根据这一界定,基层行政执法者可以说是街头官僚的典型代表。因此,借助街头官僚理论的视角,将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基层行政执法的自由裁量空间。
(一)街头官僚理论
街头官僚理论认为,街头官僚所作出的决定、所建立的规则程序以及为应对不确定性和工作中的压力所创造出来的机制,均有效地转化成了其所执行的公共政策[3]30。显然,在街头官僚理论中,街头官僚其实才是真正的政策制定者。换言之,街头官僚所执行的实际政策与政策文本可能相分离,执行过程在事实上便成为了街头官僚对公共政策重构的过程,而这种政策重构的可能性则存在于街头官僚所拥有的大量自由裁量权之中。利普斯基认为,裁量权是街头官僚的基本特征,而较大幅度地减少这种裁量权往往比较困难。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街头官僚的工作环境往往都很复杂,以至于街头官僚往往无法根据固定的规则或政策来决定他们的行为;二是街头官僚的工作环境往往需要其对情境中的人性层面作出回应;三是街头官僚必须与公民进行互动,并在互动中获取尊严与权威,从而促成国家的合法性[3]15-16。因此,在自由裁量权的衡量中执行公共政策,这是利普斯基对街头官僚分析的核心。街头官僚拥有自由裁量权,并在此基础上解构并重构其所执行的公共政策,是街头官僚执行政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无法完全消除的。从而,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便取决于街头官僚的行动选择,而这种选择则源于街头官僚对具体情境的主观判断。可以说,利普斯基试图通过考察街头官僚在特定情境下的主观心理状态,来解释其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行为逻辑。有学者称该逻辑为生存逻辑[4]179。
(二)基层行政执法自由裁量空间存在的必然性
根据街头官僚理论,基层行政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将不仅仅根据法律文本,而且还将根据其对安全、秩序、完成工作的便利性以及在执法过程中对个案正义性的综合考量作出行动的选择。这种综合考量构成了基层行政执法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裁量权在事实上是难以完全消除的,其在执法过程中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基层行政执法过程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现代社会,立法者所要应对的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且问题所处的环境在不断地变动,从而存在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这种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一方面使得任一法律文本事实上都难以对所有的事务均作出详细的规定,并考虑到所有的细节。因为无论法律如何详细,现实的复杂性与多变性都将远远超出规则制定者的想象力[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行政法研究学者王名扬指出:“现代社会极为复杂,行政机关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决定,法律不能严格规定强求一致。”[6]另一方面,当复杂问题的治理权限集中在立法者和高层管理者手上时,由于“高层的决定是高度原则性的,而基层的决定则具有高度的可操作性”[4]164,有些法律本身在操作设计上便不够合理,从而无法在执法过程中恰当地回应问题的复杂性。这意味着,这些不合理的法律在具体执行中将必然造成行动与法律的背离。
其次,基层行政执法所面临的工作环境决定了裁量空间存在的必然性。一方面,基层行政执法通常是在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境中执行法律和政策的,比如决定时间的紧迫、信息获得的困难、人力资源的不足以及财政资金的有限。资源的有限性一方面决定了基层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将更加希望能够快速地处理大量的事务,减少执法工作量过大所带来的不适感受;另一方面,基层行政执法过程所面对的是具体的个案,而非抽象的群体。由于法律的首要目的在于形式的公正,试图对所有的行政相对人形成普遍的约束力,因而往往只能对相对人的行为进行抽象地规范,而难以考虑具体的个案。而“惟有借助于行政裁量,才能将法定的目的与具体个案结合起来,从而缩小法律之下的形式公正与个案正义之间的距离”[7]。
第三,基层行政执法者的自主性将促使基层行政执法者积极主动地通过各种方式寻求获得足够的裁量权。对此,利普斯基的解释是,“街头官僚拥有裁量权是因为,从本质上讲,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需要人来作出判断,而这种判断是无法事先规划,也无法由机器加以替代的”[3]161。而在越是复杂和不确定的情境中,基层行政执法者的这种判断的主动性就会越强烈,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规避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根据这一观点,基层行政执法者也可以被界定为适应性的、有目的的行动者。适应性是因为他们为环境的信息所引导,他们必须控制其基本的变量,以与其特有的限制相适应,从而巧妙地解除由环境施加于他们身上的压力。有目的性则是因为他们会基于其有限的信息,以及他们对如何规避风险的理解作出他们的决定和调整。因此,具有适应性和目的性的基层行政执法者,将会试图主动寻求解除环境所施加的压力,从而通过其与其立法者和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获得自由裁量的空间。
二、自由裁量权治理的两种模式: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
自由裁量权在基层行政执法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基层执法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选择、法律原则与多种法律规范的适用性的选择、行政运作程序的选择等三个方面[2]。按照前述观点,这种自由裁量的空间必然存在于行政执法过程当中,因而裁量权本身在事实上是无法完全消除的。然而,当前我国行政法学界在理解和治理行政裁量权方面,却仍然呈现出一种规范主义的思维模式,试图通过进一步规范和强化法律的控制,治理甚至消除基层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
按照周佑勇教授的考察,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行政裁量的治理模式可以概括为规范主义的控权模式和功能主义的建构模式两者基本类型[7]。规范主义受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者政治思想的影响,是西方传统的主流公法思想。自由主义关注社会中个体的自由权利,而保守主义则更加关注传统和权威。但两种政治思想在处理法律和行政之间的关系上,却表现出相当高的一致性,即强调行政权力应当在法律的规范和限制框架下运作,认为裁量权在本质上是执法者将个体意志强行施加于行政相对人身上,游离于法律规定之外,从而是不受法律承认和保护的一种政治权力。因而,在规范主义的思维模式下,基层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制约与控制,而基层行政执法者只有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来执法,才能维护法治原则的权威性。
可见,在规范主义否定并试图消除基层行政执法的自由裁量权。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法领域对该裁量权的主流观点,便是在这一思维模式下的研究成果。然而,现代社会中基层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空间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是不可完全消除的。尤其是,当规范主义片面追求形式法治从而忽视实质正义、忽视行政执法过程的复杂性以及将执法者看做是执行的机器时,裁量权的消除便更为困难。因此,当立法者和管理者将治理裁量权的努力聚焦于消除裁量权时,其治理的意图必然将要落空。而且,这种错误方向的努力也将影响到对基层行政执法裁量权的有效治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导致了基层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近年来频繁诉诸于报端的城管执法、食品药品的监督执法等各种执法冲突和争议,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因此,当裁量是不可避免同时也是不可完全消除和控制时,对基层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治理便需要转变长期以来传统的治理思维模式。长期以来被我国行政法学界所忽视的西方公法思想的另一种传统,即功能主义的传统,可以为思维模式的这种转变提供有效的借鉴和启发。功能主义的思维模式在对待法律与行政之间的关系时,迥异于规范主义的思维模式。在功能主义看来,行政并非必然是侵犯公民自由权和扰乱社会秩序的罪魁祸首,因而行政权力的形式也就并非必然需要完全置于法律的严格制约与控制之下。相反,功能主义强调,“政府是一种促进进步的进化式变迁的机构”[8],从而法律便成为促进行政过程的创新、维护并实现公共利益的工具。换言之,行政并非在法律的制约与控制下成为维护形式法治的工具,相反,法律将是实现行政公益目的的功能性保障。可见,功能主义的思维模式承认并鼓励行政过程中的裁量权,并认为通过行政裁量权的合理使用,有助于行政公益目的的更好达成。功能主义的这种思维模式,是符合现代社会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目的的。在现代社会,“法律作为政府行为的依据,其目的也是公共利益,加之对个体利益的合理分配”[9]。
三、行政执法的有效性与基层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治理
对基层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理解,功能主义持有与规范主义明显不同的观点,这与功能主义在西方福利国家建设的背景下,对法律与行政关系的理解和重构有关。“在公法中的功能主义看来,由于福利国家的出现和积极行政的生长,原有的议会和法院仅仅通过严格的规则来对这种服务型政府及其能动性裁量权的机械法律控制已不再有效,行政法必须从控制和权利转向功能和效率,以有效发挥行政裁量权的自身能动性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功能,这已成为时代的必然”[7]。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保障制度等民生工程建设的关键时期,法律在为行政权力的运作提供规范的同时,如何更好地促进行政的有效性,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公民和社会,促进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实现,便成为行政法学研究中一个亟须关注的重大课题。其中,如何通过有效治理,促进基层行政执法者合理、有效地运用自由裁量权,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协调或分配社会福利,提供安全有序的社会服务,实现社会的实质性正义,则是该课题的核心内容之一。
当然,本文主张吸收和借鉴功能主义思维下对基层行政执法裁量权的治理模式,并不意味着否定基层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可能性。事实上,在人的自利化倾向下,“所有的自由裁量权都可能被滥用,这仍然是个至理名言”[10]。尤其是,在专制传统的历史文化和计划经济的长期影响下,法律从属于公权力的思想在我国的基层行政执法领域仍然大量存在。这也往往成为规范主义控权模式成为我国行政法领域裁量权治理主流观点的现实社会基础。因此,本文对基层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治理主张,建立在以下三个观点的基础之上:一是承认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即基层行政执法的自由裁量权在事实上是不可完全消除的,这是治理的前提;二是防范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这是当下治理的重点;三是鼓励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因为裁量权的存在可以促进行政执法的有效性和执法过程中个案正义的实现,这是未来治理的方向。为达成以上治理的目标,需要重点做好两个方面的事项:一是设定合理的裁量基准;二是建构简易、公正的执法程序。
(一)设定正当的裁量基准
裁量基准(Discretion Criterion)指的是行政机关颁布的、以细化行政裁量标准为目的、为行政机关提供行动之实体和程序要求的内部规范性文件[11]。裁量基准对基层行政执法具有直接的意义:它有利于本地方或本系统的行政执法能保持一定的灵活性;能切合本地或本系统的具体情况;同时还有利于本地方或本系统执法能具有一定的连贯性,让执法保持相对统一的尺度[12]。
正当的裁量基准的设定需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在裁量基准的设定中引入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实现实质正义的核心路径。在裁量基准中引入比例原则,其目的是通过形式正义达成实质正义,兼顾行政执法的效率与执法权力的限制两个方面,从而促成行政机关对裁量基准的设定能够与行政目的相适应、成比例。比例原则在裁量基准中的应用,可根据行政相对人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等基本要素,细化不同违法行为的判断标准和量罚标准。第二,基准设定的科学与合理,具有可行性。当前我国在行政执法领域也在推行裁量基准设立的实践,但这些基准大都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如将违法情节进行较轻、一般、较严重、严重等十分模糊的划分,因而对基层行政执法人员裁量权的界定事实上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科学合理的裁量基准的设定应该给出对相对人违法程度的构成要件进行列举,并在广泛吸纳基层执法人员参与的基础上,根据实际的执法经验商定各种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第三,裁量基准必须向社会公开,尤其是在执法过程中向行政相对人明示,从而将基层行政执法裁量权的运用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减少基层行政执法人员利用裁量权进行权力寻租的机会。第四,裁量基准必须具有可诉性。当公民认为裁量基准可能损害自身合法权益时,可以提出行政诉讼,司法机关可以对裁量基准的正当性进行审查。
(二)建构简易、公正的基层行政执法程序
基层行政执法人员往往承担着极为繁重的执法任务,面对着可能彼此迥异的行政相对人及其违法行为。在执法现场,基层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往往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对不同个案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作出决定,“过于正式化的程序设计可能会加大行政成本,造成行政过程的阻滞,阻碍行政任务的实现,阻滞整体上正义的实现”[2]。因此,十分有必要建构简易、公正的行政执法程序,促使基层行政执法在法律的实质正义和行动的有效性之间寻求合理的均衡。
简易、公正的行政执法程序的建构可以通过流程再造来实现。由于受到行政组织各项规章制度的约束,基层行政执法工作有其特定的工作流程。然而,这些流程中所规定的程序往往包含了“增值的工作、必须但非增值的工作、返工的工作以及不必要的工作”等四种情形,其中,“返工占用了我们30%~40%的工作时间”,而“少于30%的时间被用来做一些增值性的工作”[13]。这便为基层行政执法程序的分析、改进和简化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对简易行政执法程序的建构应鼓励并吸纳基层行政执法人员的参与,共同商讨哪些程序是必要的、哪些程序是非必要从而是可以简化的,在商讨结果的基础上建构标准操作流程(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SOPs),并将该标准操作流程以类似于“书面执法指南”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发布。这种体现行政执法程序的简易性和公正性的“书面执法指南”与传统的行政执法程序相比较,其操作更为明确,形式更为灵活,更多地考虑了基层人员行政执法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从而也就更容易为需要短时间内做出裁量决定的基层行政执法者所接受。
[1]罗豪才.行政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宋华琳.基层行政执法裁量权研究[G].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8.
[3]LIPSKY Michael.Street-level Bureaucracy[M].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0.
[4]米切尔·黑尧.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M].赵成根,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5]BOVENSM,ZOURIDISS.From Street-level to System-level Bureaucricies:Ho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s Transforming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and Constitutional Control.Public[J].Administration Review,2002(2):174-184.
[6]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7]周佑勇.行政裁量的治理[J].法学研究,2007(2):121-132.
[8]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M].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88.
[9]赵娟.论行政法的宪政基础——对行政法与宪法之间关系的再认识[J].中国法学,2005(2):46-52.
[10]威廉·韦德.行政法[M].徐炳,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70.
[11]胡建淼.行政行为基本范畴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122.
[12]王天华.裁量标准基本理论问题刍议[J].浙江学刊,2006(6):124-132.
[13]史蒂文·科恩,罗纳德·布兰德.政府全面质量管理——实践指南[M].孔宪遂,孔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8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