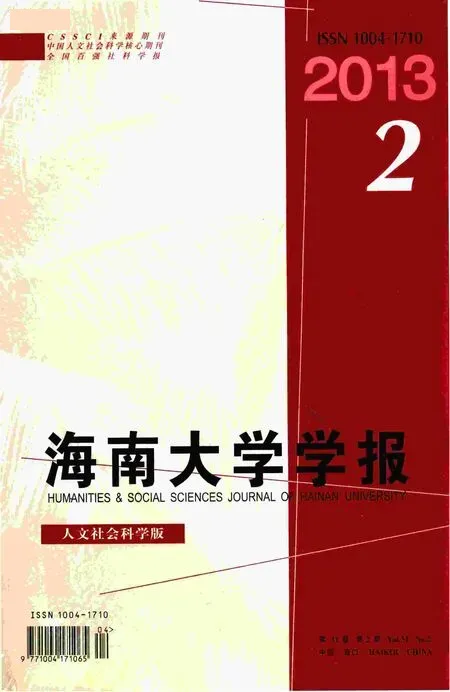诗歌翻译中“音美”的转换——以Wild Nights——Wild Nights为例
2013-04-06钟凌
钟 凌
(海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海南 海口570228)
好的文学翻译应该是在“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1]375的同时,把原作的长处完全地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使“译文读者(读译文)获得和原文读者(读原文)一样的理解欣赏。”[2]116“这样的翻译,自然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求译者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合适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和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1]375-376
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是独特的语言音、形、意“三美”的结合。诗有节奏,有韵律,有抑扬顿挫,有轻重缓急,读来朗朗上口;诗是由短行构成,由行而成节,组节成篇,分布排列,观来井然有序;诗的语言蕴意深刻,一字一词,无不令人浮想联翩,品味无穷。从表层观察,诗歌中,形式就是指音与形,而内涵是指意,也就是意境。但深层意义上,意境不仅指诗歌中的言辞带来的语义联想,由于诗歌的歌唱诵读特点,还指音、形、意,特别是音、意相互作用,共创的协同效果。因此,诗歌翻译中的原诗意境的传递固然重要,但绝不应当忽略其中的音与形。
由于中、英的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等方面差异,特别是语言本身具有的差异,翻译中完美地再现原诗“三美”很难,在“音美”方面尤其如此。惟有透彻领悟诗歌中“音美”所具有的“形式的认识论意义”与“形式的本体论意义”之统一[3]391-393,对原诗文本的“音美”层次作深刻具体的分析考查,清晰地了解音律对“意美”构建的作用,才有可能在翻译的过程中把握好原诗“音美”在译诗中的再现,让译诗的读者能像原诗的读者那样,在体味诗歌的神韵的同时,也能感受诗歌原本的节奏、韵律美。
以下通过对比研究美国女诗人Emily Dickinson的作品Wild Nights——Wild Nights以及江枫的汉译文本的“音美”特征及其与作品“意美”构建之意义,借助文本分析的方法,考查诗歌翻译中,“音美”的转换对表现原诗意境、风格和特征的影响。本文中,“音美”指的是诗歌的韵律、节奏的建构方式及其对营造诗歌美感和风格的贡献。
原诗如下:
Wild Nights——Wild Nights
——By Emily Dickinson
Wild Nights——/①诗中的“/”为划分音步的标记,为本文作者根据英语诗歌节奏划分单位“音步”添加。Wild Nights
Were I/with thee
Wild Nights/would be
Our lu/xury!
Futile——/the winds——
To a heart/in port——
Done with/the compass——
Done with/the chart!
Rowing in/Eden——
Ah,/the sea!
Might I/butmoor
Tonight——/In Thee!
一、原诗的“音美”特征分析
一般来说,诗歌都借助音韵、节奏、音调以及音节的长短等变化来实现独特的音美效果,表达特定的心境思绪和不同的风格情调。
Wild Nights——Wild Nights这首诗,从押韵的角度分析,第一节以半元音[w]作头韵,如wild,were,with和would,分别出现在前三行的开头和中间,节中重复三次Wild Nights,再配上二、三、四行thee,be,luxury三个词尾的由[i:]或[i]构成的abbb尾韵模式。
第二节,韵式有所改变。一、二行以futile和to中的元音[u]作为头词元音韵,三、四行变成[daun]作头韵,并采用重叠句“Donewith the××”,一、三行末是轻辅音[s],二、四行末为轻辅音[t],形成abab式辅音尾韵。
第三节中,might,I和tonight构成行间韵,与第一节中wild,night和I遥相呼应,第二、四行以sea和thee中的[i:]构成abcb尾韵模式,并与第一节中二、三、四行[i:]或[i]尾韵产生呼应效果。
韵律的布局产生和谐悦耳、声音回环的旋律美,特别是一、三节的尾韵呼应,能使诗歌诵读在经历第二节的变化后,重复体验某种特定、类似的调式。
节奏方面,除第六、七、九、十行外,每行四个音节。第六行“To a”连读成一个音节[uə],第七行compass虽有两个音节,但元音[Λ]和[∂]时值较短,使整词音长读起来与第八行中chart相当,第九行中的Rowing in有三个音节,也可通过连读Rowing的[əu]和[iŋ]部分,将时值缩短到一个音节的长度;相反,第十行中的Ah虽只有一个音节,通过延时,也可拉到两个音节的长度。这样,在诵读的过程中,每行都基本能达成四个音节的效果。每行四个音节分为两个音步(foot),全诗12行24个音步,其中21个音步用英语诗歌中特别受欢迎的抑扬格(iamb)节律模式。主体的抑扬格使得音节搭配模式整齐匀称,读起来轻重相宜,诗文富有整体节奏美。
纽斯凯尔小堆正在接受美国核管会(NRC)的设计认证评审,是迄今为止第一种也是唯一一种接受核管会设计认证评审的小堆设计。核管会于2018年4月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评审,并计划于2020年8月完成安全评估报告。纽斯凯尔预计将在2020年9月获得核管会发放的设计合格证。
诗的节奏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抑扬格背景下的扬抑格(trochee)又为诗文揉入了节奏的变化。作者在第五以及第七至十行的开头音步,反过来运用扬抑格模式,在具动态美的节奏变换中,造成节拍上的前后不协调,以配合在疾风暴雨中觅求风平浪静强烈语意对照,从而凸现出诗境里主人公冥想中情绪的转折,与诗中人物得意、俏皮的心境紧密契合。
律动舒缓也是这首诗的一大音韵特色。诗歌正文共有50个元音音节,元音以打开大阖的双元音和长元音为主,共计25个(包括[ai]11个,[au]3个,[əu]1个,[i:]4个,[a:]3个,[a:]1个,[ɔ:]2个),占50%。这些元音多与通音[w],鼻音[n]和擦音[h]、[s]、等发音比较绵长的辅音组合,使得整首诗在总体上弥漫着滞缓或舒展、压抑或豪放。
而逐行分析则可以看出,该诗的律动也存在与诗歌意境相应的动态变化。全诗一半的长元音和双元音都集中在第一节前三行,使诗的开篇带有显著滞缓、压抑、沉闷的语音氛围,紧密契合该部分压抑叹息的情感;但从第四行起,随着短促音(如爆破音、塞擦音和短元音)的连续出现,以及破折号和断句反复使用,诗的语音氛围逐步由轻盈、灵动,过渡到雀跃、开朗,并积累成第二节三、四行果决的激情迸发。第三节,随着短促音的减少和长音的增加,语音氛围又回复到缓慢,并孕育出结尾处超凡脱俗、静谧祥和的意境。其中第一节的“缓”与第三节的“缓”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缓”是激情迸发前的铺垫,后“缓”是迸发后,随激情消弭而来的惬意、安详。
诗歌的宏观语音布局按三个诗节的“滞缓—轻快—舒缓”模式同步变化衍生出律动美,存在广义的节奏感,鲜明映射出风雨中见彩虹般乐观、浪漫的情怀。
以上分析表明,这首形式短小精干的诗文中,丰富多彩的音韵、错落有致的节奏和缓急相间的律动等语音手段,对体现诗歌变化起伏的手法,赋予作品典型Dickinson式诗歌骨感、简约、内敛的风格[4],展示其作品中惯有的在暴风骤雨的世俗人间追求方外仙境的精神,衬托诗歌主人公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豪气等,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二、译诗“音美”特征转换的比较与分析
汉、英语言的语音体系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汉语是声调语言,汉字是单音节。诗歌“音美”特征体现于阴、阳、上、去等声调变化产生的平仄起伏。而英语是重音语言,英语单词多是多音节,有轻、重之别。借助轻重变化引发抑扬,赋予诗歌“音美”色彩。
其次,英汉诗歌音韵规则大不相同。英语诗歌有头韵、行间韵、尾韵等,汉语诗歌多为尾韵;英语诗歌无论元音、辅音,实词、虚词,发音相同或近似,都能用作韵脚,汉语诗歌则以相同韵母作韵脚,而且多数是表意实词(除早期的古诗外,如屈原的《离骚》、《九歌》中多用“兮”)。
再从节奏来看,汉语诗歌以“音组”[5](或称为“顿”)为节拍单位,“音组”多由两个、三个抑或是四个汉字放在一起,它们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同时又形成语音单位的一种自然的起落,通过平仄交错的变化调配出各种音调节奏。“以顿为节奏单位既符合我国占典诗歌和民歌的传统,又适应现代口语的特点。”[6]英语诗歌是以“音步”为节拍单位,每个音步不少于两个或多于三个音节,并含一个重读音节,通过轻音和重音的交替,形成抑扬格、扬抑格、抑抑扬格和扬抑抑格等节奏模式。
英诗汉译时,常采用“以顿代步”的策略,即“用相当的顿数(音组数)抵音步而不拘字数来译这种格律诗,既较灵活,又在形式上即节奏上能基本上做到相当,促成效果上的接近。”[7]“英诗重节奏而压韵次之,可以说节奏是英诗的根本,是以节奏统韵律;而汉诗则不然,是音韵与节奏并重,而且特别讲究押韵,可以说音韵是汉诗的根本,是以音韵统节奏。”[8]1从某些意义上讲,“汉语音节的结构便于形成乐音。”[9]
因此,英汉诗歌互译中,要达到译品的音韵之美与原作绝对的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翻译时一定要照搬移植,死守硬扣英文原作的音韵风格的话,只怕天下找不出一个翻译家能做得到天衣无缝。从这层意义上讲,不同语言诗歌的“音美”是不可译的。尽管如此,诗歌翻译艺术家们依然能借助各自无限的想象力,创造性地发挥汉语本身的语音特点,将英语诗歌的韵律、节奏、情调和风格,以各种手法加以展现,使译本读者或尽可能地领略英语诗歌原汁原味的语言风采,享受原诗的音律美。以下,通过分析江枫先生在汉译中所采取的转换手段,讨论诗歌“音美”的翻译实现。
三、江枫译本的“音美”转换手法及特点
资深诗歌翻译家江枫的英诗汉译造诣独到,其诗译讲求形神兼似、贴近风格[4]。他的译文不仅完美体现原诗的神韵和意境,而且在遣词造句上尽量与原诗契合,在间行、分节、停顿,甚至标点符号,都尽量贴近原诗,将原诗风格原汁原味地再现出来。狄金森诗歌形式短小奇特,表达言简意赅,风格简约;江枫译文,也简约精干,并体现他一向倡导的译诗原则。在“意美”、“形美”处理上如此,在“音美”处理方面也绝不例外。江译文本“音美”转换手法及特点分析如下。
江译文本:
暴风雨夜
——江枫译
暴风雨夜,/②诗中的“/”为划分“顿”的标记,为本文作者根据汉语诗歌节拍划分单位“顿”添加。暴风雨夜!
我若和你/同在一起,
暴风雨夜/就是
豪奢的/喜悦!
风,/无能为力——
心,/已在港内——
罗盘,/不必——
海图,/不必!
泛舟在/伊甸园——
啊,/海!
但愿我能,/今夜,泊在——
你的/水域!
译诗音韵以尾韵和重复为主。如第一节,在首行和第三行与原诗相同位置,三次重复“暴风雨夜”;另外一、四行末“夜”和“悦”押韵,形成abca式尾韵。第二节,一、三、四行末的“力”、“必”、“必”押尾韵,韵式为abaa,并重复“不必”,以求复制原诗重复“Done with”的效果。第三节,一、四行末“园”和“域”声母相同,三、四行末“海”、“在”押韵,基本可归结为abba式尾韵。此外,第一节的第四行末,第三节一、四行末的“悦”、“园”、“域”三字,也出于声母相同的原因,虽不能在严格的汉语意义上押韵,仍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首尾语音呼应的效果。由于汉语基本不用头韵、行间韵等音韵手段,与原诗比较,尽管译诗音韵体系更为简约,但因为押韵位置的选择与原诗相同或相当接近,依然能营造与原诗相当近似的音韵回环美。
就这首诗而言,江译最能把握原诗风格韵味之处在于节奏和律动的处理。译文在音律节奏布局上非常接近原诗。
译诗正文共计65个汉字,也即65个音节。这些音节按四字、三字、二字一个音组,甚至一字一音组,分为24个音组。其中四字音组9个,三字音组3个,二字音组8个,一字音组4个(两个短促加停顿的单字,“风”、“心”;两个长音加延音的单字,“啊”、“海”)。如此,译诗12行、24顿,每行两顿,完美对应原诗12行、24个音步,每行两音步。
这24个音组(顿)也非随意取用的。译者依照原诗意境和音律的抑扬起伏、轻重缓急,以四字一顿的长音组,如“暴风雨夜”、“我若和你”、“但愿我能”等,体现原诗中的长元音或双元音绵长、滞缓的语音效果,如“Wild Nights”、“Were I”、“Might I”等;以二字一顿或一字一顿的短音组,如“喜悦”、“风,”、“不必”等,体现含短元音音步短促、灵动的音效,如“xury”、“the winds”、“Done with”等,从而通过长短不同音节搭配模式传递原诗变幻的节奏和律动风格。这一点充分表现在每节、每行语音组合的分布当中。
首节,较长的四字一顿音组数量最多,9个四字音组中5个出现在第一节;首节的音节数量也是最多的,共27个,占总音节数42%余;此外,除第一行外,其他三行皆无行间断句。长音组较多,音节数较多,每行诗句较长,共同营造出缓慢、滞涩的朗读效果,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原诗首节双元音和长元音带来的压抑和沉闷。
反观第二节,一半短音组集中于此,形成8个音组中有六个短音组的格局,四个二字音组和两个短促加停顿的一字音组(“风”、“心”),外加音节数最少,行间断句最多,使第二节的朗读自然而然地带上灵动、雀跃、果决的色彩。这无疑与原诗,无论在意境,还是在语音表现手段上,都近乎一致。
第三节,三字音组和两个长音加延音的单字(“啊”、“海”)的加入、音节的增多和延长减缓并冲淡了被第二节加快了的节律,使诗歌情调又回复些许舒缓,从而营造出惬意、祥和、宁静的语音氛围,这又刚好吻合原诗空灵界外的心态和超越尘世的境界。
以上分析表明,江译文本整体上和原诗一致,也同样宏观地具有“滞缓—轻快—舒缓”律动特色。这样的译品,首先在语义和意境上能使译语读者产生与原语读者相似的情绪共鸣,然后在咏唱或朗诵中,译语读者会进一步领略诗歌给原语读者带来的、相近的韵律、节奏和律动美,当心灵的共鸣和官能的体验高度合一的时候,和原语读者意念相似的联翩浮想便也会在译语读者心中油然而生,使译语读者获得近似的精神升华。在翻译的视角上,这样的译品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奈达提倡的“翻译功能对等”理念。
四、结语
音效上尽可能的对等,是江枫英诗汉译倍受推崇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本诗而言,江译文本显然比其他译本高妙许多。有些译本虽能表现出原诗的一些意境,并有一点押韵,却无视原诗音韵特色和风格,没有丝毫“音美”、“形美”,最多只能算按诗行排列的散文,读不出诗意,更谈不上让译文读者品味原诗的音、形、意相辅相成、三位一体的精髓。
另外的译本运用“五言四行”齐言的格式,再造出方方正正、井井有条的视觉效果,还完全打破原诗的格律和韵式,套用汉语诗歌的用韵策略,一韵到底,重新构建了诗歌的形式结构。译作读起来虽然朗朗上口,具有极好的歌唱性,可是过度的创意不仅会背离原诗的“意美”,而且会在宏观上、微观上严重损坏原诗的“音美”氛围。该译文通过“狂情似火烧”的野性、“相思债未了”[8]6-7的轻佻和节奏的敏捷轻快,来阐释E.Dickinson以“暴风雨夜”为铺垫抒发的爱情畅想,并将这种手法解释为“摆脱‘英诗格律这条洋锁链去跳中国的舞蹈’”[8]2,这无论在意境上,还是在节律上,都彻底颠覆了原诗的情调和境界,总有些以通俗的小调儿翻唱高雅的咏叹的味道。
诗歌翻译虽不能原封不变、生搬硬套地将一种语言的音律模式移植到另一语言中,但也绝不应完全抛弃原诗的“音美”特征,另起炉灶,彻底以译入语的音律模式替代。对于诗歌来说,如果“感心”的“意美”是诗歌的灵魂,那么“感耳”的“音美”则是诗歌的血肉,对意念的表达和风格的体现,它都具有绝对的贡献。
“形式”和“意义”二元统一之辩证关系说明,形式既是认识的手段,又具有本体论意义。诗歌的核心表达形式“音美”与诗歌的意义“意美”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诗歌的翻译既不能只顾“意义”,不顾“形式”,过分地创造,也不能陷于死扣“形式”的“硬译”、“死译”。只有重视译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形式的“功能对等”,寻求恰到好处的“音美”对应,才可能尽量保证译诗原汁原味地传递原诗的神采和风韵。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诗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NIDA E A.Language,Culture,and Translation[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刘宓庆.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4]刘晓敏.艾米丽·迪金森诗歌两个汉译本翻译风格比较[J].语文学刊,2010(10):91-94.
[5]孙大雨.诗歌底格律[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2):12-17.
[6]罗新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G]∥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19.
[7]卞之琳.译本说明[M]∥沙士比亚.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4.
[8]吕志鲁.英语爱情名诗选译[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3.
[9]钱冠连.美学语言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