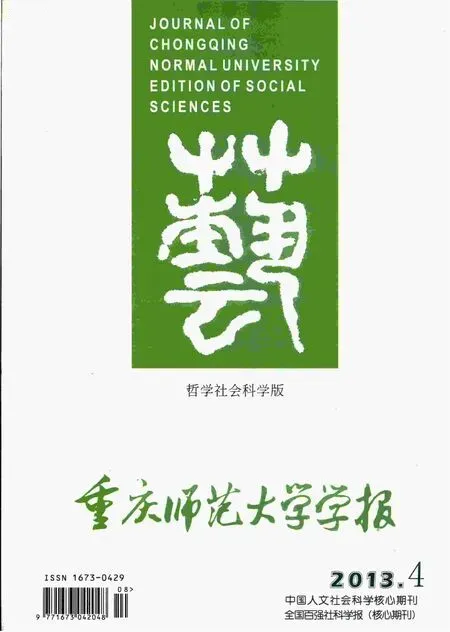论《搜神记》中的鬼神与“神道”
2013-04-02孔毅
孔 毅
(重庆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重庆 401331)
《搜神记》为东晋干宝所撰。《搜神记》原本已散失,今本系后人缀辑增益而成二十卷。《搜神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1](序),虚实相混,精彩纷呈,传统将其归到志怪小说类。20世纪以来,不少研究者从民俗学、宗教观、人文精神等方面对《搜神记》进行解读。[2]其实,干宝自谓撰《搜神记》的目的是“发明神道之不诬”[1](序),也即阐发并证明“神道”并非虚妄。因而一部《搜神记》,就是用人的道德观对鬼神道德的诠释。
一、《搜神记》中的鬼神
何谓鬼?《说文解字》:人所归为鬼。从人,像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凡鬼之属皆从鬼。[3](鬼部)古人认为,人死之后化为鬼,而归于幽冥之间。所以鬼又称亡魂、亡灵、幽灵、幽魂。何谓神?《说文解字》: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从示、申。[3](示部)《辞海》:鬼是“宗教及神话中所幻想的主宰物质世界的、超自然的、具有人格和意识的存在”[4](362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鬼与神虽然是不同的生物状态,但都有某种非凡法术神力,所以鬼神常常合称。如鲁迅所言:“天神地祇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祇。”[5](10)同时,古人也认为,鬼神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触摸或看到的,因而不宜去证明其实在性,但可以通过真诚祈祷、祭祀等等方式与鬼神沟通。所以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
(一)《搜神记》中鬼神的特点
鬼神的观念源于原始社会时期。鬼神的观念又与灵魂不灭观念相联系。两汉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促使人们对肉体和灵魂关系有了重新认识。如王充说:“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6]鬼神是社会政治败坏和人“思念存想”所致。[6]又如西晋杨泉在《物理论》中用“薪尽火灭”这一形象的比喻,否认灵魂不灭观念,认为“人死之后,无遗魂矣”[7]。然而随着魏晋乱世的到来,佛教的神不灭和道教的神仙思想大行其道。虽然干宝没有参与到神灭与神不灭的论争之中,但是“宝以为人死神浮归天,形沈归地,故为宗庙,以宾其神”[8]。宝父有嬖人死而复生,宝因此“有所感起”(《世说新语·排调》注引《孔氏志怪》)[9],而作《搜神记》。干宝之作《搜神记》虽然不是为“神不灭”作论证,却是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神道”捧场,即所谓“发明神道之不诬”。即是说,《搜神记》讲鬼神的故事只是形式,阐发神道以警示人伦才是目的,因为如果人们“上则顺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内则以孝于亲”(《礼记·祭统》),社会秩序就不会混乱,人际关系就会和谐。所以,《搜神记》中的鬼神,也就与佛、道之鬼神有一定的差异。
其一,鬼神是气化的产物。
干宝的鬼神观,有其传统宇宙观的渊源,这就是宇宙生成论。“中国哲学宇宙成因论的最高理论思维成果是元气论”,“汉代以后,大多数哲学家都认同元气说”[10](80)。干宝也不例外,认为鬼神灵怪与人一样,都是气化的产物:“然则天地鬼神,与我并生者也;气分则性异,域别则形殊,莫能相兼也。生者主阳,死者主阴,性之所托,各安其生,太阴之中,怪物存焉。”[1](卷十二)不同的是,干宝赋予气以鲜明的道德特性。他认为:“天有五气,万物化成。木清则仁,火清则礼,金清则义,水清则智,土清则思:五气尽纯,圣德备也。木浊则弱,火浊则淫,金浊则暴,水浊则贪,土浊则顽:五气尽浊,民之下也。中土多圣人,和气所交也。绝域多怪物,异气所产也。苟禀此气,必有此形;苟有此形,必生此性。”[1](卷十二)即是说,宇宙间有金、木、水、火、土五气,这五气有清有浊,且各具道德属性,其流行不息变化成就了万物。一般来说,中土多圣人,这是因为气和之故。而偏远之地多怪物,也是由于气异的产物。“尔则万物之变,皆有由也”[1](卷十二),这个“由”,即是气的变化。世间千奇百怪之物的变化如“千岁羊肝,化为地宰;蟾蜍得苽,卒时为鹑。此皆因气化以相感而成也”[1](卷十二)。同样,怪异之物也是气化的产物。“妖怪者,盖精气之依物者也。气乱于中,物变于外,形神气质,表里之用也。”[1](卷六)
其二,鬼神有大德。
在《搜神记》中,鬼神有许多美好的品德。这一点将在下文详论之。认为鬼神有德,源于古人对鬼神浩大无边、无所不能之功德的想像。如《礼记·中庸》载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这种想像,导致人们对鬼神的敬畏、崇拜,乃至于“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从而心生诚、敬之德。
其三,鬼神能施祸福予人类。
干宝认为,万物之生死变化都是鬼神施以神力的结果。鬼神并非虚幻,“神仙岂虚感,应运来相之。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菑”[1](卷一)。而且,鬼神的功能又是人所不能及的,“从此观之,万物之生死也,与其变化也,非通神之思,虽求诸已,恶识所自来”[1](卷十二)。同样,人世间的祸福吉凶也不是无来由的,王祥卧冰,“孝感天神”[1](卷十一),谅辅 “至诚”,“一郡沾润”[1](卷十一),孙策疮崩而死[1](卷一),孙綝被诛[1](卷一),皆为鬼神的赏罚所致。所以,“鬼神者,其祸福发扬之验于世者也。”[1](卷十二)
(二)《搜神记》中鬼神的分类
《搜神记》中的464条故事中直接涉及到鬼神的约一半左右。[11]
第一类,始祖神类。如神农鞭百草、赤松子掌管雨水、陶安公铸冶、宁封子出五色烟等,这些神人同形的、具有神力的华夏始祖,敢于为民众的生存与天斗,与地斗,创造出不朽的惠及万民的业绩。
第二类,仙道类。如赤将子轝、师门、冠先、琴高、刘根、偓佺、彭祖、葛由、王子乔、阴长生、鲁少千、于吉、左慈、葛玄等,不仅长生,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神术。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往往生活在社会下层,周济救急则是他们的特点。
第三类,死而复生类。这类在《搜神记》中很多,因其情况灵异,所以也被视为神:冠先被宋景公所杀后数十年复活[1](卷一),平常生数死而复生[1](卷一),徐光被孙琳所杀,后复活作大风使琳车为之倾[1](卷一),张璞二女投水后又复生[1](卷四),李娥死后十四日复活[1](卷十五),贺瑀死后三日复活[1](卷十五),等等。
第四类,鬼魂类。颖川太守史祈的父母死而为鬼。[1](卷一)胡母班见父母在阴间著械徒作。[1](卷四)丹阳丁氏女被姑虐待自杀死而为鬼。[1](卷五)颛顼氏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疟鬼;一居若水,为魍魉鬼;一居人宫室,善惊人小儿,为小鬼。[1](卷十六)
第五类,下凡的神仙类。尤以仙女居多。有助园客养蚕的“神女”[1](卷一),有助孝子董永织缣的“天之织女”[1](卷一),有与弦超共饮食的“天上玉女”[1](卷一),等等。
第六类,精怪类。这一类型特别多,是由一些人及动植物发生变异,获得某种超自然力而化为带有诡秘色彩的灵异精怪。如“马化狐”[1](卷六)、“人产龙”[1](卷六)、“马生人”[1](卷六)、“女子化男”[1](卷六)“木生人状”[1](卷六),“狗作人言”[1](卷七)、“女化蚕”([1](卷十四)、“人化鳖”[1](卷十四)、“顿丘鬼魅”[1](卷十七)、“客化老狸”[1](卷十八),等等,它们是鬼神的异型。
以上这些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神彩各异的鬼神,大多被干宝塑造成或善或恶的伦理典型。然而支配着这些鬼神的根本精神是对道德的尊崇,对邪恶的鞭笞。这种道德精神既体现在那些对华夏文明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贡献的超人身上,也蕴含于芸芸众生平凡而普通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形成了政治化、伦理化和世俗化了的“神道”。
二、“神道”及《搜神记》中的神道
《辞海》释“神道”有相关的四义项:天道、神术、神祇、墓道。[4](3625)后人对“神道”的诠释可谓五花八门。有学者把它们归纳为神妙无形说、自然无为说、至诚如一说、礼乐刑政说、祭祀礼仪说、巫筮鬼神说等六种观点。[12]《礼记·中庸》:“君子之道……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即神道与天道相通,君子要比照神道考察人道,如果二者没有冲突,才算知天。也即神道是沟通天道与人道的中介,所以“圣人”以神道教化百姓,此谓神道设教。“神道设教”的实质即《晋书》卷六十五《艺术传序》所云:“艺术(即沟通人神的巫术数术之类)之兴,由来尚矣。先王以是决犹豫,定吉凶,审存亡,省祸福。曰神与智,藏往知来;幽赞冥符,弼成人事;既兴利而除害,亦威众以立权,所谓神道设教,率由于此。”《搜神记》中的神道,即指具有道德属性之鬼神“既兴利而除害,亦威众以立权”的政治伦理功能。
前已述及,干宝自云作《搜神记》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言下之意,时人或以为神道虚妄。这是因为,神道的功能被无限的扩张,如《中庸》说鬼神之德浩大无边,包纳万象,但只可意会不可名状,亦难以把握。这样一来,神道就成为一种形上的存在了。由于神道被不断改造和夸张,乃至于“诡托近于妖妄,迂诞难可根源,法术纷以多端,变态谅非一绪,真虽存矣,伪亦凭焉”(《晋书》卷六十五《艺术传序》)。其教化功能的发挥必然受到限制,以致后人有“神道幽昧,探赜之求难以常思,错综之理不可一数”(《晋书》卷八十三《江逌传》)之叹。干宝的功劳就是通过鬼神的记载,阐发和证明了神道的实在和可信,从而使神道由无形转为有形,由幽昧变得清晰。
(一)作为华夏民族的精神象征的神道。
《搜神记》中的神道,突出地体现在那些富于道德色彩,对华夏文明有重大贡献的具有神性的超人身上。这些具有神性的超人在今人看来多半是神话或传说。发生这些神话和传说的时空虽然难以指实,却是保留在民族记忆中的不灭印记,并作为神道的象征而定格。首先,他们是华夏始祖,还是启蒙先知。他们的形象是神道的观念与华夏始祖观念的融合体。他们的行为鲜明地体现出华夏民族的自我关怀,具体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和命运的维护、追求及关切,也昭示着华夏民族精神追求的方向。其次,他们是华夏先民,有无比的聪明才智,支配各种自然原质与自然力相对抗,教人们用各种方法去获取生存的手段。这些都反映出华夏先民对自身创造力的自信,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追求,以及支配自然力量使之为自己服务的幻想和愿望,同时也是先民奋起与各种灾害顽强抗争的精神写照。
其一,以天下为己任,勇于抗争的精神。
华夏始祖舜虽然为历山一劳苦农夫,但“知天命在己,体道不倦”,最终成就了大事业,众甚惧。武王为拯救生民而伐纣,面对“雨甚,疾雷,晦冥,扬波于河”等自然障碍而无所畏惧,英勇抗争,体现了鲜明的主体精神及斗争精神。[1](卷八)
其二,厚生爱民,自强不息。
早期人类处境恶劣,华夏先祖们不辞辛劳,锲而不舍,以超群的智慧和勇气,为人们解决各种生存问题,如“播百谷”的神农、掌管施雨的赤松子、木工之父赤将子轝、制陶业之父宁封子、采药父偓佺、铸冶师陶安公,[1](卷一)等等。在这些故事中,作者把华夏民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为了改变生存条件,克服各种自然障碍,并涌现出各种日用发明和创造的事迹,都加在一个个有着神异的经历或本领的人身上。这些具有神性的主人公的行为也诠释了神道之厚生爱民意识,涌动着华夏民族自强不息的壮阔气象。
其三,为民谋利,勇于牺牲。
华夏先民生存环境的艰苦,激发了其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由此而孕育出一大批以至诚之心,不惜牺牲自己与自然抗争、为民谋利的民族英雄。商汤“既克夏,大旱七年,洛川竭。汤乃以身祷于桑林,翦其爪、发,自以为牺牲,祈福于上帝。于是大雨即至,洽于四海”[1](卷八)。后汉谅辅“时夏枯旱,太守自曝中庭,而雨不降;辅以五官掾出祷山川,自誓曰:‘辅今敢自誓,若至日中无雨,请以身塞无状。’乃积薪柴,将自焚焉。至日中时,山气转黑起,雷雨大作,一郡沾润。世以此称其至诚”[1](卷十一)。王业,“汉和帝时为荆州刺史,每出行部,沐浴斋素,以祈于天地,当启佐愚心,无使有枉百姓。在州七年,惠风大行,苛慝不作,山无豺狼”。[1](卷十一)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或为传说,或为实有,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明显被神化了,且被用来阐发并证明神道。
(二)作为日常生活之道德体现的神道
《搜神记》中的神道,还体现在作为普通的各式各类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实际上是当时人们道德生活的反映。如鲁迅所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5]这种神道不关心那些宏大的、终极的问题,例如世界的本原、万物的根本等,甚至也不会涉及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神灵,却与芸芸众生的生活、烦恼和憧憬密不可分,因而其内涵更为丰富和实在。同时,这种神道通常是体现于看似明确却不易坐实的时间和场所之中,即使是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因“不知所之”,“不知所从来”[1](卷一),“不知所在”[1](卷一、卷十四、卷十七),“不知何许人也”[1](卷一、卷四),“不知何氏之女也”[1](卷十一)而被范式化、神秘化,因而又具有超越时代和地域的普遍意义。
其一,抗争命运,为民除害。
有何敞,“里以大旱,民物憔悴……叹而言曰:‘郡界有灾,安能得怀道!’因跋涉之县,驻明星屋中,蝗蝝消死,敞即遁去。”[1](卷十一)又安阳城南有一亭,夜不可宿;宿,辄杀人。书生明术数,乃过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后宿此,未有活者。”书生曰:“无苦也。吾自能谐。”遂住廨舍。……凡杀三物,亭毒遂静,永无灾横。吴时,“庐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辄死。自后使官,莫敢入亭止宿。时丹阳人汤应者,大有胆武,使至庐陵,便止亭宿。……至三更。竟忽闻有叩阁者。……知是鬼魅。……以刀逆击,中之。……自是遂绝(鬼魅)”。[1](卷十八)最为感人的是少女李寄为民除害,使更多的小姐妹免遭恶蛇的吞啮。[1](卷十九)其智慧和勇敢超越常人,因而其形象也神性化。值得注意的是,《搜神记》中勤劳、善良、坚贞、勇敢的主人公不少是女子,因此,《搜神记》中的神道又多了几分尊重女性的意蕴。
其二,恪守孝道,孝感天地。
孝道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在寻常百姓那里有着极其深厚的基础,因而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习俗。在《搜神记》中,干宝辑录了大量有关普通百姓恪守孝道,以至感天动地的故事。如曾子从仲尼在楚而心动,辞归问母。母曰:“思尔啮指。”孔子曰:“曾参之孝,精感万里。”王祥“性至孝。……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炙,复有黄雀数十入其幕,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郭巨念举儿妨事亲,“欲埋儿,得石盖,下有黄金一釜,中有丹书,曰:‘孝子郭巨,黄金一釜,以用赐汝。’于是名振天下。”[1](卷十一)因恪守孝道而得神助的还有东海孝妇、河南乐羊子之妻[1](卷十一)、健为孝女[1](卷二十一)等女性。这类故事说明,作为当时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孝道,因其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故在百姓口耳相传的过程中逐渐神秘化、神圣化,进而被纳入神道的范畴。
其三,坚守爱情,忠贞不渝。
爱情本是人类社会所产生并专有的,它因异性间相互吸引,而彼此产生爱慕并引起心理变化的情感活动。爱情往往与婚姻相联系,“夫妇阴阳二仪,有情之深者也”[1](卷六)。然而,中国古代社会婚姻的基础是封建宗法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必然要求门当户对,由此导致具有神话色彩的爱情悲剧不断发生,而男女主人公坚守爱情、忠贞不渝的美德亦由此彰显。如秦始皇时,有王道平与与同村人唐叔偕女生死相恋的故事,“实谓精诚贯于天地,而获感应如此”[1](卷十五)。类似的事还有晋武帝世,河间郡男女的故事。更为感人的则是脍灸人口的韩凭夫妇的故事。[1](卷十一)韩凭夫妇为爱情生死相随、精魂不灭的故事体现了神道与人类美好情感息息相通。
其四,知恩图报,有仇必报。
知恩图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民间有深厚的土壤。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其教义中的不杀生、因果报应等内容广泛传播,使中华传统文化中珍爱生命、知恩图报的思想影响更为深远。在《搜神记》中,这类故事的主角或为人,或为动物,无不体现出这一中华传统美德。
珍爱生命与知恩图报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搜神记》卷二十记载了不少这类故事。这类故事或发生在人与鬼神之间,或发生在人与动物之间,由于其体现的过程和方式特别奇异,所以也被视为神道的反映。如报恩于人类的龙,报恩于妇人的虎,报恩于孝子的玄鹤,报恩于杨宝的黄雀,报恩于隋侯的蛇,报恩于孔愉的龟,报恩于老姥的龙之子,报恩于董昭之的蚁,报恩于李信纯、华隆的狗,报恩于庞企的蝼蛄,以及报恩于麋竺的新妇(实为天使)[1](卷四)、报恩于老翁的丁氏女(已故)[1](卷五),等等。宣扬此类故事旨在训示人类要知恩感恩:“犬之报恩,甚于人,人不知恩,岂如犬乎!”[1](卷二十)同时,故事中的那些人往往因珍爱生命而得到善报,这不仅有劝导人们要有仁爱精神的意味,也宣扬了佛教因果报应的思想。
这种因果报应的思想还体现在恶有恶报上,如因虐杀猿子而其家疫死灭门的临川东兴某人、因射杀大麈而死的虞荡、因射杀大蛇腹痛而卒的陈甲[1](卷二十),等等。这些故事有两方面意义,一是劝善,二是止恶。它既是神道的内容,又是神道的体现。它勉励人们修德避祸,“安身养德,从容光大,勿以神奸,污累天真”[1](卷三)。这样,即使遇到妖孽也无忧,因为“夫神明之正,非妖能害也”[1](卷三)。
此外,知恩图报的另一面是有仇必报。人类的复仇现象及观念渊源于古老的原始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民间土壤。在《搜神记》中,最为普遍的复仇首先是冤死鬼报生前之怨。如汉时民女苏娥“冤死,痛感皇天,无所告诉”,故其鬼魂向交州刺史何敞状告杀害自己的凶手,使之受到惩罚。[1](卷十六)孙策既杀于吉,“每独坐,彷佛见吉在左右。……如是再三。扑镜大叫,疮皆崩裂,须臾而死”。吴时大将军孙綝杀徐光。“将拜陵,上车,有大风荡綝车,车为之倾。见光在松树上拊手指挥嗤笑之,綝问侍从,皆无见者。俄而景帝诛綝。”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杀龙师师门“而埋之外野。一旦,风雨迎之。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祷之,未还而死”[1](卷一)。其次是为父母复仇。“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即杀之。莫邪子名赤,比后壮……日夜思欲报楚王。”后以自己的头献给刺客,让刺客替自己报了杀父之仇。[1](卷十一)还有一类复仇是为捍卫自己尊严,便利用鬼神的超自然力来复仇,使那些蔑视、侵犯、有负自己的人或被震摄,或付出沉重的代价。卷一第19则载:“汉阴生者,长安渭桥下乞小儿也。常于市中丐,市中厌苦,以粪洒之。……洒之者家,屋室自坏,杀十数人。”卷二第48则载:东晋时,有“风流令望”的镇西将军谢尚无儿,其原因是他年少时,“与家中婢通,誓约不再婚,而违约;今此婢死,在天诉之,是故无儿”。
以上这些复仇者或是自己或亲友有冤屈,或是自己被蔑视、侵犯,而复仇的对象往往强暴、邪恶,践踏他人尊严,因而复仇者被视为正义的化身,其复仇行为亦如有神助,从而昭示着神道惩恶扬善的意志。
三、《搜神记》中的鬼神所折射的现实世界
干宝自谓《搜神记》所载之人和事既有“承于前载者”,亦有“采访近世之事”[1](序),说明其鬼神观既有对魏晋前人思维模式的承袭,又是对时人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的展示,同时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
其一,兵连祸接。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13](149)。西晋末年,内有八王之乱,外有“戎羯称制”,导致晋室南渡,南北分裂,“兵凶岁饥,死疫过半”(《晋书》卷九《元帝纪》),人民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一如《搜神记》中描述的下层民众刘赤父、周式等面对死亡,哀告无用、逃避无门的悲苦与无助。[1](卷五)
其二,政治昏暗。
在《搜神记》卷六中,干宝集中记载了历代种种妖孽怪异现象,极力指陈这些都是由于风气不正,政治黑暗所造成:“人君不用道士,贤者不兴。或禄去公室,赏罚不由君,私门成群”;“宫刑滥”,“妇政行”;“兴徭役,夺民时”;“有德遭害……行刑暴恶”;“政不顺……贤士不足”;“执政失”;“诛不原情”;“君不正,臣欲篡”;“君吝于禄,信衰贤去”;“臣私禄罔干”;“邪人进,贤人疏”;“弃正作淫”;“君有妄诛之暴,臣有劫拭之逆。兵革相残,骨肉为仇,生民之祸极矣。”干宝指出:要消除妖孽怪异,就要澄清风俗,革新政治,如果“不改,乃成凶也”。这些评语具有强烈的暗示和指向性,实为借古喻今。
其三,道德衰颓。
干宝认为,古先哲王以德化人,以德治国,“故其民有见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义,又况可奋臂大呼,聚之以干纪作乱之事乎?”然而,西晋末年以来,“民不见德,唯乱是闻,朝为伊周,夕为桀跖,善恶陷于成败,毁誉胁于势利”[14](卷一二七)。像《搜神记》中的蒋子文,生前好喝酒,喜欢女色,轻薄放纵没有节制,死后仍索取无度,官府不仅无力制止,反而“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侯,次弟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缓,为立庙堂”[1](卷五)。这说明官府是道德衰颓的推波助澜者。
其四,风俗淫僻。
社会风俗为社会文化群体精神的存在情形,并与统治阶级的导向、政治状况的好坏紧密联系,所以干宝认为,“盖民情风教,国家安危之本也”[18](卷一二七)。干宝所处的时代,政局复杂动荡,民族斗争剧烈,社会混乱无序,这也使得自汉以来社会风俗发生深刻的变革。[15]这些变革在具有正统思想的干宝看来,却是“风俗淫僻,耻尚失所”[14]。一是衣冠服饰的变化。依儒家的说法,衣冠服饰的来历可以追溯到圣人:“圣人见鸟兽容貌,草木英华,始创衣冠”(《晋书》卷二十五《舆服志》),可谓神圣之极。同时,衣冠服饰还是等级制度的重要表征:“《周礼》,弁师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自后王之制爰及庶人,各有等差。”(《晋书》卷二十五《舆服志》)因此,服饰饮食成为华夏文明区别与蛮夷戎狄的表徵。然而礼教失效、思想解放、王朝更迭频繁、民族文化交融等诸种社会历史因素使得魏晋以来风俗巨变。干宝将这些变化与乱世、衰世、末世相联系。如在卷七中,干宝评论晋武帝泰始初年,衣服上身简单下身讲究,穿衣服的都把上衣掩进下衣里面,“此君衰弱、臣放纵之象也”。又说晋太康年间,妇女都穿方头木屐,和男人没有差别,“此贾后专妒之徵也。”晋太康年间,全国用毛毡做头巾和腰带、裤口,以至于老百姓都互相开玩笑说:“中国其必为胡所破也。”又晋惠帝元康年间,妇女的服饰有五件是兵器。“盖妖之甚者也”。二是饮食上的变化。如胡床、貂槃本是翟族的用具,羌煮、貊炙是翟族的食品,但从晋武帝泰始年间以来,中原地区都流行这些东西,此“戎翟侵中国之前兆也”。三是伤风败俗。干宝曾在《晋纪总论》中指陈当时国风民俗败坏的情景,颇为痛心疾首。在《搜神记》中,干宝则将伤风败俗与国破君亡相联系。如说晋惠帝元康年间,贵族子弟披散头发,赤裸身体,聚在一起饮酒,互相玩弄婢女和妾,这是“胡、狄侵中国之萌也”[1](卷七)。
其五,巫术、谶纬和佛道盛行。
巫术是人类社会发展初始阶段形成的一种原始宗教形态,鲁迅先生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5](24)干宝所处的两晋时代正是这样一种情形。在当时乱世中,人力无法完全支配和控制个人、家族乃至王朝的前途和命运,而儒家思想又不能有效化解时人的精神困惑,人们只好诉诸巫术、谶纬和佛、道,因为它们不仅满足了时人的共同精神需求,也抚慰着动乱社会里各阶层人士的心灵。因此,在《搜神记》中,可见大量有关巫术、谶纬和佛教、道教的故事,这实际上是当时儒学衰落、思想多元,以及时人精神和心理状态的真实反映。
四、《搜神记》中的鬼神及“神道”的意义
《搜神记》中的鬼神承载着时人对政治清明、道德纯厚以及自由、平等、爱情的渴望和追求,也折射出时人所憎恶的各种社会乱象。因此,鬼神在魏晋时的重新泛起,源于时人的现实需求,《搜神记》中的鬼神及“神道”的价值也在此体现出来。
首先,干宝通过对鬼神之事的记载,“发明神道之不诬”,给乱世中无数绝望的人们以生存的希望。正如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人事中有一片广大的领域,非科学所能用武之地。它不能消除疾病和朽腐,它不能抵抗死亡,它不能有效地增加人和环境间的和谐,它更不能确立人和人间的良好关系。”[16](48)只有鬼神能够施以神力和神术,将人们从对现实的普遍绝望中拯救出来。对于人们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望和理想,鬼神就作为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权威力量,使那些美好愿望和理想得到非凡的体现。例如那些被压迫、被侮辱的人们在生前的冤屈与无助通过死后为鬼,或借助神力、神术进行复仇,这就使得有类似经历的活着的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毫无出路的情感得到痛快淋漓的发泄。同时,这也消解了人民潜在的叛逆倾向,将它引导至统治阶级所期待的方向。
其次,《搜神记》中的鬼神及“神道”是具有弥补功能的精神安慰剂。它“自有其另成一格的功能,这功能和传统与信仰的性质,文化的绵续,老幼的关系,以及人类对于过去的态度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其功能在于追溯到一种更高尚,更美满,更超自然的,和更有实效的原始事件,作为社会传统的起源,而加强这传统力量,并赋与它以更大的价值和地位”[16](73)。通过对鬼神及“神道”体现出来的原始精神要素和古朴道德的重温,弥补了底层百姓生活中诸多缺憾和不足,使“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廉耻笃于家闾,邪僻销于胸怀”[14],“神道设教”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再次,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借助鬼神超自然的力量和神道强大的教化功能,提供给现实社会以正统道德价值的模式,“故众知向方,皆乐其生而哀其死,悦其教而安其俗”[14],俯首听从命运和秩序的安排。同时,对于坚守正统价值取向的干宝而言,相信并传播这种神道,还有更重要的意义,这就是通过阐发和证明“神道之不诬”,一方面把现存的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加以神圣化和合法化,另一方面,为统治阶级寻找政治权力和道德权威的理论依据。这样,源自远古的鬼神和“神道”观念通过《搜神记》活灵活现的阐发和证明,进一步政治化、伦理化和功利化了。
[1][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Z].中华书局,1979.
[2]杨淑鹏.20世纪《搜神记》研究综述[J].晋中学院学报,2010,(5).沈星怡.近十年《搜神记》研究综析[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
[3][东汉]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辞海[Z].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5]鲁迅撰,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东汉]王充撰,袁华忠,方家常译注.论衡全译·论死[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7][晋]杨泉.物理论[A].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魏晋隋唐之部·上)[Z].中华书局,1982.[8][晋]干宝.驳招魂葬议[A].严可均辑.全晋文[C],卷一百二十七.中华书局,1958.
[9]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下)[M].中华书局,1984.
[10]宋志明,向世陵,姜日天.中国古代哲学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11]王福栋,王中良.论《搜神记》中的现实题材故事[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9,(5).
[12]李定文.“神道设教”诸说考辨[J].福建论坛,2008,(7).
[13]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A].宗白华选集[C].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14][晋]干宝.晋纪总论[A].严可均辑.全晋文[C],卷一百二十七.中华书局,1958.
[15]孔毅.论葛洪《抱朴子·外篇》的社会风俗批判思想[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9,(4).
[16][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