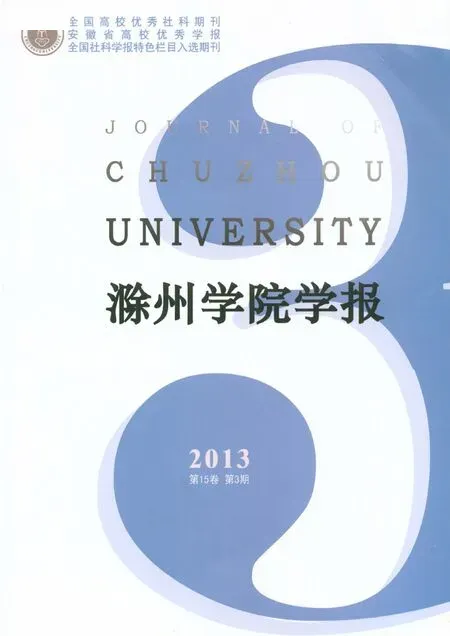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女性形象
2013-04-01宿美丽
宿美丽
知识女性,指知识分子中的女性群体。一般说来,接受高等教育是成为知识分子的首要前提。所以,知识分子中女性数量的增加,有赖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增长。二十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不断增长,层次不断提高,1949年全国女大学生仅有2.32万人,不足在校生总人数的20%,到1951年就达到了23.4%,经历了文革的高等教育断层之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数量自七八十年代开始快速递增,到1993年达到了85.2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33.6%。随着女大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知识分子中的女性队伍不断扩大,蔚为壮观,女性知识分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很自然的,这一群体走进作家的视野,成为作家审视、表现、思考的对象和主体。但是,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受社会思潮的影响,描写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的作品屈指可数,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女性知识分子才成为不少作家关注、描写的对象,使知识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本文考察的对象,是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女性,从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开始,知识女性以主角的身份,以各种不同的姿态,普遍的走上了文学舞台,直到九十年代,一度占据了舞台的中心。
一、八十年代的知识女性
八十年代的知识女性,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一部分,在思想启蒙的社会背景下,高扬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传统知识分子的道统,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实践和追求事业的动力,成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骨干和中坚。《淡淡的晨雾》中的梅玫,自觉和人民站在一起,成为反封建的勇士。《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是医院手术做得最漂亮的眼科大夫,是受病人信任的好医生;好朋友姜亚芬甘当绿叶,甘当副手,二人配合默契,成为手术室的最佳搭档。《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钟雨,是受人欢迎的女作家,一位和她熟悉的作家这样跟她开玩笑:“光看你的作品,人家就会爱上你的!”一句玩笑话也能反映她取得的成就。《方舟》中的曹荆华、梁倩、柳泉,各有专长,荆华从事理论工作,写的论文引起了社会争鸣;梁倩是电影导演,成功执导了影片;柳泉精通外语,受到外国客人的称赞。《祖母绿》中的曾令儿,是出色的电脑软件专家。这些知识女性,自觉肩负起时代、社会赋予的使命,成为当时的先锋和楷模,这是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兴起的女性批评中,梅玫和陆文婷因为缺少性别意识而被人淡忘,但在一个百废待兴的启蒙时代,她们哪里来得及关注自身的小我呢?只能自觉不自觉的成为时代浪潮中的一滴水,汇入浩瀚的海洋之中。恰恰因为这一点,她们才具有了崇高、坚贞的品格。
作家同样认识到两性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生理上的,更表现为文化传统的内在要求。身为女性,长期的文化传统要求她们首先扮演好母亲、妻子的家庭角色,知识女性身为知识分子的一员,在社会角色上有与男子同样的价值需求,回到家里,她们要成为贤妻慈母。所以,她们身上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她们必须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能取得和男子同样的成功。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知识女性开始了对自身性别身份的思考。梅玫想在专业上有所突破,来自丈夫的阻力使她的想法不能变成现实,最后,她选择了离开。陆文婷长期家庭事业两肩挑,虽有善解人意的丈夫的扶持,但终因过度透支,倒在了下班回家的路上。钟雨、曾令儿是单身母亲。曹荆华、梁倩、柳泉是离婚女人,她们不善持家,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妻子,一心追求事业的成功。梅玫的离开带有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的政治色彩;陆文婷则已经认识到自己身上母亲和妻子的责任;钟雨、曾令儿不能说不是称职的母亲。而到了荆华、梁倩、柳泉这里,妻子身份的失去导致她们在追求事业的道路上屡屡受挫。从这些女子的遭遇中可见女性追求事业的艰难,《方舟》的题记宣称:“你将格外的不幸,因为你是女人”,一语道出了女性的艰辛。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女性意识一旦凸显出来,女性发现自身的重担并没有减轻,反而在兼顾家庭和事业的道路上步履维艰。
但八十年代毕竟是激情飞扬的时代。尽管艰难,她们甘愿奉献。天然的母性决定了她们的奉献和牺牲精神,这种女性与生俱来的品性被冠以爱的名称。八十年代的知识女性多被塑造成爱与美的化身。她们慷慨的施予爱,爱又创造了女性本身。梅玫美在青春、热情;陆文婷、姜亚芬美在宽厚、无私、正直,就连作品中的那个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也并非面目可憎。在陆文婷眼中的秦波:“(五十多岁)眉清目秀。染过的黑发经理发师稍稍冷烫过,既蓬松又不显轻浮时髦,十分得体。身上穿的是普通式样的干部服,但质地考究,剪裁合身,显得很有精神。”读者又怎能否认她的美呢?尤其是她能知错就改。陆文婷、姜亚芬、秦波身上的夫妻之情、同志之谊充溢作品,使这部八十年的问题小说几乎变成了一曲爱的赞歌。钟雨用世俗的标准衡量不能叫漂亮,她美在气质淡雅、从容淡定,象一副水墨山水画。她对一份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坚守了二十年,成为那个精神至上时代的典型。苦难和岁月都不曾在曾令儿身上留下痕迹,她安闲自若,身材窈窕,连理发师和昔日的情敌都望而叹佩。她从对初恋的坚守出发,感悟到令她心潮激荡不已和无穷眷恋的已非初恋情人,而是她度过如许美好年华的大地,以及她慷慨献出自己所有的、那颗无愧的心。她以无穷思爱的力量完成了对爱的意义的升华,成为理想化的爱与美的典范[1]。相比之下,三个组成方舟之家的离婚女人则显得有些另类:美丽、贤淑、温柔这些传统女性的特质与她们格格不入,她们粗粝甚至强悍,带着雄化的特征,但是,她们依然相信爱情,只是希望将爱的权利掌握在自己手中;她们不把美片面理解为“女为悦己者容”,而是希望心与心的碰撞与交流。这是对美的更深层次的理解,是直面生活痛苦之后对爱的召唤。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知识女性对真爱的固守——爱是建立在两性平等的基础上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八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知识女性持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被视为崇高理想的化身,并逐渐认清女性的双重角色身份,女性意识不断凸出。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退潮,知识女性不再是文学追踪的对象;从1987年开始的新写实小说,重在表现人的精神的琐屑化、平面化、庸常化,排斥崇高、理想等字眼。因此,与八十年代前期相比,八十年代后期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女性逐渐淡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批工商界的成功女性,或被称为女强人、白领,逐渐成为文学表现的对象和中心。
二、九十年代的知识女性
综观九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此一时期的知识女性更多的承载着女性意义的话题,与八十年代的知识女性相比,她们展示了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事业与家庭的矛盾,婚姻与爱情的冲突,在自我与本我的交战中落败。理想褪色,爱情失意,在自我的小圈子里自怨自艾,甚至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无限膨胀的欲望符号。
方方笔下的星子对市民趣味表现了有限度的认同;池莉笔下的宜欣表面上看来衣着得体,谈吐文雅,气质脱俗,在暴发户和小市民面前感觉良好,鹤立鸡群,却和小市民一样对爱情、婚姻充满了功利的打算;《一地鸡毛》中,小林妻子对世俗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已经全面认同并实践。新写实作家更多的从普通人的角度去观察知识女性,退去精英知识分子的光环,发现她们人性的弱点。她们对于物质的追求、对平庸的认同,预示着精神家园的荒芜。
庄严、崇高的理想褪色之后,来自女性本能的爱的要求,她们把爱当做了生命的全部来追求,希望从爱的追求中获得身心的满足。但是,在商业化的包装机制中,知识女性对真爱的追求要么陷入第三者、婚外情的尴尬境地:如铁凝的《无雨之城》中的女记者,霍达的《未穿的红嫁衣》中的女教师都属此类;要么陷入追逐异性的游戏中:如张欣在近于通俗文本的“都市系列”中,将“白领女性”的登场、出演以及出演的尴尬作了浅近而不失精细的描述[2],这些白领表面上看来情爱潇洒,实际上被权力金钱物化;要么沦为男权文化下被看的对象,甚至成为一种都市欲望的符号:如身体写作潮流中的重要作品《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很少有评论者将她视为知识女性,确实,她除了一个大学生的头衔之外,其余都是关于女性成长、独特体验的代言者,大学只是给她提供了一个更为宽松的体验的场所。《我爱比尔》中的阿三是学绘画的大学生,却因为爱上了美国人比尔走上了卖淫的道路,在感情困惑、身体欲望的泥潭里越陷越深,迷失了自我。身体的解放带来的快感是短暂的,情感上、身体上的受伤者最终却是女性。
即使在正常的爱情、婚姻当中,我们也很难发现像八十年代的曾令儿那样因爱而获得充盈、乃至升华的女性形象。《红蘑菇》中的梦白是一位解放了的知识妇女,已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应有权利,但她内心盘桓着的依然是脆弱的依赖性,她对丈夫的自私、虚伪有清醒的认识,却因为丈夫身上的教授、文雅、体面这些能满足她面子的东西而维持着家的完整。《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中的青年女教师和老舞蹈家更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看着内心龌龊的男子的无耻表演,这种道德训诫的两性对立的姿态使她们获得心理上的快感,却没有得到爱的满足[3]。《厨房》中的枝子是一位事业成功的商业女性。她在年轻气盛的时候曾十分厌恶日常的婚姻家庭生活,于是“她义无反顾、抛雏别夫,逃离围城,走了”,然而,事业成功以后,却又开始“怀念那个遥远的家中厨房,厨房里一团橘黄色的温暖灯光”。“爱上一个人,组成一个家,共同拥有一个厨房,这就是她目前的心愿。[4]”八十年代呼风唤雨的女强人,到九十年代渴望回归家庭生活。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女人的一厢情愿。爱非其人、想爱而不得,女性虚弱的自尊和矛盾心理显露无疑。作家对女性的剖析是严厉的,她们发现了在爱和婚姻背后女性的传统无意识的脆弱和爱的矛盾。这种女性的集体无意识比八十年代的金乃文更具有隐蔽性和传承性。金乃文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女性,自觉的皈依、顺从贞妇烈女的封建道德观念,解决她困境的途径有许多条,作家清晰的摆在人们面前。而面对梦白、枝子的困扰和困惑,劝诫或者高喊几句妇女解放的口号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在妇女解放的背后,中国社会隐匿着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文化观念,织成了潜形的巨大网络,无处不在地束缚着人们的意识与思考,为当代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带来种种无法言说的烦恼。谁又能超然独立于文化之外呢?智慧的作家们也无法给出答案。
对异性之爱的幻想落空了,知识女性能否从同性世界中寻找爱呢?八十年代由荆华、梁倩、柳泉组成的姐妹方舟已经倾覆。九十年代的知识女性试图再次寻求突破。《相聚梁山泊》中9个优秀的女性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均有相当的建树,她们产生了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自豪感,她们在聚会时大声称兄道弟,以一种对男性称谓的僭越借用来对男权进行某种意义上的颠覆消解。就在她们沉迷于“兄弟”情谊般的酒酣耳热之际,柳芭的情人——位高大俊朗的男士出现在她们面前的时候,刚刚还壮士断腕的姐妹豪情马上就烟消云散了。她们的女性同盟“梁山聚义”被一位男士的出场就轻而易举地消解得了无痕迹[5]。《弟兄们》中“三个已婚的美专进修女学生”“样样事情做得比男人出色”,三位女性均以男性称谓方式按照年龄顺序称为老大、老二、老三,并把自己的丈夫分别称为“老大家的”“老二家的”“老三家的”,来表明三位女性不甘居于第二性的反男权立场。但是离开了学校这个特定环境,她们之间那兄弟般的情谊方舟也就迅速覆没了。这标志着“她们在本能的母性妻性的夹击下终于溃败”。女性的同性之爱可以看做是女性一种自救的方式,但作家暗示我们女性用同性爱的方式拒绝男性来寻求女性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讲,女性拒绝男性就是拒绝人类的生存。女性拒绝不了男性,而男性也拒绝不了女性,这是人的本质使然。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知识女性的变化不仅折射了社会的变化,也显示了作家对社会的深度思考与把握。八十年代初期,知识女性还没有来得及辨识自己的女性角色便站到了社会的前沿,她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勇于奉献的传统结合在一起,升华了自身的社会形象,成为社会精英的代表之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知识一度贬值,社会精英风光不再,于是,对平凡乃至庸俗的认同与实践成为作家津津乐道的对象和视角。但人生不仅有安稳的一面,更有飞翔的一面。当作家们认同并理解乃至欣赏这种安稳时,读者们读到的是一地鸡毛、头皮屑这些琐碎、琐屑的事实,而不是生活的态度和意义。人的存在不仅是物质的,也是文化的、精神的。精神的荒漠,价值的缺失表面上看来是女性的解放,实则是对女性的再次伤害。《我爱比尔》中的阿三,从才华横溢的美院大学生到卖淫女到囚犯,一直没有找到自我的文化定位,直到在逃跑的途中发现了柴堆角落里遗失的处女蛋,才忍不住痛哭了起来。这个结尾意味着她将重新寻找自我、重新出发。于是在九十年代的知识女性当中,很大一部分女性选择了传统文化意义下的女性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不管表面上她们是多么独立、自强。虽然有的作家对此调侃乃至痛惜,但不得不承认文化传统的强大作用。九十年代张洁的知识女性形象虽然颠覆传统,以反文化的面目出现,实则依然是以传统女性为参照,作为传统女性的对立面来设计的。
从八十年代精英分子的一员,到九十年代对传统价值观的皈依,知识女性该如何在强大的男权文化传统中找准定位,知识女性们还在寻找,作家们也没有给出答案。但是当时的知识女性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对自身性别身份的反思与反叛,无论有无出路,无疑给了生活在当下的知识女性以深刻的启迪。
[1] 荒 林.女性的自觉与局限——张洁小说知识女性形象[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2).
[2] 唐利群.飞升与坠落: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悖论[N].文艺报,1999-11-11.
[3] 王红旗.九十年代女性小说中的女性形象[EB/OL].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10594.
[4] 王丽霞.性别神话的坍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写作批判[J].当代作家评论,2005(1).
[5] 黄柏刚.徐坤创作转型与女性主义文学式微的动因管窥[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