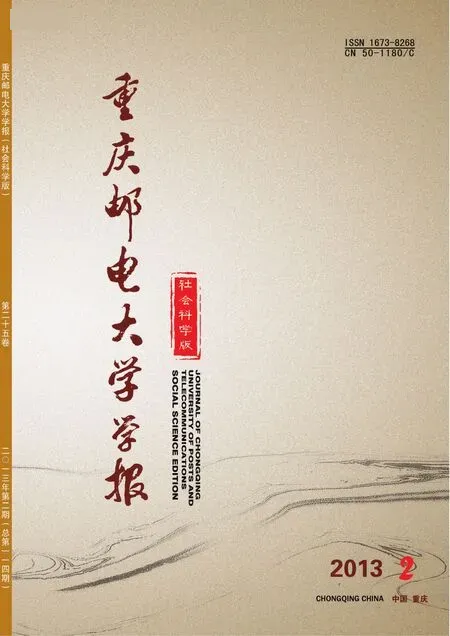华裔男性刻板印象的解构与英雄本色的重构*
2013-03-31汪凡凡
汪凡凡
(信阳师范学院,河南 信阳464000)
中西方父子关系内涵有着巨大差异。中国的父子关系神圣而庄严,与家族、民族的传承与发展紧密相连,不涉及个体情感、意志、人性等方面的需求,注重家庭伦理观,强调父对子的绝对权威和子对父的绝对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父子关系颇为人性化,充满了原欲的对立与冲突,强调个体意志、尊严和平等对话,表现了一种保持或超越生命本原的渴求。华裔美国男性作家们,通过对中西文化传统的吸收与变异,展示了华裔父子关系的深刻而独特内涵,表现了父子间的血缘维系以及文化和精神的传承关系。他们通过追溯与再现华裔父辈在美国的血泪史与奋斗史,重构为美国主流社会所隐没的华裔光辉历史,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追寻华人英雄气质,重塑华裔男性形象和英雄传统。
一、被“阉割”或“白化”的血缘之父
华裔父子关系可以分为“血缘父子”与“精神父子”两种类型。“血缘父子”是指有血缘关系的父与子;而“精神父子”没有血缘关系,“精神父亲”或者有着具体形象,即象征着某种精神的父系人物,或者代表一种纯粹的精神及父系传统。在美国主流强势文化的“凝视”下,华裔现实生活中的血缘父亲与中华文化传统中强大的父亲形象不同,他们劳碌而卑微,暗淡而失落,被“阉割”或被“白化”,无力为“儿子”树立阳刚的父亲形象。因此,华裔男性作家们往往通过追忆和挖掘自己父系祖辈挖矿山、修铁路等建设美国的辉煌历史,来展现华裔男性的阳刚之气,或者从中国文学文化经典中寻觅华裔男儿的骁勇善战,以此建立华裔男性的英雄传统。
华裔美国女性作家笔下的父亲形象大都是缺席、沉默、失声、“被阉割”的,这既是女性颠覆“男权”的一种写作策略,也真实反映了华裔男性在美国被去势、被“女性化”的现状。汤婷婷在《中国佬》中讲述了唐敖的美国奇遇,深刻揭露了华裔男性遭受的不人道待遇。唐敖为了寻找金山,漂洋过海,却来到“女儿国”,当即就被放哨的女子逮捕。接着,他被这些女子涂粉、穿耳、缠脚,遭受种种“变性”的折磨。唐敖的遭遇隐喻了所有华裔父亲的共同命运。在所谓的“自由”之都,他们并未找到梦中的“金山”和实现“美国梦”,却被迫从事卑微而辛劳的“女性化”职业——洗衣工,这是当时华人男子的普遍职业。美国的种族、阶级歧视和压迫牢牢禁锢了他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严重扭曲了他们的性别角色,致使华裔男性成为美国主流文学及大众文化中胆小懦弱、缺乏阳刚之气的男性代言人。“刻板印象”(stereotype)意指“个人或某个群体对他人或别的群体持有的过分简单化的、公式化的理解、观点或形象”[1]32。刻板印象往往因其过于简单化而影响人们对他人或群体的全面客观认识。露琪·卢卡·卡娃理-索扎指出:“偏见和种族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人类倾向于制造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赋予了一个群体一些特殊属性。”[1]34无论是白人的“沉默仆人”甘加丁,还是臃肿、口齿不清的“娘娘腔”陈查理,亦或是残忍而狡诈的“黄祸”邪魔付满洲等,华裔男性始终未能摆脱被丑化、扭曲和“变性”的厄运,被赋予了种族歧视性的刻板印象。对此,金惠经指出,在美国主流文化对华裔形象的再现中,“亚裔男性被描写为没有任何性能力,而亚裔女性除了性能力以外什么也没有,其目的都是为了证明白人男子的阳刚之气”[1]40。于是出现了两种极端的再现,美国白人为维护对于有色人种生理维度的优越性,将非裔男性再现为动物般性暴力倾向者,而华裔男性则被残酷地“阉割”。生长于美国的华裔后代们大多接受了美国的意识形态,已被美国的“内部殖民”思想俘虏,根本无法认同和接受现实中低下而狼狈的父亲。
在华裔美国文学中,除了被“阉割”的父亲,还有在美国主流文化冲击中“白化”的父亲。赵健秀在《甘加丁之路》中,以一个为英国殖民者驯化的印度民族叛徒——仆人甘加丁为原型,塑造了华裔父亲关朗曼这一形象,其一生都在追寻这条“甘加丁之路”。关朗曼是好莱坞跑龙套的小演员,为了成为美国人,他愿意扮演任何角色,甚至是光屁股婴儿。他毕生最大的愿望是饰演“陈查理”——美国白人作家比格斯塑造的华人侦探形象。看似英勇的大侦探、所谓的华人英雄,其实带有明显的白人主流社会对华人男子的刻板印象:一个漫画似的“臃肿的、咬文嚼字却又口齿不清的、娘娘腔似的小侦探”[2]57。正是这个为白人臆想的具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角色,却成为关朗曼一生追逐的理想。关朗曼是甘加丁式的“沉默的仆人”,为白人利益不惜牺牲自己;一个彻底“白化”的、同化的华人;一个甘愿为白人践踏、丧失尊严的“父亲”形象。关朗曼为自己的“白化”欣喜若狂,并积极拥抱美国的文化“同化主义”:“圣父以完美的白种男人的形象献出了自己的儿子,让他领着白人走上了通向赎救的正途……于是白人又以完美的华裔美国人的形象献出了一个儿子,让他带领黄种人建筑通向接纳和同化的大路。啊,多美妙的同化”[2]60。“同化主义”的实质就是“白化”。美国的“同化”政策要求凡与美国主流文化相悖的任何文化,都必须被削弱乃至灭绝,凡与主旋律不和之音必须被消解。同化了的华裔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附属品,陷入“失语”状态,迷失了自我,成为白人社会沉默无声的仆人。李健孙的《支那崽》也塑造了一位典型的“白化”父亲形象。丁凯的父亲丁国凡本是英勇的国民党军官,可是在美国的事业和生活极不成功。他娶了一位白人妻子,渴望着被同化、被“白化”,全心全意地想成为美国人,梦想获得美国式的成功,并竭力抹杀自己的中国属性。婚后的父亲受制于、服从于妻子艾德娜。面对艾德娜在家里推行文化沙文主义,仇视中国文化并迫使他们与中国文化决裂,进而对丁凯姐弟施加语言及肢体暴力,父亲却始终保持沉默,无动于衷,致使子女们在精神和现实层面都深陷困境。艾德娜的种种“同化”思想,已经“内化”浸入父亲的灵魂,他无言地支持了白人妻子对中国文化的践踏和对儿女们的虐待,放弃了华裔文化身份这一生存根基,注定他将在美国飘摇终老,这象征着弱势的华裔文化已经臣服于强霸的美国主流文化。
二、对理想中“精神之父”的追寻
在《天堂树》中,徐宗雄以“天堂树”隐喻了华裔移民不畏困难与艰险,在美国成功地移植、生根、生长、开花、结果和世代繁衍。主人公陈雨津年少时父母相继离世,成了孤儿。他通过讲故事、书信、想象与梦幻等相结合的形式,追忆着父系祖辈在美国的血泪史、奋斗史与英雄史,彰显了华人参与美国国家建设的光荣业绩,恢复了被压抑的民族记忆,带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陈雨津的曾祖父曾参与修建穿越内华达山脉的美国铁路,见证了华裔劳工为美国早期国家建设作出的巨大牺牲与不朽贡献。那时,许多华工被冻死在铁路沿线,尸横遍野,惨不忍睹。然而,这些“开国功臣”们并未得到任何回报,反遭白人嫉恨和遣散,致使多数华人在西部流浪;“排华”法案的通过,更使华工遭到白人的排斥、拘捕和袭击,甚至是驱逐和屠杀。虽然成千上万的华人参与建造了美国大铁路,但美国正史试图压制和隐没这段历史,甚至把他们刻画为缺乏阳刚之气的洗衣男工。《天堂树》以颠覆和解构正史的方式揭示出白人主流社会持有的华人刻板印象的荒谬和恶意。曾祖父被迫回到旧金山的唐人街,过着穷困潦倒、孤苦无依的生活。对美国失去信心的曾祖父把唯一的儿子——陈雨津的祖父送回中国抚养长大。成年后的祖父在天使岛经历了种种非人待遇,差点在那里丧命,最后终于渡过重重难关才回到美国。他参加过美国横贯公路的建造,学会了骑马,是职业“放马人”。这一职业表现了祖父的男儿雄风,颠覆了华裔父亲只能从事洗衣、烹饪等“女性化”职业的刻板印象。陈雨津的父亲也继承了父系的英雄传统。父亲是一位出色的海军工程师,参加过“二战”,也是一位优秀的田径运动员和游泳健将。父亲有着一种“独特的种族傲慢……他的传统和历史像伤痕般根深蒂固,他只记得他父亲和祖父的悲痛,并从那些孤独男子的生命中养育自己的感性”[3]。对于陈雨津痴迷于飞机、汽车、火车等事物,父亲大力支持和鼓励,因为这些是华裔男孩儿的精神食粮。对英雄主义的热爱,使陈雨津最终也成为运动健将。在追寻父系英雄传统时,陈雨津迷失于现实与梦幻之间。他时而变成建造铁路的曾祖父,时而变成了在天使岛遭受囚禁的祖父,时而又回到关岛与父亲在一起。通过土生华裔对父系祖辈悲怆经历的追忆与缅怀,《天堂树》创造出了独特的族裔感性,它与美国大地血脉相连,感伤却阳刚,使美国华裔一生引以为豪。《天堂树》对华裔父系英雄传统的追寻与挖掘无疑具有深刻的历史、政治和文化隐喻。其中陈雨津父系祖辈所从事的铁路工人、放马人、海军工程师等“男性化”职业,以及陈雨津对于体育运动的热爱,颠覆了华裔男性“女性化”的刻板形象,但是在界定华裔男儿本色时,仍然受制于白人的刻板印象和主流文化的束缚。
处于中美双重文化背景下的华裔,由于受到白人的种族、阶级歧视以及对其历史和文化的漠视,华裔美国人始终未能在美国主流历史和文学中获得公正的地位,更不用说阐释和书写自己的真实历史。白人一直将有色人种视为“他者”,白人主导的权力话语可以借助意识形态等国家机器蓄意歪曲、丑化华人形象,压制、隐没华人历史。而追寻美国华裔历史和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是重塑华裔男性气质的最主要因素。赵健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根溯源,并从这些古典名著所宣扬的英雄主义中汲取力量,重振华裔父系雄风,建构华人英雄形象。赵健秀的《唐老亚》将华裔父辈们修建美国铁路的光辉历史与《三国演义》中关公的英雄故事结合起来,将关公定为重构的华人英雄形象。在唐老亚的梦境中,关姓工头不畏强暴,有勇有谋,在与白人经理科洛克的谈判中屡占上风,他带领华工挺过严冬,并用一天时间打破了铺设铁轨的世界纪录。唐老亚观察着关姓工头,“像父亲的眼睛,但更胜于父亲的眼睛”[4]22,更像京剧中关公那双“可以杀人的眼睛”[4]22。他认定关姓工头就是关公的化身。梦醒时分,唐老亚注视着关公像,“关公……他有一双与梦中的铁路工人领班一模一样的眼睛”[4]22。唐老亚的父亲是唐人街的一位乐于助人的厨师,而厨师被美国主流视为“女性化”的职业,因此唐老亚认为父亲缺乏阳刚之气,就连父亲本人也认为自己不能给儿子树立好的榜样,于是经常用儒家英雄主义传统教育唐老亚。唐老亚感到唐人街里关公的影子无处不在,并最终把关公作为父系形象的认同,从而造就了理想的“精神父亲”。受到美国强大的“内部殖民”教育,受制于华人刻板印象和主流文化的束缚,华裔美国男孩唐老亚从小就对生活充满抱怨,异常排斥、厌恶与中国有关的一切。唐老亚内化了美国白人对华人的刻板印象,认同白人历史老师米恩莱特对中国人性格的歪曲性描述:生性胆怯、内向、懒惰,缺乏自信心和进取心。这些特征与唐老亚的美国身份强烈冲突,因此他以自己的中国血统为耻,抵触自己的民族、历史与文化。对中国的排斥与其内化美国主流价值观的过程是一致的。唐老亚从小就被美国白人教育所同化,表现出被殖民者的性格特征。失去历史意味着失去身份,并且灭绝就会临近。苏珊娜·林纳德认为:被遗忘的过去可以通过想象而重新获得,以此便可以重建曾经被压制和湮没的族裔历史。唐老亚的身份危机源于对华裔祖先男性气质的无知,他的梦境象征了所有美国华裔的集体无意识。华裔美国人艰难的生存和生活经历转化为他们心灵深处的潜意识,这种受压抑的记忆始终伴随着华裔,并成为华裔的民族记忆和集体潜意识,而这种被压抑的记忆有朝一日必定重返。在华裔的身份濒临灭绝之时,这一潜藏的集体历史记忆不期而至,呼唤着华裔书写自我历史,追求民主政治权利。这一寻根之梦以及受到父亲、伯父等男性的华人文化传统的引导和影响,唐老亚认识了在白人中心权力话语下隐没的华裔美国人的光辉业绩,不再厌恶自己的华裔身份,甚至开始质疑歪曲华裔形象的白人老师。唐老亚从蔑视、抵制、仇恨中国文化到认识、崇拜中国文化中的战斗型英雄人物,并从中汲取成长的力量。《唐老亚》以重构华裔历史的方式彻底颠覆了主流历史,以非理性的梦境再记忆、断续地重构华裔父辈最初的被否定、被湮灭的美国历史经验,建构了华裔父亲的新形象。关公形象所蕴含的忠诚与英勇体现了华人的伟大人格,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意象,是美国华裔的“精神之父”,这一形象有力地驳斥了白人种族主义者捏造的阴柔、懦弱、堕落的华人刻板印象。赵健秀一直找寻的理想父亲形象在关公身上得以补偿。
美国人对暴力有着极强的认同感。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斯洛特金曾指出,美国的国民性格是在早期欧洲移民的暴力中形成的。早期移民不断地与严酷的自然环境及美洲大陆的土著居民作斗争,因此暴力既是美国开疆拓土的重要手段,也是美国国民性格形成的重要原因。早期移民通过对他者或异族施暴以确立美国身份,尤其是男性身份。暴力也成为美国同化异族文化的特权,暴力同化的目的是消灭文化差异,使边缘文化臣服于主流文化;为确保暴力的合理性,他们又给暴力披上了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华丽外衣。正如美国作家詹姆斯·比德文所言:“在美国,暴力和英雄主义是等同的,当然,黑人在这一点上除外。”[5]79美国文化中的英雄主义与暴力统一,英雄主义必然伴随着暴力,唯有暴力才能够完成英雄身份的建构。后来,美国移民也逐步接受美国的暴力价值观,认同了“通过暴力建立再生的神话”[5]65,暴力成为实现“美国梦”和美国人身份建构的手段。“儿子”们崇拜、追随的“精神父亲”都是充满阳刚与力量的英雄男子形象,与现实中“隐退”的血缘父亲形成鲜明对比。在华裔男性化建构过程中,暴力成了有力手段。为了找到华裔男子独有的感性,重塑华裔父系英雄传统,赵健秀把《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李逵塑造成了一个“嗜血的、杀气腾腾的疯子”[4]55。而在《甘加丁之路》中,他甚至为唐人街的“儿子”们取名为本尼迪克特·汉、尤利西斯·关、戈迪·张,这来源于《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的“桃源三结义”故事,也从侧面表明赵健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好战”一脉的青睐,只是他走向了极端。尤利西斯·关是关朗曼的小儿子,他痛恨美国的种族歧视,鄙视父亲所追求的“白化”理想,采取了挑衅、好斗的方式反抗美国种族主义和文化同化,坚决维护华人尊严和民族特性。在《支那崽》中,由于“白化”父亲的怂恿、白人继母的精神和身体暴力、锅柄街黑人男孩们的拳脚相加,饱受欺凌的绝望的丁凯从小就信奉“暴力”哲学。基督教青年会的三位拳击教练成为他认同的“精神之父”。他们教给丁凯拳击技术和“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使他渐渐成长为街斗英雄。丁凯找寻“精神之父”的过程也是背弃自身民族文化的过程,最终成为丧失文化根基的“孤儿”,这是痛苦和无奈的。在随后的《荣誉与责任》中,丁凯成为西点军校最具阳刚之气的美国人之一。依附于美国主流文化的暴力认同,李健孙用暴力让主人公丁凯完成了男性身份和非“他者”身份的建构。
为反击和颠覆美国白人主流强加的带有种族偏见与歧视的华裔男性刻板印象,作为“文化民族主义”战士的华裔美国男作家们塑造出了英勇好战的华裔男性形象,甚至不惜以扭曲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为代价。他们宣扬战斗为儒家文化之精华,认为“我们生来就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正义而战,所有的艺术都是尚武的艺术。写作就是战斗……生活就是战斗,就是斗争”[5]90,这一矫枉过正的认识恰恰陷入了美国“内部殖民”的话语体系。阿尔都塞指出:“当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作为常识被整合进了被统治者的意识之中后,会在被统治阶级继续盛行”[5]103。在文化协调与一体化进程中,华裔在性和性别诸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白人文化与价值观。他们在对抗美国种族主义歧视时,并未挑战主流男性气质定义,却默认了白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了西方好战型、攻击型、暴力型英雄传统。在他们笔下,关公、李逵等传统英雄形象的代表性美德并未得以展示,而只是大力渲染这些人物强悍、好战的行为,并将博大而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化甚至扭曲了。他们没有体现出华裔身份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因此无法建构出可以替代的华裔男性气质,而“儿子”们所追寻和认同的理想父亲并非中国主流文化中儒雅的、有正义感和道德感的父亲形象,不过是“中国形,美国神”的“精神之父”。
三、结 语
通过梳理和分析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不同类型的父子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华裔男性作家在反对主流意识形态强加于华人男子的刻板印象和偏见、重构华裔父系传统和英雄形象等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唯有建构一个能够代表中华文化传统和华人男子真正特质的华人英雄形象,才能完全取代美国种族主义者别有用心的荒谬而虚假的华人刻板印象,让华人乃至美国人重新认识华人及其文化,增强华裔族群的凝聚力,有效抵御美国的文化霸权及种族主义。而“儿子”们理想的父亲应该刚柔并济,具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雅与正义,也具有英勇与阳刚之气,在中西文化的土壤中,在精神上引领着“儿子”们不断前进和成长。
[1]吴冰,王立礼.华裔美国作家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2]赵健秀.甘加丁之路[M].赵文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3]徐宗雄.天堂树[M].何文敬,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67.
[4]赵健秀.唐老亚[M].赵文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5]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