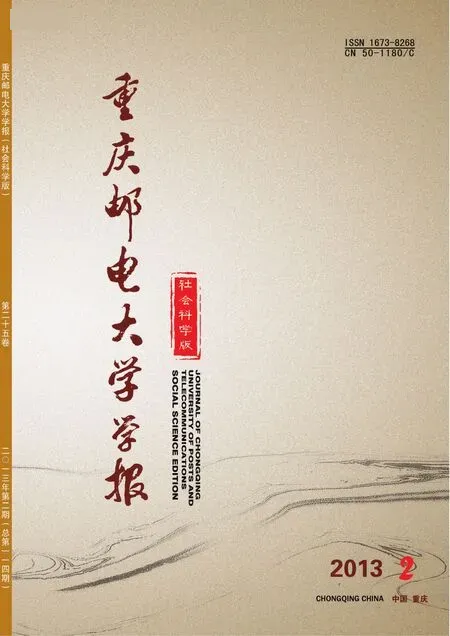大众文化的银幕投影
——对第六代电影的商业性重估*
2013-03-31宣宁
宣 宁
(四川音乐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系,四川 成都610500)
“第六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学界赋予张元、贾樟柯、王小帅、路学长、管虎、张扬、李欣等年轻导演的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这批出生于60年代中后期,于80年代接受学院式教育的年轻人,在80年代末登上影坛之际,即以其高调的艺术姿态和先锋的实践行为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然而管虎片头的“85”标识难以遮掩这一看似统一的团体中巨大的创作裂隙。一些第六代导演频频涉猎的商业电影创作,不仅给“第六代”这一统一称谓带来危机,甚至引起学界关于中国导演代际划分合理性的世纪末争论。时至今日,第六代早已在导演们各自的艺术追求下分崩瓦解,而迟来的金狮与金熊没能唤起他们昔日的荣光,反而凸显了这批导演在当下创作格局中的尴尬处境:第六代没有如其所愿从第五代手里抢过艺术权威的地位,在电影市场建设取得初步成果,商业创作成为主流的当下又显出一些不合时宜。因此在电影产业发展、商业电影创作成为实践、研究热点的语境下,我们对第六代电影实践的重估似应弃艺从商,选择另一种思路。正是基于此,本文从商业的视角重估第六代的电影创作,剖析其商业电影创作所体现的大众文化机制。
大众文化究竟为何?文化学界对其定义莫衷一是。在比较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后,英国学者斯特里纳蒂得出了较中肯的界定:“大众文化是通俗文化,它是由大批生产的工业技术生产出来的,是为了获利而向大批消费公众销售的。它是商业文化,是为大众市场而大批生产的。”[1]16
作为大众消费商品的商业电影自然也是大众文化的承载者、体现者。而第六代制作的一系列商业电影(李欣的《自娱自乐》、《花眼》,施润玖的《美丽新世界》,张杨的《爱情麻辣烫》,王小帅的《梦幻田园》,张元的《绿茶》等)正是通过对现实矛盾的回避和虚假解决、提供消费符号、模式化的生产方式等创作策略来传播大众文化和凸显自身商业价值的。
一、对现实的回避和对矛盾的虚假解决
大众文化向人们许诺轻松、休闲,因此它极力避免深刻和思考,而避免的最佳方式就是遮掩生活真实,对矛盾作虚假的大团圆式的解决。因此斯特里纳蒂指出大众文化是一种“缺乏智力的挑战和刺激,偏爱一无所求的幻想和逃避现实的舒适……把现实世界简单化,掩饰其中的问题”[1]20的文化。而理查德·模特比将此理解为是文化“提供了逃避现实的方法,这种逃避不是往返某个地方的逃避,而是乌托邦式的自我精神逃避”[2]。这是对大众文化遮掩现实的乐观理解。体现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第六代电影在内容安排上采取的也是这种通过对矛盾的虚假解决而遮蔽现实的策略。
王小帅的《梦幻田园》就完成了一次对现实矛盾的虚假解决。影片导演王小帅说他想通过这部影片来表现中国社会先富起来的一代人走向自己梦想生活时的困难,“我以为主要是中国的大环境和城乡之间及贫富之间的落差以及家庭内部观念的冲突,使这一过程充满了些许的苦涩和艰辛”[3]。应该说,影片选择了当下中国社会个人的幸福追求和整个社会大环境之间相互牵制这样一个极有现实意义的矛盾,但是精巧的戏剧性情节却将这一矛盾游戏化了。《梦幻田园》情节结构的核心在于隐藏和暴露间的冲突,丈夫极力隐藏初恋情人的踪迹,而家人的到来却使初恋情人时时都有被暴露的可能,这无疑是一个极富喜剧意味的情节构架,于是在“梦幻田园”里上演的便是一出略显荒诞的闹剧。这种近似喜剧的搬演无疑极大地削弱了影片所应该具有的社会现实意义。而以一场恶梦来勉强解决矛盾则将人们的思考完全禁锢在影片之内,换来一声“原来如此”的慨叹和大团圆的心满意足。至此影片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供消费、休闲的完美故事,避免了任何“费事”的思考和“不愉快”的感受,而这也与王小帅最初的创作意图南辕北辙。
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张杨的《洗澡》和施润玖的《美丽新世界》中。《洗澡》讲述的是父子两代的隔阂和隔阂消除的故事。故事本身指涉了当下社会生活的一个深刻矛盾,即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与现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之间的矛盾。为了避免探究这一矛盾所带来的深刻思索和沉重体验,张杨宁愿停留在表层,使它成为人们在工作劳累后的一剂温情调料。影片刻意将新旧价值观、生活观的矛盾推后,重点突出大儿子与父亲交流时的脉脉温情。这种温情是老年人所熟识的,也是年轻人经过激烈竞争而伤痕累累时所急需的,于是影片很自然地将观众导向了对温情的重温或体验,而不是对新旧矛盾的思索,这也许是这部影片老少咸宜的秘密所在。儿子渐渐懂得父亲的影片结尾也十分符合中国的传统道德要求,但是现实生活绝不会这么简单,影片实际上没有也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完满的解决方案。
如果说张杨的《洗澡》所打的文化牌还有一丝艺术气质,它毕竟暗指了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大矛盾,那么施润玖的《美丽新世界》就完全是一个凭空捏造的童话故事了。整部影片由张宝根中奖定下了基调——纯属虚构的爱情童话。但观众不管你是否具有现实意义,他们需要奇迹,也渴望看到奇迹的发生,对于张宝根的中奖、他与黄金芳的悬殊爱情,观众是乐观其成的。而导演正是抓住了观众这一心态,为他们创造了一个脆弱的中国版爱情神话。
二、消费符号的提供
大众文化之所以极具消费性,在于它包含了很多易于接受和理解的消费符号。第六代那些体现了大众文化的影片也必然以提供消费符号为己任。
关于大众文化里的消费符号,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在分析消费社会里的大众传播文化时有所涉及。他曾提出最小公共文化(P.P.C.C)的概念。最小公共文化即“普通消费者要获得消费社会公民资格而必须拥有的最小一套同等物品——因此P.P.C.C就代表了普通个体要获得文化公民资格而看来拥有的最小一套同等‘正确答案’”[4]106。这里的“同等物品”实际上就是在大众文化商品中通行的为消费者所熟悉和喜爱的各种消费符号。波德里亚将通行的消费符号的认知程度作为一种对消费社会公民的资格考查内容。同时他又指出在大众消费社会里存在着“文化再循环”,这种再循环要求人们“做的是‘悉知内情’、‘了解目前的情形’、每月或每年对自己的整套文化进行翻新……忍受这种像时尚般永远动荡着的简单摆动的约束”[4]102,当然这种再循环不可能成为科学理性的积累过程(实际上,波德里亚认为这种“文化”是对传统文化概念的颠覆)。这样看来,大众文化商品还要负担起“文化再循环”的职责,不断提供新鲜的消费符号。
结合波德里亚提出的两个概念,我们可以认为,作为极具消费潜力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商业电影对消费符号的提供也应该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它们要提供为大众所熟悉的消费符号;第二,它们还要提供一些新的、有潜力的消费符号。而在这两个方面第六代的商业电影以及一些有商业意味的影片都做得十分出色。
首先,这些电影为当代中国大众提供了许多熟悉的消费符号。在题材的选择上,第六代导演选择了深得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喜爱、且屡试不爽的题材加以表现。比如张杨的《爱情麻辣烫》一共讲述了五个独立的小故事,从早恋到黄昏恋再到婚姻中的“七年之痒”,每个故事都有着特定的消费群体。不仅《爱情麻辣烫》,在其他影片中我们也会看到相似或熟悉的题材。比如《花眼》里的校园爱情,《离婚了就别来找我》的情感纠葛,等等。
在情节的架构上,第六代也十分注意观众的接受能力,竭力按观众的观影习惯安排情节。具体到中国电影观众,为大家所熟悉的情节架构是完整、流畅的叙事结构,也就是说要包含开始、发展、高潮、结局几部分。第六代商业电影大多是按照这一情节定式铺展的。如《爱情麻辣烫》虽然有五个故事,但个个完整且独立,由《结婚》的线索连接,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丰富多彩的人生。又如李欣的《自娱自乐》完整叙述了男主角通过拍电影追求女主角的故事,该片对于男主角拍电影的由来、拍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男女主角的情感变化都有交待,让观众很容易把握影片的叙事脉络。
第六代商业电影所表现出的价值观念也是为观众所熟悉的。如《自娱自乐》、《美丽新世界》等片所表现的有情人终成眷属,《非常夏日》所表现的善恶有报等,都是观众熟悉且易于接受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
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些电影里活跃着一批为大众所熟悉和喜爱的明星。《爱情麻辣烫》里的演员几乎个个都是明星,如徐帆、吕丽萍、徐静蕾、邵兵、王学兵等,这些为人所熟知的明星毫无疑问也是影片提供的消费符号之一。
其次,这些电影还努力提供一些新鲜的、有市场潜力的消费符号,这一过程无疑融进了第六代导演的艺术探索中并体现了他们的个体主体意识。在题材的选择上,第六代导演努力将一些最新的社会热点问题引入电影创作中。比如《美丽新世界》就是基于彩票中奖这样一个当下社会生活的新鲜热点,《网络时代的爱情》则将时下青年中颇为盛行的网恋搬上了银幕,《自娱自乐》选取了一个由农民自筹资金拍摄电影的题材。应该说,在这些影片里各类新题材层出不穷。
在情节的架构上,第六代导演也努力在观众接受的程度上做出新意来。比如同是讲述多个故事,李欣的《花眼》在情节的安排上就与张杨的《爱情麻辣烫》不同。《爱情麻辣烫》里的五个小故事主要采用单独叙述的方式,而《花眼》里的五个故事则交替讲述,即各自进行但又交织在一起共同进入“我”的叙述视野,导演在五个故事间利用共存时空进行巧妙的切换。这种交叉讲述的情节安排很明显是受西方影片的影响,如《低俗小说》、《时时刻刻》等。可贵的是第六代导演将这种全新的叙述方式成功地植入当下中国的社会土壤中,呈现给观众的是新鲜而不是费解,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对于这种刺激当然是推崇的。其他如《绿茶》中的“我”与无芳和朗朗两个人、两段故事的交替等都是第六代导演对影片情节架构的新尝试。
此外,这些电影还提出了一些新的切合当下潮流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如《花眼》里背包女孩的出现实际上呈现了另一种爱情观,即追求爱情不再是男孩的专利,大胆的女孩也应该拿起自己的爱情地图去寻找真爱。
三、模式化的生产方式
大众文化产品为了满足市场消费、赢取利润必须采用模式化的工业生产方式进行大批量的生产。商业电影作为大众文化产品之一种,无疑也采用了模式化的生产方式。在此,我们需要加以注意的是,商业电影的生产不仅仅指影片的摄制完成,还应包括影片的发行、放映等。商业电影的模式化生产方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影片的整个制作、发行、放映过程中,导演、编剧、制片、发行商、影院经理等各个部门应明确分工,共同组织起一条高效率的电影生产流水线;二是就影片本身来说,已经形成了若干生产类型,这些类型都是屡经市场考验为观众所喜爱的。每一种类型都有固定的题材和表现方式,导演只需要按照类型的要求进行内容填充就可以了。
中国电影一开始就进行过商业化生产模式的探索,这一探索在建国后曾一度停滞,在进入新时期以后重又开始快速发展。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体制的转轨、电影集团公司的组建、民间发行公司的出现、电影院线的建设等,都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商业化生产模式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同时也急切盼望这种生产模式的出现。第六代导演的电影创作中也不乏对这种生产模式的探索。像坚守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导演集体发表《中国电影的后黄土地现象》这一艺术宣言一样,这批探索中国电影商业化生产模式的导演们也发表了自己的实践宣言——《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在《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中,他们提出“富于创意的、富于想象力的低成本商业电影”[5]即是新主流电影。全文围绕“新主流电影”的概念、操作上的问题、新主流电影的特点等内容展开,完整呈现了他们心目中的新主流电影。总而言之,他们所追求的新主流电影的生产模式是低成本(150万~300万)加导演创新(导演的独立和想象力)加大众目标观众。对于颇有些理想色彩的理论构想,有些专家则提出了质疑,如电影是需要高额资本投入的产业,过少的成本如何保证电影的质量?新主流电影的制作资金主要来自于国家的电影机构,仍然是在主流的指令下操作,与他们所提出的效仿对象“独立制作”相距甚远。
如果说《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主要是一种理论上的自觉或一种姿态的体现的话,那么下面我们将要分析的就是第六代经过实践检验的两种效果不错的生产模式。
一是产生了《爱情麻辣烫》、《洗澡》、《美丽新世界》等优秀影片的“艺玛”模式。1996年,一个叫罗异的美国青年来到中国创立了艺玛电影公司,并依托西安电影制片厂采取买厂标的方式投资拍片。罗异主要与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张杨、施润玖等青年导演合作。罗异的投资给张杨他们创造了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加上后期颇具商业意识的运作,最终推出了票房颇佳的《爱情麻辣烫》等影片。这种由外资参与的制片方式确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二是由国有电影制片厂参与完成的。世纪之交,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都启动了相似的“青年电影工程”,即两个电影制片厂拿出一定的资金资助本厂的年轻导演从事拍片实践。王小帅的《梦幻田园》、路学长的《非常夏日》等影片就是这两个电影工程的产物。“青年电影工程”无疑是国有电影制片机构面对市场,转变以往的制片态度,从年轻导演那里吸取新鲜观念,拍摄具有商业潜力的影片的有益尝试。
从商业性视角重估第六代的电影实践,评析其商业电影创作中体现的大众文化内涵,冲破了第六代坚硬的艺术外壳,充盈起他们多面的银幕形象。这些在世纪之交作出的成功尝试,不仅推动了中国电影制作的商业转型,具有影史留存的价值,其具体的制作策略更是不乏现实意义。
[1]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3.
[3]程青松,黄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320.
[4]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马宁.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J].当代电影,199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