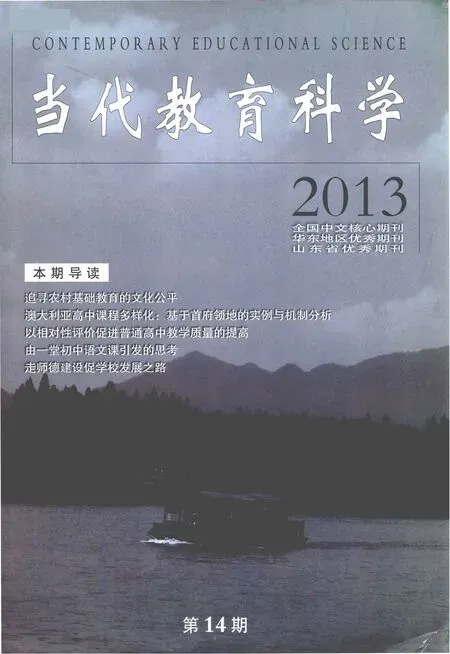追寻农村基础教育的文化公平
2013-03-27皮武
皮 武
国内近年来对于教育公平的探讨已经日趋深入。比如,针对城乡长期二元分割而导致的教育不公平现象,学界曾以不同的视角加以分析,也提出了诸多建议。笔者以为,在所有公平的谱系中,最为隐秘和难以实现的莫若文化公平,从文化的角度追寻教育公平,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触及影响教育公平的深层因素,更深刻地分析、解释并进而消除教育实践中影响教育公平实现的真正障碍。
一、文化公平的理论视野
文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人类学之父”泰勒给出的定义最为经典:“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人种志的意义来看,乃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他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性”。[1]较狭义地看,文化是“一定社会群体习得且共有的一切观念和行为”。[2]因此,文化与教育——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密切相关。学校教育具有将弱势群体整合到主流的社会结构之中的功能,但是,如果没有文化公平,它却更有可能有助于统治群体,从而复制社会不平等。
(一)伯恩斯坦的符码理论
英国教育社会学家伯恩斯坦指出,学校教育是社会阶级再生产的工具,造成了劳工阶级孩子在学校中处于不利位置的事实。在他看来,不同类型符码的使用大多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劳动分工产生并分配的。劳工阶级往往基于年龄、性别和阶级的传统权威结构,形成“有局限的”语言符码和意义系统,说话人往往使用“简约”形式,并且认为别人能明白其中的意图和意义;相反,中产阶级的家庭具有开放的、变通的结构模式,家庭人际关系较为平等,在社会交往中他们力图使别人明白自己的意思,因而使用的是更为规范的语言系统和精致符码。学校原本就是中产阶级开办的一些机构的发展和延伸,使用与中产阶级相似的语言,对劳工子弟不利。质言之,“局限符码”与低级社会经济群体有关,“精致符码”与中产阶级有关,使用局限符码的儿童在正式的学习情境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趋于被动,缺少激情,难于适应言语推理。[3]
(二)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观点是学校以 “符号暴力”的形式采取“教育行动”,以使“文化独裁”强加给主流群体,这一过程的结果取决于受教育者的惯习,而在大多数教育体系中,中产阶级而非工人阶级发现学校是与其惯习相适应的。符号暴力的可怕之处在于,被统治者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赞同了统治者的统治逻辑,并构成了统治基础的重要一环。“社会秩序的合法性不是……深谋远虑、目标明确的宣传或符号哄骗的产物;毋宁说,它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行动者面对社会世界的客观结构所运用的感知和评价的结构,正是社会世界客观结构的产物,并且,这种感知和评价的结构倾向于将世界视为不言自明的。”[4]布迪厄将以上理论运用到教育研究,得出了“统治阶级子女在教育上的优势,是因为他们拥有文化资本”的结论。[5]教育通过再生产“文化资本阶层化的分配”使自身得以再生产,教学便有利于那些当权者,劳工阶级缺乏受统治阶级和学校制度所重视的文化资本,是“文化被剥夺者”。
(三)威利斯的抵制的亚文化理论
英国的保罗·威利斯把新马克思主义和人种志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对反文化群体的研究揭示“调和与抵制”的动力机制。他通过对一个工人社区的一所中等学校里的十二名工人阶级“烈德族”(1ads)的研究,认为这些“烈德族”基于相同的工人阶级家庭背景形成了一种与学校主流文化相对立的亚文化——反学校文化,它通过抵制学校所传授的文化和教育实践,抵制统治阶级的社会价值和意义,拒绝学校教育承诺的改善个人的社会地位、促进个人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反学校文化的最基本、最明显的特征是对‘权威’的根深蒂固的、普遍的和体现着个人倾向的抵制。”[6]威利斯特别指出了这种抵制文化的再生产功能,正是“烈德族”对知识和技术的拒绝使他们失去了解放的可能性。实际上,这又是一个既成社会结构再生产过程,这个再生产过程是在抵制与反抗过程中实现的,而且工人阶级总是不利的、失败的一方。
二、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文化区隔
进入8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理论更鲜明地出现一种“文化转向”,其主要特征就是不再将文化视为外部社会结构及社会变迁的简单反映,而是将其作为独立于其他社会设置的领域,认为文化有自己内部的组织及其运作的动力。[7]群体与群体的不同,不再以他们的经济关系,而是以他们越来越突出的文化特征或文化取向来决定。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城乡差别还会持续下去,目前很难超越城乡之上建立全社会的阶层模型,所以,上述源于西方的理论对于我国的城乡教育公平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一)学校与乡村传统的冲突
晚清以降,新式学校的建立是“异质”文化对传统乡村社会的侵入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国家力量对农村的强力“渗透”而逐步完成。“新式教育主要反映了创建一个强大而现代的民族——国家的雄心壮志,这个民族——国家具有触及每个灵魂的力量”[8]因此,原本作为西方的一个相对保守的组织,新式学校一旦进入中国,却能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革命性”的组织和现代性的标志,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转型和变迁。“它以分学科和班级授课制为标志,同时,还体现出一个新的观念和价值追求:新的身体观念,教学方式,国家观念,学校与家庭,村落的疏离,现代卫生观念,个人自由等,使得学校与传统社会之间形成冲突”。[9]富有意味的是,新式学校是在清末“毁庙兴学”运动过程中和传教士手中建立起来的,作为本土信仰象征物的庙宇的被毁,在村民和学校之间也就埋下了本土观念同外来观念冲突的种子。也许是这种冲突基因的遗传效应,今天的乡村学校教育仍然试图以城市文化去改造乡村文化乃至取而代之,以忽视、贬低、解构乡村当事人的主体性作为推进教育的方式,以期达到所谓农村的城市化与现代化。
(二)教师多元文化意识的缺乏
人创造文化,也为文化所创造,不同的文化是不同环境中的人赖以生存的控制机制,“人明显地是这样一种动物,他极度地依赖于超出遗传的,在其皮肤之外的控制机制和文化程序来控制自己的行为。”[10]当前农村学校教师主要存在两种控制性文化,一种可称为“离乡型”文化,指大部分年轻教师的单纯的城市文化认同,对城市生活方式无限向往和依赖。他们在购物、娱乐、衣着、饰品等方面都竭力显示出自己是农村环境中的 “异类”。他们对农村传统基本持否定态度,“农村学生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些等待他们用现代文明加工与包装的土坯,其家长则是顽固不化的落后的乡土文化的代表”。[11]另一种则可称为“向乡型”文化,指的是多年在农村工作的中老年教师对农村文化的认同。他们从乡土文化中“生长”出来,既是学校里教学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权威”,又是村庄里与其他农民父兄一样的庄稼汉。当前随着“离乡型”控制性文化取得压倒性地位,“向乡型”文化已经逐渐式微和边缘化。农村教师不论拥有上述哪种单一的文化意识,本质上都是一种自我束缚,都不利于城乡教育公平的推进。
(三)课程文化的城市化倾向
课程是学校教育的核心问题,课程的文化选择问题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虽然时有轻重,但我国义务教育课程文化的城市化倾向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以新课程开发为例,其前期试验主要以城市学生的学力为根据,课程内容以反映城市儿童的经验为主,远离农村学生的生活经验,课程价值取向、课程内容、文本言说方式、课程实施与考核方式等方面仍然带有明显的城市化倾向。即使当前的教材一定程度上注意了城乡的平衡,如大部分选择中性内容,插图和课文在绝对数量上的差异也不明显,但是城乡孩子学习起来仍有难易之别。原因可能在于“城市的优越使得城市孩子知道得更多,不仅对占课本大多数的中性内容可能更熟悉一些,而且对典型化农村特征的内容也可能不陌生”。[12]家庭教育所传承的文化资本与学校教育的连续与非连续性导致了学习的易与难,导致了学业的成功与失败。[13]课程文化的不公导致了农村学生在学校教育中始终受到隐秘的不公正待遇。
(四)校园中的语言霸权
在布迪厄看来,语言是教育系统中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起到了与其他类型的资本同样的阶层划分作用,他十分重视语言在学校“文化过滤”过程中发挥淘汰作用的机制。由于教育系统的信息效益总是随接受者的语言能力而变化,所以在学校产生效益的语言资本在各社会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分配便成为隐蔽得最好的中介之一。学者们对教材的研究表明,教育内容的表达话语完全是来自城市的书面方式,是一套农村孩子陌生的符号系统。事实上,“没有任何语言、文化或品味惯习天然优越于别的语言、文化、品味惯习,然而在现实的文化社会中,某些语言、文化类型包含更多的文化资本与符号资本,被社会行动者‘集体无意识’误认为更具有合法性、正当性”。[14]千百年来在乡村流行的日常口语朴实、形象、生动,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鲜活的语言,但教育体制的“符号暴力”使得教师和学生不约而同地把刻板而教条的城市书面语——那样一种远离他们生活的语言奉为圭臬。因为语言的障碍,造成一些学生在学校教育中人际交往失败和学业失败已经屡见不鲜。就这样,文化等级作为一种社会建构,成为一种隐性的“霸权”,难以察觉地复制着社会等级,只要这种“霸权”存在着,农村儿童——这些由文化等级所决定的社会底层人员的子女就难以通过受教育来实现社会升迁,真正的社会公平也就无法实现。
(五)反学校文化的流行
因为文化的冲突,必然容易导致农村孩子的学业不良,等待他们的往往不是锦绣的前程,而是与父辈相近的命运。所以,如果说现时城市孩子面临学习“负担过重”的话,农村儿童却因为文化的区隔效应而根本“够不上”这些负担。这种状况催生了保罗·威利斯所说的“反学校文化”,其典型表现就是认为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大多是无用的,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混日子、抽烟、喝酒、早恋、打架斗殴成为“酷”的表现,对学校的一切持怀疑的态度,不认为成绩差或中途辍学是人生的失败,高年级学生甚至迫不及待要步入成人社会,幻想着闯世界、挣大钱。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一项研究发现,几乎每一所学校的初中部都有类似的小“帮派”,他们喜欢以油嘴滑舌的方式来挑战老师的权威,譬如寻找老师的弱点或特征,背地里给老师起绰号;当老师在讲台上很严肃地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挑其中的语病而制造“笑场”。[15]其实,他们的反学校文化是底层阶级文化的延伸,是通过对社会主流文化的拒斥实现的,这为他们步入社会底层做好了准备,在此意义上,充满活力的抵制,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挫败,它强化了他们在社会分层结构中所处的不利地位。
三、文化视野中推进城乡教育公平的路径选择
要实现真正的城乡义务教育公平,必须充分考虑到文化因素,努力改变文化的区隔与等级划分,倡导一种多元的文化价值观,并且注重进行文化整合。
(一)以多元共生的观点看待城乡文化
在我们热衷于“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16]过程中,农村文化自然容易被视为落后保守的代名词,唯恐弃之不及,殊不知此时的发达国家正在反思和批判工业社会的理性文化,倡导后现代的多元文化。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够适合所有的时空和主体,我们必须以多元共生的观点看等城乡文化,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各种文化都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各有千秋,要树立两种文化各有特点、不分优劣、共荣共生的信念,如果以自身的文化标准评判其他文化的先进或落后,只会跌入社会学家所说的“种族中心主义”陷阱。对此,农村教育需要承担起营构积极的文化空间的职责,既要发挥传统的教育功能,又要充当乡村少年成长的精神保姆,最终不论受何种文化体系的滋养,每个人“均被视为具有同等价值的人”。[17]
(二)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
实际上,对于城乡文化之间非此即彼的偏向,来源于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随着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和国家的政策扶持,城乡国民待遇差距不断缩小,农村文化自身的存在价值自然就会被肯定,城乡两种文化“无优劣之分”的观点也自然容易深入人心。其时,农村教育将会担当起文化责任,立足乡土,传承农村文化,依托农村的文化传统资源,发挥农村文化的优点,并借鉴城市文化的长处,发展农村文化,使生活在农村的人民实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而不是产生一种被剥夺感。
(三)在文化的普遍性和多样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在现有的农村教育中,知识是以城市文化的“现代”标准来界定的,农民的实践智慧和农村中许多隐性的文化资源无法成为课堂上的“法定”知识。而农村地域文化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地域、民俗文化传统,以及农村生活现实中就存在的许多合理的文化因素,有着对于乡村生活秩序建构弥足珍贵的价值成分。为此,我们一方面要确立地方性知识资源的价值与合法性,要把地方性、异质性因素引入教育机制,赋予农村教育更多的自主权;另一方面,过度强调多元文化无止境的自我认同,同样不利于在共同的组织框架下实现社会融合。实际上,城乡文化之间本无不可逾越的鸿沟,许多城市文化,只有从乡土文化的底色与基础出发才能深刻理解。因此,要超越不同文化的纠葛,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受教育者提供具有同样价值的教育内容,在文化的普遍性和多样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四)培养农村教师的文化敏感性
所谓文化敏感性,指“教师能代表社会的文化多元性,敏感地察觉到学校教育诸因素中文化的差异,同时重视文化整合,能够运用适当策略增强社会中的共同核心价值。”[18]这样的教师才不会一看到城乡文化差异就想到“抹平”或“修补”的手段,而更可能把这种文化差异当作学校教育过程中促进教育公平可以利用的丰富资源,能够教育学生欣赏和尊重他人的文化,为处于文化不利地位的学生提供适当的及补偿教育的机会,以促进来自不同文化团体的学生的教育平等。为此,一方面,要从培养农村教师职前教育中,实行多元文化教育,给农村文化的传播留下一席之地;另一方面,要把文化敏感性培育当作农村教师培训中的重要内容,培养更多的适应农村教育的新型师资。
总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社会中的人,没有文化公平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在当下推进我国城乡教育公平的实践中,尽管有的地方在教师资源、硬件设施、课程设置等方面获得极大改进,甚至有的地方把农村初中全部搬进城,进行“教育移民”,以期“彻底抹平教育差别”,却仍然改变不了农家子弟在学校教育中的不利境况。对此,文化视角引导着我们在更深的层次上解析教育不平等的根源,为教育公平的研究和实践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1]转引自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0.
[2]郑金洲.教育文化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4.
[31See Richmond,W.K.,The literature of Education,London,Methuen&Co.,1972,pp.137-138.
[4][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320.
[5]吴永军.课程社会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73.
[6]转引自杨昌勇.新教育社会学:连续与断裂的学术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42-143.
[7]Gartman.Bourdieu’s Theory of Cultural Change:Ex-plication,Application,Critique[J].Sociological Theory,2002(6).
[8][丹麦]曹诗弟.文化县——从山东邹平的乡村学校看二十世纪的中国[M].泥安儒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10.
[9]司洪昌.嵌入村庄的学校: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39.
[10][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57.
[11]高小强.乡村教师的文化困境与出路[J].教育发展研究,2009,(20):53.
[12]余秀兰.中小学教学内容的城市偏向分析[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94.
[13][英]M·F·D·扬.课程作为社会构成知识的一种研究取向[A].厉以贤.西方教育社会学文集[C].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1992.663-669.
[14][法]布迪厄,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28.
[15]熊易寒.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J].开放时代,2010,(1):102-103.
[16]郑杭生等.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9.
[17]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225.
[18]皮武.教师的文化敏感性及其培养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201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