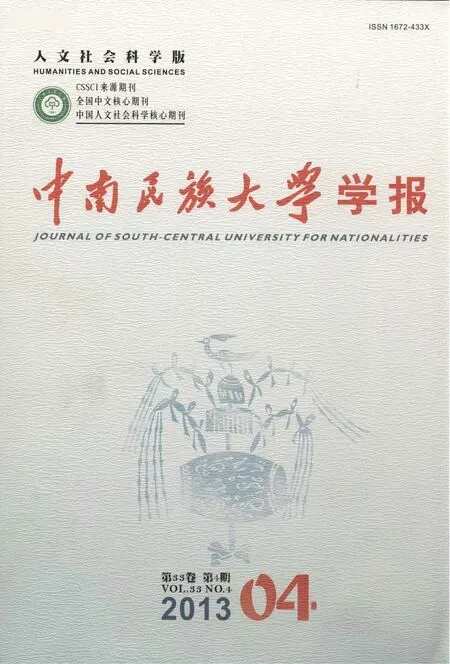论《儿女英雄传》的谱系归属
2013-03-21王同舟
王同舟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是继《儒林外史》、《红楼梦》之后颇具艺术个性的小说作品,它对以前诸种小说传统的融合,一直受到研究者关注。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的角度着眼,《儿女英雄传》似乎有意将侠义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结合起来,写出兼备“儿女”之温柔与“英雄”之侠烈的形象。在最早的小说史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将其置于“侠义小说”下论述,更关注作品与侠义小说的渊源。[1]孙揩第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将其归于“烟粉”小说(爱情婚姻小说)的特殊类型“英雄儿女”[2],他后来在《关于儿女英雄传》中也说,这部作品的“作风算来仍是才子佳人的苗裔”[3],可知他较为关注《儿女英雄传》与才子佳人小说的渊源。此后,学者多采取孙楷第的命名方式,称这部小说为“英雄儿女小说”,或者称为“儿女英雄小说”[4]。
笔者重新审视《儿女英雄传》的谱系归属问题,主要从作家对侠义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两种小说类型的态度出发,来把握《儿女英雄传》的主题与艺术个性,并借此进一步讨论传统小说谱系梳理中的理论方法问题。
一、从《儿女英雄传》的整体意图看流行观点的错误
《儿女英雄传》所叙何玉凤救助安骥的故事,沿袭了侠义小说的写法,这是将《儿女英雄传》视为侠义小说的主要依据。但是,整部作品的意图并不是张扬侠义精神。《儿女英雄传》的主人公何玉凤,她的角色功能有着显著变化。从第四回至第十二回,叙写何玉凤救助安骥,在这个侠义故事里,何玉凤扮演着拯救者的角色,但这只是何玉凤故事的开头,是为何玉凤性格、命运的转变进行铺垫。从第十四回到第二十八回,叙写“雄心侠气”的何玉凤在安学海引导和帮助下迷途知返,回到现实社会的“安乐窝”,这时的何玉凤是一个被拯救者。第二十九回以后,叙写何玉凤操持家政,助夫成名,这里的她更多的是安学海思想的实践者、代言人。从整部作品看,在传达作品的意图方面,安学海的声音更具权威性。当情节进展到安学海找到何玉凤并规劝她回到正常社会时,作品开始偏离侠义小说的轨道,转入教化型世情小说的主题,并且将第一部分的侠义故事转化成为服务于这一主题的铺垫性情节。
一些研究者致憾于《儿女英雄传》将何玉凤写成一个半截子侠客,为小说后来将她写成“凡庸”的家庭妇女感到惋惜,这是对作品主题的莫大误解。在整部小说中,何玉凤命运转变的关键在于安学海用他的“天理人情”化掉了何玉凤的“侠气”。何玉凤接受安学海的教诲和安排,找到人生的“安乐窝”,代表着年轻气盛的侠客向一个儒家的忠厚长者输诚,这有力地表达了以儒家思想规范侠义思想的主题。《儿女英雄传》之所以写何玉凤的侠义故事,不是为了宣扬侠义思想,而是先将何玉凤写成一个侠客,而后写出她的思想转变,并借这个转变表达作品的主题,彰显“天理人情”之可贵。
需要指出的是,小说标题中的“英雄”二字并不暗示作品秉承了侠义小说的传统。文康心目中的英雄不是侠客,也不必有什么武艺。《儿女英雄传》中最大的英雄是安学海,这一点可以通过小说对何玉凤的心理活动描写得到确证:“这位安长官才是位作英雄的见识,养儿女的心肠!”[5]安学海之所以被视为英雄,在于他能够诚笃地践履“天理人情”。至于何玉凤,则是在接受安学海的教导、化去矫激性格之后,才成为合格的“英雄”。
《儿女英雄传》因为叙及安骥与何玉凤、张金凤的爱情婚姻故事,其人物、情节与才子佳人小说相似,因此被视为才子佳人小说。但是,如同这部小说写到侠义故事而意在消解侠义小说的传统一样,这部小说虽然写到爱情婚姻故事,实际上却消解了才子佳人小说。因为才子佳人小说的主人公对爱情有着主动的追求,对婚姻有着自主的愿望,“他们大都不经父母之命,不由媒妁之言,由于郎才女貌互相倾慕,自订婚姻约而成”[6]。《儿女英雄传》则不然。小说中的“双凤奇缘”,都不是青年男女主动追求的结果。张金凤与安骥的结合,是因为何玉凤“横刀联嘉耦”;何玉凤与安骥的婚姻,完全是安学海等人为何玉凤着想而极力撮合的结果,何玉凤几乎是在诸人水磨工夫“逼迫”下答应这桩婚事。青年男女对爱情的主动追求与社会、家庭的重重阻力,二者常常构成一般才子佳人小说的主要情节线索。《儿女英雄传》则把青年男女因为担忧有违“天理人情”而拒婚作为重头戏来写,表达的意旨与才子佳人小说全然不同。
针对着才子佳人小说,《儿女英雄传》有不少的调侃,三十一回“双美激新郎”的描写表现得格外鲜明。安骥曾大发雅兴,邀请何、张“双美”酌酒赏花、吟诗联句,二人却借题发挥,要安骥读四书,作八股,博得科举及第。她们的想法令安骥大为扫兴,被安骥斥为“俗”、“腐”、“丑”。但面对“双美”提出的养亲尽孝诸种现实责任,安骥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闺阁闲情、风雅举动无济于事,不得不接受她们的劝导,老老实实地从事“俗”、“腐”、“丑”的事业。通过安骥失败了的风雅举动的喜剧化描写,文康调侃了“才子气”的无用与可笑。在他看来,正如何玉凤成为“英雄儿女”需要克服侠义小说里张扬的“雄心侠气”一样,安骥成长为合格的“英雄儿女”,也需要消除那些才子佳人小说格外钟情而实际不合宜的“闺阁闲情”与“风雅”作派。因此,与其说《儿女英雄传》是才子佳人小说的“苗裔”,不如说它是作为才子佳人小说的比较物和对照物而创造出来的讽刺性的模拟作品。
二、文康的身份意识及谱系意识
文康在创作中借用和参照了侠义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的某些元素,但是这些元素在《儿女英雄传》失去了它们原有的功能,转而服务于新的意义结构,甚至直接服务于批评它们原本所属的小说类型。在考虑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之后,如果仍然执着于《儿女英雄传》借用和参照的元素,或许可以说《儿女英雄传》是“反侠义小说的侠义小说”,或者是“反才子佳人小说的才子佳人小说”。但是,这样的说法就好像把《堂吉诃德》称为“抨击骑士小说的骑士小说”一样,对于讨论小说的谱系归属来说,当然是令人尴尬的。
不过,“反才子佳人小说的才子佳人小说”之类作品的谱系归属表面上暧昧难辨,实情却非如此。一位作家如果能写出这种具有明显文本对话色彩的作品,说明他有较为清晰的谱系意识。因为风格翻转的基础是对风格谱系的感知,主题翻转的基础是对主题谱系的感知……不然,作家就无从发起这种对话。因此,笔者借助作家对谱系的感知来分析《儿女英雄传》的谱系归属问题。
作家创作中的谱系意识,始终与作家的自我身份意识相关。他选择怎样“站队”,也就选择了创作中的身份,更准确地说,是“隐含作者”的身份。相对而言,通过主题的选择而呈现出来的“隐含作者”的身份与作家在实际生活中的身份意识具有密切的关联,大型叙事文本尤其如此。这就决定了小说文体中主题谱系的变化能更生动地体现社会生活及社会意识的变动,作家现实生活中的身份意识在谱系的辨认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文康出身于仕宦世家,他是一位颇为正直而有能力的官员[7],晚年却因对后代的教育失败陷入困顿,于是著书自遣。这样的生活经历与创作动机,使《儿女英雄传》集中于探讨青年子弟如何成长的问题。《儿女英雄传》中的男女青年,无论是何玉凤在困顿中养成不近人情的“侠气”,还是安骥在顺遂之时沾染上“风流”习气,都在“贤父兄、良师友”的及时引导下迷途知返。最后,安家和睦安乐,“安老夫妻寿登期颐,子贵孙荣,至今书香不断”[5]605。就文康个人的遭遇来看,《儿女英雄传》无疑是带有强烈补偿意味的“白日梦”。胡适在《〈儿女英雄传〉序》中极为鄙视这部小说的思想,称它“都只是一个迂腐的八旗老官僚在那穷愁之中作的如意梦。”[8]后来的研究者也多半不肯为这部小说的思想辩护。但是,就像不能单纯地把《红楼梦》看成曹雪芹个人的“自叙传”一样,《儿女英雄传》也不是文康个人的“白日梦”。作家对自身的经历、处境的理解以及在文学创作中的加工处理,总是与更为广泛的思想传统、社会思潮相联系。采取何种思想指导创作,取决于他的自我身份意识。我们虽然不能确知文康所遭不幸的详情,但他在写作中表明的却是这样一种态度:只要正确掌握儒家的精义,善教善学,笃实践行,家庭的美满和乐以至社会的和谐都可以得到保障。文康选择了儒家学者的身份和立场,他的“白日梦”是用儒家思想维系这个可能崩坏的世界。
《儿女英雄传》的创作继承了儒家“载道”、“教化”的传统。写“男女之感”与“英雄之性”本来是中国传统小说的两大流行题材,两者的典型分别是才子佳人小说和侠义小说,但《儿女英雄传》标置的“儿女英雄”却是儒家的理想人格,作品对于生活意义的理解,对于人生道路的主张,也打上了鲜明的儒家烙印。在这部颇多议论的作品里,时常可以看到对儒家“仁”、“礼”、“中(庸)”等核心观念的精微辨析。这种辨析有时甚至失去必要的节制,却正是作者儒家立场的一个显著证据。
就思想的谱系而言,文康是以“正统”自居的,他坚信儒家思想对于争取人生幸福来说是实际的、有效的,从这一点出发,他发现传统小说的主题表达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才子佳人小说、侠义小说所表达的主题带有“异端”色彩。二是这两类小说都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是脱离了社会现实因而“不实际”的。从思想的谱系出发,自觉地选择一种更讲究现实性的艺术派别,是文康这一教化小说的独特之处。
文康思考青年成长问题,是把问题提升到如何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层面上,因而赋予小说更广泛的教化意义。他提出的答案是,在一个有缺陷的社会里,需要遵从社会的既有规范,其核心是儒家提倡的人格理想和人生道路,在体制之内寻求成功。《儿女英雄传》故事背景是清代雍正年间,真正展示的却是清代后期可称为“礼崩乐坏”的社会。对于这样的社会,文康没有采取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着重批判和反抗的主题。他也没有采取浪漫主义的做法,幻想青年男女在现存秩序之外获取幸福生活。虽然小说虚构了一个夫贵妻荣的美满结局,但那只是满足“为下下人说法”的教化需要,作家思考问题的方式并非浪漫的。
文康认为,侠义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都不具备“现实性”,无论是实现社会正义还是追求个人幸福,它们提供的方案都脱离了社会现实,不具备可行性,而他本人则力求在关注现实条件的基础上指示具有现实性的生活道路,由此形成了《儿女英雄传》与侠义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在艺术风格上的根本区别。文康本人对此了然于胸,因此在托名“观鉴我斋”所作的《序》中说:“是书以眼前粟布为文章”[9]。在小说第三十四回,作者将《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进行对比,一方面老实承认自己的小说不为“略常而务怪,厌故而喜新”的读者所喜,另一方面却又为自己小说的“腐烂喷饭”[5]454感到得意。这种自信源于他认定自己的小说具有充分的现实感。1935年文艺出版社所刊《儿女英雄传》,书首的“本书特点”一栏中指出:“本书虽为消闲性质之小说,却处处教人脚踏实地做事,实为阅历有得之言,不得以含有教训的意味而少之。”①此处引文出自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重排本,此一版本书名改题《侠女奇缘》。“脚踏实地”、“阅历有得”,确实道出了《儿女英雄传》主题具有强烈现实性的特点。
三、《儿女英雄传》对世情小说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看,谱系研究就是研究文本之间的互动与对话,并把它作为文学演进的一个重要机制。在作家发起文本互动与对话的时候,自然受到先在作品的影响,这正是将《儿女英雄传》视为侠义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的学者注意的方面。但是,文本的互动与对话以何种方式进行,取决于作家的创作动机以及由此动机选择出来的“身份”,不同互动与对话方式将产生不同的结果,这才是谱系梳理中更具决定意义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不妨将《儿女英雄传》、《红楼梦》、才子佳人小说三者联系起来考察。《儿女英雄传》是针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它也没有放过同样是针对才子佳人小说的《红楼梦》,甚至针对《红楼梦》的痕迹更加显著。这种复杂的纠葛正好提供了观察文学演进机制的一个实例。
《红楼梦》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与才子佳人小说相似,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曹雪芹颇为鄙薄才子佳人小说的艺术手段和思想主题。在艺术手法上,曹雪芹反对才子佳人小说人物形象的类型化,情节的模式化,力求写出具有高度艺术真实感的生活场景。在价值传达上,曹雪芹认为才子佳人小说只是“雅”皮“俗”骨,《红楼梦》力求写出一种真正脱“俗”的“雅”。在曹雪芹眼里,才子佳人小说的主人公也罢,小说作者也罢,都还没有摆脱对夫贵妻荣的歆羡,还只是“雅”皮“俗”骨。《红楼梦》将才子佳人小说张扬的“雅”提升为一种对抗现实的内在生活方式。贾宝玉极度鄙视功名富贵,写诗作赋等雅致的生活方式代表着他对诗意世界的建构,代表着他对“显亲扬名”等社会责任的逃避。《红楼梦》所钟情的“雅”由此具有探索生命意义、寻找心灵归宿的意义,决不是功名之士的外在点缀。与此相关,《红楼梦》在另一主题“情为何物”的探讨上,也超出才子佳人小说。它强调爱情是自由的心灵的高度契合;宝、黛爱情的基础,是二人都蔑弃一切外在的荣耀与成功,都珍视自己的个性与自由。
《红楼梦》对才子佳人小说的这种提升,使它超越才子佳人小说的范畴而成为世情小说的巨著。不过文康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认为恰恰是这种提升使它的流毒超过了才子佳人小说,所以《儿女英雄传》的做法是针对《红楼梦》,将对才子佳人小说的批评结合进来。这种针对表现在情节上,也流露于作品的议论之中。例如小说针对《红楼梦》中宝玉与黛玉、宝钗的关系,设计了安骥与何玉凤、张金凤的故事;甚至还针对《红楼梦》中袭人这一形象,设计了嫁与安骥作小妾的长姐儿这一角色。两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及其关系彼此相似,结局却截然相反,贾宝玉等人下场悲凉,安骥等人幸福安乐。文康通过这种对比说明,《红楼梦》中所写的贾宝玉的悲剧,不是源于礼法对贾宝玉的压迫,而是源于贾宝玉对礼法的反抗,源于整个贾府未能有效地贯彻礼法的精神。而安府上下的幸福安乐,仿佛在自信地宣布“名教之中自有乐地”。
由于《儿女英雄传》是在《红楼梦》同一向度讨论社会、人生问题,也就使它与《红楼梦》同属世情小说的范畴。它们的差异在于作家的立场,《红楼梦》借助于佛、道两家的思想为自己反抗礼教的思想张目,《儿女英雄传》则牢牢握定儒家思想,要求人们遵从礼法。但是,《儿女英雄传》也不能不回应长久以来小说中对礼教的质疑,特别是回应《红楼梦》这样的流行广远的著作。文康的回应是重新解释礼教的含义。他感受到社会思潮的变化,并试图越过理学家,对“礼”做了带有某种新意、更具弹性的解释,淡化“礼”森严的一面,强调它“和”的本质与功能。小说描写最为精彩的不是青年男女的爱情,而是家庭生活的细琐事件,它们贯穿于整个作品,以至使读者感到这确是一部家庭小说而不是爱情小说。安府家人之间亲切和睦关系的描写在古典小说中罕有其匹,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这正是作者要强调的“和”。反映在人物形象上,是代表“礼教”的安学海性格特别地热情、随和,是一个迂腐而可爱的老头;代表着传统的其他年长者安太太、佟舅太等人,也都特别通情达理,真心实意地关心爱护安骥、何玉凤等后辈。作品通过对长辈极富生动性、真实感的描写,显示出“礼”无往不在,却不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而是促进了人们相处的和睦。《儿女英雄传》如此地把“礼”与人际间的关爱紧密联系起来,这一现象值得专门讨论,笔者在这里只想指出,从小说发展的角度看,为了回应对立性主题的挑战,《儿女英雄传》在表达主题的时候,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这部作品的成就当然还不能与《红楼梦》相提并论,但它与《红楼梦》的对话仍然强化了作者的谱系意识,并提升了儒家立场的教化型世情小说谱系的思想深度。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是,在考察一部小说的谱系归属时,必须充分注意作者的写作意图。小说写到什么样的故事并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个故事服务于表达何种思想或主题。当问题推进到这一层次时,就会发现,作者所表达的思想、主题是由其创作过程中所选择的身份确定的;而作者创作中所选择的身份,不仅受其个人的特殊经历影响,也受到思想传统、文学传统的影响。小说谱系的背后潜藏着一个哲学思想、社会思想的谱系。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03.
[2]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151.
[3]孙楷第.沧州后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169.
[4]常雪鹰.二十世纪《儿女英雄传》研究回顾[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1(6).
[5]文康.儿女英雄传[M].何晓亚,点校.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
[6]谭正璧.古本稀见小说汇考[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177.
[7]李永泉.《儿女英雄传》考论[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36.
[8]胡适.胡适文集(第6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54.
[9]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