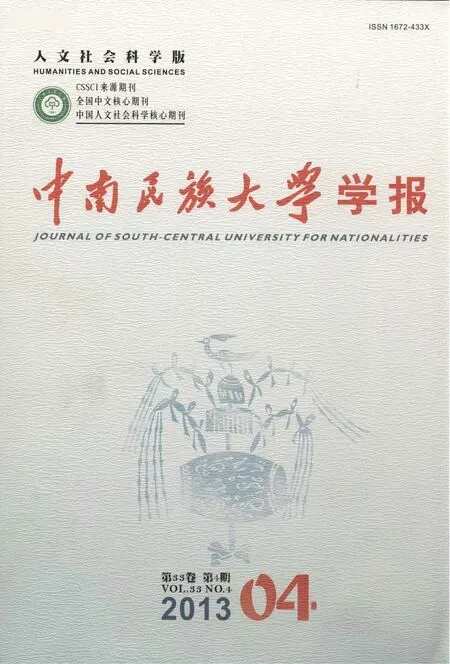旅游开发与民族村寨社会变迁
2013-03-21陈思莲
陈思莲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海口 570228)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村寨旅游兴起。民族村寨旅游使旅游“目的地”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更引起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传承问题的担忧。如何看待民族村寨在旅游开发后发生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如何处理旅游开发中“传统”与“现代”、“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的关系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为此,本文拟就民族村寨社会变迁的内容、特征、动因等方面略作阐述,并求教于学界方家。
一
旅游业的发展使民族村寨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始于生产方式,止于价值观念、禁忌习俗。在旅游开发中,村民们程度不同地从原本的农牧业转移到与旅游相关的产业,与农牧业相联系的生活方式也就被与旅游业共生的生活方式取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换,必然引起村民的生活习俗、价值观念、禁忌等的相应变化。
被开发出来吸引城市、异地居民“到此一游”的民族村寨一般都是经济落后、交通闭塞,但自然风景秀丽、民族文化别具一格。村民们世代从事农牧业,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如著名的民族旅游村寨贵州雷山县上郎德村,在旅游开发前,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全村234名劳动力,全都从事农业生产[1]。云南省石林县湖村1999年农业收入占村民家庭收入的73.76%,牧、副、渔业等占26.24%,“农业种植”是主要产业,“个体农业经济和家户式生产仍占主体地位”[2]193-194。
由于产业落后,民族村寨经济发展整体滞后,村民生活较为贫困。为了改变落后状况,地方政府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相号召,以民族村寨独特的文化、自然资源为“卖点”,期望通过发展旅游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旅游业兴起后,越来越多的村民卷入到与旅游相关的产业中。他们或完全放弃传统农牧业,转而从事家庭旅游接待,向游客兜售民族手工业品;或半农牧半旅游,在旅游旺季、游客到来时从事旅游业,淡季时又回到农牧业。著名的郎德上寨已形成了农业生产与旅游经济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当游客到来时,村民们会暂时停下农业生产从事包括刺绣、农家乐、商业表演等活动。贵州肇兴侗寨“直接参与乡村旅游服务的人数占全寨人数的11%”。云南香格里拉的落茸社区在旅游开发前,民众的主要经济来源为畜牧业,辅以松茸为主的林业产品收入,偶尔有个别村民外出打工,获得少量的经济收入。可是在旅游开发以后,无论男女老少,每月都会有6天以上的时间在公园里,村民对于农业劳作的积极性降低了[3]。贵州花溪镇山村在旅游开发前,村民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辅以一定的渔业和家庭养殖业。旅游开发后,大部分村民都成为旅游接待户,那些家庭条件好一些的村民完全投入到了旅游中,稍差一点的则在农忙时务农,农闲时从事旅游服务。即使老人也通过出售蔬菜、水果、小商品等方式参与到旅游服务业中[4]。2006年,四川理县桃坪羌寨直接或间接从事旅游服务的人数已占全寨总人口的96%,成为当地著名的“旅游专业户”[5]。
生产方式的变革,劳动力由农牧业向旅游产业的转移,引起了村民生活方式的变化。在旅游开发前,村民的日常生活紧密围绕农作物、牲畜的生长周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旅游开发以后,大量游客的涌入,原本平静的乡村社会变得喧嚣起来,村民的家庭结构、社交范围、饮食结构、娱乐方式及内容乃至作息时间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为显性的变化是村民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在旅游村寨,人们的生活原本以家庭、田间地头为中心,村民交往主要限于村寨内部及邻近村寨之间。旅游开发后,则转移到码头、风景区,重点是与各种“闯入者”之间的交往。另外,随着外来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现代的、城市社会的娱乐方式、娱乐内容进入村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村民已经习惯收看电视节目、玩扑克、打麻将、唱卡拉OK等。旅游业的发展还改变了民族村寨的家庭结构,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根据田野调查,随着女性走出“家户”,开始从事与旅游相关的歌舞表演、工艺品销售、餐饮接待等工作,经济收入的提高使她们在家庭事务决策中获得“拥有比以往更多的发言权”,在一些民族村寨,甚至有“不少家庭是由女的当家”[6]。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进一步引起村民生活习俗、日常禁忌、价值观念的变化。田野调查发现,在云南某傣族村寨,人们的宗教观念逐渐淡漠,“很多男童都不愿进佛寺做小和尚。宗教礼仪对他们来说渐渐成为一种形式,出现了宗教观念淡化的一代。”[7]在贵州屯堡,随着旅游开发,以“地戏”为中心的一系列禁忌习俗已荡然无存。为了吸引游客,原本只能在特定节日才能演出的地戏被常态化。由于地戏面具被商品化,流传于民间的地戏面具信仰也被彻底颠覆,“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件工艺品或旅游纪念品,而不再把它当作具有灵性的‘神’”,“人们不再相信面具是神灵的化身和载体”[8]107。即使是追求生命延续的丧葬仪式,也融入了很多现实性、利己性、交易性因素。在这过程中,人们获得的不再是神灵、祖先的庇护,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名誉、声望、人情和面子[2]240。
二
民族旅游村寨近30年来的社会变迁是全方位、深层次的。综观民族村寨的社会变迁,民族村寨社会总体上正在朝着开放化、多元化、世俗化方向发展,开始呈现开放、多元、世俗等特征。
旅游开发前,民族村寨基本都与世隔绝,是相对封闭、独立的经济、社会、文化单元。村民们将农牧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进行以家庭消费为主要目的的生产劳动,很少与外界发生经济文化往来。据田野调查资料,在20世纪90年代初,香格里拉落茸社区只有个别家庭有人外出打工,主要农产品青稞、洋芋等也基本自给自足,偶尔“有相对富裕的家庭会采用以物换物的形式将多产的青稞或洋芋拿到中甸县城交换一些玉米和少量的大米”[3]。由于交往范围有限,婚姻基本都在本村或邻近村寨之间通过族内通婚或血亲通婚等方式进行。同时,由于村寨内部能够为村民提供“可以相互沟通的紧密空间”,能够满足大家“对于人际交往和情感交流的需要”[2]62,因此,无论是村民个体还是整个民族村寨,都缺乏与外界主动交往的现实需求。在长期封闭的经济、社会生活中,民族村寨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呈现出与周边地区完全不一样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伦理道德等。
旅游业兴起后,民族村寨的“自我封闭”格局被打破。一些民族村寨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引进旅游开发公司负责基础设施建设、日常管理,使外来资金和现代的组织、管理方式进入民族村寨。与此同时,村民们或开设“农家乐”,或出售民族手工艺品、农牧业产品,或投身民族歌舞表演。他们的生产劳动不再是为了满足家庭消费,而是为了与游客进行“交换”。在四川理县桃坪羌寨,村妇们农闲时做的刺绣、服饰,原本仅供家人穿戴,或赠送亲朋好友,“从没想过会用来出售”,但旅游开发以后,这些手工艺品成为村妇与外来游客进行劳动交换的重要商品[9]。在郎德上寨,苗族妇女们的刺绣“也不再只用于家庭服饰装饰生活所用,而是进入了商业活动的范围”,成为村民与外界交换的商品[10]。
与外界交往的不断深入,民族村寨正变得越来越多元化。首先,民族村寨内部出现了多元“权威”。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新中国建立以后逐渐形成的、单一的村寨“政治精英”——国家权力的代理人的权威被削弱,出现了以致富能人为代表的村寨经济精英、以村干部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以民间祭司等为代表的村寨文化精英、以退休回村的原国家干部为代表的村寨社会精英共同执掌村寨话语权的局面[2]198。在一些民族村寨,由于地方政府引入旅游公司参与旅游开发,在民族村寨内部形成了以旅游公司为中心的强大权力场,逐渐形成“行业组织”的权威[11]。其次,旅游村寨内部出现多种文化共存、碰撞的局面,呈现多元文化共存的特征。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民族村寨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开发、挖掘其传统文化以吸引游客,一些早已消失的“传统”开始复兴。而“闯入”民族村寨体验其独特文化生活的外来者则不自觉地将各种外来文化带到旅游目的地,于是民族村寨成为多种文化交织的场所。再次,村民的经济生活也呈多元化趋势。在民族村寨,彻底放弃原本的农牧业,完全从事与旅游相关的服务业仅是个别现象,绝大多数村民或以旅游业为主、传统的农牧业为辅,或者以农牧业为主、旅游业为辅。即使从事旅游业,他们的就业方式也是多元的。根据田野调查,湖北神龙溪罗坪村2006年全村1044人中有797人从事旅游服务工作,是一个以旅游为主业的村寨[12]。但即使是从事旅游业,村民们具体参与、就业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的利用房屋改装成家庭旅馆,从事“农家乐”等旅游接待工作;有的则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从事民族工艺品的生产、销售;有的则通过民族歌舞表演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总之,旅游村寨原本单一的经济生活方式已被逐渐变得多元。
民族村寨的世俗化是指随着旅游开发,原来的各种宗教信仰、鬼神崇拜逐渐削弱,人们逐渐以人为中心,按照经济理性原则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安排自己的社会生活。民族村寨独特的宗教、文化、生活习俗往往与一定的宗教信仰、偶像崇拜、神话传说等有关。如贵州安顺屯堡地戏,原来叫跳神,“本来是保一方平安的娱神活动”。围绕地戏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仪式以及相应的禁忌,如不许女人触碰面具,尤其忌讳怀孕的女人触碰面具。演员戴上面具以后,忌讳互相呼叫姓名,如果有事商量,只能呼叫彼此扮演的角色名称[8]104。再如云南小屯村的关索戏的演出也有一套严格的规矩,在筹演期间要举行“领生”仪式,要杀鸡、喝鸡血酒,要洗澡净身,且不能与女人同床,不能抱孩子等[7]195。而云南香格里拉落茸社区的村民则通过对神山的朝拜,祈求风调雨顺,但是神山崇拜也是有禁忌的,即“只有本村男人可以祭拜,女人不允许祭拜,外来人也不允许祭拜。”[3]
但是在旅游开发中,一些极具地方、民族特色的戏剧、节日被包装为吸引游客的“商品”,成为供给外来者体验的文化商品。在这过程中,它们原本的“神性”逐渐消逝,成为“娱人”的表演节目,相应的禁忌也不得不在蜂拥而来的游客面前取消。如前述安顺地戏,本来只能在特定时间才能演出,现在一年四季甚至大年三十都要演出,相关的“开箱”、“封箱”仪式只能简化,各种禁忌也就逐渐被淡忘。
村民们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日常行为越来越“市场化”、“商品化”,是否对自己有利成为日常行为的重要标准。在传统民族村寨,由于内部成员相对熟悉,彼此之间的互相帮助、协同生活是共同的惯例。在农忙时节,当个体家庭出现婚丧嫁娶、盖房建屋等生活大事时,在修桥补路、村祭社火等公共事务中,人们互相帮助,分工协作[2]64。但是在旅游开发后,人际关系中的“钱”味越来越浓,“情”味则越来越淡。如在德夯村,村民普遍抱怨现在大家交往看重“钱”,“一些村民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只结交对自己有用的人,建立功利性很强的交际圈子,而对于自己无益的人,……甚至亲人都很少交往。”[6]在贵州镇宁石头寨,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正在被功利观念替代,农民的交际活动首先考虑的是“利”的获取,而不是“感情”的维系,熟人社会正在被陌生化。村民们反映,“从2005年开始,如果不是自家人,你是请不到人换气哩,你要拿钱,人家才给你做事情。”[13]
三
民族村寨社会的急速变化,引起了人们对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忧虑。有学者认为,在旅游的发展中,村寨的民族文化在出现某种“复兴”的同时,外来客商和外来游客却在不知不觉中“同化”旅游目的地独具地域特色和族群特色的文化,使民族文化传统出现了流失或变异[14]。还有学者发现,一些民族习俗“经过舞台化、程式化的包装”,“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内涵”[11],进而使“民族文化的精髓正在不断弱化甚至丧失,……民族应有的精神家园正在逐渐迷失。”[15]
其实,旅游开发并非民族村寨社会风气改变、民族文化消逝的“祸首”。新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村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云南省石林自治县湖村,有学者发现早在改革开放前,原本“具有年龄身份标志意义的传统民族包头全部被头巾和解放帽所取代;特色鲜明的传统撒尼服饰逐渐失去了穿着展示的时空场域;主要用于服饰点缀的传统桃花刺绣工艺也随之在撒尼妇女的日常生活中逐渐隐退。”[2]167在四川理县桃坪羌族村寨,20世纪80年代民族服饰就已基本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寨中除了老人、中老年妇女还常年穿着民族传统服饰外,其他人在生活中基本上都穿现代流行服饰,只有在参加婚礼或重大节日集会等浓重的场合才会穿民族服饰”[5]。
社会各界对旅游开发中的民族文化保护担忧,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他们从文化的多样性出发,希望在社会发展变迁中,各地域、民族都能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但是这种担忧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强势文化的某种“文化强势”,一些生活在现代城市里的现代人企图在民族村寨找回自己迷失的“精神家园”。在一些学者看来,旅游开发使民族村寨的社会风气“恶化”,人际关系越来越散发出“铜臭”,热情好客、吃苦耐劳、重义轻利等古朴民风消逝殆尽。“随着民族旅游业的发展,一些朴素美好的文化价值发生了明显的退化,如民风不再淳朴,商品短斤缺两等现象。不仅破坏了旅游的气氛,也影响了民族旅游的形象”[4]。有学者发现,随着旅游开发,“商品经济初期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所固有的那种尔虞我诈、惟利是图的本性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这此原本淳朴的群众当中,导致部分少数民族个体失去其固有的传统美德,个人价值观发生变化。”[16]这些现象确实在各民族旅游村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上述批评无疑也是城市“现代”生活的某种回应,反映了久居城市的旅游者对早已“失传”的古朴民风的某种向往。事实上,已经习惯“尔虞我诈、惟利是图”生活的“外来者”无权要求村民们在追逐“美好生活”时保持古朴民风。同样,我们也无权因为要体验“异质”文化,而要求年青村民们放弃幽雅、舒适的现代环境,重新回到树林里,在蚊虫的包围中“谈恋爱”。
笔者认为应该将民族文化视为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流体”,而非一成不变的“固体”。不断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任何文化的基本特征,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保存完好”的、被永远“冻结”的文化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文化是一种生存、生活方式,是一定生产方式、自然条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随着生产方式的变迁,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社会文化也必然发生变迁。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村民生产方式的变化,交通、通讯的发展,与外界信息交流的日益频繁,必然会导致民族村寨发生文化变迁。因此,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并非“冻结”,而是随着社会现代化逐渐转型,是在充分挖掘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适应社会的现代性变迁并保存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
[1]李天冀,孙美.“工分制”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模式成因的文化生态学探析——以贵州省雷山县上郎德村为个案[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6).
[2]肖青.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结构——一个彝族村寨的个案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
[3]王哲,胡晓.旅游发展对落茸社区生态文明变迁影响的个案研究[J].旅游开发,2009(4).
[4]刘青梅.现代化背景下民族村寨的传统文化及其变迁——以贵阳花溪区镇山村为个案[M]//“改革开放30年与贵州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暨贵州社会学学会2008年学术年会论文集.贵阳:2008.
[5]周丹.民族旅游与村寨文化变迁——以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为例[D].成都: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7:19.
[6]刘超祥.民族旅游村寨的人口移动与文化变迁——以湘西德夯村为例[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7]杨惠,等.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102.
[8]吴晓萍.屯堡重塑:贵州省的文化旅游与社会变迁[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
[9]吴其付.旅游发展与公共空间的变迁——以阿坝州理县桃坪羌族为例[J].旅游论坛,2011(4).
[10]袁洁.民族旅游开发与苗寨社会生活变迁研究[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5).
[11]刘琼.民族地区旅游效应下的社会变迁——以巴东县神龙溪漂流地罗坪村为例[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1(6).
[12]杨川梅.旅游“这碗饭”怎么吃[N].中国经济导报,2007-09-27.
[13]李仕蓉.旅游开发与石头寨社会关系变迁[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1:34.
[14]周星.旅游产业给少数民族社会带来了什么?[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5).
[15]贺能坤.旅游开发中民族文化变迁的三个层次及其反思——基于贵州省黎平县肇兴侗族寨的田野调查[J].广西民族研究,2009(5).
[16]范秀玲,蒋昌丽.促进民族文化与地域经济发展的良心互动——海南传统文化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中的物化[J].行政与法,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