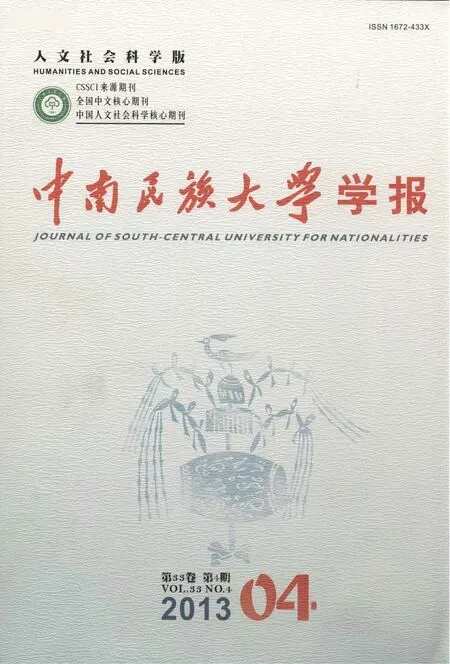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生产”——以东乌珠穆沁旗“那达慕”节日为例
2013-03-21邱泽媛
马 威,邱泽媛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民族文化保护》提出了“确定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目标,目的在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和传承发展,维护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完整;对于提高文化自觉,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至今,有5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后文简称“保护区”)先后得到文化部批准设立,已经承担起优化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保障“非遗”活态传承的重任。
然而,作为现代性产物的“保护区”,其存在意义和价值超过了保护“非遗”文化本身,体现了现代性对差异感的追求与建构,构成了“空间生产”现象。本文以东乌珠穆沁游牧文化生态保护区那达慕活动的个案为例,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后现代空间理论解析“保护区”现象,分析“保护区”操作中面临的两难问题,关注“保护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并为“保护区”的价值提升提供参考性建议。
一、空间的理论研究
空间研究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成熟而兴起和发展,对空间的思考是社会科学现代性框架的产物。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和齐美尔都对空间命题有所探讨,尤其是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将社会关系引入空间视角,认为空间具有社会性,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启发了空间的社会学研究[1]。而齐美尔的《空间社会学》[2]一文则明确将空间研究放置于都市化背景中进行审视,空间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被赋予了意义,从空洞的变为有价值的。20世纪6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城市化生活方式占据西方世界的主流。在理论界,空间正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后现代理论家通过以都市为代表的空间研究来对现代性进行批判与反思。
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以《空间的生产》一书开启了后现代主义的空间研究。列斐伏尔将空间作为研究主体,明确了空间的社会本质,“空间是通过人类主体的有意识活动产生的”,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在资本主义时代,“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内含于财产关系之中,也关联于形塑这块土地的生产力”[3]。
列斐伏尔将城市化放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中,全球化是城市化的全球化,无所不在的资本权力将所有的差异都一一抹平,“民族化通过控制时间来控制空间,全球化则通过控制空间来控制时间,全球化的实质是城市化,消灭代表历史差异的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将一切事物标准化和同质化”[4]。
为了反抗资本主义空间的“均质化”,列斐伏尔提出了“差异空间”的概念,差异空间的生产是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目标。实现“差异空间”的途径有二:其一是回归具有创造力的日常生活。“游戏的城市将改变日常生活的形态,它不再有平庸性或习惯化的单调乏味的工作,不再有恐怖”[4]。其二是改变生产关系,实现地域范围的自治。“将先前由‘自上而下’生产出来的社会空间,重新建构为‘自下而上’的空间,也就是普遍性的自我管理”,建立一种人道主义的城市理念,“社会主义的空间将会是一个差异的空间”(a space of differences)的构想成为列斐伏尔最终的乌托邦[5]。
在列斐伏尔的启发下,20世纪70年代开始,卡斯特(Castells)、布尔迪厄、福柯、詹明信、吉登斯、索加(Edward Soja)、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等学者基于空间视角对现代性进行了解读,产生了非常具有反思精神的空间知识体系。
总之,面对充满控制欲的、阶级分层的、消费主义的、碎片化的后现代主义空间,学者们持有批判态度,他们希望能够通过社区治理、微观政治、女性与少数族裔运动等差异化奋争来打破空间垄断,消除空间的区隔、断裂,使空间充满人的能动性,实现空间对人的意义承载。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虽然大多数“保护区”并不在城市,或者超越了城市范畴,但是,这一现象本身即体现了在城市化、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对于差异性空间的追求与保护。
二、作为文化空间的“那达慕”
本文选取的案例是在位于内蒙古东部锡林郭勒盟的东乌珠穆沁旗。由于该旗地势优越,自然生态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民俗事项保留完好,人们传承热情很高,内蒙古自治区将该旗作为保留和传承蒙古民族文化的重要地区。2009年底,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被首批列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生态保护区”,这一荣誉使该旗在保护传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传承之外,还承担了恢复和保护游牧生态文化的重任。2009年、2010年暑假,笔者连续两年受邀参加东乌珠穆沁旗举办的“草原文化节”,感受到当地浓郁的那达慕节日气氛。仅2010年一季草原文化节,该旗就举办了大大小小200余场内容各异,举办主体各不相同的“那达慕”,可以说“那达慕”成为串起草原文化节的珍珠,没有那达慕,就没有草原文化节。当地政府不仅积极兴办那达慕,还鼓励集体和家庭举办各个层次的那达慕。“那达慕”则成为东乌珠穆沁旗传承保护民族文化、整合民族文化资源、展示民族特色、凝聚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
“那达慕”从字面意义上有“娱乐”、“玩耍”、“玩笑”的意思,是蒙古族重要的传统娱乐节庆之一。草原生态与游牧生产方式是“那达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形态依托。那达慕形成于13世纪,其产生与敖包祭祀有关,元代之后,日益被统治者重视,屡次运用该活动形式推动内政和外交,“相传古代的每个家庭为了检查自己的实力、维护和分配草场,每年要聚会一次,大家在一起娱乐游玩,……远在十三世纪初,蒙古族的首领们举行大聚会时,要有规模较大的那达慕大会”[6]。该节日内容也随之不断丰富,不仅具有宗教意义、娱乐功能,还囊括了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歌舞文化等内涵[7],但是不论如何变化,包括摔跤、赛马、射箭三项在内的“男儿三艺”仍然是那达慕的经典项目[8]。
“敖包那达慕”是那达慕最古老的形式,围绕敖包信仰而开展的那达慕仍然是最具有生命力的形式之一。东乌旗境内有100座左右敖包,到1999年为止仍有69座敖包在进行祭祀活动[9]。敖包那达慕主要活动有搏克、赛马两种。
当地政府一直都在那达慕的举办中扮演主导角色。1986年,旗政府就在旗首府乌里雅斯太镇修建了占地1.7平方公里的那达慕会场。之后,每年政府都会在民间那达慕举办密集的时间段举办10次左右的形式各异的赛事或文化展示活动。
每次那达慕的开办都将蒙古族文化展示在这一特定空间内。在那达慕节日庆典中,可以看到人们对蒙古族悠远历史的追溯,人们搭建蒙古包、身穿蒙古袍来营造传统氛围,传统形式被一一调用,赞词、长调、“男儿三艺”等形式必然出现,内容中也多有赞颂“成吉思汗”、赞颂“长生天”等。
出于对长调的喜爱,笔者追随着参加哈扎布杯长调比赛的选手们,在一个个作为分赛场的蒙古包外转。虽然是首届举办长调比赛,但是报名的人数已经达到2万多人。人们来自四面八方,还有二十几位选手从外蒙过来。政府办公室秘书小张介绍说:“这些人都不止参加这一场比赛,从7月开始,各个盟、旗都有比赛,一直到8月份,有的人可以参加十几场呢,但是,他们宁愿不参加自己盟里的比赛,也要到东乌来”。东乌珠穆沁旗的长调比赛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该旗的长调文化氛围更为浓厚。长调大师哈扎布生长于斯。2004年7月,道·桑杰、东布日勒、德木其格、阿·呼和等热爱长调、有志于传播长调的人,组织了“东乌珠穆沁长调协会”。2005年,以该旗为主要代表的“长调”与外蒙一起成功申报了“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将东乌珠穆沁旗命名为“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长调民歌之乡”。2008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东乌珠穆沁旗“中国蒙古族长调之乡”的称号。所以,人们认可东乌作为长调之乡的象征意义,认为在这一空间中能够展示出更为纯正的蒙古族长调。
一个个蒙古包组成的赛场上所展示的不仅是歌,而且是蒙古族文化的凝聚。人们集中起来,就可以看出服装的差别,有的服饰色彩艳丽,用料讲究,款式宽大,有的则色彩黯淡,刺绣风格简洁,袖口和衣襟的滚边也不同。这引起了笔者的兴趣,政府办小张介绍说:“从他们服装的差别可以看出他们是来自哪里的,我们东乌珠穆沁的袍子用的布料颜色都比较鲜艳,滚边也比较宽大,图样复杂,绣工花费功夫更多。察哈尔的服装简洁一些,布料也不那么鲜艳。”7月的正午,气温很高,人们仍然身着厚厚的盛装,器宇轩昂。“我们东乌旗的人从小就有自己的蒙古袍,以后每隔几年都会再做一身,婚礼的时候再正式置办一件,以后每到隆重的节日就穿上。不管冷天还是热天。”(张 YB,女,29岁,东乌旗人,旗政府办事人员,访谈时间2010年7月27日)歌手们身着蒙古袍,华丽而庄严。歌手们选唱的曲目都是传承已久的,评委也以体现原汁原味的长调特色作为打分标准,“绝大多数蒙古族都会唱一些长调,现在学长调的氛围特别浓厚,小孩子几乎都会几首长调”。虽然长调比赛并不是传统那达慕的内容之一,但是人们已经认可了这种形式。
虽然孕育那达慕的物质与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那达慕承载的意义也发生着变化,但是,作为一种寄托民族情感和象征意义的那达慕却依然持续进行下去。那达慕总会在一定的时间里,为人们创造一个文化空间,人们根据对那达慕的不同理解向其中填充着多元和能指极为丰富的文化符号。那达慕浓缩了蒙古族对既往历史的追溯,建构着同一民族、同一地域、同一信仰群体的认同。同时,将很多新的元素纳入到展演中,被时代推动着拓展表达的空间。甚至工作居住在北京的蒙古族也要通过每年一度的城市“那达慕”实践“共同体的想象”,来个“精神游牧”[10]。
这里要关注的是政府的作用。虽然有些学者对于政府介入主办那达慕活动的做法颇有微词,尤其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篡改那达慕内容,在那达慕中间添加各种符合时尚潮流的内容。但是,笔者在注意政府负面作用的同时,也观察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组织、协调,并且给予经济支持,才使得那达慕的传承拥有了合法性,一些人正是在频繁参与官方那达慕后,产生了举办家庭那达慕的想法。近些年,除了官方举办的那达慕之外,更多的那达慕是由家庭、协会等举办的,而且官方在举办那达慕的时候,也会请民间协会的人士参与筹措。在那达慕仪式过程中,政府官员一般只在开场时出现,将官方属性镶嵌于仪式空间,随后他们很快消失,活跃在那达慕中间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参与者,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述说着对那达慕的理解。
东乌旗以其别具优势的天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被授予自治区级“游牧文化生态保护区”,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于复归游牧生产方式的期待。然而,就如同当年“定牧”是在政府主导下实现的一样,如今游牧生产方式也要在政府的主导下一步步回归。
在一次次的聚餐中,人们不断地将话题引入到“游牧”,“定居下来的就不能是蒙古人”、“保护草场也不能把人赶走”、“我们几千年游牧,都能把草场保护得那么好”、“应该在东乌恢复(游牧),让后代还能看到啥是游牧”。如果说,那达慕是浓缩的空间,浓缩的空间中已经培育了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回归,以及人们对于纳入生产方式为内容的文化空间营造,我们能否将这一空间稀释到一片更大的空间中,用文化回归带动生产方式回归,使东乌旗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呈现更为立体。
三、那达慕节庆民俗对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的意义
与内蒙古其他地区一样,东乌珠穆沁走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2010年,东乌旗生产总值达到58.7亿元,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34%提高到56%,实现了地区经济由畜牧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转型,资源开发和加工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最大,主要以原煤、有色金属开采与加工为主,与此同时,政府投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压缩农牧人口比例,使城镇化率达到52%①参见《2010年东乌珠穆沁旗政府工作报告》。。传统牧业形式也彻底改变,不再是一家一户的散养,而是以“公司+合作经济组织+牧户”的产业化模式,并将牧业切分为各个专业门行业,有专门饲养肉羊的、有专门饲养种羊的、有专门经营草业的现代家庭牧场。市场化、资本化、现代化的转型,已经根本改变了该地区传统游牧所蕴含的实体主义经济学意义,经济与生存、生态、文化都脱节了,变成了市场化的一个环节,草原空间面临着被均质化、资本化、科层化的威胁,草原、五畜与人不再合为一体,而是成为生产资本和驾驭资本的工具。正如列菲伏尔所描述的那样: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生产力与产物之中[6]。草原空间失去了本来具有的神圣性、生命力和文化再生产能力。
2009年,东乌旗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首批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一,“保护区”实际上就是在市场经济导致的均质化社会里建立一个差异化空间,使草原文化在这里能够生生不息地延续。“‘那达慕’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伴随和见证着蒙古社会游牧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成为蒙古人整体文化结构和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1],那达慕正是凝聚草原文化精髓,并作为差异性呈现的文化空间。“那达慕”字面上有“游戏”的意思,按列菲伏尔所言:“游戏的城市将改变日常生活的形态,它不再有平庸性或习惯化的单调乏味的工作,不再有恐怖”[4],那达慕的游戏项目一方面呈现了仪式感,同时,人们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体能、技能和创造力优势,摔跤手、骑马能手、歌手的荣誉感给予人们不甘于平庸的斗志,敦促人们参与竞争,展现旺盛的创造能力。人们在参与中,即使是作为观看者也在分享着不断创造文化巅峰、超越平凡的体验。另外,那达慕期间,人们用自己的力量营建空间,并参与空间管理,摆脱了科层制对空间的乏味切割。在敖包那达慕、家庭那达慕中,民众的自治力量得到充分实践,“地域范围的自治”在那达慕中具体而微地呈现,建立一种暂时抵抗市场化压迫,回归人文整体的文化空间。
四、结语: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及其运作模式
文化生态保护区项目实际上就是对于承载某一独特文化的地域划定出“文化空间”,执行特别规划,使之为传承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生态屏障,在其中,自然、地域、时间、人与文化五位一体,互相依存,空间留存时间,时间丰富空间,人为空间赋予文化的意义,空间又反过来承载着人对文化的表达,“文化空间”体现了文化传承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使文化在这一空间中得到活态承继。
对于“保护区”的认定,主要依据以下原则:一是传统文化历史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并为社会广泛认同。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分布较为集中,且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和鲜明的区域特色、民族特色。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良好。四是当地群众的文化认同和参与保护的自觉性较高。
在实际运作中,“保护区”结合了商业运作、政府操作和民间合作等多重维度,包含了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主体性/客体性、同质性/异质性等多重张力,构成了具有复杂性和深度的文化读本,为空间研究提供了适合的阐释对象。
1.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如前文所述,“保护区”建立的目的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这些“非遗”大多是在历史的代代传承中逐渐孕育成型,与独特的人文生态相互依存,成为地域性很强的文化景观,其价值在于它的差异性。借用中世纪历史文本学的一个概念“历史重写本”(palimpsest)来比喻“保护区”,这一词源自中世纪书写用的印模,原先刻在印模上的文字可以擦去,然后在上面一次次地重新刻写文字[12]。重写本的价值是独特的,独特的之处就在于它不可复制。一个“保护区”就是一部“重写本”,其文化价值在于时间的堆积和沉淀所形成的差异性。“保护区”是在普遍的抽象空间中隔离出绝对空间,用空间来抵抗时间的侵袭,让“发展”的脚步慢一些,甚至绕过“文化生态保护区”,使文化生态保护区成为文化价值传承的净土,实现传统文化传承的价值理性。
然而,在操作中,“保护区”所拥有的文化差异性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商业资本,短视的急功近利往往使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人们迫切地用货币来衡量稀缺的“差异性”,“保护区”成为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法宝。而且越是“保护区”,越具有差异性,越成为资本追逐的对象,开发价值潜力越大,以此吸引的商业资本越多。“远离商业”的目标变成了“商业空间”建立的手段,而货币一旦进入对空间的衡量,就会造成空间的碎片化,失去它的完整价值。如政治理论家西奥多·罗伊(Theodore Lowi)所言:“理性被用于市场之中,也同样被用于市场之上”,“后来被置于其他所有价值之上”[13]。
2.主体性与客体性。在充满批判精神的后现代空间理论中,学者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空间对于人们主体性的挤压,而认为“回归主体”即是解放的象征。詹姆逊也呼吁要通过“文化自主”来使我们“能够面对过去的空间想象力”[14]。
世居于“保护区”内的人们是文化的创造者、承载者和传承者,他们创造性地构建了地方文化,把握了对文化空间的阐释权,也最终决定了文化会以何种方式存在下去。所以,对空间的保护首先要落实于对人的保护,对人的保护则需要落实到对人主体性的尊重。
在制度层面,对主体性的保障体现于两个方面,第一,借用社区原有的政治资源。任何文化社区都有或曾有原生的权力系统,这些权力系统对于文化的形成和再生产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微观政治往往会形成对国家行政力量的制衡,减弱外界对内部文化资源的冲击。第二,建立民主管理方式。保留传统权威,并不是鼓励建立社区威权,民主管理才是体现主体性的根本保障。在“保护区”的实际运作中,应该充分发挥社区民众的主体作用,组织文化管理委员会,制定本社区文化方面的各种保护条例,实施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保护区”是对某种文化形态的保护,但并不是对其封闭,现代人不能为了投射对于过去美好的梦想,而将保护区隔离于发展之外,在现代社会,人人都有权利分享现代技术所带来的便捷。所以,生活在“保护区”的人们同样可以决定发展的方式,同样可以在传承的基础上过着现代生活,而事实证明,只要处理得当,传统与现代可以并存,人们可以在其中进行自主的选择。
3.差异性与均质性。文化特性是代代相传的固定不变的事物,与区域紧密联系,而文化空间逐渐受到种族或民族观点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血与土”的联合体,文化景观被看作是装载传递文化财产的容器。不同的文化空间拥有不同的文化风格、文化面貌,也有着异质性的人文素材和历史底蕴。
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文化多样性带给人类的福祉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文化多样性注意到人类以往所有经验、智慧和实践的精华。只要一种文化清楚本身的特质,它就能够从与其他文化的比较中获益良多”[15]。
[1]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吉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M].林荣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M].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Cambridge USA:Blackwell,1991.
[4]吴宁.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J].社会,2008(2).
[5]列斐伏尔.空间:社会的产物与使用价值[M]//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55.
[6]邢莉.游牧文化[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7]邢莉.蒙古族“那达慕”的变迁[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5).
[8]萨仁高娃.蒙古族“那达慕”以及文化意义[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1).
[9]百丽丽.草原牧区“那达慕”的传承与保护[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08.
[10]纳日碧力格.都市里的象征舞台[M]//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56.
[11]扎格尔,巴雅尔,巴特尔.蒙古游牧文化溯源[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36.
[12]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7-28.
[13]尼古拉斯·恩爵金.场所、地区和现代性[M]//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359.
[14]Jameson F.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364
[15]张玉国.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