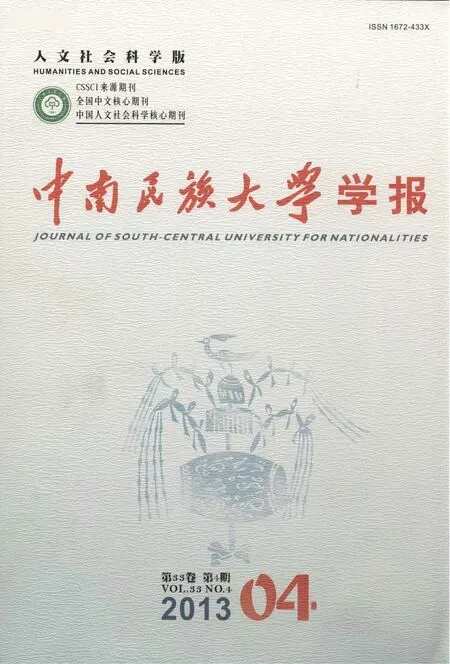客家婚礼饮食行为的社会记忆与象征隐喻——以广西博白县大安村为例
2013-03-21石奕龙
石奕龙,谢 菲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自早期进化学派以降,人类学从不缺乏对饮食及其行为研究的兴趣。从饮食行为作为集体欢腾的社会事实到区隔社会阶层的指示,从饮食系统中生食∕熟食、可食∕不可食、洁净∕污染等结构性对比关系中建构分类与秩序的象征体系到食物作为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认同的象征符号。总之,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我们选择吃什么、怎么吃、和谁吃等并不仅仅是人的生理需要而已,更是社会关系、文化偏好与物质资源价值判断和选择的反映与指示。
至于人类学将饮食与记忆并置思考的命题,由于受记忆与社会关系讨论的局限,直到晚近才方兴未艾。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感官人类学的发展,陆续有部分学者从身体感官的角度,讨论饮食、身体经验与记忆的关系。尽管在西方哲学或物理学的探讨中,对于物质与记忆的关联早已被笼统地认定为先验性的前提,认为食物的颜色、形状、触觉、声音所建构的感官经验,是人类理解周遭世界、获取知识和凝聚记忆意象的主要资源。但是,这种概念前提,如何具化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如何型构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却有待更深入、丰富的民族志资料的检验[1]。基于以上的思考,笔者尝试从广西博白县大安村客家婚礼饮食行为的结构展演中,探讨饮食行为、身体记忆与仪式的互构方式及其关系。
一、饮食、仪式与社会记忆
作为一个族群社会秩序的道德感召力,社会记忆与所属群体的各种社会实践交织互渗。美国社会学家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以记忆在历史积淀或积累的方式不同,将社会记忆的实践分为体化实践(incorporating)和刻写实践(inscribing)。前者以当下身体的举动表达与传播信息,后者以文字记录的方式捕捉与储存信息[2]。可以将前者视为“身体记忆”,将后者视为“文本记忆”,它们都属于社会记忆。
作为社会记忆或文化记忆的一种传承方式,仪式是现场的、直接的,受到时空限制,需要通过人们的亲身参与才能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属于一种典型的体化实践或身体记忆方式。美国社会学家贝格森(Albert Bergesen)根据仪式行为及所参与人群范围的大小将仪式划分为微、中、大型三个层次,三者各有指向。微型层次的仪式(Micro-rites)指的是一个人类群体规范化后的仪式化用语,中型层次的仪式(Meso-rites)相当于集团内部的个人在日常生活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而大型层次的仪式(Macro-rites)就是那些需与日常生活区别开来的集体性的庆典仪式[3]。对于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个体而言,婚礼是个人生命通过仪式的一个驿站,具有重要的教化功能与意义。作为婚礼仪礼的一个子系统,婚礼主角的饮食行为与日常生活的饮食行为有所区别,但同时,它也离不开所属群体的亲身参与和见证,因而其呈现出贝格森所分类的大型仪式的特点。
《礼记·礼运》记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作为一种具象的社会行为,饮食在祭祀礼仪的启示下萌发了食礼的最初形态。“衣食既足,礼让以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现象和社会关系认识的不断丰富与深化,“礼”的初始意义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其内涵不断地向外延伸与拓展,远远超出了祭祀活动中恭敬而虔诚仪式的狭窄范围,广泛地涉及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关系的内涵,也涉及行为规范、惯习等方面的含义。
尽管“礼”的范围与意义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人生仪礼依旧是“礼”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现代乡民社会中,人生礼仪饮食习俗除了承继对神灵的崇敬之外,更多的是表达和体现人生礼仪活动中,具有心理需要和社会交往的群体对于现实利益的诉求。
在特定的婚礼仪式中,围绕“礼”的文化精神,群体对于饮食行为的编排(choreography),大多是通过礼仪主角的身体记忆来表达和实现的。这种身体的践行是群体社会价值理念的展演与再现。正如萨林斯所言:“物质力量本身是没有生命力的,它们的特定意向和确定结果只能通过将其与文化秩序的坐标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解释。”[4]作为一种物质存在的可见性,仪式主角饮食行为的编码与婚礼仪礼的精神所在唇齿相依,不可分割。在婚礼仪式的行进过程中,礼仪主角的饮食活动与婚礼仪式的情境相关联而显现其意义,婚礼仪式的本质层面也需要借助特定主角的饮食活动的身体记忆来展现自我,而它们的糅合即婚礼饮食行为以物质实体与感官经验的互动过程展演深层次的象征符码,将地方文化的历史记忆、现时的饮食行为与个人社会角色的未来命运紧密连接,持续传递群体的文化价值与理想。
从仪式的结构而言,婚礼仪式的规矩是用某种联姻的社会学系统取代源自生理的血缘关系系统。这样一来,婚俗规矩和亲缘关系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语言[5]。作为一种体化式的语言记忆方式,婚礼仪式的饮食行为并非建立在对需求与享受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物品/符号)的编码之上。在婚礼仪式上,物品与符号、能指与所指,构成了一个全面、任意、缜密的符号系统——文化系统,用一种分类及价值的社会秩序取代了自然生理秩序。它通过物化的符号——食物,将个体身体记忆的体验与群体一致的文化诉求相连接,以身体力行的体化实践,通过身心愉悦的释放将社会规则与理念内化为自我的行为指向,复述与强调地方性知识与生活策略。
二、客家婚礼饮食行为展演与结构
在闽、粤、赣客家聚集地之外,广西是中国客家人的第四大聚居地。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桂东南地区。大安村位于桂东南地区的玉林市博白县龙潭镇,是一个中等规模的纯客家人的村落。据该村各姓氏族谱记载,最早定居该村的客民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时期,其始祖主要来自江西与福建两地。因迁徙来源和时间的不同,大安村逐渐形成了围绕宗祠聚集而居的村落生活空间布局。这种空间聚落的生成是迁徙群体为了自身族群生存与发展需要而考虑的结果。与此同时,这种思量也潜隐在该群体“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婚礼观念中,通过婚礼主角的饮食行为的身体记忆,一次次予以强调与重申,主位地将此体化实践展演自我表称为承继了中原正统汉人的文化传统。
在大安村客家婚礼饮食行为的结构体系中,涵括了男女双方共食、分食的食物,献祭食物,以及食物性礼物等,甚为复杂与繁琐。为了论述方便,本文先以婚礼举行的顺序为线索,对饮食行为予以展演与分析。
1.婚前。在大安村,正式婚礼前有“看家门”、“提亲”、“定亲”、“过礼”等一系列的习俗。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家庭设宴款待外,茶食成为双方是否订立婚姻关系的一种无声表达方式。无论是女方上男家看家门,还是男方上女家提亲,都通过以茶相待的方式来表明对对方的是否首肯,是否可以履行婚姻的下一步程序。女方上男家看家门,男家以茶为礼,即表示愿意继续,女家饮茶则表示愿意继续,如不饮则表示不愿继续。男方上女家提亲亦然,女方如果愿意,就端出茶来,如不愿意,就不上茶。当然,此时的茶食与平常待客的茶食是不同的,即在看家门、提亲的相亲环节中,男女双方家庭都以用片糖、橄榄、木瓜条冲泡而成的茶食相待,以示重视与喜庆之意,并以此身体记忆之体化实践来象征其遵从中原汉人的传统。因为在汉人的婚礼仪式中,这种以茶为礼的习俗自古有之。据宋人的《品茶录》记载:“种茶树下必下子,若移植则不复生子,故俗聘妇,必以茶为礼,义固可取。”古代汉人订婚程序中以茶为礼是取其不移置子之意。也就是说,订婚阶段行礼用茶是通过茶树生长的“茶不移本,植必生子”的自然特性来暗喻喝了定亲茶,两家之好就已缔结,便是从一而终,铁定不移,绝不反悔,而且也暗喻两家男女青年一旦完婚,其必能繁衍后代,瓜瓞绵延。因此,这一阶段的茶食俨然成了双方融洽感情,订立婚姻盟誓的一个见证,也成了鉴证姑娘、小伙品德的一个象征。故汉人民间常有“好女不吃两家茶”之说。
在繁复的婚礼程式中,过礼也是一项必备的程序,一般选在正式婚日前十五天举行。在大安村,村民们普遍认为女儿的出嫁不仅是娘家抚养其长大在经济上的一种损失,也是未来其家庭现实生产劳动力的直接缺损。因而在定亲与过礼阶段,男家都会以礼钱或实物的形式对女家进行适当的补偿。所以,在当地,婚前过礼的食物是相当丰盛的,除了制作宴席的米、沙虫、虾仁、楠粉、红枣、橄榄、瓜子、喜糖、饼干等礼物外,两只阉鸡、两只鸭、猪肉,一对红烛,两瓶酒,一对猪腿(分别赠送给女家的媒人和外婆)是主礼,当地人称为“五味”(客家话谐音),其数量和内容,一点也不能差次。在切割和重量上也十分讲究,切割时必须顺猪头到猪尾的方向进行分割,重量须带有八或九的尾数,以喻示这对新人的婚姻能白头到老,长长久久,发财发人之意。相对于其他的食物礼物,过礼仪式中的“五味”并没有强调其物质的原初性,而是将其转换为更深层、更复杂的文化符码:以仪式场景中切割数量与形式的瞬间行为置换为新婚夫妇对历时性婚姻生活的追求。过礼后,按照规矩女方需回礼。回礼的礼物看似简单,但意义深远。即回送一对公鸡和母鸡,喻意新婚夫妇婚后的生活成双入对,有子有后;由送礼人带回去给新郎食用的食物是用一双筷子串成的一个熟的公鸡头、一对翅膀和一个鸡尾。公鸡头代表新郎的威严,翅膀则寓意新婚夫妇即将成为男家的左臂右膀,能撑家立业。鸡头与鸡尾相连,则预示新婚夫妇未来婚姻生活有头有尾。
婚日前两天是新娘开面的日子。男家会遣人送来带双数的开面礼:鸭子、面团、红烛、红鸡蛋、红包。开面时,“全福人”一边用熟的红鸡蛋和面团来回替换着在新娘的脸上揉搓,一边讲吉言。值得一提的是,鸡蛋在婚礼的开面以及稍后的洞房撒帐仪式中是重复出现的,而且针对的对象都是新娘。在大安村村民的文化意象中,母鸡与妇女、鸡蛋与子嗣被想象为具有同一性,如无生育能力的已婚妇女被村民戏谑为“不会下蛋的母鸡”。鸡蛋是当地人向神灵祈子的主要食物之一。在日常生活中,村民向神灵祈求子嗣时都会将个人心愿通过鸡蛋这一媒介向神灵表达,并用与女性接触方式予以实现。因此,鸡蛋在婚礼的仪式场景中频繁地使用,成为增强妇女生育能力的一种吉祥的象征性食物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朴素自然的表达方式,不仅是古代卵生神话累积而成的食物致孕观念的直接反映,也是将自身的生育与鸡产卵视为同类互渗现象的一种思维方式。
在大安村,婚礼前日,女家还有宴请乡邻与亲戚吃汤圆的饮食行为,应和着“结婚吃汤圆,幸福又团圆”之意。请吃前,新娘需盛五碗汤圆上祖堂祭拜,请祖宗先行食用后,方能群食。
2.婚日女家的饮食行为——食离娘饭。婚礼当日,在父母的引领下,新娘备好三牲、米饭、楠粉、茶、酒等,上祖堂祭拜。这既是出嫁女向祖宗辞行的离别仪式,也是一次成年仪礼的教育仪式。在此仪式上,父母需对即将出嫁的女儿进行教育。礼毕后,女家备酒席款待亲朋好友。在酒宴上,新娘一一向宾客敬茶斟酒。此时,在整个仪式中,新娘处于与娘家分离的阶段,因此禁止在此宴席上进食,否则视为不敬。
迎娶当天,新娘唯一在娘家食用的饭菜,称为“离娘饭”,且必须在其闺房里食用。食用之物是新娘在祖堂拜祭时的供品,内容包括一碗米饭、一个鸡腿、一盘辣椒猪肉炒楠粉。这是出嫁女在娘家食用的最后一餐饭,气氛颇为凝重。不管姑娘对娘家有多么不舍,情绪伤感。按照规矩,她必须尝几口离娘饭,但又不能吃完,需把吃剩的饭菜放在娘家的米缸上,意味着把新婚的福禧之气传递给娘家的弟弟或侄儿等男性同辈或子嗣,或者寓意不能把娘家的福禧之气完全带走。这种与平时不一样的模棱两可的饮食行为与中原一带盛行的“催轿汤”有异曲同工之趣。与离娘饭一样,“催轿汤”是新娘临行前,娘家嫂辈特做的一顿饭食。食用时非常有讲究,新娘既不能吃完,又不能不吃。探寻其中的缘由,当地的民歌唱词“如若是喝了吧,怕娘家穷;如若要说不喝,怕穷婆婆;罢罢,我喝一半,留一半,两头都过好生活”[6]的表述,揭示了个中含义。可见,客家人的离娘饭与中原汉人的“催轿汤”同样具有蕴涵“福气、财气”之意,成为人们试探新娘心思的一种饮食行为。不过,对于这一用意,新娘都会事先被告知。由此可知,“食离娘饭”原本具有的社会功能已经丧失,已逐渐蜕变为当地婚礼实践中的一种程式化的饮食行为。
在大安客家人的婚礼仪式结构中,仪式主角的这种程式化的饮食行为仍具有某种意义,因为其与婚礼仪式结构中处于过渡的阈限期有着密切的关联。阈限期是人生礼仪活动中的一个特殊时期。它是“介乎两种状态之间的过渡时期。”在此过渡阶段,“新人是‘模棱两可’的,他的位置既不在这里又不在那里。”[7]在大安客家人的婚礼当中,当新娘在祖堂中拜别自家祖先后,即进入了这样一种阈限期,因此,她的位置“既不在这里又不在那里”,模棱两可身份所导致的饮食行为及其心理表述的“模棱两可”,显示出在此阈限期中仪式主体正处于角色转换中,食离娘饭这种身体记忆形式也就充当了仪式主体——新娘此时角色转换的体化实践展演。在婚礼行进的这一过渡期中,新娘的“不确定”性或“反结构性”饮食行为——食离娘饭,既昭示了作为娘家女儿与夫家媳妇角色欲图两全兼顾的矛盾心态,亦成为大安地方社会群体对人生礼仪的某种过渡仪式中角色变换的一种认同方式。
3.婚日男家的饮食行为。结婚当日,新婚夫妇在男家有关的饮食活动包括“喝交杯酒(茶)”、“闹洞房”、“撒帐”、“拜祖宗”、“行捧茶钱”等习俗。
婚日上午,新郎在亲友的陪同下到新娘家“娶亲”。女家设筵招待女婿及其迎亲的宾客,然后择时“发亲”。到男家后,新娘与新郎双双被迎进洞房,端坐在床前。由男家的嫂辈请两位新人喝交杯酒(茶)。这是大安村婚礼过程中,新婚夫妇唯一的共食行为。对于这一共食行为所隐含的象征意义,韦斯特·马克在《人类婚姻简史》一书中予以翔实的论述:“这种共食婚俗,也是一种以共同行为表示双方结合,并对双方产生相互约束的仪式……,共饮如同共食一样,首先也是一种表示男女结合的象征,或者是作为加强夫妻关系一种手段。”[8]在新婚夫妇履行完交喝杯酒(茶)仪式后,一群孩子特别是男孩争先恐后地涌入洞房,在家长的怂恿下,爬上床翻滚、嬉戏,以图子孙成群的吉兆。
洞房是新婚夫妇孕育生命的场所。村民们习惯将特定的食物摆放在洞房里,表达早生贵子、多子多福的意愿。如梳妆台上摆放一对果盘,盛有橄榄(意“揽子”)、红枣、花生、桂圆、瓜子(意“早生贵子且花着生”)、木瓜条(意“多子”)、冰糖(意“婚姻生活甜蜜”)和一对煮熟的红鸡蛋等食物。在婚床的角落里,都会放置一个盛有米、谷、炒米花、冰糖等物的“福筐”。新婚之夜,男家邀请村里的“全福人”负责挂蚊帐,铺被子。铺床时,“全福人”把炒米花撒在床上,边撒边吟唱:“富贵双全,白头偕老,天长地久,子孙满堂。”如若不然,村民认为新娘会落下腰痛与家庭无后之虞。
俗话说,不拜祖宗,新娘子还算不上一家人。新娘欲成为夫家的一员,开始新家庭的生活,上夫家的祖堂认宗拜祖是必不可少的一项程序。供奉时,新婚夫妇把子孙被铺设在地,设案摆放一只撒有粗盐的整鸡、一块带皮的五花肉、一条咸鱼、两碗发糕(意“发人”、“生活步步高”)、五碗饭、三杯茶、五杯酒,点香燃烛三叩九拜。在大安村客家人的认知体系中,祭祀活动的祭品在天神、祖宗与灶神、鬼等不同等级的超自然力量面前,其丰俭程度、呈现和处理方式是有清晰明显的界限。首先,对于以天神、土地伯公为首的神灵,村民供奉的祭品最为丰盛,用全生、完整的五牲与五素敬供。其次,对于供奉神明与祖先的祭品的区分是模糊的,只有调味的区别。除观音用素食供奉外,其他神灵如花公、花婆、妈祖的供品,与祭祖供品并无二致,只是在烹调上略有差别,即在祭供前稍加烹煮但并不调味,属于半生状。不过,在当地,灶神和祖宗是一并供奉的。特别是新嫁入门的媳妇,厨房是她们日后劳作的主要场所,更是尽其礼数,虔诚祭拜。祭品只是常人所食之物,即煮熟的三牲。除鸡外,其他祭品都是不完整的,如猪肉只是一大块,鱼也只是用干咸鱼替代。盛放时,撒了些许粗盐调味。经过拜祖与祭灶等一系列的仪式,新过门的媳妇才能算是男方家庭的正式成员。
婚宴后,有新人向宾客敬茶的习俗,即宾客喝新娘所敬的甜茶,此即所谓的“食新娘茶”。敬茶时,由媒人或家人作伴,新郎新娘手端茶盘,以甜茶敬宾客,客家人也称之为“认亲”,即亲戚朋友借此认识新娘[9]。宾客受其茶,饮毕,将红包压于茶杯下为贺礼,讲吉言以贺之,此钱俗称“捧茶钱”。
4.婚后饮食行为——头面春。婚后第二天,新媳妇给公公、婆婆舀洗脸水,敬茶。男家“摆朝”(客家话,摆酒席之意)款待前来探朝的女方父母兄弟等亲戚。摆朝过后,新娘与新郎就可以回门了。
结婚翌年春节的初八或初九,新婚夫妇在小叔(或小姑)的陪同下,带着婆家制作的发糕回娘家认亲戚门。发糕是男方根据女家村里的户数而定制的,一户一对。到达娘家后,新婚夫妇在女方父母的引领下,主动上门介绍自家的新姑爷,赠送发糕。村里人热情地把新姑爷请进家门用酒食招待一番。为讨吉利,每家每户都会在酒桌上摆放白斩鸡这道菜,以示对新姑爷的厚待。回家时,在女家哥哥或弟弟护送下,夫妻俩带着娘家回送的发糕和饭心而回。如若当年新婚夫妇带着自己小孩而回,娘家定会回送一对公鸡和母鸡,俗称“带路鸡”,喻示新婚夫妇凤鸾和鸣,传宗接代。这一系列过程,当地人称为“头面春”。它不仅表示该习俗发生在一年之初的春节,也隐喻娘家人招待新姑爷满面春风、热情备至之意。
“人生礼仪虽然总是伴随着各种生理特征方面的转变,并以此为前提条件,但更为重要的意义却在规范与培养作为社会的人的方面。”[10]人生礼仪活动不仅仅是一种对主体社会角色单纯性的转换与认同仪式,更重要的是蕴涵了对主体社会角色权利与义务的教化与规范意义。在婚礼饮食行为结构中,这一功能通过新娘的饮食行为诠释得较为细腻与通透。在婚礼中,新娘的角色转换和认同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订亲阶段,“定亲茶”的饮食仪礼让新娘开始进入了即将成为新社会角色的心理预备期,缓冲了其对未来生活的不安与恐惧。迎亲当天,新娘用三牲向自家祖宗的辞行,如同一次深刻的成年教育仪式,接受祖辈的教导和嘱托。过后,新娘食用供祖的食物,通过饮食的方式,新娘把祖宗的教诲完全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以期在未来的新家庭能较好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迎娶后,男家祖宗对新娘身份认同是首要的,拜祖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接着,新婚夫妇行“捧茶钱”的饮食习俗逐渐把人生礼仪引入男家亲属对新娘身份认同的阶段。巧妙的是,大安村的客家人依托新娘敬茶、亲属喝茶的方式,把拘束的家庭社会等级关系的认同场面自然而然地融入饮食当中,彻底消除了新娘作为男家新成员初次待客的局促。随之而来的宴席,则把角色的转换与确认推向了社会认同的阶段。婚后第二天,新娘以新的社会角色(媳妇)示人,给公公、婆婆敬茶,最终完成整个仪式中新娘社会角色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角色中。
三、客家婚礼饮食行为的象征隐喻
作为知识对象或者话语对象,身体往往被看作是社会的构成。在婚礼中,婚礼的仪式主角通过在场参与的群体其他社会成员,根据社会规则用审视目光注视自己的身体,不断重复并修正自己的饮食行为,以符合社区的社会期待,完成群体通过仪式的社会教化与洗礼形式,承接与转换个体生命历程与社会角色,体现不同社会阶段个人社会存在的意义。个体的社会存在与意义,往往通过与他者的联系予以凸显。在婚礼仪式中,仪式主角的直接饮食之物以及与之发生关联的饮食对象,往往通过集体性的仪式庆典活动一一呈现。这一无声的交流方式,无论是仪式主角的饮食行为,还是仪式场域中饮食物品的陈展,都是通过仪式主角的吃的行为,以及参加群体的体会与经验给予淋漓尽致的解码与诠释。反之,这种身体行为编码以族群社会规则为圭臬,以个人与群体基于共同文化记忆积淀的身体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生理机制,通过个体体化与群体欢腾的方式,对族群文化模式予以复述与强调。
1.视觉象征。在大安村人生礼仪主角的饮食习俗活动中,视觉象征并不依赖于个体的进食行为予以表达,往往根据日常生活中常见食物的形状、颜色、数量等直观可视的显性信息,赋于食物特殊意义和功能。首先,这些食物原初形态与村民观念意识中的事物具有直接的相似性。在视觉上,这些平常之物在婚礼仪式上将族群社会的历史记忆和人生礼仪主角的现实与未来连接在一起,洋溢着吉祥、幸福、快乐等愉悦之感。如在婚礼的过礼程序中,女家回礼中打发给新郎吃的食物,即用筷子串起的一个首尾相连的熟鸡头和鸡尾、一对双双欲飞的鸡翅膀,生动逼真地表达了女家对男方及其新婚夫妇未来生活的期望。其次,在当地村民的意识中,食物所呈现的颜色是直视可见的,通过人生礼仪主角的饮食活动,可以自然而然地渗透与转化到个体身上,对该对象产生积极有利的效果。如婚日当天,新娘食用的红糖汤圆,极富表现力地渲染着人生礼仪活动的福喜之气。
除食物形状与颜色之外,食物的数量是视觉象征符号体系的又一个直观性符码。在大安村婚礼仪式中,除祭品外,食用与陈设的食物一律以双数呈现,以图吉利。单数往往忌讳。
2.味觉象征。饮食视觉象征是通过视觉的一目了然予以编码,而饮食味觉符码构成则需借助食物味觉的内在特质进行推理与演绎。在大安村婚礼主角的饮食习俗活动中,用食物的味觉类比生活实践结果的例子俯拾即是。如用食物的甜味比喻生活的美满,如新娘所吃的红糖汤圆。不过,运用食物味觉的内在属性进行类比与转换,最为深刻的是拜祖与祭灶、祈福禳灾的祭品。村民通过祭品的生熟、调味与否,象征与其亲疏远近关系的超自然力量。
3.听觉象征。听觉象征是大安村人结合客家方言的读音,把谐音现象广泛运用到婚礼主角饮食习俗当中,以期通过单字和嵌入式发音的方式,在听觉上产生音近相谐,意蕴纷呈的效果。如婚礼中,洞房摆放的橄榄(客家话“揽子”),象征新娘婚后早日揽子在怀等意义。这种谐音现象是通过一种特定食物类比某种观念,具有单一性;而嵌入性谐音现象则是通过撷取几个不同名称食物中的一个字,嵌合成一个符号簇,赋予吉祥、幸福的内涵。如婚礼中常见的红枣、花生、桂圆、瓜子,象征新婚夫妇能够早生贵子且花着生。由于话语同音异义的特性,在婚礼仪式活动的不同场域,同一食物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如婚礼仪式活动出现频率较高的发糕。它可以谐音为高兴、婚后家庭人财两发,生活步步高等吉祥寓意。因此,从物质层面同音异意的多样性与听觉经验的契合中,可以反映出大安村客家人的身体记忆模式并非依赖抽象性的逻辑概念而一成不变,而是趋于重视情境、情绪和意象性讯息的即时转换。
4.触觉象征。在大安村婚礼仪式中,触觉感官体验往往利用特定食物的属性和功能与仪式主角的接触,使其具备同样的属性和功能。尽管这些食物在仪式过程中并不被仪式主体通过身体进食的方式予以消解,但食物与身体的接触能达到和体化同样的效果与作用。因它以触觉为媒介,将其固有的属性、功能与特定的个体联系起来,并予以移动和转化。如婚礼仪式中频繁出现的鸡蛋,以其卵生属性,与新娘的每一次接触,就将其旺盛的生殖力传递给新娘;吃剩的离娘饭放在娘家的米缸上,以物物接触的方式,无形地将新娘的“福禄”之气传递给了娘家的男性子嗣。
综上所述,仪式食物作为特定情境的一种重要媒介,比起其他器物具有更高的普遍性、生活性、愉悦性等特质,也蕴含更丰富多样的感官层次,如触觉、味觉、嗅觉与视觉等等。因此,在婚礼仪式中依次使用的茶食、离娘饭、鸡与鸡蛋等食物,透过其在仪式中的作用与角色的转换和多种感官知觉连生共感(synesthesia),唤起对客家文化的记忆与维系。同时,附着在仪式食物中的多种感官特性,如红糖汤圆的黏与甜,发糕的膨胀,或猪肉的切割方向,随着仪式进行中食物的食用和交换,而成为跨越时空界线的文化意象的关键要素。加之,处理食物的仪式情境如离娘、认亲的叠加与强化,催化了多重感官知觉的共鸣运作,交织形成丰富而生动的记忆要素。这种共同分享和体会(embodiment)的食物经验,使得一些难以言传的记忆符码得以在不同世系的大安村人身上展现,持续传递客家人对美好生活期盼与向往的人生价值和理想。
四、结语:物质、感官与记忆
纵观大安村婚礼主角食俗的表达方式,视觉象征、味觉象征、听觉象征、触觉象征是饮食象征符号以群体身体感觉和知觉的方式,对婚礼礼俗文化的一次次展演与体味。在婚礼中,人生礼仪主角的“举止姿态可能有高度的结构性,完全可以预见,尽管它既不挂在嘴边,也不有意识地教;它可能如此自动,以致不被认为是能和行为分开的部分。”[2]而且,在婚礼仪礼的实际信息交流中,四者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如婚礼中用作礼物的“五味”,村民们对其切割方向和重量尾数所要求的旨趣,巧妙地将视觉象征与听觉象征结合起来,赋予了食物自我观念与意识,内涵深邃隽永,回味无穷。
细究大安村的饮食象征符码,大都是与当地人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之物,由于独具特色的外形或内在属性等形上特质(mete-properties)而被选择强调成为转换中的不变体(invariants under transformation),在婚礼的不同场景中征用,成为背负婚礼仪式文化思想与意念的一个承载体,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构筑了一个物化的交流平台。因此,物质符码作用力的来源,不见得需要完全的模仿,也不一定需要透过视觉,有时可能在实际行动过程衍生的不同感官经验之中转移和延续[11]。这种身体记忆模式强调物质符码与感官经验共鸣的互动作用与效果,具有长期累积、沉淀与转换的特性,而此种特性是在特定的社会中孕育与成型的。从身体记忆的角度而言,广西客家婚礼饮食行为所型构的文化真实并不是科学与理性的真实,而是物质符码与感官经验交织情境下的一种建构性的真实。
[1]胡家瑜.赛夏仪式食物与Tatini(先灵)记忆:从文化意象和感官经验的关联谈起[M]//黄应贵.物与物质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4:174.
[2]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91.
[3]王霄冰.文化记忆、传统创新与节日遗产保护[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
[4]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M].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68.
[5]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61.
[6]任聘.民间禁忌[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42.
[7]维克托·W·特纳.模棱两可:过关礼仪的阈限时期[M]//史宗.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下).金泽,宋立道,徐大建,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512.
[8]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简史[M].刘小幸,李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28-129.
[9]苏斌.桂东客家人[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71.
[10]郭振华.中国古代人生礼俗文化[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8.
[11]Gell Alfred.Art and Agency: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