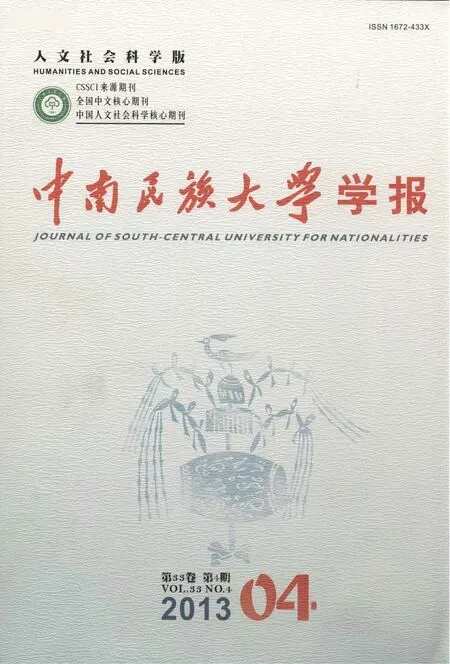试论西方国家的“宽容”与少数群体权利
2013-03-21何俊芳
冯 润,何俊芳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宽容是人或群体之间的处事原则,它既可以是一种个人态度,也可以是一种保证人或群体之间平等共处的制度安排。西方国家提倡宽容,在维护个人权利的同时,赞同少数群体拥有一定的群体差别性权利,并包容和接受文化多样性。但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此种差别性权利要求的宽容限度在哪里?当群体成员的个人权利受到少数群体行为的侵犯时,国家是否应该干涉?该如何干涉?实际上,不同的国家参考个人权利为其所奉行的宽容设定了自己的限度。在解答上述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宽容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
一、宽容的内涵
1.对宽容的界定。英文中的宽容(tolerance)一词源自拉丁文tolerare,其本义指“容忍、忍耐”;从广义上讲,该词还有“养育、承受和保护”的含义[1]。《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宽容(forgiveness,tolerance)的解释是:允许别人自由行动或判断;耐心而毫无偏见地容忍与自己的观点或公认的观点不一致的意见。其他一些西方学者对这一概念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从我们所掌握的有关宽容的文献看,西方学者对宽容的界定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一些学者认为,宽容不能算作一个单独存在的概念或实践,除非某种与它相悖的想法或实践出现时,宽容才被提及。Bernard Williams指出,宗教上的宽容是在某群体把他群体看作是“亵渎、厄运、淫秽”时才出现的。“宽容其实只是不宽容的产物。”[2]同样,Thomas Scanlon也仅将宽容理解为“一种抑制反对或不赞成情绪的态度。”[3]有人从更宽泛的视角认为,只要不反对某些想法或实践就是宽容。
不少政治哲学家从历史视角把宽容看作一种政治制度,认为宽容制度使那些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能够和平共处。例如MichaelWalzer把宽容看作是“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能使有着不同历史、文化和身份的群体和平共处。”[4]同样,Benjamin Kaplan在对欧洲近代早期历史的记录中,强调应把宽容理解为,“是与持有不同宗教观点的人们的和平共处”,是“使持有不同信仰的人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城镇或乡村”的制度安排[5]。
还有一些学者从宽容的不对称性来解读它。一些学者认为,宽容是一个具有不对称性的概念,是强者对弱者的特权,而弱者并不能处于宽容强者的位置。由于宽容的不对称性,一些学者把宽容只看成是一种有限的美德,另一些学者则把它运用于人口规模、影响和权力等方面有差异的群体的对比研究中,如Rainer Forst对“允许概念(permission conception)”与“尊重概念(respect conception)”的探讨就属于这类研究。Rainer Forst提出的“允许概念”指的是宽容意味着“当权者允许少数群体成员按其信仰生活,但少数群体必须接受当权者的主导地位”;而按照“尊重概念”,宽容意味着“平等公民彼此尊重其在立法和行政上的公平,尽管他们在民族和宗教观念中对真善美有着极不相同的看法”[6]。其实,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的潜在价值取向是共和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另外,学者们认识到作为社会实践的宽容与作为个人美德和态度的宽容之间有区别。作为社会实践,宽容是由立法和执法机构来界定并保证其实施的,而作为个人美德和态度,它仅仅具有个人属性。
2.宽容的特性。第一,不对称性。从某种理解来看,宽容是一个具有不对称性的概念。当我们谈及宽容时,大多时候脑海中浮现的是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包容与隐忍,而少数群体并不需要用相同的方式对待多数群体。换句话说,宽容是强者对弱者的特权,而弱者就不需处于宽容强者的位置之上。这里的强者不仅指数量上的多数,还指权力上占优势者。在欧洲宗教战争期间及之后,对宽容的这种理解逐渐发展为一种政治价值观,要求宗教多数派应该有限度地宽容宗教少数派,但宗教少数派并没有相应地被期待去宽容宗教多数派。
第二,工具性。出于某种强大的政治意图或动机,宽容是政治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特别是在多元社会中,宗教派别或少数群体与多数群体之间要和平共处,宽容的制度就是他们的共同诉求。美国学者Anna Elisabetta Galeotti指出,为了在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实现平等权利,可以给予少数群体在公共生活中一种承认的宽容,使其非主流地位得到补偿和平衡[7]。然而,仅仅有宽容的制度还不够,还必须坚持宽容的实践才能使其工具性得以显现,否则它的作用是有限的。
第三,自相矛盾性。从宽容的主体看,它既强调根据个人选择和群体权利来安排生活的重要性,同时也表示要悬置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处世原则来包容异己,接受其合法性。换句话说,一方面,宽容作为一种美德,只有广泛植根于自主的价值观,它才可能允许发展不同的信仰和实践。另一方面,宽容别人也相当于让渡自己的价值原则,屈从于自己原本所不能接受甚至深恶痛绝的实践和生活方式,然而这样一来,对宽容的延伸也就可能威胁到自身的完整性。但是,作为对人类价值、理想和原则的重要回应,宽容就是必须在本身的自相矛盾中寻找某种互补形式,来维持一种精妙的平衡。
总之,宽容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并具有不对称性、工具性和自相矛盾性。归纳起来说,宽容既是一种个人态度,也是一种制度,即一种保证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平等共处的制度安排。
3.自由主义的宽容。自由主义的宽容理念,涉及维护个人信仰自由、保护个人持有与群体不同意见的权利,同样保护少数群体不受国家迫害的权利。对自由主义者而言,“宽容是尊重个人存在的私人领域之不可侵犯的准备就绪状态。”[1]就是说,自由主义者强调的宽容要求社会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许可禁止一切妨碍个人自由实践的行动。在西方国家中,宽容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西方国家能够包容异己,并接受文化的多样性,但这样的宽容限度在哪里?
二、宽容的限度
1.对自我与对他者行为的宽容。宽容,常常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此,宽容在许多情况下是有限度的,特别是涉及到少数群体权利时,宽容并不意味着满足所有少数群体的所有要求。首先,我们必须把由于信仰、习俗等群体规范对自身和他人造成的伤害区别开来。这种区分源于对自我与他者行为的传统二分法。我们来看一下耆那教中与死亡相关的行为。耆那教是印度的一支传统小众宗教,当这一宗教中古老禁欲主义的教徒即将面临死亡时,他们拒绝以任何暴力形式来伤害生命,而是诉诸一种特别的行为——绝食。耆那教教徒被允许在特定场所结束自己的生命,更确切地说,是以非暴力的形式欢迎即将而至的死亡。但其教义又规定,并不是每个耆那教教徒都有权实施绝食仪式,他们必须得到高级僧人的准许,只有那些患有不治之症或年事已高身体遭受折磨的信徒才被允许进行绝食仪式,换句话说,只有合理正当的理由才可能实施自我伤害。又比如说另一种在非洲文明中较为常见的行为,即给身体留下伤疤的宗教仪式。其传统认为,伤疤是公民身份、群体成员的标志,或是入会的标识,并被看作是美的象征。我们假设移民们把这样的仪式带到自由民主国家,那么国家是没有理由进行干涉的,尽管这种自我折磨的习俗在自由主义国家不被提倡和鼓励。但是,由于该文化深厚的历史传统及其强烈的信仰,他们应该得到文化上的宽容。然而,一旦涉及他者的行为,情况就不一样了。诸如殉夫、杀婴、女性割礼,或是为了家族荣誉而谋杀他人的行为,是西方国家也可以宽容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2.少数群体所要求的两种权利与宽容。两种权利,即有关对其成员的约束和对外部社会反抗的权利。这两种团体权利都是通过应对不同的不稳定源来维护民族或宗教群体的稳定性。第一种权利用于群体免受内部力量的破坏,如个体成员不遵从传统实践或习俗。第二种权利则用于保护群体免受外力的侵害,如来自外部世界的经济或政治决策的影响。这两种权利可以称作“内部限制”权利和“外部保护”权利。
第一,“内部限制”权利。从公民权利来看,“内部限制”绝大多数是不公平的。当然,群体有权利在自发组织中对成员资格进行限制,但不能使用行政权力或分配公共利益来约束成员自由。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在群体中行使权力者必须尊重其成员的民事和政治权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在以色列的一些群体文化中,为了家族荣誉实施谋杀行为,这种行为较多发生在贝多因人、德鲁兹人中,有时也出现在基督徒身上。大多数情况下,牺牲者都是那些被认为“行为不端”的妇女。在这样的群体中,荣誉通常被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文化看得比法律更重要。有报告称,妇女被暗杀是因为她们的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8],已婚女违反性道德,自然会招致杀身之祸[9]。而单身女子,常常被指控犯了“原罪”而被处死,除非她嫁给性伙伴。这些群体规范都超越了西方国家的宽容极限。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这些做法是错误的,因为这些群体规范本身就是错误的,所谓的道德规范对妇女和孩子造成有形伤害,如焚烧寡妇、溺杀女婴、严酷的女性割礼,以及为了家族荣誉而实施谋杀等。因此,可以说群体对其成员的限制权利并非绝对正义平等,社会应该公平地干涉某些特别的文化行为。
较难处理的例子是对内部持不同政见者的限制。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限制并不会对其成员造成有形伤害,也就是说,少数群体并不通过严酷的身体伤害来控制群体成员。在民主国家,道德规范必须由所有人共享而不论他们的文化差异。而由此倒推回去,规范实施的范围是有限制的。那么,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民主规范是必须尊重他人的人权,而不对其施加伤害。这里可以提出“尊重原则”,即我们应该自觉地尊重他人作为人的权利,即他人有权按照自己的计划生活,有权按照自己的选择来发展其与生俱来的才能。同时,尊重他人的人也应该获得尊重,并且宽容的边界由是否伤害他人来决定,这也是“尊重原则”。Thomas Scanlon指出:“我们看重宽容的原因在于它使公民成员间的关系成为可能。”[2]虽然他并没有详述所指的是何种宽容,但其大意为宽容的社会就是一个相互尊重的社会,宽容表达了一种对他人生活方式的认同。另外,由此我们还想到了“伤害原则”。伤害原则指当很有可能发生对个人或群体造成伤害的暴力事件时,就要对自由加以约束。尊重原则和伤害原则是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权利的维护,比如说妇女、少数民族、宗教少数派、文化少数派以及同性恋者等。
第二,“外部保护”权利。对于“外部保护”权利来说,只要能促进群体间平等,而不是主宰或压制其他群体,不与国家法律相抵触,则是可以被接受的。因此,决定民族文化群体权利的要求是否合理的关键,在于它是否压迫和剥削他人及其他群体的权利。从少数群体的角度而言,它没有权利去迫使整个社会遵从它的信仰和文化传统。如果某一少数群体试图做这样的尝试,那么社会其他成员将与该群体平等协商。但假设平等协商失败,社会其他成员将诉诸权威,并抵制少数群体对其造成的压迫。
另外,假设某一文化少数群体想脱离社会,按照自己的标准和规范各行其是,并且它的文化表现出在尊重群体规范的同时却要践踏到个体成员的利益,例如某些文化在女性角色上表现出的狭隘共识——女性应该处于较低地位。这样的文化会限制妇女上大学和履行公职。但是,只要该群体中的女性不喜欢这样的规定,她们能轻易地离开该群体并且加入到大社会中去。那么,国家去强制地干涉或禁止这一群体行为也许是不正确的。然而,这里说不正确并不意味着这种行为道德上合法。相反,从自由主义的观点看,它是不公正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合法的理由将我们的道德标准强加给该群体。
国家这个共同体表明公民承载着共同的历史,对仪式、象征、神话的认同,对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服饰风格、工作休闲方式、餐饮等习俗的共享;移民则携带着他们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价值等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差异就是争论与冲突的根源。但是,西方社会能够仅因为文化少数群体与它格格不入的价值观而拒绝接纳吗?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不对群体外的任何人、任何群体构成威胁的和平的少数群体或教派,强迫它按照“我们的”自由原则去重新组织他们的共同体,从根本上讲谈不上宽容[10]。再来看另一种情况。假如相当数量的法西斯分子企图移民到某个国家,并宣称要将其带入新的繁荣,那么西方社会将如何反应?是任由其发展吗?无可辩驳,法西斯的本质就是极端暴力,是威胁国家和平存在的势力,它的任何煽动行为都是暴力的组成部分,当法西斯的势力足够强大时,他必将对民主和少数群体构成威胁,这是一种可怕的黑色力量。移民接纳国必须作出公正的决定来制止法西斯群体的入侵。这样做最充分的理由是:法西斯信仰没有宽容,没有对他人的尊重。法西斯主义敌视人权,践踏自由国度的根本基石,这就是最充分、正义的理由。政府的职责是保护和促进公共利益,准许法西斯群体的加入与此职责相悖。民主要捍卫自身不受侵害,就算将不宽容的群体驱逐也不为过,因为他们的理念违反人类尊严和不尊重他人,他们诉诸暴力来达到政治目的。所以在这个例子中,国家可以基于煽动暴力和跨信仰的敌意与自由民主的准则不符为由而将其拒之门外。
综上所述,首先,宽容的限度在于行为是否对自我和他人造成伤害。如果行为是对自我造成伤害,那必须得有合理正当的理由才被允许;如果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则超过了宽容的限度而不被允许。其次,从少数群体的两种权利要求来看,“内部限制”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符合尊重人的平等与尊严,即人权的原则;“外部保护”权利则要保证少数群体与多数群体之间的平等地位。西方国家也要宽容少数群体文化而不进行干涉,但如果涉及践踏人权的少数群体文化则要坚决加以抵制。西方国家应该采取一种毫无偏见地容忍接纳的政治态度,即少数群体内有自由,少数群体与多数群体间有平等。
三、“头巾法案”与少数群体权利
通过对宽容的内涵及限度等问题的讨论,现在我们转向讨论今天欧洲所面对的一个与宗教自由相关的争论: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所佩戴头巾的权利问题。
2004年2月法国国民大会通过的《头巾法》规定:“严禁国民在公共场所配戴明显的宗教标志,包括穆斯林头巾、犹太教小帽、基督徒的大型十字架等。”[11]其中的一条关键性规定是:“严禁学生在公立中小学穿戴明显反映自己宗教信仰的服饰、标志。”[11]公立学校学生违反此法者,可能被学校开除。法国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但法国拥有500万穆斯林,是西欧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都有很大势力。然而,法国是一个公开标榜世俗化的国家,并颁布了《世俗法》。对此法案持反对态度的人就认为,一块小小的头巾里并没有那么多的政治、宗教含义。法国相关的法律已经很多,如果再仅仅因为头巾就立法的话,它非但不会加速法国的世俗化进程,相反会加重穆斯林群体与法国大众之间的相互排斥现象,不利于整个国家的整合和民族团结,或许轻缓一些的行政手段更适宜。
然而,法国的解决方案并不是欧洲用于解决自由民主与群体权利之间关系的唯一策略。欧洲各国以各种方式平衡着群体间的整合与协调。在比利时,关于公立学校中穆斯林头巾的争论也同样让政要和评论家们倍感压力。但在比利时没有任何公开实施的禁令,在学校由此引发的冲突完全通过对话得到有效解决,而不需要法律程序。在德国,随着大量穆斯林社区的出现,关于穆斯林学生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的争论也成为了立法者面对的问题。但至今,在德国还没有出台任何关于学生的头巾禁令,因为对话和沟通一直是用来缓解与穆斯林社区紧张局势的途径。在德国另一引起更激烈争论的话题是,老师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的权利问题。德国最高法院裁定各邦有权自行决定新的相关法规。而教育部出于教育中立性的考虑,希望禁止任何宗教或政治意味的象征或标记出现在学校[11]。
荷兰也是一个拥有大型穆斯林社区的国家,但该国没有将头巾问题看作是宗教自由问题,而是把它作为非歧视事务来处理。争论主要靠非司法程序解决,即所谓的“平等协调委员会”,主要处理反歧视性立法,并负责所有与头巾相关的投诉。依据传统的自由主义路径,学生被允许在公立学校佩戴宗教性标识。唯一的限制是出于他们自身的安全考虑,例如体育课上佩戴头巾是危险的。
英国和法国一样,也是一个世俗化的多种族、多宗教国家,但是,穆斯林妇女在英国被法律授予在公共场所佩戴头巾的权利,尽管也有一些人试图去限制它。依据传统的自由主义路径,英国当局通过非立法手段来处理头巾问题。根据2006年专设的“政府整合委员会”,国家与少数文化群体的关系必须基于现存的最优可持续性发展方案来解决,因此要更进一步扫除整合和内聚的障碍。“在英国,一个出身印度锡克族的英国警察,就可以带着具有强烈种族和宗教含义的头巾和其他警察一样在大街上执勤。”[11]从这点可以看出,英国人明显比法国人宽容得多。
从上述可见,欧洲各国对待“头巾问题”的做法迥异。从理论上看,作为多元文化社会的产物,多样化平等观、尝试“尊重差异”、宽容异质性,以及文化和解才是恰当的开明态度。然而,穆斯林群体在欧洲的不断扩大,是多元文化论者不得不应对的一个更复杂的社会现实。但无论如何,当违背民主的核心价值——尊重他人人权时,是没有任何“和解”可以接受的。为了避免群体间张力和维续欧洲的所谓自由民主,“限制”与“和解”之间的平衡必须谨慎处理。有人指出,欧洲穆斯林移民群体应该在对文化忠诚还是对国家忠诚之间作出抉择。这其实是潜在的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误导。移民群体有权保留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只要他们不违背国家法律,西方国家应该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和宗教自由,但同时他们也有义务对国家忠诚,这是作为公民的先决条件。
因此,类似此种案例,对话和非立法程序会比司法来得更有效。所谓自由民主之下的社会契约仍然应该是欧洲当局首要关注的,西方国家应该表现出寻找有效制度工具的强大意愿,以此调和移民群体的需要,并同时秉承西方的核心价值,不伤害他人,尊重人权。欧洲人权法院在2004年指出,关于头巾的争论应该通过寻求个人的宗教自由权与开放民主社会的集体利益之间的平衡来解决。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了公共秩序,如果公开展示宗教信仰对他人权益构成威胁,那么西方国家就要合理地加以限制。然而,不论是通过立法(如法国),还是通过非法律程序(如比利时和德国),在少数群体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张力不断升级的时代,一定程度的政府干涉是需要的,因为欧洲正面临着社会和人口的大变迁。
许多少数群体表示愿意遵守国际人权声明。现在已经有许多在双方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加强尊重个体权利的机制存在,而不仅仅是强加给少数群体自由的价值观。除非是发生了重大的践踏人权事件才要强行干涉少数群体的内部事务,比如蓄奴、谋杀、严重的身体伤害等这些与人权和国家法律相抵触的事件。因此,决定是否干涉少数群体内部事务的因素应该包括少数群体内部个人权利被压制的程度,群体内纠纷解决机制的应用范围,群体成员对这些机制的重视程度,不同政见成员离开群体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少数民族要求自治的某种历史性协议。
四、结语
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发展出一种综合性的少数群体权利宽容理论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处理好少数群体的诉求,如何培养人们的宽容态度,西方国家面临着新的挑战。真正的宽容也许可以从“反对”态度产生的方向性上进行探讨。第一种情况是,少数群体的规范违反了群体内或群体外成员的自由权利,这里的“反对”来自西方国家,指向该文化群体,如西方国家对少数群体成员实施割礼的反对。第二种情况是,西方国家赋予所有公民的公民权受到文化群体的抵制,其理由是它违背了文化群体的规范,而在文化群体看来,这些规范理应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这里的“反对”来自文化群体,指向西方国家,如少数群体内女性成员上学的权利。因此,上述这两个不同方向产生的“反对”态度带来了少数群体与西方国家间的张力,并由此产生宽容问题。西方国家对全体公民所赋予的权利应该得到维护,当某宗教或文化少数群体的行为违反公民权或侵犯人权时,西方国家理应进行干涉,但如果该宗教或文化少数群体否认其群体行为违反公民权或侵犯人权,那么双方就会相互指责不够宽容。所以,理解是关键,只有如此才能使陌生变得熟悉,遥远变得亲近,多样性也可以得到丰富,国家与群体间需要架起沟通的桥梁,通过认同机制与法律机制的调节来消除理解的障碍。
[1]陈根发.宽容的法理[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7,34,59.
[2]Bernard Williams.Toleration:An Exclusive Virtu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18.
[3]Thomas Scanlon.The difficulty of Toleran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226,212.
[4]迈克尔·沃尔泽.论宽容[M].袁建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
[5]Benjamin Kaplan.Divided by Faith[M].Cambridge:Belknap Press,2007:8.
[6]Rainer Forst.Toleration and Its Limits[M].New York:New York Unviersity Press,2008:5,9.
[7]Anna Ellisabatta Galeotti.Toleration As Recogni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57.
[8]Kressel,Gideon M.Scroricide/Filiacide.Homicide for Family Honour[J].Current Anthropology,1981(2):65.
[9]Glazer,Ilsa M.and Wahiba Abu Ras.On Aggression,Human Rights,and Hegemonic Discourse:The Case of a Murder for Family Honor in Israe[J].Sex roles:A Journal of Research,1994(30):73.
[10]威尔·金里卡.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一种自由主义的少数群体权利理论[M].马莉,张昌耀,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218.
[11]刘作翔.从法国“头巾法案”等看政教分离原则与宗教平等权的意义[J].学习与探索,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