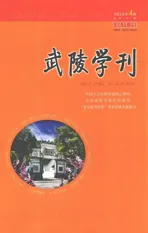边缘化的“朝圣者”
——论土改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2013-03-19程娟娟
程娟娟
(菏泽学院中文系,山东菏泽274015)
边缘化的“朝圣者”
——论土改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程娟娟
(菏泽学院中文系,山东菏泽274015)
土改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供了契机,他们从启蒙者变成了学习者,需要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成长。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知识分子面对着恶劣的生存环境、单调的精神生活以及革命与家庭的两难抉择。而知识者对于暴力革命的怀疑,对群众精神弱点的认识,对自我的认知等都在作品中成为批判的对象,同时也潜在地构成了对于主流话语的质疑。
土改小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一从启蒙者到学习者
在现代中国历史中,知识者所扮演的角色由“启蒙者”逐渐变成了“学习者”。“知识分子以自任‘启蒙’和‘唤醒’民众的光荣使命开始,却渐渐地觉得在‘群众’面前自惭形秽,愧为‘启蒙’之师;继而觉得自己不得不跻身于革命的洪流里,跟在后面跑;终于又觉得自己变成必须受群众‘再教育’甚至挨批挨斗的角色。”[1]20世纪40年代土改文学中出现的对知识分子的丑化与“五四”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启蒙者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知识者的学问由改造社会人生的力量源泉变成了只是用来炫耀自己、毫无实际价值的资本,这样的变化自然与延安整风有着密切的关系。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广大知识分子开始投入到实际的斗争中,在战争的血与火中油然而生一种沉重的原罪感,面对目不识丁的工农群众产生一种由衷的自卑感。
20世纪初,知识分子处于秩序混乱中的断裂社会之中,以学校、社团、刊物为中心,借助于文化传媒,拥有了相对独立的知识空间。他们高举着“科学”与“民主”的旗帜,猛烈抨击传统观念,开展文化启蒙运动,呼唤民众的觉醒,希望能够借助西方的价值观念来让古老的中国重新焕发出生机。“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变得象征化和符号化,只是以知识的符号形态影响社会,通过抽象的话语方式启蒙民众。知识分子与社会特别是乡土社会这种象征化的联系,背后所缺乏的,正是过去士大夫阶级那种制度化的渊源。而抽象的话语一旦匮乏建制化的基础,就会变得无足轻重。现代知识分子不再是社会的中心,反而在‘断裂社会’中愈趋边缘。”[2]知识分子空有宏观大论,他们是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缺乏权力的后盾和社会的支持,因此他们的呐喊在死寂的中国是寂寞的,得不到任何回应。作为“自由漂浮者”的知识分子,希望可以采取实际的革命行动以实现社会的重大变革。
知识分子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革命的理论和政党。社会越是混乱无序,人民就越急于采用极端的暴力方式使问题彻底解决。“暴力对某些知识分子总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同希望得到激进的、绝对的结论是一致的。”“知识分子同暴力的结合是如此经常地发生,不能认为这是一种偶然现象。它常常采用赞美‘行动者’即实行暴力者的形式”[3]。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说初期的知识分子是随风飘浮的“毛”,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可以依附的皮。“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的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4]体制下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尖锐批判问题的自由,在革命实践中也充分暴露出自身眼高手低、虚荣骄傲的特点,再加上一再强调的“原罪说”,知识分子开始洗心革面,转而向工农兵学习,认真地按照政策要求改造自我。“共产党说‘思想改造’是一种‘民主的’教育方法,是通过连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思想转变的方法。这种方法始于40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风运动’,自那时起它一直是一种重要而有特色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手段。这种方法首先不是被看作一种惩罚形式——虽然有时被用于惩罚的目的或最后导致惩罚的结局,但主要是作为一种产生‘正确思想’的‘教育’工具,这种正确思想随后会带来正确的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5]
知识分子敏于思考,怯于行动的弱点,也在革命实践中暴露无遗。他们受过高等教育的熏陶,虽然渴望社会革命带来新的气象,更希望以温和渐进的方式来完成。知识者温文尔雅的个性与土改所需要的激进气氛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运动一来,知识分子也就帮着做个记录什么的,口号都喊不响亮。农民提出实际问题回答不了,白天干不了农活,又不敢摸黑走夜路,江涛滚滚,驾不得船,山路漫漫,攀不得崖;甚至不会说大话,不会说粗话,不会说胡话,更不会说假话,得,赤贫革命的性质,决定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贬值,决定了理性精神的苍白无奈,也决定了人性道德的不着边际。尽管早期中国革命首先是由知识分子精英所发动的。”[6]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习惯于在书斋中埋头于学问,在土改中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宗法关系,要和缺少文化的农民打成一片,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正是因为这先天的弱点,每当土改小说中工作出现失误或者进入僵局,被归罪的角色往往就是知识分子。只有贫雇农出身的干部才能扭转乾坤,顺利完成土改工作。
《暴风骤雨》中的知识分子刘胜一进村就主张开大会,而不是先去调查研究,结果遭到了“意料之中的失败”,在一斗韩老六失败之后,他就开始收拾行李打算离开。在萧队长看来,“他碰到过好些他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常常有一颗好心,但容易冲动,也容易悲观,他们只能打胜仗,不能受挫折,受一丁点儿挫折,就要闹情绪,发生种种不好的倾向。”[7]虽然萧队长也是知识分子,但他的知识者的印记只是一支金星钢笔和写日记的习惯,他是已经脱胎换骨的知识分子,是能够与党的政策方针保持一致的成熟的革命者的形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则善意地讽刺了文采的不懂装懂、自命清高,开了六个钟头的大会,只会夸夸其谈,不深入群众。他先入为主,认为张裕民有流氓习气,沉浸在斗争江世荣的胜利中,对钱文贵还保留着恻隐之心。章品的到来扭转了工作被动的局面,“他的出现,结束了工作组中文采和杨亮间空洞的争论,结束了村干部们的变天思想的发展,结束了暖水屯工作的混乱情况,他的出现,突出了小说斗争钱文贵的中心,完成了小说的反霸的主题思想。然后,在斗争钱文贵以前,他匆匆地走掉了,正象一阵风一样地来了又去了。”[8]
土改小说情节中主角都是根正苗红的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在情节中只能承担可笑的配角,他们以自身的幼稚、冲动、自满处处反衬出领导者的成熟、稳重、谨慎。他们需要在实际的斗争中锻炼,才能改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弱点,磨掉自身性格上的棱角,加入革命者的行列。虽然小说中的知识分子都是受到嘲讽的灰色人物,他们对于革命的积极性还是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文本中还留下了继续成长的空间。《一个空白村的变化》(那沙)中的莫步晴,对待实际工作也是“摸不清”,“他为人十分能干,性质好强,工作总想占先,喜欢把事情弄得轰轰烈烈,呼呼啦啦”。他被“笑面虎”的开明假象所迷惑,没有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习惯于做表面功夫。“对于减租,莫步晴是十分热心的。那样的大热天气,他蹲在屋里连夜写减租计划。方式、方法,中心、步骤,一个大问题几个小问题,一个大点几个小点,写了厚厚一小本。满心想把工作搞在别人头里,弄出一点成绩来。”经过在县上的学习之后,莫步晴洗心革面,改名为莫得晴,广泛地发动群众,成功地组织了翻身大会,将“笑面虎”斗倒,改选了农会组织。可见,知识分子只要经过了从“摸不清”到“摸得清”的变化,努力改变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作风,最终是可以成为成熟的革命领导者的。
二艰难的选择
人的改造是十分艰难的过程,即便知识分子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和赶上时代的迫切心理,在实际的工作中他们还是要面对生活习惯、思想方式、个人情感等诸多方面的挑战。
知识分子都接受了现代都市文明的熏陶,奉行的是现代的生活方式。为了拉近与群众的距离,知识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甚至连刷牙这样的基本卫生习惯都无法坚持下来,因为这些现代的生活方式,在村民眼里是古怪的西洋景,会造成无法理解的隔阂。“临下乡以前,故意连一本文艺书也不敢带,甚至因为刘老太婆天天用诧异的眼睛看我刷牙,我觉察了,就连牙也不敢刷了。”(韦君宜《三个朋友》)知识分子向农民的学习是单方面的膜拜,而不是双方的交流,知识者没有能力促成乡村由保守到现代的转变,向村民灌输现代的思想观念,只能入乡随俗,尊重农民的生活习惯,努力消灭知识者的印记。他们首先面对的困难就是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咆哮了的土地》(蒋光慈)中的革命者李杰下乡后面对着难以下咽的食物,“饭菜异常地粗劣,碗筷在表面上看来是异常地不洁,那上面似乎粘着许多洗濯不清的黑色的污垢。张进德拿起碗筷来就咕哧咕哧地吃起来,似乎那饭菜是异常地甜蜜,而李杰在开始时却踌躇了一下,皱了一皱眉毛,接着那饭菜的味道使着他感觉到他和张进德的分别……”这是摆在革命者面前的生活关,对革命的激情促使他们对低劣的生活条件反而感到甘之若饴,他们怀着革命的激情坦然承受低劣的生活条件,并在苦难的磨砺中升华出一种崇高感。
韩丁在《翻身》中曾描写过在村民家吃派饭的情形:“我们走进他家的屋门,一阵难忍的恶臭扑鼻而来。地上散发呛人的童尿的臊气,隔壁传过来鸡屎的强烈臭味,燃烧麦根的余烬腾起一股股的青烟,整个屋子的空气里充满着那个女孩从溃烂的肺里呼出来的腐败的气味。”“我知道,在这些碗筷上面,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都已经沾染了结核病的细菌,可是我必须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吃饭,这是每一个土改工作者全都经历过的毅力考验。如果你不愿意与人民同甘共苦,你就得不到他们的信任。”[9]333另一位工作队成员戚云“对寒冷、疲劳、虱子、跳蚤、粗糙的食物和坚硬的木板床似乎都毫不介意。她把这一切都看做是‘到群众中去’的一部分”。他还注意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知识分子的干劲远远要比地方干部高得多,虽然土地改革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9]301-302
艰难的生活条件没有吓退知识分子,他们将其视为革命必须克服的困难坦然接受。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物质的匮乏可以忍受,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寂寞空虚。生活中骤然失去了书本的相伴,没有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言谈举止必须符合农民的生活习惯,避免流露出些许不安的情绪,这才是对灵魂的残酷凌虐。在《三个朋友》(韦君宜)中,“我”遭遇到了一场精神的危机,“挖土担粪我全不怕,只要咬牙就能成;只有一点终归骗不了自己,心里总好像有一块不能侵犯的小小空隙,一放开工作,一丢下锄头,那空隙就慢慢扩大起来,变成一股真正的寂寞,更禁不住外界一点刺激。好像靠‘枪手’替考了一百分的小学生,一当堂试验就露了马脚”。在石碾子的嗞唔声,女人“唠唠唠”的长吼声,大猪“呣呣呣”、小猪“吱吱吱”的叫声中,“我”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寂寞之中,怀念着过去充满情趣的日子。“这一个黄昏,他们全家老小就只在谈论那掉在茅坑里的小猪,吃饭也在谈,做活也在谈。我本来知道,我应该随着一起谈的,但是那寂寞既经来了,就不肯去,越扩越大,像一块石磨一样压住我的心思,我一言不发的吃饭,连饭都吃得很少。放下饭碗,背着手走到院心,在这阵寂寞的袭击之下,我把别的道理一下子都忘了。”知识分子与普通农民的精神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单纯的迁就农民务实本分的传统心理难免会发出寂寥的感慨。在小说中,这种寂寞感很快随着在劳动英雄刘金宽的影响教育下得到了改观,在红太阳绿麦田的劳动中,“我”不再留恋那个淡蓝色墙壁的世界,拒绝了地主黄四爷的拉拢,对另一位知识者罗平也产生了反感。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文采在人群中感到了一种无法言传的孤独,街上的女人正叽叽喳喳地说话,“看见文采同志走过来,就都停住了,四个眼睛定定地望着他”。而等他走过,两个人又开始叽叽喳喳,“文采听不清,也听不懂,好像这次正说他自己,他只好装做完全不知道”。在街上他看不见一个认识的人,不知去哪里才好,街上众人又对他指指点点,“他并不怕这些人看他说他,可是总不舒服”[10]。在这里,文采所流露出的孤寂感实际上是作家丁玲投射到人物身上的,当知识分子处身于大众中必然会产生异己的隔膜感,只有当产生融入人群的惬意感时,才意味着思想改造的成功。“这里很热闹,全部的人马都到了这里。我一整天夹杂在这里面,并不感觉舒服。我的不群众化,我的不随俗,是始终没有改变,我欢喜的人与人的关系现在才觉得很不现实。”[11]
知识分子在向大众学习的过程中实现自我灵魂的蜕变,要承受蛹化为蝶时破茧而出的痛苦。“一面是真实而急切地去追寻人民、追寻革命,那是火一般炽热的情感和信念;另一面却是必须放弃自我个性中的那种种纤细复杂和高级文化所培育出来的敏感脆弱,否则就会格格不入。这带来了真正深沉、痛苦的心灵激荡。”[12]1063“把知识者那种种悲凉、苦痛、孤独、寂寞、心灵疲乏统统抛去,在残酷的血肉搏斗中变得单纯、坚实、顽强。”[12]1066
知识分子所遇到更为艰难的选择,是自己的家庭与革命事业之间的冲突。他们往往出身于小康富足之家,否则就不会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经历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考验之后,他们还要舍弃自己的家庭,自觉地站在革命战线。“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与封建制度有若干联系,如果舍不得割掉封建的尾巴,舍不得为整个革命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和家庭的利益,就会发生立场上的动摇,其中一部分就会堕落到袒护地主反对农民的立场上去,或者堕落到自私自利独占农民斗争的果实的富农立场上去。”[13]
这些地富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要与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更要与自己的亲人反目成仇,以此证明革命的坚定性。个人只有抛弃了家庭的束缚,尤其是摆脱剥削阶级的家庭,才能够加入到革命的大家庭中来。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情感上难以接受的事情。有的人甚至会因为巨大的心理压力而精神失常。韩丁就遇到一位想不通出身问题而精神崩溃的年轻学生,“在学习会上,他拒绝正视地主家庭出身这一事实,受到不断的责备。在土改工作队里,他因为骄傲自大受到同事们的严厉批评。他感觉失望、孤独,不能理解或同情农民。他的精神最后终于完全垮了下来,成为他的同志和他自己的一种讨厌的负担,后来他想逃回国民党统治区去。这是土地改革没有能够改造好的一个年轻干部,至少是暂时地把他压垮了”[9]427。
即便是已经划清界限的革命者,心里也是充满了难言的歉疚。一位干部的私人信件中提到了要“舍父保母”的无奈之举,以尽可能地保全家人。“我生平(四十岁)从未敢批评我父亲,此次不得已我写了逾三千言的一封信,这是破天荒新纪元的批评和揭发我父的缺点”,提出把父亲孤立起来,全家人搬出去自立门户。他想尽量在不违反革命性的同时对父母略尽孝道,“我们党员既非枭獍,谁无父母?苟非万不得已,孰肯与父母决裂如此”[14]?
小说《秋千》(孙犁)中的大绢在冬学会议上被别人指出爷爷当年曾经剥削别人,立刻觉得十分羞愧。“李同志觉得在他的面前,好像有两盏灯刹的熄灭了,好像在天空流走了两颗星星。他注意了一下,坐在他前面长凳上的大绢低下了头,连头发根都涨红了。”她哭着离开了会场,此后,她再也不到冬学来了,再见到李同志时,她好像比平时矮了一头。直到纠正了她家的成分,大绢重新上学了,“她瘦了些,可是比以前更积极更高兴了,就是:火色更纯净,刚性也更坚韧了”。小说见微知著,反映了因家庭成分不好而给人们造成的精神伤害。这种痛苦的经历孙犁也有过切身的体会。“冬,土改会议,气氛甚左。王林组长,本拟先谈孔厥。我以没有政治经验,不知此次会议的严重性,又急于想知道自己家庭是什么成分,要求先讨论自己,遂陷重围。有些意见,不能接受,说了些感情用事的话。会议僵持不下,遂被‘搬石头’,静坐于他室,即隔离也。”[15]17在土改中为避嫌,更是不敢擅自回家。“麦收时,始得回家。自土地会议后,干部家庭成分不好者,必须回避。颇以老母妻子为念。到家后,取自用衣物,请贫农团派人监临,衣物均封于柜中。”[15]18
三在斗争中成长
建国后不久,很快又开始了对于新区的土改。这次土改涉及地区更多,范围更广,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土改,不仅解决了当时土改干部不足的急迫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实际的斗争中,让知识分子逐步接受阶级观点,改造思想,促进他们对国家政权产生认同和崇拜之感。“他们亲眼目睹了中国乡村的落后、封建土地制度的危害,了解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中农在革命中的动摇、贫苦农民觉醒后的伟大。激动、痛苦、惶惑、愧疚、愤怒、怜悯……种种情感体验交相更替,构成了这些特殊的土改工作队员的典型心态。正是在激烈的现实阶级斗争和复杂无比的内心冲突中,他们获得了执政党所期望的政治上思想上的进步。”[16]
毛泽东曾在1951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鼓励民主人士去各地进行参观视察[17],各机关部门号召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土改。在政府的积极倡导下,大量知识分子参与到了土地改革中来。其实,这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主动要求,他们多是从国统区或海外过来,在建国后万象更新的气氛中为自己的不劳而获感到羞愧,在朝气蓬勃的革命队伍中产生了落伍之感,他们希望在实际的锻炼中能够接受革命的洗礼,接受先进思想的武装,正式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我处处自惭形秽。”[18]这种未参加革命的羞愧感和知识无用的原罪感是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心态,他们积极主动要求下乡参加土改,在革命实践中改造自我。
这些埋头书斋的知识分子在土改中接触到了农村的真实境况,在斗争过程中对农民的苦难感同身受,对地主也产生了仇恨之情。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进一步坚定了阶级立场,确立了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在世界观、阶级感情上悄然发生了变化,对于政治的态度由之前的超然物外转而为对政权的拥护。这样,参加土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自我思想改造的过程。“土改的土字,要是下面的一横写短了就是士字,那么土改就成为士改了。”[19]
小说《美丽的南方》(陆地)具体描写了知识分子如何在土改中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塑造了一批蕴含着“五十年代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党和国家无比崇敬,对劳动人民无比热爱,对生活怀着满腔热忱,以昂扬的斗志积极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其中的傅全昭、杜为人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典范。杜为人走过的思想历程极富代表性,“他觉得自己经历的思想道路是崎岖的,他曾经忍受无数失眠之夜的煎熬,也流过不少的个人主义者的眼泪。开头,要他放弃美术的爱好,服从当时革命斗争迫切的任务,他思想曾经那样的缠绵,那样的悲痛呵,后来,实际斗争的锻炼,把他从个人主义的歧途慢慢引上宽阔的集体主义的道路来了。过去,曾经那样魅惑着他的幻象,他都把它埋葬了”。小说中,傅全昭与柳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傅全昭积极深入群众,用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为农民服务,也拉近了与农民的距离。而柳眉一开始是一位娇小姐,整天皱着眉,噘着嘴,每天忙于买零食,跑邮局,不与群众接触。此外,还有画风景画的画家兼诗人钱江冷,忙于抄写县志的俞任远,口头禅是“不堪设想”的教授黄怀白,思想在逐渐进步的副教授徐图,不时诗兴勃发的诗人丁牧,个人主义者王代宗等等,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知识分子群像图。
经过整风之后,知识分子结束了东游西逛的“休养”状态,开始深入到群众中,尽心尽力帮助农民翻身。钱江冷为土改绘制了宣传画,柳眉也去做土匪家属的工作,他们似乎已经在革命的熔炉里脱胎换骨了。不过,钱江冷留给傅全昭的《苦难的历程———两姐妹》里头夹着一张金色的鹰爪兰花瓣。“‘她还没有读完!’全昭不觉低语道。”《苦难的历程》没有读完,这也意味着现实中的改造还未真正完成,里面夹着的美丽花瓣意味着知识分子纤细敏感的审美趣味,这与改造所要求的粗犷豪迈之气也相差甚远。用小说中人物的话来说:“觉得自己小资产阶级的病根还是没有根除,遇到相当的气候又要发作了。”
这里的改造也不是在和风细雨中顺利完成的,在批评会上,人们先是进行自我批评,接着又开始对他人进行批判,对于问题严重的同志采取集中批判的方式。“思想斗争的气氛迅速地弥漫了整个工作团。被点了名批评的人表现不安,凄凄惶惶;有类似这种思想错误的人,表现苦闷、紧张,异常敏感。休息时的歌声和笑声少了,邮局、糖果店的门口忽然冷落了。”在革命与落后之间已经截然划出了一道界限,人们必须对此作出明确的选择,否则就会被划为另类。这是在巨大的集体舆论压力下被迫做出的选择,他们除了改造已经无路可走。
在土改小说中,知识分子所暴露出来的思想问题以反面教材的形式一一进行了批判。一是人道主义思想。《春回地暖》(王西彦)中塑造了一位怀着热烈期望参加土改,又经受不住土改考验的知识分子肖一智。促使他“临阵脱逃”的直接原因是“可怕的”公审大会。“自始至终,他肖一智都情绪紧张地参加着,还站在一处离台不远的地方。好几次,他接触到那个跪在台上的罗佩珠的眼睛;每接触一次,就使他胸口发一阵紧。公审大会一结束,茶山上的枪声一响,他肖一智就再也撑持不住自己。他惶惶惑惑地回到村子里,就没有吃饭,晚上也睡不好觉,胃病也发作了。”他对于枪毙五个地主的做法心有疑虑,“这样你杀我,我杀你,难道不是生命的悲剧吗?符合崇高的人道主义的原则吗?还有那罗佩珠,徒刑一判就是十年!对一个像她那样的年轻女人说,这够多么悲惨!多么不人道”!消灭地主在群众眼中是大快人心的事件,而在肖一智的眼里是一种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漠视。
这种对地主及家属的恻隐之心会被认定为立场不稳受到指责。土改中特别强调政治立场的问题,要以阶级作为判断一切事情的标准,绝对不允许对地主有同情的心理。“我们只看到今天这个服服帖帖的老头子,但是农民所看到的却是当年作威作福的土皇帝……我们潜意识中仿佛认为地主扫雪是可怜的,假如扫雪的是一个长工,我们就会视为当然,再也不去理会它了。我们只知道地主没有骡子就活不下去,但是忘了多少农民从来没有过一亩地。”[20]
二是知识分子的自负清高。要在实际行动中与农民同食同住同劳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美丽的南方》中的教授黄怀白私下里讲,“老实说,我脑子还是想不通,老百姓那样落后,有的简直是愚蠢,粗野,叫我们这些人跟他们三同,打成一片,岂不是开倒车,向落后看齐了”?知识分子以启蒙者自居,为渊博的学识所自许,在见识了城市文明之后再来看落后的乡村,要认同一直沿袭着传统的农耕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农村社会,他们确实在思想上转不过弯来。他们也都有读书的习惯,容易失眠,在生活习惯、思想观念上与农民简直是云泥之别。
三是“和平土改”的思想。有人认为,“象何其多那样,认识到大势所趋,愿意把田地交出来的,一定不在少数。只要政府出一张布告:宣布没收地主的田地,分配给贫雇农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发动群众斗争呢”(《美丽的南方》黄怀白语)?一些知识分子认为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必然会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人们造成巨大伤害。既然地主已经老实伏法,就没有必要选择激进的方式实施土改。这种“和平土改”的思想在党内受到严厉的批判,仅仅将土改理解为经济层面的平分土地显然还没有领会土改的真正意义,只有以土改为动力将广大的农民发动起来,打倒地主的威势,才能彻底改造乡村政权结构,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
四是对艺术的品味情趣。以农民的实用观点来看,艺术品不能吃穿,只是废物而已。他们对艺术品的糟蹋浪费在知识分子眼中就是煮鹤焚琴,大煞风景。“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思想?辉同志活生生一个。那些死物件———硬木家具啦,贵重陶瓷字画啦,农民把它当废物,不像粮食,可以充饥;不像衣服,可以防寒。所以说,农民不需要。小资产阶级就不是这样,对农民拒绝把这些废物当果实感到不理解,藐视贫农不识宝。同志们,你们把白米和珍珠掺和起来喂老母鸡,老母鸡吃不吃珍珠?有人试验过,母鸡把米吃下去,把珍珠推到水沟里——你看,小资产阶级的好恶怎么比不上老鸡?”(程贤章《仙人洞》)
五是对“原罪”的不满。知识分子被认定受过反动思想的毒害,必须正确认识自己的出身,而出身又是先天注定无法更改的,这种罪就成了永远无法赎清的“原罪”。地富出身的知识分子李蔚抱怨待遇的不公,“现在你们这些老贫农吃开了,一土改就当队长,土改完了就是一个县委书记。不,分区司令员等着你呢?我们这个样的,一闹运动就挨整,先整思想,后整作风,要不就整立场,一条一段没个完了”(梁斌《翻身记事》)!土改中更是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思想问题,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春回地暖》中的肖一智以胃病为由要求请假遭到拒绝,被指责为思想问题。“思想问题!这简直是他们这些人的口头禅!他们总爱把什么事情都归结到这个问题上面去!连胃病发作也是个思想问题!”
结语
耐人寻味的是,在小说《春回地暖》中没有明确地交代肖一智的结局,他最终是被成功改造思想,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还是冥顽不化,受到严厉的批判,这些都不得而知。这里出现的叙事空白是意味深长的。叙述盲区“比明白说出的内容能揭示更多的东西,它们是作品不完美的‘症状’,它们无法造成逼真感。……它们讲出的是关于观念形态的真相,被意识形态所压抑的真相,存在于意识形态本身之中的真相”。作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作者应该为自己所依附的政治意识形态进行形象化的阐释与宣扬,按照这样的话语逻辑,小说中的肖一智最终必须转变思想,重返革命阵营,或者改造失败,逐出革命队伍。在这里,作者不想让人物落入俗套,既没有把人物塑造为改造成功的样板,也没有过于愤激地批判其“异端邪说”。显然,作者在肖一智的身上投射出自己的思想情感,希望这个人物形象能够保持自身的完整性,而作者又无力与主流话语正面对峙与抗衡,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这些以反面角色登场的知识分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作者的真实心声,尽管是以批判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他们对暴力革命的反感,对农民落后思想的批判,对艺术品位的追求,对自我的认知定位,现在看来都对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质疑,这种质疑成为涌动在地下的暗流,只能改头换面地出现在作品中。而知识者的这种不合主流的思索与反省同时折射出知识者的独立人格精神,无论在现实中受到何种挤压与打击,思想上产生怎样的波动与煎熬,在万马齐喑的年代里,知识者还在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这声音十分微弱。在强势的权力面前,知识者并没有全部缴械投降,他们所接受的现代科学知识与西方启蒙观念的影响,在革命的疾风骤雨下还没有彻底荡涤干净。至少在他们的心中对于现实中天翻地覆的斗争场面存在着某种疏离,对于盛行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现出某种抗拒。
总之,尽管知识分子极力追赶时代的步伐,他们怀着真诚的信念,以大无畏的勇气走上了义无反顾的朝圣之路,在土改叙事中,知识者的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内心的纠结挣扎与痛苦的抉择都被主流话语遮蔽了,他们沦为了夹缝中生存的可笑又可悲的角色。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正是现实中知识者命运际遇的一种折射。可以看出,作家作为体制中的一员,他们受限于这种体制的束缚,而又试图在狭小逼仄的有限空间里传达出复杂多元的信息。“相比而言,知识分子是最不安分的,他们好像不懂得向命运低头,即使他们已被定位在社会体制的某一环节上,他们很可能仍然没有安身立命之感。在灵魂深处,他们总是漂泊的,他们在漂泊不定中不断寻找着归宿……”[21]知识者依附于政治权力,并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归宿,知识者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在小说文本中还是时有闪现。而在当下社会,市场经济的繁荣使得知识者再次面临边缘化的境遇,他们需要摆脱政治话语的挤压和物质利益的诱惑,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才能坚持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思想关怀,成为社会的批判性良知。
[1]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59-260.
[2]许纪霖.“断裂社会”中的知识分子[M]//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3.
[3][英]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M].杨正润,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433.
[4]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M]//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53.
[5][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张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109.
[6]赵瑜,胡世全.革命百里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256.
[7]周立波.暴风骤雨:上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117.
[8]竹可羽.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M]//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385.
[9][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M].韩倞,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10]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148.
[11]丁玲.东行日记(1947年5月29日)[M]//丁玲全集:1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336.
[12]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M]//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13]新华社.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N].人民日报,1947-09-01.
[14]邵燕祥.一封1949年的旧信[M]//向继东,编选.2009中国文史精华年选.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139.
[15]孙犁.陋巷集·《善闇室纪年》摘抄[M]//孙犁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6]于风政.改造[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46.
[17]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M]//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43.
[18]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M]//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28.
[19]袁方.我们的土改工作组[M]//陈体强,等.从土改中学习.北京:新建设杂志社,1950:20.
[20]陈体强.从土改中学习马列主义[N].文汇报,1950-08-14.
[21]黄平.知识分子:在漂泊中寻求归宿[M]//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10.
(责任编辑:田皓)
The Marginalized Pilgrims——The Image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Land Reform Novels
CHENG Juan-juan
(College of Literature,Heze University,Heze 274015,China)
Land reform movement offered an opportunity for the intellectuals’ideological reform.From the initiator to the learner,they need to revolute in the furnace of exercise.In the process of idea transformation,intellectuals faced harsh environment,monotony of the spiritual life and the dilemma of revolution and family.Their suspicion of violent revolution,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piritual weakness of the mass people and their self-cognition all became the object of criticism in their works and also potentially constituted the suspicion of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land reform novels;intellectuals;ideological reform
I207.42
:A
:1674-9014(2013)04-0090-07
2013-03-27
程娟娟,女,山东肥城人,菏泽学院中文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