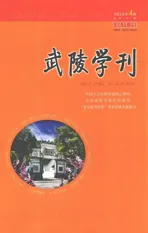宋代农林资源保护法制研究
2013-03-19李巍涛李晓峪
李巍涛,李晓峪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44)
宋代农林资源保护法制研究
李巍涛,李晓峪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44)
中国传统文化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于一种和谐共存的状态,不主张通过征服自然来谋求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在此观念上形成的哲学思想、法政制度与今天所提倡的生态文明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相通性,强调对农林资源的保护和有限利用也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随着哲学思想的发展、社会因素的汇集和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农林资源保护文化发展到宋代时达到传统社会的顶峰阶段,为当今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确立与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渊源。
宋代;农林资源保护;法制;生态文明
重视农林资源保护是我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极富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哲学新思潮的勃兴、特定的历史动因和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使宋代农林资源保护达到传统社会的顶峰时期,为维护政权的存续和推动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经久而有益的社会影响。本文旨在通过阐释宋代农林资源保护的哲学基础、历史动因和制度保障,对当今生态文明理念进行历史性的解读。
一宋代农林资源保护的哲学基础
(一)“天人合一”观念的新发展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一致,既包括人的行为与自然规律的协调,也包括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昭示着人作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作为对象所体现的客观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受此观念的统摄,第一层面上人们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和征服自然,而是应该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利用和开发自然,在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同时能够维持自然界万物正常地生长发展,使得有限的农林资源得到尽可能长久的利用。第二层面上自然界并非主宰人类社会的神秘力量,而是可以被认识、可以为我所用的客观对象。所以,“天”既不必是“人”匍匐顶礼的神圣上帝,也不会是“人”征伐改造的并峙对象[1]。这种主张人应该能动地对自然规律加以适应的“天人合一”观念在先秦诸子百家的论述中已经有所体现,孔、孟、老、庄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和强调了人应该与“天”形成协调一致的关系。对于这一观念的提出,早期理性主义①的影响远远比宗教崇拜的因素要大,“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表达了将民人视为主体存在的呼声,也实现了“天”、人之间的沟通。“天人合一”观念的长期奉行和累世继受最终形成了传统文化自然界与人相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相统一,内心平衡与自然和谐相统一这一独特气质,并由此达成“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实现传统社会完满和谐的价值诉求。
受阴阳家思想的影响并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汉代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观念增加了强调国家和个体在外在活动和行动中与自然及社会相适应、协调和同一的内涵,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渗透到人与社会的关系,其经由“天人感应”而对宇宙图式有机整体进行反馈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尚未完全褪去的神秘色彩有所恢复,这既是“天人合一”观念社会化的途径也符合其加强王权的目的。与汉代“天人合一”观念旨在建立人的外在行动自由的宇宙模式不同,宋代的思想家将“天人合一”提升至内在伦理自由的哲学高度,“天”也由原来指代自然进而升华为指代精神,并抽象为“理”,其适用范围也随着这一概念的抽象被无限扩大。“天人合一”的观念在宋代逐渐被抽象扩充,“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3]236。张载之谓诚乃“天人合一”精神修养的最高境界,明则为此境界中所有被认知的对象,即为最高的智慧[4]。而天和人都是实在的,“天人”之“用”是统一的,二者又皆以“变易”为本性[5],在张载看来所谓“天”指无限的客观世界,“由太虚有天之名”[3]22。可见宋代“天人合一”的观念以生态文明为基础却不以生态文明为界限,此时天、人的概念早已超越了自然与人的范畴。宋代不仅继受了前朝的思想,还将“天人合一”延伸为一种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使人们以农林资源保护为基础的生态意识与作为传统社会核心价值的伦理道德观念不断融合,对整个社会形成了更广泛的影响。在社会实践中,宋代不少君臣都将农林资源保护和生态文明阐释为哲学问题,社会生态意识最终与“理”的观念结合起来成为深具道德性的意识。
(二)从“重义轻利”到“义利并举”
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6]的义利之辩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观念影响深远,我国自古以来就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制度设计上往往对商业加以限制,歧视商人身份,以致社会整体形成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观念。这一风气到宋代有所转变,传统的“重义轻利”开始趋向“义利并重”。宋太宗就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让官员们研究理财富民之道,到宋神宗时则更是提出“政事之先,理财为急”[7]323的观点。总之,“有宋一代三百二十年间,传统‘重义贱利’思想向‘利义均重、利义相辅’思想的转变促使千百年的传统思想观念进一步发生变化。这些对维持两宋庞大而虚弱的国家官僚机构和集权统治体制,适应客观经济和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乃至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8]73。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唯一没有长期推行“抑商”政策的王朝,甚至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轻民的传统做法,相当重视义利并举的经济立法,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时期。不仅立法活动频繁,而且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在法规的制订、实施各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想象力,运用法律手段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经济发展。
随着社会观念的变革和佃农人身依附关系的弱化,大量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活动,再加上国家政策层面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重视优化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民间经济迅猛发展,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义利并举、农商兼重的观念经由国家经济政策和立法得以贯彻,丰厚的财政收入使政府避免了通过向农民征收重税增加收入的恶性渠道,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国家治理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萌芽于唐,历经五代、北宋,以一年两熟为基本形态的复种连作制在南宋趋于成熟并得到推广,向世人展示了传统农业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宋代甚至形成了与当今现代化生态农业观点类似的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农业生态系统循环观。由于政府对农事的重视,因而在有关农事的环境保护法制思想与实践方面也有一些前人所不及的建树,以致“这一时期,传统的官僚政治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社会经济也达到小农社会自然经济的顶峰”[8]前言Ⅳ。但是从公元1077年北宋税赋总收入来看,农业税占十分之三,工商税占十分之七,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南宋永嘉学派最早提出“事功”思想,直接强调利与义的一致性,“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反对当时空谈义理的儒家主流学派,极力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9],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的合理性,永嘉学派的出现成为宋代义利并举观念最好的总结和注脚。
二宋代农林资源保护的历史动因
(一)财政增收的需要
宋代政治制度,尤其是文官制度的完善为农林资源保护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科举制度为宋代政府招揽了大量人才,客观上为包括农林资源保护在内的经济管理活动准备了人事条件。另一方面,随着科举考试制度的变革,文官队伍日益庞大,再加上宋代高薪厚禄优待官员,一般如“太常博士以上春、冬绢各十匹,谕德以下春加罗一匹,冬绵三十两,余客绢七匹”,官至宰相、枢密使则“春冬服各绫二十匹,冬绢三十匹,绵百两”[7]5130,导致冗官冗费激增,再加上军队的供养,每年仅仅是官俸、军饷支出就给政府财政造成相当大的负担,加强对稀缺资源的保护利用有助于增加政府收入,缓解财政压力。传统社会的农林资源大都为国家所有和管理,据《周礼》记载,西周时已经开始征收山泽税、矿税、盐税等,并以此来管理各类资源的开采利用。西汉时桑弘羊最初在各郡设置盐铁官署主持盐铁官营开启了我国的禁榷专卖制度,这一制度既能快速增加政府收入,又可以很好地实现对农林资源的保护,尽量减少植被因盲目开采而被破坏和水土流失的现象,不至“浴河棋布,致使河水日细,泽梁日涸,土地泽饶,变成往事”[10]。当然,禁榷制度的主要目的还是增加财政收入,对农林资源的保护只是其附属结果之一。禁榷之“榷”本义为独木桥,引申为垄断、专利、专卖之意,宋代是我国传统社会禁榷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期禁榷制度一方面朝着更为细密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又兼顾民生,并未盲目扩大禁榷的范围,大体控制在那些不便由私人经营的大宗货物或者与国计民生及国家财政有着重大关系的物资领域。宋代通过强化禁榷积极参与商业经营,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宋代政府的官商体制。禁榷制度大幅增加了宋代政府的财政收入,禁榷所得居然能与两税收入旗鼓相当,同时禁榷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经济发展中的混乱现象,通过政府的宏观控制使经济发展处于较为稳定健康的状态,实现了政府加强经济管理的需要。
(二)优化环境的考量
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宋代自然资源保护的范围主要集中于林木、矿产、野生动物、鱼类等,与其他资源的保护只能通过限制开采、捕捞不同,林业资源除了消极保护,还能积极种植,所以从封建君主到地方官吏都积极倡导民人植树造林,重视对林业资源的管理和保护,每年新植林木的数量都要由官方进行统计,以此作为减免百姓税赋、考核基层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11]。宋太祖曾重申后周的法令:“课民种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太宗甫一登基即规定“两京、诸路许民共推练土地之宜、明树艺之法者一人,县补为农师……”[7]5187并多次下诏要求“列树以表道”。行道树的种植既能养护道路、荫庇行人,又能增补官用木材,战时还可用其隐蔽军事行动,所以广植行道树是我国一项历史悠久的农林资源保护措施。宋徽宗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仅福州行道树“共栽植杉松等木三十三万八千六百株,渐次长茂,已置籍拘管”[12]7502。蔡襄任泉州知州时曾主持“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闽人刻碑纪德”[7]9547。大量史料证明宋代行道树的种植对优化环境、方便出行有相当的成效。据《四明它山水利便览》载:它山原本林木高大茂密,即使遭遇暴雨,沙土因被树根盘固也不至流失太多,后林木被肆意砍伐,水土流失变得严重。而保护林木等农林资源不仅可以美化环境、保护生态,还能降低洪涝灾害的影响,有利于农业生产。因此,宋代也十分重视堤岸林的种植,几乎每任君主都颁布诏令命兵民沿堤岸密植榆柳,且往往明令禁止采伐[13]。林木还因伐薪烧炭成为民人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宋祁曾号召属民种植恺木,因其“厥植易安,数岁辄林,民赖其用,实代其薪……亦得所宜,民家漪之,不三年可倍,斧而薪之。疾种亚取,里人以为利”[7]8411。主要基于优化环境的考量,以林木为主的农林资源在宋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保护,对其的利用也遵循了生态文明的理念。
(三)对外作战的压力
随着马鞍的普及,游牧部落的战斗力迅速提升,北部和西北部的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始终虎视着富庶的宋王朝,而宋与辽、西夏之间的地形以平原为主,有利于骑兵作战。面对游牧民族骑兵战斗力上的优势,宋政权创造性地发展了森林等农林资源的功用,通过绿色屏障来抵御外敌的侵扰。因此,营造、保护军事防御林带成为宋政权巩固边防的一项重要措施。不仅边境地区的原有森林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而且北宋的历代君主都一以贯之地推行“植榆为塞,以捍奔突之势”的政策,屡颁诏令“差官领兵遍植榆柳,冀其成长,以制敌骑”[14]。曾主政宋辽边境要塞雄州的李允则就“下令安抚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种榆。久之,榆满塞下。谓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骑战,岂独资屋材耶?’”[15]2145经年累月之后,终于“茂密成林,险固可恃”[12]4517。据时人统计,“定州北境先种榆柳以为塞,榆柳植者以亿计”,数量极为可观。宋仁宗时防御林的功效已现:“往岁抚使贾宗患边地平坦,不足以待寇,故植榆柳为塞,以绝戎骑之奔突其后。林木既成,虏人患之。”[15]6542宋政权曾绘制《北边榆柳图》,认为充当军事设施的防御林足以长期保障中原地区的安全,直到宋高宗时仍有“河东黑松林,祖宗时所以严禁采伐者,正为藉此为阻,以屏捍外夷耳”的言论[7]405。长期的维护和营造使得御敌林的规模蔚为壮观,“使人每岁往来之路,岁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络翳塞”[16]14。宋代上至皇帝下至边疆官员一致重视将森林作为军事防御手段的做法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明代还在利用森林充当抵御蒙古骑兵侵扰的屏障,这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农林资源的目的。
三宋代农林资源保护的制度保障
(一)明确的法律保护制度
经由五代战乱造成的资源匮乏使宋政权领悟到了农林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尤其是有计划地合理利用农林资源的必要性,形成了理性面对农林资源的观念:“天地生财,其数有限,国家用财,其端无穷,归于一是,则‘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之外,无他技也。”[16]5108宋政权并没有将农林资源保护停留于意识层面,而是通过全面的法律制定和管理机构设置对之做出了制度上的保障。鉴于五代战乱导致民人流离失所,大量土地荒芜,宋政权积极推行垦荒政策,通过立法确认垦荒者对土地享有永业权,并在每年考核时以属民垦荒田亩的数量作为衡量地方官吏政绩的标准。垦荒政策的推行使宋代私有土地的数量大增,在全国土地总数中占有绝对优势。
农业资源立法的主要任务即为保护土地私有权,巩固新的土地关系,促进农业发展,官府不仅不干预民间土地买卖,还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合法的土地权益不受侵犯。宋代曾一度盛行围湖造田,不少有识之士对此持有异议,龚明之就在《吴中纪事》指出:今所以有水旱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围湖造田,围了湖,湖泊便失去了蓄水能力,水涨时无处蓄水,遇天旱时湖自水枯,不能浇地,因而其祸无穷[17]134。由此可见当时的农林资源保护意识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与当今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念存在相通之处。除了保护土地资源立法之外,宋代还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和发展林业资源的法律制度,如“户内永业田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应课植而不植者,每一事有失,合答四十’,以及“诸毁伐树木、稼墙者,准盗论”,“心生盅害,剥人桑树,枯死至三工绞。为三工及不枯死者等第科断”[18]372。宋代法律还有明确规定焚烧山中野草要在农历十月之后,次年二月之前,因为“火田之禁,著在礼经,山林之间,合顺时令。其或昆虫未蛰、草木犹蕃,辄纵燎原,则伤生类”。还规定,“诸荒田有桑枣之处,皆不得放火”。若违反规定要处以重罚,“诸于山林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者,流二千里,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其在外失火而延烧者,各减一等”。“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答五十”。同时,宋代立法还严格控制政府机构因公伐木的活动,要求官司依法行事,“诸系官山木所属州县,籍其长阔四至,不得令人承佃,官司兴造须采木者报所属”[18]516。虽然上述规定深受传统社会农林资源保护立法的影响,并非全部由宋代创制,但法律的严于执行有效地抑制了滥砍乱伐和森林火灾,以严厉的刑事制裁手段达成发展保护农林资源的目的得以实现[19]。宋代法律文化有很多创新之处,重视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社会调控的特点在农林资源保护方面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一点不仅影响了后世各朝的生态文明意识,也对当今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完善的管理机构
据《周礼》记载,舜帝时就已经设有虞官负责农林资源管理,通过规定采伐时限、在物产资源丰富的地方设置藩篱等措施来禁止民人任意占有、支配和滥用农林资源的行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同时伴随着金银、铜铁和盐等重要矿产资源及林木、鱼类、野生动物等动植物资源被列入国家自然资源管理和保护的范畴,宋代自然资源管理机构分工越来越细密,职责越来越明确专一。作为中央管理机构的工部下设屯田、虞部、水部等多个分支机构分别管理环境资源事务,均属环境资源管理机构,其中虞部掌管着全国矿产资源的开采冶炼[17]146。宋代继承了前代的重农思想,设置了一套以户部为中心、中央与地方机构共同履职的农业管理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都大力督促和组织农业生产,把农业生产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首要任务,在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劝课农桑、推广农业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宋太宗年间初设劝农使,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则规定:“自今少卿监、刺史、图门使以上知州者,并兼管内劝农使”,其余知州、通判等,皆兼劝农事[15]1392。地方主政官员必须兼任辖区劝农使,知州上任后颁布《劝农文》这些制度设计彰显了农业管理在宋代政府管理机制中的重要地位。
宋代还设置了一套完善的森林资源管理机构,《宋史》载工部掌管“天下城郭……山泽、苑囿、河渠之政”,“虞部郎中、员外郎,掌山泽、苑囿、场冶之事,辨其地产而为之厉禁”。地方政府则由通判和县丞兼理森林资源管理,采造务、都木务、采木务等设置于林业资源相对集中的地区专司管理相关业务。京西北路的“采造务”、河北路的“盘阳务”、陕西路的“阳平务”同属专司官府所需木材供应与采伐的机构,这些机构同时担负着经营、管理和保护林业资源的职责,中央与地方分司协作、统筹兼顾的机构设置模式有效地提高了林业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效率,有利于农林资源的整合与平衡发展[19]。农林资源管理与保护机构自上而下的设置和管理职能的细化很好地反映了宋代生态文明建设意识的增强,其职能明确、权责统一的行政管理风格也值得当代社会借鉴。
结语
传统“天人合一”观念的突破性发展,以及义利并举思想的萌发和广泛适用为宋代农林资源保护提供了哲学基础。经济水平的大幅提高、经济发展模式与范围的不断拓展为农林资源保护意识的提升和普及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只有充分认识到作为本体的人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到农林资源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使之上升到一定的哲学高度才有可能触及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题,而宋代在这一领域的成就为我们今天的举措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渊源。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到:“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能站在自然界以外——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在于我们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0]近代以来,天人相分、天人相争即强调人对自然的控制、征服、对峙是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主题之一,一方面标志着人类通过技术手段挣脱自然束缚的趋势,另一方面又注定了西方社会势必以精神层面和自然环境的衰败为代价来换取物质层面的丰富。今天世界范围内对环境问题的普遍焦虑宣告了西方早期经济发展模式的终结,作为有着后发优势的新兴国家,中国应该站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制高点上,倚靠本国优良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开创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
注释:
①理性主义早播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西周“敬天孝祖保民”观念的提出开启了传统文化的理性之维,某种意义上承认了天与民之间存在相通性,能否做到“怀抱小民”第一次成为衡量一个王朝成败的标准,原初的民本思想也就此产生。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02.
[2]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241.
[3]张载.张子正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35.
[5]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3-12.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39.
[7](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赵晓耕.宋代官商及其法律调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9]叶适.习学记言序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7:115.
[10]张克复.《五凉全志》校注[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72.
[11]张全民.论宋代的生物资源保护[J].史学月刊,2000(6):27-34.
[1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3]李克华.宋代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及影响[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324-325.
[14]刘华.宋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6(1):36-41.
[1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6](宋)王明清.挥麈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7]袁清林.中国环境保护史话[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
[18](宋)窦仪.宋刑统[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9]郭文佳.简论宋代的林业发展与保护[J].中国农史,2003(2):32-36.
[20][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05.
(责任编辑:刘英玲)
Stud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esources Protection Law in the Song Dynasty
LI Wei-tao,LI Xiao-yu
(College of Law,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Beijing 100044,China)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aintains that man and nature coexist harmoniously and argues against the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by conquering nature.And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legal system based on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day.It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protection and proper us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esources.Along with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society and improvement of legal system,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protection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Dong Dynasty,which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oday’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dea.
the Song Dynasty;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esources protection;legal system;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929
:A
:1674-9014(2013)04-0065-05
2013-03-21
李巍涛,男,河北廊坊人,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传统法律文化和行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