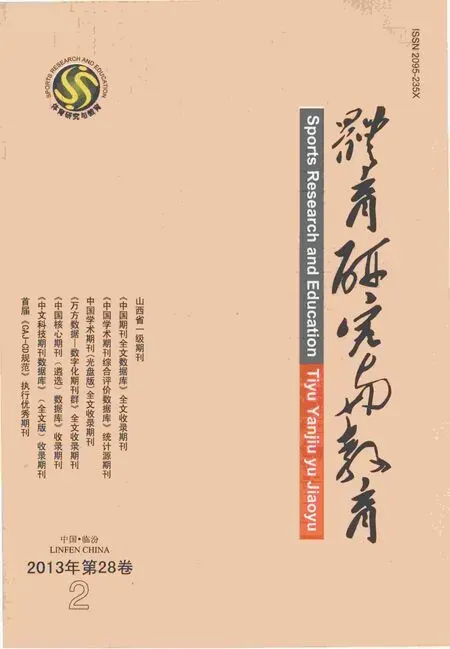古典和现代,变迁与融合:透视城市化进程中的广府龙舟文化
2013-02-15时杰
时 杰
(广州大学体育学院,广东广州510000)
龙舟运动起源于中国,是我国传统的民俗体育项目,具有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广州作为中国的“南大门”,自秦汉以来就是对外开放的门户,近现代以来,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正大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自1978年就已进入了社会的转型期。近30年来,社会变迁使广州大部分地区社会环境和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信仰体系等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革命性变化。随着广州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广府龙舟文化也在嬗变和融合,作为当地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它既折射了村落民俗体育文化在当代城市建设中的遗失和没落,也彰显了龙舟文化不惧岁月洗涤能够与时俱进的独特气质。
1 广州龙舟习俗的渊源和传说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广州端午节的“扒龙舟”(即划龙舟)与许多地方的新兴的赛龙舟活动不同,是一项具有鲜明的乡土文化传承特征的民俗活动。广州的“扒龙舟”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这项民俗活动一直是持续的。从1953年起,广州市有关部门几乎每年组织龙舟比赛和表演(除文革期间被迫中断),时任市长朱光曾作诗:“广州好,端午赛龙舟。急鼓千槌舟竞发,万挠齐举浪低头。屈子不须愁”。
广府龙舟文化作为一项民俗体育活动,产生于岭南水乡民族特定的社会生存空间,来源于先民的生活、生产方式,与现实生活和社会有着直接的关联,表现着岭南人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结构。“北人赛马,南人竞渡”,《汉书·地理志》注:古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淮南子·原道训》也说越人“断发文身,以像鳞虫”。这些都说明了龙图腾崇拜与人们长期在水中活动而产生的保护神信仰有关。古越人以舟楫为家,长期生活在“陆事寡而水事众”的南方水网地区,舟船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生产工具;而龙,是越人即岭南人的祖先崇拜的图腾,古越人为避免海上蛟龙的侵害,便将船制成龙的样式,划龙舟也便成为南越地区人们的一种习俗。所以,赛龙舟风俗可追溯到古越时候,是古时南越人举行的“图腾祭”节日之一。在《南汉书》中记载有南汉后主刘长在广州疏浚“玉液池”,于每年农历端午节举行龙舟竞渡;清《番禺县志》也有端午龙舟竞渡的记载;另据最新考古发现史上最豪华的大型龙舟,就是埋藏于广州市番禺县大洲的“宣和龙”,该船是南宋两位幼帝南下航海时造成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曾详尽描述了两条颇为“传奇”的番禺龙舟,揭开了番禺与龙舟文化息息相关的历史。其中大洲龙船的故事至今仍在当地村民中流传,人们每到四五月份就会传唱两句岁时歌:“四月龙头随街绕,五月龙船抢大标”。这两句岁时歌,可见出端午节斗龙船在此地风气之盛,历史之久。
2 广州龙舟民俗活动形式的嬗变及坚守
2.1 广州龙舟的原生态性与乡土性
原生态的广府龙舟文化来源于农耕文明,是珠三角流域的民间代代传承下来的,与当地水乡农民精神生活相关,也与当地与地域环境相适应的水文化,包括赛舟习俗和与船有关的制作工艺等相关。广府龙舟文化与北方不同,是一种集体育、音乐、文化、饮食、造船工艺于一身的“跨界”文化,其中最能体现广府文化与众不同的就是大量的加入音乐元素,水里的人“扒龙舟”,岸上的人“唱龙舟”。《赛龙夺锦》就是一个著名的音乐作品,它充分体现出了“唱龙舟”的特色。另外,“粤人始做船”的精致的造船工艺、刺绣雕刻工艺(龙首龙尾)、特色的饮食文化(龙船饭)等也是广府龙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广府千百年丰富的龙舟信息,不仅丰厚了龙舟文化内涵,使龙舟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之根,并构成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使其不致被历史湮没。原生态的广府龙舟表演形态,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传递了欢乐、圆满、和谐、吉祥、平安等文化价值,所以它的生命力很强,沿袭至今依然保留着一种淳朴的原始意识。
2.2 广州龙舟习俗的程序和礼仪
2.2.1 广州“扒龙舟”的形式 广州的“扒龙舟”有“游龙探亲”和“龙舟竞渡”两种形式。“游龙探亲”又称“游龙船”、“龙船景”。各方龙船前来应景,只表演技巧,不排名次,从农历五月初一至初五,是各村龙舟探亲的日子,邀请别人叫“招景”,龙舟前去探亲叫“应景”或“趁景”。“招景”与“应景”是相互的,你来我往。龙舟每到一地,往往要进行一种礼仪性和表演性的赛龙活动,由此形成各地不同的“龙船景”。“趁景”仪式有起龙、进水拜神、采青、划船、吃龙船饭、入窦过程,主要是赛技巧、赛艺术。龙舟竞渡俗称“划龙船”、“斗龙标”或“划斗龙”等,“斗龙舟”在“趁景”热身之后举行,比赛规程较为复杂。广府龙舟竞渡时,选手用桨叶插入水中,再往上挑,使水花飞溅;船头船尾的人则有节奏地顿足压船,使龙舟起伏如游龙戏水一般。其中起龙、投标、斗标、散标仪式无不体现出热烈欢娱的性质,斗龙船主要是赛体力、赛毅力。在宗族制度发达的南方社会,“斗龙标”这种男性集体的娱乐更带有强烈的宗族色彩,可视为族团内的联欢与族群间的博弈。实际上古代龙舟的“江上年年夺锦标”的“夺锦标”就是现在龙舟竞技比赛的雏形,是现代竞技比赛中的“锦标赛”最初来源,这也就使得传统龙舟文化能够演变出符合现代体育精神的竞技龙舟项目。
2.2.2 广州“扒龙舟”的程序、仪式及禁忌 广府龙舟民俗活动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独到特色的仪式程序和礼节文化:例如打造龙舟时的诸多禁忌、龙舟如何下水、如何归仓等。到了“斗龙”之日,起龙船与扒龙船、藏龙船三大项构成了赛龙舟的整个程序。在赛龙舟的每个程序中,都有着一定的礼仪规则。“四月八,龙船透底挖”,待“龙抬头”后,方可选择“开日”“起龙”,“恭请”“出龙”。扒船期间,早上先打龙鼓,族人齐集“龙船亭”“拜龙船”,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然后“取龙舟头”,晚上再“送龙船头”,一送一还,一日两次。迎送的队伍一定要保证龙头先行、龙尾殿后的原则,目的是保证一个完整的龙身顺序,俨然“真龙”在世。值得注意的是,对龙舟进行装饰是“圣化”的正式礼仪,船头雕刻成龙头形,船身画有龙鳞,不仅形似而且神似,这也正是龙舟的称谓由来。在挪动龙舟的过程中,所有视为抓、抬、提等动作,都在忌讳之列。
“圣化”之后,一系列象征性的仪式如洗龙舟水、饮龙舟水,投龙船标、送龙船标、散龙船标,吃龙船饭,藏龙船等都带有与神灵进一步沟通的意义。广府龙舟文化里特有的采青、送青、点睛、请神等环节也是龙舟“圣化”礼仪的延续,如在广州天河区,农历四月初八起龙的时候除了放鞭炮,敲锣鼓,给龙船上油以外,人们还有进行“采青”的习俗。据《广州市天河区志》记载:“农历四月初八是起龙舟的日子。起船时,要放鞭炮,敲锣鼓,待船洗刷干净并上油后,再拔几棵禾苗分别放在船头和船尾上,谓之“起船采青”。其中两株连根的水稻,起名为“禾花春女”,富有诗意。另外,“开光点睛”也是岭南各地在正式的龙舟比赛之前进行的一项重要的竞渡祭仪。龙舟节前后仪式的威严、圣洁,已然将龙舟“圣化”,使其成为一种受人尊敬的“真龙”。人们心怀敬畏,虔诚地进行一系列的龙舟“圣化”礼仪,使得北帝的保驾护航“扒龙船”便有了更可靠、更有效的祈福禳灾功能。如龙舟歌谣唱道:“打鼓仔,扒龙船,扒得快,好世界,米又平,仔又大,娶埋新抱着花鞋”,歌中寄托着人们朴素率真的理想,其中既有对农业丰收的渴望,也有对生活幸福的企盼,由此可见,赛龙舟是对自然环境与生态及人自身的生产方式的调适和平衡。这正是“龙舟祭”的目的所在,从中也体现了广州人务实的文化风格。
2.2.3 广州“扒龙舟”习俗里的“龙舟饭” 珠江三角洲最具有传统龙舟活动区域特点与文化功能的活动当属“龙舟宴”,龙舟具备调适人际关系的现代功能。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龙船“得胜还埠,则广召亲朋燕饮”。这种宴饮,珠三角人称为食“龙舟饭”。一年一度的龙舟饭,是大家期盼已久的团体盛宴,不管什么人都可以食用,以广结“龙缘”,遍得“龙福”。祖先祠堂里的“龙船饭”包含有图腾祭和祖先祭的双重意义,是隐含于龙舟祭之中的祖先祭祀行为,藉此实现敬宗收族、扩充势力的目的。龙舟活动作为契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众之间的乡土情谊。
3 城市化进程中广府龙舟文化的变迁和隐忧
3.1 广州龙舟文化的“保真”和与时俱进
岭南水乡借龙舟竞渡谋取食物的活动,常常带有宗教迷信成分。古代农耕民族就常有在农业生产的开始和收获结束时举行各种各样的庆典和祭祀活动的习俗,这些仪式经过多年的流变慢慢演化成今日的龙舟祭,而龙舟仪式中承载的恰恰是民俗文化的内核。透过“圣化龙舟”仪式的有序和威严,我们可以看到由龙舟竞渡形成的广府龙舟文化是岭南水乡农耕文化的产物:乡村的原始性、自然性环境,和龙舟文化的精神元素是统一的。或者说有农耕文化背景,才有岭南人朴素率真的生活意象:欢庆丰收、寄托理想、祈盼平安等等,这些都是老百姓最真实、最原始的需要。每年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除了激烈的比赛,还有来自广州各个区(县级市)的彩龙、游龙表演。海珠区联星庄头村历史上以种植各种名花闻名,因此该村龙舟队素有“未闻龙舟锣鼓声,罗伞花香已醉人”的说法;珠村的彩龙、游龙除了宣传自己的文化外,也不忘与时俱进,整个船身写着“龙腾盛世共筑中国梦,凤仪珠村同绘乞巧情”等大字,格外显眼。又如1965年广州出现第一支女子龙舟队成为大事件,这一举改变了过去妇女不能上龙船的旧传统。现在,广州各区如番禺、黄埔、天河等都组织起了女子龙舟队,妇女们顶起了龙舟的“半边天”。妇女上舟是对传统男子地位和观念的一种挑战;这种变化表现了时代和社会的进步,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3.2 广州龙舟文化的“没落”和被动遗失
3.2.1 广州城市化建设导致自然环境的改变 近年来,随着珠三角地区城市化的不断加深,城中村被拆迁与重建,传统的农耕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被改变,广府龙舟文化里的传统仪式细节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如过去的“扒龙舟”活动,在龙船点睛开光仪式之后,村民们纷纷跑来取“龙舟水”进行洗浴,据说给小孩子洗身,一年远离疮疥;用来浇花,能够久不凋零;直接饮用,可以强身健体。但如今因为河水受污染水质变差的缘故,村民只好用纯净水或自来水充当“龙舟水”。
岭南农村典型的文化标志祠堂、河涌、榕树、龙舟等具有民族文化特质和元素,承载着人们深层的精神世界,是彰显族姓身份的表征,同时也构建了广州“城中村”特有的龙舟文化风景线。城中村里一个个座落在水塘旁榕树下的祠堂、在广州城里四通八达的河涌,是“扒龙舟”民俗的文化空间。然而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和旧城的改造,城市边缘的环境形态也不同程度地发生着改变,由于以往广州城市发展对此没有相应的关注,城区建设和市政道路往往切断或占用河道,从而割裂了龙舟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环境,如广州东部的“猎德涌”仅剩最后百多米可以划船。端午节,石牌村人在现代都市最后的缝隙中,执着而无奈地挥动起最后的船桨,追寻着最原始的村落文化记忆。而诸如棠下涌等,现在都只有涌而无龙舟了,尽显落寞与沧桑。尽管珠江分岔流经市区,以江为主流仍然贯串着不少大大小小的支流河涌,但是可以想象伴随着岁月更迭,河涌(chong)随着城市化的建设会渐渐消逝,传统的龙舟民俗恐怕只能移师珠江之上,将要失去游弋在自己村庄河涌里的那份荣耀。
3.2.2 广州城市化建设导致人文环境的改变 过去,广州的赛龙舟活动上龙舟的人都是以青壮年为主,近年来龙舟上的艄公呈现中老年化的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城中村”的拆迁重建,使原住村民“社区化”流动,年轻人不是在外求学就是在企业谋职,另一方面是由于认识层面上代际分化,年轻一代趋向对城市文化的认同,而年长一辈则更多的是坚守村落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看到的在龙舟活动中参与群体大部分是中老年人的缘故。要解决龙舟的传承问题,政府应该积极倡导和组织民间的“龙舟俱乐部”,通过比赛,激发年轻人的参与热情,培养新一代龙舟队伍。
3.2.3 社会大环境的变迁
(1)市场经济发展对人的价值观的冲击。广州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市场经济的发展无疑将促进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文化精神的转变,但随之而来的就是风俗习惯的改变、社会伦理道德的变化以及个人的内心的价值冲突、思维方式的变化、审美观的变化等等。人们文化素养的提高,迷信禁忌的减弱,带动了龙舟民俗由娱神、酬神的夺标赛会,变成了娱己、娱人的民族传统体育盛会。经过移风易俗运动的洗礼,随着现代龙舟竞赛体制趋向实用和标准化,龙舟运动也不可避免地步现代舞龙、舞狮的后尘,原始习俗礼仪正逐步减少,一些宗教祭祀活动在流于形式,竞赛中原有的严格规定和禁忌则在慢慢松弛甚至消失,固有的民俗文化内涵越来越稀释:一是削弱了端午节的娱乐化程度;二是消解了龙舟竞渡民众参与的普遍性;三是弱化了龙舟竞渡的礼仪文化内涵。我们要认识到这种现象发生在龙舟由民俗活动向现代体育转变的过程中是必然的,这与社会大环境的变迁是分不开的。
(2)现代体育精神对人的价值观的影响。传统龙舟文化是现代龙舟运动的根基,现代龙舟运动的发展离不开传统龙舟文化。传统龙舟中的龙舟样式、比赛形式、祭祀仪式等在现代龙舟运动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它制约着现代龙舟运动发展的方向。现代龙舟是古代传统龙舟的一个延续,我们万不能忽视民族文化的传承,必须找到龙舟文化与社会价值新的契合点,突出龙舟礼仪和秩序中的威严,保留其民族的核心形式。现代龙舟运动中传统祭祀色彩依然存在,正是古老的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生活中为维护自身存在而做出的回应和努力。“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唯有此,龙舟文化才能发扬光大。
4 城市化进程中广府龙舟文化的发展和启示
4.1 龙舟民俗和端午节以及屈原的三者联系
据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列举的百余条古籍记载及专家考古考证,端午的起源是中国古代南方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广州端午节“扒龙舟”最初并不是为了纪念屈原,岭南水乡“扒龙舟”的习俗在广东远远早于祭祀屈原,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后来,有关端午起源与端午习俗的原始神话色彩被充满人文色彩的关于屈原的历史传说所取代,龙舟竞渡作为连结龙文化与端午文化的核心纽带,也从“图腾崇拜”“祭祀神灵”“攘灾驱瘟”“祈农丰收”等逐渐集中到纪念屈原一个人身上。此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人们便以“龙舟竞渡”来纪念屈原。而屈原人格中最动人的部分,是他超越个体和时代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种情怀早已融入中国人的血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维度。人们把“龙舟竞渡”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彰显了同是“龙的传人”、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等道德伦理意义和慎终追远、感念祖先的感恩意识。因而,后来的“龙舟竞渡”是一个既受端午节早期节日性质的决定而出现,同时又在节日性质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节俗活动。端午节作为龙舟文化生存的载体和土壤,是龙舟文化能够在广州依然存留的组织依托。如今,端午节已被正式纳入我国法定节假日,端午习俗也成功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1994年广州市政府更是把端午节定为龙舟节,这对进一步弘扬本土传统龙舟文化,增加民族凝聚力,无疑具有极为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逐渐恢复龙舟民俗和端午节日中原汁原味的文化形态,进一步挖掘其内在的精神文化内涵。
4.2 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精神家园中的返璞归真
“扒龙舟”是岭南水乡百姓的一项重要民间活动,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精神崇拜,不管是祭祀也好、娱乐也好,都能真实地反映不同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生活面貌。温家宝在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时说得好:“第一,它是民族文化的精华;第二,它是民族智慧的象征;第三,它是民族精神的结晶”。龙舟运动是老祖先给予我们回归自然、认识自我的恩赐,人们通过参与这项民俗体育运动,亲身体会集体活动项目高度的集体荣誉感,自觉或不自觉地会融入到比赛中去,全身心地体会共同努力、齐心协力、争取胜利的感受,进而增强集体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4.2.1 广州地区浓厚的宗族意识 广府龙舟文化传递的是真实的乡土气息,是老百姓在龙舟文化上“保真”的创造。其中浓厚的宗族色彩是岭南龙舟节的共同特色。在广府文化里,“扒龙舟”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民间竞技,而是与族群集体意识、信仰世界、情感生活紧密联系的重要符号。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宗族社会里,“扒龙舟”是村内最隆重的庆典,其热烈程度堪与春节相媲。旧时的“龙舟竞渡”是为了唤起广大族众的历史感、道德感和归属感,既满足族人文化娱乐的精神需求,又通过活动进一步增强宗族内聚力。我们知道“斗龙船”,有祈福禳灾的意义,追逐的是雄武有力的理想,营造的是心惊肉跳又动人心弦的氛围,而在神秘、庄严的祭祀中龙舟人的精神得到了神灵的抚慰。在旧时的现实生活里,“竞斗夺标”是宗族社会里人们为了维护个人和本族利益,展现个人英雄主义而采取的激烈的、对抗的相对较为原始的集体游戏,既有血腥,也有刺激,因此“扒龙舟”对于现代人仍有着难以言说而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4.2.2 现代都市人们精神家园的回归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州“扒龙舟”再次充当了整合器和压力阀的角色,成为“城中村”村民在融入城市文化后一种群体身份的特征,是一种维护传统、凝结情感的强力黏合剂。时至今日,“扒龙舟”依然以宗族为单位开展,并延续着“游龙探亲”的风俗,大鼓和船桨上依旧鲜艳的标明宗族姓氏的大字,具有标榜自我的象征意义。但在广州的现代社会里,“扒龙舟”的意义得到了扩展,由宗亲之间血缘联系的文化符号衍变为地缘之间的人群情感连结纽带,“游龙探亲”为都市“乡村人”再造了一个熟人社会。其中,猎德村刚好嵌在广州顶级商务中心的“城中村”,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观看“扒龙舟”赛事,历来是广府人们端午节必备节目之一。每年猎德村、天河塘厦、荔枝湾、番禺等地都有举办龙舟赛的传统。每年端午,从涌边高楼倾巢而出的村民,构成了一幅都市乡村怀旧的画面,桨声灯影里的龙船景,或许正是村民力图挽留的精神家园。
4.3 广府文化的有容乃大和开拓进取
广府文化具有兼容并包性、多元性、开拓开放性和务实性等特点。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就开风气之先,发展市场经济,切实展现了广府人的龙舟精神。龙舟文化中体现出来的“齐心协力、团结协作、拼搏进取、奋勇争先”精神正是广府文化的精髓,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和很好的传承。
4.3.1 广州人的性格使然 龙舟运动在广州有着浓厚的草根基础。“广州国际龙舟节”的举办,正是四乡龙舟活动使然。在广州至今还流传着一段龙舟比赛佳话:民国年间,广州曾举行过一次赛龙舟,当时番禺沙亭村的龙舟和小洲村的龙舟都划到了第一,但在夺标时,两个船队把那面写着“通海第一”的标旗撕扯成两半,沙亭村抢到了“通海”二字,小洲村抢到了“第一”。据了解,这面被撕破的旗子保留至今,成了文物。由于番禺与龙舟文化的深厚渊源,中国民协授予番禺石楼“中国龙舟文化之乡”和“龙舟文化传承基地”的称号。
广东人有句俗语,“龙船划得快,今年好世界”。赛龙舟作为岭南水乡最生动的显影,曾经被记录在一首人们耳熟能详的广东音乐《赛龙夺锦》中(清末音乐家何柳堂作),曲子的音符打破了广东音乐一贯轻盈灵动的节奏,间中加入了阵阵鼓点。此曲响起,人们如身临龙舟比赛现场,龙舟似离弦之箭冲浪前进,龙舟的锣声鼓点萦绕于耳,不由地精神亢奋,并随着鼓点的节奏而产生一种身体与精神的共鸣和协同,使人得到直接的、令人愉悦的情感抒发和宣泄。水任器而方圆,赛龙舟是广州人性格的最好诠释。
4.3.2 广州政府的积极扶持 广州市政府于1994年把端午节定为龙舟节,使得龙舟文化与民俗节日融为一体,体现了广州城市文化的包容和魄力。2010年广州亚运会龙舟首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从此它便成为了现代体育项目大家庭中的一员。至今广州已连续举办了20届的“广州国际龙舟节”,在这个“龙舟的盛会,人民的节日”里各个阶层的人们广泛参与其中,使龙舟这一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全民健身”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并且具有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时代发展中彰显了新的亮点。
4.3.3 广州注重文化生态环境建设 广府文化的兼容并包,注重传统,也体现在了城市建设理念的变化上。广州城市规划建设具备文化生态的眼光,城市文化生态环境建设通过调和城与村的矛盾,注重河涌所承载的环境文化,把“河涌-滨水公园-城市生态绿化带”作为理想前景,保留了村头榕树,旧时祠堂,龙舟活动和良好的城市景观环境生态。广州媒体曾经做过的《广州地理》、《新广州人》等系列节目就是以“扒龙舟”等传统乡土文化作为广州都市文化特色而构建起来的新的都市想象。
4.3.4 龙舟赛事彰显现代中的传统 传统的龙舟竞渡与体育比赛结合形成了现代竞技龙舟运动,使得这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龙舟运动走向了世界,可以说“龙舟竞渡”从民间走向竞技,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如何使这一古老的体育项目能够得到很好传承与发展,笔者认为不能一味地提倡竞技性质而忽略龙舟作为民俗体育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其实无论现代龙舟运动如何发展,它都摆脱不了传统龙舟运动的影响。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看到中国龙舟协会在近年来举办的一系列赛事活动中,除了弘扬“团结协作、拼搏进取”的龙舟精神外,还刻意保留和延续传统龙舟活动中的点睛、游龙、喝黄酒、吃龙舟饭等民俗。说明作为广府龙舟文化的特色——珠三角的“龙舟说唱”、龙船制作的考究、龙船饮食文化,已经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并制定了若干培养政策,鼓励民间力量的发展和壮大,这对广府龙舟文化保持独树一帜的风格意义重大。
5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继承和弘扬龙舟文化
5.1 挖掘龙舟文化更深层次的内涵和特质
文化是产生价值观的基础。要使龙舟文化传承、发扬下去,龙舟人就要树立更高的文化自觉,增强传播民族体育的责任感和传承民族文化的自觉性,将文化的穿透力、感召力、影响力更多的渗透在龙舟中,以增强龙舟的文化影响力。要不断地通过丰富龙舟文化的内涵,打造面向世界、面向基层的龙舟运动,既保持传统性的龙舟文化风采,又要具备多样性的现代龙舟运动神韵。作为龙舟人要自觉培育和传承龙舟精神,挖掘广府龙舟文化最深层次的内涵,体现岭南人锐意改革和务实创新的特质,注重其与中华民族精神、中华体育精神和广东精神的契合,把握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体育的要求,在保持传统的前提下积极融入时代发展潮流,为广州市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广州乃至整个广东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发挥出社会体育应有的功能。
5.2 力求将龙舟精神与广州社会发展融为一体
任何文化形态必须服务于社会才具有存在价值,才具有生命力。现代龙舟运动应大力弘扬“团结、协作、拼搏、进取”的龙舟精神,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主体生存意志与勇猛精进的民族个性传承下去。广州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敢于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就是龙舟文化与广府文化的契合点。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历来都是文化传统得以传承千古的巨大动力,也是一个地方形成团结精神和集体力量的最好根基。具备了这种文化根基,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就会后劲十足,对传统继承与超越的动力就能源源不断。
[1]何培金.中国龙舟文化[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
[2]胡潇.文化现象学[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3]高小康.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都市文化的包容性[J].山东社会科学,2011,185(1):61 ~64.
[4]储冬爱.城市化进程中的都市民间信仰——以广州“城中村”为例[J].文化研究,2012(1):69~75.
[5]刘泳斯.地缘和血缘之间:祖神与“会馆”模式祠堂的建构[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0(1).
[6]练情情.猎德拆了龙舟照扒[N].广州日报,2008-06-07(6).
[7]云琼菁.广州体育资源优势与发展对策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8,28(3):17 ~20.
[8]倪依克.当代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思考——论中国龙舟运动的现代化[J].体育科学,2004,24(4):73 ~76.
[9]杨罗生.驾起承载雅俗文化的龙舟——论龙舟竞渡的起源及其文化意义[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26(5):27 ~31.
[10]赵东玉.端午龙舟竞渡民俗的文化选择[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5(3):116 ~119.
[11]肖毅强,孙一民,周剑云.环境文化的重构——记广州天河区深涌景观改造工程[J].中国园林,2002(2):14~16.
[12]徐勤儿,简波.文化形态学视野下的中国龙舟运动文化特征[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06,22(6):11 ~13.
[13]罗会珊,花传国.原生态龙舟文化符号和乡村旅游[J].农业考古,2010(6):337 ~339.
[14]王福民.龙舟竞渡与中华民族精神[N].光明日报,2012-06-22(4).
[15]储冬爱.社会变迁中的节庆、信仰与族群传统重构——以广州珠村端午“扒龙舟”习俗为个案[J].广西民族研究,2011(4):55.
[16]黄心豪.广州打造“中国龙舟名城”[N].中国体育报,2010-06-28(7).
[17]孙适民.屈原、端午与龙舟文化[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79~84.
[18]李培.中国首届龙舟文化节今日番禺开锣[N].南方日报,2009-05-28(B3).
[19]储冬爱.“城中村”民俗文化嬗变与和谐社会调适[J].广西民族研究.2009(3):90 ~95.
[20]曹彧.龙舟人要树立更高的文化自觉[N].中国体育报,2012-01-02(5).
[21](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下)[M].中华书局,1985.
[22](宋)文天祥.端午感兴[M].京市中国书店,1985.
[23]凌远清.顺德改革发展进程中对广府文化的传承与超越[J]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