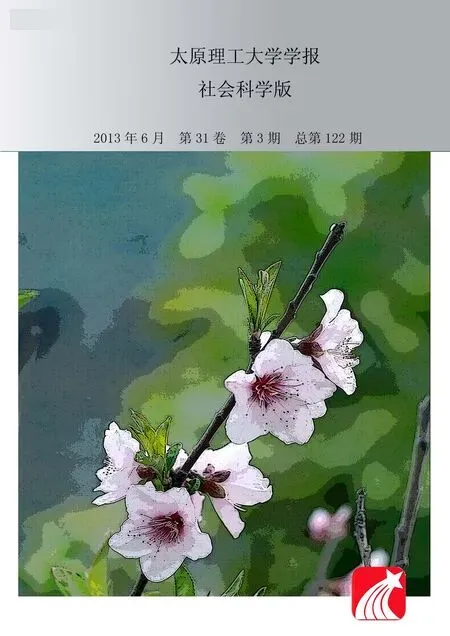运输型犯罪废止论
——以运输毒品罪为视角
2013-02-14张洪成
张洪成
(安徽财经大学 法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以运输作为犯罪客观方面的罪名,在我国刑法中并不罕见。从立法上看,运输行为一般都是与其他的相关行为,如贩卖、制造等行为并列规定,其规定的方式既有配置完全相同法定刑的,也有单独予以规定的,但无论是哪种立法方式,都将运输行为予以独立犯罪化。这样的规定本身肯定了运输行为的独立性,不过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还是值得商榷的。本文以运输毒品罪为视角,论证运输型犯罪在刑法中没有独立确定为一类犯罪的必要,而且即使废止了运输型犯罪,该类行为仍然能得到刑法的充分、合理评价。
一、我国运输型犯罪立法现状
运输型犯罪作为一项单独犯罪在我国《刑法》中比较常见。在很多涉及特殊物品的犯罪中,运输均与核心的、危害性较为严重的贩卖、制造等行为被一起犯罪化,而且配置了完全相同的法定刑,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但也有一些条文明文规定,运输行为与危害性较小的购买、持有等行为并列确定为一类犯罪,并配置了相同的法定刑,如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事实上,单纯的运输行为,往往很难构成独立的犯罪,只有在和其他具有密切联系的行为合并在一起时,才有单独处罚的必要。但是,从立法上看,运输行为有时是和危害性严重的制造、伪造、贩卖、买卖等源头性、流通性较强的行为并列规定,并赋予其强烈的可谴责性,而有时又与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的购买、非法持有等行为并列规定,赋予其相对较小的可谴责性。如果我们不论具体行为的犯罪对象,单纯考虑运输行为的社会意义,就能发现,刑法对该类行为的立法是存在很大矛盾的,即同样的流通性质的行为,赋予了完全不同的社会意义,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运输行为本身要么全部与源头性的制造、贩卖、伪造等行为并列,要么就只和后续的购买、非法持有等行为相并列,这样才能保证对同一行为谴责上的平等性,而现行实施却并非如此。
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涉及运输类犯罪的主要罪名有: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刑法》第125条第1款);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刑法》第125条第2款);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刑法》第171条第1款);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刑法》第341条第1款);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刑法》第344条第1款);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刑法》第345条第3款);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刑法》第347条第1款);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刑法》第352条)等。实际上,从这些运输行为与核心的贩卖、制造、伪造等行为的关联性上看,核心行为一般均能涵盖运输行为[注]这取决于如何理解运输的含义,从目前的理论及实践看,使物品发生空间上的位移无疑就充足了运输的客观要件。,如果把运输行为再单独规定,与贩卖、伪造、制造、购买、非法持有等行为并列确定罪名,有重复评价之嫌;而且,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看,单纯的运输行为,尤其是和贩卖、伪造、制造行为无关的运输行为,其社会危害性明显低于贩卖行为,将这二者纳入同一量刑层次,会显得量刑明显失衡。故这类运输型的犯罪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与危害性较为严重的核心行为并列规定都是存在问题的。
在我国现行法中,明确将运输行为作为核心贩卖行为外延之一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立法模式值得我们借鉴。按照我国《刑法》第240条第2款的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这里明确规定,作为运输方式之一的接送、中转行为,均属于拐卖妇女、儿童行为的一种,在认定拐卖妇女、儿童罪时,没有必要再将运输行为单独作为运输妇女、儿童罪来处理。这就可以避免拐卖行为与运输行为评价上的冲突与矛盾。但这种模式,也仅仅是通过解释的方式实现的,其在实体法上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认可。下文拟以运输毒品罪为考察的视角,来论证在我国《刑法》中废止运输型犯罪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期为立法与司法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国外运输毒品犯罪行为之立法模式
将运输毒品罪单独作为犯罪论处的国家对运输毒品罪的规定与我国相似,即运输毒品罪单独成罪,并配置相应的法定刑。从目前世界各国的立法上看,多数国家还是与我国的立法体例相似,都将运输行为与贩卖、制造等行为并列规定[1]。但因为具体司法体制上的差异,对于同样的运输毒品行为,虽然法定刑配置相同,但在中外具体的量刑上可能存在重大差异。
为了将运输毒品行为与贩卖等行为进行区分,以实现合理评价,有不少国家和地区没有将运输毒品行为单独设罪,而归入走私毒品、贩卖毒品或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中予以惩处。如日本刑法就将贩卖毒品行为与运输毒品行为结合在一起,形成所谓的贩运毒品罪。日本之所以将其规定在一起,主要是考虑贩卖毒品罪与运输毒品罪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而成立贩运毒品罪,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贩卖或者运输的行为之一即可[2]。
我国香港地区的刑事法也与日本刑法类似,从香港地区《危险药物条例》第4条和第6条的规定看,涉及毒品犯罪的两个重要罪名就是贩运毒品罪和制造毒品罪,但从其法条的明确解释来看,这两个罪名实际上包括了类似于我国《刑法》中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四种行为方式。“具体而言,香港地区‘贩运’之含义,相当于大陆‘走私、贩卖、运输’含义之总和,并且范围更广。《危险药物条例》第2条规定:贩运之含义包括输入或者输出、获取、提供及以其他方法经营或者买卖毒品,或者以贩运为目的而持有毒品。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看出,香港地区‘贩运’一词内容的广泛性。”[3]香港地区“贩运”的含义非常广泛,“以贩运为目的而持有毒品的”,应以贩运毒品罪论处[4]。可见,这是将运输毒品罪涵盖于其他相关犯罪中的立法实践,而且实现公正评价,亦非不可能。
从目前多数国家的刑法规定看,运输毒品是与贩卖、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等相并列的行为,但事实上,这些行为之间因为存在天然的密切联系,导致运输与相关行为的界限非常模糊。那么,刑法将运输毒品罪如此规定,有无意义,抑或运输毒品罪本身有无存在的必要,均是刑法理论上争议较大的问题。
三、国内运输毒品罪存废之争
运输毒品罪是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的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相并列的罪名,因此,在理论及实践中,赞成运输毒品罪存在的观点属于主流观点,而且很多专著与论文均立足于存在论的角度,对其构成要件展开了讨论[注]现有的刑法学教材基本都将运输毒品罪作为独立的犯罪行为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并列论述,肯定了其在刑法上具有独立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讲,作此处理的论者实际上都是肯定了运输毒品罪独立价值的。。而从司法实践上看,对行为人判处运输毒品罪的案件还是比较多的,据统计,目前毒品犯罪案件中,运输毒品罪的判决占据了所有毒品犯罪案件的三分之一[5]。从这个角度看,运输毒品罪在当前的毒品犯罪刑法规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运输毒品罪应否存在,也并不是没有争议的。从理论的角度分析,有论者就认为,即使不单独规定运输毒品罪,也可以对该类行为进行处罚,相反,将运输行为单独设罪,会产生量刑上的不均衡。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实践中对那些能够证明确实是受毒品所有者雇佣,为他人运输的行为人,在确定刑罚时可否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的行为有所区别,在法定刑幅度之内,量刑时酌情从轻。特别是适用死刑时,比走私、贩卖、制造毒品在毒品的数量上把握更宽一些”[6]。既然运输毒品罪是与走私、制造毒品罪并列的行为,那么在量刑上就必须保持一致,但这样无疑对于运输毒品的人来讲是不公平的,无法实现罪刑均衡,因为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上讲,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明显较运输毒品罪重,而且从运输毒品罪的犯罪诱因上看,其更多的是社会经济、生活上的因素,故无必要将之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并列规定。而《刑法修正案(八)》在考虑是否应当废除运输毒品罪的死刑过程中,也产生了争议,有论者就认为,运输毒品犯罪行为是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犯罪的辅助环节或者手段,在整个毒品犯罪中具有从属、辅助性特点,其社会危害性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等源头性犯罪明显不同。而且从涉罪主体看,该罪的行为人大多是受雇、受指使的贫民、边民、孕产妇及无业人员,并非毒品所有者,不是最大的获利者,很多是出于生活贫困或受人利诱赚取少量运费,主观恶性一般不大。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出发,对运输毒品罪死刑的适用标准应当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有所区别[5]。既然从社会危害性等角度考察,运输毒品罪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存在重大差别,而且,运输毒品行为一般在该类犯罪中起次要作用,那么将运输行为与上述三类行为并列规定,配置完全相同的法定刑,其本身就是不合理的,现行的刑事立法方式必须转变。
从司法实践看,运输毒品罪主要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存在:第一,在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的过程中,同时实施了运输的行为;第二,行为人本身对毒品不具有所有权,而是受到走私、贩卖、制造毒品者的要求,帮助其运输毒品的;第三,行为人利用不明真相的人员进行运输毒品行为。对于这三种情况,即使我国刑法中没有运输毒品罪的规定,区分情况分别认定为走私毒品罪、贩卖毒品罪、制造毒品罪或者非法持有毒品罪就可以达到充分评价的目的,而且还可以贯彻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在第一种情形下,运输行为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只是走私、贩卖、制造等主要犯罪的前提或后续行为。这与制作、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的人运输或雇佣他人运输淫秽物品一样都不具有独立价值。对此,直接将该行为定为走私毒品罪、贩卖毒品罪、制造毒品罪即可,没有必要再单独定罪;在第二种情形下,行为人实际上是走私、贩卖、制造者的帮助犯,在其中起到帮助作用,以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论处即可;至于较少见的第三种情形应当视为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的间接正犯或帮助犯。
通过这三种处理方式,就已经充分评价了运输行为,对其在刑法上的意义进行了全面的评价,而无需再把运输行为单独予以列举。
从现实情况看,当前我国刑法中单独设立运输毒品罪是存在较大隐患的。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在目前的立法、司法现状下,很难保证其立法目的不被背离:“其一,大众话语的影响,司法中往往把一些没有走私、贩卖、制造的实行故意或帮助故意不全然具有‘运输毒品罪’主观的行为人,误为运输毒品罪判处。刑法赋予运输毒品罪严重的可谴责性,最高可科以运输毒品罪死刑,并不在于‘毒品在运输’中,根本的是行为人为何运输。如系为自己吸用,立法者绝对是不会认其为‘罪可处死’的犯罪行为,不过是持有毒品罪的行为人在‘动’而已。其二,司法中对于帮助他人运输而构成的运输毒品罪的,普遍偏重,甚至畸重。这使得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在毒品案件的贯彻中大打折扣”[7]。因此,将运输毒品罪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并列规定为独立的罪名,很难实现刑法的立法目的,造成罪刑上的不均衡。
运输毒品罪在立法和司法上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就是废止该罪名,通过相关的刑法理论来进行解决。事实上,在一些案件的审判过程中,不独立判处运输毒品罪,而将运输行为评价在贩卖、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中,或者作为相关犯罪的间接正犯,也实现了公正处理的目的。
四、运输毒品罪废止之可能性
国内外理论及实践界关于运输毒品罪存废可谓众说纷纭,而立法及司法实践似乎支持了存在论的观点。但是,运输毒品罪真的具有那么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需要动用严厉的刑罚措施进行处理吗?对此,有论者就认为,对运输毒品罪从严处理是具有正当化根据的,因为“运输毒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于便利了毒品的流通与蔓延。对于那些远离毒源地的吸食者而言,他们自身的购买、运输毒品行为,无形中促成了走私、贩卖毒品犯罪的猖獗。不考虑运输毒品的目的性,正是为了制止走私、贩卖等毒品犯罪,禁止公民长期吸食、注射毒品,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治安秩序”[8]。就是从这个角度看,运输毒品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等行为安排在同一量刑幅度内就显得比较合理。但事实上,这样的观点可能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走私、贩卖、制造这些行为直接产生出毒品,并直接流通到民众中间,直接危害社会,而运输毒品的行为仅仅是为这些行为提供一定的帮助,而且从实践中运输毒品的多数主体看,运输毒品的行为人主观恶性一般明显小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的行为人,这些人多是处于社会的底层,从事运输毒品在很多时候可以说是生活所迫,不考虑这些因素,而将运输毒品者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的人员同等处罚,忽视了重刑不一定是有效治理措施的基本观念。
在强调刑罚轻缓化的今天,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限制死刑的适用呢?笔者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通过司法方式限制运输毒品罪的死刑适用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做法。但从长远来看,运输毒品罪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该罪名存在的唯一功能就是可以剥夺罪犯的生命及财产,其他的正面功能基本没有,而且该罪名的存在,也使国家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很难落实。
事实上,虽然我国《刑法》将运输行为与核心的犯罪行为并列规定,但其能否同等处罚,还是有诸多疑问的,而且有论者就从运输行为与核心行为的关系角度提出,应当限制运输行为的处罚。以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为例,张明楷教授就认为,所谓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是指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出售、购买或者运输,且数额较大的行为。同时认为,伪造货币并出售或者运输伪造的货币的,以伪造货币罪从重处罚,不另成立出售、运输假币罪。但这仅限于行为人出售、运输自己伪造的假币的情形。如果行为人不仅伪造货币,而且出售或者运输他人伪造的货币,即伪造的假币与出售、运输的假币不具有同一性时,则应当实行数罪并罚[9]。同样的观点在毒品犯罪中就应当是行为人贩卖毒品或者运输毒品的,以贩卖毒品罪从重处罚,不另成立运输毒品罪,这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论。同样,将运输毒品罪废止,或者适当降低其法定刑亦是一个解决之道。但论者更加倾向于将运输毒品罪废止,因为废止这个罪名并不会为司法实践带来任何的障碍。
从刑法理论的角度分析,选择性罪名在刑罚的适用上,其犯罪构成与法定刑应当是同一的,但事实表明,运输毒品罪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的社会危害性存在明显的差异,将这几类行为适用同等的刑罚幅度,对于运输毒品的行为人来讲无疑是不公平的,无法真正实现罪刑均衡。
我国的《刑法》第61条明确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规定判处。按照现行的做法,受雇于他人运输毒品的,其恶性通常要比贩卖毒品的人轻,主观恶性小,只要有证据证明运输行为人是在替他人运输,所运输的不是运输人所有的毒品,而是另有其主,可以以运输毒品罪定罪,但是如果单纯地以单独正犯处理,则其从犯的地位无法认定,对之处罚上仍然较重。虽然可用部分犯罪共同说在运输的范围内认定运输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是,这样的处罚并不能使其刑事责任减轻,仍然无法实现对运输毒品行为人的适当定罪处罚。
笔者认为,即使我国《刑法》不规定运输毒品罪,也可以实现对运输毒品行为的充分评价,区分不同的情况认定为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就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还可以实现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这在前文已经进行了一定的论证。
另外,从司法实践看,被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多数都是无法证明行为人具有贩卖毒品的故意,而其又在运动过程中携带大量毒品的情形,根据《刑法》的设置规则,在无法证明行为人的行为属于贩卖毒品罪时,其最优先的堵截罪名应当是非法持有毒品罪,而非运输毒品罪,如果认定为运输毒品罪,可以判处与贩卖毒品罪相同的罪名,那么刑法设置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堵截规定又有何意义呢?可见,废止运输毒品罪是完全必要的,亦是可行的,正如主张废止论者指出的那样,没有运输毒品罪,我们仍然可以实现对嫌疑人、被告人的适当处理。
第一,如果行为人是为了自己贩卖毒品而进行运输的,仅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即可。如行为人甲住在沈阳,有一个北京的买主通过电话与甲联系,希望购买其海洛因50克,交易地点选择在北京,甲于是开自己的私家车或者坐火车携带毒品到北京去交易,在交易时被抓获,那么对甲的行为单纯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即可,而不需要再认定为贩卖、运输毒品罪,其理由是,在该案中,甲的运输毒品行为不具有独立的价值,仅是贩卖毒品行为的必然行为,正如贩卖过程中,持有毒品行为不需要单独考虑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是同样性质的。
第二,行为人明知他人贩卖毒品,而接受其委托进行运输的,则按照贩卖毒品罪的帮助犯进行处理即可。例如,行为人甲明知乙从事毒品贩卖,一次,乙让甲为其从沈阳带一批货到北京,甲明知该货物可能是毒品,但鉴于乙支付的运费比较高,于是用自己的私家车将毒品送到北京,那么,对甲按照贩卖毒品罪的共犯(帮助犯)论处即可,因为这样不但可以保证对甲的严厉处理,也体现运输与贩卖行为之间的巨大差别,即帮助犯比照实行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样更能保证刑罚的适正性。
第三,行为人不知道毒品所有者让其运输毒品的目的,而其也有相应理由认为所有人可能是用于吸食的,而为其运输的,则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即可。如甲接受乙的委托,从沈阳将50克海洛因运到北京,按照甲的判断,乙是为了搬家,害怕毒品丢失才让其帮助运送的,那么甲的行为按照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即可,勿将其认定为法定刑畸高的运输毒品罪。
可见,废除运输毒品罪,不但具有理论上的支撑,而且具有实践上的依据。通过相关的刑法理论,完全可以实现对运输毒品行为的充分评价。
五、结语
在我国刑法中废止运输毒品罪,不但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刑法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如此的做法不但可以使刑法的适用与刑法基础理论更加协调,而且更能实现刑法罪刑均衡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 赵秉志.现代世界毒品犯罪及其防治[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108,115,137.
[2]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654-655.
[3] 于志刚.毒品犯罪及相关犯罪认定处理[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425.
[4] 姜 敏.祖国大陆与我国香港地区毒品犯罪比较[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7(2):92.
[5] 黄太云.《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一)[J].人民检察,2011(6):7.
[6] 郑蜀饶.毒品犯罪的法律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78-79.
[7] 赵秉志,肖中华.论运输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之立法旨趣与隐患[J].法学,2000(2):34.
[8] 温黎红,李铁威.对动态持有毒品行为之定性[J].人民检察,2008(14):64.
[9] 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