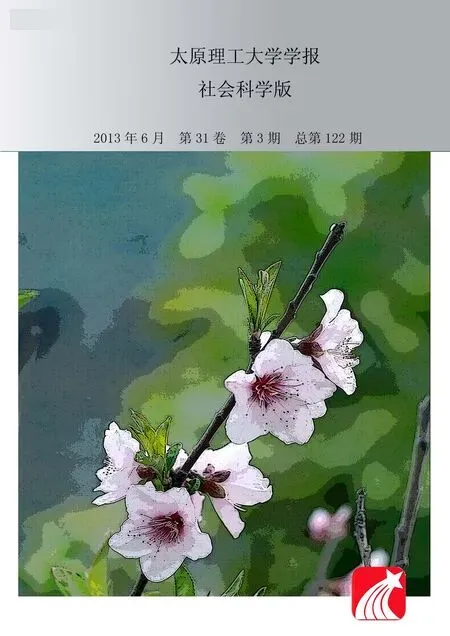《白雨斋词话》秦观“近开美成”说质疑
2013-02-14许净瞳
许净瞳
(陕西理工学院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23000)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曰:“秦少游自是作手,近开美成,导其先路。”[1]之后又曰:“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1]此二论自提出后,深入人心。研究者随其流而扬其波,如陈匪石《宋词举》、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王辉斌《论周邦彦与北宋词坛》等,这些研究者指出秦、周二人并非同辈,从而得出周邦彦吸收了苏轼、秦少游等人创作技巧的结论。王兆鹏在《唐宋词论稿》中,根据词人的生卒年将苏轼及其门人与周邦彦分做一个代群,并从社交群体着眼,将他们划分为苏门词人群与大晟词人群,认为周邦彦是在“苏轼及黄、秦、晁、陈等苏门中坚词人”去世后,供职大晟府时才开始大放光彩的。因而,王氏在撰写《中国文学史》宋代部分第六章第三节时,总结道:秦观“语言清丽淡雅,周邦彦得其丽,而发展为精雕细琢的典雅富丽。”[2]这不能不令人感叹陈廷焯的观点影响之深远。那么,究竟秦观有没有可能在创作上影响周邦彦呢?
一、从交游考证此说之误
王兆鹏在《唐宋词论稿》中,以时间发展为序,将宋代词人分为六代词人群体。虽然秦观和周邦彦被归为一个代群,但对二人的关系论述不详,据徐培均《秦少游年谱长编》和罗忼烈笺注《清真集笺注》后附录年谱可知,秦观生于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十二月,长周邦彦七岁。至和二年(1055)始入小学,时秦父元化公正从胡瑗游于太学。胡瑗精通音乐,这可能对秦观作词熟于音律有一定影响。熙宁七年(1074)十月苏轼移知密州,此时才通过孙莘老知闻秦观,二人尚未见面。而熙宁四年(1071)苏轼通判杭州时,已与周邦彦叔父周邠交游。即苏、周交往在苏、秦相知闻之前,换句话说,在熙宁七年以前,周邦彦不可能通过其叔父知晓秦观的创作情况。且此时秦观的创作尚未达到天下知闻的程度,因此周邦彦与其叔父似乎也不太可能由其他途径,如青楼歌女口中知道秦观词,从而学习他的词创作技巧。元丰元年(1078)三十岁的秦观初次入京应举,秋试不售,退居高邮。次年(1079)二十四岁的周邦彦入京为太学生,二人不曾见面。周邦彦二十四岁入都前,作词多为中调与小令[3],而秦观作词基本上以小令为主[4]。元丰五年(1082)春秦观又入京应举,落第而归。其间生活“滥浪”,宋代《王直方诗话》便曾记载其冶游之作[5]。周邦彦喜好作词听曲,兼之此时身为太学生有机会出入青楼,也当作了一些艳词。是时,汴京一片繁盛之态,歌台舞榭,竞睹新声,世人沉醉于宴游之间,词人们不断创作应歌之词。周、秦二人当有机会于勾栏瓦肆、市井之间相识,然二人文集中不见唱和应答之作,史书、杂记亦未见二人交游之记录。神宗元丰八年(1085)秦观再次入京应举,三月孙莘老权知贡举,五月秦观登焦蹈榜进士,除定海主簿,岁暮赴蔡州教授任。是年周邦彦尚在京任太学正,二人仍无交往之迹。哲宗元祐元年(1086)正月秦观到任。十一月二十九日诏试学士院,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并授馆职,而秦观未与。元祐二年(1087)春周邦彦回杭扫墓,三月赴庐州教授任。元祐三年(1088)九月秦观入京应贤良方正不售,引疾归蔡州。元祐五年(1090)五月秦观离蔡入京,六月为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绍圣元年(1094)夏四月秦观离京。闰四月丙戌又因事落馆阁校勘,贬监处州酒税,随后降授左宣议郎,依旧监处州酒税。从元祐二年直到绍圣三年(1087-1096)这十年间,周邦彦一直在庐州、荆州和溧水辗转任职,未曾回京。绍圣三年(1096)周邦彦自溧水还京为国子主簿,哲宗召对,使诵前作《汴都赋》,除秘书省正字。同年秦削秩徙移郴州。自绍圣三年到元符三年(1100)周邦彦一直在京任职,而秦观贬官在外直到死亡也未回京,两人未见交往通问之迹。
自上述时间、任职比对可知,秦、周二人入仕之前完全没有来往,即使周邦彦与秦观有两次机会同处京师一段时间,以他们相近的喜好,居然全无交往,不能不说是件十分奇怪的事。仔细翻检张耒、黄庭坚的交游情况可知,周邦彦与此二人亦无联系。从接受学的角度来看,周邦彦的词创作不可能受到秦观的影响。因此陈匪石先生说柳永、苏轼、秦观、贺铸等人皆“为周所取则”[6],以及吴熊和先生认为秦、贺二人影响了周邦彦的创作一说有待推敲[7]。
从上文考述亦可知,周邦彦完全有机会与秦观或是苏轼交往,但最终却独立于苏、秦等人的交际圈之外。这可能与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仕途倾向有关。沈家庄认为周邦彦政治上属于新党,拥护新法[8],沈松勤也持此观点[9]。也有学者认为周邦彦不明确属于哪个阵营,例如叶嘉莹认为他写《汴都赋》只是为了歌颂赞美。还有学者认为他只是纯粹从国计民生的角度去论述新法,完全没有党派之争的意识,孙虹《清真集校注·清真事迹新证》即持此观点。不论他是否加入新党一派,总之没有人把周邦彦归入旧党。这意味着周邦彦与旧党之间界限分明并且态度明确,因此即使他的叔叔与苏轼一门交好,苏轼对于好友那个才华横溢的侄子却没留下只字片语的赞美提携。而周邦彦似乎也并不看重苏轼的评价。当然,周邦彦也自有其可傲气的才华,他词的特色与地位“顾曲”名堂,正是对自己音律知识的自信与自负[9]。据史料记载和秦、周二人存词可见,周氏能自度曲,所创词调颇多,而秦观虽识音律却填词不多。至于文采斐然的苏轼所作之词,在当时得到的评价并不高,相信周邦彦并未将这几人当做模仿学习的对象,因而也不可能间接接受秦观的影响。
二、从词学分析此说之不可信
那么,陈廷焯是从何得出秦观开美成之先的结论的呢?我们或许当由周邦彦的集大成的成就来看。他不仅艺术上吸收了前人,以及同时代词人的技巧,而且在音律上吸收他们的长处,充分利用自己熟于音律的优势,不断开拓词创作的领域,他所做的尝试均为南宋婉约派词人们模仿吸收。研究者大都认同这一观点。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言“两宋词各有盛衰,北宋盛于文士,而衰于乐工;南宋盛于乐工,而衰于文士”[10]。从创作上言,周邦彦既有文士之感发与思力,又兼有乐工之精于音律,具二者之长,无二者之短,的确是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然而他兼有众人之长的艺术才能和艺术创作,并不等于秦观就影响了他的词创作,因此陈廷焯这一说法是有问题的。
研究者将二者定位于影响与被影响者的关系究竟是着眼于何处呢?笔者概括了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秦、周二人都娴于音律,他们的词作均是曼声合律能够应歌的作品,很受世人尤其是秦楼楚馆歌者的欢迎。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说秦观“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11]。这一点,从后世流传的笔记小说故事如“山抹微云女婿”亦可以略窥一二,而周邦彦的词和婉动听,填词时于四声安排独具匠心,十分注重平上去入的搭配,连清浊轻重也十分讲究,吴熊和先生便以此点作为周邦彦承袭秦观的论据。
第二,秦观学习花间、柳永,并隐括前人清词丽句入词,周邦彦亦学前人并使用这些技巧,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秦少游词得《花间》《尊前》遗韵,却能自出清新。”[12]沈义父《乐府指迷》认为清真最懂音律且词作中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遣词造句往往得自唐宋诸贤诗句。关于秦、周二人化用前人成句和使事用典,前人已多有成说不再赘述。他们二人都创作了不少应歌之作,很多都是为青楼楚馆的歌儿舞女所作,宴间尊前之词自然不会有多高雅,男欢女爱题材的泛滥使用既是当时所有北宋词人学习花间词的结果,也是他们创作这一类型词的必然,欧阳修亦不乏此类词作,因此这也不成为秦观影响周邦彦的证据。柳永爱以俗字俗语入词,周邦彦的《归去难》(佳人约未知)也使用了俗语,秦观同样爱使用俗语,他年轻时所作的《品令》便使用了高邮的方言俗语[5]。正是他们同样的师法前人的做法,使得后人误以为秦观引导了周邦彦。不过,论者常说周邦彦博学多文。与常以典故、前人成句,以及精致的篇章结构来将词文人化、雅化的周邦彦相比,秦观纯粹以感伤幽怨之情写词的确有些单薄。因而,当代著名词人兼词论家李清照认为秦观用典不多,缺少故实,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13]。
第三,秦观在“传统艳词题材中,融注了词人自我独特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2],如《满庭芳》(山抹微云)亦即在写歌妓的同时表达了自己的孤独悲伤;周邦彦也在创作中将恋情词自我化、雅化,他所写的失恋很多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周济《宋四家词选》说:秦观“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10]周邦彦也在词中融入身世飘零的哀伤和仕途坎坷的痛苦,使得他的词具有常读常新的特色,如:《过秦楼》(水浴清蟾)借着艳情写痛苦,错乱时空,杂糅现实与想象,在人物景色交错变换后,使之相互照应而使全篇浑融,满纸既是思妇泪又是词人泪,由思妇的痛苦联想到词人羁旅行役之苦,恋人的年华老去映衬了自己的年华不再而功业未就。两人对于传统艳情词创作相似地艺术处理技巧,也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第四,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都是婉约派的代表作家,周邦彦的主体词风虽然富艳精工,但脍炙人口的《玉楼春》(大堤花艳惊郎目)与秦观的《玉楼春》(参差帘影晨光动)词风便极为相近。其实婉约派作家要表达某一种情感类型时,必然会使用相同词牌,如:柳永写《少年游》(长安古道马迟迟)和周邦彦的《少年游》(并刀如水)都是流丽谐婉的词风,黄庭坚也有此类词风的作品,我们不能就此论说周邦彦曾向黄庭坚偷师,因此某些词作风格的相近相似并不能证明两位作家之间必然有师法关系。
实际上,秦、周二人虽同为婉约派词人,但在总体倾向上仍有不同,秦观的创作倾向于小令,周邦彦则倾向于慢词长调。周邦彦喜欢在作词时讲求章法,精心结撰全篇,同时在细致铺陈地叙写中,把玩咀嚼自己的哀乐,缓慢地由字里行间,丝丝缕缕地流淌出来。相较而言,秦观更关注仕途,也更容易被仕途变迁所影响。他在短小篇章中将一腔哀怨愁苦尽情宣泄出来,他一直在痛苦与欢乐中沉浮,淮海词也显得纤丽脆弱,他的词是感性的,故冯煦《宋六十一家词序例》称赞秦少游的词作写出的是词人的词心。而周邦彦虽然在后期攀附蔡京以求仕途的荣华,但他在看待仕途的穷达起伏上,较秦观略为旷达。《宋史·文苑传》称周氏:“居五岁不迁,益尽力于乐府,”[14]这种心态可以从他流传的诗文词中读到,所以他无论外放或在京任职,都是有闲情制乐度曲创作慢词的。此外,秦观因为早卒[5],其创作时间相对于活到六十六岁的周邦彦而言显得短暂。秦观与哲宗同年谢世,相比度过徽宗朝的周邦彦,的确给人以秦观长周邦彦一辈的错觉,因此研究者误以为秦观的创作影响了周邦彦。
仔细考量北宋词坛的发展状况,周邦彦与秦观等人同处于一个创作时段,他们都顺应了一种文学发展的要求,努力改变它的原始状态,使之从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变为文人雅士展现高雅的新载体。周邦彦的创作兼有文人的思力和乐工的合律,因为他饱读诗书,又得天独厚地拥有音乐才华,所以他走得比秦观要远。周邦彦在同样吸取前人的艺术成就、文学营养的时候,比秦观等人更能体会词不同于诗的创作要求,苏轼、秦观他们当时尚在做以诗为词和以词抒情的尝试,但是我们并没有更多例子可以证明周邦彦受到了秦观词创作的影响,只能说二人的审音辨律、琢磨艺术技巧是在词创作中,对于词自身发展的要求做出了同样的回应。因此陈廷焯这一观点缺乏根据,是需要重新审视的。
参考文献:
[1] 陈廷焯,屈兴国.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3:63,74.
[2] 王兆鹏.唐宋词史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5,24.
[3] 周邦彦,孙 虹,薛瑞生.清真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358.
[4] 秦 观,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56.
[5] 徐培均.秦少游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2:38-39,197.
[6] 陈匪石,钟振振.宋词举:外三种[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83.
[7]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13-217.
[8] 沈家庄.论清真词沉郁词风的形成与演变[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1):24-26.
[9] 沈松勤,黄之栋.词家之冠——周邦彦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18-19.
[10] 周 济.介存斋论词杂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
[11] 叶梦得.避暑录话:全宋笔记[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286.
[12] 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09.
[13] 李清照,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516.
[14] 脱 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23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