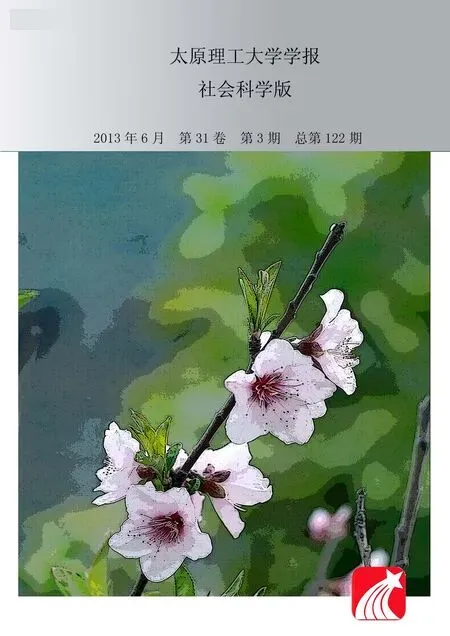论《儒林外史》中鲁编修“高智”低能的症结所在
2013-02-14薛莲
薛 莲
(太原科技大学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儒林外史》中的鲁编修,他高官得做,却盼不上肥美差事而虚度时日,被人认为是“俗气不过的人”;他培养的女儿写出了“礼真法老,花团锦簇”的八股文章,可偏偏不能进考场;他选的入赘女婿有科举资格,可就是厌学八股文章;他想再娶妾生个儿子光宗耀祖,可此路却走不通。他因为中了进士而走运、生气、身亡,这一被他认定的标准不仅害了他自己、害了女儿,又被女儿恶性循环地害着孙子。事实告诉人们,“中了去”不能成为人生的唯一价值标准,仅用这个标准会遇到种种解决不了的困难和问题,一味地墨守成规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最终必将自食其恶果。
一、解决不了“中了去”的标准与实际能力的矛盾
鲁编修虽然“中了去”身居编修之位,坚守儒家之正派操行,但却处处表现出官职与能力的矛盾与冲撞。
美差谋不上,家事理不好。他亲口告诉娄太保的孙子娄三、娄四公子从京城返乡的理由是:“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事。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白白坐在京里,赔钱度日。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再作道理。”[1]69这表明鲁编修不仅对从事的工作“美差谋不上”,连家里的事也没处理好。年近五十岁了还空名无实地在京城虚度光阴。这些能全怪翰林院、怪别人太会钻谋而自己不会或者不愿意去钻谋吗?内外之事都解决不好,只能说明鲁编修的能力太差了。
只知有八股,不识诗词赋。鲁编修也像周进之类的人一样,把科举看得高于一切,而把诗词歌赋等看做“杂览”。娄府公子拿出一首“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1]68的诗让鲁编修看,这是杨执中抄袭古人的诗,他根本看不懂,只是按“中了去”的标准高谈阔论指责说:“这样的人,盗虚声者多,有实学者少。我老实说:他若果有学问,为甚么不中了去?只做这两句诗,当得甚么?”[1]69-70两位公子听了从心底里认为他“是俗气不过的人”,后来鲁编修发表对两位公子结交的人及从事的活动的看法时,两位公子就更认为他俗气不过了。不少科举高中者当官后都抓紧补上因为参加科举考试落下的诗词歌赋这一科,而鲁编修则不同,虽身居编修之位、年将五十对诗词之类还处在懵懂之中。所以,他除却“中了去”还会有何能?
欣赏的枯思,思维的异样。鲁编修被邀请到娄府做客,他在书房里“见瓶、花、炉、几位置得宜,不觉怡悦”,对焚香使书房墙壁、板缝都喷出香气来“觉飘飘有凌云之思”。但他怡悦的不是瓶、花等的优美,而是位置的摆放。完全错位的欣赏角度使人们认为他只剩下驯服者的规矩意识,除此之外不理解他在赞叹什么。
矛盾的所为,滑稽的“选婿”。鲁编修在娄府见到前任南昌遽太守的孙子遽公孙,谈起了王惠投降清朝叛军宁王的问题,因为王惠是遽太守的接班人。鲁编修谈到“无兵无粮,因甚不降”,只是王惠带领数郡一起归降所以朝廷要悬赏捕拿。他又趁兴念了王惠曾经求卦得来的命运卦词《西江月》:
羡尔功名夏后,一枝高折鲜红。大江烟浪杳无踪,两日黄堂坐拥。
只道骅骝开道,原来天府夔龙。琴瑟琵琶路上逢,一盏醇醪心痛![1]52
他还逐句解释,似乎对诗词也懂一点,其实王惠投降出了名,连同王惠的判词也被传开了,谁都了解卦词的大意。娄府两位公子拿出“嘉兴蘧来旬先夫氏补辑”的《高青邱集诗话》缮本给鲁编修看,还夸赞遽公孙年少美才,鲁编修在叹赏了许久后问了蘧公孙的年龄和生辰,很快就托人来保媒。可疑的是,坚守“中了去”标准的鲁编修怎么疏忽了蘧公孙这个“如意女婿”是喜欢诗词杂览的人呢?蘧公孙是在王惠逃跑时得到《高青邱集诗话》缮本的,听爷爷说过“这本书多年藏之大内……天下并没有第二本……真乃天幸,须是收藏好了,不可轻易被人看见”[1]59,于是蘧公孙就萌发了以“天下孤本”扬名的想法。他套添上自己的名字印了几百本送人,从此“少年名士”就在浙西流传开了。此时鲁编修看上的是蘧公孙是蘧太守的孙子、曾做过太守的爷爷给孙子捐有监生名分、蘧公孙有孤本独握的资本、有少年美貌等,当“只做两句诗能当什么”这个原则摊到自己头上时,鲁编修竟然置之脑后了。更奇怪的是《高青邱集诗话》是被追查的反朝廷之作,收集本朝名人文集的卢信候就说过“高青邱是被了祸的”[5]242,身在朝廷的鲁编修岂能不知?鲁编修死守的“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1]76的硬道理此时怎么都无影无踪了?不知是作者有意讽刺,还是鲁编修一时过度兴奋甚或一时糊涂的决定,总之这个俗气人此刻就真的俗气起来了。
身居高位的鲁编修,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可怜的。年近五十了还没明白自己的一生,只是叹息没捞到美差,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中了去”的标准不能代表并衡量全部世事。他偏激到了极点,只能是八股科举的“专家”,根本不懂得科举的弊端和穷途,把自己圈在自以为是的自定标准中,根本认识不到“中了去”代表不了适应社会能力的自然提高。
二、解决不了“中了去”的理想与家庭承继的矛盾
首先是具备了考状元水平的女儿不能“中了去”。才貌双全的鲁小姐从小被父亲训练成了非凡的八股才女,而且被熏陶后的思想意识与父亲也极为相似,“父女两都是正派人,而且太正派了”[2]。父亲培养和训练女儿的方法就是:“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就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得滚瓜烂熟,”[1]76还教她写出了优美的八股文章。鲁编修的指导思想就是:“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1]76在父亲教诲下,女儿从来不正眼看诗词歌赋,只读“文章”。训练的结果是:十六岁的女儿,熟读背会了三千多篇科举中了的好文章,写作八股文达到了“理真法老,花团锦簇”的水平。对此卧评(清代乾隆年间刻本“卧闲草堂本评语”简称“卧评”)曰,“书中言举业者多矣,如匡超人、马纯上之操选事,卫体善、隋岑庵之正文风,以及高翰林之讲元魁秘诀:人人自以为握灵蛇之珠也,而不知举业真当行,只有一鲁小姐。”[3]152只可惜科举社会剥夺了女子上考场的权力,所以鲁编修常常叹息:假如女儿是儿子的话,几十个进士、状元都考中了。
其次是转寄赘婿“中了去”大失所望。女儿不能进考场考试,鲁编修就把女婿作为转承中进士的对象。在定女儿结婚日子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要蘧公孙入赘。他不甘心自己一生的心血白费,要把“中了去”的期望转寄到招赘的女婿身上。蘧公孙的爷爷蘧太守也不反对孙子招赘,因为在清代民谚有“入赘女婿不是人,倒栽杨柳不生根”的说法,但“士绅阶层不涉及受欺凌或更姓改宗等辱没祖先的事,两家都是平等的选择。他们不会因赘婿的身份使夫妻关系蒙上阴影”[4]。鲁小姐首先发现了蘧公孙不能完成“中了去”的目标:他对满书架的科举文章不在意。她让他写“身修而后家齐”的作文,蘧公孙付之一笑说:“我于此事不甚在行。……这样俗事,还不耐烦做”。对此黄评(清代咸丰年间刻本“黄富民评点《儒林外史》简称“黄评”)曰:“‘身修’想是中进士,‘家齐’想是小姐做夫人耳。”[3]142她多次找他谈举业,他根本不理会还说她俗气。现实击碎了鲁小姐的梦,积了一肚子的气和泪,她叹息说:“如此光景,岂不误我终身?”母亲劝她说,新姑爷是个人才,是你爹看上的少年名士。她说:“自古及今,几曾看见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个名士的。”[1]77对此齐评(清代同治年间刻本“齐省堂本评语”简称“齐评”)曰:“越是不中进士越要自称‘名士’二字何用?小姐要二者相兼,未免苛求太甚了。”[3]143母亲和养娘劝说:“两家鼎盛,就算姑爷不中进士,做官,难道这一生辈还少了你用的?”她回答说:“‘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依孩儿的意思,总是自挣的功名好,靠着祖、父,只算做不成器!”[1]77直到劝说女儿生儿子再教成状元、“封诰”是有盼望时,鲁小姐才不叹气了。鲁编修也考查蘧公孙,见蘧公孙勉强成篇的都是些诗词之类,不是正经文字,很生气,可女婿是自己选的,只能独自生闷气。父女俩这时才形成了同一认识:靠蘧公孙考中进士没有一点指望了,转寄“中了去”的希望全落空了。这对只认唯一标准的鲁编修来说,真是当头一棒,致命一击。卧评总评曰:“精于举业之才女古未之有也。夫一女子而精于举业,此则女子之俗可知。该作者欲极力写编修之俗,却不肯用一正笔,处处用反笔、侧笔,以形击之。写小姐之俗者乃所以写编修之俗也。”[3]152
出现如此重大失误,缘于鲁编修“中了去”的标准是理想的不是现实的,一厢情愿地用这个标准衡量一切,当然就会出现问题和矛盾了:一是鲁、蘧两家培养人才的出发点有很大区别。鲁家要“中了去”,做官显身扬名;蘧太守不求做官,认为当官是作孽的事,宦海凶险,儿子蘧景玉早逝是对自己做官的报应。因此,“进士”与“少年名士”二者之间产生无法逾越的鸿沟是必然的。二是鲁、蘧两家培养人才的标准有很大不同。鲁家要“中了去”;蘧家是“膝下承欢”。蘧太守曾对娄府两公子说过:“我只得这一个孙子,自小娇养惯了。我每常见这些教书的先生,也不见有甚么学问,一味妆模作样,动不动就是打骂。……老夫姑息的紧,所以不曾着他去从时下先生。……自你表兄去后,我心里更加怜惜他,已替他捐了个监生,举业也不曾十分讲究。近来我在林下,倒常教他做几首诗、吟咏性情,要他知道乐天知命的道理,在我膝下承欢便了。”[1]60看来要指望蘧公孙把举业作文与诗词杂览统一是万难做到的。三是鲁、蘧两家在培养人才选择道路上有很大差异。鲁家“中了去”是唯一之路,蘧家对举业不在乎,虽为蘧公孙捐了个监生,但不指望孙子成事。蘧公孙刻孤本送给人几百本,“少年名士”传扬,蘧太守知道了也不干涉,还乘机教他写诗词、写斗方跟名士赠答交友。因此这就必然产生考中“进士”与捐来“监生”的严重冲撞。周进也是捐来“监生”后步步高进的,但二者不同的是周进用了一生的心血去钻研八股,是不沾“杂览”边的。仅这三方面的矛盾,就足以证明鲁编修用自定的标准对“门当户对,才貌相配”衡量的严重不足,对解决家庭矛盾的无能与无奈。
三、解决不了“中了去”的固守与自己心胸的矛盾
无情的现实摆在眼前,失去希望的鲁编修,把生闷气变成唯一的办法。
生气得了重病。原因很清楚,一是蘧公孙不肯做举业,二是女婿是自己亲自选的,看走了眼,有难言之隐。实在是穷途无路了,他想出了一个拯救的办法,就是自己再娶一个“如君”(妾)养儿子,教读书、长大中进士。五十岁了再娶妾生儿子中进士,这是多么渺茫的希望。夫人知道后劝他,他生了重气跌了一跤,造成了半身麻木、嘴眼歪斜的后果。娄府公子来看鲁编修,见鲁小姐泪眼汪汪只叹气,大夫说这病是忧、怒和抑郁所致,顺气祛痰才能渐渐好转。但是病中的鲁编修仍然固守标准不变,对娄府公子请宾客游莺脰湖说“令表叔在家,只该闭户做些举业,以继家声,怎么只管结交这样一班人?如此招摇豪横,恐怕亦非所宜”[1]88。其实,这是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娄府公子,两位公子也根本没改变对鲁编修的看法,说不理解鲁编修怎么就“俗到这个地位”![1]88
病中乐极生悲。还未痊愈的鲁编修突然接到朝命:升任侍读(与皇帝一起读书)。全家人欢天喜地,摆酒席庆贺,不料鲁编修痰病大发不省人事了。痰病大发不仅仅是因为高兴,更是因为他深深积郁的哀愁总暴发:五十岁了后继无人的忧心、无人中进士续接书香门第的忧愤、目标和理想不能实现的忧虑。老病新愁的集中暴发,使这位科举制度的誓死捍卫者在愁苦与欢喜交加中瞬间离世。这位带着人生最大遗憾辞别人世的鲁编修,长眠地下也不会瞑目的。
鲁小姐转移了希望。她毕竟没有父亲对“中了去”的深切体验,但教子成状元“封诰”的盼头是她希望的又一次转寄。遽公孙只好每晚陪着鲁小姐教子到三、四更天,有时候儿子背不熟,鲁小姐就监督念到天亮,打发遽公孙先去睡觉。由于鲁小姐的专注与少情趣,使丫头钻了遽公孙喜欢献殷勤的空子,知道了朝廷追捕的王惠与遽公孙有过来往的事儿,差点牵扯出遽公孙的一场“钦案”来,最后是马二倾囊相助才平息了事端,避免了鲁家一场大灾难。蘧公孙也看到了表叔娄府两位公子半世豪举落得一场扫兴,把当名士的事也看淡了。
鲁小姐对丈夫期望值很高,想让他进学、升高官、出人头地,实现父亲和自己的唯一期望,所以当事与愿违时,她痛苦、烦恼、怨恨、流泪、无奈,这就决定了鲁小姐一辈子都不会幸福的命运。她所转寄给儿子的希望能否变成现实,儿子能否承载起三代人“中了去”的重负,还是个大问号。就算儿子将来不辜负她的期望,那每天死读八股、不与社会接触、不提高能力,就是“中了去”也会是鲁编修的翻版。因此鲁编修毒害了女儿,女儿在继承父亲的意志后不知又会带来怎样的恶果。蘧公孙出生于官宦家庭,祖父姑息他给他捐了监生,还常教他作几首诗,他偶得《高青邱集诗话》后成了浙西少年名士,与斗方名士结交起来,还骗过了鲁编修。鲁编修招他为倒插门女婿寄予厚望,当他的才学暴露后,气坏了鲁小姐、气死了鲁编修。作者有力地抨击了在科举社会氛围下欺世盗名、混世名士造成的自欺欺人的现象。鲁编修在失望中痛心、难言、患病,不久之后就怀着遗憾与无望离去,更是对他固守科举制度、把“中了去”当做唯一标准和出路的深刻讽刺。
参考文献:
[1] (清)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
[2] 李汉秋,张国风,周月亮.《儒林外史》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355.
[3] 李汉秋.《儒林外史》彙校彙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 顾鸣塘.《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