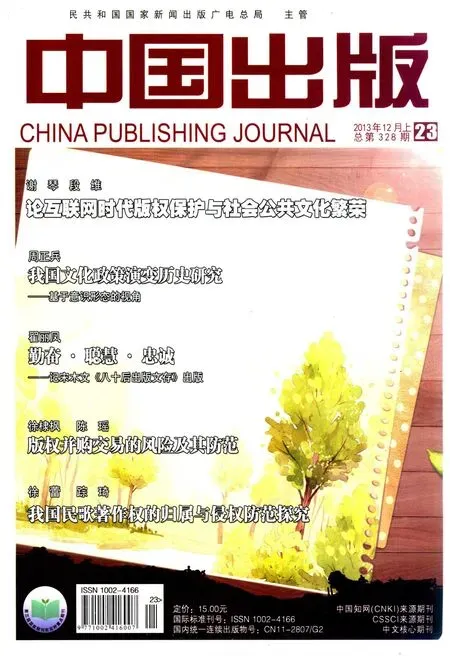论孙幼军的童话观
2013-01-30孙建江
文/孙建江
孙幼军常说自己不擅长理论思考,曾不止一次借同学之口说自己身上“连一个理论细胞都没有”。[1]如果说,理论思考仅仅是指理论家的学理型研究的话,那孙幼军的确不以此见长。但理论思考显然不限于此。在众多理论思考的方式和路径中,作家创作经验型的思考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重要的存在。尤其是重要作家的创作思考。童话作家孙幼军的创作思考就属这一类。
孙幼军童话思考最大的特质是实践性。困惑于实践,感悟于实践,启发于实践,验证于实践,发展于实践,完善于实践。笔者认为,这种实践性,正是作家创作经验型理论思考的价值所在。
一、幼儿思维特征
孙幼军的思考涉及诸多方面内容。其中最为重要,也是孙幼军自己反复强调的,我以为,是其提出的“幼儿思维特征”问题。也可以说,“幼儿思维特征”是孙幼军童话观的核心。
关于童话的“幼儿思维特征”,孙幼军有明确的论述。
“我的认识是,童话是具有幼儿思维特征的幻想故事。”[2]“我逐步形成的童话概念比较简单,那就是,具有幼儿思维特征的故事。”[3]“我认为,童话的幻想应该是,实际上也是,具有‘小孩子特征’的。”“大概由于听故事的多数是较小的孩子,是幼儿,这种‘小孩子特征’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幼儿思维特征’。”“我认为一切优秀的童话都具有幼儿思维特征,并不仅限于幼儿童话。”[4]“无论童话还处于民间口头流传的阶段抑或进入作家创作的阶段之后,童话作品,尤其是优秀的童话作品,都具有鲜明的幼儿思维特征。幼儿童话如此,一些给较大孩子阅读的童话也如此。”[5]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孙幼军对“幼儿思维特征”说的界定。孙幼军认为:其一,“童话是具有幼儿思维特征的幻想故事”;其二,“优秀的童话都具有幼儿思维特征。幼儿童话如此,一些给较大孩子阅读的童话也如此”。换句话说,“幼儿思维特征”,并非仅仅对应于幼儿童话,而是所有童话的。因此,实际上孙幼军的“幼儿思维特征”,一定程度上也涵纳了“较大孩子”的思维特征。
孙幼军所以特别强调“幼儿”,而不是“儿童”或“少年”,是因为在孙幼军看来,“幼儿”思维特征,最能应对童话的幻想,或者说“幼儿”的思维特征最具童年性、最契合童话特质。这是一种极致的强调。
孙幼军如此看重“幼儿思维特征”,这与他的讲故事“实践性”密不可分。童话作家或多或少都会为儿童讲过故事,但像孙幼军这样长时间(持续30年以上)为儿童讲故事的人还真不多。孙幼军是家中长子,下面有四个弟妹,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给弟妹讲故事。他在《和朋友们交流一下童话创作》[6]一文中说:“大概由于从小喜欢弟弟妹妹,我后来离家求学,无论到了哪里,身边总有一群小孩子围着,我仍是用讲故事来哄他们玩儿。等到我有了自己的孩子,讲故事更成了我无法推却的义务。女儿和儿子相差八岁,天天要听故事,使我这项‘工作’持续了很长时间。”孙幼军讲述的故事大约有三类。一类是从姥姥(孙幼军姥姥是个“故事篓子”)、父亲(孙幼军父亲曾留学日本,懂日、俄等三种外语)那里听来的民间故事和外国故事的转述;一类是自己看过的故事的现场发挥和复述;再一类是自己的即兴创作。这可能是孙幼军与我们很多童话作家很不一样的地方。
也正是因为这一讲故事实践,使得孙幼军在没有成为童话作家之前就知道孩子最需要什么,最喜欢什么,什么样的故事最能吸引住孩子。换句话说,孙幼军“幼儿思维特征”的提出,不是即兴的、随意的、外在的、硬性的,而是在长时期身体力行的讲故事实践中自然形成的。在他那里,写给孩子看的童话本来就应该是这样。这是一种与孩子产生心灵共鸣后的自然表达。“童话作家为了适应这一群独特的‘读者’(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不过是‘听众’),往往采用这些‘读者’的认识、理解,摹仿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进行创作。于是乎,猫也说话,狗也说话,树也说话,花儿也说话。没有生命,只具人和动物形体的玩具说话,甚至既无生命也不具生物形体特征的东西也会说话乃至行动。”[7]童话创作如果不与“幼儿思维特征”对应起来,那只能是与孩子无关的成人们的自娱自乐。
“我童话里那些‘幻想’,通常情况下并非现实生活在我头脑中产生的‘折射’,只不过是我模拟小娃娃们的思维方式编造出的情节。”[8]“模拟小娃娃们的思维方式”是孙幼军童话创作的“前提”。显然,也是他童话创作的根本“立足点”。可以说,在孙幼军看来,没有幼儿思维方式,童话也就不复存在了。
孙幼军常列举两个例子来强调成人思维与幼儿思维的不同。例子一:由于房子拥挤,书没地方放,大人们盼着有几间“广厦”,可女儿却爱在三屉桌上搭个床单,抱着布娃娃钻进“小房子”玩。你说,如果写童话,是写“广厦”,还是写“小房子”?例子二:唐山大地震期间,大家不得不从“窗明几净”的家里搬到大操场上。每逢下大雨,操场成了一片汪洋。大人们苦恼不堪,孩子们却开心得不得了。老是撩开塑料布,美滋滋往外看,把“小房子”想象成大海里的一条乌篷船了。你说,如果写童话,是写“窗明几净”,还是写“乌篷船”?成人与幼儿思维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往往是带有功利性的思考,而后者则往往是非功利的思考。
理论家或许不一定会留意这两个身边的故事,但童话作家孙幼军就不同了。首先,自己是写故事的,生活中的任何故事他都会留意,何况这两个故事本身就很有意思;其次,这两个故事如果从不同的思维——成人思维和幼儿思维——方式出发,完全可以发展成两种不同结果。而一个为小读者写故事的人,他是不可能不特别注意这一关键节点的。这也就是孙幼军让人佩服的地方。他的思考落在了最该着力的地方,落在了故事的生成方式及其走向上。
“幼儿思维特征”一说,是孙幼军为孩子讲故事写故事的长期创作实践中自然形成的看法和观点,是孙幼军作为一个专为儿童写作的童话作家听从内心召唤的必然结果。不过,“幼儿思维特征”的提出,与当时的童话理论氛围可谓相去甚远。据孙幼军日记披露,1982年孙幼军应邀赴北师大给儿童文学教师进修班学员做关于童话创作的报告,报告会上他首次提出了童话的“幼儿思维特征”一说。但此说并没有获得认可,当时北师大一位童话理论老师对孙幼军说:“你谈的是你自己的童话。”言下之意,真正的童话创作完全不是孙幼军说的那回事儿。[9]
的确,在当时,清规戒律很多,很多人的思维定势中还是既有的童话界定。可问题是,一些既有的童话界定一旦深入探析,往往破绽百出无从解释。
在《探索的得失》[10]一文中,孙幼军对“两位著名的童话作家”强调的“童话的逻辑性”,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否定态度。作者所说的“两位著名的童话作家”即贺宜和洪汛涛。其实,这两位童话作家,真正提出“童话的逻辑性”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是贺宜。贺宜在《简论童话》[11]中说:“一只好客的兔子在招待客人的时候,也并不请人家大吃‘红烧牛肉’和‘鱼汤’,因为它一向是素食的。”“这说明了两点道理。一是童话尽管容许幻想,但是任何幻想都只能在生活的基础上产生;二是幻想固然很‘自由’,但是它仍得根据童话的逻辑。”其实,贺宜的这个兔子不食荤的“童话的逻辑性”观点,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即已形成。贺宜在《童话的逻辑性和象征性》[12]一文中说:“当一只兔子在童话世界里屠狮宰虎,准备以丰盛的筵席来款待它的朋友的时候,任何一个小读者都会惊疑不止,甚至要认为作者不是在给他们讲故事,而是在哄骗他们。如果一个故事产生了这样不愉快的效果,这不能归咎于童话的幻想,而只能归咎于作者不尊重童话的逻辑性,破坏了生活的规律和自然的规律。”孙幼军认为,他们的“童话逻辑”不符合童话的创作实情。事实上,不少经典童话完全没有遵循这个所谓的“童话逻辑”。他们的“理论也并非研究了古今中外的童话作品而概括出的较为科学的规律,不过是从自己的创作归纳出来的经不起推敲的结论”。孙幼军进而指出,更重要的是,“在那套理论里,一条最厉害的,我觉得是彻底否定童话中的幼儿思维”,“照我看,‘小孩子逻辑’是否定不得的。那恰恰是童话中最可宝贵的东西。我觉得,世界上最优秀的童话,都具有这种东西,有些并非童话作品,但是由于具有近乎幼儿的想象,也得到孩子的青睐。……我想,就因为这太像弟弟们的‘胡思乱想’,就是说,具有幼儿思维的特征。在童话创作上,我总觉得‘小孩子逻辑’应该能够成立,不可以随便‘规范’掉,反而应该受到重视”。[13]显然,这是一位坚持独立思考同时又拥有丰富创作实践经验的童话写作者的理论思考和发现。
然而,毕竟还存在着高于幼儿的少年阅读童话的问题。那么,孙幼军幼儿思维观如何应对非幼儿思维类作品呢?
孙幼军是这样解释的:“我的感觉是,童话一旦面向少年读者,就会在不知觉间改变性质,成为幻想小说。……就我个人的感受说,给低幼年龄段的孩子写,容易写成童话;给少年写,容易变成幻想小说。但我并不认为,事情一定就是这样。”[14]
孙幼军的这个写作经验或许不一定有普适性,但说实话,却巧妙地解决了他所主张的“一切优秀的童话都具有幼儿思维特征”说法。因为,在他看来,给幼儿写“容易写成童话”;给少年读者写“容易写成幻想小说”。这样一来,“童话”与“幼儿思维特征”的关联度就更加紧密了。
孙幼军关于童话创作“幼儿思维特征”说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我以为,其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实意义。拨乱反正,即使不被人理解,也要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力促创作者们思考童话写作最该注重的是什么。第二,本原意义。强调幼儿思维特征,其实质是强调儿童本位的写作。童话是写给儿童看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要回到本原,回到真正为儿童而写作。唯有这样,才能真正赢得读者。第三,理论本身意义。这是典型的来自创作实践的感悟和阐释。创作经验型思考是童话理论不断充实丰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孙幼军“幼儿思维特征”说有什么局限的话,笔者认为恐怕恰恰也出在它的矫枉过正,出在它的“幼儿”之于“整个童话”的涵盖面上吧。
二、大教育观
对于儿童文学教育性的认识,孙幼军有一个从困惑到逐渐清晰的思考过程。
20 世纪60年代初,孙幼军将平生创作的第一部长篇童话《小布头奇遇记》投给少年儿童出版社,未被采用,出版社在退稿信中云,这部作品“主题思想不突出”,“小布头这个主角只是作为一个反映社会的联系物,他的思想和行动,我们也感到缺乏鲜明的教育作用”。对此,孙幼军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小布头在我心目中只能是个幼儿形象,要他的‘思想行动’生出‘鲜明的教育作用’却是我无法做到,也不想做的。所以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处理这部稿子。”[15]
在《〈孙幼军童话全集〉自序》[16]中,孙幼军援引金燕玉《中国童话史》所述:“在童话理论领域,从50年代末期起,出现了一种极‘左’理论,并很快地取得主宰地位。持这种理论的人提出庸俗社会学的观点:童话要更直接、更迅速、更深刻、更完满地反映时代精神,表现重大主题。”这是当时童话创作的大环境。孙幼军说:“我面对对童话创作的这种政治要求,同时又面对孩子的审美要求,时时感到其中的矛盾。我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求发展,一方面照顾到‘时代精神’和‘重大题材’,一方面想着孩子们,竭力使我的童话写得‘好玩’些。这种情况持续得很久,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一段时间。”毋宁说,这是一位想有所作为、想真正为儿童而写的作者在时代潮流中苦苦寻觅方向的心灵写照。“我是给自己的孩子讲过一些仅仅是‘好玩儿’‘真逗’的故事的。但一进入创作过程,便觉这些东西无法称得上是‘教育儿童的文学’,于是全部抛开,一心去寻找‘教育’了。时间一长,不免产生疑问:何以成人茶余饭后可以捧上一本《隋唐演义》或《福尔摩斯探案》去消遣,而孩子便无权看一篇只使他感到快乐而无需回答‘你受到了什么教育’的童话?这样想,也就这样说出来了”。[17]所幸,孙幼军不仅这样说出来了,还这样写出来了。这就是进入20 世纪80年代后孙幼军创作的《小狗的小房子》《怪老头儿》等作品。关于《小狗的小房子》,孙幼军说:“和以往写童话不同,这一篇没有一点儿‘主题先行’的情况。……动笔的时候我有些犹豫,不知道人家看了这样的东西会说什么。两年以后,我在一篇小文里回忆当时的心情说:我写了二十几篇童话,多数都被认为‘有教育意义’,大约来那么一篇没有的,也不至于构成什么‘倾向性’的问题。这是在给自己壮胆儿,看得出我当时的不安。”果然,作品发表后遭到指责批评:作家究竟想告诉孩子什么?但这次的整体大环境已完全不同了。除了有评论家力挺,作品还荣获《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影响甚大的《儿童文学选刊》也给予了转载。尤其让作者高兴的是,作品受到了小读者们的真心喜欢。这更坚定了孙幼军强调“真正为儿童而写”的决心。[18]
孙幼军很清楚儿童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孩子纠缠着要听故事,那光景大抵也如纠缠着要吃巧克力,要买玩具,当家长的对此是心领神会的。虽说是下意识的,却真正承认了文学社会功能之一的审美作用。于是讲起来也就设法适应孩子的要求,适合他的趣味,使他得到快乐,得到美的享受。”[19]孙幼军这里强调“审美作用”是文学的社会功能之一,强调“趣味”“快乐”“美的享受”,显然是在呼吁创作者摈弃狭隘的儿童文学教育观。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指出,不宜把对孩子的教育理解得过于狭隘。当下的童话说教味足了些,翻来覆去老一套。“如果考虑到文学作品(尤其是童话)的功能,考虑到低幼儿童的特点,那恐怕还不仅仅是‘不够’,怕是还‘不妥’。”[20]
基于此,孙幼军提出了自己的大教育观。他认为:想象力、幽默感、美感、同情与爱等同样具有“教育意义”。[21]
三、童话文体及其他
孙幼军虽然也创作散文和小说,但童话创作无疑是他一生的最爱。他在童话创作上倾注的精力和心血无疑也是最多的。长时期搞童话写作,使得他对童话这一特殊的文体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
孙幼军认为:“童话是具有幼儿思维特征的幻想故事。”直截了当,言简意赅。这,笔者前面已引述过。
除了正面论述什么是童话,孙幼军还常常从童话与相近文体彼此的关系来阐释辨析什么是童话什么不是童话。
1981年,孙幼军尝试创作了一篇《蓝色的舌头》。写完之后,自己也觉得怎么看怎么不像童话。“我以往童话里追求的那种‘孩子的眼睛和心灵’没有了,故事完全是以我本人(一个成人)的幻想作为基础。这样,它‘不像童话’是必然的。到这时,童话真的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折射’了。我认为,这话讲的是幻想小说。”此后,作者创作幻想小说的比重明显加重。“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我觉得创作的路子从此变得开阔,在题材选择上更自由,有点儿‘解放’的感觉(写我心目中那种具有天真、童稚美的童话实在很难很难!);另一方面,也由于我扩大了读者对象的层面,开始较多地关注少年。我的感觉是,童话一旦面向少年读者,就会在不知觉间改变性质,成为幻想小说。”孙幼军认为,囿于时代的局限,很多过去笼统称之为“童话”的作品,其实并不尽然。比如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卖火柴的小女孩》,“我看也不过是使用较大幅度夸张手法的幻想小说,而不是童话”。[22]“我国的童话理论还不够成熟,研究也还说不上深入,这是主观上的。客观上说,从民间童话到作家创作,这中间产生大量作品,确实也很难产生一个包容所有童话作品的童话定义。但是我们又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总不能写了半天,不知道‘童话是什么’吧?新时期以来的许多儿童少年幻想作品,被笼统地称作‘童话’。例如我写的《蓝色的舌头》,刊物就归入‘童话’,其实它是一篇幻想小说。”[23]
但他“不认为,‘童话’和‘幻想小说’有什么高低之分,只想区别一下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也许在安徒生时代这两种样式一律称作‘童话’的,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区分一下的时候了。过去争辩中我曾因此受到嘲笑,再受一次也无所谓”。[24]
孙幼军的这个文体发展意识毫无疑问值得高度肯定。事实上,他超越了“嘲笑”,也超越了“历史”。儿童文学的发展业已证实了这一点。如今,“幻想小说”已是一个开始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概念了。
[1]孙幼军.孙幼军童话全集[M].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2;孙幼军.孙幼军论童话[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124
[2][3][4][5][6][7][9][10][13][14][15][17][19][22][23][24]孙幼军.孙幼军论童话[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204,257,160-162,78,210,255,245,244,245,260,241,15-16,15,261,205,261
[8][16][18]孙幼军.孙幼军童话全集[M].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24,11,17
[11]贺宜.儿童文学讲座[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18
[12]孙幼军.童话的逻辑性和象征性[J].甘肃文艺,1962(3)
[20][21]孙幼军.我对幼儿童话的点滴想法[J].儿童文学研究,第九辑,19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