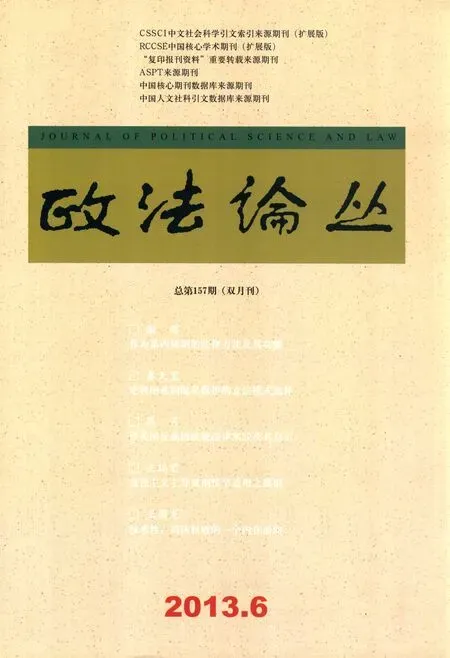论“狱侦耳目”制度被滥用的危害及对策
2013-01-30闫斌
闫 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论“狱侦耳目”制度被滥用的危害及对策
闫 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狱侦耳目”制度被滥用的危害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狱侦耳目”制度作为一项刑侦手段,有可能异化为变相的刑讯逼供,破坏监管秩序,或者引诱犯罪,从而影响司法公正,危及法治的实现和人权的保护。为防止“狱侦耳目”制度被滥用,首先应该在立法层面对此项制度的适用范围作出严格限制;其次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应对由“狱侦耳目”作出的证人证言谨慎对待,最后即使必须使用“狱侦耳目”,也应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培训和考试,若有违法行为应追究刑事责任。
狱侦耳目 刑讯逼供 危害 对策
近日以来,“浙江张辉、张高平冤案”震惊全国。尽管真实的案情已经水落石出,冤案已经得到平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公安厅都对当事人作出了道歉,但是广大公众、媒体、学界对案件的讨论和反思才刚刚开始。人们从各个角度思考着这一冤案,有人痛斥刑讯逼供的危害,有人质疑案件证据链的证明力,有人批判“有罪推定”思维方式的弊端……,①无可置疑,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且长期被误读的问题——“狱侦耳目”问题。
根据本案预审人员的口述,在“浙江张辉、张高平冤案”中,没有能证明张辉、张高平实施犯罪行为的痕迹物证,且被害人手指甲内的DNA成分经鉴定与张辉、张高平无关②,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张辉、张高平为什么会主动提交供述自己实施犯罪的口供呢?仅仅是因为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原因,还是存在其他潜在的原因?其实,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口供的作出与一个叫袁连芳的人物紧密关联。袁连芳就是刑侦部门安插在看守所中的“狱侦耳目”,事后证明,他在另一起冤假错案(马廷新案)中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可谓警方的“金牌卧底”,作为酬劳,除了在看守所内的各种优待,他还被前后两次减刑。③
一、“狱侦耳目”制度内涵解读
“狱侦耳目”制度是刑侦机关或者罪犯监管部门在看守所或者监狱内安插指派一部分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充当其耳目的制度。“狱侦耳目”又被称为“监所线人”、“监狱特情”以及“狱侦特情”等。“狱侦耳目”制度并非新生事物,早在1927年至1937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锄奸行动中就有类似的制度,当时称为“狱侦特情”制度,1953年全国“二劳”工作会议又将“狱侦特情”改为“临时耳目”。[1]P25由公安部人民警察干部学校刑侦教研室于1982年编撰的内部机密教材《刑事侦查》一书将“狱侦耳目”制度概括为:“抓住把柄控制利用的办法”,对此的评述为:“这是一种强制使用的方法,是对少数从犯罪集团中拉出来的,或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建立特情时使用的特殊办法。有的犯罪分子在被拘押期间,因刑侦机关侦察工作需要,被提出来使用,令其戴罪立功。有的是已办好劳教手续,征得劳教部门同意,留下来使用,‘手续’我们攥着,令其立功赎罪。”1997年司法部《狱内侦查工作规定》对具有“狱侦耳目”特性的相关制度作出了规定,各地监狱以此为范本实施该项制度。国外对“狱侦耳目”制度的研究和应用也并非空白,最早可以追溯至法国1810年提出的“维多克侦查模式”,此模式旨在以罪犯对付犯罪、减少犯罪、治理犯罪。前苏联A·H·瓦西利耶夫教授则将“狱侦耳目”制度归纳为“吸收社会人士参加揭露和预防犯罪”,他认为:这种方式“首先表现在能发现犯罪事件并及时将犯罪情况通知侦察机关,而这是迅速破案的必要条件。”[2]P427
按照刑侦部门的设想,我国当前的“狱侦耳目”制度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维护看守所、监狱的正常监管秩序。“狱侦耳目”为监管部门探听消息,有效防止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的自杀行为、袭警行为、逃脱行为以及各种不利于维护监管秩序的行为。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群体相较于其他人有较高的人身危险性、可能具有一定的犯罪能力和技巧,且由于即将接受审判或者正在服刑,其始终处于应激的心理状态之中,其不稳定的心理情绪加之较高的人身危险性,对看守所和监狱管理带来了各种难题。监管部门选择罪行较轻、人身危险性较小、认罪态度好、文化水平较高的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秘密探知监狱或者看守所内的各种潜在危险信息,防患于未然,大大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监管秩序。同时,监管部门也可以根据“狱侦耳目”秘密提供的信息来确定重点监管对象,也极大地提高了监管效率、降低了监管成本。二是协助刑侦部门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和各种对侦破案件有用的信息。一般而言,犯罪嫌疑人对侦察人员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和戒备心理,如果没有关键证据的威慑,很难使犯罪嫌疑人主动交代犯罪细节和经过。按照制度设计的初衷,侦察人员选择有文化、有经验的在押人员充当耳目,他们往往被安排与犯罪嫌疑人共处一室,或者对犯罪嫌疑人动之以情,或者对他们晓之以理,以局外人的身份影响犯罪嫌疑人认罪伏法,主动交待犯罪事实,这种方法从内部和心理上影响甚至瓦解犯罪嫌疑人的抵抗情绪,十分有利于提高案件侦破效率。即使在以上手段无效之时,“狱侦耳目”还可以探听一些有利于案件侦破的信息,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走上法庭充当证人,提供证言。
二、“狱侦耳目”制度被滥用的危害
尽管按照最初的制度设计初衷,“狱侦耳目”制度有很多优点,但是在实际的刑侦过程中由于“特情侦查的手段特殊与行为保密,致使司法程序与社会力量难以制约,容易产生所谓“诱惑侦查”或“警察陷阱”等效应。”[3]必须说明的是,“狱侦耳目”用来稳定和维护监管秩序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一旦被滥用为一项刑侦手段就有诸多危害。上文所提到的“狱侦耳目”袁连芳就两次与警方合作,两次威逼犯罪嫌疑人,两次为冤假错案充当证人。“浙江张辉、张高平冤案”中的预审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是他作案的,他不可能说得那么细,关键就是他不能说得那么准,你在一个点上准了,你不可能每个点上都准。”她是想说明通过侦察实验得来的案件细节与张辉、张高平的供述比对,二者丝丝入扣就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系统,因而可以在没有关键物证和疑点颇多的情况下为犯罪嫌疑人定罪。殊不知犯罪嫌疑人所作出的口供是“狱侦耳目”袁连芳提供的,只不过威逼犯罪嫌疑人抄写后再通过袁连芳上交警方,而袁连芳如何得知案件细节?可想而知,此案中的“狱侦耳目”袁连芳与警方合演了一曲双簧,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警方通过“狱侦耳目”袁连芳传递给犯罪嫌疑人的,而作为该案的预审人员以口供与案件细节高度吻合作为证据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里应外合,任意出入人罪至此,令人瞠目结舌。④结合本案,笔者从制度和理念两个层面将“狱侦耳目”制度的危害总结如下:
(一)从制度层面来看
第一,“狱侦耳目”制度非常有可能异化为变相的刑讯逼供。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可见,刑讯逼供为我国法律明文禁止。刑侦人员为了提高办案效率,同时避免承担刑讯逼供的责任,在“有罪推定”的心理定势思维之下,利用充当“狱侦耳目”的牢头狱霸,对犯罪嫌疑人威逼利诱,直至犯罪嫌疑人承认自己犯罪。在这种情况下,“狱侦耳目”实质上充当了侦查人员进行刑讯逼供的工具,在本质上与侦查人员实施的刑讯逼供达到同样甚至更恶劣的效果,因为利用“狱侦耳目”实施的刑讯逼供形式更加隐蔽,很难被有效监督,即使被发现,背后主使的侦察人员依然可以辩称自己毫不知情。另外,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还加入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侦察人员通过“狱侦耳目”威逼犯罪嫌疑人认罪的做法,可能会对此条法律的顺利实施构成威胁。
第二,“狱侦耳目”制度可能破坏监管秩序。侦察人员或者监管人员依靠“狱侦耳目”获得信息,就必然会给予其一定的优待,“狱侦耳目”依靠侦察人员或者监管人员的庇护极有可能成长为牢头狱霸,比如浙江冤案中的袁连芳就被奉为监狱“老大”。维持监狱、看守所正常的监管秩序必须建立在狱内正常人际关系的基础上,侦察人员、监管人员对“狱侦耳目”的庇护以及“狱侦耳目”的特权和跋扈的气焰都对其他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构成一种心理上的伤害,他们可能会通过其他方式发泄这种愤懑,甚至可能演变为恶性的越狱、袭警事件,从而可能对监管秩序构成极大破坏。
第三,“狱侦耳目”制度极有可能演变为“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由于现代社会新型犯罪的增加,诱惑侦查已经成为许多国家侦查案件的一种方式。虽然诱惑侦查有可能被片面的理解为“侦查陷阱”或者“警察圈套”而遭致各种质疑与批评,但是亦不宜对其全盘否定。诱惑侦查主要包括“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和“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一般说来,‘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因而通过这样的诱惑侦查所获得的证据应当采纳,而对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不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因而通过这样的诱惑侦查所获得的证据不能采纳。这实际上是对诱惑侦查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底线要求:政府不能为了侦查、追诉的需要而教唆一个本来无意实施犯罪的人去犯罪,简而言之就是政府不能诱导他人去犯罪。”[4]我国《刑法》第 78 条规定,罪犯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狱侦耳目”为了获得相应的减刑回报,会向侦查机关提交其获知的其他罪犯准备犯罪或者已经犯罪的信息,这同时有助于侦查机关预防犯罪或者极快地侦破案件。但是,这也引发了其他问题。很多时候,在其他罪犯没有犯罪动机或其他犯罪事实,为了获得减刑回报,或者侦查机关基于上级机关及社会要求尽快破案的压力,单纯的基于效率考量,“狱侦耳目”自行或者在侦察机关的授意下引诱罪犯实施新的犯罪活动。通常情况下,侦查机关会给予“狱侦耳目”一定的优待,这为他们发展成为“牢头狱霸”提供了便利,从而助长了其实施引诱犯罪行为的能力。“公民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其选择实施犯罪行为的自由意志。但是,线人可能对本无犯罪意图的公民予以引诱,干预其认识与判断机制,介入其犯罪意图的形成过程,影响其意志自由,或许会导致本不存在的犯罪。”[5]惩罚犯罪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秩序。引诱犯罪与这一目的背道而驰,不利于监狱的监管,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二)从理念层面来看
第一,滥用“狱侦耳目”制度可能妨碍司法公正,影响司法权威。“狱侦耳目”的隐匿侦查行为是一种秘密侦查措施。根据公安部出台的《关于刑事侦察部门管辖案件的范围、立案标准和管理制度的规定》,“耳目不得公开出庭作证。必须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秘密侦察得来的材料,通过合法的形式,转换为公开的证据,才能在诉讼活动中使用。”这也就是说,“狱侦耳目”一般是不出庭作证的,得来的材料也是不可以直接作为证据来使用,实践中通常的做法是,公安机关并不将通过此种途径得来的证据归入诉讼卷向检察院移送,而是写一份“情况说明”来解决。这意味着,“狱侦耳目”的使用及其证据来源并不向检察院和法院披露,辩护人也并没有享有对此种证据材料的阅卷权,辩护人无法对证人证言是否相互矛盾,是否可以相互印证作出判断,难以对证据的合法性与客观性进行把握,证据在庭审过程中得不到有效的质证,这种情形在刑事诉讼法理论中被称为“证据突袭”,而实践中法院通常又不会对案件主动进行调查,审判工作基本依赖于控辩双方证据的展示和质证,由此作出的判决很可能与实质正义相悖。同时由于这种侦查行为具有隐蔽性特征,被告人既使提请非法证据排除,但由于不能尽到初步的证明责任而难以引起法庭的重视和审查。然而,“法律适用在很多情况下就是设法把不明确的法律规范明确开来,把不清楚的案件事实清楚开来,以便确定是否将规范所规定的法效果赋予该事实。”[6]如果案件事实被“狱侦耳目”制度所蒙蔽,法律适用就极有可能出现偏差,法院一旦得出错误的裁判结果必然会严重危及了司法的公正与权威。
第二,滥用“狱侦耳目”制度可能破坏法治。众所周知,“国家权力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权力行使者都是利益最大化和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随时都有异化的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性是实实在在、已被历史所证明的,而强大的国家权力是个人力量所远远无法抗衡的。”[7]“权力一旦被滥用,它给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造成的伤害将是灾难性的。”[8]从本质上来说,侦查权是一种公权力,因此侦查权的行使要遵循侦查法治的原则。侦查方法的运用必须遵循合法性的原则,不能以违法手段来实现侦查目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1条对隐匿侦查做了相应的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相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这一规定对隐匿侦查的适用范围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而只是用“必要的时候”这一模糊的语句来作出限定。实践中,侦查机关在侦查案件的过程中通常会运用“侦查假说”,即“在刑事案件发生后,侦查人员根据现场勘查和调查访问的情况,运用科学原理、侦查经验和逻辑推理,对案件情况、作案人情况等作出的初步推测。”[9]P80侦查假说与无罪推定并不矛盾,而且是侦查过程中的必要的环节。但是,侦查假说必须建立在初步侦查取证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侦查机关根据已有的证据,可以推测谁是作案人;否则,在无法证实时,仍然是根据“存疑从无”原则作出处理的。《刑事特情工作细则》也明确了刑事特情只能用于侦查、控制刑事犯罪和犯罪嫌疑人。在张高平叔侄强奸冤案中,公安机关并没有从被害人身上发现精斑,并且指甲里的DNA与张高平叔侄明显不匹配。在这一案件中,对定罪影响重大的两项证据或者未被发现,或者检测结果不匹配,公安机关在直接证据缺乏,且间接证据难以相互印证的情况下的侦查行为,很难被理解为是对“案件情况、作案人情况等作出的初步的推测”,也很难据此就可以得出张高平叔侄是作案人的结论。因此,本案中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已经不是“侦查假说”的运用,而是基于“有罪推定”或者迫于上级机关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而异化为单纯追求破案率的权力滥用行为。法治的核心是运用法律来控制权力,那么侦查法治的核心就是运用法律来控制侦查权,从而使得侦查权的行使被限制在法律的范围之内,防止被滥用。在张高平叔侄冤案中,“狱侦耳目”制度的运用已经突破了法律的底线,必然有违侦查法治。
第三,“狱侦耳目”制度的滥用可能危及人权。人权是作为人普遍享有和应当享有的权利,即人权有着普遍性和应然性的特征。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是对人权的尊重,这不仅意味着保护守法公民的权利,而且昭示着维护违法公民的权利,相比较而言,后者之人权保护更具有迫切性。人权在本质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道德权利,对其保护与否不应以“坏人”和“好人”分而待之,其具有的普遍性和应然性要求对那些所有称之为“人”的自然生物都应平等对待。在侦查中的人权保障应着重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即使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分子的人权也不应被随意地侵犯。侦查活动对人权的“侵犯”和“限制”必须是合法的而且应该是作为“最后手段”加以使用,“秘密侦查的手段应当是在根据掌握的证据能够相对确定被侦查对象实施可疑的犯罪行为,在使用常规侦查手段无法查明犯罪事实的情况下才能适用”[10]。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已明确: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侦查机关受“口供中心主义”的思维影响,通常还是热衷于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有时即使采取非法手段也在所不惜。“狱侦耳目”制度被滥用而异化成为一种隐匿的刑讯逼供手段体现了这一点。本案中,张辉曾回忆在监狱的日子,一进监狱里,袁连芳曾交给张高平叔侄一份口供,让他们背熟,否认或者背不熟就会遭到毒打,甚至不让睡觉吃饭。⑤这份口供与被害人被强奸的现场等细节的描述高度相似,让人不禁猜想作为本案“狱侦耳目”的袁连芳是否受到侦查人员的操控。在侦查实践中,这种侵犯人权的侦查行为似乎已经演变为“公开的秘密”,这并不只是由于侦查人员受“口供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的影响,同时也根源于侦查权缺乏有效的约束与监督而导致的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极度轻视。
三、“狱侦耳目”制度被滥用的对策
妥善解决“狱侦耳目”制度的滥用不能寄希望于短期的运动式突击治理,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的治理本身也是一个立体化、多维度、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治理工作需要各级立法部门、司法部门、执法部门的配合与协作,它的治理过程贯穿法律运行的各个阶段。
第一,在立法的层面对“狱侦耳目”制度作出科学的规范和限定。目前指导“狱侦耳目”实践的规范性文件只有司法部1997年发布的《狱内侦察工作规定》。该规定只是原则性描述,各地监狱根据这一文件再制定细则,因而这一文件并不能在防范治理“狱侦耳目”制度被滥用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首先,立法必须对“狱侦耳目”用途作出明确界定,应限定“狱侦耳目”只能被作为稳定监管秩序之用,作为一项侦察手段的“狱侦耳目”应该少用、慎用直至不用。其次,立法必须明确滥用“狱侦耳目”的责任。侦察人员滥用“狱侦耳目”进行变相刑讯逼供应承担何种责任?“狱侦耳目”本人是否作为共同犯罪处理?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和研究。最后,立法可以对“狱侦耳目”人员的证人资格作出限定。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对“除特殊情况外”一词进行解读,或许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将“狱侦耳目”非法参与其中的情况纳入其中。
第二,公安机关将“狱侦耳目”作为一项刑侦手段时也应当少用、慎用甚至不用。公安机关在利用“狱侦耳目”提高办案效率之时,也提高了冤假错案发生的几率,因为即使侦查人员并未授意“狱侦耳目”对犯罪嫌疑人体罚威逼,作为“狱侦耳目”的在押人员也一定想通过协助侦破案件获得减刑和狱内优待,因此根本不会考虑方式方法,也不会顾及犯罪嫌疑人是否真的实施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冤假错案极易发生。另外,“在当代法治国家,刑罚的目的大多倾向于预防主义,也就是说科处刑罚的目的是为了预防行为人再次犯罪,同时通过对行为人的示范惩罚来预防社会中其他人犯罪,前者被称为特殊预防,后者被称为一般预防。”[11]公安机关应明确侦破案件是为预防再次犯罪,而不是为了单纯地惩罚犯罪嫌疑人,若以后者为指向,就很可能会在侦察过程中不择手段,甚至违法违规。
第三,在司法审判阶段,司法机关对由“狱侦耳目”作出的证言必须谨慎判定其证明力。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由与犯罪嫌疑人一同监押的人员提供的证言必须十分谨慎。首先要根据司法经验判断证人是否为“狱侦耳目”,若是,则需慎重研究犯罪嫌疑人口供与“狱侦耳目”证词的关联,判断是否为变相刑讯逼供所得证词,即使不存在上述现象,对“狱侦耳目”证词的证明力也必须谨慎认定。因为,一般而言,“狱侦耳目”证词是间接获得的,属于言辞证据、传来证据,其真实性并不十分可靠。“司法独立是现代国家法治化的重要标志。”[12]法官必须善于排除侦察机关的干扰,对案件作出独立和中立的判断。如果法官对“狱侦耳目”问题不闻不问,一味迁就,就必然还会造成类似“浙江张辉、张高平案”、“马廷新案”等冤案。当维护正义的公器沦为权力部门任意施为的工具,当本应秉承司法独立精神的司法机关成为为虎作伥的武器,人权和法治就无从谈起。因此,司法机关必须对“狱侦耳目”证人证言谨慎对待。
第四,即使在刑侦过程中适用“狱侦耳目”制度,也必须对作为“狱侦耳目”的对象进行事先的培训考试,事后进行必要的考核,若涉嫌非法采集证据,应追究刑事责任。若一定要在案件侦察过程中适用“狱侦耳目”制度,首先要谨慎选择作为“狱侦耳目”的人选,选择那些犯罪时主观恶性小、犯罪后认罪态度好并且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充当“狱侦耳目”,另外,还必须强调自愿的原则。对于这一点,公安部制定的《刑事特情工作细则》已有相关规定:“特情人员应当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特情应当具有发现和接近犯罪分子的条件;二是特情应当具有一定的活动能力;三是特情应当愿意为侦查机关工作,或具有为侦查机关控制使用的条件。”浙江省公安厅、检察院与监狱管理局2006年制定的《会议纪要》更进一步细化了这些条件:“一是狱侦特情自身刑期应在10年以下,少数尖子特情的刑期可以在10年以上,最长不得超过15年;二是认罪服法;三是有立功赎罪愿望,愿意为公安、检察机关工作;四是有一定文化素质和社会阅历;五是有较好的心理素质和口头表达能力;六是知晓或初通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13]对现有规定依然有丰富完善的余地,例如是否可以考虑限制故意犯罪的人或者恶性刑事犯罪的人充当“狱侦耳目”,由那些过失犯罪和主观恶性较小的人来承担这项任务。其次,必须对他们进行事先的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政策法规、心理调适、案件背景,这是因为作为“狱侦耳目”的人员必须依法行事,不能为了立功而以非法手段逼迫犯罪嫌疑人招供,他们还必须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还应对特定案件的背景有一定的了解以便于开展工作。复次,在培训结束之后进行相应的考试,以此决定他们是否具备充当“狱侦耳目”的资格。考试形式可以由笔试和面试组成,笔试主要考察他们法律知识与政策掌握的熟练程度,面试应考察他们的心理素质与应变能力等。只有通过考试才能选拔合格的“狱侦耳目”,并防止他们变相刑讯逼供,危害犯罪嫌疑人的各项诉讼权利。最后,必须有事后的追责机制。如果“狱侦耳目”涉嫌违法采集证据以及变相刑讯逼供,构成犯罪的应移交司法机关,由法院宣判之后与旧罪数罪并罚,不构成犯罪的也必须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只有明确追责机制才能有效威慑作为“狱侦耳目”的人员不至于不择手段违法采集证据证言。
注释:
① 参见:浙江十年奸杀冤案始末,http://zj.sina.com.cn/news/d/2013-03-31/084469353.html,访问日期:2013年3月30日。
② 参见:无懈可击:聂海芬,http://www.cctv.com/program/dyx/20060515/103263.shtml,访问日期:2013年3月30日。
③ 参见:服刑线人被指2次参与伪造证据致无辜者入狱,http://news.timedg.com/2011-12/09/content_7620263.htm,访问日期:2013年3月30日。
④ 参见:浙江叔侄强奸冤案:警方串通牢头狱霸逼供,http://news.ifeng.com/shendu/nfzm/detail_2013_03/30/23698349_0.shtml,访问日期:2013年3月30日。
⑤ 参见:袁连芳:一个谜一样的人物,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7928075&boardid=1,访问日期:2013年3月30日。
[1] 李永.狱内侦查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9.
[2] [前苏联]A·H·瓦西利耶夫.犯罪侦察学[M].原因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
[3] 徐克林.狱侦特情:监狱秘密侦查制度的理性回归[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2,3.
[4] 王超等.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及其证明[J].政法论丛,2004,4.
[5] 蒋鹏飞.刑事侦查中线人使用的二元法律规制[J].北方法学,2013,2.
[6] 孙培福,黄春燕.法律方法中的逻辑真谛[J].齐鲁学刊,2012,1.
[7] 闫斌.论哈贝马斯交往权力理论[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8] 闫斌.网络言论自由权宪政价值初探[J].理论月刊,2013,4.
[9] 毛立新.侦查法治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10] 丁延松.法治语境下我国秘密侦查制度的现实困境和出路[J].政法论丛,2011,04.
[11] 张斌峰,闫斌.“化学去势”立法探讨:争议与鉴借[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3,1.
[12] 闫斌.论网络言论自由权的两个限度[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3,2.
[13] 王武良,陈章,张凡.狱侦狱控之技能[J].中国检察官,2008,9.
(责任编辑:黄春燕)
The Harm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Intelligencer in Prison System’s Abuse
Yan Bin
(Law School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Hubei 430073)
It has been long neglected that the harm of the system of Intelligencer in Prison that is absued.As a means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this system may become a disguised form of extort confessions by torture,disrupting the order of prison administration,or induce others to crime.Therefore,it may undermine judicial justice and threate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ule of the law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In order to prevent this situation,the first thing is to make strict limitation to its applicable scope at the legislative level;then the testimony of the Intelligencers in Prison should be treated with caution by the judges in the judicial process;finally,even this system must be applied,intelligencers should achieve necessary trainings and exams,and they should bear the criminal responsbilities if they violate laws.
intelligencer in prison;extort confessions by torture;harm;countermeasures
D793
A
闫斌(1982-),男,山西阳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
1002—6274(2013)06—1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