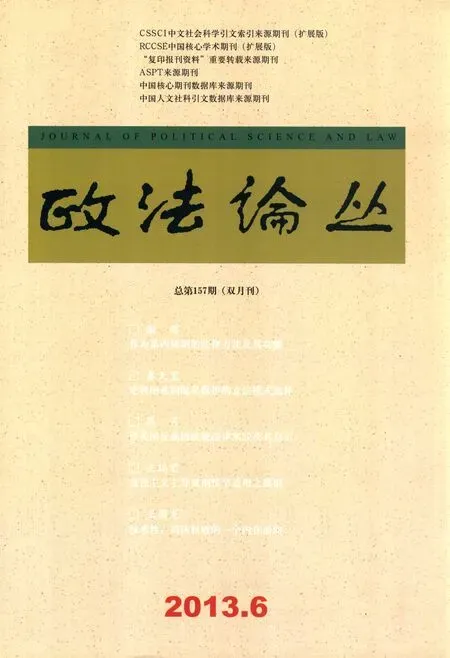论合作作品中主体身份的确认
2013-01-30陈明涛
陈明涛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44)
论合作作品中主体身份的确认
陈明涛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44)
就合作作品的主体身份确认的要件而言,共同创作的行为与共同创作的意图历来被认为是核心要件。然而,对两个要件内涵的理解,一直存在模糊的认识。为此,有必要对两个核心要件进行深入地阐述和分析,以期建立正确的判断标准,从而引起司法实务的重视。
合作作品 共同创作 主体身份 合作作者
合作作品,在英文中是“works of joint authorship”,德文是“Werke von Miturhebern”,日文则译为“共有著作物”,是指两人以上共同创作的作品。[1]P65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三条对合作作品进行了规定:“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合作作品整体的著作权。可以说,在著作权法领域,合作作品历来是争议最多、最为复杂的作品类型之一。现行法规定并没有解决合作作品主体确认问题,对其理解存在不同的观点,如“二要件说”①、“三要件说”②、“四要件说”③等。实际上,不管是“二要件说”、“三要件说”还是“四要件说”,本质性区别不大,均明确了两个核心要素:共同创作的意图与共同创作的行为。其他要件说增加的“两人以上的人数要求”及“创作最终形态为可版权性作品”标准,是合作作品所包含的应有之义。从国外版权法比较来看,也通常将“共同创作的行为”和“共同创作的意图”作为构成要件。如美国第二巡回法院在著名的Childress v.Taylor一案中提出了成为合作作者两大要件:(1)对作品做出了独立的并且可版权性的贡献;(2)有成为合作作者的充分意图。
问题在于,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如何才能正确适用和理解这两个核心要件,即必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何种类型和数量的创作可以使创作贡献的人成为作者;二是何种情形下的主观意图可以使一个人获得合作作者的地位。[2]P194就已有的理论探讨来看,相关学者对此问题的探讨深入不够;就已经发生的合作作品案件来看,法院在适用过程中存在模糊的、不统一的认识。在此,笔者将对两个核心要件进行深入地阐述和分析,以期建立正确的判断标准,从而引起司法实务的重视。
一、共同创作的行为分析
什么样的共同创作行为才能成为合作作者?美国著名的版权学者分别提供了两个不同的判断标准:一种是Nimmer教授的“超过最小限量”标准。其认为假定两个人要成为合作作者,只要其中一个对于整个作品的创新本质可以提供一些实质性的贡献,即使不能提供可区分的版权性材料,也不能阻碍其成为合作作者。并且,这些作者对于作品的各自贡献没有必要是相等——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上,但是每个作者的贡献必须要超过最小限量。[3];另一种是Goldstein教授的可版权性贡献标准。[4]P130其认为合作性的贡献不必然产生合作作品,一个贡献者也不必然成为合作作者,除非是这种贡献成为一种原创性表达,以至于其自身构成版权法的客体。[5]P379
对于这两种观点,美国学界评价不一。如Zemer教授就指出,英国法律的观点可能更接近于 Nimmer教授的“超过最小限量”标准。对于Goldstein教授的独立的可版权性要求,其认为将挫伤作者创作或者其他作者有价值创意的积极性,并且最终将损害创新。[6]P685然而,美国法院普遍采纳了 Goldstein教授的可版权性标准,而没有适用Nimmer教授“超过最小限量”标准。其原因在于:一是由于版权法无法保护创意,而只能是保护表达。如果限制作者吸取已存作品中的想法或者创意,将会严重地阻碍创新;[4]P130二是采用可版权性标准,将在版权法和合同法领域达到一种恰当的平衡。当合同没有明确约定时,版权法能够保护创作出版权性的作品一个人或者多个人。而合同法则可以让一个人雇佣其他人创作可版权性的作品,并赋予他作者身份;④[7]三是可版权性的标准,是容易被客观实证的标准。当然,随着新作品类型的出现,美国法院在采纳“可版权性标准”的基础之上,也开始借鉴“超过最小限量”标准的合理因素。
1.Childress v.Taylor一案法院支持可版权性标准的经典案例。被告Taylor是一名从业40多年的职业演员。当被告在百老汇之先锋戏剧扮演“妈妈”马布利(著名的喜剧女演员)一角时,她开始有兴趣基于马布利的生活创作出一部戏剧。在此期间,Taylor收集了“妈妈”马布利的相关资料,采访了她的朋友和家人,收集了她的笑话,检索了图书馆的资料。1985年,Taylor与原告剧作家 Childress签订了合同,由Childress写作该剧本,Taylor为此提供了相关素材和资料。[7]在此期间,Childress独自创作了该戏剧的剧本,被告认为他提供的研究材料和想法,使之有权利成为合作作者并分享戏剧的利益,而原告Childress明确拒绝了被告的请求,只认为自己是该剧本的单独作者。在剧本完成后,被告未经原告的允许复制了剧本并交由另外一家成剧院出演。[7]因此,原告Childress以被告Taylor侵犯版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被告Taylor则抗辩认为自己是该剧本的合作作者。[7]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美国第二巡回法院完全采纳了可版权性标准,指出为了防止某些人伪造虚假的声明,从而达到分享单独作者的目的,要求每个合作作者必须作出可版权性的贡献。[7]更重要的是,法院指出可版权性标准在合同法及版权法之间谋求了一种平衡,版权法保护可版权性贡献的参与者,没有可版权性贡献的人可通过合同来获得保护。⑤[7]
2.Gaiman v.McFarlane一案的出现,使得法院在特定作品中借鉴“超过最小限量”标准。原告Neil Gaiman(尼尔·盖曼)和Todd McFarlane(托德·麦克法兰)都是世界漫画领域的知名人物。Neil Gaiman主要是从事剧本创作并不绘画,McFarlane不仅绘画,而且出版漫画图书。1991年,在McFarlane创立自身的漫画公司不久,其自己创作了著名的“Spawn”(再生侠)系列漫画。由于早期剧本受到批评,McFarlane决定聘请四个顶级漫画作家,原告Gaiman就是其中一个。然而双方没有签订任何书面的合同,也没有对版权问题进行约定。Gaiman不是McFarlane所属公司雇员,也不存在任何委托关系。在Spawn第九期,Gaiman创造了 Angela,Medieval Spawn和 Cogliostro三个重要人物,McFarlane绘画了这些人物。这些人物创作取得巨大的成功,McFarlane也支付相应的报酬给Gaiman。1996年,Gaimain听说McFarlane可能要出售他的公司,因此请求与之签署书面合同。然而双方谈判最终没有成功。随后,McFarlane给Gaiman发送最后通知明确表明Gaiman没有Medieval Spawn和Cogliostro两个人物的版权。Gaiman因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为上述作品的合作作者身份。[8]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创作人在混合媒体作品(像漫画书、电影作品)中合作创作可版权性角色,很难满足Childress v.Taylor一案可确立的可版权性标准。因为这一创作性产生过程使得很难存在独立的可版权性贡献。[8]例如,漫画作品通常包括四类创作者:写作人、素描人、着墨人和涂色人。每一类创作人所作出的贡献很难成为独立的可版权化的客体。因此,法院主张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最终的作品是具有可版权性,即使合作创作的行为不具有独立的版权性,也不影响当事人取得合作作者身份。[8]因此,法院最终确认了原告的合作地位。当然,法院也指出,这种更低的标准要求仅仅适用于“混合媒体”作品。[9]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⑥学界对共同创作行为要件的内涵分析,存在着不同的主张:(1)独立思维说。[10]认为合著作品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一类是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人在同一作品中使用了同样的表达形式。如共同撰写文章,共同作画等,这种形式下,如果创作思维是独立的,则为共同创作。另一类是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人在同一作品中使用了不同的表达形式。如歌曲创作,一人作词、另一个人作曲,此种形式下为归类为共同创作;[11](2)独创性劳动说。认为合作作者的共同创作行为是一种不可分割独创性劳动,即合作作者在作品表现形式上创作成分,是作品不可缺少的,不论量上还是质上缺少则作品不完整;[12](3)价值决定说。以提供决定艺术作品价值的创造性劳动决定合作作者——谁的创造性劳动决定着该作品的价值,谁就是合作作者,可以共享著作权;[13](4)还有学者认为,共同创作行为所完成的合作作品,应达到著作权法所要求的作品标准。那些专为出版之需,对作品进行纯技术性的编辑加工的行为,并未赋予作品本身新的表现形式,不属于合作创作行为。[14]P94
由此可见,我国学者对共同创作行为的分析非常不统一。“独立思维说”过分强调思维在创作中的重要性,既无质的规定,也无量的确定,且思维是无法被著作权法所保护的,这就造成司法适用过程难以判断。“独创性劳动说”强调了独创性劳动对作品的完整性的重要,却没有进一步分析独创性劳动本身质与量的要求。而第(4)种说法倾向于Goldstein教授的观点,却没有进一步深入阐述其理由。价值决定说则是一种特殊化的观点,更加难以在法律适用中权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二人以上按照约定共同创作作品的,不论各人的创作成果在作品中被采用多少,应当认定该项作品为共同创作。⑦可见,该条可解释为作品共同创作行为不以量为准,这有点类似于“超过最小限量”标准,只不过没有明确表明要超过最小限量。然而,该规定没有要求各人创作成果的可版权性。《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又规定,著作权法所称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为他人创作进行组织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物质条件,或者进行其他辅助工作,均不视为创作。⑧该条规定可以推论出,共同创作行为应当符合可版权性的标准。但遗憾的是,该条并没有对共同创作的行为进行特别规定,而是泛指创作行为。
现行法的上述状况,是一种分散性的、非明确性的规定,必然造成法院理解的不够透彻,解释的标准不一,掺加了自身的主观判断,出现了相当混乱的局面。仅举两种典型表现:
1.没有理解合作作者应有独立性的可版权性贡献的要求,将演绎作品中已有作品作者的创作行为与合作作品的共同创作行为相混淆。如肖涛生与邹士敏著作权权属及侵权纠纷一案。1982年,邹士敏拍摄了几张表现五个小孩在草垛上吹哨子的场景的照片,并将照片提供给了肖涛生。邹士敏基于上述照片在1983年3月创作完成了油画作品《田间小曲》(以下简称《田间小曲》)。其间,肖涛生见到过该幅作品。1984年前后,肖涛生与邹士敏约定在《田间小曲》的基础上合作创作油画作品《吹响响》,由二人共同署名参展。随后,肖涛生在第一稿的基础上又完成了《吹响响》的第二稿,两稿为同一作品,其中的第二稿被他人收藏,邹士敏没有参与过《吹响响》的执笔绘制工作。2005年1月,肖涛生在美国举办了名为人与自然的个人画展,画展上展出了《吹响响》;2006年9月,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四川省美术馆主办了名为联合国总部肖涛生个人画展——家乡汇报展的个人画展,《吹响响》在画展上展出,并印制在请柬、宣传画以及名为《肖涛生绘画作品世界巡回展》的宣传画册上,在上述活动中,肖涛生均未在《吹响响》上署邹士敏的名字。因此,邹士敏向法院提出诉求,要求认定他的合作作者身份,并向肖涛生提起侵权请求。[15]肖涛生认为,邹士敏对《吹响响》没有执笔,应当视为不存在共同创作行为。而一审法院却认为,本案认定共同创作的关键在于《吹响响》作品中是否以非独创的方式包含了著作权人邹士敏作品《田间小曲》中的独创性成果,而这种“包含”系邹士敏同意以合作创作的方式使用在新作品《吹响响》中的。[15]二审法院更进一步认为,由于我国著作权法所称的“合作创作的作品”,是指作者对作品的创造性智力劳动方面的贡献,每个合作者不一定都必须亲自动手、亲自执笔,故,肖涛生以此为由提出邹士敏没有创作《吹响响》不符合法律规定。[15]
由此可见,法院将共同创作行为与演绎作品行为相混同。演绎作品中的创作行为往往是建立在已有作品创作的基础之上,包含原作作者的独创性成果。而该案中,肖涛生对《吹响响》的创作,显然是对邹士敏作品《田间小曲》的再创作,包含了邹士敏的独创性成果,应当是演绎作品的创作行为,而不能认定为合作作品的共同创作行为。二审法院认为,由于合作作品是指作者对作品的创造性智力劳动方面的贡献,每个合作者不一定都必须亲自动手、亲自执笔的观点,更是完全错误的。合作作品的共同创作行为不包含对创意的简单保护,这种创意必须转化为可供版权法保护的表达形式。显然,二审法院根本没有理解共同创作行为的可版权性标准。
2.对于合作创作行为的认定,没有形成确定、一致性的标准,缺乏法理性分析,更多是事实性罗列下的主观判断。如刘国础诉叶毓山著作权纠纷一案。1981年夏天,共青团重庆市委、重庆市教育局、文化局决定在全市少先队员中发起为修建《歌乐山烈士群雕》的集资活动,并一致同意聘请叶毓山为《歌乐山烈士群雕》的创作设计人。歌乐山烈士陵园管理处指派上诉人刘国础负责同有关单位联系的工作。11月25日,在重庆市各届代表参加的“群雕奠基典礼仪式”上,叶毓山展示其创作的30余公分高的《歌乐山烈士群雕》初稿,并就创作构思主题思想、创作过程作了说明,获得与会者鼓掌通过。奠基会上还展示了刘国础根据有关领导指示为说明《歌乐山烈士群雕》所处环境位置而制作的歌乐山烈士墓模型。此后,叶毓山在《歌乐山烈士群雕》初稿基础上又制作了一座高48公分的群雕二稿,与刘国础一道根据初稿、二稿基本形态的要求,指导木工制作了放大稿(又称定稿)骨架。刘国础除参加了堆初形外,还在叶毓山指导下参与群雕泥塑放大制作和其他一些工作。叶毓山的一些学生也曾到现场对泥塑初形进行初步的艺术造型。放大制作过程中,叶毓山经常到现场进行指导和刻画修改,并对有关方面对群雕艺术造型提出的合理建议予以采纳。刘国础在放大制作中通过口头或实际刻画提出过一些建议。叶毓山认为符合自己创作意图和表现手法的,给予采纳认可。[16]1984年5月,全国首届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览会在北京举行,重庆市选送了《歌乐山烈士群雕》、《烈士墓沙盘》等作品参展。叶毓山送展的《歌乐山烈士群雕》、《鹰塔》获得了纪念铜牌。参展的沙盘不属雕塑作品,不颁发纪念铜牌。1987年,刘国础以《歌乐山烈士群雕》系同叶毓山共同创作,参加全国首届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览会所获纪念铜牌应共同享有,叶毓山侵犯其著作权为由,向四川省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叶毓山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16]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烈士群雕放大稿是在叶毓山亲自参加和指导下完成的,刘国础参与了放大制作,做了一些工作,通过口头或实际刻画制作提过建议,但最终是否采纳认可,取决于作者叶毓山。群雕放大稿与初稿相比较,在主题思想、整体结构、基本形态、表现手法等方面是一致的,没有实质的改变。出现的一些变化也是在叶毓山的指导、参加和认可下完成的,是在初稿基础上的修改完善。且不存在建造倡议单位委托刘国础参加群雕创作的事实,刘国础与叶毓山之间也没有合作创作的口头或书面约定。因此,刘国础以实际参与制作的放大稿较初稿有变化和存在事实上的约定关系,从而应享有著作权的主张不能成立,不能认定其为烈士群雕的共同创作人。[16]然而,一方面,法院以刘国础的创作行为取决于叶毓山,显然是强调了合作作者对作品的控制力的重要性,但是对刘国础的行为是否可以构成创作行为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另一方面,法院以群雕放大稿与初稿相比较,没有实质的改变来否定刘国础的创作行为,缺乏法理性的分析,没有对共同创作行为的质与量进行限定,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不相符合。
实际上,可版权性贡献标准是对合作创作的行为进行质的规定——可版权性;而“超过最小限量”的标准是对合作创作的行为进行量的规定——超过最小限量。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可版权性贡献标准与超过最小限量标准可以有机的结合,即对行为质的要求上符合可版权性,在质量规定上符合超过最小限量。就现行法而言,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对“创作”的定义显然可以扩大理解为可版权性标准,民通《民法通则》意见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也可以用来解释超过最小限量标准。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应当摆脱现有审理思维,充分认识现行法的内在原理,结合可版权性及超过最小限量标准,明确相关的法律判断。
二、共同创作的意图分析
共同创作的意图要件更多地体现在创作人的主观心理状态。需要明确的问题是:共同创作的意图是主观明示的意图,还是应当通过客观证据推定的意图;共同创作意图与对作品实质性、可版权性创作行为的关系是什么;共同创作意图是将自身贡献合并到作品中的意图,还是包括成为合作作者的意图;共同创作意图需要对作品创作有实际的控制能力的意图,还是仅仅对可版权性贡献的意图;共同创作意图是共同创作的事实状态的内心意思反映,还是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这些问题都需在司法实践中统一标准并明确解释。
(一)明示的意图与客观推定的意图
同样,在贾力坚诉骆根兴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中,我国法院对共同创作的意图也采取了客观证据推定的立场。贾力坚诉称,1995年正值抗战胜利50周年,其独立创作了以刘伯承师长为核心人物,以普通战士为衬托背景,以换帽徽为情节,名为《大敌当前》的版画草图。在同年7月的一次会议上,骆根兴提出上述主题以油画表现更好,他同意了这个提议,和骆根兴商定由双方共同完成该作品。此后,经双方努力,1997年完成了该作品,和骆根兴共同署名,题目仍为《大敌当前》。该作品多次参展,获得了许多奖项。2005年,骆根兴擅自将《大敌当前》油画拍卖,获得人民币209万元。[18]而骆根兴辩称,油画《大敌当前》是其1996年3月到1997年7月间独立创作的作品,从来没有见过贾力坚的版画《大敌当前》草图,也从未与贾力坚就版画《大敌当前》草图进行过研讨,更没有与贾力坚协商合作创作油画。1997年和1999年,油画《大敌当前》两次参展前,贾力坚多次向其请求在参展作品上署名,考虑到他与自己同在总装备部工作并为油画《大敌当前》做过模特,就同意贾力坚在该画参展时的标牌上署名,但并未同意他在作品上署名。[18]法院审理后,认为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一方面,贾力坚实际参与了《大敌当前》从构思到完成的过程,从事了提供构思草图、寻找素材资料、安排人物模特拍摄等工作;另一方面,骆根兴多次在作品上共同署名“骆根兴贾力坚”,且油画《大敌当前》获奖的稿酬也分给了贾力坚一半,在电视采访时也与贾力坚共同陈述创作的事实、共同署名。从上述两方面可以看出,贾力坚的陈述与骆根兴的上述行为能够互相形成对应。因此上述事实能够印证在两人间存在共同创作的口头协议并实际进行了履行。[18]
(二)共同创作意图与共同创作行为的关系
只要不存在共同创作的意图,即使当事人一方对作品做出独立的、可版权性的贡献,也不能成为合作作品。美国国会关于合作作品的立法报告中就指出,在作品完成的时候,意图才是“试金石”条款。实际上,共同创作行为只不过是意图的推定和检验。[19]如上所述,Thomson v.Larson一案中,Thomson与 Larson的密切合作下,作品与最初版本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Thomson为作品付出了创作性劳动,也符合独立可版权性标准的构成要件。然而,美国第二巡回法院依然认为原告并没有成为合作作者,其理由就在于Thomson不存在成为合作作者意图。
在我国,李淑贤诉李文达等侵害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著作权一案,是一起里程碑式的经典案例,同样采纳上述标准。爱新觉罗·溥仪在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期间曾由本人口述,其弟溥杰执笔,写过一份题为《我的前半生》的自传体悔罪材料。1960年初,在征得溥仪同意后,群众出版社派李文达与溥仪一起对该材料进行修改、整理。同年七八月间,有关部门派李文达亲自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及溥仪过去生活过的地方进行调查,澄清了一些讹误的历史事实。1961年8月,李文达在群众出版社的有关会议上汇报了修改计划和该书应反映的主题思想,并对该书的主题、叙述形式、对溥仪思想性格的反映和内容的真实性等方面提出了重要的意见。此后,溥仪与李文达在新的主题思想下重新撰写,由溥仪回忆口述、提供材料,李文达执笔,由二人对写成的稿件进行审阅修改。经二人密切配合,1962年完成了初稿,后二人在广泛征求领导和清史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又几次修改。1964年该书正式出版,书名仍为《我的前半生》,署名:溥仪。溥仪逝世后,李淑贤(溥仪遗孀)、李文达、群众出版社发生了谁享有该书著作权的争议。[20]
该案引起了巨大的关主,先后经过国家版权局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及高级人民法院的多次审理,从起诉到终审判决历时近10年。在多次的审理过程中,对于作品著作权归属问题形成完全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的前半生》是李文达与溥仪合作作品,他们都应享有著作权。主要理由:一是李文达不是简单地记录、整理溥仪的口述材料,而是直接参与了该书的创作,因此他是作者之一;二是李文达与溥仪创作该书的过程已形成合作创作的事实,故改书是合作作品,二人均享有著作权;三是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是作品的形式,不保护作品的思想。作品不论以甚么口气、甚么人称写的,不影响著作权的归属。李文达用文学形式表达出溥仪的想法,李就享有该书的著作权。[20]可见,这种意见认为实质性、独创性、可版权性共同创作行为可以取得作者身份,而不必存在共同创作意图。而后一种意见认为,《我的前半生》一书从修改到出版的整个过程都是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进行的,李文达是有组织指派帮助溥仪修改出书,故李文达与溥仪不存在合作创作的事实。《我的前半生》一书既是由溥仪署名,又是溥仪以第一人称叙述亲身经历为内容的自传体文学作品;该书的形式及内容均与溥以个人身份联系在一起,它反映了溥仪思想改造的过程和成果,体现了溥仪的个人意志;该书的舆论评价和社会责任也由其个人承担;因此,溥仪应是《我的前半生》一书的唯一作者和著作权人。[20]实质上这种意见认为,共同创作意图要件是认定合作作品主体身份必备要件,李文达不具有成为涉案作品合作作者的意图。最终法院采纳后一种意见,认为涉案作品不构成合作作品。
(三)成为合作作者的意图与自身贡献融入作品的意图
意图不仅是将自身贡献融入到整个作品中的意图,还应包括成为合作作者的意图。美国国会立法报告中,认为合作创作意图的检验标准就是在写作完成之时,创作的各个部分能被吸收或包含在整体之中,虽然这些部分自身可能是不可以分离的或者相互依存的。[19]此后,美国法院却严格解释了合作的意图要件。在Childress v.Taylor一案中,法院就认为,当事人应当有成为合作作者的意图,而不仅仅是自己的贡献被合并的意图,虽然这种意图是被法律所定义的。并且,法院认为合作作者的意图也就是分享合作作品的意图。[21]实际上,现实生活很多情况也促使法院不得不进行限缩解释。例如,在作者与编辑关系情况下,编辑经常对作者已完成的作品进行修改,甚至修改的意见往往是版权性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编辑应当成为合作作者,因为编辑没有成为合作作者的实际意图。还如,在作者与其工作助手的关系中,工作助手也会对作品的创作提供帮助、发表意见,同样也不能认为助手可以成为合作作者,因为助手也没有成为合作作者的意图。
1988年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由别人代为起草而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会议讲话作品其著作权(版权)应归个人所有的批复》指示:“《汉语大词典》主编罗竹风,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关于介绍《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进展情况的发言稿,虽然是由《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工作人员金文明等四人分头执笔起草,但他们在起草时就明确是为罗竹风个人发言作准备的;罗竹风也是以主编身份组织、主持拟定发言提纲,并自行修改定稿,嗣后以其个人名义在大会上作发言。因此,罗竹风的发言稿不属于共同创作,其著作权(版权)应归罗竹风个人所有。罗竹风同意在其他刊物署名刊载发言稿全文,不构成侵害他人著作权。对金文明等人在执笔起草发言稿过程中付出的劳动,罗竹风在获得稿酬后,可给予适当的劳务报酬。”实际上,这一批复可解读为强调成为合作作者意图的决定性意义,仅是将自己贡献融入作品的意图不能成为合作作者。
制造能力随着生产过程中制造资源、制造活动和约束条件的变化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制造能力由制造活动组成,不同制造活动执行情况影响制造能力,为了实现对制造能力的度量,借鉴ISA-95[23]对生产能力的描述,给出以下概念的定义:
(四)可版权性贡献的意图与有控制创作能力的意图
意图要件不仅强调了对作品有可版权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能够控制作品的创作。在Aalmuhammed v.Lee一案中,法院对于共同创作的意图要件有了最新的发展。1991年,华纳兄弟公司与Spike Lee及其制作公司合作拍摄电影有《Malcolm X》。Spike Lee撰写了电影剧本、指导并合作出品这部影片。该片由丹泽尔·华盛顿(Denzel Washington)出演Malcolm X一角。因为Aalmuhammed对于Malcolm X和伊斯兰教十分了解,丹泽尔·华盛顿聘请他帮助角色的准备工作。原告全面分析了Spike Lee和Denze的剧本并提供了全面的修改建议,并大量参与整个电影的拍摄工作。[20]在此期间,Aalmuhammed与华纳兄弟公司、Spike Lee及其制作公司并没有签署任何合同,但是分别从Spike Lee和丹泽尔·华盛顿那里获得相关报酬。在1992年夏天电影正式发行之前,Aalmuhammed请求作为电影的合作作者在电影中署名,然而这一请求遭到拒绝。随后,Aalmuhammed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确认其合作作者的身份。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认为过于扩张的解释将使合作作者身份扩大到一些“过分要求的贡献者”,例如编辑、助手、先前配偶、情人或者朋友都会因为提出可版权性的意见而成为合作作者。因此,法院通过对 Childress v.Taylor案及 Thomson v.Larson的分析,提出了成为合作作者意图的三个标准:(1)一个作者通过实施控制措施完全主管作品;(2)可推定的作者可通过客观证据表示出成为合作作者的意图;(3)作品可以呈现出创作贡献,这种贡献是无法分割评估的。并且法院认为在许多案例中,控制将变成最重要的因素。[22]
如前所述,刘国础诉叶毓山著作权纠纷一案也体现了控制创作能力意图的重要性。因为烈士群雕放大稿是在叶毓山亲自参加和指导下完成的,刘国础参与了放大制作,做了一些工作,通过口头或实际刻画制作提过建议,但最终是否采纳认可,取决于作者叶毓山。[16]原告刘国础也就不具备控制作品创作能力的意图,因此不能成为合作作者。
(五)事实状态的意图与法律行为的合意
对于共同创作的意图,不能片面理解为共同创作的合意。从民事法律关系角度,大陆法学者通常用“意思表示一致”或“合致”的表述来概括“合意”的内涵,其本身是合同本质的一种表述方式,是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如果将共同创作的意图理解成共同创作的合意,将导致合作作品是合作作者之间合同履行的后果。实际上,共同创作的意图,既不是一种意思表示行为,也不需要了解其中的法律后果,只是事实状态的意思,即内心意思的一种反映。进一步讲,共同创作意图是在合同没有明确约定前提下,合作作品主体身份确认的构成要件。如果存在合作作者之间的合意,而根本不需要进行主体身份的确认,依据各方形成的合意或者合同形式就可以认定。
然而,当前的司法实践完全混淆了这一要件的理解。如肖涛生与邹士敏著作权权属及侵权纠纷一案,法院就认定合作作品的要件是指二人是否具有共同创作的合意,是否存在共同创作的行为。法院认为从案件的事实来看,肖涛生在1998年将《吹响响》收录入《肖涛生油画集》,并在该画集出版后签名赠送给邹士敏,纵观该画集的所有油画作品,肖涛生只在《吹响响》旁标注了“与邹士敏合作”的字样,该事实能够印证邹士敏关于双方口头约定合作创作《吹响响》的主张,故对邹士敏主张的双方存在合意的事实予以确认。[15]实际上,只要能认定双方存在创作合作作品的合意,也就表明双方对合作作品的创作存在合同关系,完全不必要再对共同创作的意图要件进行讨论。
三、结语
共同创作的行为与共同创作的意图是合作作品主体身份确认的核心要件。对两个要件内涵的理解,理论界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司法实务也缺乏一致的判断,实有形成明确相关标准的必要。对于共同创作行为,应当以可版权性贡献标准为基础,借鉴“超过最小限量”标准的合理因素。对于共同创作意图,应当明确共同创作的意图是明示的,也必须通过客观证据来进行推定;应当明确不存在共同创作的意图,即使对作品做出独立的、可版权性的贡献,也不能成为合作作品;应当明确意图不仅是将贡献融入到整个作品,还必须是成为合作作者的意图;应当明确意图不仅强调了可版权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能够控制作品的创作;还应当明确共同创作的意图不能片面理解为共同创作的合意。
注释:
① 参见吴汉东著:《知识产权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
② 参见刘春田著:《知识产权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③ 参见刘宁著:《合作作品构成要件与认定标准探析》,《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吴东汉著:《知识产权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④ 在美国版权法中,雇佣作品中的雇主可以被法定的视为作者。
⑤ 在案件审理,第二巡回法院认为没有必要就Taylor行为是否具有可版权性进行分析,而是认为Taylor即使存在可版权性的贡献,由于其不具备合作作者的意图,因此不能成为合作作者。
⑥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三条。
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四条。
⑧ 参见《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
[1] 吴汉东.知识产权法(第三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2] Mary LaFrance,Authorship,Dominace,And The Captive Collaborator:Preserving The Rights Of Joint Authors.Emory Law Journal,2001,50.
[3] Melville B.Nimmer,1 Nimmer on Copyright?Matthew Bender& Company,1998.
[4] [美]朱莉·E·科恩,莉迪亚·帕拉斯·洛伦,鲁恩·甘那·奥克蒂基,莫林·A·奥罗克.全球信息化经济中的著作权法[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5] Paul Goldstein,Copyright:Principles,Law,and Practice?Matthew Bender& Company,1989.
[6] Roberta Rosenthal Kwall,The Author As Stewardquot;For Limited Timesquot;.The Trustees of Boston University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2008,88.
[7] Childress v.Taylor,945 F.2d(2d Cir.N.Y.1991).
[8] Gaiman v.McFarlane,360 F.3d(7th Cir.Wis.2004).
[9] Teresa Huang,Annual Review 2005:Part II:Entertainment Law And New Media:V.Copyright In Entertainment Law And New Media:A.Note And Brief:Gaiman v.McFarlane:The Right Step in Determining Joint Authorship for Copyrighted Material[J].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2005.
[10] 冯晓青,廖永安.合作作品法律认定新探[J].知识产权,1994,3.
[11] 于伟.合著作品的认定标准[J].法学,1990,12.
[12] 李迟善.合作创作决定著作权共有[J].著作权,1991,12.
[13] 张佩霖.认定合作作品及著作权共有的法律界限再探[J].政法论坛,1992,1.
[14] 刘春田.知识产权法(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5]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川民终字第668号民事判决书.
[16]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1990)川法民上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
[17] Thomson v.Larson,147 F.3d(2d Cir.N.Y.1998).
[18]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6)朝民初字第13440号民事判决书.
[19] H.R.Rep.No.94 -1476(1976).
[20]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995)高知中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
[21] Laura G.Lape,A Narrow View Of Creative Cooperation:The Current State Of Joint Work Doctrine.Albany Law Review,1997,61.
[22] Aalmuhammed v.Lee,202 F.3d 1227(9th Cir.Cal.2000).
(责任编辑:黄春燕)
The Authorship of Joint works
Chen Ming-tao
(Law schoo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ommunications,Beijing 100044)
Although currently no universal guidelines exist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or not a person's contribution to a copyrighted work constitutes joint authorship,the act of collaboration and the intention of collaboration are still two crucial criteria.To this end,the two core elements should be analyzed in depth,in onler to establish the correct judgment standard,thus caused the attention of the judicial practice.
works of joint authorship;collaboration;authorship;joint authors
DF529
A
陈明涛(1980-),男,山东青岛人,法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
1002—6274(2013)06—093—08
【文章编号】1002—6274(2013)06—1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