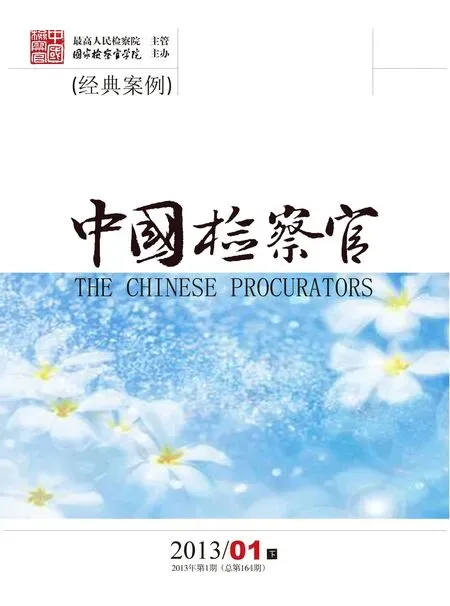将他人占有物误认为是遗忘物据为己有的行为定性问题探析——兼论盗窃罪与侵占罪的界分
2013-01-30蔡雅奇徐梦萍
文◎蔡雅奇 徐梦萍
盗窃罪和侵占罪都是常见罪、多发罪,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着易混淆之处,因此,对这两个罪名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分,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代为保管物的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区别这一视角上,而在行为人将他人的占有物误认为是遗忘物据为己有的情况下,到底该成立盗窃罪还是侵占罪,其判断的切入点又是什么,则关注较少。对于上述问题,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甚至上下级审判机关的观点看法都可能存在分歧,以致出现案件定性上的偏误。因此,对上述问题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并提出简易可行的判断标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盗窃罪与侵占罪的学理界分
根据我国《刑法》第264条和第270条,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占有的数额较大的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或者扒窃的行为。而侵占罪则是指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或者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行为。概言之,盗窃罪的犯罪人是违背财物占有人的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变为自己所有,而侵占罪的犯罪人则是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他人脱离占有的财物变为自己所有。
由于盗窃罪和侵占罪都是财产型犯罪,因此,二者在侵犯的法益和罪过形式等问题上都是相同的,但它们也存在着诸多区别,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如下三点:
首先,二者的犯罪对象不同。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是他人占有的财物,自己已经占有的财物不可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此外,自己所有但由他人合法占有的财物也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例如,将自己所有但已出借给他人的财物擅自取回的行为,应认定为盗窃罪。再如,自己所有但被国家有关机关依法扣押的财物,也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
反观侵占罪,其犯罪对象则为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他人的遗忘物、他人的埋藏物三种。其中,第一种对象可以表述为“代为保管物”,后两种对象可以表述为“脱离占有物”。对于这里的“代为保管”应做实质性的扩大理解,不能过于狭隘。代为保管,说明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委托关系,既包括基于明确的合同而形成的委托关系,也包括基于事实上的委托行为而形成的委托关系;既包括明示的委托保管,也包括默示的事实上的保管。所谓遗忘物,应与遗失物做相同的规范意义上的理解,即“非基于他人本意而脱离他人占有,偶然(即不是基于委托关系)由行为人占有或者占有人不明的财物”。至于埋藏物,则是指埋藏于地下或者藏于他物之中的无主物。如果将他人有意识埋藏于地下的财物占为已有的,只能成立盗窃罪而非侵占罪。
从对二者犯罪对象的差异的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盗窃罪侵犯的是他人的占有权,即将他人占有的财物变为自己所有的财物。而侵占罪则并未侵犯他人的占有权,因为在“代为保管物”侵占的场合,行为人是将自己已合法占有了的他人财物变为自己所有,自然未侵犯他人的占有权,而在“脱离占有物”侵占的场合,由于财物已处于脱离他人占有的状态,因此行为人更是未侵犯他人的占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侵占罪的法益侵害性要轻于盗窃罪。
其次,二者的行为方式不同。盗窃罪是将他人占有的财物变为自己所有的财物的行为,而侵占罪则是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他人已脱离占有的遗忘物或埋藏物变为自己所有的财物,并且拒不退还的行为。简言之,盗窃罪是将他人占有变为自己所有,侵占罪则是将自己合法占有变为自己非法所有。此外,在侵占罪中,“拒不退还”与“变为自己所有”表达了相同的含义,前者是对后者的强调,意在强调行为人将已合法占有的财物变为非法所有的财物的事实。因此,“拒不退还”既可以是表现为作为的方式,也可以表现为不作为的方式。前者如消费、变卖、抵债、毁坏、赠予他人、编造财物被盗的虚假理由从而免除自己的返还义务等,后者如拒不交出、拒不返还、拒不承认等。
最后,二者的犯意产生时间不同。盗窃罪是将他人占有的财物变为自己所有的财物的行为,因此犯罪人的犯意产生于财物尚在他人占有之时。而侵占罪则是将自己已合法占有的财物变为自己所有的财物的行为,因此犯罪人的犯意产生于已合法占有他人财物之后。单从犯意产生的时间先后来看,盗窃罪的犯意产生时间要早于侵占罪。对于侵占罪的犯罪人来说,由于财物已经处于其合法占有的状态,而该状态对犯罪人具有一定的诱惑性,因此主观恶性要轻于盗窃罪的犯罪人。
二、将他人占有物误认为是遗忘物据为己有的行为该如何定性
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于盗窃罪和侵占罪的界分,更多地集中在盗窃罪与“代为保管物”侵占罪之间的区别问题上,而对于盗窃罪与“脱离占有物”侵占罪之间的区别,则论述相对较少。对于司法实践中较为多发的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误认为是遗忘物进而据为己有的行为该如何定性,即到底是成立盗窃罪还是侵占罪,由于涉及罪与罪之间的区分、犯罪构成理论、刑法的基本原则等诸多问题,则更是鲜有涉猎。目前更是没有提出一个清晰明确、操作性强的标准,以作为破解该难题的“钥匙”。
对于这一问题,即在将他人占有物误认为是遗忘物据为己有的情况下,到底该成立盗窃罪还是侵占罪,笔者提出一个简易可行的判断标准:如果这种 “误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应成立侵占罪,反之,则成立盗窃罪。主要理由有两点:
第一,这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虽然不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但它也是认定犯罪的一项重要原则。根据该原则,在判断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等问题上,必须将主观认识内容与客观案件事实紧密结合起来,既不能只看客观要件,也不能只看主观要件,而应该在客观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内容,并在二者相统一的范围内决定是否成立犯罪以及成立何罪。那种只看客观案件事实而忽视行为人主观认识内容的做法,可称之为客观归罪,反之,那种只看主观认识内容而忽视客观案件事实的做法,则可称之为主观归罪。客观归罪和主观归罪的做法都是片面的,错误的。
就盗窃罪和侵占罪而言,虽然二者的客观要件有一定的重合之处,即都是将他人的财物变为自己所有的财物的行为,但盗窃罪的行为人还必须具有窃取他人占有的财物的故意,即主观上具有将他人占有变为自己所有的意思。而侵占罪的行为人只具有将自己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遗忘物或埋藏物占为己有的故意,即主观上具有将自己合法占有变为自己非法占有的意思,其在主观上根本就没有侵犯他人占有权的罪过,缺乏盗窃罪的主观违法性。因此,当行为人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误认为是遗忘物而据为己有时,如果这种 “误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则只能在主客观相统一的范围内认定为侵占罪,反之,则应成立盗窃罪。
第二,这符合犯罪构成的相关刑法理论。将他人占有物误认为是遗忘物据为己有,实际上是犯罪构成中的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问题。所谓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是与具体的事实认识错误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具体是指行为人所认识到的事实与客观实际上发生的事实,分别属于不同种法益,二者已经超越了同一种犯罪构成。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实际上存在两种类型:一是主观方面轻而客观方面重,二是主观方面重而客观方面轻。前者的典型例子就是行为人主观上只具有盗窃一般财物的故意而实施窃取行为,客观上却发现所盗对象为枪支弹药;或者主观上基于侮辱尸体的故意而实施奸淫行为,事实上被害人当时并未死亡。与之相对,后者的典型例子就是行为人主观上基于盗窃枪支弹药的故意而实施窃取行为,客观上却发现所盗对象为一般财物;或者主观上基于强奸活人的故意而实施奸淫行为,事实上被害人当时已经死亡。
在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的场合,应当在故意内容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的范围内,即应当在主客观相统一的范围内,来认定犯罪。因此,在客观事实是重罪,主观认识是轻罪的案件中,要判断重罪的客观事实能否评价为轻罪的客观事实,如果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就应认定为轻罪的既遂犯。因此,将他人的占有物误认为是遗忘物据为己有的行为,实际上属于客观事实是重罪(盗窃罪),主观认识是轻罪(侵占罪)的情况,当行为人的“误认为”合情合理时,只能成立轻罪,即侵占罪,反之,则应成立盗窃罪。
三、对典型案例的分析
根据笔者的观点,当行为人将他人占有的财物“合情合理”的误认为是遗忘物而据为己有时,应成立侵占罪,反之,则应成立盗窃罪。以此观点为基础,结合案例做具体分析。
[案例一]庄某系社会无业青年,几乎每天都出入某地县城的“极光速网吧”上网打游戏。2007年4月14日早上7:30,该网吧刚开门营业,庄某就第一个进门,在完成了正常的验证、缴费等手续后径直来到8号电脑前。这时,庄某突然发现电脑桌上有一个LG KG90型号的手机(价值人民币3600元左右),就偷偷地将该手机据为己有。事实证明,该手机是网吧老板早上打扫房间时放置在8号电脑桌上的,而庄某始终声称自己以为是前一天晚上其他玩家遗忘在该网吧的手机。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庄某成立盗窃罪。庄某将老板占有的手机误认为是其他玩家的遗忘物,这种“误认为”并不合情合理。首先,该案件发生的时间是早上7:30网吧刚开门营业时,行为人第一个进入网吧,从社会一般人的观念来看,不太可能发生其他玩家遗忘手机的事实;其次,即便真的是前一天晚上其他玩家遗忘的手机,该手机也应该转移给建筑物的管理者,即网吧的老板占有。理由在于: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即使原占有者已经丧失了对财物的占有,该财物也应自动转移给建筑物的管理者占有。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该手机都应该由网吧老板占有。因此,犯罪嫌疑人庄某虽然在主观上将老板占有的手机误认为是他人的遗忘物,但这种“误认为”,无论从刑法理论,还是从案件客观事实,抑或是从社会一般人的观念来看,都是不合情合理的,因此只能成立盗窃罪。当然,如果在其他案件事实不变的情况下,将本案发生的时间由早上7:30改为其他时间,例如改为“网吧已营业三个小时之后的10:30”,那么行为人发生认识错误就是“合情合理”的,则应考虑成立侵占罪。
[案例二]陈某是某公交线路的司机。2009年7月28日上午,陈某在驾驶公交车时,将自己的手提包放在了离自己不远的第一排乘客的座位上。犯罪嫌疑人何某于9点左右上了该公交车,由于无座位,就一直站立在车厢前侧。在多名乘客上下车后,何某发现该手提包一直无人认领,于是趁人不备将该包占为已有 (内有现金、身份证、信用卡等,共计价值人民币14800余元)。司机陈某发现自己的手提包丢失后立即报案,当侦查机关找到何某时,何某拒不承认,且一直坚称自己以为是前面乘客遗忘在该公交车上的手提包。
本案中,何某虽然在客观上实施了将本归司机占有的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但其在主观上却将该财物误认为是其他乘客的遗忘物,而且这种 “误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应成立侵占罪。理由主要有三点:首先,从社会一般人的观念来看,在公交车这一开放的空间内,个别乘客遗忘财物是很正常的;其次,从具体案情来看,在“多名乘客上下车后,该包一直无人认领”的情况下,行为人形成“该手提包应该是其他乘客的遗忘物”这一主观认识,也是合乎情理的;最后,从刑法理论的角度而言,行为人主观上只具有侵占他人遗忘物的主观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占有他人占有物的行为,无论是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还是根据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结论,都只能成立侵占罪。
[案例三]杨某是某地有名的女富豪,平日穿着打扮时尚。2008年8月7日,杨某在自家阳台上(13层)摆弄新近购买的金镯子(价值人民币21000元)时,不小心将金镯子滑落至楼下的人行道上。杨某边喊丈夫来盯着金镯子,边急忙跑下楼拾捡。恰在此时,犯罪嫌疑人温某路过此地并发现了该金镯子,遂捡起来据为已有。归案后,温某拒不返还,说自己以为是其他路人丢失的金镯子,且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早已被杨某的丈夫“尽收眼底”。
本案中,温某成立侵占罪。在路上行走时偶然发现他人遗忘的财物是正常的、合乎情理的,据此占为己有的行为,由于只具有侵占他人遗忘物的主观故意,因此只能成立侵占罪。当然,在阳台上一直盯着金镯子的杨某的丈夫如果朝行为人喊了一句类似“别动,那是我们的镯子”之类的话之后,行为人仍然将财物据为己有的,则只能成立盗窃罪。因为当他人喊了类似上述意思的话之后,足以说明该财物仍然由他人占有,毕竟,占有的意思对占有的认定起补充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主观上明知该财物由他人占有,客观上仍实施将财物占为己有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当然应成立盗窃罪。
注释:
[1]季翔虎、蔡永彤:《侵占罪中“代为保管”认定的难点与消解—兼论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分野与厘定》,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年第11期。
[2]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04页。
[3]至于“合情合理”的判断标准,则应该在综合考虑案件的各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以一般人的认识为评断标准。可供参考的评断标准包括但不限于:犯罪行为发生的时间是否足以使行为人的“误认为”显得具有合理性;犯罪行为发生的空间是开放空间还是封闭空间;作为犯罪对象的财物的形状、尺寸、大小等是否足以使行为人“误认为”是遗忘物;行为人获得财物之后的行为表现,等等。
[4]同注[2],第255—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