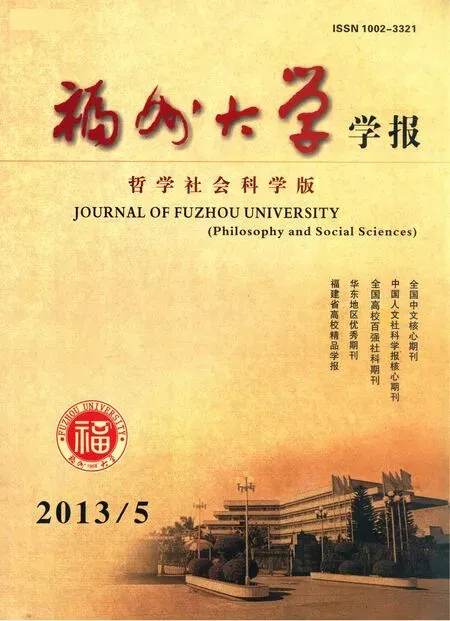意象油画的本源与逻辑探微——兼论意象绘画的阙值
2013-01-25冯巍朱峰
冯 巍 朱 峰
(1.福建广播电视大学,福建福州 350001;2.南昌航空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江西南昌 330063)
意象油画是近年来我国美术界提倡的绘画理论,针对于抽象或是具象艺术,其创作目的是为了达意(表达“至理”),绘画的性质既不是对描写对象的再现,也不是单一的情感表达,而是通过“表意于象”的方式创造“表意之象”。[1]不过,我国传统绘画的意象特征向来明显,为什么会在当代受到重视,并且出现在西画领域,这是有一定原因的。
该理论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对中西绘画异质同构关系的需要。[2]由于油画在我国作为一种从西方舶来的艺术形式,自登陆伊始便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来自传统意象审美意识的反向渗透,它既是民族审美自我防范心理的物化外显,更是油画作为典型外来文化的本土化适应与改良。是故,不少意象油画研究多立足于“民族性”与“本土化”视角,若作为意象油画的形成原因与环境研究,显然是必要的。
然而,本源自《周易》中的意象概念究竟在意象油画中有多大成份的体现,尤其是当代意象绘画毕竟不同于传统的写意绘画,与西方具象、抽象、表现、象征等表现手法亦有所区别。那么,我们要问:意象绘画是如何界定的?它的边界何在?该怎样划分美术作品的抽象、意象或者是表现特征?
一、“民族性”与“本土化”追求不等同于意象
民族性与本土化的追求集中反映了我国油画创作群体的学术自醒,如果说这种自醒在刘海粟、林风眠等老一辈油画家年代还停留于潜意识认知意向的话,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是伴随着以董希文为代表的油画中国风命题的提出以后[3],日渐成为国内艺术家所共识的审美研习基本视角。绘画的意象特征便是在这种视角的认知下挖掘而来的,学界普遍认为,“意象油画”其实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油画民族化提法和90年代在全球化背景下本土化提法的延续和变种。[4]
很显然,意象绘画(一般情况下,本文更愿意使用此术语,因为相对于意象油画,其适用范围更广。)的提法似乎绕不开民族性与本土化命题,但是,在当代全球文化一体化的前提下,艺术本应是不分彼此的,即便是杰格德最初提出“以非洲为中心”的本土化艺术审美策略时[5],依旧未能达到摆脱欧洲中心倾向的现实结果;对于中国而言,文化民族主义必然是文化多元主义即文化地域主义,一个抽象的大一统的传统的民族文化,同样令人怀疑。[6]更详尽的论证可参阅王林与顾丞峰的相关论文,在此不再赘述。
本文所关心的是:难道就不能脱离开民族性与本土化命题理解意象绘画了吗?答案是肯定的。意象概念自古有之,民族性与本土化视角仅仅是发现而不是发明了它。意象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典型视觉逻辑规律之一,必然具有其普遍性与普适性特质,民族性与本土化提法限定了它的普适性。试问难道可以关起门来不让西方学界涉入(在此为第一人称视角而不是作为亚洲文化研究的旁观视角涉入)?其实,西方对意象的相关研究亦从未间断,只是未如我国传统文化审美中这样具有体系化,但是作为另外一种文化视角的摄入,他们的不少研究成果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结论:无需将意象和民族性与本土化等同,全球化语境的认知可以否定后者,但不一定要牵涉前者,意象绘画在概念上是可以调整并谓之为道的。
二、围绕意象绘画而展开的学术争鸣
意象与具象、抽象概念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苏天赐认为意象是指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的形象表达形式[7],孙宜生在《意象艺术论纲》中持相似观点[8],曹桂生特就此在《西北美术》上两度撰文质疑[9],孙宜生则均在同期刊物上给予了回复[10],形成了激烈的学术争鸣。
学术界对意象绘画的争论颇多,此为一例,早些时候艾中信、詹建俊对董希文、倪贻德在上世纪60年代左右提出的油画民族化反思亦算一例[11],近期尚辉、梁江与王林、顾丞峰的本土与年代之争则更为热烈。如此众多的争议一来说明了学界对意象的重视程度,二则反映出意象绘画在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对此,本文的理解是:
首先,就意象本身谈意象绘画,在基础概念的逻辑整合尚未完成之前,先别忙着加载过多的外延,别急于插旗子、下定义。概念应越清晰越好,“一个概念的外延无限扩大以后,内涵将会同比例地缩小。”[12]外延的加载必须依赖概念本源的逻辑支撑(严谨的推论是加载的唯一有效途径),脱离了原初概念的外延尽管也必然有其提出的动因与内在逻辑性,但由于与本源在联系上的不紧密,当遭遇实证或是质疑环节时再来寻求回溯推导就很容易与原初概念割裂,一旦割裂形成,对外延定义后的所有工作都将飘絮化,进而堕入理论大厦基础层被架空后的坍塌。
其次,暂且不论意象的归属,而应尊重概念的普适性,也即是适用应广泛、越具发展潜质越有效。将某一普遍概念区域化、种群化的做法对将来的艺术史研究或许有效,但对于概念本身来说是自我束缚,也即是对意象竖起的所有屏障都是“固步自封”,应尽快去除,唯有如此,方可有利于意象绘画的发展以及意象概念的国际化共识。
再次,意象中的“象”为表意样象,所指不仅仅是形象,更多的是现象与心象;而意象绘画所追求的“象”为艺术形象,两者具有形而上下间的本质区别。也就是说,研究意象概念,要多运用形而上哲学思辨;探索意象绘画,要多采取可实证的形而下科学态度。意象绘画是意象概念的适用范畴,同样理由,如果在艺术世界切实产生意象流派的话,未必就一定是意象油画,可以是其他画种、也可以是其它艺术表现形式,正如英国在20世纪初亦形成了以休姆(T.E.Hulme)与庞德(Ezra.Pound)为代表的意象派诗歌。
因此,对意象绘画的研究应立足于视觉规律与艺术创作的实证需要,博采众长,努力揭示意象的生理与心理成因,并运用于艺术表达行为,形成目标明确、有迹可循的创作方法、审美规律以及评价体系。
三、意象的心理与生理成因
就“象”的层面来看具象、抽象以及意象皆有着接受阶段与表达阶段的区别,在形成上是有先后差别的。下面,我们以婴儿的感知与表达状况对其形成时序加以分析:
1.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当婴孩还未出生时,便具备了一些基本的感知能力,如听觉、触觉等等,并由此产生了选择性意向(喜好倾向)。
2.视觉感知能力则需要建立在第一次睁眼之后,或许是因为涉及感知器官的复杂程度所决定,通常认为视觉是最后产生的感知能力(至于味觉产生于第一次吮吸还是在母体内尚未发现心理学相关实验数据支持)。在此阶段,便获得了关于“象”的最初状况——具象接受,比如一张母亲的脸。
3.在选择性意向的驱使下,婴儿所要做的最早的工作便是将具象感知转化为抽象化认知,如“什么是什么”、“什么可以怎样”,并以此确保吮吸、触摸的准确程度。尽管我们认为抽象是从众多的事物中抽取共同特征与本质特征的研究方法,但是实际上首次感知便可进行抽象:“一个儿童也许仅看到过一只狗,但刚一看到这只狗时,他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关于狗类的清晰概念(虽然这个类,仅包含一个成员)。”[13]抽象的结果是形成概念,虽然这个概念不一定准确。婴儿所形成的概念不可能是文本形式,而属于具有可识别特征的觉知范畴,如通过抽象化活动形成抽“象”(形象)记忆。
4.在思维活动中的样象便可称为意象,前面所提及的具象与抽象均停留于感知与接受而非表达环节,儿童涉及“象”的表达最先是通过意象图示来实现的,即在未经历任何沟通符号化的外部学习时,最准确、便捷的达意方式便是意象图示。为了表达意图,儿童与原始人最先采用了意象的方式,通过对古代岩画的分析可以获得意象的图示化基本方法:(1)对基本形态在具象的基础上抽象处理;(2)突出典型样象差异以区分相似含义;(3)通过极简化与范式化处理以强调造像意图的权重。
由此可见,意象绘画的产生是出自表达的需要,早期的意象或许与具象表达能力的欠缺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其目的亦是为了“立象以尽意”[14]而不是再现,在对形象的极简与范式追求过程中许多原始部落产生了诸如象形文字一类的意象图示的符号化延伸。可以认为:感知、选择的意向性、具象接受、抽象概括、记忆、表达环节是意象形成的先决条件。
意象发展所遵循的逻辑规律是艺术逻辑而不是科学的形式逻辑,多有象征、借代、通感与联觉等投射式表达而放弃对精准程度的要求。同时,抽象后概念的摄入使得对意象的感知与接受环节增加了对理解与记忆方面的要求,也即是对意象的接受需要通过对知识的习得与运用才能获得,尤其当意象发展到脱离写实性意念表达形象的阶段,如《易传》中所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的卦象[15],又如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例举的想要制造三角形的一般意念[16],就对知识的掌握有了更高的要求,不仅是儿童,即便是未经专门教育的成人亦无法获得。也就是说,对意象的把握受到理解力与知识水平的限制,不同的阶段将演化出不同的样象与状态。
四、意象是否游离于具象、抽象之外
倘若是要考虑意象是否在具象与抽象两极之间,不妨直接考虑意象、抽象与具象三者间的关系来得更为直接。其实,就具象与抽象是否确如多数学者认为的绘画两极就有待商榷,因为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大多数“非此即彼”的二元论逻辑都因在判断上的局限性而被消解,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波普尔爵士对决定论的颠覆[17],在绘画中所认知的具象与抽象间的对立关系将面临同样的诘问。
就目前情况来看,阿恩海姆将具象与抽象对峙视为“一种极为有害的二分”无疑是正确的:“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具体’和‘抽象’这两个字眼把经验对象划分为两大不同领域,它们二者既不是一对反义词,也不是指两类相互排斥的东西。‘具体性’是一切事物都具有的性质,而在这一切事物中,有好多东西都可以成为抽象的。”[18]所有证据可证实具象与抽象的关系划分仅仅是认知时序上的前后关系而不是概念上的。一个简单的比方:临摹一幅康定斯基的作品,其所有要素无论形状或是色彩对我而言都具象的;同样,在进行具象再现创作时,当第一根线条落在画幅上就决定了其抽象特性(摄影中的理化转换关系是否属于抽象还须进一步确认)。若是非要在适用层面上将两者加以区别,那么或许可以这样认为:抽象源于具象,具象认知早于抽象并涵盖之。
同理可知,意象源自抽象,凡是意象的内容都具备抽象的特征,但并不是所有抽象内容都能被纳入意象。然而在时序方面,东西方在理解上有着较大的不同,西方理论重视由抽象介入象征的方式产生意象,意象中的“象”与“意”属于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也即是目标意象的视觉特征与代表内涵是可以分离与给派的。阿恩海姆就曾指出意象具有三种功能:作为绘画、符号以及记号[19],它们的区分方式就是其抽象性、内涵与形态间的再现与切合程度。与此相比,东方在对意象的理解上显然要复杂与整体得多,意象即为意象,意象本身既是象也是意,而无需也无法对其内涵给予文字性解码。象为道生,可感知、可参悟、可表达,但不存在主观给派环节,也就没有时序上的前后关系。并且,意象没有规定程式,所谓“象其物宜”,更多的是强调整体“意境”而非形态。
下面,我们试着用图表与公式的方法来进一步解释以上认识:
1.就生成关系来说,“象”始于具象并止于具象
这是以心理意象为中心的表达式,抽象与具象作为意象与现实沟通的操作手段,其中意向性主要涉及情绪、认知、愿望等三种主观因素,它们影响着觉知与表达结果。最终,作品将以具象的样状呈现。如下所示:

2.作品的样象分类

具象(作品)再现(无情绪) 表现(有情绪)现实(有概念) 抽象(有概念) 浪漫(有概念)写实(无概念) 冷抽象(无内涵) 意象(有内涵) 热抽象(无内涵) 涂鸦(无概念)符号 象征
此处情绪为将个人内心情感融入艺术的创作手法,如具象表现或抽象表现创作;概念为抽象后获得的共性认知,是意义的载体,重视作品意义的创作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或是抽象创作;内涵可相对于外延来理解,为概念的内在属性,具有模糊性与指代特征,有时候相同的表达在不同的语境中是不同的含义,所以意象必须通过“境”的营造方能实现准确表达。当然,一件作品往往具备各种样象,需要根据其侧重划分。
3.意象思维与意象作品
在心理与意识环节所有思维活动均为意象性的,唯有可形成记忆的具象、抽象内容方可被意象化,当然也可以依据侧重细分为具象思维、抽象思维以及意象思维等等。我国传统绘画所追求的意象性便是思维意象的直接表达,通过“象”来摹写“意”,是对意的具象化,作品最终的视觉呈现将由以下内容组成:

稍加留意就能发现,凡是间接摹写类作品都多少包含以上内容,这一方面说明意象性是创造性绘画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传统写意绘画中尤为明显;另一方面,感知记忆表达的要求可用于区分纯抽象以及非绘画类意象作品,如抽象形、符号、记号、书法等艺术形式;经习得知识引导绘画是意象绘画的先决条件,它控制着感知与表达的切入视角,它可用于区分直接摹写类作品,如临摹、写生;而在表达过程中技法与行为的要求恰恰是意象绘画重“意”轻“象”的体现,它可用于判定一般性赋意表达还是纯意象创作,如象征作品中的隐喻与暗示均为局部意象,却不是以意为本的整体、全局性意象绘画。
五、悬而未决,呼之欲出
当对意象绘画的理解涉入了意象油画的内容以后,实际上既是将传统审美体系置于西方绘画语境,其结果势必诱发对传统意象认知的全新理解。当下对意象绘画的解释众多,有些出自字面理解,有些根据典型作品样象,更多的是源于由《易经》演化而来的意象哲学审美认知,这些解释虽不尽相同,但皆从各个方面对意象绘画给予了有效界定。不过,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对意象绘画给予明确的、清晰的、普适的概念依旧是一项悬而未决的研究课题。
我国传统意象概念博大精深,无论是用于审美抑或儒道与禅宗的哲学方面,由于意象概念自身的复杂程度与“意会”特征,要想通过文本彻底描述清楚就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本文无意重新界定意象绘画的概念,而仅仅是以当代视角多方向地追问意象绘画的阙值,探际的结论与传统认知有着较大的差别,并且由于对“意象”选择语境的不同而产生出相应的差异甚至背反。作为对意象绘画的针对性认知补充,这样做有利于对意象本质的无限接近并使之呼之欲出,正切合了“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20]的意象观点。
注释:
[1]曹桂生:《意象范畴考辨——意象概念的嬗变与重整》,《人文杂志》2001年第6期。
[2]尚 辉:《意象油画百年》,《美术》2005年第6期。
[3]董希文:《从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谈到油画中国风》,《美术》1957年第1期。
[4][7][12]顾丞峰:《意象油画,形而上还是形而下?》,《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
[5][美]Dele.Jegede,“Art for life’s sake:African art as a reflection of an Afrocentric cosmology”,The African aesthetic:keeper of the traditions,edited by Kariamu,Welsh.Asante,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94,P237 - 247.
[6]王林:《意象油画及油画民族化思考文艺研究》,《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
[8]孙宜生:《意象艺术论纲》,《美术》1992年第1期。
[9]曹桂生:《意象新释──兼评孙宜生先生的“意象艺术”观》,《西北美术》2000年第4期;《再评孙宜生先生的“意象艺术”观》,《西北美术》,2001年第1期。
[10]孙宜生:《意象艺术观答诘问》,《西北美术》2000年第4期;《意象艺术观答诘问(续)》,《西北美术》2001年第1期。
[11]艾中信:《再谈油画民族化问题》、詹建俊:《“油画民族化”口号以不提为好》,见《油画讨论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 年,第166,187 页。
[13][18][19](美)阿恩海姆(Rudolf.Arnheim):《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滕守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209,203、206,179 -184 页 。
[14][15]《易传.系辞传》系辞上第十二章,系辞下第一章。
[16]洛克(John.Locke):《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90页。
[17][奥]Karl.Raimund.Popper,The Open Universe:An Argument for Indeterminism,London:Psychology Press,1992.
[20]《庄子》第二十六章《外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