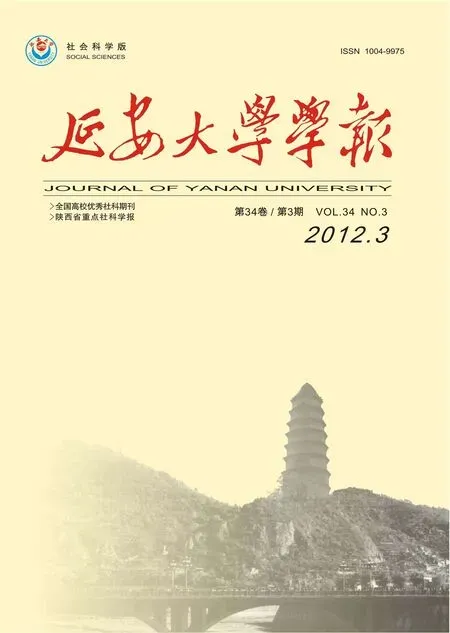解放区以政治标准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模式探析
——以解放区小说批评为考察对象
2012-12-09刘刚圣江震龙
刘刚圣,江震龙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以政治家、军事家的视角与眼光,提出了针对解放区文学格局和未来发展的系统性的规范、要求与原则”;“进一步凸现了‘阶级性’、‘政治化’、‘人民大众’等观念在‘革命’的文艺活动中的极端重要性”;“以文艺的‘革命功利主义’为核心,以革命立场问题为基点,以态度、对象、工作和学习问题为中介,以接受者的接受程度与接受需要为切入口,引申出一系列对立的矛盾范畴和关系”“来展开其基本的理论构架,在二元对立的理论表述中,蕴含着鲜明的倾向性和不同的侧重点”[1]。解放区文学批评按照《讲话》所确立的批评标准来规范与要求特定历史场域下作家创作。《讲话》之前发表的作品也被重新拿来“检阅”,评判其是否遵从《讲话》所规范的原则。《讲话》开启了解放区以革命功利主义来重塑文学批评的重要时期,解放区文学批评逐渐以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强调政治标准一维的单一政治批判,开始生成一种主流批评模式:“以政治标准为中心”的批评模式。“以政治标准为中心”的批评模式具有两个明显的批评操作新成规:“一基点与三维度组合”式批评思路和“真善美与假恶丑对照”式批评逻辑。
一、“以政治标准为中心”的批评模式
毛泽东的《讲话》中把文艺批评定性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提出文艺批评具有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2]。其中“政治标准”有两方面突出的内涵:其一,强调文艺的政治倾向,在抗日救亡的大环境下,对文艺的政治要求主要看“利于抗日和团结”还是“不利于抗日和团结”;“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战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战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民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其二,强调文艺的社会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文学作品好坏分别要看其社会效果,“判断一个作家”,必须“要看实践”,“顾及效果”,“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讲话》作为“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文本”[3],它对解放区文学批评的“明确”规定,必然成为解放区文学批评家及文学批评观念中的教谕式“圣旨”。留给解放区文学批评家的任务,就是如何贯彻《讲话》精神,如何按照《讲话》要求来指导文艺批评实践。
“以政治标准为中心”批评模式即把《讲话》视为文艺批评的“标杆”,当作衡量文艺作品的“砝码”,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奉为文学批评的信条,从政治实用主义角度出发,追求作品的政治倾向及现实社会效应,突出作品既要有鲜明的阶级分析观又要有正确的政治观,把对作品“思想性—政治性”的评判放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功利性地强调文艺成为宣传教育大众的工具,发挥鼓舞激励群众、促进推动革命的政治功用。同时坚持把文学批评逐渐转化为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即把文学批评的职责完全归结为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当然这一批评模式也并非完全忽略文学的艺术问题,它同时也强调文学批评的“艺术标准”,可作为艺术问题的文艺审美鉴赏批评要么淹没在“喧哗”的政治“声浪”之中,要么仿佛蜻蜓点水、稍带提及,或者被降到可有可无的位置,使得文学批评的审美特性逐渐趋于稀薄。至此,《讲话》所强调的“两标准”,在“以政治标准为中心”批评理念作用下的具体批评实践中,往往功利性地、简单化地转变为“唯政治”的单一标准,只有“第一”找不见“第二”。伴随着解放区文学制度的体制化、组织化及行政化进程,文学批评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形式上逐渐“划一化”,规模、程度上逐步体制化、运动化。“它由对文艺的批评完全指向了对于创作主体的思想批判,并转化为一种高度组织化的规训与惩罚手段”[4]。同时被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种工具,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与现实阶级斗争,为工农兵服务,对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思想感情、思维方式及其文学作品的选材范围、风格形式、语言传达等都确立了革命功利主义的询唤规训与批判惩戒功能;推动文学确立塑造新人物、新生活、新思维的典范作家与规范文本的传播接受功能。这是一种典型的革命意识形态批评,强调批评家必须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与革命意识。批评家在对具体的文学文本进行评判时,依据的并不是文学文本自身所提供的实际内容,而是以某种先验性政治预设、革命意识对文本进行功利化的“解读”。批评家已不再依据批评主体性进行“自由言说”,而是作为政治规训下的“媒质”或“中介”,说什么、怎么说已经身不由己。批评家熟练地套用着《讲话》中的批评语汇(革命/文艺、军事/文化、政治/艺术、世界观/创作方法、现实/理想、客观/主观、工农兵大众/文艺工作者、光明/黑暗、歌颂/暴露、赞扬/批评、普及/提高、政治标准/艺术标准等等),并且逐步形成一些新的文学批评概念术语和话语方式(“工农大众”、“工农兵形象”、“正面英雄人物”、“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级斗争”、“阶级关系”、“政治立场”、“政治态度”、“革命”、“党”、“集体”、“真实”、“生活本质”、“片面性”、“通俗性”、“口语化”等等)。这种文学批评模式“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由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它遵从的是政治实用主义的逻辑而非文艺本身的逻辑”[4]。这种文学批评模式的“政治本意”,就是试图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彻底扫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而达到解放区作家作品“纯粹”的“无产阶级化”。
“以政治标准为中心”批评模式的典型代表,就是周扬式的以“权威批评话语”“姿态出现的”“训导式批评文体”[5];“他的批评文章职责在阐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6]。这种批评模式正好印证了伊格尔顿所言的,文学批评不可能脱离思想意识的价值,它总是“某种特定的政治形式”,那种认为存在着“非政治”批评的观念只是一个“神话”[7]。但这一批评模式过分夸大政治,极力在政治与文学间划上等号,造成文学面临被取消的危险。在具体批评操作中,往往遵循“一基点与三维度组合”式批评思路及“真善美与假恶丑对照”式批评逻辑两种新成规。
二、“一基点与三维度组合”式批评思路
“一基点与三维度组合”式批评思路是“以政治标准为中心”批评模式的一种典型批评线路。“一基点”指的是对作品批评总有一个明确的“基点”,即以“政治标准”为中心,始终以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政治观念来解读作品,强调作品的政治倾向及社会效应,突出作品发挥宣传教育大众的工具性职能,甚至把文学过于简单地等同于政治。“三维度”主要指的是人物、主题及艺术技巧三个批评分析作品的维度。“政治标准”是裁定作品价值、合乎规范与否的出发点和归宿,“人物”、“主题”及“艺术技巧”是检验作品“政治标准”切合度的三个路径与批评操作的三个维度。
延安文艺整风过程中,批评者对莫耶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丽萍的烦恼》进行批评时,依据《讲话》精神功利性地把文艺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并且随着批评的日益深入,政治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如果说非垢与叶石的批评意见还稍微显得中肯并且带有一些艺术气息的话,那么沈毅的批评意见则就属于是一种粗暴式的政治评判,他指出这部小说是“一篇含有小资产阶级偏见和歪曲现实的作品”,“已不是莫耶同志个人观念问题,只能说是晋西北学风文风中的一股阴风”;“使许多女同志,婚者与未结婚者统统陷入于五里雾中,而惶惑苦恼,无以自解”[8]。以简单的政治评判取代理性的文学批评,功利性地从政治角度出发,过分苛责强调作品的政治性及现实社会效应,片面突出作品之于大众的宣传教育功用。在具体的批评意见上,批评者指责作家在小说中对主人公“丽萍”和“赵国华”的形象塑造是“缺陷”多于“完美”,“谴责”多于“同情”;批评者认为即使作者原本意图是想说明“一个人能够工作就应该工作,谁也瞧不起不劳而获的人,要使自己进步只有工作”[9],但是小说“冲淡了隐没了”,“作者这一善良的意图”,“使读者所感到的仅仅是作者对于丽萍式婚姻的否定,和对于长式老干部的厌恶”的主题[10];批评者在艺术技巧方面简单地把作品的“失败”归结为作者过分爱惜材料,作品成为“材料的堆砌而不是精心的洗练,形象的罗列;而不是艺术的概括”[10]。甚至有的批评者联系莫耶的家庭出身问题来进行政治批评,不但作品受到不公正的指责、被定性为反党文章,莫耶受到所在部队召开座谈会斗争、被打成反党分子,连刊发小说的《西北文艺》也因此被迫停刊。
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在延安文艺整风中也被重新“审查”,受到不应有的责难。批评者把作品对革命胜利、党的形象、同志团结的有利程度作为评判的唯一标准,虽然承认陆萍形象塑造得比较成功,但是认为作者对陆萍完全是“同情的,无批判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不该是具有个性、主体性的启蒙者,而应该刻画成被改造者,尤其应当突出改造的心灵变化、思想转变过程;批评者功利性地指出:“这篇小说底题材和主题发生了裂痕,从而表明了主题的不明确性”,集中表现“在于对主人公的周围环境的静止描写上,在于对主人公性格的无批判上”,片面强调作品主题必须明确,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批评者虽然承认作者的艺术技巧成熟老练,但细致地指出两处有关“苍蝇”的“景物描写上的错误”,“将个别代替了一般,将现象代替了本质”[11]。
批评者对张棣赓的工农兵题材小说《腊月二十一》的批评,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批判。周扬把小说创作中出现的艺术问题直接上升到思想问题、政治问题的高度加以论断,功利性地从某些政治观念出发,抓住小说中存在的一些缺陷与不足,简单武断、上纲上线地宣判:它“的确是一篇很坏的作品”;作者“站在一个错误的立场”,甚至说“没有立场”也不“冤枉”;小说中所有形象塑造都是失败的,没有把纪有康塑造成英雄,敌人却是“天真可掬”、“还可原谅”;抗日工作人员“凶的可怕”、“十分幼稚”;唯一代表进步力量的牺盟会青年却被刻画为一个“小丑”;小说主题对抗日救亡各方力量团结的强调与对国家意识的突显,被周扬粗暴地断言为是对敌人的“夸饰”,对自我力量的“丑化”;在周扬的政治批评话语中,艺术技巧问题则完全被抛空、从未提及;最后周扬还严厉地指出,希望作者能“展开真实的自我批评的精神”,“联系过去全部的言行,能有一个诚心诚意的深刻的反省”[12]。周扬的批评并不“从具体复杂的社会生活出发,不顾活生生的人物的现实处境和心理状态,而是从若干政治观念出发”[13],一味地对小说人物进行简单化、政治化、概念化设定,对作品的批评进行轻率地“政治裁判”,不仅“一棍子打死”了小说,而且封杀了一个年轻的艺术生命。另外,对小说《意识以外》、《落伍者》等的批评,批评家也都是运用“一基点与三维度组合”式批评思路进行,这里不再赘述。
“一基点与三维度组合”式批评思路,始终突出以政治标准为中心,以人物、主题及艺术技巧为三个批评维度。片面强调作品鲜明的政治性及强烈的现实效应,即与“政治标准”的完全吻合。同时,依据三个维度与“政治标准”的离合程度来裁定作品是否符合规范,突出作品完美的人物塑造、纯粹政治化主题和配合人物刻画及主题阐述所需要的艺术技巧,认为人物、主题能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作品价值,大有“人物决定论”、“主题先行论”之嫌。批评者以《讲话》为理论依据,把《讲话》奉为指导文学批评的艺术真理。而“《讲话》立论的基本逻辑就建基于这‘内’与‘外’的二项分立之上。你是‘内人’,你就必须歌颂‘内面’的光明。你是‘外人’,你才会暴露我们的黑暗。二者必居其一。暴露‘内面’的黑暗者其作品未必伟大,歌颂‘外面’的光明者其作品必定渺小”[14]。解放区作家作为体制内的“公家人”,已成为政治上的“内人”,歌颂“内面”的光明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职责”。而部分作家以“内人”身份暴露“内面”的黑暗,违背既定“规定”,不仅作品必然遭到批判,而且作家也容易受到牵连,被敌视为“外人”。在批评具体操作过程中,“批评者倾向于以事实成规而非审美成规为基础来接收和评价文学文本”,“批评者往往不加怀疑地认定作者=叙述者,作品中人物呈现的立场=作品世俗生活中的立场,作品的思想主题=作者的思想观念”[4]。正是在这一批评观念的引导下,如果作品受到批判,作家也就难逃其责,往往与作品一道遭受质疑、甚至被谩骂打击。至此,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平等的地位被完全打破,作家在批评家面前只能“俯首称臣”、唯唯诺诺。
三、“真善美与假恶丑对照”式批评逻辑
“以政治标准为中心”批评模式中,除“一基点与三维度组合”式批评思路外,还生成一种突显“真善美与假恶丑对照”式批评逻辑。
“对照”即故意把两个相反、相对的事物或同一事物相反、相对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用比较的方法加以描述或说明,这样就能把好与坏、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等的对立面揭示出来,给人们以深刻印象和启示,是语文意义上一种惯用的修辞手法。“真善美与假恶丑对照”式批评逻辑就是基于这一含义,以“对照”思维方式对作品作出判断。片面功利地要求作品纯粹地突显好的、美的、善的、前进的正面,要求作家必须割舍与其相反的方面,或者只能将他们作为正面的“陪衬”。试图使作品达到纯而又纯的通体光亮,从而完成对文学进行想象性的引导、激励功能。这种“对照”式批评逻辑尤其体现在对作品人物形象塑造的批评分析上。批评者指出小说《丽萍的烦恼》中主人公丽萍性格上的缺陷,仅是整个进步的现实中的一小部分的缺点,不应该“通过露骨的艺术形象把它再现出来,加以一般化”,“作者忽略了同样值得重视的一件工作,没有拿来与另外一种同属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物(无论是女性或男性)所具备的积极的,热情的,叛逆的,渴慕自由与仰望光明的浪漫气质(如‘丽萍’的偕随‘林昆’向一个最进步的地方出奔就是一例)相对比,以致徒然片面地强调了她的缺陷,变成革命队伍里没有远见自甘堕落的多余人”[10]。同样,作者在自我“辩护”中也不无真诚地坦白:在创作过程中“忽视了以整体的进步现实中的肯定人物来作对照”[9]。
批评者评论小说《落伍者》中主人公伙夫老王形象塑造时,一口否认八路军队伍中没有这样的“怪人”、“时代的落伍者”,即使有的话,在八路军的教育和感化下,也会变成一个时代的前进者、英雄式的人物。批评者所依据的是《讲话》规范,即对工农兵形象的塑造应该把他们描述成“纯粹”的“英雄”,即使这个性格有缺陷,“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13],更不能对这样的“怪人”给予充分的肯定与“同情”。面对批评者粗暴的功利主义政治批判,作者也以“对照”式思维承认自己所犯的“过错”:“只专心于刻画《落伍者》个人命运的悲剧,而忽视了客观环境正面的描写。只强调表现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的落后意识的错误,忽略了拿光亮的背景作强烈的衬托”[15]。显然,“真善美与假恶丑对照”式批评逻辑要求无论是知识分子形象塑造、还是工农兵形象描写,都应该是积极的、前进的、纯粹的正面的英雄人物,至于人物身上的部分“污点”、“杂质”,则必须通过反复“淘洗”予以清除干净。批评者功利性地强调作品应当塑造“英雄式”的人物形象,树立“榜样模型”,这样才是“典型的表现”,从而完成作品“对内”发挥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的教化作用,“对外”断绝给予敌人提供造谣中伤依据的可能。批评家的初衷委实具有现实合理性与愿望善良性,但却忽略了人物形象塑造的特殊性,作家塑造典型形象方法和途径的丰富多样性。“真善美与假恶丑对照”式批评逻辑片面强调正面英雄式人物的塑造,反映出这些批评者对典型形象塑造的认识尚处于不成熟的发展阶段,也暴露出它并不属于学理意义上的文学批评。
批评家将“真善美与假恶丑对照”式批评逻辑引入批评视野,无非是想通过对“问题”作品的批判而实现文艺批评的规训、惩戒功能,从而完成对解放区新政权、新社会、新生命所应该具有的纯粹光明、健康、先进政治的文学想象。“对内”构成一种“团结力”,号召解放区人民团结一致,为保卫革命果实、建设新社会贡献力量;“对外”形成一股“吸附力”,感召沦陷区、国统区的积极分子,踊跃投身到解放区区的战斗生活中来。批评家这种美好的政治情愫,在战时政治环境下,具有历史的现实性、合理性与必然性。
“以政治标准为中心”批评模式走向极端就会使得解放区文学批评家片面地强调“政治标准”唯一性,功利性地以政治评判来取代文艺的审美批评;与此同时生成的“一基点与三维度组合”式批评思路与“真善美与假恶丑对照”式批评逻辑,一方面容易使得解放区作家可以不惜丢弃自身的人格与良知,一味陶醉于歌功颂德的阿谀之中;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解放区文学作品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以政治标准为中心”批评模式不仅成为解放区文学后期的主流文学批评模式,而且对当代“17年”与“文革”文学批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1]江震龙.解放区散文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59.
[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N].解放日报,1943-10-19.
[3]吴敏.延安文人研究[M].香港:香港文汇出版社,2010:297.
[4]袁盛勇.论后期延安文艺批评与监督机制的形成[J].文艺理论研究,2007(3).
[5]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99.
[6]朱鸿召.延河边的文人们[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222.
[7]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90-300.
[8]沈毅.与莫耶同志谈创作思想问题[N].抗战日报,1942-07-07.
[9]莫耶.与非垢同志谈《丽萍的烦恼》[N].抗战日报,1942-06-16.
[10]叶石.关于《丽萍的烦恼》[N].抗战日报,1942-06-30.
[11]燎荧.“人…在艰苦中生长”——评丁玲同志底《在医院中时》[N].解放日报,1942-06-10.
[12]周扬.《腊月二十一》的立场问题——与张棣赓同志的通信[N].解放日报,1942-11-08.
[13]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312-314.
[14]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8-29.
[15]陆地.关于《落伍者》——自我批评,兼答程钧昌同志[N].解放日报,1942-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