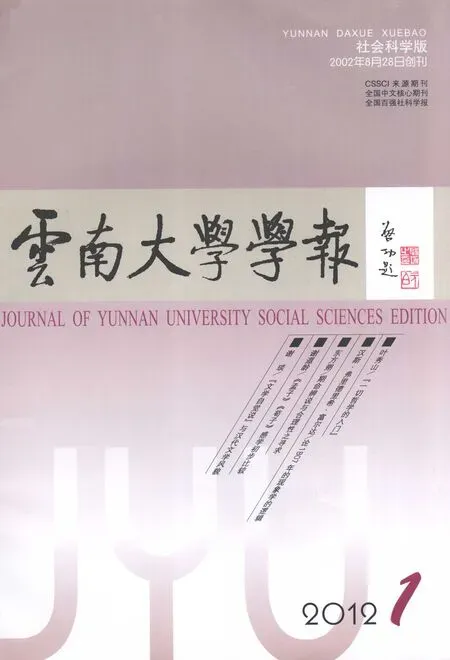亚里士多德论有美德的行动
2012-12-09蔡蓁
蔡 蓁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241]
亚里士多德论有美德的行动
蔡 蓁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241]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美德;行动;决定;慎思
本文依据《尼各马可伦理学》对亚里士多德的有美德的行动的概念进行了分析。通过考察一个真正表达了美德的行动包含了哪些重要因素,且每种要素是如何贡献到一个有美德的行动当中的,以表明一个有美德的行动是如何被驱动的,而一个具体的行动过程又是如何被选定、如何有助于实现整体的幸福的。进而,笔者认为,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做有美德的行动并不仅仅是一个培养习惯的过程,而且必须要求理智上的卓越。
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仅仅知道伦理美德是什么还不足以过一种道德上善的生活,因为伦理美德不同于理智美德,它不是知识而是品格的状态, “形成于对相似活动的不断重复”(1103b 20)。①本文所采用的英译本为Terence Irwin的译本 (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Terence Irwin,Trans.,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85),文中所有引文均根据该英译本译出。因此,伦理美德是和表现美德的行动密不可分的,而一个行动正是因为展现了美德才是值得选择的,从而也是值得赞扬的。这样,真正表现了美德的行动究竟包含着哪些要素,又如何将有美德的行动从不具有这些特征的行动中识别出来,就成为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将把亚里士多德在只是符合美德的行动和真正展现美德的行动之间所做的区分作为出发点,②这个区分受到了罗伯特·奥迪的“出于美德而行动”(Robert Audi's“Acting from virtue,”Mind,Vol.104,No.415,July 1995,pp 449-470)一文的启发。并首先表明,一个行动之所以是有美德的并不在于它所引发的事态所具有的特征,而主要在于行动者的状态,进而,我将分析这种状态包含哪些要素,每一种要素又是如何贡献到一个有美德的行动当中的。但我将不讨论这些要素是否是引发一个有美德的行动的充分条件,而主要关注于一个有美德的行动是如何被驱动、被选定,又是如何有助于促进行动者的整体幸福的。通过这种考察,我将表明理性是如何在有美德的行动中发挥作用的,进而论证,虽然处于灵魂的不同部分的伦理美德区别于理智美德,且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行动来表现,借助于习惯来培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有美德的行动完全是通过习惯化来解释的——习惯化通常又被处理为一个无意的过程,也不意味着表达了伦理美德的行动可以完全独立于理智美德而产生。③就理智对美德的重要性,请参见罗伯特·索拉布吉的“亚里士多德论理智在美德中的作用”(Richard Sorabji’s“Aristotle on the Role of Intellect in Virtue,”in Essays on Aristotle’s Ethics,ed.A.O.Rort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p.201-219)。
亚里士多德在只是做有美德的事情和以有美德的人的方式来做有美德的事情之间作出了区分。他的一个为人所熟知的观点是:人们通过做有美德的事情变得有美德,即“我们通过做正义的行动变得正义,通过做节制的行动变得节制,通过做勇敢的行动变得勇敢”(1103b)。但是,在这里,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如果我们首先不拥有美德的话,我们如何能去做有美德的事情?亚里士多德为了澄清这个问题而做了一个区分,即“仅仅只是做正义而有节制的事情”和“以正义而有节制的人的方式来做正义而有节制的事情” (1105b5-10)之间是有区别的。为了说明这个区别,他采用了学习文法这门技艺作为类比。作为一个文法初学者,他完全有可能出于偶然或者遵从老师的指导而造出符合文法的句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文法家了,因为他完全有可能在另外一些语境下或者在没有老师示范的情况下犯错误,而一个真正的文法家在说出一个符合文法的句子时,他表达了已经内化在他心中的稳固的语法知识。通过这样一个类比,亚里士多德试图表明:作为美德的学习者,我们首先要通过模仿和不断地重复去做符合美德的事情,逐渐培养起做这些事情的稳定的倾向,这种倾向又“引发我们去做相同的事情,表达美德本身” (1104b25),也就是以有美德的人的方式去行动。虽然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要回答的是,我们如何可能在还未拥有美德的情况下去做有美德的事情,但他的论点还是引出了一个相关的区分,即只是符合美德的行动与出于美德而做的行动之间的区别。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区别,让我们以“勇敢”为例来考察这两种不同的行动。在一场战争中,职业军人可能和作为公民的士兵表现得同样的勇敢——他们都能灵活地使用武器,积极地抵御敌人的进攻,但能不能根据这一点就判断他们的行动都展现了勇敢的美德呢?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仅凭这一点是不够的,职业军人可能是凭借他们的经验发现敌人根本不堪一击,因此表现得很勇敢,而一旦局势有所不同,即敌人强于自己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就立刻溃逃了。而作为公民的士兵无论在哪种局势下都会保持坚定,因为他们认为,逃跑是可耻的,而勇敢御敌本身作为高贵的事情是值得选择的。所以,虽然这两者的行动可能在引发的事态上并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根据行动者所具有的不同的状态,前者只是符合美德的行动,后者才是出于美德并真正表达了美德的行动。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对于表达了美德的行动来说,行动本身处于正确的状态并不足以使行动是节制的或正义的。而是说,行动者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必须处于正确的状态下。”(1105a25-30)
那么,究竟什么是行动者所具有的正确的状态呢?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三个条件:“首先,他必须知道[他正在做有美德的行动];第二,他必须选定这些行动,而且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选定这些行动;第三,他必须出于一种稳定不变的状态来做这些行动。” (1105a30-1105b)下面我将依次讨论这三个条件。
我们可以把第一个条件称之为认知条件,认知的内容是和行动相关的特殊的知识,①亚里士多德在不同的语境下多次提到过“在知道的情况下行动 (act knowingly)”,尤其是在讨论不自制者如何可能知道自己所做的行动是不好的却仍旧如此行动的时候,他详细分析了这样的行动者所具有的知识,而这里涉及到的知识是有关事物或行动的价值属性的一般知识或特殊知识,行动者在这个层次上的认知状态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的行为。我将在下文中表明,这种知识主要是在第二个慎思-决定的条件中起作用。而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是把这种认知看作是拥有美德的条件中比较不重要的一项,因为它是拥有技艺和拥有美德的条件中唯一共有的一项 (1105b-5),且它本身并不能充分地将这二者区分开来,因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指的知识更倾向于是指有关一个特殊行动的可感知的知识。包含对情境中的各种特殊要素的感知,这些特殊的要素包括是谁在做这件事情,他做了什么,是针对什么来做的,又是以什么方式做的,采用了什么工具,出于什么样的后果,等等(1111a-5)。换言之,行动者必须知道他所处的情形,并且是有意识地做这个行动。举例来说,如果你从阳台上失手扔下一盆花,而这盆花正好砸晕了一个逃跑的贼,那么,我们并不能说你的行动是勇敢的或者正义的,因为你并不知道这时有一个贼经过,也没有意识到你的举动会有助于抓住这个贼。所以,你只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碰巧做了一件符合美德的事情,因而并不能真正算作是展现了美德的行为。
但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仅仅拥有对行动的各种特殊要素的感知就能就引发一个行动,毋宁说,这只是一个先决条件,引发行动的并不是知识,而是人们在某个特定的情境中想要引发出某种事态的欲望,但并不是任何形式的欲望都可能产生有美德的行动,比如,单纯由激情或冲动所形成的欲望是不可能驱使任何展现美德的行动的。有美德的行动必须是由有理性参与的欲望所驱动的,这种欲望是由慎思 (deliberation)所产生的,亚里士多德把这种慎思的欲望称之为决定(decision)(1113a10),这也就引出了他所说的有美德的行动的第二个条件,即决定的条件。
亚里士多德强调,有美德的行动必须是通过决定产生的,他甚至在其他地方更明确地说道: “美德就是某种决定,或者[确切地说]美德要求决定” (1106a),那么,决定是如何产生的呢?亚里士多德在多处提到决定是慎思的结果 (1112a15,1113a5,1113a10),那么,是不是只要是由慎思产生的决定就能驱动有美德的行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阐明慎思指的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在第三卷的第三章中集中讨论了慎思的对象和方法。在这里,他把慎思处理为通过我们自身的能动性对实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的探究和分析。也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的情形中,人们首先设定一个想要实现的目的,然后通过理性的计算得出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应该采取的最佳手段,从而形成一个决定。但这里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慎思是一种目的-手段式的慎思,它并不参与目的本身的形成 (1112b15),也不保证目的就是一个善的目的。比如说,一个吸毒者以弄到毒品为他当下的目标,他通过理性的计算设计出一套得到毒品的步骤,并按照这个决定去行动,那么,虽然这个行动包含着慎思,但其绝不是一个有美德的行动。因此,作为一个有美德的行动,除了必须经过慎思之外,慎思所指向的目的也必须是善的目的。但这个善的目的又是如何认定的?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又说有美德的行动是出于自身的目的而被选定的呢?
对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亚里士多德有关善的观点。他区分了两种形式的善。一种是无条件的、完满的善,我们并不因任何其他目的的缘故而选择它,它本身就是所有其他的善所指向的最终目的,亚里士多德把它称之为“幸福(eudaimonia)”。与此相对,另一种形式的善就是有条件的善,即,它是善的仅仅因为它有助于实现一个更高的善。比如药物,它们只是因为能够使人恢复健康才被看作是善的,这种善是纯粹工具性的善:药物和健康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药物之所以被选择,仅仅因为它有助于健康,而一旦有任何更好的恢复健康的手段,比如手术或者运动,那么,它就会被替换掉。但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善,它们一方面本身就是善的,另一方面又构成了更高的善。像诸如快乐、荣誉和各种美德就是这样一种形式的善(1097b5)。以美德为例,美德作为一种人类的“卓越”,即便它不会带来额外的好处,它本身也是好的,高贵的,值得选择的,比如,城邦的公民在战场上依然会选择勇敢地战斗,即便这样做不会带来名声和财富;但同时,人们也正是通过培养美德,做有美德的事情而获得幸福。因此,不同于药物和健康之间的这种纯粹手段-目的式的关系,美德和幸福并不是相分离的两种东西,而是美德本身就构成了幸福,是幸福的一部分,同时,它也因其自身的原因而被珍视。①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幸福作为终极目的,它是一个由部分构成的复合体。必须承认的是,是应该把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概念解释成一个包含了两种或多种有价值的活动或善的复合体,还是解释成一个只包含了一种有价值的活动或善——理论沉思 (theoretical contemplation)——的单一的目的,这是有争议的。我在文中采取了前一种解释,在这里不展开具体的证明,就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请参见托马斯·内格尔的“亚里士多德论幸福”和阿克里尔的“亚里士多德论幸福”(Thomas Nagel,“Aristotle on Eudaimonia,”and J.L.Ackrill,“Aristotle on Eudaimonia”in Essays on Aristotle's Ethics,ed.A.O.Rort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p.7-33)。通过这种区分,我们可以看到,幸福是最高的善,所有其他的善——无论是只具有工具性的善的事物还是本身就是善的事物(goods in themselves)——都指向幸福,而其中本身就是善的事物又是幸福的组成部分,但它们是以构成性的方式而不是以工具性的方式有助于幸福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作为最高的善,是人类所有行动的终极目的,有美德的行动必然也是指向这个终极目的的,但单凭这一点并不足以将有美德的行动同其他行动区别开来,因为有些人虽然追求幸福,渴望生活得好,行动得好,但他们却没有能够发现那些构成了幸福且本身就是善的事物,因此,也就无法为自己的行动形成正确的目的。而一个有美德的人则是能够发现究竟是哪些本身就是善的事物构成了作为最高的善的幸福,并由此形成了正确的目标,从而作出正确的决定的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有美德的行动是以幸福为目的的,另一方面又认为有美德的行动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而被选定的。
当我们澄清了有美德的行动的目的所具有的双重性质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对于行动者来说,这些有助于幸福且本身就是善的目的究竟是如何被选定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是实践智慧 (phronēsis)的任务。实践智慧是一种理智美德,它不同于我们上面所提及的伦理美德,而是灵魂的有理性的部分所表现出来的卓越。具体来说,这种理智的卓越状态在于,它能够很好地慎思究竟“是什么促进了一般而论的好生活” (1140a25-28),换句话说,实践智慧是对如何实现幸福的慎思,这不仅是对促进幸福的手段的慎思,也是对构成幸福的要素的慎思,这种慎思为行动形成了一个善的目的,这也是一个有美德的行动的决定性根源。但这样一来,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在第三卷第三章中明确说到,慎思是对促进目的的手段的慎思而不是对目的的慎思 (1112b15),而在第六卷第五章中谈到实践智慧的时候,慎思又被用于目的,那么,如何能对这两种说法作出一个连贯的理解呢?为此,我们有必要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在两种好的慎思之间所做的区分,即,有条件的好的慎思和无条件的好的慎思。这种区分是基于慎思所针对的目的而言的,“无条件的好的慎思是正确地促进了无条件的目的 [即最高善]的慎思,而[有条件的]好的慎思是正确地促进了某些[有限的]目的的慎思” (1142b30)。换句话说,前者是针对幸福的慎思,而后者是针对一些有条件的善的慎思,比如健康和财富——这些善是因为一些更进一步的目的而被追求的。按照这个区分,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一个内涵相对广泛的慎思的概念,即,慎思作为灵魂的有理性的部分功能,是对如何促进目的——既包括终极目的也包括有限的目的——的探究,这种探究不仅仅是要发现实现目的的工具性手段,也要发现构成了终极目的的那些成分,从而为行动找到可以识别的、具体的目的。因此,对一个行动来说,慎思不仅仅参与到手段的形成过程,也参与到目的本身的形成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说,好的慎思是一种正确的思考,必须引出正确的结论,通过正确的步骤,指向正确的目的 (1142b15-30)。当然,亚里士多德也承认,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要达到这种正确的思考,不仅需要对事物属性的普遍知识,也需要对不同处境的具体知识,例如,一个人可能知道勇敢是善的,但他还必须在具体的情境下识别出究竟怎样行动才算是勇敢,并采取恰当的步骤实现这种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对于好的慎思或者实践智慧来说,特殊的知识甚至比一般的知识更重要 (1142a20-25)。而要获得这种针对具体行动的特殊知识,则需要长期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而由于慎思本身是一个理性的活动,因此,这种经验也不是仅仅通过对某一类行动的单纯重复或模仿就能形成的,而是需要一个有理性参与的不断反思的过程。一个能够作出好的慎思的人是一个有实践智慧的人,他能够为自己的行动设定善的目的,并引出正确的决定,这个决定作为一个慎思的欲望引发他去行动。
通过以上对决定以及引发决定的慎思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决定的条件意味着一个有美德的行动必须是由理性的欲望激发的,这个理性的欲望又是由在先的慎思形成的。通过慎思,行动者发现那些有助于实现终极目的,即幸福的诸要素,即一些可识别的、具体的目的;也是通过慎思,行动者设定了实现这些目的的最佳手段。有美德的行动必须是由在这些慎思基础上形成的决定所引发的。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勇敢的行动单纯是由激情所引发的,那么,根据决定的条件,它就还算不上是一个表达了美德的行动,还必须加入恰当的目的和正确的决定 (1117a4-5)。再比如,一个人在战场上表现得不惧死亡,如果这是因为他想以死来逃避贫困、爱欲或者任何痛苦的事物,那么,他的行为也不算是真正勇敢的行为,因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躲避可怕的事物,而不是说这样面对死亡本身就是高贵的、善的,且是有助于实现他所追求的终极善的 (1116a10-5)。
接下来的问题是,有些人即便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通过慎思形成恰当的决定,并由此驱动着去做了一件正义或节制的事情,这个行动也并不一定就真正表达了美德,因为它完全有可能是一个偶然的行动——在境况发生改变的时候,这个行动者有可能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因此,亚里士多德还要求,一个有美德的行动必须是出于稳定的倾向,也就是一个人的品格,由此引出了第三个条件,即品格的条件。美德是一种品格的状态 (1106a10-5,1106b15),这种状态是通过长期习惯化的过程变得稳定而牢固的,因此,有美德的行动并不是分离的、偶发的行动,而是被终极目的整合在一起的连贯一致的行动。但出于品格的行动容易被混同于出于惯性的行动,似乎一旦一种稳定的品格状态形成以后,行动就变成一种不假思索的机械的重复。例如,一个行动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面临突然而来的危险时仍旧保持勇敢镇定,的确很难说这个行动是经过周详的慎思和决定而作出的,它似乎只是一个自发的行动。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这样的行动,它也是一个包含着决定的行动,因为,首先,它不同于一个单纯为欲望所必然化的行动,它并不是被头脑中涌现的最强的欲望所直接驱使,而是必然出于某种理由;其次,虽然慎思和决定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以至于行动者自己都很难清晰地识别出一个理性计算的过程,但是,当我们试图询问为什么他要如此行动,或者他本人在事后反思他的所作所为时,他仍旧会诉诸某种恰当的理由来解释或辩护他的行动。因此,通过习惯化的过程,出于一种稳定的品格来做有美德的事情并不是一个不假思索的,或者说缺乏理性参与的过程。比如,我们似乎把买完东西之后交钱、将垃圾扔到垃圾箱里都看作是一些自发的、不用思考的行为,但如果不是根本上我们把这些行为看作是一个得体的公民生活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并不理性地认同这些行动的话,很难说我们会养成并保持这些习惯。所以,虽然亚里士多德强调,有美德的行动必须是同人的品格中具有稳定性和牢固性的那些因素相联系的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有美德的行动是出于惯性的、不假思索的行动。
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对有美德的行动给出的三个条件并澄清其中可能的疑义,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对表达了伦理美德的行动来说,关键不在于它所引发的后果,而在于行动者的状态,这种状态又包括了认知、决定以及品格三个方面的要素,但无论是哪种要素,理性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美德属于灵魂中能够倾听理性但本身并非理性的部分,并因此主要靠习惯而获得,但通过对展现了伦理美德的行动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伦理美德的展现是同理智的卓越密不可分的。首先,行动者必须对他所处的情境有所感知,拥有有关行动的特殊的知识,这成为他决定并引发一个行动的认知基础;其次,一个有美德的行动的重要特征是,它是由好的慎思所形成的理性的欲望即决定所驱动的,而慎思是灵魂的理性部分所具有的功能,好的慎思不仅是一种目的-手段式的理性计算,也是对幸福的构成要素的慎思,也就是说,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理性的实践功能并不仅仅是为实现欲望寻求手段,而是参与欲望本身的形成,即参与到行动的可识别的、具体的目的的设定。最后,亚里士多德要求,一个有美德的行动必须是出于稳定的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有美德的行动培养为不假思索的、按照惯性的举动,而是说,它仍旧是一个表达了决定的行动,而一种行为习惯的形成与保持,都可以基于它是否有助于实现最高善而开放于理性反思。因此,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给出的有美德的行动的三个条件的探讨,我们看到,有美德的行动并不仅仅是引出了善的结果的行动,也不是单纯通过模仿和重复就能形成的行动,理性在引发和培养有美德的行动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B502.233
A
1671-7511(2012)01-0068-05
2008-03-03
蔡蓁,女,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
■责任编辑/袁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