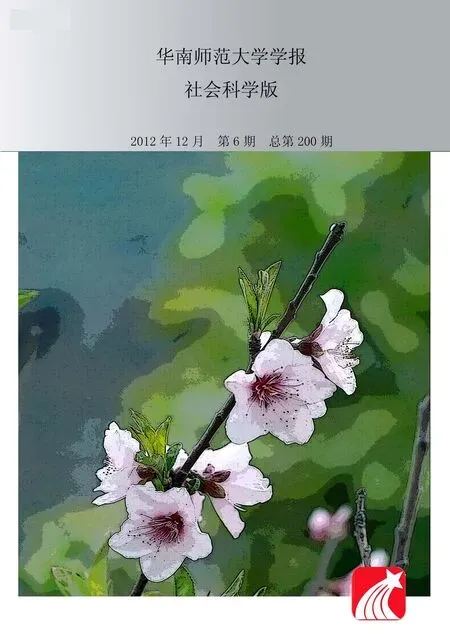唐代士大夫之家在室女的家庭地位
——以唐代在室女墓志为中心
2012-11-21焦杰,胡娜
焦 杰, 胡 娜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近些年来,随着唐人墓志资料被大规模辑录整理并出版,越来越多的唐代女性资料呈现在我们面前,为唐史学界利用墓志研究唐代妇女生活与地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注]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简称《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注]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简称《续集)所收录的5 100余方墓志中,大约有1 400余方以女性为墓主的墓志,其中有66方是在室女墓志。[注]过于简略,只有墓主姓名、生卒年等内容的在室女墓志,不在统计之列。此外《汇编》武德001《女子苏玉华墓志铭》被认为是 “伪”作,但可备考证。因墓主苏玉华生卒年为公元604年-公元619年,主要生活在唐以前,故亦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虽然这66方在室女墓志仅占整个《汇编》和《续集》志总数的1.3%和女性墓志总数的4.7%,但有鉴于中国古代包括唐朝在内的正史及传世文献中有关妇女尤其是在室女的资料十分稀少,故这66方墓志无疑为今人探求唐代在室女的生活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本文即以这66方墓志为中心,辅之以其他相关墓志,并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对唐代士大夫之家中在室女的家庭地位进行详细考察。
一、墓志所见唐代在室女的家庭背景
社会性别学的理论认为,妇女作为一个群体并不是铁板一块,她们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会因阶级、身份、种族、宗教、教育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在父权制的社会里,女性即使自身非常优秀,也很难确定其独立性的地位。她们的身份必须被贴上父或夫家的标签才得以彰显。所以,要想通过墓志了解唐代在室女的家庭地位,必须了解她们所属的社会阶层。唐代社会风气尽管相对开放、文化兼收并蓄,但父权制家庭仍然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因此要想了解唐代在室女的情况,首先要做的必须是了解她们的家庭背景。在唐代,虽然士族门阀已经没落,但矜夸标榜之风仍然存在,表现在碑刻墓志里,总要追述碑主或墓主的家族世系和仕途履历,在室女的墓志也是如此。这种记载方式虽然体现了女性依附于男性的社会现实,但却为今人研究历史上女性群体中的阶级差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在本文正式利用这66方室女墓志进行探索和阐述前,首先要对墓志所反映的在室女出身情况作一个详细统计,这样会有助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更为客观。
墓志中士族室女的出身情况统计如下表。

表1 墓志所见士族室女出身情况统计表
从墓志所见室女出身情况统计表中我们可以知道:66方在室女墓志所载68位在室女中有16位出自当时的山东五姓,即太原王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2位出自博陵崔氏;44位出自陇西李氏、京兆韦氏、京兆杜氏、河东柳氏、河东裴氏、弘农杨氏、河南独孤氏、清河张氏、彭城刘氏等二三流士族。当然,由于受六朝以来士族门阀矜夸之风的影响,唐代有冒充士族的做法,所以上述在室女的出身并不是百分百真实的。但山东五姓中的崔、卢、李、郑、王[注]唐代墓志中有这样一种情况,有姓王氏且为太原人,在墓志中也称太原王氏。表中《汇编》咸通017墓主外祖为清河崔氏,必是太原郡王氏无疑,《续集》大中023不好判断。及与清河崔氏同出一宗的博陵崔氏一般是难以冒充的;而京兆韦氏、杜氏及弘农杨氏因地处关中,河东裴氏和柳氏支系较少,且名气较大,河南独孤氏也是小姓,且地处东都,想冒充并不是太容易;琅耶支氏出自西域,不需要费心冒充。能冒充的也就是乐安孙氏、安定张氏、南阳樊氏、彭城刘氏等名气较小的士族。所以上述在室女基本可定为士族出身。退一步来讲,就算她们的士族出身有不少是假冒的,但她们的父祖基本上都曾是出仕为官的。另外6位在室女虽然不是出自名门,但她们的父祖或亲属也都有入仕为宦者。唐代入仕途径除了军功之外,不是门荫就是科举,中唐以后基本上以科举为主。因此,这66方墓志主人的出身都可以划归为封建士大夫家庭,而且绝大多数属于社会的中上层。所以这些墓志反映的是唐代士大夫家庭中在室女的情况。
上述66方墓志有些在室女不仅出自同一姓氏,而且还有更为亲近的血缘关系。比如《汇编》显庆079《张氏亡女墓志铭》[注]《汇编》显庆079《张氏亡女墓志铭》载张婉卒于“□庆三年六月十一日”,编者误以为“显庆三年”而系于显庆年中,根据《汇编》开成041和大中099墓志可以断定张婉的卒年应为”长庆三年”。的殇女张婉和《汇编》开成041《有唐张氏之女墓志铭并序》的殇女张蝉同为张士阶的女儿,《汇编》大中099《唐安定张氏亡女墓志铭并序》的殇女张婴为张士阶的孙女;又如《续集》大中016《唐故臧李氏故第二女墓志铭并序》中的殇女李国娘和《续集》大中061《唐故陇西李氏女墓志》的殇女李第娘同为李胤之的女儿;还如《汇编》大中113《支氏小娘子墓》的殇女支子璋为支竦的女儿,《汇编》大中114《支氏孙女子墓》的殇女支子珪为支竦的孙女。这种情况说明,唐代士大夫家庭为未嫁而死的女儿撰写墓志现象比较普遍,在很多家族中属于一种惯例。
唐代墓志属于传记性质的文体,是记载墓主姓名、出身、生平事迹、生卒年及人品才学和功过评价的哀悼之文。这些早夭或年长未嫁的在室女受“在家从父”的伦理约束,其活动范围一生未离家庭的樊篱;加上有的室女生命极其短暂,所以墓志内容相对简单,基本为她们在父母家生活的情况、个人才学修养及行事人品方面的简短介绍和评价。但也部分地涉及到了在室女的家庭教育和家庭权力与地位以及她们与父母兄弟等亲属关系等内容。墓志往往是墓主的亲属所作,或是受墓主亲属的嘱托而作,所以在谈及墓主个人道德品行及才学修养方面往往充斥着大量的套语和溢美之词,可能与墓主的真实情况并不完全相符。但透过这些套语和溢美之词可以考察唐代士大夫家族对在室女性教育的导向意图,因而也可以用来探讨唐代主流社会对女性的理想化期许。而那些在室女与亲属关系及其日常生活方面的记载则比较客观,可以用来考察唐代士大夫家庭中在室女的真实情况。
二、墓志所见在室女的家庭教育
在初唐开放的社会风气下,女性受礼法约束较小,上层社会妇女妒悍现象时有发生,以致于出现女皇武则天、韦后、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等皇家女性参预政治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女性都可以享有这种权利。从前一节的分析可知,墓志中的在室女大多出自士族家庭,其中一等士族山东五姓亦占一定比重,这个出身无疑会对在室女的教育影响较大。陈寅恪先生指出:“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注]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第 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这番话点明了隋唐时期政治地位不断下降的士族门阀仍然得以维持其生存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延续不断的家学文化传统以及因恪守礼法、保持门风而获得的社会声望。所以在整个唐代,士族子弟多重家学、守礼法, 其家族中的女性成员也不例外。
在那些以礼法家风著称的士族家庭里,柔顺守礼依然是女子应有的道德修养,这种女性观在士族室女墓志中有明显的表现。《汇编》贞元109《赵郡李氏殇女墓石记》中李氏女“禀天之和,而聪明孝友,得礼之节,而恭敬廉让,奉上顺下,动无所违”;《汇编》圣武002《范阳卢氏女子殁后记》中卢氏女“孝友得于天资,婉顺非乎外饰。明心远鉴,洞见几先,鸣环动步,必循礼节”。士族之家的女儿多幼习女训著作,养成遵循礼法的习惯。如《续集》开元117《唐韦君故长女墓志铭》中韦氏女“念尔明慧,幼儿有知,发言有礼,动不逾规。虽事女则,未成妇仪”;《汇编》咸通103《唐弘农杨氏殇女墓志》中杨氏女“动止语默合礼,奉上爱下,唯顺兼仁,早念诗,习女诫,各得旨焉”。在这些墓志中都极力赞美在室女温柔贤慧,言行举止合乎礼仪。
唐代士族除了培养在室女柔顺守礼的品行外,还注重对女儿孝行的培养。从内容来看,在室女之孝行主要有两种表现:其一,日常生活中对父母非常恭顺,父母患病时,在室女能随侍在侧,亲奉汤药,细心照料。如《汇编》咸通025《范阳卢氏室女墓铭》中卢氏女在母亲患病时照料起居,必能 “先意承顺,动无违者”。其二,父母死亡后,在室女往往号泣过礼,因至孝而成疾,甚至徇孝而终,其中有五位室女[注]在墓志中记载的因至孝而成疾、或徇孝而终的室女有:《汇编》贞元112张氏女、贞元114唐氏女、大和055田氏女、大和089郑氏女、大中094李氏女。的夭折就与其哀伤过礼、悲痛成疾有关。如《汇编》贞元112《唐故清河张氏女墓志铭并序》张氏女“丁太夫人忧,号泣过礼,哀瘵成疾”。当然,大多数在室女墓志并没有提到她们有哪些具体的孝顺行为和孝顺对象,有可能属于溢美之词;但也说明了孝行是唐代女子必须具备的德行之一。
仕宦家庭对女儿的期望与旧士族也无本质的不同,如汇编《开元》200《大唐故唐氏女墓志铭》中唐氏女“夫其体备幽闲,门传礼则,克柔其性,有婉有容”;《汇编》乾符028《唐故吴兴钱氏女》中钱氏女“生植慧性,夙成淑姿,执先君之丧,尽其哀,事吾嫂刘夫人心本乎孝,爱异母之属极其仁,奉长幼之序均其分。有自然之深识,得自守之常规”;《汇编》会昌047《米氏女墓志铭》中米氏女“贞淑温□,□家孝行”;在孝行方面,《汇编》贞元114《唐孙氏女墓志》中的孙氏女堪称典范:在父亲病重之际,她与其兄弟们一同分劳照料父亲,“不离床枕之间,先意敬养,曲尽情礼,与诸子之无疾者均其劳”;父亲去世后,她“号慕哀绝,感动无心,痛之一至,忘其患苦,不纳勺饮,七日而终”。
除了注重品行培养外,唐代士族家庭也比较注重对女儿进行文化方面的教育,这在墓志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墓志显示,唐代士族大家庭的女子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大都能讽诵儒家经典、诗词文赋,甚至史传等。如《续集》乾符029《大唐河中观亲察支使试秘书省校书郎孙揆季妹墓志铭》中孙氏女“通何论,毛郑诗,诸箴史赋咏,未尝辍诵于口”;《汇编》咸通004《唐博陵崔氏亡女墓铭》中崔氏女“尤嗜诗典”。有的在室女还会有超出常人的见解,甚至会写一手好文章。如《汇编》显庆079《张氏亡女墓志铭》张氏女“而又雅好文墨,居闲览玩篇籍,或优劣是非,无不暗符先贤微旨”;《汇编》贞元112《唐故清河张氏女墓志铭并序》“讽诵诗书,必赜先儒之旨趣,博通艺能,皆出常人之阃阈”。这说明唐代士族在室女受到了较好的文化教育。
不过细读墓志行文却可发现,唐代士大夫家庭对在室女的教育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读书识字、阅览讽诵而非创作;二是重品德礼仪、轻文化素养。在66方室女墓志里,赞美室女品德礼仪优秀出色的有51方,占到室女墓志总数的77.3%;而赞美室女才学修素出众的有23方,仅占总数的22.7%。很多墓志都对在室女能讽诵诗史津津乐道,但很少提及她们会创作诗文。一些士族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就让其学习女训之书,如《汇编》大中077《范阳卢鄯幼女墓志铭》称赞卢氏女“才能诵而讽女仪”。这说明,虽然士族家长重视在室女的文化教育,希望她们德才兼备,但重点是气质品德礼仪和文化素养。
唐代士大夫家庭对在室女的培养特点与他们对女儿的期望有关。出身于赵郡李氏的中唐文学家李华在《与外孙崔氏二孩书》写道:“妇人亦要读书文字,知古今情状,事父母姑舅,然可无咎……《诗》、《礼》、《论语》、《孝经》,此最为要也。”[注](宋)姚铉编:《唐文粹》卷九○《与外孙崔氏二孩书》,(清)许增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一五亦收,第3195-3196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其目的是让她们能够学习和效仿古代典范女性,做到知书达礼、温顺体贴,将来能够胜任相夫教子、和睦家庭的重任。一些在室女也很好地领略了父母的教育苦心,如《汇编》咸通099《唐御史中丞乐安孙府君长女墓志铭并序》中孙氏女所云:“学古遗文,潜心大业,识异亡治乱之际,窥三坟五常之道,未若敦睦宗族,恪慎克孝。”
唐代士大夫家庭对在室女教育呈现出来的特点与唐代主流社会对女性的期许是分不开的。尽管社会风气相对开放,但上层社会还是比较注意对女性的教育。初唐时期有长孙皇后《女则要录》十卷,魏征《列女传略》七卷;[注](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第1486,1486-1487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武后当政时期,“尝召文学之士周思茂、范履冰、卫敬业,令撰《玄览》及《古今内范》各百卷,《青宫纪要》、《少阳政范》各三十卷,《维城典训》、《凤楼新诫》、《孝子列女传》各二十卷,《内范要略》、《乐书要录》各十卷,《百僚新诫》、《兆人本业》各五卷,《臣轨》两卷,《垂拱格》四卷,并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注](五代)刘昫:《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传》,第133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中唐以后,又有尚宫宋氏《女论语》十篇,薛蒙妻韦氏《续曹大家训》十二章,王抟妻杨氏《女诫》一卷。这些女教著作的作者所属的社会阶层和年代不一,有皇后、名臣、士族官宦女性,时间跨度从唐初太宗到唐末昭宗。除了宋氏的《女论语》是针对于平民女性施教外,[注]高世瑜:《宋氏姐妹与〈女伦语〉论析兼及古代女教的平民化趋势》,见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第127-15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其他主要针对的是社会中上层的士族家庭女性。如薛蒙妻韦氏《续曹大家训》写完后“士族传写,行于时”[注]《旧唐书》卷一六九《韦温传》,第4380页。,在晚唐以后的士族家庭中影响较广。
三、墓志所见在室女的家庭地位
“男尊女卑”是中国古代两性生活状况和地位的集中概括,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的具体生活中,两性地位各有其特点。在唐代,出身于士大夫家庭中的女性地位既不同于拥有着较大的自由空间、甚至可以染指政治的皇族女子,又不同于困于家庭生计而奔波的下层贫寒女子。
从墓志的口气和措辞来看,唐代士大夫家庭中的在室女很得父母长辈的钟爱,在日常生活中得到非常好的照顾。《汇编》开成041《有唐张氏之女墓志铭并序》中的张蝉自幼被家人悉心抚育,备受宠爱:“乃选其乳姐洎高年女奴两三人,令常常抱弄于几前,唯所欲。及稍能理红妆、衣绮罗,则凡是珍奇,莫不堆在眼。”有的父亲还亲自给女儿传授诗书知识。《续集》贞元018《唐故监察御史陇西李府君之女墓志铭》中李氏女“府君因宠秩而名之,钟爱之深可见也。爰自襁褓,明慧过人,在龆龀时,善言词歌咏,监察府君每以慰目前。教以婉娩,聪智日就,能工巧听,顺又过人,妣荥阳郑夫人亦以此慰目前”。
从资料来看,在室女中的长女最受父母长辈的钟爱。如《续集》开成026《唐工部尚书杜公长女墓志铭并序》的墓主特受父亲喜爱是因为“有子多不育,及生女在褓,懿性已兆,自是遂无孩殇,为弟娣长,以此尤爱之”。《续集》大中061《唐故陇西李氏女墓志》中的第娘深得父亲李胤之钟爱,除了因为第娘正好生于李胤之进士及第的大和八年外,还因为她是“余之元女”,该志由李胤之亲自撰写,字词之间流露出一个父亲对女儿深深的怜爱:“自汝襁褓,迨至成长,廿年间,吾南北宦游,绵历万里,辛勤道路,羁旅两京,必自携持,未尝一日离间。”对此,前辈学者赵凤喈《中国妇女在法律上的地位》中指出:“中国之礼教,素重视伦常,而‘长幼有序’,即五伦之一。故女子在家庭中之地位,虽较同辈之男子为卑逊,而长幼之名分,仍然保持。因此年长之女子(即姊),不特对于同辈年幼之女子(即妹),享有优越之待遇;且对于同辈年幼之男子(即弟),有时亦立于较优之地位,毫不受‘男女异长’说之影响。”[注]赵凤喈:《中国妇女在法律上之地位》,第8-10页,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在中国古代社会里,虽然“男尊女卑”的大格局一直没有改变过,但“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长女地位。
当然,唐代士大夫家庭宠爱和重视未出嫁的女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基于骨肉亲情;但除此之外,还有些特殊的原因,使得在室女获得长辈的重视和爱护。这些原因包括:一是某些家庭中少女或养女不寿。《汇编》贞元112《唐故清河张氏女墓志铭并序》中墓主得父亲珍爱是因为“家君三子,唯是一女,爱念所钟”;前述《汇编》开成041《有唐张氏之女墓志铭并序》的张蝉受家庭重视是因为“吾门不寿女,故世世怜女而甚于珠玉”。二是在室女天性纯孝。据《汇编》贞元114《唐孙氏女墓志》所载孙氏女在其父死后“号慕哀绝,感动无心,痛之一至,忘其患苦,不纳勺饮,七日而终”的事迹来分析,孙氏女平日肯定是非常孝顺,所以墓志才会说“九族珍爱,一朝夭殁,亲戚痛悼,安可支也”;《汇编》大中094《唐故江夏李氏室女墓志铭并序》中赵郡李氏女“丁蕲县公之丧,哀毁过节,故特为季父今赞善大夫、叔母卢氏夫人之所钟爱”。三是有些在室女特别聪明伶俐、品貌出众。如《汇编》开成028《李司徒亡女墓志铭》中陇西李氏女“自幼敏慧,为尊父器之,及长贤利,为亲戚重之”;《续集》大中066《北平田君夫人李氏墓志》载李氏自幼“生有奇姿秀韵,举家钟惜,才离襁褓,便有成人风。及稍长,酷好经史诗笔,虽眠食亦闲以讽诵。……白水君与张氏夫人日益怜异,亦曲从其好”。
另外,“作嫔君子,以援吾宗”[注]《唐代墓志汇编》,大中016《唐姑藏李氏故第二女墓志铭》,第980-981页。也是在室女受到家族钟爱和重视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在唐代,“合两姓之好”仍然是婚姻的主要目的。女儿本身虽然不能光宗耀祖,但却可通过婚嫁的方式给本族带来实际利益。盛唐时期的杨贵妃就为这种观念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注解。从墓志来看,越是聪明伶俐、美丽可爱的女儿越得父母珍爱,在婚姻问题上极为慎重。如前文提到的《续集》大中061《唐故陇西李氏女墓志》中的李第娘“洞察是非,尽知情伪,周深敏晤,无与比伦。尤好文籍,善笔札。兄弟读诗书,一关听闻,莫不记览。当代篇什,名人词藻,皆能手写,动盈箱帙,商较文赋,皆尽妍蚩。刀尺女工,裁缝绣画,不习而妙”。她父亲认为女儿“必配贤良,极享富贵”,故为其择婿时“选择益难其人,前后亲族求者不少,竟无良敌,遂未克从”,导致其24岁未嫁而卒。再如《汇编》贞元112《唐故清河张氏女殇墓志铭并序》中的张容成“婉嫟柔闲有德礼,贤和仁孝,聪慧具美”,父兄在她择偶问题上也是慎之又慎,以致耽误了终身。
唐代士大夫家庭中的在室女不仅在情感上获得家长的喜爱,受到很好照顾,而且她们成人后也承担家事,参与家庭日常事务的管理,有一定的发言权。如前述《汇编》开成041《有唐张氏之女墓志铭并序》墓志中的张蝉及笄后“奉中外周旋,故家事巨细,与商量而后行,无不克中”。前述《续集》大中061《唐故陇西李氏女墓志》中陇西李氏女“与姊妹弟兄四五院聚居襄州,生侄数十人,长幼数百口,尔未十岁,皆能承侍敬奉,曲尽殷勤。姑叔姊妹所阙,必为陈请,人人满惬,咸爱重焉。尔来家道有无费用丰俭,悉与筹之,无不得所” 。当然,在室女能参预家事管理,实际上也是“主中馈”能力的训练,使其婚后能承担起家庭主妇的责任。
对年长的在室女,尤其是长女,家人还非常尊敬,在家事的处理上多听取她们的意见。如《汇编》咸通020《唐鸿胪卿致仕赠工部尚书琅耶支公长女炼师墓志铭并序》中的支氏女信仰佛教、居家为佛弟子,主持家政,管理家事,并训导弟妹们,权力很大。其“训勉诸弟,唯恐不立。好古慕谢女之学,择邻遵孟母之规,虽指臂不施,而心力俱尽”,年老后得 “卑弟奉养”,受到家人的尊敬。 长女的权力并不因为她们出家而被削减。如《汇编》永贞003《张君夫人樊氏墓志铭并序》载樊氏的长女出家为尼,当父母死后她就担负起照看弟妹、监管家产的重任,“有女五人,长女出家,宁刹寺大德,法号义性,戒律贞明,操行高洁,弟妹幼稚,主家而严”。

四、结 语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衡量女性的社会地位,主要看她们享有什么社会权利;而探讨女性的家庭地位,则要看她们享有什么家庭权利。从前面三部分内容的分析可知,唐代士大夫阶层(包括士族和官宦之家)在对在室女的培养方面主要沿袭了传统的性别文化观,希望她们柔顺守礼和孝顺父母长辈,将来能够胜任“主中馈”的内职。但在文化繁荣、风气相对开放的社会背景下,唐代士大夫之家的在室女的家庭地位还是比较高的。首先,她们享有一定的教育权利。唐代士大夫家庭中的在室女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仅能讽诵诗书的很多,而且还有不少极有创见者,甚至有能文擅画者。其次,她们享有较好的生存空间。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室女在日常生活中会受到很好的照顾,尤其是聪明伶俐品貌出众者更得父母的关心。最后,年长的在室女地位受长幼有序礼法的保障、在家庭生活中享有较多的特权,成年以后也有权管理家事,她们的意见也会受到尊重。在特殊情况下,她们还能承担“主丧奉祭”的重任。
唐代士大夫家庭中在室女家庭地位的几种表现,有的是比较独特的。比如女性受教育的权利。虽然历史上受过教育的女性有很多,但像唐代这样普遍还是较少的。从墓志来看,几乎所有的墓志都对在室女的文化素养津津乐道,表现出极为欣赏的倾向,事实上大多数唐代女性墓志也有这种倾向。这说明唐代士大夫阶层的女性享受教育的现象比较普遍,至少要比宋代以后普遍得多。因为自宋代的司马光提出“ 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诗,执俗乐,殊非所宜 ”开始,“妇人识字多诲淫”、“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话语便出现了。当然,唐代士大夫们对女儿实施诗书教育的目的并不是让她们光宗耀祖,而是为了其将来能胜任贤妻良母的重任。所以教育的内容是重讽诵而非创作、重品德礼仪而非文化修养。即便如此,与后世观念相比,唐代上层社会的女性观还是比较开放的。人们认为女性有权接受教育,应该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
年长的在室女享有较多的特权,不仅能主持家政,而且能“主丧奉祭”,甚至年长不嫁者也极受尊重。尤其是像支氏女,信仰佛教居家为佛弟子,在家主持家政、管理家事,并训导弟妹们,权力很大;不仅在许多事情上都有发言权,而且在家中很受尊重。这在历史上恐怕并不多见。虽然“主丧奉祭”是一种权宜之策,也受礼法许可,但像唐代士大夫家庭中显得如此平常恐怕也是比较特殊。联想到初唐公主对政事的参预,或许这是唐代比较特殊的现象。这些都说明唐代士大夫阶层中的在室女享有较高的家庭地位。当然,士大夫家庭的在室女享有较好的生存空间,在日常生活中能得到很好的照顾主要与家庭环境相对较好有关;同时也受其他因素如骨肉亲情、少女或养女不寿、女儿特别懂事、借助女儿的婚姻给家族带来某些荣耀等方面的影响,这些可能并不是唐代社会的特殊现象,但至少可说明我国古代女性地位的多元化与非固定化。
墓志所显示的唐代在室女的情况非但不能对传统社会女性地位较低作出有力的注解,反而质疑了“男尊女卑”的主流话语。它向我们显示,唐代士大夫家庭中的在室女尤其是长女的家庭地位至少是不比她的兄弟们低的,有时甚至比她的兄弟们还要高。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存在多重等级标准,既有贵贱、贫富之分,又有长幼伦理次序以及男女两性之别……在各种等级标准交错中,性别等级是从属的,要服从其他等级划分” 。 这就使得长女并不因性别的劣势而降低其家庭地位。同时,由于骨肉亲情的作用,女儿总是会得到来自父母兄弟的关爱,特别是在那些女儿较少的家庭里;再加上某些女儿的个人气质比较优越,或聪明伶俐,或才貌双全,或孝顺懂事,深得父母欢心、兄弟爱怜,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女儿在性别上的劣势。女性的一生主要由三个阶段组成:未嫁为女、出嫁为妻、育子为母。三个阶段三种身份,家庭地位各不相同,所拥有的权力也不尽相同。高世瑜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女儿-妻子-母亲的角色变换,她们的地位与权力呈上升趋势,而母亲则是她们在人生舞台上扮演的最光彩的角色。” 笔者却认为,女性三个阶段的家庭地位各有特色。如果说母亲时代是女性登上权力巅峰的时代,那么女儿时代则是最受亲人珍爱的时代。当然这局限于传统社会的封建士大夫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