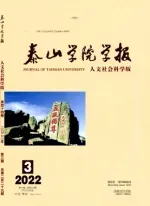论近代欧洲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空间与性别权力
2012-08-15程新贤
程新贤
(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15世纪的下半期到18世纪是西方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期,该时期欧洲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过渡。在这一重大社会变迁过程中,欧洲经历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重要的发展。对该时期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也一直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社会史的兴起和发展,学界更加注重把欧洲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作为转型时代进行长时段的考察,并把普通社会群体作为研究社会变迁的主要对象。其中,城市史和妇女史及性别史的结合,为社会转型时期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一些学者在对该时期城市空间问题进行研究时,注重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分析两性群体在城市中的发展状态。在国内,对欧洲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空间与性别之间的关系还鲜有论述。本文将在汲取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揭示欧洲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都市空间发展状况和特点。
一
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社会经历了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迁。从经济的发展来看,繁荣的商业经济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很多城市作为商贸中心得到快速发展,进而发展成政治和文化中心。仅从城市数量上来看,从1500年到1700年这两百年间,小城市的数量激增,而人口超过1万的城镇几乎成倍的增长。[1](P40)新的经济方式的产生和生活空间的扩大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中世纪时期较为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逐渐被打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增加。人们开始注重除宗教以外的自我需要,为自己寻求更多的权益。不过,在该时期的城市中,不同阶层、群体、性别之间仍存在着较为严格的等级差别。就两性关系而言,逐渐从中世纪走出的人们并没有摆脱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女性在很多方面仍受到种种限制。
欧洲的思想文化在这一时期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重要发展。人们对女性的认识虽然相比于前历史时期的贬抑态度有所改进,比如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人文主义学者认为女性可以接受文化教育,但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对女性活动范围的约束更加严格。在城市生活中,人们把男性和女性界定在不同的领域,并会通过多种方式来强化这种区分。在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方面,很多学者不赞成女性参与社会生活。例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科卢乔·萨卢塔蒂就曾明确指出积极的社会生活的理想只针对男性,不包括女性。[2](P88-89)即使有极个别的女性有机会担任社会公职,也会受到种种非议。16世纪苏格兰著名的神学家约翰·诺克斯曾这样批评女性统治者:让女性来做统治者,犹如病者照顾健康的人,或者像一个愚者在咨询一个智者。[3](P132)面对当时种种贬抑女性的言论,就连当时身为英国国王的伊利莎白一世也不得不借用男性身份来显示自己的强大:“我知道我仅仅拥有一个女人柔弱的身体,但我有一颗国王的心。”[4](P292)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这种主导地位也决定了城市中与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有关的场合如广场、集市和大街是属于他们的,女性基本上被排除在外,她们主要在家中养育孩子和照顾家庭,其活动范围也主要局限在以家为中心的地方,包括家周围的街区和教堂。正如意大利学者阿尔贝蒂在《论家庭》借人物雷奥那多之口所说:“既然女人因看守孩子和管理家产,她就不适合外出置理所需之物”。[5](P102)事实亦是如此,长期处于怀孕生子循环之中女性根本无暇关注社会事务。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注重私人空间的设置,不过,对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区分却是以女性活动的范围为标准的。有学者指出,除了大街、广场和教堂这些地方属于公共空间,凡是妻子被外人看得见的地方也属于公共空间,如庭院、门口、窗户和阳台。[6](P22)在这一标准下,女性的活动范围被进一步缩小,仅局限于家中而且是不能被外人看得见的地方。
女性这种职责和活动范围皆属于家庭的观念在宗教改革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新教在反对天主教的独身主义而积极肯定婚姻和家庭价值的同时,更强调了女性在生育方面的价值和妻子要依附于丈夫的夫妻关系。女性肩负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被一些宗教改革家极力渲染。如马丁·路德就宣称女性的生育能力可以遮盖她所有的缺点。还有一些学者根据《圣经》中夏娃产生于亚当肋骨的论调出发强调妻子必须要依附于丈夫。因此,在种种论调之下,很多修女院被解散,大部分修女回归了世俗的家庭生活,承担起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所以当时社会倡导的理想的女性形象就是:和她的孩子们坐在一起,在听一场布道或者在阅读《圣经》,衣着素雅,头发一丝不乱中透出几分谦逊。[4](P29)
相比于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人们对女性的认识在启蒙运动时期则明显带有社会转型时期的过渡特点。学者们对女性的评价一方面充满了溢美之词,另一方面在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论调之下强调女性的软弱和缺陷。“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狄德罗对女性在社会中的悲惨处境抱以强烈的同情的同时,认为“虽然丈夫和妻子在结合中有着共同的利益,但欧洲的法律和习俗只能把文明国家的积极的权利明确地授予男性,因为男性天生具有更强的体质和精神力量,在人类和神圣的事务中为公共利益贡献更多。因此,妇女应该绝对隶属于她的丈夫,在整个家庭事务中服从他的命令。”[7]293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和以往时代相比,这个时期人们的女性观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女性属于家庭的观念反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因此,这也使得女性在城市中的活动范围受到更多的限制。
二
任何群体在城市中不仅要面临生存问题,而且还要面临如何确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问题。虽然该时期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不应离开家庭,但商品经济的发展仍为女性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提供了诸多机会。不过,她们在城市中的生存之途并不顺利。传统的厌女思想以及在其影响下的社会实践都使得她们在城市中处于不利地位。
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在城市中的生存状况存在着不同。对于社会上层和中产阶层的妇女来说,在没有重大变故的情况下,家庭在很大程度上为她们提供了生活的保障,她们基本上不用外出为生活而奔波。由此,家庭及其周围临近的街区、教堂和修道院就是她们主要的活动范围。而普通社会阶层特别是社会下层的女性通常为生活所迫特别是要为自己准备一份嫁妆而外出工作。她们的这一行为一方面超出了人们所认为的女性本应属于家庭的传统认识,另一方面,她们对城市经济生活的参与使得她们逐渐进入到原本由男性占主导的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危及了男性的利益。所以,她们在城市中谋得生存的同时会受到种种制约。特别是随着城市政府权力的逐渐增强,她们也日益成为城市管理的重点对象。
从16世纪开始,欧洲很多民族国家逐步形成,中央政府的权力扩大,欧洲逐渐脱离了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与此同时,社会经济活动的多样性,城市快速发展及其带来的种种问题,都要求政府加大对城市的管理和控制。正如亨利·皮朗所言,当国王的权力增加时所开始产生的国家观念,促使他们自认为是“公共福利”的维护者。[8](P204)为维护统治,近代早期的欧洲在政治上确立的基本上是家长式的管理方式,统治者往往把自己称作市民家庭集体之父。例如,英王詹姆士一世把自己定位为养育、教育和管教孩子的父亲,由此认为自己是一位照顾所有臣民的君主。同时,他还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配偶,称自己是一个丈夫,而整个爱尔兰则是自己合法的妻子。[1](P136-137)政治上这种家长式的统治意味着男性不仅垄断了国家权力,而且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都处于主导地位。这可从城市政府对进入城市的女性的种种管理措施上体现出来。
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大批乡村人口迁往城市,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到城市去谋生,其中就有很多女性。不过,当时很多城市限制女性进入城市,并颁布了相关法律。在德国和法国,法律规定未婚女性不能进入城市,寡妇须有儿子或男性监护人的陪同,而有婚约的未婚女子须和男性亲戚或雇主一起才可进入城市。[9](P210)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政府主要针对的是没有婚姻保护的女性。在政府看来,政府和家庭有内在的一致性,即家庭内良好的秩序是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因此,没有家庭的人被视为危及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尤其是进入城市的未婚女性,“未婚的自立的女人对他们的道德秩序是个威胁”。[10](P267)尽管城市政府对女性能否进入城市进行了限制,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移民构成了城市家庭服务业的主要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服务业经济的发展。不过,与男性相比,她们的职业不太稳定。比如,男性在做工时通常会和雇主有一定的合约,而女性却没有。所以,她们更易成为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和乞讨者。
在欧洲近代早期,与中世纪相比社会经济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大多数人仍属于贫困阶层。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暂时或者长时期没有工作。根据当时的观点,没有土地、工作和监护人的人被视为流浪者。对于女性而言,任何的贫穷以及没有婚姻身份的状态都使得她们被划归在流浪者行列。事实亦是如此,女性职业的不稳定和低收入是她们在城市生活中的常态,而这种没有保障的生活使她们成为城市中的贫穷人口。有史料记载,1561年西班牙的塞戈维亚人口调查显示,女性在都市贫穷人口中占60%。[3](P98)由此,在很多城市的流浪人口中有很多女性。当时的很多政府针对流浪人口采取了多种措施,最典型的是颁布济贫法。不过,大多数济贫法的实施是以受救济者参加劳动为前提条件的。在英国,政府通常是不考虑乞讨者的劳动能力迫使他们参加劳动,且给予很低的的待遇。所以,济贫法的效果并不明显,城市中仍有大量流浪人口。政府对女性流浪者实行严格管制。在威尼斯,政府曾颁布法规要求流浪的女性到官方进行登记。英国则要求妇女乞讨时必须带上官方颁发的通行证。通行证上记录着乞讨者的姓名、身份、允许乞讨的地方以及时间限制等信息。[3](P97)对于禁止人们流浪和乞讨的措施,虽然有学者指出,政府的用意旨在维持秩序和加强公共安全,而不是出于对不幸的人们的盲目仇视和对劳工阶级的敌意。[11](P79)不过,当时的城市政府之所以对女性在城市中的活动进行严格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女性的偏见,认为女性本身软弱的、容易堕落的弱点会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
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男性和女性在城市中有着和自己身份和地位相匹配的空间。这一空间无论从地理概念上还是从其代表的社会权力而言,都具有文化建构的含义。因为,人们不仅在观念上认为男女两性应分属于不同的空间,而且通过多种形式来强化这一观念。
在法律方面。男性和女性在城市中有分属于自己的活动空间,并且享有这一空间所赋予的权力。如果他们的行为危及了这一空间的公共利益,那么在法律上他们将受到相应的惩罚,即会丧失在这些空间的某些权益。对于男性而言,城市内的广场、大街和集市是他们进行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这些地方彰显了他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如果他们在这些地方侵犯了其他群体的公共利益,所受到的法律制裁通常是根据情节的轻重让其在该地区丧失名声或经济利益。例如,威尼斯的十人委员会曾判处三名损害了政府利益的贵族男子禁止进入圣马可广场和里亚尔托桥及其附近地区(当时威尼斯主要的商业中心),并禁止他们使用城市中主要的商业干道。[12](P341)和男子一样,女性所赖以生活的地方对她们的身份及名声有着同样的意义。如果一个女子的名声或身体遭到侵犯,法庭给予肇事者的惩罚往往是要求其在女子生活的街区恢复她的名声,或者提供一笔嫁妆或直接娶该女子为妻。从这些法律的仲裁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男女所属的空间对他们身份的塑造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仪式和节日庆典方面。当代法国思想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曾言,仪式是与人怎样思考世界相符合的。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城市中,存在着多种名目的仪式和节庆活动。其中,很多仪式与劳作有紧密的关系。这些仪式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在劳动领域内的关系和地位。中世纪中后期开始形成的同业公会(又称行会)是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形成以前城市中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其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享有某一职业的独占权。为了向外彰显他们对某一行业的控制,很多行会会在特定的日子举行仪式或比赛活动。由于行会成员基本上都是男性,所以在这些活动场地基本上看不到女性的身影。而且,仪式活动都比较激烈和危险,也根本不适合女性靠近。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很多城市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活动,例如,在威尼斯,不同行业的手工业者或工匠通常在广场和大街上进行一些仪式或比赛活动。其中一个非常激烈的比赛称之为搭建人体金字塔。在一次比赛中,最高的金字塔是由8个年轻力壮的男子搭建起来的,大约有40英尺高,顶上是一个男孩,手里拿着旗子和一瓶开口的葡萄酒。[13](P24)其实,在当时的意大利城市中,男子在大街上不仅进行剧烈的比赛,而且还经常会有各种打斗。男性就是通过这些充满男性气质和力量的行为活动来表现他们在职业领域和城市公共空间内的优势地位。
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本身在职业领域和城市公共空间内并不占优势。所以,完全由女性参加的仪式并不多见。不过,女性也有其维护自己空间的方式。其中,街区在女性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她们生活、休闲的重要场所。由于活动范围有限,她们更注重和街区内的近邻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于普通阶层的妇女来讲,邻居通常是最好的朋友,不仅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帮助,而且平时大家相互走动,共同分享日常生活的点滴。有时,她们之间还有一些经济活动。一些妇女把房子租赁给在城市中谋生的单身女性,而后者出于安全以及经济等原因多选择和其他单身女性共同居住。可见,在街区中女性之间的联系还是非常紧密的。而女性在街区内良好的邻里关系有助于困难的解决和处理,特别是在女性的婚姻状况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如,妻子有时把虐待自己的丈夫告上法庭,此时邻居通常会到庭作证向法庭提供有利于女性的证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街区这个主要是女性活动的地方对男性的权威起着一定的限制作用。不过,在以男性统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性在近邻之间的活动并非完全自由的。英国贵族妇女安妮把自己描绘为囚禁在自己家中的犯人,因为她的丈夫试图割断她与近邻和朋友之间的所有联系。[14](P153)
可见,男女两性分属的不同空间往往是和他们所担任的角色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意味着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他们享有不同的权力。在此基础上,人们又通过思想观念、法律、仪式和节庆活动等方式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社会特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欧洲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内地理空间、性别和权力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综上所述,在近代转型时期的欧洲城市中,男性和女性所属的空间有严格的区分。广场、集市和大街等公共场合属于男性,而家及其周围的街区等较私人的空间属于女性。这一区分是和他们所承担的社会和家庭角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这一区分随着城市政府管理职能的逐渐完善而进一步加强,所颁布的法律法规使得女性在城市中无论是从活动范围还是职业领域内来说都处于不利地位。而充斥于城市日常生活中的仪式和节日庆典等活动在很多情况下进一步加强了城市空间的性别化特征。这表明,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的进步有时和两性关系平等化的实现以及妇女的真正解放并不是同步的,而后两者的实现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1]Sandra Cavallo,Silvia Evangelisti eds.A Cultural History of childhood and family:in the early modern Age[C].Oxford·New York:Berg.2010.
[2]G.Kohl,G.Witt,eds.,The Earthly Republic[C].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1.
[3]Meg Lota Brown and Kari Boyd McBride,Women’s Roles in the Renaissance[M].London:Greenwood Press,2005.
[4] Merry E.Wiesner,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5][意]阿尔贝蒂.论家庭[M].梁禾,译.西安:西安出版社,1998.
[6] Catherine King,,Renaissance Women Patrons:Wives and Widows in Italy c.1300 -1500[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8.
[7]裔昭印,等.西方妇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8[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M].乐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9] Renate Bridenthal,Susan Mosher Stuard,and Merry E.Wiesner,eds.,Becoming Visible: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C],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8.
[10]Natalie Zemon Davis,and Arlette Farge,eds.,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West:Renaissance and Enlightenment Paradoxes[C],Cambridge: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1992.
[11][法]G·勒纳尔 G·乌勒西.近代欧洲的生活与劳作(从15—18世纪)[M].杨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12]Dennis Romano.Gender and The Urban Geography of Renaissance Venice[J].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23,No.2(Winter,1989).
[13]Judith C.Brown,Robert C.Davis,eds.,Gende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C],London:Longman,1998.
[14] StephanisTarbin, Susan Broomhall, eds.,Women,Ident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C].England:Ashgate.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