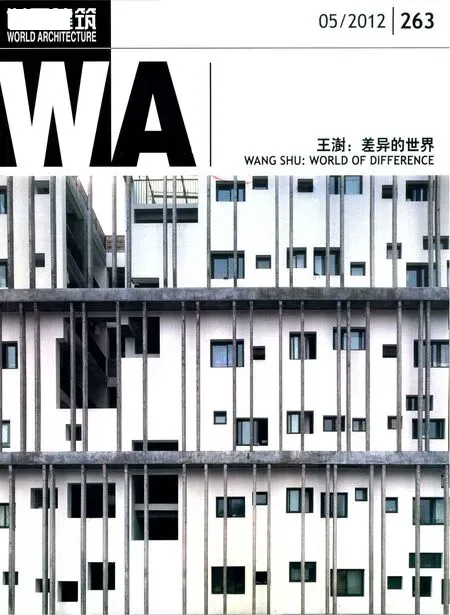读王澍和他的苏州文正学院图书馆
2012-07-04刘家琨LIUJiakun
刘家琨/LIU Jiakun
中国的众多城市已经被一场半专业的建设风暴弄得又新又脏,一模一样,而在乡村,地方精神仍清晰可辨。沿沪宁高速一路东南──像紧握的拳头慢慢松开──王气森森的郊野转入世俗的鱼米田园,石头南京的方硬变成了水苏州的随意。新区非城非乡,难以名状;在一片弥散着无序与分裂气息的地方,王澍设计的苏州文正学院图书馆采用了离散和重构的手法,也就没有什么突兀不当的。王群问王澍,那些变异在总平面上有没有依据,后者顾左右而言他,语气比那些依据还远。根据王澍的设计倾向来判断,我觉得依据就是现场,落实到水边上这块坡地的具体情况:比如说,这样就长那样就短,或者是转一转就得到了合适的间距。如果以隔着童明处理得很灵秀的庭院和庭院炮打翻山似的某一条概念线作为依据,似乎更为专业,其实相当可疑。
我觉得王澍也这样想,我甚至觉得他可能认为依据其实就是自己,说不说出来,还没有拿定主意。
都说王澍有些反叛,我不觉得。与南工不同,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教学传统,重建工的野孩子们从一年级开始就什么都玩,到毕业的时候一头雾水,就像《美国丽人》中的那个女孩子,其实什么都没有干,好像什么都干过了,而南工的学子们接续着六朝古都的中轴精神和中国第一代建筑大师们的严明,出手时都还保有着一份庄重,至少遵守着一些规矩。我看这些青春期的濡染就是王澍的底子。他是太严肃、太认真,不愿不求甚解,不愿人云亦云,他是因为打破了砂锅才被人当作异类的。
在王澍身上,有3 条线索是足够明显的:第一,对烟雨江南传统元素那种文人式的眷恋;第二,对民间智慧、构筑物,亦即对他自己所言“业余”或“临时”的那种非建筑、非设计、非正式的关注;第三,从南工学士到同济博士那读了又读的现代主义专业教育历程。其中第一条似乎已经进入下意识,第二条是有意为之,并希望以此作为原创源泉。第三条,虽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在极力挣脱,但却仍然是最系统、最强有力的──我就这样一面观察王澍,一面观察苏州文正学院图书馆。
关于这座图书馆的设计构思及设计依据之类,应该由王澍自己来写。关于至关重要的功能是否设计得合理,应该由业主来写。我想写的只不过是另一个建筑师在一个阴雨天的午后对这幢建筑的印象,虽然由一个建筑师来评论另一个建筑师的设计似乎是很少见的。关于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应该由王群来写。




在去现场之前,我对这幢建筑已经大致有些印象。我暗暗有点担心:那些平面上的偏转叠加手法,是我熟知而不敢用的。我隐约觉得有些多了闹了。但站在童明的廊桥上一眼望去,这幢建筑比在图片上和雄辩中沉静多了。它横在水边,素白、青黑、深灰,有着很好的情态。
也许是因为图像明确易于叙述,或者是因为设计之初必须首先弄得很明确的就是平面布局。关于这幢建筑,讲得比较清楚、给人印象较深的是它的平面。由于平面上有着这样一下、那样一下的倾斜,我一直恍恍惚惚地误认为它是2 套甚至3 套网络体系的叠加。到了现场,面对体量的主次,我发觉,与其说是体系的叠加,不如说是一条轴线对一个体系的冲撞。主要的体块本来是同一体系、平行规矩、老老实实的,但由于有一条通道从上面的庭院冲下来由建筑群中斜穿而过直插湖边,像列车开过后的劲风,使道路两边的小一些的东西微微摆动。演播厅(它本来在功能上就有相当的独立性)侧了侧身,与主体形成一道夹角,效果是在它们之间的夹道中造成紧张。那个钢梁焊铆的天窗盒子连身都没有转,它下面的柱网既不独立,又未侧转,因此它其实只是动了动脖子。我想这大概是为了平衡演播厅的侧转,或者是顺便给门口的戏台(王澍称为“非楼梯”)让点位置。或者是这样:既然作了一个大大的立体天窗,就干脆强调它的独立。或者上述兼而有之。由于角度不大,这两次侧转都属于同一体系内的摆动,而不是另一体系的加入,──这样一看就明晰多了。
虽然体量小得多,独立性更强的是轨道上的4 个盒子。由于它们的数量、相似性和密集排列,已经自成体系。它们的有趣之处在于相互之间的左右远近,以及相对于主体系的内外穿插关系。不过,比它们自身之间有趣关系真正更有意义的是它们与主体的对比。由于这组体量,主体体量被破解,从而在尺度上谦和了许多。具体些讲,如果没有临水的那一个半盒子,临水的主体会显得有些庞然,有些简单。比起依靠自身切割破分而削减体量的手法来,依靠另外体量的对比而削减体量,是个更加干净完整、各保全身不见刀痕的办法。
以功能体块为单元进行离散解析(而不是以梁、柱、板等等建构单元进行解构,那样会贫瘠些),使王澍手中掌握了一批元素,足够重构一个小世界。比如模拟一个水边集落或是一处园林。这两者都有一个基本要素,即所谓的移步换景,但在组织结构和生长方向上有所不同。通常,以小见大的园林世界是确立了边界以后向内生长的,而村镇集落是形成了中心后向外蔓延的。观念上固然可以把一个功能化的平凡主体视为无物,任线路及其周边元素内外穿插、左冲右突,但实际上却不可能忽略。在图书馆上下内外走了一圈,由于我看见的更多是处于边缘的场景圈绕着中心,原始印象上并不像园林那样有一个明确的外部界定和规定性比较强的环游路线设定,因此,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村落的体验。这是一个生动的现场。在每一个自成场所的地方,王澍都设置出一种情境:青砖小院,柱林,临水走廊,入水的“诗歌屋”── 一个水上的亭子。而那个入口小广场,几乎就是场镇中心。在这个盐市口、菜市口或者干脆叫做书市口上,各个角色汇聚:高台阶(非楼梯)的盒子,头顶倾斜的盒子,演播厅前特意以脱缝方式独立出来的门廊,立体钢天窗,从下而上的坡道和从上而下的坡道,夹缝中的梯级(如果它通向水边就更像村镇场景),这些建筑角色自身进行着表演(这到也常见),并刻意提供给人们演出场地(有点像戏中戏)。于是,在“非楼梯”上嘻嘻哈哈的人们,就成了王澍手中的提线木偶身上的虱子。最得意的是王导演。王澍在构建的方法上绝对专业,而在构建的目标上却相当感官化,归根结底,他是赋于戏剧性的。
平面的偏转和体量的穿插仍然是这幢建筑引人注目之处,但我更感兴趣的却是它的剖面关系。我觉得这幢建筑暗暗分为上下两大部分,在设计动机和现场状态上都是如此。有一条凹槽似乎是个暗示。以“书市口”地面为界,向上,即建筑的“正式”部分,或称建筑主体,换句话说,就是在需要秩序、需要认真计划主要功能的地方,基本上都是非常专业化的现代主义手法。那些元素对峙,体系叠加,偏转冲突,都是刻意设计而成的。有点复杂,有点炫技。清楚、紧张,类似思辨游戏。这是明确的方法,可以用在很多地方。而向下,即从地面一直下到水边,那通常是作为“利用”的部分,却表露出一种交融随意,暧昧动人。它们对斜岸的依附,它们的近水,传达出与场地的直接生长关系。有一点很有趣,即平面标高与水的距离。不同的距离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状态:如果与水面离得较远,其下便出现“桥下”状态,显得颇不寻常。如果与水面距离较近,则成为亭榭杆栏,具有传统韵味。我不知道王澍是否意图明确地这样设计。有可能,因为两种状态都是他关注的。但似乎又不是,因为那效果不像是刻意而像放松偶得。王澍自已也曾几次解释那个伸入水中的盒子为什么离水远了些,言词中有些无奈。但是我看没有关系,这个盒子,近水时是个“诗歌屋”,远水时,就算是个水文站也并非缺陷,那是个“非常”场所,这就行了。这两种状态中无论哪一种,都比上面那些由强大清晰的专业手法制造出来的戏剧冲突来得简单动人。它们所处的“地下”状态,几乎是象征性地表现出了王澍的专业手法之下的情感基础,即前述的第一和第二条线索。是不是王澍所关注的“弃物”的魅力也必须在他自己部分放弃的状态下才会出现?


仍然与前述的3 条线索相对应,图书馆的建构及表现大体上有3 类:一是青砖砌筑,斩假石压顶收边这类传统作法;二是型钢组合,焊接铆固。有时候两者组合:如青砖墙上那一道阿尔托·罗西式的槽钢过梁,或者用型钢组合的“美人靠”。有时候单独强调:如那个体量独立的天窗盒子,其意象可能来源于工业厂房。而基本的结构体系是最通用的框架结构,与这一体系配套,是常用的填充墙、砂浆抹面、弹涂外墙涂料等等。最新的技术可能就是朝向水面的玻璃肋钢夹板点驳接玻璃幕墙了,最机巧的构造可能是打算用于通风的钢制推拉小机关,这是一些不同时期的工法,但可以这样说,无论选用哪一时期的材料和技术,王澍在建构上的倾向是简朴。唯其如此,正因为用语朴素,才能压得住那些多少有些跳跃的情节。总体而言,这幢建筑的工艺水平比想像的好,我感觉确实是工人修的而不是农民修的。材料和色彩也控制住了。可能有童明帮忙,苦口婆心,软说硬磨。或者业主确实品位较高、无意堆砌,或者有心乏力、无钱堆砌,或者被王澍的雄辨和阴沉给镇住了。由于和当下时代的心态相悖,追求简朴有时候极为艰难,还不是经费能控制得住的。据我的体会,工程后期,当没有结构安全问题而且大象已现时,往往会突然冒出来许多设计人,沉默了许久的人们和靓丽、光鲜、豪华一起复苏了,而栏杆、面层、玻窗这些地方又是最容易被作为子项工程分解发包的。我有好几个工程就在后期被又轻又薄、溜光贼亮、还自带珠珠灯的不锈钢圆棍棍一劳永逸地给糟蹋了。控制力应该属于专业以内的事,而需要专业以外的能力。
如何保持设计的明晰简约,同时又具有充分的自由度和可读性,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我很注意王澍的策略。各人战术不同:或者屏蔽其他,一次着重解决一个问题;或者并置各种因素然后统一覆盖一层秩序。看来王澍的策略接近后一种,他以现代主义的饺子皮包裹起个人的、非正式、非专业的等等混合馅,以期形成外部单一、内部复杂矛盾的东西。这样做的关键在于掌握好外部单纯度和内部复杂性之间的平衡。这是一对矛盾。一般说来,皮太厚了容易沉闷,设计者还得自我解说提请注意;馅太大了利于展现,但得意之处就在犯险。由于从小就这样做,王澍对犯险有种迷恋,个性使然。站在我的角度上,我觉得有些地方似乎说破就破但还没有破,有点儿惊险。如果是我,我宁愿把图书馆属于饺子皮的那一部分做得再单纯些。具体说来,有几个局部:比如门卫室(第一个盒子)上的倾斜造型,在图上很引人注目,似乎是个重点,在现场却显得可有可无、意义不足,属于小角色的夸张动作。不像演播厅靠山那一面的斜切,那是大人物的随和姿态,有些谦逊,有点动人,其依据又来自演播厅内部声学斜墙的对称性。再说内部那个楼梯,平面上的偏转和暴露的梁柱两种处理交织在一处。由于梯段本身在竖向关系上必然有的斜度,平面和竖向两个角度的斜度重合在一起,使平面上的偏转效果弱化,处于在与不在之间,本身已经有些微妙,如果到此为止,将会完全生效,微妙动人。但这微妙在交叉梁柱的大喊大叫声下几乎被淹没掉了。如此说来,不作平面偏转也行,或者只要偏转不要梁柱,会不会更好些?站在我的角度上,我对这些重叠变异有些质疑,从战术上讲,与它带来的许多麻烦相比,有点事倍功半的感觉。此外,如果一定要偏转,把它反方向,也就是与演播厅的内墙,与天窗盒子一致,会不会形成逻辑上的顺势搭接关系,虽然实际效果无甚变化,可能平面上会好看些?又,这一处楼梯离另一个楼梯,以及它们之间的天桥有点太近,使天桥的效果被消解……话越来越多了,反正我就是对这一带真正有些不满。
还有几处地方,属于元素复杂并列后必然带来的如何定义的问题。比如柱阵,虽然有“先栽柱子后栽竹子”这样抒情的说法,但那些钢筋混凝土柱子更多地表现出粗砺赤裸的构筑物意象和未完成痕迹,它们的高细比和整体性表现出“浇筑”工法,而“斩假石”毕竟是“石”,用斩假石作为饰面,似乎在工艺属性上隐约有些不合之感,人工味十足的斩假石好像用在砌筑意象中更恰当些。如果高,应该有所依附,如果是柱子,应该粗大得让人觉得可以砌起来──我这样想。坡道两边的小青砖十分好看,为建筑增色不少。但青砖如此温文,用作挡土墙(它不是城墙大青砖),虽然也不是扛不住,但有点像木兰从军。那么,不这样处理又怎么办?因为这青砖墙一转就到了一个有水池的小院,青砖在这里是非常合适的。在转角处分别处理吗?恐怕不行。我也想不出怎么办更好,提个问题而已。也许更为重要的材料表现和现场感觉早已超越了这类问题。
坐在上海南京路上那个铁血寒光的“顶层画廊”里,我本想用这一类问题拷问王澍。我们在成都那次青年建筑师论坛上建立起来的“拷问”机制,有点儿像“建筑创作质量互查小组”,使每个被逼问到墙角的人,无论是谈到以前的作品或是以后下手都得加倍小心。而此刻,他已经作好了被拷问的架势。但我转念一想,我是有文字任务的,要是被他都先解释了,提笔时只好哑口无言;如果照样把对话写出来,则会被坐在一旁听过一遍的王群看作偷懒。如果要问,我宁愿分手后以文字的方式问,也给他机会以文字作答,这样会严谨些。但回到成都,我连这个都放弃了。误读就误读吧,误读是另一扇窗。重要的是这幢建筑值得一读。尽管王澍对“顶层画廊”更为得意,但我更看重这个苏州文正学院图书馆:一个是在夜色掩护中制造梦幻,一个是在光天化日下处理现实,难度系数不同。大家都才刚刚起步,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建筑,从根本上,王澍也不把完美作为目标。但它显而易见的专业深度已经引起了建筑界的关注。前来参观的人已经不少了。走这条路子的人可以把它当作肩膀来踩,不走这条路子的人可以把它当作参照系。走不走这条路子,都应该学习它的品质,而其中的不妥协性却不是人人都可以学到的。诚然,我们都可以来指指点点(像我一样),也还可以举出一些不满,但从整体上讲,我真心喜欢这种有争议的动人,而不愿看那些近于完美圆熟的庸俗。□(2001.01 写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