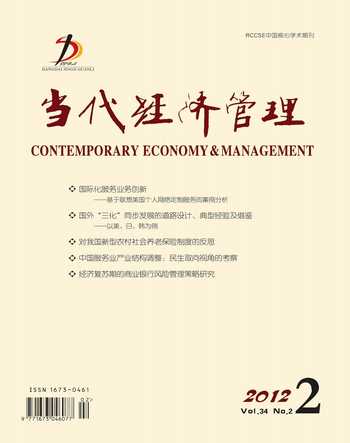上海市商务成本构成趋势对产业转移的影响
2012-04-29苏云霞孙明贵
苏云霞 孙明贵
[摘 要]探讨了上海商务成本构成趋势对产业转移的作用。研究表明:上海商务成本构成趋势显示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一般而言,随着经济发展,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交易成本逐步下降,而商务成本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商务成本构成趋势以及总体上升的趋势会加速产业转移方式由基于产品间分工的产业转移模式向基于产品内分工的产业转移模式的转变,并对产业转移产生影响,大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成熟阶段的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发生对外产业转移,处于产业生命周期创新和成长阶段的新兴行业则向该区域产业集聚,不同产业、产业价值链不同环节沿时间向量在同一空间转移和集聚,最终会促使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
[关键词]商务成本;要素成本;交易成本;产业转移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2)02-0055-08
近年来,随着上海土地价格、劳动力工资等上涨,制造业许多工厂不堪成本重负而外迁,“产业空心化”的担忧也水涨船高。然而,又有许多企业看好上海优质软环境如人才资源充足、高效透明的政府运作、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悄悄将总部设在上海。新兴产业如信息产业在上海的发展势头也高于周边区域。这种产业对流转移的“悖论”现象,显示出商务成本对产业转移“推”与“拉”的双重影响。本文拟回顾有关文献,对上海商务成本构成趋势进行分析,探讨这种趋势对产业转移的作用机理,并通过研究上海产业转移的趋势和特征,来实证这种作用存在的可能性。
一、相关文献回顾
商务成本的研究,源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财富》杂志对全球最佳商务城市的排名。英国、日本的研究机构和一些国际知名咨询公司也相继围绕金融中心运营、e城市竞争力、商务选址决策等问题开展商务成本与投资环境的调查与研究。国外有关商务成本的研究特别是商务成本比较研究,受到各国学术界和民间的广泛关注。国内有关商务成本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①对商务成本的含义、构成,商务成本分析与评价等基础问题的研究(傅钧文等,2003;傅永军等,2003;安礼伟等,2004;陈珂、陈玮,2005;潘飞等,2005;陈建军、郑瑶,2004)[1][2][3][4][5][6];②城市商务成本研究(朱家良,2004;赖涪林,吴方卫,2005)[7][8];③区域商务成本的比较研究(傅钧文等,2003[1];安礼伟等,2004[3];陈建军、郑瑶,2004[6]);④商务成本与产业分布格局的关系(江静、刘志彪,2006[9];周扬波、李文静,2009[10]);⑤商务成本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吴炎太,2008[11];陈建军、崔春梅,2010[12])。
产业转移是指产业的空间移动或迁移,包括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综合流动,它不仅涵盖整个产业生产的转移,而且还包括同一产业内部各生产阶段的转移(冯根福等,2010)[13]。产业转移理论国内外已有丰富的成果,主要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梯度转移理论、雁行模式理论、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中心-外围理论等(王辉堂、王琦,2008)[14]。这些理论的共性在于:一是都涉及成熟产业的产业转移和发达国家/地区向欠发达国家/地区转移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的研究,方向具有单一性;二是都涉及内生动因。当前产业转移趋势呈现双向性,不仅成熟产业而且服务业也发生转移,不仅发达国家/地区向欠发达国家/地区进行产业转移,而且进行双向转移。如,原小能(2004)认为第三产业投资成为国际产业转移中的新热点[15],Dunning(1982)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双向性尤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16]。从现有研究中国产业转移的文献来看,除了内生动因外,也有学者研究地区政策等环境因素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如Fujita和Hu(2001)使用GDP和工业产值数据描述1985年~1994年中国的地区差距问题,将其归因于倾斜性的地区政策[17]。
通过对已有文献分析,学术界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很多,普遍偏重于研究影响传统产业进行转移的因素,鲜有研究影响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进行转移的因素。对商务成本与产业转移本身的关注相对较少,研究商务成本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时,也是偏重于传统产业的分析,忽略商务成本构成的特性对产业转移所具有的双向影响,很少研究它对新兴产业的影响。本文拟同时研究商务成本对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产业转移的影响。
二、上海商务成本构成趋势及分析
本文认为,商务成本是指投资者和企业为完成各类交易活动而支出的与所在地(行政区域)相关的成本总额。商务成本的界定须强调“主体依存、商务依赖、属地相关和边界有限”。商务成本由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两部分构成。要素成本主要是指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因此选择商业设施与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来考量;交易成本主要是在交易过程中发生的间接成本,因此选择政府运作效率、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研发能力四项指标来考量。
(一)要素成本
1. 商业设施及土地成本
以房屋租赁价格指数、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土地交易价格指数考察商业设施及土地成本变化。三种价格指数上涨,说明土地成本上升,要素成本上涨。
表1可以看出,房屋租赁价格指数、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土地交易价格指数三个指数逐年提升,房屋租赁价格指数增长20.3%、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增长29.7%,土地交易价格指数增长幅度最大,增长达到34.5%。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除经济与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之外,2010年上海世博会召开,2004年起开始居民和厂房拆迁,也进一步提高土地交易价格指数。上海土地价格增速较快,除了级差地租的客观因素以外,投资开发用地中征地安置农民的办法是引起地价上升的重要原因。上海工业区征用土地使用的是一次性解决农民农转非问题的办法,养老吸劳费用超过土地成本的三分之一(伏玉林,2004)[18]。由于土地价格上涨迅速,上海许多制造企业将其工厂迁出上海,而国外投资者也更愿意将其制造基地设立在上海周边的一些地区,主要是长三角地区。2009年上海浦东川沙工业区工业地块地价一般在2,500元/平方米,同期,苏州工业园区一般在1,500元/平方米左右①。
2. 劳动力成本
用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人均教育支出费用衡量劳动力成本。两个指标其值越高,说明劳动力成本越高,要素成本越高。
表2可以看出,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和人均教育支出均呈现递增趋势,平均工资指数以年均15.9%的速度增长,人均教育支出指数增长更快,年均增长速度为27.7%。经济高速增长、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优化、城市化直接导致上海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人均教育支出费用增长更快,除与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的人均收入提高有关外,还与上海“科教兴市”战略的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有关,新兴产业发展增加对高素质劳动力需求,传统产业向外转移产生劳动力再就业需求,都迫使增加职业培训费用和普通教育支出。同时,人均教育支出增长越迅速,也说明上海地区的教育水平越高,企业会更便利、更经济地获取所需人力资源和产业升级的技术基础。
(二)交易成本
1. 政府运作效率
以机关人员占就业人口比重、行政性收费收入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比重、地方税收总额占GDP比重衡量政府运作效率。一般地,机关人员占就业人口比重越高,政府运作效率越低,企业交易成本越高。行政性收费收入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比重、地方税收总额占GDP比重越高,企业负担越重,交易成本越高。
表3数据看出,2001年机关人员占就业人口比重有所增长后,2002年起逐年降低,并于2005年起趋于稳定。这与2001年对奉贤、南汇撤县建区,上海市严格执行中央厉行节约的规定,进行机构精简,提高行政效能,减少政府支出,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有关。上海行政性收费收入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比重2002年上涨明显,与财政部、国家计委出台《关于发布2001年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的通知》有关,随着降低行政性收费的呼声高涨,2004年该比重下降,2005年起有一定波动,上海该比重在全国以及长三角地区来说都是偏低的,说明上海行政性收费收入比较合理、透明,基本不存在乱收费现象。上海地方税收总额占GDP比重逐年升高,从2000年到2009年比重增加6.8%,企业税负较重,尤其2007年以后地方税收总额占GDP比重增加明显,这主要与2007年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有关,也与上海内外资企业结构比重有关。
2. 市场化程度
以非农业人口比重、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GDP比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衡量市场化程度。非农业人口比重反映城市化程度,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GDP比重反映市场开放度,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反映市场服务能力,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反映市场规模与质量。四个指标其值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交易成本越小。
表4数据显示,上海非农业人口比重逐年提高,其与奉贤、南汇撤县建区,浦东新区与南汇区合并成立“大浦东”,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召开密切有关。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GDP比重反映上海近年吸引外资情况,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GDP比重2001年较2000年上升4.9%以后,开始下降,至2009年共减少7.7%,该比重下降说明随着上海经济发展,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已经一定程度阻碍外资进入。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反映劳动力结构,从2000年到2009年该比重基本逐年增加,它与上海市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有关。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反映市场规模与质量,该指标逐年增长,2000年到2009年增长183.4%,上海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增长潜力,注定它始终是国内外资本追逐的热土。
3. 基础设施
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公路通车里程占总面积比重反应基础设施情况。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比重反映市场发展速度及潜力,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反映上海产业结构水平,公路通车里程占总面积比重反映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情况。三个指标其值越高,企业交易成本越低。
表5显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比重除2001年和2004年该比重有小幅提高外,其他时间段小幅下降,说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幅小于上海GDP增幅,固定资产投资对上海经济增长起加速度作用。也可以用“每百元增加值占用的固定资产”来说明,工业“每百元增加值占用的固定资产”由2001年276.88元降为2008年228.59元,第三产业“每百元增加值占用的固定资产”由2001年215.16元降为2008年185.26元②。工业和第三产业每百元增加值占用的固定资产不仅降低,实现固定资产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且第三产业固定资产使用效率高于工业。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除2003年、2004年两年该比值低于50%以外,其余年限均高于50%,并于2004年起开始提升,上海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已超过第二产业,上海产业结构正不断优化。上海自2000年以来公路通车里程占总面积比重逐年递增,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情况逐渐改善。上海除加强公路建设外,市内轨道交通、城际高铁、机场、海运大桥建设等也成绩卓著,为上海打造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中心城市地位打下坚实基础。
4. 研发能力
用每万人口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每万人专利授权量、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衡量区域研发能力。每万人口拥有专业技术人员反映研发人才密度与技术人才资源可获得性,每万人专利授权量反映创新产出水平,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反映研发投入强度,体现科技投入与发展潜力。三个指标其值越高,企业交易成本越低。
由表6看出,每万人口拥有专业技术人员该指标2002年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2009年较2000年下降20.4%,其与上海1999年实行人才强市战略,后来,上海人才引进的户口政策逐渐趋严有关。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逐年上升,年均增长率为9%。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一个国家发展初期R&D强度一般在0.5%~0.7%左右,国际公认的经济起飞阶段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1.5%,上海从2000年起就已经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每万人专利授权量基本呈现上升趋势,上海这项指标在全国来说也是偏高的,而且,在“每万人口拥有专业技术人员”2002年后基本逐年下降、“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年均增长率为9%的情况下,“每万人专利授权量”年均增长70%,说明上海科技产出效率相当高。总体上,上海人才资源、研发投入和科技成果三个分项指标发展较为均衡。
(三)商务成本结构性变动趋势分析
商务成本结构性变动趋势显示,随着经济发展,上海要素成本逐年上涨,同时,代表交易成本降低的指标数超过代表交易成本上升的指标数,总体上交易成本呈现降低趋势,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考量商务成本需综合考虑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变化,不能单纯用房价上涨、工资上涨来简单判断商务成本上升,也不能单纯用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来简单判断商务成本降低。从动态角度看,商务成本变动取决于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变化,具体表现为:①要素成本的上升与交易成本的下降相等时,商务成本不变;②要素成本的上升小于交易成本的下降时,商务成本降低;③要素成本的上升大于交易成本的下降时,商务成本上升。一般而言,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随着经济发展,商务成本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三、商务成本构成趋势对产业转移的作用机理
(一)要素成本变动趋势对产业转移的作用
机理
要素成本由商业设施与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等构成,前述分析已知上海要素成本呈现逐年上涨趋势。考虑资本逐利性,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会追求收益最大化,对于要素成本占据运行成本份额较大的企业来说,会进行企业空间转移。由于商务成本具有“属地相关”性,企业会迁移到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继续生产运营。因此,要素成本上升会促使对于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占据产业运作成本更大比重的制造业尤其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比第三产业更易发生产业转移。对于处于产业生命周期成熟和衰退阶段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来说,其市场已经成熟稳定,进入价格竞争为主的阶段,技术创新以“干中学”式创新为主(Gort和Klepper,1982)[19],要素成本上升也可能会促使其产业转移。
(二)交易成本变动趋势对产业转移的作用
机理
交易成本主要由政府运作效率、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和研发能力四项指标衡量,前述分析已知上海交易成本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与处于产业生命周期成熟和衰退阶段的产业相比,逐渐下降的交易成本、逐渐改善的商务软环境对处于产业生命周期创新和成长阶段的产业来说更具吸引力。Agarwal和Gott(1996)研究产业生命周期的阶段性对厂商进入和退出的综合影响,发现危险率与厂商“年龄”成反比[20]。Klepper和Graddy(1990)认为在产业发展早期,对产业进入者创新要求高,使得具有较大创新效率的最早进入者能成长为最大厂商[21]。王传英(2006)强调社会经济网络优势是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22]。王缉慈、王可(1999)特别关注企业与区域创新环境的关系,认为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中小企业,只有扎根在本地才能形成良好的区域创新系统,政府应该营造有利于区域创新的环境[23]。卢福财、何炜(2005)认为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较其他外部关系更微妙,且由于历史原因政府对企业的隐性影响极大,这些在西方社会中处于弱势的交易安排在中国看来潜在力量相当大。转轨过程中政府具有的资源调配权有降低趋势,对经济活动的规制权不断增强,它会使各类型企业有更公平的竞争环境[24]。邹国庆等(2010)认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正式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及与社会关系的协同]化是进一步推进企业大规模技术创新的决定因素[25]。于是,由于处于产业生命周期创新和成长阶段的产业比成熟和衰退阶段的产业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和技术创新风险(张会恒,2004)[26],尤其需要政府运作效率更快捷、市场机制健全完善、基础设施完善、研发能力强而先进的商务环境。因而,处于产业生命周期创新和成长阶段的新兴产业如高科技产业趋于向交易成本降低的区域转移和集聚。
(三)商务成本上升趋势对产业转移的作用
机理
要素成本的上升大于交易成本的下降时,区域商务成本上升。随着经济日益全球化,产业转移方式已由基于产品间分工的产业转移模式]变为既包含产品间分工又包含产品内分工的产业转移模式(张少军、李东方,2009)[27],企业分割和整合价值链,将附加值低的产品生产工序转移到要素成本较低的区域,将产品研发、设计和营销等附加值高的工序转移到交易成本较低、软环境优越的区域,通过双重途径以降低成本来谋求收益最大化。商务成本这种变化趋势即要素成本的上升大于交易成本的下降会加速产业转移方式由基于产品间分工的产业转移模式向基于产品内分工的产业转移模式的转变。
企业将产品研发、设计和营销等附加值高的工序转移到交易成本较低、软环境优越的区域促使该区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发展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张三峰、杨德才,2009)[28]。江静等(2007)认为,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生产性服务业所包含的知识资本、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大幅度提高制造业的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张促进制造业的整体效率提高[29]。Cusumano、Kahl和Suarez(2006)考察服务贡献在企业和产业]化中的作用,发现随着厂商成立时间和年份的增加,服务在企业和产业]化中的贡献越来越大,并最终取代产品占据第一份额[30]。于是,要素成本上升与交易成本下降同时作用,不同产业、产业价值链不同环节沿时间向量在同一空间进行转移和集聚,逐渐引起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
四、上海产业转移的趋势与特征
(一)上海产业转移的测量
1. 测量方法
本文根据区位商(Location Quotient,LQ)概念,使用黄钟仪等(2009)[31]提出的产业静态区域聚集指数和产业动态区域聚集指数测量江、浙、沪产业转移状况。产业静态区域集聚指数反映某一产业在某地区的现有生产能力和产值在全国(省)所占比重,是衡量目前产业生产分布的存量指标。产业动态区域集聚指数反映某一产业在一定时间段内向某地区的集聚速度,体现产业生产的区域转移方向和速度。
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对制造业22个行业(与中国统计年鉴分类一致)选取2001年与2009年的产值(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选取2003年与2009年数据),第三产业14个行业(与中国统计年鉴分类一致)选取2005年与2009年的产值以及相应的上海总产值、国内生产总值进行计算。第三产业中的“其他”包括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7个行业。数据来自2002、2004、2006和2010年上海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处理,均采用当年价格,以剔除价格水平变化因素导致的偏差。
本文对计算结果的处理方式是:①产业动态区域集聚指数大于1,无论产业静态区域集聚指数是否大于1,即无论该产业是否专业化,均归为产业集聚;2009年产业静态区域集聚指数大于1,则归为专业化,否则归为非专业化。②产业动态区域集聚指数小于1,该产业视为经历产业转移,2001年时制造业产业静态区域集聚指数/2005年第三产业产业静态区域集聚指数小于1的产业不在下图1、2中显示出来,2009年产业静态区域集聚指数大于1,则归为专业化,否则归为非专业化。③本文计算结果显示所有的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在全国范围内都在扩张。④上海只有化学纤维制造业其动态区域集聚指数小于零,发生绝对产业转移;其他产业动态区域集聚指数均大于零,同时,产业动态区域集聚指数小于1时,则该产业视为经历产业相对转移。
(二)上海产业转移的趋势
下图1、图2分别给出上海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产业转移趋势图。
图1、图2中,同时产业集聚又专业化的说明该行业向上海集聚并实现专业化;同时产业集聚又非专业化的说明该行业向上海集聚但未实现专业化;同时产业转移又专业化的说明该行业由上海向外转移但仍具专业化优势;同时产业转移又非专业化的说明该行业由上海向外转移并失去专业化优势。
(三)上海产业转移的特征
1. 制造业发生产业转移的行业数量比重大于第三产业,制造业发生产业集聚的行业数量比重小于第三产业
制造业发生产业转移的行业数量较大,22个行业有20个行业(包括6个2001年未具备专业化优势的行业)发生产业转移,第三产业14个行业有5个(包括1个2001年未具备专业化优势的行业)发生产业转移,比重小于制造业。制造业发生产业集聚的行业数量很少,22个行业只有2个行业发生产业集聚,第三产业14个行业有9个(“其他”包括7个行业)发生产业集聚,比重超过制造业。
2. 制造业产业转移程度高于第三产业,制造业产业集聚程度低于第三产业
图1显示上海制造业有14个行业发生对外产业转移,其中13个相对产业转移,这13个行业中10个仍具有专业化优势,3个行业不再专业化,化学纤维制造业则发生绝对转移,2009年产值较2001年有明显减少。图2显示第三产业有4个行业相对转移,并仍具有专业化优势。与制造业相比,第三产业部分行业虽然发生相对产业转移,但仍具有专业化优势,制造业则因行业不同,发生不同程度转移,有些仍具有专业化优势,有些不再专业化,甚至发生总量萎缩。图1中2个制造行业发生产业集聚并专业化,图2中发生产业集聚的9个行业(“其他”包括7个行业)均实现专业化。
3. 发生产业转移的大多是处于产业生命周期成熟阶段的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发生产业集聚的主要是处于产业生命周期创新和成长阶段的行业
图1显示的发生产业转移的制造业各行业,从产业生命周期阶段来看,14个行业有8个处于成熟阶段,4个处于创新阶段和2个成长阶段。处于创新阶段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这3个行业,其余处于创新或成长阶段的3个行业均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海制造业有2个行业发生产业集聚,并具有专业化优势,分别为处于创新阶段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成长阶段的资源密集型产业③。
图2显示的发生产业转移的第三产业各行业,既有传统服务业也有现代服务业。而发生产业集聚的第三产业各行业,都是现代服务业。
以上实证结果初步表明:随着经济发展,上海要素成本上升、交易成本下降,商务成本总体上升的背景下,制造业发生产业转移的行业数量比重大于第三产业、制造业发生产业集聚的行业数量比重小于第三产业、制造业产业转移程度高于第三产业、制造业产业集聚程度低于第三产业、发生产业转移的大多是处于产业生命周期成熟阶段的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发生产业集聚的主要是处于产业生命周期创新和成长阶段的行业。对于处于创新阶段的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来说发生对外产业转移,原因可能是随着要素成本的迅速上升,而处于创新阶段时行业利润又很低(张会恒,2004)[26]或者缺乏产业集群支撑(何奕、童牧,2008)[32]等原因,所以发生对外产业转移。另外,上海产业结构也有所优化,2001年上海产业结构是1.5∶46.1∶52.4,2008年是0.8∶45.5:53.7,与2001年相比,2008年第一产业下降0.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下降0.6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上升1.3个百分点。图2显示发生产业集聚的第三产业各行业都是现代服务业,也为产业转移方式转变创造条件。
五、结论与研究方向
上海商务成本结构性变动趋势显示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一般而言,随着经济发展,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交易成本逐步下降,而商务成本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商务成本结构性变动以及商务成本总体上升的趋势会加速产业转移方式由基于产品间分工的产业转移模式向既包含产品间分工又包含产品内分工的产业转移模式的转变,并对产业转移产生影响,大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成熟阶段的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发生对外产业转移,处于产业生命周期创新和成长阶段的新兴行业则向该区域产业集聚,不同产业、产业价值链不同环节沿时间向量在同一空间转移和集聚,最终会促使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
安礼伟等(2004)对长三角5城市商务成本进行比较研究,发现5城市间存在商务成本总体差异和内部结构差异。未来则需要根据“整体性、主导性、可靠性、层次性和动态性”原则,对商务成本构成及指标赋予权重来综合考量,研究区域商务成本如华东地区或者东、中、西部商务成本总体差异和内部结构差异情况,并探索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进一步验证本文结论的可普及性。如果区域内部各地区商务成本存在总体和内部结构的差异,这种差异又对产业转移路径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区域内部产业转移方向和路径是否存在上述规律,也需要研究验证。
商务成本对于企业来说,是无法控制的外生性成本,考虑其商务依赖、属地相关的特性,企业只能通过对投资地和商务活动方式的选择来最小化商务成本。然而,受产业属性、企业生命周期、企业规模、企业家精神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企业对商务成本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不同企业对商务成本以及各构成要素的评价将会不一样,因此,未来有待研究处于产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产业,具体到特定的行业,对企业采用问卷和访谈等研究方法,探讨究竟是否、如何受商务成本结构性变动和商务成本上升的影响,受影响程度有多大,产业转移方式有无多样化,是否进行了价值链的分割和整合等。
① http://www.landlist.cn/2009-02-24/2414761.htm。
② 上海统计年鉴2009、2002。
③ 关于行业属性及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判断依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的“关于上海产业梯度转移的研究”,http://www.fzzx.sh.gov.cn/listAwardg.aspx?CID=1406。
[1] 傅钧文,金 芳,屠启宇. 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商务成本比较研究[J]. 社会科学,2003(5):14-18.
[2] 傅永军,盛靖芝. 上海商务成本问题探究[J]. 上海经济,2003(6):35-37.
[3] 安礼伟,李 锋,赵曙东. 长三角5城市商务成本比较研究[J]. 管理世界,2004(8):28-36.
[4] 陈 珂,陈 炜. 商务成本的构成及其评价问题的研究[J]. 价值工程,2005(5):91-93.
[5] 潘 飞,马 杰.商务成本因子分析[J]. 财会通讯,2005(12):24-27.
[6] 陈建军,郑 瑶.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商务成本比较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2004(12):34-41.
[7] 朱家良. 商务成本与城市空间结构[J].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4,5(3):21-23.
[8] 赖涪林,吴方卫. 日本东京圈的商务成本[J]. 现代日本经济,2005(2):46-51.
[9] 江 静,刘志彪. 商务成本:长三角产业分布新格局的决定因素考察[J]. 上海经济研究,2006(11):87-96.
[10] 周扬波,李文静. 长三角商务成本]变与产业分布格局调整[J].特区经济,2009(5):43-45.
[11] 吴炎太. 商务成本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以广州市为例[J].改革与战略,2008(9):130-132.
[12] 陈建军,崔春梅. 商务成本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我国三大地区间的经验证明[J]. 上海经济研究,2010(10):49-57,65.
[13] 冯根福,刘志勇,蒋文定.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工业产业转移的趋势、特征及形成原因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2010,32(2):1-
10,124.
[14] 王辉堂,王 琦. 产业转移理论述评及其发展趋向[J]. 经济问题探索,2008(1):45-48.
[15] 原小能. 国际产业转移规律和趋势分析[J]. 上海经济研究,2004(2):29-33.
[16] Dunning J. and McQueen M.,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Hotel Industry[J]. Annals of Tourism Reaearch,1982,9(1):69-90.
[17] Fujita,M. and Hu,Dapeng.Regional Disparity in China 1985-1994: 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J].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01,35(1):3-37.
[18] 伏玉林. 上海商务成本分析与调控对策[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49-54.
[19] Gort M.,Klepper S.,Time paths in the diffusion of product innovation[J]. The Economic Journal,1982(92):630-653.
[20] Agarwal R., Gort M.,The Evolution of Markets and Entry, Exit and Survival of Firm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6,78(3):489-498.
[21] Klepper S.,Graddy E.,The Evolution of New Industries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Market Structure[J].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990,21(1):27-44.
[22] 王传英. 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是什么[J]. 经济纵横,
2006(1):49-52.
[23] 王缉慈,王 可. 区域创新环境和企业根植性——兼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开发区的发展[J].地理研究,1999,18(4):357-362.
[24] 卢福财,何 炜. 论中国传统关系网络对外部网络的影响[J]. 当代财经,2005(2):71-74.
[25] 邹国庆,郑剑英,高向飞. 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嵌入与引致机制分析:一个制度视角[J]. 工业技术经济,2010(8):45-49.
[26] 张会恒. 论产业生命周期理论[J]. 财贸研究,2004(6):7-11.
[27] 张少军,李东方. 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商务成本与学习曲线的视角[J]. 经济评论,2009(2):65-72.
[28] 张三峰,杨德才. 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研
究——基于我国中部地区的分析[J]. 经济管理,2009(8):27-32.
[29] 江 静,刘志彪,于明超. 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效率提升: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世界经济,2007(8):52-62.
[30] Cusumano M.,Kahl S.,Suarez F.,Product,Process and Service:A New Industry Lifecycle Model[M]. MIT Working Paper,2006:228.
[31] 黄钟仪,吴良亚,马 斌. 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产业选择研究——以重庆为例[J]. 科技管理研究,2009(8):182.
[32] 何 奕,童 牧. 产业转移与产业集聚的动态与路径选择——基于长三角第二、三类制造业的研究[J]. 2008(7):50-56,79.
The Influence of the Business Cost Structure Trend
in Shanghai on Industrial Transfer
Su Yunxia,Sun Minggui
(Glorious Su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Donghua University,Shanghai 200051,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n industrial transfer by the trend of structural changes in business cost in Shanghai. The trend of structural changes in business cost in Shanghai shows that factor cost is increasing and transaction cost is decreasing. Generall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rings about the rising of business cost. The structural change in business cost and its overall upward trend accelerates the conversion from industrial transfer mode based on the division among products to industrial transfer mode based on the division in products, and influences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Most industries in the mature stage of industry life cycle and labor-intensive are likely to industries transfers outwards, while emerging industries in the innovation or growth stage of industry life cycle tend to assemble. Various industries and various parts of industry value chain both transfer and assemble along the time vector in the same area and lead to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 words:business cost;factor cost;transaction cost;industrial transfer
(责任编辑:张改兰)